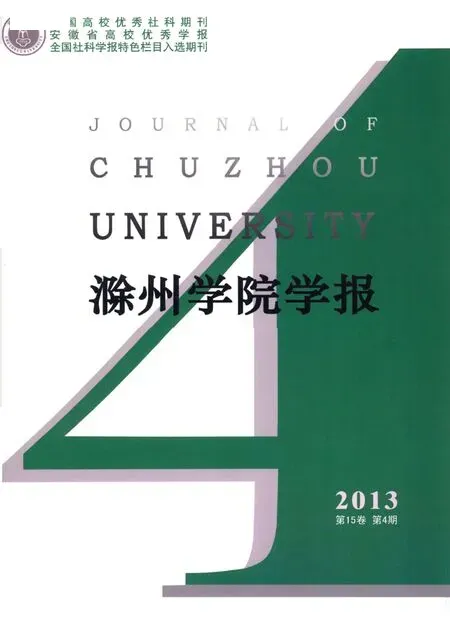内秀外敛:评合肥大剧院建筑设计
2013-05-14沈莹莹
沈莹莹
合肥大剧院作为合肥市文化艺术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设计建设是全面提升合肥市的文化品位,满足对外文化交流的需要,并结合政务文化新区的总体规划而提出的。剧院于2003年初开始征集方案,经过4年时间,最终上海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项秉仁建筑师事务所的设计方案中标。
一、外部环境设计——理性有余,张力不足
合肥大剧院位于政务区天鹅湖畔,场地设计阶段建筑师要解决的主要目标是既要试图营造一个优美、高雅反映时代特征的造型来衬托位于中心轴线远处的市政府大楼以及未来的艺术馆(图1),又要使其成为符合天鹅湖自然形态的背景建筑。通过对基地环境的理性分析,设计师采取的策略是在总体布局上将剧院与市政府办公楼、综合艺术馆(规划中)构成三角形的稳定对位关系,同时以天鹅湖水面为原型抽象出“波浪”作为造型意向(图2)。

图1 合肥大剧院与政府办公楼、艺术馆轴线关系

图2 合肥大剧院鸟瞰
临水虽然为建筑增添了柔和与诗意的背景,但水的自由灵动也对建筑的风貌同样有所要求。或如悉尼歌剧院(图3)扬帆起航,或如密尔沃基美术馆(图4)欲振翅飞翔,水边的建筑总是充满张力,正如水面一动一静间的临界状态。而从实际建成效果来看,由于合肥大剧院主轮廓呈下降的弧形,在视觉上弱化了形体的张力;加之建筑高度不高,弧度平缓,整体造型略显扁平。这些因素使得“波浪”这一造型意向的灵动大打折扣。此外,大剧院黯淡的主色调、过实的表面都掩盖了剧院建筑所应具备的优雅气质,在一个以建筑环境而非自然环境为主要背景的区域中,合肥大剧院就显得“消隐”过度。

图3 悉尼歌剧院

图4 密尔沃基美术馆
“建筑不是孤立的个体,如浦东陆家嘴,有些外国人说它是‘建筑动物园’,就是说每栋建筑都是一个动物,都不一样而且互相独立。”[1]从这段话不难看出建筑师对城市建筑的整体性的强调。建筑师强烈的环境意识和突出的逻辑思维能力让合肥大剧院能够实现与周边环境的和谐统一,然而让建筑成为环境的主角却需要超越理性分析的创造力。合肥大剧院的造型缺乏灵动与张力,但这一问题并非个例。也许问题的症结不是建筑师的能力有限,而是由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强大影响力。从人们的生活方式到建筑的材料与工艺都可以通过学习引进实现快速现代化,但是古代建筑天人合一,尊崇自然,建筑从属于自然的这种环境意识的改变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实现的。传统的思维模式让设计者与使用者都惯性地采用了保守的造型。正因如此,作为文化建筑典型代表的剧院建筑更应该打破这种局面,为传播先进理念、提供公众的审美能力树立旗帜。
二、内部空间——高雅艺术的亲和力
与较为简单的外形对比鲜明的是大剧院精彩的内部空间设计,尤其是公共前厅的空间设计。合肥大剧院的入口如贝壳微微翘起的边缘,观演前厅正是利用了观演厅与入口间的高差形成的三角形空间,在主次入口间高度较低处设置了公共休闲区(图5),而层高较高处则设置了跌落式的三层挑台,不仅从视觉上消解了歌剧厅较大的体量,也从心理上起到了很好的缓冲作用。流线型是大剧院前厅的另一大特色(图6)。不同于外部造型的拘谨,前厅的内部设计大胆夸张,最耀眼的莫过于蜿蜒自由的挑台,如同流淌的音符,与旋转楼梯一起,仿佛诉说着艺术的灵动与优雅;直跑楼梯、景观电梯种种元素统一在弧形天顶之下,横竖对比,曲直交错,充满视觉趣味的共享空间与大剧院里上演的一出出高雅艺术相得益彰。亲和力则来源于色调与材质上的精彩处理。木色的铝扣板铺制的弧形天顶、乳白色压条的平台栏板、音乐厅外墙的细木装修,处处显示着乐器的质感。金属材料与玻璃的运用不仅增添了光影变幻,也体现了大剧院的高贵现代;木材与暖色调的配合则展示出大剧院的温暖典雅,这种调和传递着大剧院高雅中带着一份亲切。

图5 合肥大剧院休息区

图6 合肥大剧院前厅
剧院自发源时起就是人们重要的社交场所之一,现代剧院作为城市重要的公共文化建筑,理应承担城市客厅的职能,让人们在其中充分吸收、交流文化和享受文化。作为城市公共文化建筑的杭州市图书馆新馆在国内首开先河,打造了具有浓郁氛围的家居式阅读环境,不仅吸引了大批读者,大大提高了图书馆的使用率,更是提升了市民的音乐审美与文化生活品质,从而促进了城市文化产业的发展。此外,杭州市图书馆新馆还配备了具有国际一流水准的音乐图书馆(图7),不仅增添了图书馆的特色与亮点,更是打破了图书馆在人们心中的传统概念。这些现象都反应出“以人为本”不再只是口号,而是化作设计理念在文化建筑设计中得到的实践。如果说这一理念在合肥大剧院建筑设计中的体现更多是视觉上和心理上的,那么杭州图书馆则是把这一理念深入到了功能上,颠覆传统,综合发挥公共文化建筑对市民文化生活的积极影响。以合肥大剧院优越的硬件设施,如果也能够植入人性化的服务体系,软硬结合,将更能展现其亲民的特色,丰富合肥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图7 杭州图书馆音乐图书
三、文化价值——拒绝符号,感受精神传承
除了关注建筑的环境价值、实用价值、社会价值,艺术与历史文化价值也是建筑批评价值论的重要组成。建筑作为一门艺术,总会折射出出建筑师的价值观以及时代的思潮。在 “欧陆风”“复古风”泛滥的时代,简单的生搬硬套与符号化设计带来的“千城一面”问题已经开始让人们意识到文化断层的危机,建筑的文化价值也开始引发人们的关注,越来越多的建筑师开始探索地域文化精神在建筑上的表现与传承。
初看合肥大剧院,现代化的材质与工艺、流线型的造型、加之所处的政务新区的一派新城风貌,似乎很难让人感受到地域文化精神的表达。但仔细品味,大剧院这种沿大地延伸的水平造型正是中国人美学的反应,王澍曾说过:“中国人的美学不是向上走的,是沿着大地水平向外扩展的”[2]。正如传统诗歌所展现的“悠远”,中国人追求的是无限向远方飘散的意境。古代的建筑也是如此,故宫并不高,在大地之上,天空之下,简练地用台基与屋顶划分出了人生存的空间。大剧院主入口与东南观景台处微微翘起的屋面缓和含蓄,颇有故宫屋顶的“反宇”的意味。夕阳西下之时,更容易感受到合肥大剧院散发着古建筑的平和宁静的意境。这也许只是建筑师无意识下的巧合,又或许是建筑师对中国文化精神传承的一种理解,虽然传达的力度似乎还很弱小,但是可以看出建筑师拒绝符号化表达,追求建筑“精神”的传承的鲜明立场。之所以没有成为引人注目的地标建筑,一方面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中落后的建筑环境意识,另一方面也是缘于合肥本土文化特色的缺失,以及缺少对地域文化的深度挖掘,这些因素制约了合肥大剧院在地域文化特色上的表现。
相对而言,宁波历史博物馆的传承则更为主动,也更加深刻。设计师从宋代山水画汲取灵感,结合亲身感受,用抽象形体构成的建筑语言表达“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传统哲学意境。除此之外,设计师极力寻求当地传统文化的保存与延续,让建筑扎根于他所处的环境中,焕发出更强大的生命力。在就地取材与传统工艺的基础上,融入改良后的现代材料与建造手法,让整座建筑不仅得宋代建筑的神韵,又兼有现代气息,与周边的新建现代高层建筑形成对话,成为鄞州区乃至宁波的新地标建筑。
四、结束语
剧院作为文化建筑的代表,不仅是城市精神生活的载体,更是城市内涵的象征。从建筑外部环境设计与建筑造型处理、建筑内部空间设计以及建筑在城市文化构建上的价值的角度探讨了合肥大剧院的建筑设计。大剧院建筑与城市环境有机融合,并且能够以亲民的姿态为合肥市民展现着高雅艺术的魅力,这是值得学习与倡导的设计观与价值观。将以人为本从造型拓展到功能是优化这一设计理念的方式之一。针对造型保守与地域特色缺失等问题,则必须要打破落后的环境意识,让建筑与周边环境产生化学反应;同时,深度挖掘地域特色,继承传统文化的精神。只有在这两点的共同作用下才能够产生统领环境,具有场所精神的地标性文化建筑。
[1] 王方戟.观察与思考——访项秉仁建筑师[J].时代建筑,2001(1).
[2] 李翔宁,张晓春.王澍访谈[J].时代建筑,2012(4).
[3] 保罗·安德鲁.国家大剧院[M].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7.
[4] 项秉仁,程 翌.内在理性和外在逻辑——合肥大剧院建筑和室内设计[J].时代建筑,2010(5).
[5] 郑时龄.建筑批评学[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
[6] 赵广超.不只中国木建筑[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