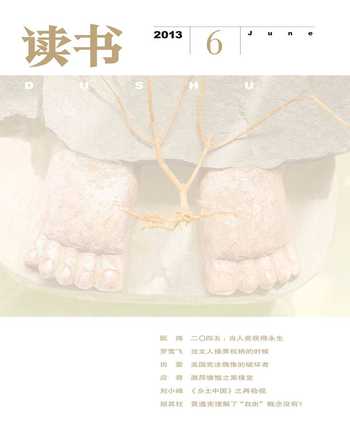历史法学的政治成熟
2013-04-29翟志勇
萨维尼和德国历史法学派专注于私法规则的提炼和体系的建构,将法学研究的历史性和哲学性统一在科学的方法论之中,试图以精致的概念-規则体系抵制社会与政治的不确定性,结果将公法学研究排除在历史法学研究的科学性之外,并最终随着德国民法典的颁行而迅速衰落。德国历史法学的缺失之处,恰恰是中国历史法学的着力之点,中国历史法学的时代使命,主要不在于法学研究本身的科学化和私法概念—规则体系的建构,而在于国家的伦理秩序和政法秩序的重建。
作为私法学的德国历史法学
虽然萨维尼直到晚年才开始使用“民族精神”一词,但法律乃民族精神的展现,无疑是萨维尼和历史法学派最具标志性的论断,不过这个论断需要具体地理解,因为在萨维尼看来,法律具有双重生命:首先,法律是社会存在整体中的一部分,并将始终为其一部分;其次,法律乃是掌握于法学家之手的独立的知识分支。随着文明的进步,法律以前存在于社会意识之中,现在则被交给了法学家,法学家因而在此领域代表着社会。职是之故,法律需通过法学家之手,才能展现民族精神,而所谓的民族精神,亦非那个自生自发的神秘莫测之物,而是经由法学家科学劳作之后呈现出来的那套精致的概念—规则体系。
萨维尼将法律与民族的一般存在的这种联系称为“政治因素”,而将法律独特的科学性的存在称为“技术因素”。这一区分对于理解萨维尼和历史法学派至关重要。法律的政治因素根植于民族的社会生活,为法律提供质料;而法律的技术因素则牢牢掌握在法学家手中,为法律提供形式。对于萨维尼来说,质料服务于形式,政治因素从属于技术因素。在这个区分中,立法者归属于政治因素,而且是政治因素中较为专断的因素。萨维尼与蒂堡的论战,实际上是争夺法律创制权的论战,是将法律交给专断的立法者,还是交给科学的法学家。
萨维尼坦言,在渴望拥有一个坚实的法律制度和寻求国族的统一与团结上,他与蒂堡的目的是一致的,他反对法典编纂,主要是反对将法律的创制权交到立法者手中,以抵御任意专断和伪善对法律的伤害。说来难以置信,抵制的手段竟然是一套基本的法律公理和精致的概念—规则体系,而这又蕴藏在历史地生成的法律之中,特别是曾经高度发达的罗马法之中,需要法学家爬梳、整理、发掘和提炼。因此,在萨维尼看来,历史法学研究的目标,在于追溯每一既定的制度直至其源头,从而发现一个根本的原理原则,借此依然具有生命力的原理原则,或可将那些毫无生命、仅仅属于历史的部分剥离开来。进而从中推导出存在于一切法律概念和规则间的内在联系及其确切的亲和程度,也就是建立具有普遍联系性的规范体系。萨维尼坚信,这些公理、概念和规则并非任意妄断之物,实乃真实的存在,法学家的职责就是在法律公理之上发掘出这套精密的概念—规则体系。
萨维尼和他所开创的德国历史法学主要专注于私法规则的提炼和私法体系的建构,虽然他自己坦言深受孟德斯鸠的影响,但对于同样发达的罗马公法,基本上没有涉及。这样一种以私法为核心的历史法学研究,实际上是建立在国家与社会二分的思维结构之上的,在当时具有法政治学的贡献,它使十九世纪市民社会的解放成为可能,因为它用其形式的手段保障了法治国,并因此保障了这一社会反对旧的专制国家的自由空间。当然,这一使命,当在争得了市民的自由之后,提出了市民法律秩序的社会正义问题之时,就终结了。
萨维尼之后,历史法学迅速实证化和形式化,并最终与立法者联手,参与了德国民法典的创制。德国公法秩序的建构,要到魏玛时期才真正兴盛起来,围绕魏玛共和制和魏玛宪法而展开的国家学和公法学大争论,一波三折,直到“二战”之后方才砥定成型,建立了现代国家的政法制度,完成德国从传统到现代的整个法律秩序的重构。因此,德国历史法学派留给后人的一个教训就是它对公法问题的漠视,缺乏政治意识和政治成熟,认为形式主义的技术因素能够驯服政治因素。事后看来,无论多么精致科学的市民社会私法规范体系,都不可能完全独立于政法体制而发挥其应有价值,更不可能以此来抵御政治的专断。
民族精神与历史的意义
学者往往习惯于将萨维尼和历史法学派的精神源头归属于德国浪漫派,虽然这与他的罗马法研究看似格格不入,但正如维亚克尔所言,把萨维尼归属于浪漫派完全失去其意义,毋宁是,必须从其自身出发,把他理解成一个在那场德国精神的普遍运动中,独立的、具有万有引力的中心。也就是说,不能简单地将萨维尼归属于文化上的浪漫派,如果一定要在这场精神运动中定义萨维尼,则萨维尼开创了浪漫派中独特的一脉,这体现在他对民族精神的独特理解上。事实上,萨维尼的著作中并没有直接阐述何为民族精神,对具有类似含义的民族信念、民族意识也是一笔带过,但从他对法律的历史渊源、双重生命以及法学研究的科学使命的论述中,可以合理地推断,萨维尼所谓的民族精神,主要不是神秘莫测、无可名状的文化和历史的生命轨迹,而是在民族历史文化中孕育成长的且被法学家科学的劳作所提炼出来的那套法律公理和概念—规则体系,以及由此形成的具有普遍联系性的规范体系,亦如法律具有双重生命一样,民族精神也具有双重生命,萨维尼念兹在兹的民族精神,不是那种原生态的民族精神,而是以具有普遍联系性的规范体系呈现出来的民族精神,如此才能够解释萨维尼的民族精神说和罗马法研究之间看似格实则统一的关系。法律乃是民族精神的展现,但民族精神经由法律展现出来的形象是法律化的民族精神,更确切地说是私法化的民族精神。
萨维尼之所以重视历史,因为在他看来,任何时代都不是独立地和任意地创造出它的世界,而是在与整个过往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中做到这一点的。既没有绝对的终结,也不会有绝对的开始,一切都是在历史的联系中存在和发展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过往的法律是至高无上之物,更不意味着历史对当下和未来的永恒主宰,历史的意义毋宁是提供当下与过往的有机关联,在这种相互关联中,我们才能拨开外在现象,把握其内在本质。历史是真正值得敬重的导师,回溯历史,是为了认识当下,从而面向未来。
就此而言,历史对于萨维尼和历史法学派同样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历史只是一份有待处理的素材,是法学的科学研究不得不去处理的最佳材料;另一方面,历史本真地存在着,蕴含着一套有待发掘的充满必然性的规范体系。因此无论是德意志的习惯法,还是古往今来的罗马法,作为历史素材,它们或许大异其趣,但作为历史之本真,它们实则内在一致,因为历史必然展现出人类的某种普遍性的结构。因此,历史法学的科学化劳作旨在赋予法律素材一种精神—逻辑的形式。这一学术目标必须是一个“真实的体系”,即法律规范的内在关联,以代替描述“外在体系”的纯粹的“素材堆积”。对于萨维尼的法学方法论而言,这一“精神—逻辑的形式”超越所有外在形式差异,秉具必然性和普遍性。
萨维尼这种独特的民族精神和历史观,与前述作为私法学的历史法学是一脉相承的,在经验层面上,是民族精神和历史造就了法律,但在逻辑层面上,恰恰相反,是法学规定了民族精神和历史。但在这种关系结构中,仍然只是私法的视角,历史地生成和展现的伦理—政法秩序并不在他的民族精神内涵之中,或者说,只能以一种私法的概念—规则体系来间接地展现。萨维尼和历史法学派放弃对公法学的研究,实际上也就放弃了对伦理—政法秩序的历史解释,放弃了民族精神所展现的公法意象,法学视角下的理性重述必然异于文化视角下的浪漫感悟,一种理性的伦理—政法秩序无法在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民族精神中得以展现,也无法在精致的概念—规则体系中展现。这里所关涉的依然是历史法学的政治意识和政治成熟问题。
现时代中国的法学研究,有些类似于德国历史法学的时代处境,我们今天仍然面临着两份不同的历史素材:一份是无法割舍的中国传统,一份是移植而来的法律规范体系。当然,对于后者,其私法层面追根溯源主要还是源于萨维尼倾注毕生心血的罗马法体系。但是,如果说德国历史法学的时代使命是追求法律研究的科学化,发现和建构这套私法规则体系,那么中国历史法学的时代使命则主要不在于法学研究本身的科学化和私法规则的提炼,而是一个浴火重生的国家的伦理秩序和政法秩序的重建,简而言之,中国历史法学必须是作为公法学的历史法学,德国历史法学派的缺失之处,恰恰是中国历史法学的着力之点。
就此而言,中国历史法学的时代使命,既不是发幽古之思,也不是从历史中提炼私法规则,而是从历史中重建伦理秩序和政法秩序,历史法学指向的不是学科建制意义上的法律史或者法律思想史研究,而是在此基础上的一种关于法律的政治使命与道德秉性的历史思考,一种透过特定时空维度,以法律为样本,观察人世生活因果关系的法律哲学,基于人曾经是什么而探究可能与应当具有何种惬意的人世生活的政治正义。因此,对于现时代的中国历史法学,急需处理的伦理—政法问题,必然是个历史问题;反过来,最大的历史问题,实际上是伦理—政法问题。
新旧政法体制与法学的时代使命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形成新旧两种政法话语与体制,两者相互寄生,斗争又合作。新政法体制的建立是通过寄生在旧政法体制之中逐步实现的,但随着新政法体制的逐步壮大并越来越具正当性,现在出现了反向寄生,即旧政法体制开始学会了新政法体制那套话语和做法,寄生在新政法体制之中,从之前的抵制转向了合作,甚至利用。借用微博上的一句话:你跟他讲法律时,他跟你讲政治;你跟他讲政治时,他跟你讲法律。旧政法体制已然学会了新政法体制的话语和策略,以使其自身更具有合法性。在新旧两种政法体制之间,夹缝中求生存的是真实世界的法律实践,既受到两种政法体制的规训,又利用一种体制对抗另一种体制,再加上社会本身孕育出来的习俗和惯例,以及转型时期的种种悖谬,真实世界的法律实践中,充满难以捉摸的不确定性。
由此,中国的政法话语、制度和实践三个层面都呈现出极端复杂的局面,法律人有切身感受,不再赘述。与这种复杂局面相对应的,是法学的日益分化,呈现出多元混杂的状况。规范法学、社科法学蔚然成型,但彼此画地为牢,各说各话,前者重视新政法体制内的规范主义的法条分析,后者重视展现真实世界法律实践的复杂面向,但两者都放弃了对政法传统和政法现状的整体性解释和理论化处理。基于对这两种研究的不满,政治法学近些年来开始崭露头角,因关涉意蒂牢结,政治法学从一诞生,要么就是“借西讽东”,以宏大的理论叙事来代替具体问题的分析,也算是一种没办法的办法;要么就是充斥真情复假意的所谓“隐微”表达,话语空间虽然有限,但足以挑动人们神经。
如果上述所言不虚,则意味着中国政法体制的复杂现状使得法学发生了内部分化,但这不是一个自然的研究取向上的分化,背后有着深层次的结构性因素,法学内部的分化是政法体制内在矛盾的根本展现,由此也注定法学虽多元但并不成熟。不成熟的表现之一,是学术上的争论理念先行,将学术争论转换为体制问题争论,结果必然是各说各话;表现之二是争论大部分停留在表面上,未能深入到问题的历史深处,因而也就无法把握问题的真正本质。就此而言,萨维尼的下述教诲,今天仍然受用,法学的历史观点的本质不仅在于对所有时代的价值和独立性的相同承认,它最为重视的是,应当认识到连接当前和过往的生机勃勃的相互联系,没有这个认识,对于当前的法状态,我们只会注意到其外在现象,而不能把握其内在本质。
以二零一二年热闹非凡的“八二宪法”研究为例,规范法学、社科法学、政治法学纷纷登场,各抒己见。但“八二宪法”是历史叠加的产物,而且这个历史不是自然展开的连贯的历史,而是充满诸多冲突与断裂的历史三峡,“八二宪法”的核心之处就在于如何将这种种冲突与断裂统一起来,讲出一个完整的故事,而统一起来的关键就在于多重的复合结构。这种复合结构的揭示,则必须回溯“八二宪法”的生成历史。例如,从共同纲领到“八二宪法”,统一战线和政治协商会议的性质与宪法地位几经变迁,只有将这个变迁过程完整地呈现出来,才有可能理解统一战线和政治协商会议的本质,以及它们在“八二宪法”体制中发挥的政治联合与区隔功能,而抛开这一点,是无法完整地理解“八二宪法”的主权结构的。因此,历史是法学各流派的最大公约数,这不仅仅因为法律必然是历史地生成的,更在于抛开历史,我们实际上无法真正理解法律文本的规范意义。
今天倡言历史法学,无论就认清中国政法体制的复杂面向,还是就超越法学多元但不成熟的现状,抑或应对复杂历史处境提出的新问题,均是必然的选择。法学研究必须要向后看,通过不断重新占有、发掘和重述历史,以应对当下,建构未来。
历史、政治与法学的成熟
萨维尼曾倡言,法学家必当具备两种不可或缺之素养,此即:历史素养,以确凿把握每一时代与每一法律形式的特性;系统眼光,在与事物整体的紧密联系与合作中,即是说,仅在其真实而自然的关系中,省察每一概念和规则。这是萨维尼针对作为私法学的历史法学而言的,对于主要是作为公法学的中国历史法学而言,法学家则必须具备历史素养和政治意识。法学的成熟需要有历史素养,其原因在于今天中国的政法状况是多种法律传统复合而成的,不是简单的规则拼凑的结果,而是层层叠加的历史话语和实践的结果,其中充满历史变迁所带来的时间的重叠和时代的错位:其一是传统中国的政法传统,姑且称之为老政法传统,虽然在形式上基本不再有所体现,但在实践中和意识中仍有很多留存,“天理、国法、人情”这一法律意识结构仍然主导着大多数人的思维,成为贯穿在政法实践中的民族精神;其二是革命根据地以来的旧政法传统,从最高层的宪政体制到最底层的纠纷解决,旧政法传统依然在中国政法体制和实践中占据关键位置;其三是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新政法传统,在民商经济领域中已经处于主导地位,在政法话语体制中似乎占有道义的高点,并据此扮演着挑战者和批判者的角色。今天中国政法实践中的诸多问题及其未来走向,实际上取决于三个政法传统的折冲樽俎。在这种复杂历史处境下,法学如果不想固守一端,在表面问题上喋喋不休,则必须以整体性的视野深入到三个传统的历史之中,探究一下哪些因素是法律体系的本质性因素,需要我们认真对待,而哪些因素仅仅是被利用的工具性因素,需要揭露其表象后面的虚伪本质。正如萨维尼对罗马法的研究,其意义不在于罗马法对当下和未来的主宰,而在于这是一个去伪存真的过程,是发现真理、建构未来的过程。如此,法学才能够触及历史真理,即上升为史学而承载民族精神,加入一个伟大的学术传统。
今天中国的政法现状,不是三个政法传统形式上的简单叠加或者是规则上的单纯冲突,而是涉及三个政法传统在最为根本的政法伦理上的冲突。老政法传统“天理、国法、人情”的多维视角和多层次规范体系,综合各种纠纷解决方式,以整体性的关切来维护儒家伦理秩序所追求的生命的和谐。旧政法伦理今天面临各种各样的挑战,在维稳的重压之下,可谓内外交困,它注重问题的实际解决,服务于政治大局,至于解决的手段和过程,往往是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形式服从于实质。新政法传统重视形式主义的程序正义,但精致的法律程序往往无法应对复杂的政法矛盾,现实的复杂性往往超出了立法者的想象力,这当然不是中国特色,在任何一个剧烈转型时期,以常态作为基础的形式主义的法律规范体系都不得不面对转型时期复杂处境下的困局。政法伦理的冲突不像规则的冲突,可以做出非此即彼的简单选择,历史处境决定了冲突的必然存在,因此也只有历史的变迁能够化解此种冲突,法学在其间起着接生婆的作用。
如果说政法伦理的冲突是最为根本的冲突,那么法学研究最终必须面对这种冲突,法学在重新占有和解释历史的过程中,需要有主体性的政治自觉和政治意识。一个优良的政治秩序的建设,以及背后所依赖的政法伦理秩序的重建,将主导着我们对历史的理论化处理。当然,此种政治秩序以及伦理秩序不是自然给定的,而是在不断重述历史的过程中呈现出来的。也就是说,政治自觉和政治意识,不是简单的站队问题,而是历史地生成的。简单地站队,恰恰是不成熟最重要的表現。就此而言,法学的政治成熟本身,也是个历史问题。法学的成熟需要有历史意识,而对历史的重新占有、发掘和重述需要法律人的政治自觉和政治成熟,这是中国法学的时代使命,更是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