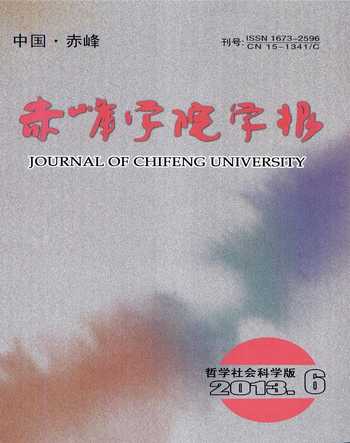试论俄苏红色经典在中国的接受与传播
2013-04-29周露叶志彦
周露 叶志彦
摘 要:俄苏“红色经典”在中国的接受与传播经历了改革开放前30年与改革开放后30年(延续至今)两个阶段。通过对这两个阶段接受与传播路径的梳理与反思,可以探讨文学与社会政治之间的关系以及文学本身的一些内在发展规律。本文将以《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为蓝本,着重探讨俄苏“红色经典”在中国的接受与传播路径及其所折射出的文学作品在他国批评与接受的演变以及文学本身的发展规律。
关键词:俄苏;“红色经典”;《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接受与传播
中图分类号:D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6-0084-03
所谓俄苏红色经典是中国文坛特有的称谓,在它的源语国、即当今的俄罗斯并没有这样的术语。红色经典的提法源自上世纪90年代前后的中国文坛,当时一批传统的革命题材歌曲、小说、戏剧、影视节目重新受到人们的关注,于是带有革命、牺牲和胜利寓意的“红色”一词与“经典”相结合,红色经典的术语开始在中国大陆流行。学者陈建华教授在谈到中国文化语境下的俄苏“红色经典”时归纳出其四个特征:“1.与社会和时代联系紧密,往往具有较为鲜明的阶级性和党性;2.表现新时代和新世界,突出新主题,塑造无产阶级新人形象;3.作者主要是一些曾投身革命运动的作家;4.作品在中国产生过重大影响。”[1]本文基本认同这一观点,认为只要符合上述特征的作品都可列入红色经典的范畴,即使从纯文学意义上来说,有的作品还够不上“经典”之称。
俄苏“红色经典”在中国的接受与传播经历了改革开放前30年与改革开放后30年(延续至今)两个阶段。通过对这两个阶段接受与传播路径的梳理与反思,可以探讨文学与社会政治之间的关系以及文学本身的一些内在发展规律。在俄苏“红色经典”中,就其影响力度及延续时间而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是一部非常值得关注与讨论的作品。本文将以《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为蓝本,着重探讨俄苏“红色经典”在中国的接受与传播路径及其所折射出的文学作品在他国批评与接受的演变以及文学本身的发展规律。
一、改革开放前30年俄苏“红色经典”在中国的接受与传播
(一)上世纪50年代依赖性的全盘接受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各国纷纷与中国断交,想把新生的共和国扼杀在摇篮中,只有苏联给予了中国全方位的支持。由于有着相同的思想政治体系与组织建构,也由于年轻的共和国尚未形成自己系统的文艺理论观与成熟的、等英雄人物成为中国人民学习的榜样。”[2]高尔基的《在人间》和《母亲》、法捷耶夫的《毁灭》和《青年近卫军》、绥拉菲摩维奇的《铁流》、富曼诺夫的《夏伯阳》、奥斯特洛夫斯基符合当时形势要求的文艺作品,所以在上世纪50年代对俄苏“红色经典”采取了依赖性的全盘接受策略。据不完全统计,“从1949年10月到1953年底,中国翻译出版苏联科学技术和文艺方面的书籍就达5183种。苏联的文学名著在中国广泛流传。保尔、卓雅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西蒙诺夫的《日日夜夜》以及《卓雅和舒拉的故事》、《普通一兵》、《金星英雄》等成为中学生的课外阅读书目,这些作品中的英雄人物形象激励着我国千千万万的青年走上了保家卫国、富国强民的建设之路。同时这些作品也影响了以王蒙为代表的一代中国当代作家的成长,他写道:“整个苏联文学的思路与情调、氛围的强大影响力在我们身上屡屡开花结果”,同时他认为:“苏联文学在中国曾有的巨大影响,这不但是无法否认的,而且是事出有因的。”[3]卞之琳等指出:“对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念和为它献出生命的决心的宣扬,决定了苏联文学的教育力度。”[4]这些表述形象地传达了俄苏“红色经典”所具备的强大的精神内涵。
以《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为例,这部作品以保尔从一个调皮捣蛋的小孩成长为一名具有坚强革命意志的战士为主线,全书处处洋溢着保尔坚定的革命性、对崇高理想的不懈追求以及无私奉献的奋斗精神,这种精神恰恰契合了当时时代的主旋律。他有关人生的名言早已融入读者的血液之中,鼓舞着一代又一代青年人的成长。无怪乎学者丁帆写道:书中的箴言“已然成为几代中国人的价值坐标,它深深地植根在我们的‘集体无意识中,成为一种20世纪的民族历史沉淀,是轻易不能抹去的近乎宗教的情绪。”[5]
(二)上世纪60-70年代日趋冷淡的选择性接受
赫鲁晓夫上台,中苏交恶。随着外交政治关系的趋冷,中国对俄苏文学的译介也逐年减少。1962年以后,不再公开出版任何苏联当代文学作品,1964年以后,俄苏文学作品一律从中国的公开出版物中消失。1966年文化大革命以后,一切中外文学作品均被打入冷宫,其中包括最正统的俄苏革命文学作品。直到1973-1976年的文革中后期,《母亲》、《毁灭》、《铁流》、《青年近卫军》、《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少数几部被视为最正统的革命文学作品才得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社再次公开发行。
但即使在堪称文化沙漠的十年文革中,《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依然是青年们的最爱。这与书中青涩又真实的爱情描写、温柔可人的冬妮娅形象的成功塑造有关。如在《冬妮娅“情结”》一文中作者写道: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我读的第一本“外国书”,也是我第一次读到涉及爱情的小说,更是我情感之琴的一根未曾拨动过的琴弦第一次有了颤动……当保尔和冬妮娅最后一次相遇又分手后,冬妮娅消失了,再也没有了关于她的只言片语。合上书,我仍在为她担忧,她以后怎么样了,她会幸福吗?二十几年如烟云过眼,我一直没有找到答案。”[6]
在文革结束将近20年后,刘小枫发表了一篇《记恋冬妮娅》的散文,堪称为冬妮娅正名的经典之作:
“二十多年前的初夏,我恋上了冬妮娅。……保尔的形象已经黯淡了,冬妮娅的形象却变得春雨般芬芳、细润,亮丽而又温柔地驻留心中,像翻耕过的准备受孕结果的泥土[7]。
因此,在那将爱情视为洪水猛兽的岁月里,在充斥着不食人间烟火、高大全主人公形象的中国文坛,《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却有幸成为中国读者的爱情启蒙教材,这在世界文学接受史中恐怕都是绝无仅有的现象。作者本人也万万不会想到,他的这本以塑造坚贞不屈的无产阶级战士为目标的小说,在遥远的东方却会收到这么意想不到的效果,为当时身处爱的荒漠中的中国读者打开了一扇通往浪漫爱情之路的窗口。这也正契合了姚斯有关作者、作品、读者三者关系的接受美学理论。
二、改革开放后30年俄苏“红色经典”在中国的接受与传播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随着政治环境的日益宽松以及文学价值取向的转变,俄苏“红色经典”文学在中国一枝独秀的局面已不复存在。在大量引进西方现当代文论及西方作家作品的同时,人们对俄苏“红色经典”进行了一系列反思,这不仅包括学理层面的,也包括社会层面的。
在对经典的不断重新解构中,即使像高尔基的《母亲》这样被誉为无产阶级文学奠基之作的作品的文学性与思想性也遭到了极大的质疑。在位列俄苏“红色经典”的文学作品中,似乎只有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得到了较为众口一词的称赞。并且在评论的过程中,其身上的“红色”色彩逐渐褪去,“经典”的含义日益凸显。其实在当年的红色经典作品中,《静静的顿河》本身就属于异类,因为它所塑造的主人公并非传统的高、大、全似的人物,而是一个处于中间地带的人。事实上当年中国为中学生开列的课外阅读参考书目中,向大众所推荐的肖氏作品并非这部《静静的顿河》,而是他的另一部更符合当年形势、歌颂农村集体合作化的作品《被开垦的处女地》。如今这部《被开垦的处女地》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俄罗斯,都已销声匿迹了。
但是在当今的中国,只有一部当年真正意义上的俄苏“红色经典”作品依然受到热捧,特别在中学生群体中,依旧很有市场,这就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而在其出生地俄罗斯它的光芒却日渐暗淡。正如加达默尔所言:“对一个文本或艺术作品里的真正意义的汲舀是永无止尽的,它实际上是一种无限的过程。”[8]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俄罗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都在被汲舀着不同的话语,被赋予不同的含义。当年在中国流行的一大批俄苏“红色经典”中,为何独独由非专业作家写就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能幸免于难,流传至今,依旧焕发出艺术的青春?笔者认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如今中国的走红,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从政体来看,中国现在依然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它所倡导的文艺理论观及价值取向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的创作宗旨是高度吻合的。因此,早在1989年我国团中央就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列为给青年人树立“人生的路标”十本必读书目中的第一本。许多学校、单位在选定青少年必读书目时,都把该书作为首选书目。在1999年《中华读书报》组织的一次名为“20世纪百部文学经典”的评选活动所公布的调查结果中,虽然俄罗斯文学作品仅有5部入选,但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却跻身其中,排名第53位,甚至位列契诃夫的名作《樱桃园》(排名第97位)之前[9]。而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出生地俄罗斯,苏联政权与政党早已不复存在,作品所宣传的共产主义精神已失去了存在的土壤,所以该书受到冷落也就不足为奇了。
其次,《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当今中国的走红与作品本身独特的艺术魅力有关。就艺术体裁而言,该书可视为一部“成长”励志小说。它生动形象地刻画了少年保尔·柯察金的成长历程,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作家尼·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一部自传体小说。它不是作者坐在家里冥思苦想出来的空中楼阁之作,而是具有坚实的生活基础与丰富的生活内涵,很容易在读者中产生共鸣。况且,保尔艰难曲折的人生经历所折射出的奋斗精神,在任何时代都是不会过时的。正如学者何云波所言:“当两个阶级的残酷的厮杀都成了往事,保尔人生所昭示的那种顽强、毅力、奋进,面对挫折的勇气,对理想的执着,又往往可以超越阶级、时代,成为人生的一种宝贵的精神财富。”[10]无独有偶,位于俄罗斯莫斯科市中心特维尔大街9号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尼·奥斯特洛夫斯基国家博物馆”在苏联解体后就已改名为“征服者博物馆”,主要举办残疾人事迹展与作品展,这大概也是因为看中了作者独特的身世及奋斗精神与残疾人所追求的精神境界有着某种契合之处吧。
就作品内容而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不仅描写了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炽热的革命斗志,同时也描写了风花雪月的爱情故事。书中对少年保尔与冬妮娅纯真的初恋之情、青年保尔与丽达朦胧的恋情以及成年保尔与达雅真挚的夫妻之情的描写都非常到位、引人入胜。尤其是保尔与冬妮娅之间那段纯美的青春之情曾引起过中国当年文化荒漠时期多少少男少女美好的联想;“冬妮娅”这三个字以它特有的异国情调和神秘婉约的意象搭配,温暖过多少渴望爱情的心灵。
第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当今中国的走红也与评论界的争论与影视媒体的助推有关。1998年《俄罗斯文艺》第二期发表了两篇针锋相对的文章:任光宣的《重读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余一中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一部好书吗?》,由此掀起了一股评论热潮。由中国深圳万科影视公司与乌克兰合拍的二十集电视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于2000年2月28日起在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黄金时间播出,也助推了这股热潮。
三、结语
反观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成立之初,在中国大陆对俄苏“红色经典”占压倒性地全盘接受与传播在世界文学接受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现象,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而在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里,俄苏“红色经典”逐渐失去了话语权,只剩下极少数作品依旧发挥出昔日的荣光。从俄苏“红色经典”在中国的接受过程和传播路径,我们可以比较深入地探讨文学与社会政治之间的关系以及文学作品本身的艺术特色对作品的成败所起到的关键作用。个中三味,尤其值得令人深思。
参考文献:
〔1〕陈建华,沈喜阳.俄苏“红色经典”在当代中国[C].中国外国文学学会.走进经典——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第九届年会论文集.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282.
〔2〕刘德喜.从同盟到伙伴——中俄(苏)关系50年[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112-113.
〔3〕王蒙.苏联文学的光明梦[J].读书,1993(7).
〔4〕卞之琳,叶水夫,等.十年来的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工作[J].文学评论,1959(5).
〔5〕丁帆.怎样确定历史的和美学的坐标——重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札记[J].文艺争鸣,2000(5).
〔6〕韩秋林.冬妮娅“情结”[N].中华都读书报,2006(8).
〔7〕刘小枫.记恋冬妮娅[J].读书,1996(4).
〔8〕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M].北京: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386.
〔9〕中华读书报[J].1999-9-15.
〔10〕何云波.当神圣已成往事——世纪之交“钢铁热”之反思[C].中国外国文学学会.走进经典——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第九届年会论文集).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2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