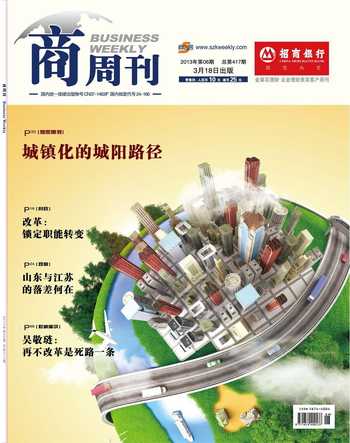反腐力量的新增长点
2013-04-29麦宇旻
麦宇旻
2013年“两会”刚刚结束,借此机会对具有中国特色的两套班子——人大和政协的职能进行重新思考,是有必要的。
“理论上讲,中国现行的反腐体系已经非常全面——党内,有纪检系统,进行党内监督;政府内,有监察部门,进行政府监督,人大,作为权力机关对政府进行法律监督,政协、民主党派进行民主监督,还有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人民群众的社会监督,可谓天罗地网。”赵高潮说。
但是,他又补充道,“当真正执行起来,又常常是不到位的。”
人大政协堪任反腐急先锋
赵高潮,中国现有八大民主党派之一——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一员,现任该会青岛市委副主委。事实上,他对目前中国这六支反腐力量的盘点是不错的,无论这些力量是强是弱,是名副其实抑或形同虚设,中国反腐事业的总体布局已经基本奠定。
六支反腐力量,按照“体制内”和“体制外”标准来划分,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体制内的力量——党内纪检系统、政府监察部门。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受制于纠缠的人事关系和隶属性质的管理体制,这两支力量在反腐过程中总得瞻前顾后,难以做到强硬反腐。
第二类是体制外的力量——新闻媒体、人民大众。千百万双雪亮眼睛与大众媒体无孔不入的曝光能力一旦结合,可照亮社会每个角落。不过,过分强大的社会效应也使这支力量容易失控,实乃社会稳定发展的双刃剑。在积重难返、需要妥协精神面对的现实国情党情面前,仅依靠新闻媒体反腐有如泻药,虽能治病,但也伤身。
第三支力量则是既可说是居于体制外、又可说是居于体制内的人大与政协两套系统。一方面,在官方的四套系统中,它们是与人民群众联系最紧密的两套班子,能够立足于民间立场,捍卫公众权益。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中不乏热血人士、草根斗士,能言敢做,无视潜规则,堪任反腐生力军。另一方面,两套系统实际上处于党和政府的有序管理之中,操作起来收放自如,安全系数较高。
与新闻媒体相比,人大、政协系统发挥政府监督职能具有明显优势。新闻媒体的曝光式反腐属于“秋后算账”型,是腐败事实发生后的一系列批评、指责、舆论压力,虽然社会效果巨大,但毕竟腐败已然发生,媒体掀起的民怨无法弥补损失,反而引起社会躁动情绪。
相反,人大和政协的政府监督属于“防患于未然”型,通过参加决策听证会、法院旁听、特定问题质询甚至介入政府审批环节,人大和政协可以实现“防腐”。
主动出击化解官僚坚冰
青岛市人大代表、青岛市委党校教授刘文俭说:“近两年,青岛市政府一些重大的决策都会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去旁听”,去年,他就参与了几次政府的意见咨询会。这种“俯下身”倾听各界意见的政府会议,在青岛越来越多。
除了“被邀请”,人大常委会偶尔也会主动出击。“当感觉政府在某方面作为不够、工作没有达到相应要求,或者怀疑在某些地方发生了重大损失,带来了一些不良影响,人大常委会可以随时去质询政府。”刘文俭说。
在人大表决方面,“全票通过”已经成为历史。越来越多人大代表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敢于动用否决票,以表达对某项工作结果的不满。虽然最终绝大部分报告因多数压倒少数而通过,“但否决票的多寡实际上已经对政府官员产生了心理压力。”刘文俭说。
民主党派也在努力行使监督权利。去年,由中国民主促进会青岛市委提交的针对“青岛中小学教师接受政府培训过多过频致严重影响个人休假”的调查报告受到政府的采纳,获得了迅速解决。
不过,并非每种监督职能都在顺利行使。去年底的青岛市两会,一个四方区人大代表的发言很能说明问题。她说,“我曾经几次到法院去旁听,受到了法官的阻挠,他对于我这种旁听的要求很不习惯,觉得我是不是在监视他,还直接取消了当天的庭审。”这位人大代表发现,法院对于宗卷的存放十分随意,文件随时有丢失之虞,存在比较严重的失职嫌疑。
这个案例让人联想到广东的“孟浩事件”。2006年,广东省政协委员孟浩因接获某中学生遭遇不公的求助,求访广州市教育局领导,遭到该局工作人员的粗鲁对待和报警威胁。次日,广州市教育局甚至发函至省政协,要求成立“联合调查组”,严肃处理孟浩。然而,在广东省政协的强硬回应,新闻媒体的广泛报道以及公众舆论压力之下,广州市教育局最后低头认错。这一事件可看做是政协在行使社会监督权方面一次重大胜利。
“如果每一个委员都有孟浩这种意识和勇气的话,我觉得政协和人大的监督作用会发挥得更好!”刘文俭说。
立法缺位监督实践有心难行
腐败总是从权力膨胀开始。要铲除腐败,就要限制权力。“政府从本源上讲是接受人民的委托、为人民办事的一个组织机构,但是时间长了之后,政府的一些部门往往都想把自身的权力搞得大一点。”刘文俭分析说。
“按照马斯洛需求理论,人最基本的需求就是生存需求,然后是受到别人尊重的需求,那么你手中有权力,就是受到别人尊重的一个前提条件,你有权力往往就能受到别人的尊重。所以,政府每一个部门的人,都不希望削弱权力,而是希望加大。”
刘文俭从理论上解释了政府的权力扩张为何难以遏制,解释了官僚权力欲望的必然性,而试图从政府内部诞生力量去阻止权力扩张是徒劳的。最明智的方法始终是从外部引入规制。引入哪一种力量的规制则是最核心的问题。人大和政协,应是一支最理想的规制力量。
目前,在国内的立法中,对于人大的相关规定则已经比较详尽,2006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详细规定了地方人大如何对政府进行审查、检查、质询、特定问题调查。不过,这一法律也对人大代表个人的监督行为产生掣肘,因为依据该法律,人大代表的监督职能基本上要体现集体意志,也即人大委员会的集体决议,若想以个人意愿进行督意,总得经过一系列繁琐程序,势必降低了监督积极性。在这一点上取得立法突破,可以进一步地激发人大系统的活力。
在政协方面,法律缺位较为明显。中国民主促进会青岛市委副主委赵高潮说,对于政协委员而言,对政府进行监督是毫无疑问的权力,但在具体的某个场合的某个事件,政协委员应不应该介入,又常是难以判断和富有争议的。这是立法缺位带来的实践不便。
在立法上,推进人大、政协的权力范围,为代表和委员介入政府决策过程打开方便之门,是最为理想的防治腐败方式。人大和政协作为反腐力量的新增长点,值得在新一届领导班子的执政布局中占有更重要的地位。
后记
中国文化熏陶下,中庸者众,奇葩者少。在今年“两会”上,一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失声,以及面对媒体时敷衍的一句“我只是过来学习的”,就反映了这种明哲保身的心态。
然而,社会的每一次进步又常常是奇葩推进的,诸如打假斗士方舟子,叫板铁道部和环保部的律师董正伟,曝光雷政富视频的记者朱瑞峰,皆属人中“怪胎”,社会“奇葩”。偏偏是这些“怪胎”、“奇葩”,最终被证明促进了社会某一步质的飞跃。
据记者观察,在人大、政协之中,奇葩型的代表也大有人在,他们对潜规则视而不见,偏偏要与法律形式上赋予的权利较真,要求质询政府,旁听法院,走访部门,讨要说法。他们比在两会上“放炮”的委员更可敬。
总之,政府应当慢慢习惯外界对自身的各种质询、怀疑和要求,而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亦应习惯对政府事务进行法律框架内的监督。一退一进,反腐局面将能海阔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