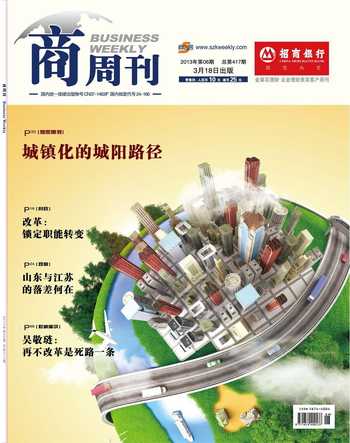改革:锁定职能转变
2013-04-29
从“职能转变”赫然写入标题,到大刀阔斧的机构整合设计,再到简政放权的“五个减少”。3月10日,备受各方关注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亮相。方案提出,将重点围绕转变职能和理顺职责关系,稳步推进大部门制改革。不仅让公众从中读出了铁路、食品安全等领域机构调整的突出亮点,更让民众看到了政府职能转变这一核心要义。
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七次重大行政体制改革,《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传递出一个鲜明的信号,政府将以更大力度,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上加快职能和角色转变。
有评论认为,人们之所以关注此项改革,一是这项改革涉及部委的调整,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二是相比那些抽象的理念,部委调整是最具体、最看得见的改革;第三,更重要的是这是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的第一个大动作,由此可窥见今后的改革走向。
“放权”而不是“分权”
“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邓小平曾如此评价机构改革。
经过前6次较大规模调整,如今这场改革仍在延续。政府机构配置逐步与市场经济接轨,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改革路径也日渐清晰。
2008年的第六次机构改革,被媒体称为“第一轮大部制改革”。当时有评论认为,新组建工信部等5个部委,国务院组成部门改革为27个,为最大限度地避免职能交叉迈出了“大部制”步伐。
参与2008年“大部制”改革方案设计的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总结,认为2008年机构改革,是权力机构调整的重要切入点,确定了行政三分制,即决策、执行、监督三分的中长期改革目标。去年11月,十八大再次提及“大部制”,十八大报告要求“稳步推进大部制改革,健全部门职责体系”。
而在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科研部主任许耀桐看来,2008年的大部制改革,是一次尝试和探索,肯定改革作用的同时,必须看到一些问题,一些合并后新组建的机构,还是分属办公,貌合神离,并没有有机融合。但大部制改革不是组织架构板块上的简单拼合,合并后融为一体,才是改革目的。这就是这次改革面对的问题。
有分析称,推进政府改革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涉及经济社会各个领域,很难寄希望于“毕其功于一役”。在明确改革目标后,重在创造条件,积极稳妥地推进,成熟一项推进一项,由此真正释放出强劲的改革红利。
此外,很多人把这一次的大部制改革看成是部委之间的权力重组。其实,这一次改革并不是部委问的权力重新分配游戏,而是一次放权革命——向社会放权,向市场放权,向民众放权。这个问题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马凯在对机构改革作说明时说得很清楚:这次改革,要以更大力度,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上加快国务院机构职能转变,重在向市场、社会放权,减少对微观事务的干预,同时改善和加强宏观管理,严格事后监管。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也认为,本次机构改革最大的亮点是放权。
减了多少个正部级机构是次要的,最关键的是向社会放了多少权。大部制改革,不是让这个部委权力更大,那个部委权力更小,而是系统地向社会放权,减少政府干预,市场能调节的交给市场,社会能自治的交由社会,地方能管理的交给地方。集中于“放权”而不是“分权”,从体制上最大限度地给各类市场主体松绑,而不是在部委间分蛋糕。
比如要“减少投资项目审批,最大限度地缩小审批、核准、备案范围”,要“减少资质资格许可,对不符合行政许可法规定的,一律予以取消”。在民政事务上的改革也是如此,要放松对社会组织的管制,更好发挥社会组织在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认为,作为行政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机构改革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推动政治体制改革,触及的是政府放权与削权,“改革最困难的就是理清政府权力清单,清楚界定政府的基本职能和权力,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社会的归社会。一方面是放权,也就是下放权力;一方面是削权,也就是权力转移,向社会转移”。
向社会放权,向市场放权,向民众放权,这才是应有的改革方向。如果改革仅仅是在部委间分权、在官员间平衡,变成部委间的权力博弈,而不是向市场、社会和民众分权,还可能滋生出更多的问题,改革只是在原地转圈圈。
《朱镕基讲话实录》中曾如此描述机构改革阻力,“我抱着粉身碎骨的决心来干这件事,”朱镕基说,1997年年底,找几十位部长逐个谈话,没有一位部长主动表示自己的部门该撤,长时间坐着谈话使朱镕基过度疲劳,每次站起来都很困难。
大部制改革是要动既得利益者“奶酪”的改革,是公众欢迎而既得利益者抵触和抵抗的改革。但涉及放权与削权的改革,相当于公权力“革自己的命”、让出自己的“饭碗”,势必陷入部门利益博弈。而这种改革的难点更在于当下扭曲的权力分配结构和利益分配结构。在公众对公权力制约不力的政治结构中,对行政权力的限制性和约束性的改革,从某种程度而言,都意味着权力掌有者的损益,并且是自我损益。这也正是以往涉及到国家行政权力的改革常常困难重重、进退往复的主要原因。
正如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所说,本轮机构改革虽是“微调”,但如何打破部门利益博弈僵局,实现真正的放权和削权,仍是关乎改革成败的关键问题。
改革不应只是“加减法”
一直以来,权力边界不明晰,有些地方对微观经济运行管得过多、多头管理,互相推诿的现象让企业头疼不已。
全国人大代表、大同煤矿集团董事长张有喜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谈到,同忻煤矿在办理手续过程中,最少需跑33个政府部门及下属单位,先后要出147个文件,盖205个公章。无独有偶,今年初广州市政协委员曹志伟曾制作一张项目审批流程的“万里长征图”,显示一个投资项目从立项到审批,要跑20个委、办、局,53个处、室、中心、站,盖108个章,共有100个审批环节,需799个审批工作日。
可见,机构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是迫在眉睫的事情。
财经专栏作家余丰慧撰文指出,从与企业密切相关的事项看,减少和下放投资审批事项:最大限度地缩小审批、核准、备案范围,切实落实企业和个人投资自主权。减少和下放生产经营活动审批事项。改革工商登记制度,不再实行先主管部门审批、再工商登记的制度,商事主体向工商部门申请登记,取得营业执照后即可从事一般生产经营活动。这些对企业都将带来重大利好,特别是民营企业的活力将会得到很大释放。
中央编办副主任王峰就《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有关内容的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也解释道,“我们机构改革方案中间加了‘职能转变这四个字,这正是我们这一轮改革的重点。过去一提到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总有人说‘机构改革,也就是把‘哪些机构整合起来,我觉得这是一个误区。”
的确,机构改革不应只是表面的“加减法”,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应该是转变政府职能,机构改革包括稳步推进大部制,这都是改革的重要内容,但是最主要的内容、最主要的任务应当是职能转变,而目的则是为了更加利民与便民。
与5年前环境保护部的升格成立,鲜明指向民众对环境问题的关切一样。撤销铁道部,重组国家海洋局、能源局等,都是从这方面考虑的,也是此次改革的亮点。
不要小看“职能转变”这4个字,要实现这个目标,比机构撤并难度要大得多。在现行有强大动员力的体制下,要撤并几个机构,或许只需要一个文件配以安置措施即可实现,但要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殊为不易。
比如,要建设“服务型政府”,要“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谈何容易——“减少微观事务管理,以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这意味着向市场放权;“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更好发挥社会力量在管理社会事务中的作用”,意味着向社会放权;而“减少审批事项”,意味着要向下放权;“减少专项转移支付和收费,减少部门职责交叉和分散”,则意味着政府要主动“削权”并斩断或多或少存在的利益链……
这些“浩大工程”,撤并机构是其中一部分。只有机构撤并的同时,政府职能同步转变,才能建立起“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正如王峰所讲,机构是职能的载体,如果职能不转变,一味地调整机构,实践证明有两种结果:一是不同类型机构硬整合起来,导致运行不畅,不多久后又有可能分开;二是机构在一定时期担负责任繁重,在运行当中顾此失彼,达不到改革目的。
(本刊编辑综合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