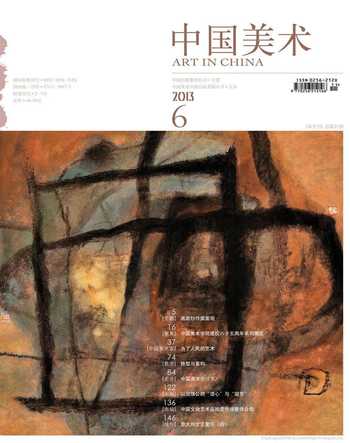沈从文与美术史研究
2013-04-29杨道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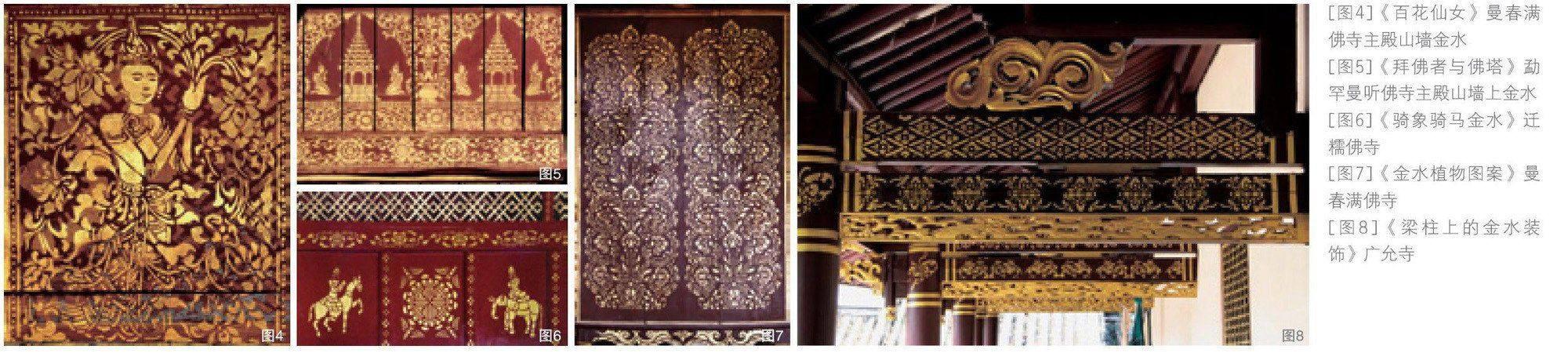


言及沈从文从作家到研究文物考古的转换,一般人多以为是不得已的事,似乎是从一个领域转入另一个全新的领域之中。但从出版的沈从文全集看,并非如此。沈从文在1934年10月写成的一篇《艺术周刊的诞生》中,开头就提到他问一个艺术学校教图案的大学教授是否对中国古锦的种类、中国铜器玉器花纹的比较、景泰蓝的花纹颜色、硬木家具的体制、故都大建筑上窗棂花样等问题有兴趣。可见他自己对这些有很多的关注和兴趣。而写于1947年7月的《读展子虔〈游春图〉》一文,几乎就是一篇极具眼光,对于中国绘画品赏鉴定和画史画论有极深研究的专业论文。其中对于《游春图》的鉴定,最重要的论据就从衣着式样来判定,其中所提出来的许多方法观点后来就被他用于文物的研究之中。这些观点被后来的研究者称为三重证据法:传世文献、出土文献和出土实物彼此互证。正是由于沈从文对于古代文物方面广泛的兴趣,才使得他对于中国美术的研究在某些领域甚至超越了许多专业的美术史家。
在很多人的眼中,沈从文似乎仅仅和服饰研究相关。但实际上沈从文对于中国美术史的贡献绝非一本《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所能涵盖的。他的全集中有五卷是有关“物质文化史”的,其中包括丝绸简史、漆工艺简史、陶瓷工艺简史、金属加工简史等多部专题史。目前由于受到西方学界的影响,我们的美术史的研究才开始关注所谓的视觉文化或物质文化。但沈从文很早就提出了“物质文化史”的概念,起初可能是出于对于艺术的关注,但解放后,由于强调学者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研究历史,特别要研究在历史中普通的劳动人民的贡献,而不是那些所谓精英和伟大的艺术家的成就,沈恰好关注的正是那些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形式,这些谁也无法归诸到某一个具体人物的头上,似乎当然就是劳动人民的贡献。真可谓阴错阳差,这种所谓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成就了沈从文的物质文化史的研究。如果仅仅是一个偶然,沈从文还不能成为一个伟大的学者,他在研究中极具前瞻的意识,对于当时历史(当然包括艺术史)研究中存在的单纯关注上层社会以及“以论代史”的问题有非常清楚的认识,对于艺术创作不能去学习中国积存千年的优秀作品有深切的忧虑。
首先,他对于历史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从我们学文物的人来说,要懂历史。离开文物就没法子说懂历史。”但历史学家存在一个偏见,不大看得起文物。他说他有一个恰恰相反的“偏见”:“要理解文物文化史的问题,恐怕要重新来,重新着手,按照旧的方式,以文献为主来研究文化史,恐怕做的很有限。放下这个东西,从文物制度来搞问题,可搞的恐怕就特别多。”(《章服之实》,6)按照这一方法,孙机先生先是以文物研究中国的舆服制度,其著《中国古舆服论丛》已成经典。接下来的《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和历史学家们所著的经济生活史一比,就可知道沈从文的话实在是高论。孙机先生也深得其中三味,故其著是用出土文物资料来研究物质文化,而非仅仅是文献。
其次,沈从文非常清楚地指出中国美术史研究的问题:“历来鉴定画迹时代的专家,多习惯于以帝王题跋、流传有绪、名家收藏三大原则作为尺度,当然未可厚非。可最易忽略事物制度的时代特征。”(《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第9页)根据历朝历代的事物制度,他指出很多传世名画的年代需要重新研究。他意识到,这些研究一定会带来方法和观点上的突破与创新。他说:“这些工作总的看来,大都不过是些七零八碎的小问题,始终难登大雅之堂。不过若善于运用,也许在文化史、艺术史,以至于文学史各部门,都可望起点竹头木屑一砖半瓦之用,也说不定。社会既在发展中,以论代史的方法论,终究会失去意义。但是习惯势力也绝不会一时即可望消失其作用,至少在本世纪内还将有一定市场。”(《章服之实》附页)这样的论述振聋发聩,看今天美术史研究的现状,一方面是传统的方式一味地重复,另一方面是对于西方所谓的新方法、新观念的关注,却没有在对美术史具体问题的研究上有真正意义上的突破,而沈从文所做过的这些工作,努力和发现甚至被美术史家所遗忘。我想起了为本雅明所称道的德国艺术史家福克斯。福克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看到了传统艺术理论的问题,开始注意到那些边缘领域的讽刺画、色情画以及唐代雕塑中那些无名无姓的殉葬品。他提出:“这些陪葬品的完全的无名姓,人们根本无从知晓每一件作品的单个创造者这一事实就是证明,即在这之中,所关涉的并非个别的艺术成果,而是世界和事物当时如何被社会整体所看待的。”(本雅明《经验与贫乏》,第334页)福克斯按照自己的观点写出了目前在学界已经成为经典的《欧洲风化史》和《欧洲漫画史》。但福克斯的研究也更多是为图像所限,而很少涉及出土文物。
羅兰巴特把服装分为三类:真实服装、图像服装和文字服装。服装史要研究真实服装的历史,而不是文献上的文字服装的历史,当然也不是图像服装的历史。沈从文的三重证据法重视出土文物,但文物未必都是实物,诸如壁画、雕塑、陶俑之类的只能算是图像。《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研究对象实际上包括很多并没有出土的真实服装,而只有图像。图像和真实服装之间的距离如何把握,这是以图证实者始终要注意的问题。沈从文是努力要以物证史,而非以图证史,只是有时把图看做实物了。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沈从文认为从传世文物来推的话,绘画上的南北宗问题应该推到汉代,是从博山炉发展而来的。(《章服之实》,28页)这个问题到底怎么看,至今未见美术史家去讨论。沈从文确实需要被美术史家们所关注所研究。沈从文对与中国美术史的重要性,考古出身的郑岩先生算是比较清楚地认识到的,就我所知,他是唯一一个把《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列在中国美术史书目之中的。很多人研究沈从文从从文学转入文物的原因,也有人总结沈从文对于文物研究的成就,但更需要有人接着沈从文继续运用他的方法,研究他所发现的问题。
唐张彦远曾指出当时的历史人物画就有混淆衣冠习俗的问题:“如吴道玄画仲由,便戴木剑,阎令公画昭君,已着帷帽,殊不知木剑创于近代,帷帽兴于国朝……详辩古今之物,商较土风之宜,指事绘形,可验时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二)沈从文据此指出很多在艺术史上似乎已成定论的传世之作年代都存在问题,但这些问题似乎并没有被人注意。一些比较权威的艺术史中根本不提及沈已经指出的问题,我把这些问题置于文后,大家看看是不是都解决了;
1.传为南唐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因其中有人叉手示敬,画中人多服绿,因此当产生于南唐灭亡之后,太宗淳化二年(991年)以前。
2.传为阎立本的《孝翼兰亭图》,因其中烧茶部分有一荷叶形小小茶叶盖罐,当产生于宋、元。
3.传为周的《簪花仕女图》,人物面貌,衣着样式皆合唐制,唯头上花冠与衣上花纹及更可能是宋人绘唐事;而其中的金项圈附于衣外,更可能是清人所添加;孙机先生从沈从文先生学习服饰名物考古,也以此来推究一些传世名画的年代,得此方法,但有一些新的发现。对于《簪花仕女图》,提出其中的金钗与1956年合肥西郊南唐墓中出土的“金镶玉步摇”类似,发髻也是南唐的高髻,故赞同谢稚柳先生的意见,认为是南唐的作品。(《中国古舆服论丛》,第242—243页)他提出金项圈在唐墓中亦有,但他未提及花冠的问题。
4.传为唐張萱的《捣练图》,其中的梳子式样、大小及应用,更可能是出于宋人。
5.传为王维作《捕鱼图》,其中渔婆的盖头乃宋代之物,故应为宋人作品。
6.传为展子虔的《游春图》(1947年发表的《读〈游春图〉有感》,)其实若懂得点历代服装冠巾衍变,马匹装备衍变,只从这占全画不到一寸大的地位上,即可提出不同怀疑,衣冠似晚唐,马似晚唐,不大可能出自展子虔之手。
7.《洛神赋图》,“全中国教美术史的、写美术史的,都人云亦云,以为是东晋顾恺之的作品,从没有人敢于怀疑。其实若果其中有个人肯学学服装,有点历史常识,一看曹植身边侍从穿戴,全是北朝时人制度;两个船夫,也是北朝时劳动人民穿着;二驸马骑士,戴典型北朝漆纱笼冠。那个洛神双鬟髻,则史志上经常提起出于东晋末年,盛行于齐梁。到唐代,则绘龙女、天女还使用。从这些物证一加核对,则《洛神赋图》最早不出展子虔等手笔,比顾恺之晚许多年,哪宜举例为顾的代表作”?(《我为什幺始终不离开历史博物馆》,《沈从文别集 新与旧》,岳麓书社1992年12月第1版)
8.传顾恺之的《女史箴图》,产生时间应在陈、隋之间;《斫琴图》,应当是齐、梁之时画家之作。
9. 传阎立本的《步辇图》,即便出于唐人,也应比阎立本晚。
10.传为唐代韩的《文苑图》,由于其中的圆领服出现衬领,又有硬翅平举式幞头,不可能早于五代十国,可能是宋代画家之作。
(杨道圣/北京服装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