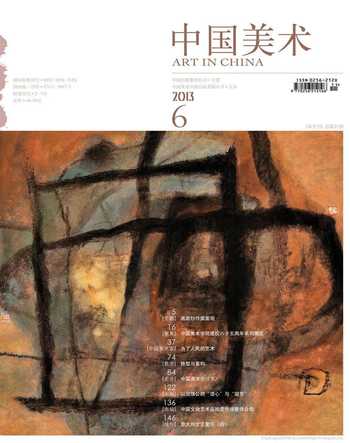古代画家“自我炒作”实例选析
2013-04-29尚晓周

高益,涿郡人,工画佛道鬼神、蕃汉人马。太祖朝,潜归京师。始货药以自给,每售药必画鬼神或犬马于纸上,藉药与之,由是稍稍知名。时太宗在潜邸,外戚孙氏喜画(孙氏有酒楼。一日,遇四老人饮酒有异,疑其神仙,因谓之四皓楼,亦谓孙氏为孙四皓也),因厚遇益,请为图画。未几,太宗龙飞。孙氏以益所画《搜山图》进上,遂授翰林待诏。(宋代郭若虚《图画见闻志》)
高益是北宋时契丹涿郡(今河北涿州市)人,善于画人物(鬼神佛道一类),宋太祖当朝时候来到京师寻找出路。虽然身怀画技,但开初他却是以卖药为生的。他自我炒作的方法,是把自己画的神鬼人物作为包装纸,随着药送给买家,借以引起大家注意。最后,他终于引起皇室外戚孙氏的注意,收藏了他的作品并厚待高益。孙氏还借太宗即皇帝位的时机,把高益所画的《搜山图》进给皇上,趁此引荐高益。随后高益如愿以偿得到翰林待诏的位子,进了皇家画院。
高文进,从遇之子。工画佛道,曹吴兼备。乾德乙丑岁,蜀平,至阙下。时太宗在潜邸,多访求名艺,文进遂往依焉。后以攀附授翰林待诏。未几,重修大相国寺,命文进效高益旧本画行廊变相及太一宫、寿宁院、启圣院暨开宝塔下诸功德墙壁,率皆称旨。又敕令访求民间图画,继蒙恩奖。相国寺大殿后《擎塔天王》,如出墙壁,及殿西《降魔变相》,其迹并存。今画院学者咸宗之,然曾未得其仿佛耳。(宋代郭若虚《图画见闻志》)
高文进善于画佛道人物。他既能够“曹衣出水”,又可以“吴带当风”,可见画技在当时是很高的。郭若虚仅以“攀附”来形容他进入宋宫廷画院,应当省略其中不雅的细节。好在高文进确实有才,在太一宫、宁寿宫、启圣殿以及相国寺等处的大型壁画中都有令皇上满意的表现。后来高文进的画在画院冠绝一时,成了宫廷画院学者效仿的模本。
假设一下,高文进、高益虽然都很有才,如果不“攀附”、不自我炒作,能够有进身的机会吗?能够有后世的名声吗?
答案可能是否定的,宋代邓椿《画继》中就记有这样一个人:
朱象先,字景初,松陵人,驰名绍圣、元符间。坡跋其画云:“能文而不求举,善画而不求售,文以达吾心,画以适吾意而已。”以其不求售也,故得之自;然世亦罕见,不知其所长也。
朱象先的文才、书画虽好,但人不求闻达于世,画不求赚得大钱,所以名声不能远播,人们并不太知道有这个才子。这是一个令人惋惜的例子。
但事情也不都是这样,还有一人就不是这种被冷落的结果:
崔白,字子西,濠梁人。工画花竹翎毛。体制清赡,作用疏通。虽以败荷凫雁得名,然于佛道鬼神、山林人兽无不精绝。凡临素多不用圬,复能不假直尺界笔为长弦挺刃。熙宁初,命白与艾宣、丁贶、葛守昌画垂拱殿御扆鹤竹各一扇,而白为首出。后恩补图画院艺学。白自以性疏阔,度不能执事,固辞之。于时上命特免雷同差遣,非御前有旨毋召。出于异恩也。然白之才格,有迈前修。但过恃主知,不能无。(宋代郭若虚《图画见闻志》)
崔白的画画得好,人的个性也强,皇帝给的官禄竟然不要。郭氏批评他是“过恃”皇帝对他的待见,我看说得未必对。崔白的做派,倒很像是纯爷们儿,一任天性,不攀名头,自在就好。尽管崔白不求“上进”,但名声依然远播。批评他的郭若虚也认为“白之才格,有迈前修”,评价他的艺术造化是超过前贤大师的。在后人眼里,崔白知名度并不亚于宋时宫廷名著画家黄荃。可见,实力才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口碑。试想,假如高文进、高益等人并无真实力,只靠攀附和炒作浪得虚名,恐怕早已湮没在历史之中了。
米元章云:“吾书无王右军一点俗气。”乃其收王略帖,何珍重如是。又云:见文皇真迹,使人气慑,不能临写。真英雄欺人哉。然自唐以后,未有能过元章书者。虽赵文敏亦于元章叹服曰:“今人去古远矣。”(明代董其昌《画禅室随笔》)
米芾的书法境界固然很高,但也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他对晋人的崇尚是无以复加的,以至于把自己的斋号命名为“宝晋斋”。可他偏偏说出“吾书无王右军一点俗气”这样的话,显然是故意大言欺人,说他“米颠”是颠语炒作也未尝不可。艺术这事儿是真性发作,外人看着不像常人,责怪他“癫狂”,那是不知道的人在误解;但如果为“颠”而“颠”,与真性并不搭界,那就是自己误入歧途了。米芾虽有装颠的毛病,但私底下还是真实清醒的。董其昌看出了破绽,所以讥讽他说:“乃其收王略帖,何珍重如是。”后世的赵孟,念叨米芾时会感叹道:“今人去古远矣。”这是宽容米芾的假颠呢?还是佩服米芾的书艺呢?我看都是。这就是大艺术家的胸怀和眼光,那是着眼于他人的艺术成就,而不是计恨于他人艺术之外的瑕疵。最可怜的人,是不知精研大家艺术,却热衷精仿大家瑕疵,其终究是应了“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这话。今天为“颠”而“颠”的急功近利者不在少数,殊不知“米颠”还有“珍重”的一面,那才是真货。
有罗克昭者,休宁人,画不逮汤朱,顾盼自喜。其乡人程不山谓其六法不一获,十二忌,独得乎全,知言哉!乎日奉吴人张宗苍为师。夫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张出黄尊古之门,而尊古得力于麓台,师学渊源,一望而见。宗苍、尊古之画,板浊窒滞。弥伽居士,《画征录》论之详矣。即步趋则效,不失毫厘,亦艺林所不取。而况尚不能形似乎?生平好为人师,凡江南北作画者,必曰“某吾弟子也,某私淑于予者也”。及观其人之画,则皆大过于罗,并有引之觌面而不相识者,以是人皆鄙之。然半生遭际,颇得力于绘事:其同里有大僚,适餐授馆,延之作画,为纳赀入方略馆,后由指挥仕至州牧而卒。(清代俞蛟《读画闲评》)
俞蛟用文字勾画了一个十足的小人。此君师法本朝技艺平平的画家(汤谦、朱文震)而且还不如,照樣沾沾自喜。这眼界不高,已是一病。此君又好为人师,大言欺世,但凡见画得好的,不管认识不认识,都说是自己的学生,借以抬高自己,有好事者引来相见,竟然根本不认得。这炒作无底线,又是一病。但是,此君却凭借画画,结交大佬,酒食无忧,后来还买了个清廷军机处方略馆的差事,最后官位做到湖北兴州的州牧。凭着投机炒作,竟然活得风光水滑,其实这也是一病。只是,这生病的是社会。孔子说:“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又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孔子一辈子没挣着大钱,却是个大写的人。孔子之大,大在经过2500年还没被人忘记,大在历经数次大规模封杀也没被打倒。罗氏之小,小在头钻浮世之利、尾遭后世之讥。也许,后人要讥讽都想不起来他。
(罗聘,字两峰),昔钱塘金寿门(金农)树帜骚坛,声称藉甚,客居维阳,两峰师事之惟谨。每作画,乞其题咏,署名其上,时人遂争购之。其实寿门固未尝有片楮寸缣之作。(清代俞蛟《读画闲评》)
有关金农作品多由罗聘等弟子代笔的说法,不独是《读画闲评》一家,看来是真有其事。其实,金农自己也隐约承认此事,如他的《自写真题记》中记:“(罗聘)近学予画梅,梅格戍削,中有古意。有时为予作暗香疏影之态,以应四方求索者。虽鉴别若勾处士,亦不复辨识非予之残煤秃管也。”“明四家”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都有代笔之作,这在书画鉴定界是人所共知的。学生借老师之名而早卖画,老师倚学生之力而多卖画,互相炒作,共同得利。实际上,这不是艺术创作,而是产品制作。在此,且不说艺德如何、商道如何。仅就艺术创作本身而言,如果总是浮在功利的心态,能深入艺道而通灵犀吗?我想,“明四家”、清扬州八怪要以画为生计,银子当然很重要,但他们绝不是只为银子,徒有小技而不通大道的匠人。他们的价值,其实是体现在道与技的独创和高明上的。而代笔、仿作 都不过是谋财的浮笔。想想,齐白石六十变法,黄宾虹七十变色,都是在探求这种独创和高明。这种治艺态度,才不枉了学画一场。其实,最可悲的也许还不是模仿别人,而是模仿自己。一些画家,勤奋一段之后有了建树,盛名之下不再精进,靠自我重复而卖名,美其名曰自有“符号”。久后江郎才尽,必然退化成平平匠人。
以上略举过去画坛故事,对今天的艺人其实并不足以为戒,因为现在新招、大招多了去了。可是,作为一个画画的人,最大、最靠谱的真招是啥,还是好好画画。
别可惜了自己。
(尚晓周/河南美术出版社副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