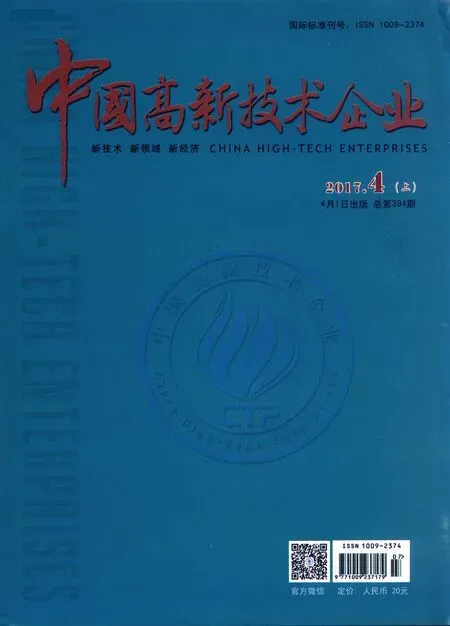对美国《拜杜法案》与中国高校技术转移的再思考
2013-04-29岳琳唐素琴
岳琳 唐素琴
摘要:美国《拜杜法案》自颁布实施以来一直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但随着专利改革实施的进展和专利产品成本控制的需求以及重新定位高校社会作用的倡导,对该法案引起的问题成为研究的一大反思。文章结合美国对实施《拜杜法案》的讨论,从公私利益矛盾、专利管理成本、实证数据的再分析、影响技术转移的其他因素以及对学术研究的影响五个方面探讨《拜杜法案》成果背后存在的问题,以期对我国类似的立法和技术转移活动起到借鉴作用。
关键词:《拜杜法案》;高校技术转移;公私利益;专利管理;转移渠道
中图分类号:D9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374(2013)10-0010-03
1 研究背景
《拜杜法案》(Bayh-DoleAct)是美国1980年颁布的《大学和小企业专利程序法案》(University and Small Business Patent Procedures Act)的简称。其因对政府资助项目科研成果知识产权归属制度的创新而备受盛赞。《拜杜法案》出台后,对亚洲、欧洲和拉丁美洲等诸多国家的立法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
《拜杜法案》颁布实施后,在美国国内引起了强烈反响,褒贬不一。BIO调查显示,美国高校专利数目是法案出台前的10倍,产学研合作为国家经济贡献了1870亿美元,为GNP做出了4570亿美元的贡献。以高校科研成果为核心的6000多家新公司成立营业。但是也有反对意见认为,尽管数以万计的报告试图说明法案大大提高了政府资助研发成果的技术进步和商业转化,高校的角色定位以及技术的发展状况却已经颠覆了法案最初的立法目的。
目前,随着专利改革的进展和专利产品成本控制的需求,在美国国内,《拜杜法案》再次成为人们审视的对象,因其知识产权保护过度而非保护不足所致交易成本增长趋势日益明显。文章结合美国国内对实施《拜杜法案》的讨论,主要从公私利益矛盾、专利管理成本、实证数据的再分析、影响技术转移的其他因素以及对学术研究的影响五个方面探讨《拜杜法案》成果背后存在的问题,以期对我国类似的立法和技术转移活动起到全面的借鉴作用。
2 《拜杜法案》的五个问题反思
2.1 公私利益矛盾再思考
自立法之初,《拜杜法案》“双重征税”的问题就引起极大关注。纳税人认为将税收资助的科研成果商业化产出的产品再卖给纳税人,是“双重征税”。赞成者则认为,加速科研成果的私有化可以鼓励创新,为公众生产更多更好的产品,同时基于技术转移而成立的公司提供了更多工作岗位。但是,赞成者的意见有时难以立足。以药品的研发和销售为例:政府资助研究推动了生物制药行业的发展,然而药品,尤其是新药品的价格居高不下,公众的薪水两次贡献给药品专利权人。
不难看出,《拜杜法案》内在的立法性质难以调和公私利益的矛盾。这和专利权通过设立保护期限来平衡公共利益和权利垄断的立法考虑如出一辙。《拜杜法案》的特殊性就在于其保护对象是政府资助的研发成果。由税收支持的国家财政资助的研究成果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本应由公众享受,《拜杜法案》却将专利权归属赋予高校及其研究人员并且允许其通过转让专利获取私人的经济利益。《拜杜法案》采取了“介入权”平衡公私利益。但是 “介入权”只有在企业未能有效实施专利或关系公众健康、国家安全的情形下才能启动,并不会干涉产品价格。《拜杜法案》无法解决专利许可带来的最直接影响公共利益的价格问题。而且,立法后的三十年里,“介入权”从未真正执行过。
《拜杜法案》的立法考虑是,由于高校和企业怠于参与技术转移活动,国家才从法律层面通过权利和利益分配激励科研人员和私人企业进行技术转移。那些对于科学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却缺乏短期商业价值的基础研究,企业只会避之不及。《拜杜法案》通过后,专利许可数量最多的哥伦比亚大学、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的前五项获利最高的专利,都来自生物医学或生物技术领域,均是所谓的具有商业价值的研发成果,采用了非独占的授权方式进行技术转移。比如,由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共同所有的CohenBoyer基因专利,获得2.5亿美元专利使用费。不过,无论是否采取专利许可形式,都不会影响基因专利的商业化应用。事实似乎并没有验证《拜杜法案》通过提供专利权属促进商业化的立法目的。
这里有两种假设:第一种假设是,对于具有商业价值的政府资助研发的技术成果,即使是国家拥有专利所有权,也不会影响企业购买和实施专利的需求,由国家收取专利使用费,部分奖励给发明人,剩余部分留存做财政收入提供其他公共物品,这样无疑是公平的。国家需要做的是设立一个专门的专利技术转移部门。而对于那些缺少商业价值的基础研究,无论权利归属国家还是私人,似乎都难以促成技术转移。如此看来,《拜杜法案》只是提高了技术转移的效率,却难以实现其大规模刺激研究成果商业化的目的。第二种假设是,那些具有商业价值的科研,完全可以采取产学研实验室合作或者企业出资资助等形式完成,直接赋予企业使用专利的权利。因此,政府的财政资助应集中于那些对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长期有利的不太“热门”的基础研究。在这种假设中,《拜杜法案》似乎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当然,上述只是假设,毕竟判断研究成果的“商业价值”并没有白底黑字的标准,因此在技术转移里还应当有一项“营销”的技术。专利权归属高校以后,高校的技术转移办公室无疑最有动力去“销售”技术成果。
2.2 专利利润少,管理成本高
《拜杜法案》实施过程中还面临管理成本过高的问题。高校纷纷建立起技术转移办公室(OTL)管理专利许可与技术转移。OTL负责申请发明专利,寻找企业,开展专利许可谈判,签订许可协议,分配许可收入。《拜杜法案》规定收取的专利许可使用费部分奖励给发明人,部分用于科研投入。通过《拜杜法案》获得大量专利许可费的高校仅仅局限在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大学、加州大学等几所顶尖高校的远近闻名的科研成果。对大部分高校而言,专利许可费只是研发投入的3%。从中减去日常运营费用和法律费用,这个数字更低。因为专利许可的高成本,很多OTL勉强收支平衡而已。
除此之外,产业和高校常常陷入利益冲突,动辄几百万美元高昂的诉讼费增加了技术转移的管理成本,成为阻碍科研的又一因素。《拜杜法案》在过度提倡专利申请和许可的同时将矛盾转化给了高校和产业,尤其是在信息产业,OTL常常由于维护专利成果与专利许可公司发生纠纷。比如康奈尔高校就某项加速计算机运算速度的技术起诉Hewlett Packard公司。伊利诺斯大学就扁板显示技术起诉FujitSu公司。《拜杜法案》中的利润导向降低了高校和企业之间的信任度,反而阻碍了二者合作,违背了立法目的。
2.3 忽略其他技术转移渠道
《拜杜法案》的实施和提高技术转移,是典型的蛋生鸡、鸡生蛋的问题。高校的研究成果通过一系列渠道转化到生产领域,包括刊物、会议、咨询、雇佣大学生等。Cohen的研究成果表明专利许可并不是所有渠道中最重要的。即使是在《拜杜法案》发挥最大作用的制药领域中,专利许可的作用也比不上其他方式。高校科研与行业创新联系最紧密的是工程技术和应用科学的研究,而物理和数学等基础学科的研究通常在一段时间之后,才能产生商业效益。而且,这些研究成果需要首先和应用技术相结合,比如新材料应用、电子工程等,从而达到技术转移的目的。另外,除了生物制药以外,其余的科研成果是在生产过程中推动新的行业研发项目。学术研究极少直接促成生产,而是为公司的研发设备提供方法和规则。
事实上,许多学者质疑,《拜杜法案》是否真的推动了科学研究,还是仅仅增加了企业和专利的授权数量。PLOS Biology杂志调查发现:无论是《拜杜法案》颁布后的专利授权和许可趋势,还是对技术商业化转移的调查研究都无法证实《拜杜法案》加速了技术转移和商业化。。
这一发现也激发了对独占许可的争议,那些原本在公共领域中的研究成果是否有成为独占许可的价值。科研成果专利化的支持者认为在实施《拜杜法案》之前,大部分高校的科研成果都未能有效利用。这种观点并不正确。因为,当时的科研成果往往通过传统的开放的学术渠道比如科研期刊、学术会议、雇佣毕业生等方式进入到商业领域,或者是广泛传播给其他研究人员。
2.4 科研与利益再抗衡
《拜杜法案》在立法之时似乎低估了个人经济利益对高校科研人员心理上的影响以及产生的不良后果。
首先,《拜杜法案》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科学创新的自由交流。以前,研究出成果后即公开发表,以供借鉴利用或共同研究。高校科研人员认可经济利益后,都希望自己最先做出先进的成果,获得报酬。同一实验室的人员彼此成了竞争对手,怠于分享研究成果或信息数据,甚至在完成商业转化之前推迟发表重要的科研成果。比如,在生命科学领域,约有20%的科研人员为获得及许可专利将科研成果至少推迟六个月发表。这些成果和信息,恰恰是使用纳税人的钱完成的,既阻碍了科学进步,又损害了公众利益。另外,在科研人员以入股的方式进行利益分配的情况下,科研人员可能出于对个人经济利益的考虑,忽略其他科研和教学任务,甚至可能借助高校的实验设备以及学生劳力,为自己的公司谋取利益,或者直接将成果转让给企业而不上报高校,侵害了研究进度、高校利益和公众利益。
同时,对专利报酬利益的追逐使得高校以及科研机构的科研重心日趋于可专利领域,从而导致基础研究无人问津。久而久之,公共领域知识日渐耗竭而造成后续研究困难。《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评论道,目前高校决定科研项目的是可获利性,而不再重视知识价值的传播与传承。高校研究人员倾向于短期可获利的具有商业转化价值的应用研究(这一点也说明了生物技术专利持续增长的原因)。
另外,《拜杜法案》的核心激励措施是赋予专利许可的权利。专利技术许可,尤其是独占许可,可能阻碍了其他研究人员从事相关科研。最有争议的一个案子是关于Myriad Genetic公司的。犹他大学发现了有关遗传乳房癌的BRCA1和BRCA2基因序列,并将其作为独占许可签约给一个刚成立的Myriad公司。Myriad公司在获得独占许可后垄断了该病的诊断服务,定价约为2300美元/次。同时,Myriad公司起诉其他希望使用BRCA1和BRCA2基因序列的研究机构。宾夕法尼亚州立高校遗传实验室的Haig Kazazian教授使用BRCA1和BRCA2基因序列进行相关研究,目的是开发出更便宜的检验程序,大概只需要1800美元/次,但是却被Myriad公司以侵犯专利权为由起诉。Myriad公司的例子表明了《拜杜法案》固有的问题,Myriad公司获得的研究成果大概耗费了460万美元的联邦资助经费,通常像这样的基础研究可以推动后续一系列研究,但是一旦由一个公司获得独占许可后,便切断了其他研究者使用研究成果的渠道。
从高校层面而言,《拜杜法案》中规定高校可以获取专利费,按比例奖励给专利发明人,剩余部分用于研发投入。从美国高校的实践来看,由各高校自行制定利益分配方法,缺乏统一的政策。专利发明人和高校专利管理部门常常就利益分配问题发生纠纷。《拜杜法案》允许扣除特定的专利许可管理费用后,其余分配给发明人。法案并未限制高校进行科研和教学的投入,只不过高校一般都将其作为管理费用留存,从公益角度来看,这样做是自私的。
2.5 成果的相关统计数据再分析
中国研究《拜杜法案》的论文通常引用一组数据“在美国实施《拜杜法案》之前,联邦政法机构拥有28000件专利,其中只有5%转化为商业产品”来说明《拜杜法案》实施的必要性。这一数据最早来源于1976年的一项调查,从一定意义上讲,是具有误导性的。
1976年Harbridge House咨询公司统计了2800项受美国政府资助研究成果的使用情况,资料是由国防部提供的,当时国防部资助的项目可以由受资助人选择保留项目成果所有权,被选择的大都是具有商业价值的研究成果,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统计数据的客观性和比较性。公司的商业化经验、技术和公众需求的相关性、商业化程度等都制约着统计结果。而且,这28000件专利大多来自于联邦政府资助的公司,而非高校。与此相对的是,当时的健康、教育、福利等部门拥有的325项专利中,授权率高达23%。由此看来,被反复提及的5%的数据,其实是基于政府所有专利中不适宜进行技术转移的专利而言的,过于笼统,以偏概全。通过对23%和5%两个数据的比较,不难看出,研究成果本身的商业价值和可转移性决定了技术转移率。此外,政府拥有的专利,有些也会未授权就被民间采用,而政府研发成果未申请专利的,也可能被商业化应用,这两种情形都未纳入官方统计。
1980年通过《拜杜法案》后,许多调查数据表明高校申请专利和授权的数量迅速增加。这其中大部分是生物科学相关的专利。有研究认为导致生物技术专利增加的原因是:20世纪60年代末兴起的生物医学基础研究、生物科学研究以及1980年以后美国的专利政策开始允许生物医学和生物科学研究成果申请专利的变革,激励了相关研究和专利申请。而且,由于生物医学技术的实用性强,市场需求大,即使没有《拜杜法案》对专利权属的配置,生物医学技术进行转移并非难事。所以,就专利数量的增加来评价《拜杜法案》的成果并不合理。
3 结语
在《拜杜法案》实施三十几年的进程里,美国国会对《拜杜法案》做过数次修改,美国高校自身也在对《拜杜法案》进行了多方位的反思。本文上述分析正是对近年来美国国内对《拜杜法案》反思的归纳。近年来,国内介绍《拜杜法案》的文章增幅迅速。尽管国内也有一些对《拜杜法案》进行反思性的研究,但绝大多数文章都遵循着立法背景+主要内容+实施后的数据+对我国的启示的研究模式,一味认为《拜杜法案》对国内的科研体系有促进意义。
然而,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与美国并不相同,如果完全照搬,对其法案移植中的立法模式与制度选择欠缺基于现实国情的利弊权衡与反思。基于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状况,适当地根据自身情况进行法案修正是非常必要的。在此,需要着力解决五个问题:公私利益矛盾的平衡;专利管理成本的降低;多种渠道的利用;科研的长效发展;法案效用的评估方式。
现阶段,我国已经通过科技进步法20条和21条,很大程度上借鉴了《拜杜法案》的内容。结合我国国情,需要全面认识《拜杜法案》,找出相关制约因素,为国内大学和科研院所研究成果产业化提供客观有效的制度。
参考文献
[1] Anthony, Bhaven N. Sampat, Arti K. Rai, and Robert C. 2008.“Is Bayh-Dole Good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Lessons from the US Experience.”PLoS Biology,6:262.
[2] Cohen WM, Nelson RR, Walsh JP.2002.“Links and impacts: The influence of public research on industrial R&D”[J].Management Science,48: 1-23.
[3] Nugent RA and GT Keusch.2007.“Global Health: Lessons from Bayh-Dole.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Management in Health and Agricultural Innovation. A Handbook of Best Practices, edited by R. Mahoney A. Krattiger, L. Nelsen, et al.169-96. Davis,CA.
[4] Peter S. Arno, Michael H. Davis. 2000. “Why Dont We Enforce Existing Drug Price Control? The Unrecognized and Unenforced Reasonable Pricing Requirements Imposes upon Patents Deriving in Whole or in Part from Federally Funded Research”. Tul.L.Rev7: 631.
[5] Rai AK. 2007.“The role of federally-funded university
research in the patent system”. Hearing before the United States Senate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 110th Congress.
[6] 徐棣枫.威斯康星之路与WARF奇迹:高校技术转移实现模式选择[J].南京大学学报,2009,(3).
[7] 傅正华.Bayh-Dole法案出台的背景及启示[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9,(3).
[8] BIO Report. Survey Reveal Importance of Academic Tech Licensing to US Economy[R].
[9] Janet R.Dupree. 2008. When Academia Puts Profit Ahead of Wonder[N]. N.Y. Times.
[10] Faye Flam, Philadelphia Enquirer 2010.“The case for and against the patenting of genes”.
作者简介:岳琳(1988-),女,山东济南人,中国科学院大学法律与知识产权系学生,法学硕士,研究方向:知识产权法和科技法;唐素琴(1968-),女(蒙古族),内蒙古赤峰人,中国科学院大学法律与知识产权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知识产权法和科技法。
(责任编辑:黄银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