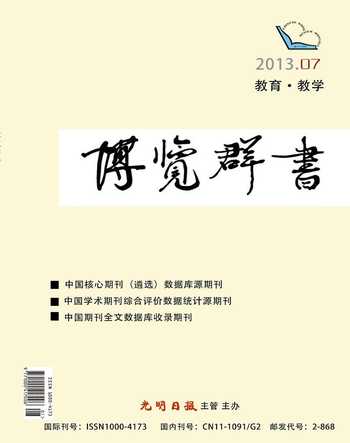浅谈儒家诗学之“立言”特点
2013-04-29莫燕军
摘 要:纵观中国传统诗学,儒家诗学是以“立言”为主要特点,其言与意之关系托寓于经学文本传达后世,这大致可以看做是儒家所持的言意态度。本文通过分析儒家诗学“立言”的特点以阐明“立象以尽意”与“赋、比、兴”的功能以及影响,从而在整体上可看出儒家诗学对中国文艺精神和相关审美范畴形成的作用特点。
关键词:儒家诗学;立言;赋比兴
西方哲学发展到20世纪,语言学才成为“显学”,但是中国哲学却不一样,它在其初始阶段——先秦时期,语言就成为各家关注的焦点和哲学探讨的中心话语。在这场围绕着语言的聚讼纷争中,语言问题就如同一个多棱镜,将中国哲学中有关语言与本体、语言与认知、语言与价值等问题聚焦、离析,折射出各家学说的要义。其中,儒、道作为传统文化的两大主流,它们在言意问题上的态度和策略,对中国文艺精神和相关审美范畴的形成都起到了直接的影响。本文主要讨论的是儒家诗学的“立言”特点。
一、言与意的关系问题
从中国哲学高度来看,“意”有两种意义指向:认识论指向和本体论指向。其中,认识论意义上的“意”是可以明言的;从道而来的本体论意义上的“意”则是不可言尽的。如在孔子那里“道”的意义就比较驳杂,既有从伦理学、认识论等意义上谈论的非常道,也有本体意义上的道。如孔子对《诗》的推崇,就说过:“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
这也说明了《诗》除了具备重要的认知功能、政教功能和社会功能之外,更能引发“兴”的审美感悟,从中领悟到本体意义的常道,达到学诗的最高境界。另外,像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吾道一以贯之”等的“道”则是明确从本体论意义来谈论的。至于“默而识之”,“予欲无言”则是体会常道的方法和反应。而在老庄那里就几乎全是从常道的角度来谈论意的不可传达性。纵观中国传统诗学,几乎不是以认识论旨向的意为目的,而基本上是以传达从道而出的本体之意为审美鹄的。儒家诗学崇尚在经典文本上的“立言”,在“汉武帝罢黔百家,表章‘六经,孔教已定于一尊矣”之后[1],在此过程中,儒家由肯定语言与实在的二元对应关系出发,肯定言(书)能明道(最高之“意”);道家则从打破儒、墨固定的名实体制出发,而追求意对言的绝对超越,由此形成了“立言”与“贵意”的双向对峙格局。儒家在语言观及其方法论上的崇“有”与道家在语言观和方法论上的贵“无”,各从正、负两端入手对言意问题做了有效的揭蔽。
令人欣慰的是,儒道之间的重大分歧并未造成中国文化的分裂与片面发展,倒是中华文化巨大的开放与包容性使儒、道与作为外来文化的佛学之间互为激荡、相涵相包,最终在中国文学美学领域开辟出“意象”乃至“意境”等一片独有的特别的审美领域。接下来本文重点讨论儒家诗学的“立言”特点。
二、儒家诗学“立言”的表现
春秋之际,言辞在国家政治、外交,个人社会交际等各方面已经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中就记载了穆叔“三不朽”之说,将立言(有关德教、政教的言辞)置于与立德、立功同样不朽的地位。儒家诗学把“立言”认同为主体存在的第一要义,因此,《谷梁传》声称:“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为人。”而通过诗歌创作来进行“美刺”和通过赋诗达到言志的目的,以及从听诗的角度来“观志”、“观风”,也已成为当时上层社会一种普遍的社会观念和文化习俗。《左传》、《国语》当中就有大量此类政治、外交方面的记载。孔子作为正统文化的继承者自然表现出对言辞的高度重视与肯定,所谓“育以足志,文以足盲”。孔子坚信“有德者必有言”,并认为适当的言辞有助于完成育语的表达。反之,则“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达不到良好的效果。就“名”、“言”的现实功能来说,儒家与当时的墨、法一样基本上都是持一种肯定和实用主义的态度,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抽象精神。
语言作为使人澄明于这个世界的手段,其构成了人在潜意识中塑造自我的最重要的文化语境,这个文化语境又直接塑造了诗学批评主体的文化心理[3],在孔子看来,名称对应着对象,而词语的意义及其本质也就等同于其所指称的实体,就此而言,语言的本性是能够起到指称事物,规范并且调整、维护现实世界秩序的作用。否则,针对春秋末期所出现的各种混乱的社会伦常和政治秩序,热切希望恢复周礼的孔子也不会着意先从正名开始,来整饬种种“名不符实”、“名实淆乱”的现状。显然在孔子看来,“正名”的重要性在于维护并实现语言与实在的二元对应,这是国家与社会一系列正常运转的出发点和保证,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
孔于对名言的肯定和重视,除了认识到语言重要的现实功能以外,也与他个人对文化典章的热爱与信仰分不开。孔子尊崇先贤,以“继文王周公之业”为神圣之使命,毕生心血全在整理、弘扬三代(主要是西周)典籍,《庄子·天运》中记载:“孔子谓老聃日:‘丘治诗书易礼乐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论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在他看来,六经已将圣人之道包举无遗,故其毕生事业就在于绍述先王之道,推而广之,从而开创了儒门一派将解释作为再创造的治学办法。孔子之后,儒家代表人物孟子又以继孔子之业为己任,《史记》中记载:“孟子序《诗》、《书》,述仲尼之意。”元儒的另一代表苟子更是强调自觉学习经典、积聚礼仪的重要性,认为这是成就君子、圣人之所必然。他说:“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道归是矣。《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天下之道毕是矣。”(《苟子·儒效》)天下之道早已在上古圣人那里探究成功了,并体现于圣人的情志、事迹等言行当中,而这些又都见之于经典。
因此,要想得道,就是要认真学习经典,于经典当中索求之。儒家自孔子首創“述而不作”的传统以来到荀子可以说达到了高潮,为儒家诗学开了宗经、征圣、明道等论调的先河。刘勰的“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以明道”正是这一经学传统在文学上的主张。汉代班固释“儒”日:“……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尊师仲尼,以重其言。”(《汉书·艺文志》)可见,儒家者流无不崇奉经典的权威意义,恪守着“畏圣人之言”的师训。儒门后学虽几经浮沉“儒分为八”;魏晋时期,玄学“援道入儒”,破除了汉儒对经书名物训诂的作法;宋明时期理学、心学又杂以佛老释儒,对儒家正义再作了新的阐述,但无论如何,都还是以“六经”或(“五经”)为本。儒家的这种宗经态度大致可以从明朝时朱熹的话中再次得到佐证:“圣人千言万语,只是说个当然之理。恐人不晓,又笔之于书。自书契以来,二典、三谟、伊尹、武王、箕子、周公、孔孟都只是如此,可谓尽矣。只就文字间求之,句句皆是。”“读书以观圣贤之意,因圣贤之意以观自然之理。”(《朱子语类·读书法》)可见,从圣人之言(书)可通乎圣人之心志,由圣人之心志又可以达于天下大道,这是儒家所坚信的明道的途径。正是出于对文本(语言)的确信,两千年来儒家以言传身教的方式,稳稳占据了中国文化的主流。在道(自然之理)、意、言(书)三者之间,儒家信奉道是意的本源,言是意的表现,正如王先谦集解对“诗言是其志”的阐释:“是儒之志。”自然之理(道)、圣贤之意可以托寓于经学文本传达后世,这大致可以看做是儒家所持的言意态度。
三、儒家诗学“立言”的功能与影响
儒家在肯定名言的指称和表意功能的同时,其实也意识到了语言的局限性,早在儒家六经之首的《易传》《系辞上》中就已首唱:“子日: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可说是率先看到了问题的所在,并随之提出了解决之法:“子日:‘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以“象”作为弥补言与意之间巨大鸿沟的中介。《易》之初仅有图像并无文字可读,仅仅依靠易象的流转变化就建构起了一个涵盖宇宙人生的符号系统,可以说“象”是整部《易》把握和解释世界的本体性范畴。《系辞传》说:“《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唐代经学家孔颖达在《周易正义》中解释说:
《易》卦者,写万物之形象,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谓卦为万物象者,法像万物,犹若乾卦之象法像于天也。
易“象”的特点是既不表示具体的特殊之物,也不表示抽象的普遍之物,作为创造性的再现,易“象”不是对事物表象的简单摹写,它来源于圣人的“观物取象”:
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vT,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易传·系辞传》)
经过古代圣人仰观俯察、化繁为简从客观世界中抽象出阴阳符号,这个符号就是卦象。这是通过从不同角度、动态的直接观察、感受和体验之后,在“观”的基础上的一种提炼、概括和创造,因而易“象”不仅是效法天地万物的繁杂形态,而且效法了物质的运动。《系辞》云: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系辞焉而明之,动在其中矣,吉凶悔吝生乎动者也。
从中可以见出:“‘象是‘非实体、‘非概念的,也就是具有非对象性、非现成性的特点,……而且‘象是动态的,是‘流动转化的,因而‘象具有不同层次。”如八卦就是按照事物的形态、结构、属性等,把世间复杂的事物分成了八大类符号,后扩充为六十四卦,每一卦包括卦符、卦名、卦辞、爻辞、爻题,在卦象的流转变化之间涉及了自然现象、历史人物事件、人事行为得失、吉凶断语等。八卦的基本属性是:乾为健,坤为顺,震为动,巽为入,坎为险,离为丽,艮为止,兑为说。经由会意、假借取象,从而衍生成自然之象:乾为天,坤为地,震为雷,巽为风,坎为水,离为火,艮为山,兑为泽。近取诸身又衍生成人体之象:乾为首,坤为腹,震为足,巽为股,坎为耳,离为目,艮为手,兑为口。……由此可见,在《易传》这里,卦象作为极为抽象的阴阳线条的组合,其实质是内涵丰富、象征物质世界的符号。正是由于八卦和六十四卦效法天地万物,故八卦和六十四卦具有了物性,包含了天地阴阳之道。这样,通过阴阳爻、四象、八卦、六十四卦以及卦辞和爻辞共同组成一个贯通各个层次的立体解释体系。正是“象的流动与转化”将个别联系于宇宙整体的动态、开放之中,显示出相互贯通的部分与全体。它把自然万物、社会人事、情志意念,天、地、人交融起来,达到对生生不息的宇宙有机整体的“真”与善的显露,从而达到表显万物内在的特性(“万物之情”)和宇宙间深奥微妙的道理(“天下之赜”)。由阴阳两仪之象、四象之象、八卦之象、六十四卦之象以及爻象、数字等所共同组成的解释体系,就是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的天地万物(形象)的模拟、写照与反映。正如《系辞》所云:
《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材而兩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材之道也。
“赋比兴”最早见于《周礼·春官》中记载,大师“教六诗:日风、日赋、日比、日兴、日雅、日颂”,后为战国儒家学者总结为《诗经》的艺术经验所特有的一组美学范畴。当代学者叶嘉莹对“赋比兴”做了深入而有成就的分析:“‘六诗或‘六义中之所谓‘赋、‘比、‘兴,其所代表的是诗歌创作时感发作用之由来与性质的基本区分,这种区分本来至为原始,至为简单,要而言之,则中国诗歌原是以抒写情志为主的,情志之感动,由来有二,一者由于自然界之感发,一者由于人事界之感发。至于表达此种感发之方式则有三,一为直接抒写(即物即心),二为借物为喻(心在物先),三为因物起兴(物在心先),三者皆重形象之表达,皆以形象触引读者之感发……”从心物关系来看,实际上“赋比兴”可视为文学创作心化过程中的三种不同的表现方式。它是在诗歌艺术中就“意”(情意)与“象”(形象)关系的分析和概括,是《易传》“立象以尽意”这一命题在审美领域中的进一步展开。叶嘉莹指出,“赋比兴”作为中国式的审美创作机制,相对于西方诗论中繁复的思维方法、技巧与模式的术语分类来说,“兴”的自然、无意和不自觉的触引,这是一种独具中国特色的特点之一,其文化之根是要追溯到“易象”上去的。文学史上从创作来谈审美起兴的不在少数,像旧题贾岛的《二南密旨》说:“谓外感于物,内动于情,情不可遏,故日兴。”把“兴”归结为一种物感后的强烈的创作冲动。再如旧署王昌龄《诗格》云:“纸笔墨常须随身,兴来即录。江山满怀,合而生兴,须屏绝事务,专任情兴”;邵雍《谈诗吟》云“兴来如宿构,未始用雕琢”;杨万里《春晚往永和》云“郊行聊着眼,兴到漫成诗”;谢榛《四溟诗话》云“凡作诗,悲欢皆由乎兴,非兴则造语弗工”……都指出在创作发生的最初阶段,借物象的触引,所导致的一种真淳自然的创作冲动。唐五代时由殷璠提出了“兴象”这一概念,它是“兴”这种方式产生和结构的意象,作为意象当中的一种,“兴象”突出的是“意”与“象”的妙合无垠,不显出外在拼合的著力。清代纪昀对之的评价是“自然流出”、“兴象天然”。
儒家经学的隐喻话语权力借助批评主体对客体文化的释放,而像这样从文本客观审美效果和对读者的重视来解读“兴”,至清代得到了积极的呼应,如袁枚在《随园诗话补遗》卷一中说:“惟其言之工妙,所以能使人感发而兴起;倘直率腐庸之言,能兴者其谁耶?”方东树在《昭昧詹言》卷十八中论“兴”时也强调“兴在象外”,“言外有馀味而不尽于句中”。最为突出的要数王夫之对孔子“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这一命题所做的创见性的推进,将其重点突出转移到“可以”二字上来,提出“随所以而皆可”的自由阐释思想,认为诗歌接受者的“情”的无限多样决定了诗意阐释的色彩纷呈,所谓“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为读者在诗歌审美中积极主动的创造性活动提供了理论依据。表明阅读并非如以镜映物那样简单机械,而是世万其人,人万其心,对诗歌的解读自然也是推阐发明,缤纷万象的。“象”转化为审美范畴的“意象”,最早见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刘勰的《文心雕龙·神思》篇:“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到了唐代,“意象”作为标示艺术本体的范畴,已正式在审美领域的广泛使用。从对物象的直观妙悟到用符号图像创造“易象”,从情志蓄蕴生成审美意象到用语言文字的空灵映现,最终实现“意”与“象”的和谐统一,这大致是儒家诗学在言意问题上对中国古典诗学的重要贡献,这有利用继续深入研究中国传统哲学的深度影响。
参考文献:
[1]皮锡瑞.经学历史[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春秋谷梁传注疏[M].大连: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3]杨乃乔.“立言”与“立意”——从经学透视儒道诗学的冲突与互补[J].中国诗学研究,1998(3).
[4]荀子集解[M].上海:上海书店,1980.
[5]王树人.中国的象思维及其原创性问题[J].学术月刊,2006(1).
[6]叶嘉莹.中国古典诗歌中形象与情意之关系例说[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7]杨乃乔.“诗言志”与批评的话语权力——论儒家诗学的隐喻对经学的承诺[J].天津社会科学,1999(1).
作者简介:莫燕军(1989.3-),女,广东鹤山人,广州大学人文学院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