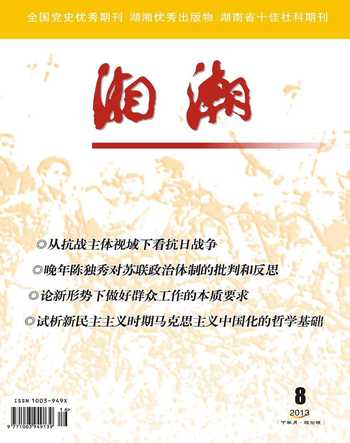朱德为何赠予徐特立“老怪物”的尊号
2013-04-29梁堂华
梁堂华


徐特立生逢满清末年,耳闻目睹帝国列强对中国野蛮侵略、清政府腐败无能,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一心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在此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他特立独行、勇于斗争的性格。在他60大寿时,老朋友朱德写了一封祝寿信,题目是《你是一个老怪物》。“老怪物”是朱德赠给徐特立的亲切尊号。一个“怪”字,点出了徐特立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苦苦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一生。
弱冠之年破产读书
1877年2月1日,徐特立出生于长沙县五美乡(今江背镇)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祖父为孙子起名“懋恂”:“懋”,指勤勉;“恂”,指诚信。老人希望孙子长大为人,一定要勤勉笃实。
由于家境贫寒,母亲早逝,年幼的徐特立从小饱尝生活的艰辛。12岁时,徐特立过继给伯祖母为孙。这时,伯祖父刚病故不久,家里仅留下30石谷的水田。伯祖母已61岁,半身瘫痪,只能靠收点租维持生活。他来到后,伯祖母很快为他娶了一个童养媳,名叫熊立诚,比他小11个月。于是,徐特立在伯祖母的教导下,一边发奋用功读书习字,一边与熊立诚操持家务,勤俭度日。
1893年,伯祖母去世,16岁的徐特立与妻子熊立诚支撑起了整个家业。为了选一个合适的职业养家糊口,他摸索了三年:最初想学医,但因找不到老师指点,惟恐误人自误,于是放弃了;又曾想以卜卦算命为业,然而发现算命人的话大多是“两可的骑墙语。由此我判定阴阳家都是走江湖的骗子”,因此决定不再去理会它。其时,人生的艰辛甚至曾使他想过学和尚及早遁入空门,却发现不少寺庙等级森严,而且明争暗斗,与世俗无异,从而放弃了皈依佛门的打算。18岁时,徐特立终于做出从文的决定,“确定教书兼习科举业”,一边在家乡收学生教蒙馆,一边勤奋读书。
然而,徐特立很快遇到了一个难题——无书可读。家中原本就没有什么藏书,借书不容易借到,买书又买不起:一部《十三经注疏》要15串,一部《庄子》也要300文,而他第一年教蒙馆所得俸金才不过3串钱,尽管后来逐渐增加到20串钱,仍是难以购置书籍。
经过反复考虑,徐特立不惜冒着成为“败家子”的风险,于20岁那年下决心做出了一个“十年破产读书”的计划。这就是,将每年教书所得的20串钱(可买25石谷)作为家里的生活开支,而将伯祖母留给他的几亩薄田,逐年变卖,专门用来买书。争取花10年时间,把书读通,但这样也就势必破产。徐特立在征得妻子同意后,果断地开始实施这一计划。但与常人有所不同的是,徐特立读书首要的目的是求学问,其次才是考科举,因此他不仅博览经史子集,也阅读传播西方文明的新书刊。他手不释卷,以“定量”、“有恒”为原则,坚持“不动笔墨不看书”的方法,以达学以致用、求得真知的目的。徐特立后来这样回忆:“我从20岁到30岁时,面前摆着习科举和求学问的歧途,又摆着或破产购书,或守财不学这两个歧途,要我抉择。我终抉择了其中之一,结果证明做对了。”弱冠之年的徐特立做出的这一决定,显现出不同于一般人的魄力与决心。
“破产读书计划”执行到第8年也就是1905年,徐特立28岁了。此时,清政府废八股,改考经义,并加历史、地理。徐特立决定去试一试,于是设法筹措了几串钱,赴岳州(今岳阳)参加会试,初试在3000名考生中名列第19名。
成功似乎已经不远,然而徐特立又面临了一个简单的难题:复试要交一元卷费,哪里去找呢?他正为此发愁的时候,同考的一位富公子表示愿意解囊相助。徐特立却不愿意接受,他断然决定不再参加复试,卷起行李踏上了归途,并口占七绝一首以言志:
丈夫落魄纵无聊,壮志依然抑九霄;
非同泽柳新梯弱,偶受春风即折腰。
为了表现自己卓然独立、不愿同于流俗、出污泥而不染的清高思想,他决定将自己的名字“懋恂”改为“特立”,立志走出一条不同寻常的人生道路。
而立之年一心办学
虽然放弃了复试,徐特立的名声却不胫而走,各处学堂争相聘用,许多学生慕名求教。他教蒙馆的年薪升至60串,除维持妻室儿女的温饱外,还略有节余。然而,徐特立却并不安心于当一个农村塾师,更不迷恋于个人的温饱生活。他觉得“除养家而外还有余力的人,其余力之来源,必然是得到社会的帮助,应该还之于社会”。他决心到更为广阔的天地中去进行新的学习,探寻救国救民的道路。
1905年3月,他考入同盟会会员周震鳞设在长沙城里的宁乡驻省中学师范速成班,在这里接受新式教育,学习自然科学、教育学以及西洋史、东洋史等课程,并且深受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影响,立下了教育救国的宏愿。师范速成班毕业后,徐特立与好友姜济寰等在离长沙城15公里的榔梨镇创办了一所新式学校梨江高等小学堂。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徐特立积极推动长沙起义,起义成功后曾担任湖南省临时议会副议长、湖南省教育厅科长等职务,然而官场的腐败使他很快感到失望和愤慨。他决心回到教育界,用教育来改革人心。他接受好友、长沙县首任知事姜济寰的邀请,在艰苦的条件下创办了长沙师范学校,为长沙县培养了一大批急需的师资。
为了发展乡村教育,1912年,徐特立拿出自己在城里教书所得的部分薪金,筹建了五美乡第一初级小学堂,免费吸收贫苦子弟入学。这是长沙县最早办起来的一所初级小学校。由于这是一所新式学校,在办学中曾遭受过地方顽固势力的阻挠和破坏,甚至校舍都被迫一再搬迁。最后,为了解决校舍的困难,徐特立征得妻子熊立诚的同意,腾出家里用老屋改建的一栋较为宽敞的新瓦房,作为校舍。他还另筹经费,扩建了两间教室。家人则住进老屋旁边新搭的两间茅屋,并从旁门出入,以此不影响学校教学。在他的带动下,五美乡后来办起了50余所国民小学(或教学点),极大地促进了当地教育的发展。
据史学家考证,1919以前的长沙教育,差不多都是徐特立一手办起来的。那时长沙小学校的所有教员大都是经他培训过,基于此,徐特立在长沙教育界享有“长沙王”之美誉。

不惑之年勤工俭学
1919年7月,已满42岁,步入43岁的徐特立为求成为“一个有学问的新人物”,准备赴法勤工俭学。面对一些亲友劝他不要“到外国去做拄拐棍的学生”的说法,徐特立诚恳地说:“一般人都说年老者不能求学。年老的人多半在社会上有些权柄,倘若全不求学,社会上受害就不小,……我今年43岁,不觉就到44、45,一混60岁来了。到了60岁,还同43岁时一样无学问,这17年,岂不冤枉过了日子?这17年做的事情,岂不全无进步了?到了60岁时来悔,那就更迟了,何不就从今日学起呢?”
11月,当徐特立到达法国马赛时,华法教育会派来接待的人,看到这位年纪大、声望高的湖南教育家竟然也和年轻人一起来法国勤工俭学,感到非常惊讶。主持华法教育会的李石曾,还特地单独约见了他。
在法期间,徐特立谢绝一切特别的待遇,坚持与年轻的同学一起生活、一起学习、一起做工,甚至向比他小得多的同学学习法文。他说:“只要学生不嫌我老,肯教我法文,我就算年老,也是一个进步的老人。”他首先补习法语,随后到一个钢铁厂半工半读,后来考入巴黎大学选学数学和物理。他还抓住一切机会,调查了解法、德、比等国的社会问题、政治制度以及教育情况,再写信告知国内朋友,或者写成文章,发表在国内的报刊上,以求引起有识之士的注意,从而有助于社会的改革。当时湖南的《大公报》曾刊登文章称赞说:“近来吾湘学界向外发展的势头很大,法国、南洋两方面去的人颇多,这是吾湘一点生机……其中我最佩服的还有两位:一是徐君懋恂(即徐特立),一是蔡和森的母亲,都是四五十岁的人,还远远地到法国去勤工俭学,真是难得哩!”
知命之年决然入党
1924年7月,徐特立回到国内。当时,国共已实现第一次合作,大革命正蓬勃兴起。徐特立参加了国民党,以图“一起来促进国民革命”。1926年12月,他会见了回湖南考察农民运动的毛泽东,并于次年春回家乡调查农民运动的情况。农村翻天覆地的变化令他惊喜不已,他开始认识到“少数学生无法挽回国运……教育救国是我30年来的一种幻想”,于是积极投身农民运动,加入大革命的洪流。1927年3月,他担任湖南农民协会教育科科长兼湖南农村师范农运讲习所主任,还被选为国民党长沙市党部工农部长,为发展湖南的工农运动做了大量的工作。
1927年4月,国民党右派公开叛变革命,5月21日长沙发生马日事变,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遭到疯狂屠杀。面对血雨腥风的白色恐怖,徐特立拒绝了反动派对他的拉拢、利诱,毅然决然地抛弃一切,他跑到汉口,冒着杀头的危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对此,毛泽东在祝贺徐特立六十大寿的贺信中称赞说:“当革命失败的时候,许多共产党员离开了共产党,有些甚至跑到敌人那边去了,你却在一九二七年秋天加入共产党,而且取的态度是十分积极的。从那时至今长期的艰苦斗争中,你比许多青年壮年党员还要积极,还要不怕困难,还要虚心学习新的东西。什么‘老,什么‘身体精神不行,什么‘困难障碍,在你面前都降服了。而在有些人面前呢?却做了畏葸不前的借口。”陆定一在《人民教育家》一文中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人民教育家徐特立同志,就这样给全党同志上了第一课:困难时不要动摇,应当更坚定地奋斗,革命是一定胜利的。徐老给我们的教科书,就是他的入党,这本没有字的教科书,比什么教科书都好,也比什么教科书都重要。”
近花甲之年徒步长征
加入共产党后,年已半百的徐特立“但为解放战,不知老将至”。1927年7月,受中央委派,徐特立赴南昌动员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代主席姜济寰支持起义。南昌起义爆发后,徐特立被选为革命委员会委员、起义军第二十军三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后随部队转战赣、闽、粤。1928年5月,徐特立被中央派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班学习,1930年底回到中央苏区后,历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部副部长、代部长,颁布了一系列教育方针和政策,领导创办了苏维埃大学、列宁师范、农业学校、列宁小学以及各种夜班和训练班,开创了崭新的工农苏维埃教育。
1934年10月,徐特立年已57岁,是长征队伍中年龄最长者。刚从江西出发时,组织上为照顾徐特立,给他分配了一匹马,并派了一名饲养员跟随。但他很少骑马,时常将马让给体弱多病的同志骑,或拉去载辎重。就这样,徐特立以年近花甲之身,脚踏草鞋,拄着一根竹杖,扛着防身用的红缨枪,随总卫生部干部连徒步行军,历尽千难万险,最终胜利到达陕北。
古稀之年定下廿载计划
1949年3月,徐特立随中共中央机关进入北平,先后参与国共和平谈判、全国文化教育事业的接管等工作。在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上,他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1949年10月1日,他登上天安门城楼,亲眼目睹了毛泽东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亲耳聆听了毛泽东庄严宣告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
这年,徐特立已经72岁,在常人看来实在可以颐养天年了,然而他却从不因年老而松懈。欢庆之余,他想到的不是革命大功告成,可以坐享清福,而是国家在经济、文化建设方面面临的艰苦任务。为此,他制订了一个20年学习和工作计划,作为晚年的奋斗目标。
此后,徐特立历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历史学会、中国地理学会名誉主席。他不顾年事已高,朝气蓬勃地投身于新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领导一批党的宣传干部和史学工作者从事中国通史、中国革命史和党史等的编纂工作,并继续以各种方式关心、指导教育工作:或报告讲演,或撰文著述,或视察调研,或接待来访,或书信交流。为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教育事业不懈地奉献着光和热。这位坚强的老战士,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1968年11月28日与世长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