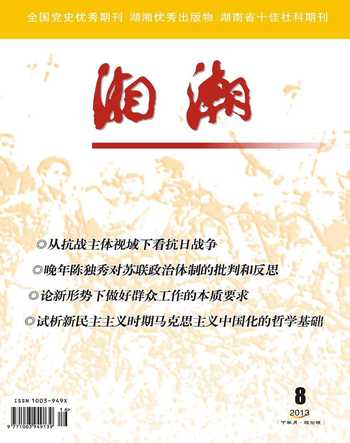毛泽东与新中国之八:“双百”方针
2013-04-29李宛聪
李宛聪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在这个开辟新纪元的历史性时刻,毛泽东不仅对新中国的政治、经济、国防建设做了一番精彩的畅想,还对未来的文化建设作出了大胆的预言。他宣告:“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这激动人心的宣言,代表了百年来科技文化落后、受尽歧视屈辱的中国人的共同愿望,展现了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宏伟蓝图。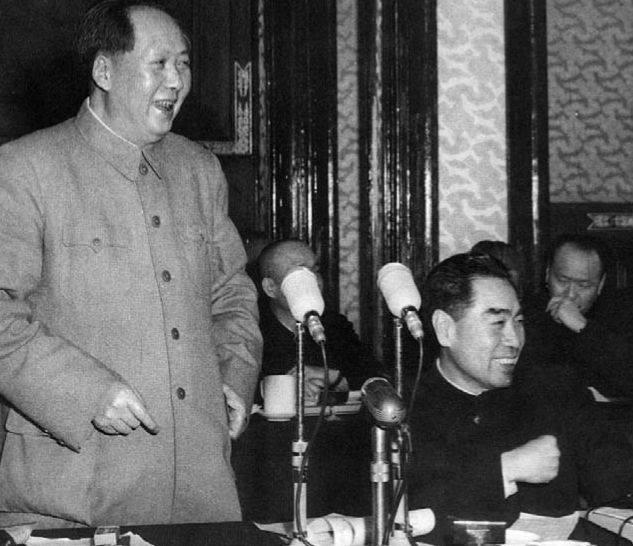
五千年的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光辉灿烂,曾使中国跻身世界文明国家之列。然而到近代,我们的文化衰落了。由于封建制度的长期存在,以及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奴役,近代中国变成了文化上愚昧落后的国家。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5亿多人口,其中80%以上是文盲、半文盲,各类知识分子只有区区200万人。大部分知识分子是爱国和革命的,但一些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身上不可避免地沾染了许多旧的东西,并把它带到新社会来。在国内百废待兴、国外有帝国主义渗透和颠覆的大环境下,文化领域呈现出十分复杂的状况。
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提出:“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根据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阐述的原则,1949年的《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政策。”这成为新中国文化建设的总方针。
1949年7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了中共中央给大会的贺电,贺电中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我们的任务主要地就是发展生产和发展文化教育。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人民政权的建立,给人民的文化教育和人民的文学艺术开辟了发展的道路。”这次大会实现了老解放区与新解放区两路文艺大军的会师;明确了文艺为人民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建立了全国统一的文学艺术界组织——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揭开了新中国文化建设的第一页。
第一次文代会上提出了改革旧戏剧的任务。在1950年召开的全国戏曲工作会议上,发生了京剧和地方戏以哪个为主的争论。1951年 4月,中国戏曲研究院在京成立,毛泽东为其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同年5月5日政务院发出《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提出:“中国戏曲种类极为丰富,应普遍地加以采用、改造与发展,促成戏曲艺术的‘百花齐放。”至此,戏曲界的一些争论不休的问题终于得到解决。
此后,以毛泽东“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为指导,对传统剧目和表演艺术进行整理改革的工作逐步开展起来,大批传统剧目焕发出了新的活力,许多濒临灭亡的剧种获得了新生。
1956年春天,昆曲《十五贯》在北京上演。这部戏在北京待了46天,演了46场,有7万多人观看。 1956年4月17日,毛泽东第一次观赏了这部戏。这出戏演完了以后,毛泽东站起来,双手举过头鼓掌。第二天就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第一,这出戏改编得很好,演出也很好;第二,全国所有的剧种、剧团,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演这部戏;第三,对这出戏的改编,对这个剧团要给予奖励。过了没几天,在4月25日,毛泽东又看了一次《十五贯》。两天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还特意提到这部戏。5月18日,《人民日报》专门发表了一篇社论,叫《从“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谈起》,这“一出戏”指的就是《十五贯》。对昆剧演员们来说,这个标题是说到他们的心坎里去了。
1956年2月,中宣部的一份报告引起毛泽东的注意。报告中说,在中国讲学的一位苏联学者,在访问孙中山故居途中,向中国陪同人员表达了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孙中山世界观的论点的不同看法,并认为这“有损于我党负责同志威信,是否有必要向苏方反映”。毛泽东看到报告,专门写信给刘少奇、周恩来等说明:“我认为这种自由谈论,不应当去禁止。这是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无所谓损害威信。因此,不要向尤金谈此事。如果国内对此类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加以禁止。如果企图禁止,那是完全错误的。”
毛泽东一直坚持学术问题可以争论的态度。早在1953年,历史学家郭沫若和范文澜就中国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分期问题发生争论,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主任陈伯达向毛泽东请示历史研究工作的方针,毛泽东讲了4个字:“百家争鸣”。1956年2月,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向毛泽东汇报了一些学科中存在的不正常的争论现象,毛泽东又一次提出要对科学工作采取“百家争鸣”的方针。
1956年,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即将完成,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日益成为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大问题是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1月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的几个问题》报告,他代表中共中央郑重宣布: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毛泽东在闭幕会上讲话,特别指出:现在叫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革愚昧无知的命,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单靠老粗是不行的。中国应该有大批知识分子。他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水平而奋斗。
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提出“双百”方针,他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同年5月,毛泽东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谈到这个方针,他说:“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说春秋战国时代,二千年以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派,诸子百家,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
在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正式载入党的文件。从此,“双百”方针成为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指导方针。露,给文艺界科学界带来了温暖的春天,极大地鼓舞了文艺工作者的创作热情,调动了科学工作者的研究积极性。
1957年3月24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民盟中央委员、社会学家费孝通的一篇文章《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文中写道:“春到人间,老树也竟然茁出了新枝。百家争鸣的和风一吹,知识分子的积极因素应时而动了起来。”这形象地表达了广大知识分子共同的喜悦感受。“双百”方针让“知识分子在新社会里的地位是肯定了,心跟着落了窠,安了。心安了,眼睛会向前看,要看出自己前途。”
然而,“双百”方针的贯彻执行并非一帆风顺,当时党内不少干部难以理解和接受这一新思路,一些人明显地表露出怀疑、忧虑乃至反对的态度。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在1957年又多次强调和重申坚持“双百”方针的重要性。
1956年9月,20多岁的王蒙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他的处女作《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这是一篇抨击党内的官僚主义现象的小说。小说发表后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有人开始“对号入座”,声明“在中共中央所在地果然有这样的区委是不可信的”,“我们这儿并不是那样呀”,等等。随后在作协主办的《文艺学习》上,掀起了关于《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的大讨论。讨论从1956年第12期开始,连续进行了4期,前后发表文章25篇。年轻的王蒙就这样出了“大名”。他在《半生多事》里回忆,那时“人们争说‘组织部”,“看到行行整齐的铅字里王蒙二字出现的频率那么高,我主要是‘得意洋洋……”不过,高兴没有多久,王蒙就发觉有些异样。首先是《文汇报》已决定连载的他的《青春万岁》不见了踪影,其次是《中国青年报》总编和副总编悄悄找王蒙谈话,他们忧心忡忡,认为王蒙捅了个大娄子。1957年2月9日,《文汇报》突然登出一篇长文,这就是《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作者是因率先批评俞平伯红学而受毛泽东欣赏的李希凡。文中比较严厉的批判了王蒙的小说,认为小说对官僚主义的描写过于夸大,不符合现实。王蒙所承受的巨大压力,可想而知。
令王蒙没有想到的是,毛泽东也关注到了他的小说。2月26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中央报刊、作家协会、科学院和青年团的负责人开会,会上他专门谈到自己对王蒙的小说以及有关讨论的看法:“王蒙最近写了一篇《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此人这篇小说有缺点,需要帮助他。对待起义将领也要帮助,为什么对青年人不采取帮助的态度呢?……王蒙写正面人物无力,写反面人物比较生动,原因是生活不丰富,也有观点的原因。……有些同志批评王蒙,说他写得不真实,中央附近不该有官僚主义。我认为这个观点不对。我要反过来问,为什么中央附近就不会产生官僚主义呢?中央内部也产生坏人嘛!……用教条主义来批评人家的文章,是没有力量的。”后来,毛泽东又三番五次就王蒙的小说做出指示。有人统计,从2月至4月,毛泽东就此共发表了5次谈话,归纳起来有三点:一,王蒙写党内官僚主义不是歪曲现实;二,要“保护”这个年轻作家;三,反对《人民文学》对小说原稿的修改。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同一个作家、作品发表如此频繁的谈话,在毛泽东一生中也是绝无仅有的。
毛泽东当时之所以抓住这件事着重加以分析,是因为这件事具有典型意义。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它反映出“我们对人民中的错误采取如何处理的方针,有大量的人是没有弄清楚的”。毛泽东想通过这件事尽可能把空气搞活,创造一个自由环境,真正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和3月12日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又重申了“双百”方针,并强调了两点:第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第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不但是使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好方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这个方法可以使我们少犯错误。有许多事情我们不知道,因此不会解决,在辩论中间,在斗争中间,我们就会明了这些事情,就会懂得解决问题的方法。各种不同意见辩论的结果,就能使真理发展”。
毛泽东的这些话,征服了知识分子的心。著名翻译家傅雷听到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后,写信给孩子说:“毛主席的讲话,那种口吻,音调,特别亲切平易,极富于幽默感;而且没有教训口气,速度恰当,间以适当的pause(停顿),笔记无法传达。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讲话的逻辑都是隐而不露,真是艺术高手。毛主席是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融会贯通了的人。”“他的胸襟宽大,思想自由,和我们知识分子没有区别。”
1965年5月12日中央美术学院几位美术教师向毛泽东写信,反映从20世纪60年代初废除模特制以后美术教育活动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建议恢复一定比例的人体习作。毛泽东看到来信后,在7月18日作了批示:“此事应当改变。画男女老少裸体Model是绘画和雕塑必须的基本功,不要不行,封建思想,加以禁止,是不妥的。即使有些坏事出现,也不要紧。为了艺术学科,不惜小有牺牲。”时隔半月,又批示:“画画是科学,就画人体这问题说,应走徐悲鸿素描的道路,而不走齐白石的道路。”毛泽东的批示体现了他对艺术规律的尊重,给中央美术学院的师生们以很大鼓舞。
建国初期,我国自然科学界,在苏联教条主义的影响下,出现了对不同学派乱贴“标签”,乱戴“帽子”,抬高一个学派,压制另一个学派的现象。例如,当时在遗传学领域,独尊李森科为社会主义学派,指责摩尔根为资本主义学派。著名植物学家胡先马肃在《植物分类学简编》中批评了李森科,竟然遭到政治批判。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有针对性地说:“讲学术,这种学术也可以讲,那种学术也可以讲,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讲的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来越多。”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讲了一段很重要的话:“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李森科、非李森科,我们也搞不清,有那么多的学说,那么多的自然科学学派。就是社会科学,也有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谈。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
1956年8月10日,遗传学座谈会在青岛召开。在开幕式上,于光远开门见山地讲:“为了贯彻‘百家争鸣,党决定,对学术问题,党不做决议,让科学家自己讨论。”这就给与会者吃了定心丸,随着会议的进行,气氛也由沉闷变为活跃,与会学者们的讨论越来越热烈、越来越坦诚。
北京大学遗传学家李汝祺也参加了这次座谈会。会后,他写了《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一文,毛泽东看后建议《人民日报》予以发表,并为其写了按语,重新拟了题目:《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毛泽东认为,百家争鸣,学术自由,是“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双百”方针反映了科学和艺术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
这次意义非凡的会议,中国现代遗传学奠基人、“中国的摩尔根”谈家桢也参加了。此时,毛泽东也正在青岛主持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指名要见谈家桢。当谈家桢来到毛泽东的住地后,毛泽东征求了谈家桢对“双百”方针和遗传学研究与教育工作的看法,听完后表态说:“一定要把遗传学研究工作搞起来,要坚持真理,不要怕。过去我们学习苏联,有些地方不很对头,现在大家搞嘛,可不要怕。”这一席话,让一度无法开课的谈家桢重登讲台。
1958年1月6日,毛泽东特意派专机接谈家桢等3人一道去杭州。当赶到西湖丁家山下的刘庄宾馆时,谈家桢见毛泽东竟亲自站在门口等候他们。那天晚上,在风景秀丽的西子湖畔,4个人像老友一样畅所欲言。毛泽东问谈家桢“把遗传学搞上去,还有什么障碍和困难么?”谈家桢把积攒很久的想法一五一十地都吐露出来。毛泽东听完,站起来说:“有困难我们一起来解决,一定要把中国的遗传学搞上去!”
在毛泽东的关照下,1959年复旦大学成立了遗传学教研室,两年后又建立了遗传学研究所,都由谈家桢全权负责。1961年五一节前夕,谈家桢在上海第三次与毛泽东见面。毛泽东问谈家桢:“复旦是个名校,把遗传学搞上去,你还有什么顾虑吗?”谈家桢说:“没什么顾虑了,多亏主席关照,我们复旦创建了遗传学教研室和研究所,两个学派的课程同时开……”毛泽东笑道:“我支持你!一定要把遗传学搞上去!”
谈家桢在多年以后回忆起这段历史,仍然激动不已地说:“‘双百方针的提出,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的召开,毛泽东主席的亲自关注,无论对中国遗传学事业,还是对我本人而言,都如久旱逢甘露,是一种莫大的支持。这是我一辈子都不能忘记的。”
1964年9月1日,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学生陈莲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反映了该院教学和演出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对实现音乐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等提出了意见。毛泽东作了批示,肯定了此信,并指示解决她所提出的问题。就是在这个批示中,毛泽东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艺方针。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都谈到如何正确对待中外文化遗产问题,十分精辟。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说:“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同年8月24日,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毛泽东又明确地讲了如何处理“古今”“中外”文化财富的问题,他说:“艺术上‘全盘西化被接受的可能性很少,还是以中国艺术为基础,吸收一些外国的东西进行自己的创造为好。”“我们接受外国的长处,会使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中国的和外国的要有机地结合,而不是套用外国的东西。”“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
在毛泽东批示精神的鼓舞下,中央音乐学院师生走出校门,下农村,进工厂,到部队,进行演出和访问,倾听群众对音乐的要求,体验生活,锻炼思想,同时搜集创作素材。各系制定了新的教学计划,增加民族民间音乐的教学比重,对外国音乐曲目认真做了遴选。音乐学习和创作重新焕发出活力,新鲜空气充满校园和舞台。
“双百”方针的提出,曾打破了思想文化界多年沉闷的空气。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界,出现了热烈的自由讨论的氛围。文艺事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优秀作品大量涌现。文化事业机构和队伍的规模,比旧中国有了几十倍甚至几百倍的增长。据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公布的数字显示,文盲半文盲占总人口的38%,比1949年下降了42个百分点。科技战线,在非常薄弱的基础上取得了十分明显的成绩,到1965年,全国科研人员达到240万人。这为以后的文化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虽然1957年夏季之后,由于“左”倾指导思想的发展,“双百”方针贯彻执行受到严重扭曲和挫折。但是毛泽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那熠熠闪光的理论内容却穿透迷雾,昭示后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继承和发展,在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新的历史阶段放射出更加夺目的光彩。
(压题照片:毛泽东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发表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