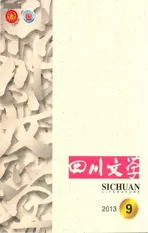躲
2013-04-29陈再见
陈再见
大半夜,他把冰箱里冻着的冷水全部喝完了,然后上了三次厕所,马桶冲水的声音很大,哗啦啦,像是外面下了一场骤雨。第一次,她翻了一下身子,第二次,她又翻了一下身子,第三次冲水的声音,终于把她弄醒了。
“下雨了吗?”她问,“把阳台上的衣服收一下,对,还有灵的书包。”
“没有。”他说。
“怎么还不睡?”
“没有,撒尿。”
很奇怪,他一向睡眠可好了,以前只要躺下,不出一分钟,便能鼾声响起。关于这点,她经常揶揄他,“没心没肺的人,就这样。”她说。他通常鬼着脸笑,说:
“基因就这样,我爸站着也能睡着。”
确实,他父亲有一次坐客车去南塘镇,没人给他让座,他于是倚在扶手上睡着了,竟然还打起了鼾。这事他父亲在他的婚礼上当笑话说了,当时在场的人都笑了,惟有她愣着,她朝他耳语:“你爸怎么这么怪?”
自那开始,父亲在她的印象里,就一个字:怪。这怪,后来不单单是睡觉的问题,似乎父亲做什么事,说出的什么话,在她看来都是不正常的。后来,也不只是父亲,他全家,姑姑,伯伯,叔叔,舅舅,妗子……似乎都不正常。
“你们父子一个样,你们全家都一个样。”
他发觉她对他家的人都失去耐性,这点从每次回老家就看得出来,只要回去住了超两个晚上,她就不耐烦,非要拉着他回深圳。
他现在却失眠了,这样的状况已经持续了一段时日。刚开始,他没在意,后来便有些恐慌。他总是感觉到摇晃,也不仅仅是身体摇晃,似乎整个世界都摇了起来,地震一般。他躺在床上,身体仿佛放大了若干倍,而床,在他想来也成了一艘船,在大海里漂着,最后他感觉自己的身体就是那一艘船了,而床已经放大到像是一片海。这时,他的头晕了,不得不起身。如果他坚持再躺一会,则会发生如下情况:他的身体会骤然缩小,小得像是一块石头,然后是一颗沙粒,往下沉,往海底沉,一直沉不到底。这时他试图伸手去抓,发现周围都是水,软绵绵的,没有一样硬物可以供他触碰……事后他感慨,其实所谓的安全感就是有一件硬物在身边。
病了?他一开始就这样想。他去医院,问医生那是怎么回事。医生建议他多运动。他嘴里应着,心里却踏实了,心想医生这么说其实就表明他啥事没有,运动也就可做可不做。他害怕医生要他做个脑部CT什么的,那样身体里隐藏着的病魔好像就有机会和他摊牌似的。他担心自己的身体出了大问题。一辈子没病的人,一病便是大病。他就是这样,从小到大,几乎没到医院过夜。
他害怕医院,那种气味和氛围。都是他所不习惯的。他坚持不上医院,像感冒之类的小疾能拖就拖,通常都能拖好,拖不好最多也是吃点药。他其实也不是心疼钱,也不差这点钱。倒是她,却是医院的常客,随便哪里不舒服,她都能咋呼呼地请上半天假跑医院。“你是那种太把身体当回事的人。”他这样说过她。她回道:“你缺乏健康意识,小疾不治,小心大病致命。”她在威胁他,像是他的身体真的隐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病灶。他听了一咯噔,但没表现出来。
后来他有了些改变,也是为了尽量配合她。女儿灵有个感冒发烧,他也能做到匆匆忙忙出去打的,到了医院,也尽量去习惯那种气味和氛围。甚至于,有一次他扭到脖子了,在她的劝导下,竟然也找了个中医院,做了一次物理治疗,虽然脖子还是酸痛,他却跟她说:“好多了。”
“听我的没错。”她总是骄傲自得。
这是她的职业病,她是天虹商场一楼的化妆品推销员,日常工作就是向那些爱美的女人推销合适的化妆品和气味古怪的香水。“听我的没错。”她总是这样说,确实有不少人选择听她的建议。她是这方面的高手,似乎是天生的,什么样的人适合什么样的香水,什么样的肤色要用什么样的化妆品,她如数家珍,却从不在自己的身上做实践,除了上班时间,一回到家,她第一件事就是到洗浴室洗去一脸的粉脂和满身的劣质香味。她就是不着一粉,脸色也洁白如玉,不用任何香水,身上也有一股香味,那味道清新,闻着让人放心。
结婚五年,三十而立的他,是越来越听话了。这听话倒不是一夜之间形成的默契,是不知不觉的,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有这么回事。有一天,父亲在电话里说了半个小时,又叫来母亲说了半个小时,最后还是没谈高兴,父亲便一把抢过电话,朝他生气地说:“看来你是越来越听老婆的话了!”他在电话里还狡辩了一下,说夫妻之间不是谁听谁的话,重要的事情总得商量着决定吧,生孩子的事真不是他一个人能说了算的。挂了电话一想,还真如父亲所言,这么些年,是他在慢慢向她妥协的过程。不知什么时候,他变得毫无主见,凡事都得听她的意见,只要她没开口,他便不敢说句果断话,而她一表态,他就在一边举双手赞成,也非无奈,他确实觉得她下的每一个决定都挺合理,有时还真出乎他的意料,他还真没往那一层去想事情。所以,无论大事小事,小到为家里添一个家具,假日去哪儿游玩,大到供房买车,都得她举手拍板,方能一锤定音。时间长了,竟养成习惯,导致他一到关键时刻就沉默,似乎也省了心,活得轻松起来。“让我先问下阿莲。”他总是这样说。别人听着没什么,在父母听来,问题就大了,甚至有点恼火,自己的儿子,怎么还得听一个女人家的,在他们那个横竖都好几里的村庄,还是头一回听说。他虽然早已不在村里住,到深圳当了律师,用父亲的话说是大状师,可终究是那个村里的人,至少是从那个村出来的,还能反了不成。
父母的意思很明确,得再生一胎,一个女儿,哪行?理由倒是说得委婉,说一个女儿,孤单单的,没一个伴,在家里多寂寞。实际上他们就是想抱一下孙子,再生一胎虽然也不一定能抱上,但总是个希望——他从小在那个村里长大,能不明白村里人这么点小心思。他说城里的孩子都这样,伙伴都在幼儿园里。父母说那幼儿园的伙伴还能比兄弟姐妹亲。他便又说城市计划生育严,不让生。他想这个理由应该可以吓退两老人家了。谁知父亲在电话里笑了,说亏你还是个律师呢,这点事都办不成,那还怎么帮人家打官司啊?父亲的口气咄咄逼人,看来是做足了功课。他看没了退路,只好亮出最后的王牌,他说是她不想生,她说一个女儿就够了,她不生他能有什么办法。
这事都说了一两年了,一直就这么僵持着。弄得每次回家,彼此都不自在。不自在,自然就回去得少,她们母女在时,父母也不敢多说什么,就旁敲侧击地,尽使一些低劣的暗示,还生怕她听不懂,实际上她已经在偷笑。他看在眼里,一场实力悬殊的对决,他惟一的感觉便是同情弱势的父母,他们又怎么能斗得过她呢?等于是一场决斗,他们已经竭尽全力,而她却站在一边,优雅地叉着双手。分明还没出手呢,就已经把对方累得气喘吁吁了。
“多生一个会死啊?我生了你们兄妹五个,不也一样过来了。”母亲这样说。母亲这样说的时候让他感觉母亲那样的女人和妻子这样的女人真的没有什么可比性了。
他害怕吵到她,更不想影响女儿的休息。他熄了客厅的灯,悄悄到阳台站着,看楼下孤零零的灯火,那些绿色的植物,青松、紫薇、海桐,还有开得鲜红的勒杜鹃,在深夜里毫无生气。女儿喜欢勒杜鹃,她总是忍不住要摘一朵,戴着回家,藏在她的房间里,没几天,她的妈妈总是能从房间里清扫出一地枯瘦的勒杜鹃,像是一地落叶。远处还有几栋烂尾楼。牵涉出的官司似乎也是他们的事务所在办理。烂尾楼里竟然还住着人家,灯火幽暗,不时总能传出几声吆喝,是他听不懂的方言。
他想起那奇怪的摇晃,似乎是从未有过的幻觉。他想抽根烟,但家里再也找不到一根烟了。他戒烟已经四年,女儿的出生,作为一个戒烟最有效的理由,他不得不遵从。四年来,他从未想过再抽一根,就那么决绝地把烟给戒了。他抽了多年的烟,也不记得是几年了,似乎从初中开始,便和表哥一起捡地上的烟嘴子抽。说戒就戒,他真有点佩服自己。但其实还是她的强硬态度让他不敢轻举妄动。有一次他看到这样一句话:不要和戒烟成功的人做朋友。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刻开始,他便不敢再在朋友面前炫耀自己的戒烟经历,似乎那已经是见不得人的事情了。而在她看来,他的成功戒烟,却是她嫁给他后的第一次大规模告捷。
任何衰败都有一个突破口,戒烟便是那个突破口。他后来越是这么觉得,尤其是在此刻。他真的需要一根烟来消解失眠的恐慌。
现在的他,别说是抽烟了,就是和抽烟的人在一起,回来了,她还是能从他的身上闻到烟味,并大肆盘问一番。她越来越成为一个洁癖者,不允许家里掺杂进任何一样陌生的气味。
“是不是工作压力很大?”医生问过他。
他想起手头受理的一单官司,难度其实不大,甚至有些小儿科,以他的经验,他可以做到百无一漏,该消失的让它们消失,该伪造的可以伪造,保证对方不可能多拿他的当事人一分钱。这是他的职业。但抛开职业,他一点都不喜欢帮这样的人打官司,这种感觉以前也有过,只是这次比较强烈。一个人在外做了小老板,暴发户,嫌妻子没给他生个儿子,便有了别的女人,接着要跟结发妻子离婚。离婚倒也可以,却不愿意多给妻子一分钱。
现状对他的当事人有利,他一接手这单官司。其实一点压力也没有,没有结婚证,能证明婚姻关系的只有一个女儿。他胸有成竹。如果再狠一点,他甚至能做得更干净。但实在没这个必要。他越想越窝火。有时他假设,如果对方请的律师是他,角色一调换,他倒情愿竭尽全力,让一个无情的暴发户得到应有的惩罚。
他其实没必要想太多,把事情做好,自己该拿的钱一分不少拿,不就万事大吉了么?他真没必要感情用事。
他见过一次那个女人,和她的女儿。那是一次庭外调解,可想而知,最终还是不欢而散。他不明白他的当事人怎么就那样决绝,所面对的似乎不是曾经的妻女,而是仇敌。人与人之间善恶可以瞬间转变。他端坐着,面无表情。说出的话也是职业性的滴水不漏。但他的心分明是虚的。他看见了那个女人的眼泪,以及她的女儿一脸茫然的无知神情。她们的无助,和当事人的得意洋洋,仿佛两把锤子,把他冷静面目下的内心砸痛了。
他一闭上眼,看到的便是她们母女畏缩着端坐在对面的身影。还有两三个亲戚,他们同样畏怯。
他又一次闭上眼,看到的还是她们母女畏缩着端坐在对面的身影,只是母女换成了他的妻子和女儿。他吓一跳。
似乎就在那一刻,世界开始摇晃。当他变成一粒尘土往下坠的时候,他看见周围亮光一片,白茫茫的,像是钻石发出的光,把他的眼睛逼得睁不开。慢慢地,那光开始呈现出规律,像是路两边的灯光,整齐排列,伸向远方,望不到那端。——这情景十分熟悉,像是在哪见过,或是曾经想象过,出现在梦境里过。
他朝着路的尽头一直坠下去,大半会过去,还是坠不到头。
他站在阳台终于想起那情景的熟悉,其实来自童年时候的一个游戏。也称不上是游戏,就是一种无聊的举动——他的童年实在没什么东西可玩。他记得那时体弱多病,隔天才去一次学校。他没有要好的同学,也没有要好的伙伴。他一个人,有时就自个儿找玩。但他没什么想象力,好静,话也不多——他从小是一个沉默寡言的孩子。以至于后来他当上了律师,村里那些认识他的人打死都不相信,一个半天憋不出一句话的人竟可以当律师。那个村里的人对律师的理解很简单,也很直接,所谓的打官司,便是吵架,所谓的吵架,本质上又和邻居间吵吵闹闹是一致的,靠的是反应,靠的是口才,靠的是咄咄逼人的气场。而他,哪一样都不具备。更多时候,他就躲在被窝里玩手电筒。手电筒能玩出什么花样?他惟一感觉自豪的便是真让他玩出了花样。他把手电筒打开,对着眼睛照,眼睛是睁着的,而手电筒的光也刚好被眼睛所接受。他努力在那些光里看见什么,当然也是掺杂进不少属于那个年龄的想象。他首先看到的是灯火,璀璨耀眼的灯火,灯火来自哪里?接着他想到那是南塘镇的夜景。南塘镇的夜景他其实只见过一次。是和父母一起去的,那次他们去看戏,八月十五,月亮很圆。父亲的单车骑得有点快,他坐在前横梁上,迎着风,心都被吹开了。单车摇摇晃晃,似乎随时都可以把他甩下来。背后是母亲,她一直喊父亲慢点,再慢点。那晚发生了什么事,他基本上忘干净了。惟一记住的只有南塘镇明亮的灯火——事实上,他后来回想,那灯火一点都谈不上明亮。他感觉那已经是好遥远的事情了,当他在手电筒的光亮里回忆南塘镇的灯火时,一次次,他把那个遥远的记忆重温。时隔多年,他第一次想起记忆竟然可以以这样巧妙的方式重叠,他是大吃一惊的。
他不知道那个曾经穷过的暴发户,在穷的时候,是否也像他的父亲那样踩着单车带着妻女去一个邻近的小镇看戏?他突然认定是有的,每一个家庭应该都有那么一段美好的记忆。而美好总是适合回忆,现实里,他们都面临着你死我活的问题。他本是一个局外人,因为律师的身份,他介入了,如同介入一个秘密。他不知道是应该感谢这种介入,还是担忧。近年来,他的担忧是越来越明显了,那些他介入的人物和事件,善恶的交集,明里和暗处的纠结和争夺。不单成为他的工作,还逐渐侵浸了他的生活,他的情绪和思想,甚至是张口吃饭、闭目睡觉,似乎都受其影响,如同漂浮的尘粒,一张张面孔,得意洋洋的,踌躇满志的,迷茫无助的,胆怯畏缩的,它们的背后都应对着一个活生生的人物和足够大的事件。他所面临的总是足够大的事件,足够的残忍和邪恶,否则他们也用不上他。大多时候,他怀疑自己是个好人,他更像是一个罪恶的拥护者。当然他也是帮过人的。站在好人这一方,或者说是站在了弱势这一边,面对的是强硬的墙壁,他竭尽全力,也赢得了官司。他颇有成就感,可他也特别累。他想一切都只是工作,和善恶无关。这么想的时候,那仅存的一点成就感也跟着消失了,积聚已久的自责和愧疚却日益强烈。
翌日,一夜的失眠又让他的眼圈黑下去一点。但他的精神总是好的,这大概是职业赋予他的一种特殊能力。天一亮,洗刷完毕,穿上她烫好的西装,他便感觉是换上了一层皮,精神也为之一抖,拉了门出去,直到去停车场开车,路上遇见熟人,他总是能热情地和人打招呼,声音响亮,笑容恰当,谁也看不出来他是一个失眠患者。
“傅大律师,忙啦?”
听到问候,他总是笑着点头,说:
“是啊,事情有点多。”
在他人眼里,律师这个行业的人让人总是有些敬畏感和神秘感吧,至少他们不是那种敞开在众人面前的职业,他们是被抬起来或者藏起来的,他们总是半明半暗,亮出来的那一面只会让藏起来的另一面更让人感兴趣。他当初选择这么一个专业,也是好奇,受吸引。当他真当上了律师,神秘感轰然消失,并以另一种物质填充其间时,他失望了。失望的他,还是得向众人隐藏,或者说,他还得表现出一个律师的严谨样子。让人继续产生错觉,不至于一眼就识破了他们的秘密。他不知道怎么就这么做,似乎也必须这么做,否则便对不起这么个职业似的。他有时真想当着众人的面把那件总是笔挺着的西装脱下来。露出本来的面目和肌肉,他本该有的真性情和咧嘴大笑,就那样,在众人面前当一回真实的自己。可他做不到了,像那时坐在父亲的单车上一样天真率真的时候已经不复存在。甚至于面对妻子,他也无法敞露,隐藏着一些自认为该隐藏的,捏造着一些应该捏造的,当隐藏和捏造都成了习惯,一切便仿佛成了自然,是他与生俱来的东西,是本来的他。他在这样的错觉里开始恍惚不定,像是眼睛透过雨幕,他永远看不真切另一端的事物,尽管另一端就隐藏在他的心里。
他又打了一次漂亮仗,尽管胜券在握,至少于他来说,属于驾轻就熟,事务所还是弄了个小小的仪式,领导讲了几句,也都是推心置腹的,他听了不免感动。这些年来,他走得其实挺顺,在一些紧要关头,当困难还没形成的时候,就已经得到完满的解决,似乎背后总有一双手,为他排忧解难。他要感谢的人也不少,领导自然是免不了的。从刚进事务所,一个打杂的,慢慢成为中流砥柱,这期间他大可以认为是自己奋斗的结果,但观望四周,谁又不曾奋斗过?所以,他宁愿把一切幸运都归功于领导的赏识和提拔。用俗不可耐的话说:他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
几个同事出去喝几杯,领导有事先走,似乎怕扫大伙的兴。领导其实是一个和蔼的男人,可再和蔼,他也是领导,得摆出一个领导的样子,于是领导在的时候,他们这帮踩着青春的尾巴的男人还是没办法放开。领导先走,同事们几乎都想欢呼,可还是忍住。谁都难以想象,一帮西装革履的律师在酒吧里欢呼起来的样子,该是多么的滑稽。他们还得保持自己的形象,显然,气氛还是活泛了不少。酒喝得有点多了,有人提议去KTV唱歌,没人反对,他更不能迟疑,他说:“我请大伙,继续喝。”
继续喝,他真的有些受不了,中途出来吐了,倒不是想吐,是那么多酒窝在肚子里难受,他到洗手间用手指抠了出来。他对着镜子洗脸,眼睛是红的,像是刚哭过,有人看着他,知道他喝多了,没敢靠近。他往回走,在灰暗的走廊里辨认着属于他们的包间,他推开了好几间包间的门,发现都不是他们的那一间。他说不出的焦虑,似乎就那样被世界所遗弃。他感觉头晕,步子轻浮,最重要的是走廊开始摇晃起来,继而整个世界也跟着摇晃,和梦里的情形一样。他差点脱口而出:地震了。
他实在找不到包间,他趴在那些一模一样的房门上听里面的歌声,希望能从歌声辨认出他们来。他们唱的歌基本都比较老,黄家驹的《光辉岁月》和张学友的《相思风雨中》几乎是他们必唱的曲目。他独唱《光辉岁月》的时候总是能博得激烈的掌声,然后是《相思风雨中》,这歌他和妻子唱过,没结婚的时候,认识他的人都认为她之所以喜欢他是因为合唱的默契,但是后来,他就很少和妻子合唱了,主要是他很少带妻子出来唱歌了。他和事务所另一个女子合唱,唱得也不错,多次,他错认为事务所新来的这个女子便是年轻时的妻子。每当有这样的念头升起,他就会感到深深的自责。
走廊摇晃得越来越厉害了。他生怕自己趴在门上偷听的动作被人看见—那样不好。他是一个律师,他怎么可以那样,像个小偷。他决定不找了,他想提前回家。走到门口时,他又想起是他请大伙唱歌的,于是他又折回来,想先埋单。问题是,他不知道该为哪个包间埋单。为这事,他在前台犹豫了好一会,直到妻子的电话打进来,妻子问他怎么还没回家。他说正在路上呢马上到。他便扔下足够多的钱,嘱咐说哪个包间没人埋单他就是为那个包间埋单。他如此狼狈。真想赶快消失。简直有些丢人现眼。
回到家,她自然是不高兴的,她除了讨厌烟味,同样讨厌酒味。女儿,也不高兴,女儿总是站在她那一边。都说女儿是父亲的小棉袄,他就从来没这么觉得。
晚上,他只能在沙发上过夜。趁着酒劲。他睡了一觉,一觉醒来,发觉自己浑身颤抖,原来被子掉在了地上,而他的衣裳也是湿的,在KTV里洗脸时弄湿的。这么一醒,他便睡不着了。也不知道是深夜几点,他不想看。他眼睁睁看着天花板,听着窗外宝源路上来往车辆的低沉的声响。他又想起了那个被抛弃的女人和她身边的小女孩,此刻,她们在哪里?
他本想请个假,一晚上没睡好,一点精神也没有。但事务所大清早来了电话,说那对母女带人闹上门来了,站在门口骂他是帮凶、狗腿子,还朝事务所扔石头,撵也撵不走,母女俩最后坐在大门口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几个亲戚站着举牌子……他听着,打了个哆嗦,却一点都不觉得意外,好像早已预知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好像自己做了坏事,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后果。
“怎么办?”电话那头问。
他也不知道怎么办,能怎么办。他想幸好只是在事务所闹,要是她们闹到家里来,把他的真面目扒给邻居左右看,他就更加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当然,熟知并能熟用法律的他,不知道怎么办也是假的。太家常便饭了。他突然有些愤怒,像是突然清醒了一般,对着电话大声说:“你说怎么办?赶紧报警,还能拿她们没办法不成。”打电话的是事务所刚来的一个小伙子,就和多年前的他,一样慌慌乱乱。
他总得表达一下愤怒和不理解。事情其实也不难处理,对方只是瞎闹,如跳跃在眼前的几枚鸡蛋,没有权势,也可断定背后没有任何阴谋。甚至,都能看见嚣张背后那一颗颗颤抖的心。警察一到,自然也就散了去。那母女坚守了一会,最终也不得不离开。他不敢看那母女。有时他也想,落到今天这地步,这女子应该也不是什么好人,即便不泼辣,不讲理,至少整天也唠叨个不停,对男人稍有一点不如意便大声辱骂,不留情面。当然,还有,诸如要男人戒烟戒酒,晚上不能在外过夜,上街不能看别的女人,陪她去商场得有足够的耐心,等等,总之,那些女人让人讨厌的毛病。她应该都有,有过之而无不及,别看她现在可怜楚楚……他这么想,似乎能让自己舒服些。但他只要一看到她们母女,立马便会否定自己的揣测。
他实在有些累。晚上吃饭时,和妻子说了下事务所遇到的事,他没强调什么,也没表达出多大的愤怒,像是说起一件电视里的新闻,与自己无关。而她也表现出同样的情绪来,哦了几声,看样子都不愿意他把事情讲出来,即使讲了,也希望快点讲完。晚上的时间对她来说太宝贵,她要陪女儿,写作业,然后赶着去桃源居上钢琴和舞蹈的学习班……当然,还有更多的事情,是他难以看见和想象的。他劝过她,别给女儿太大的压力。她还是那句话:
“听我的没错。”
这两个女人太忙了,比他还忙。忙得他都不好意思,在这个家里,他看起来倒像是个无所事事的男人,都不敢去打扰她们,哪怕是说说话。他意识到自己对女儿越来越陌生。女儿两三岁时,父女俩比谁都亲。整天粘着,妻子看着都妒忌。如今女儿已经五岁。按理五岁的女儿懂什么,还不是小毛孩一个,在村里时,五岁的孩子还得吃奶呢,可他的女儿不一样,五岁的孩子,却像大人一样,认真,敏感,使性子发脾气,甚至是察言观色,用心计,伙同妈妈欺负爸爸……都让他大开眼界,并从中看出女儿身上有着妻子太多的影子,长大了也不是一个好对付的女人。这是一种怎样的心理?家里一大一小两个女人都让他感觉害怕。
她们已经急匆匆出门,说是上了课,还得去看李云迪的演出——她们的生活比谁都充实。面对空荡荡的家,他的无聊逐渐滋生。他把冰箱开了又关上,好几次,却不记得自己是在找什么,最终每次都只是倒出一杯冰水,咕咕喝下。他想抽烟,可也知道想法的危险,她就像一条猎狗,家里多了任何一种气味,都能分辨得出。她靠的就是鼻子赚钱,整天分辨那些香水的气味和成分。结婚之前,他没意识到危险,结婚之后,他才知道,找个对气味敏感的女人做老婆,是一件多么危险的事。他甚至都不敢去靠近另外的女人。怕沾了她们身上不一样的气味,回家了她一定能闻出来,倒不是她刻意想知道,她总是在他进门的那一刻,突然说:“咦,什么味道?”
一整夜,他无事可做,不敢过早睡觉,也睡不着,怕那可怕的摇晃。看会电视,播的是中东地区战乱的新闻,镜头的画面晃得可怕,他便立马转台,他再也看不得这类摇晃的画面,一看,头就晕。
他拿出手机,想给家里打个电话,妻子在时,他不方便打,妻子对家人的反感出乎他的意料。终究没打,他怕父母接下来又是长篇大论,要他生二胎,生个儿子,女儿终究不一样,长大了要嫁人,嫁了人就等于没了,别说有事能商量,连面都见不上:男孩就不一样,再怎么样,做父母的一辈子都能使唤,随叫随到……父母的话当然片面,带着强烈的乡下重男轻女思想。这些他都知道。他是个律师,是个文化人,他想的自然要和父母想的不一样。为什么非得不一样?他也不清楚。
他来到阳台,看见远处烂尾楼里微弱的灯光,那里面住着什么人?他能想起的便是那对母女和她们的穷亲戚……宝源路上的泥头车开得正凶,附近在修地铁,要赶在运动会之前通车……他突然感觉自己和这个城市格格不入,他从来就不是这里的人,不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人情世故。他想起父亲愤怒时骂他的一句话:“你以为你能一辈子躲在深圳么?哪一天你回来了,身边没有一个儿子,看你在村里怎么过?”
父亲用了一个“躲”字。
这个“躲”字,时隔多日,终于把他吓出一身冷汗。
责任编辑:聂作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