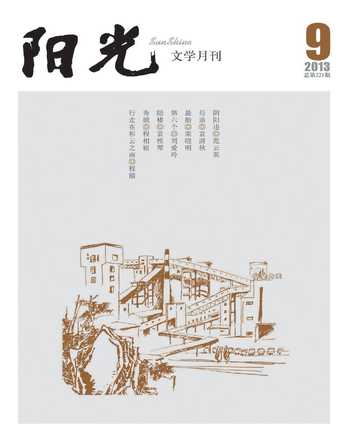行走在彩云之南
2013-04-29程豁
程豁
引 子
彩云之南,云之故乡,朵朵祥云,烟霏幽缈,问彩云飞向何处,我心随你飞翔。
彩云之南,蓝天高远,万山壁立,雪峰皑皑,翠谷幽深。我心在峰谷之间跌宕。
彩云之南,碧水泱泱,湖在“天上”,水在家旁,我心随之漾漾荡荡。
彩云之南,蝴蝶泉边,洱海铺翠,风花雪月,情意翩跹,我心痴迷于“五朵金花”之间。
彩云之南,泸沽湖上,格姆山旁,摩梭姑娘,情歌飞扬。母山母湖。拉措一家,我心依恋在母爱的天堂。
彩云之南,玉龙山上,神灵之乡,绝顶星河,寒威四方。湿漉漉的丽江,小桥流水,纳西人家。我心随“丽江古乐”悠悠飘扬。
彩云之南,澜沧江畔,风尾竹边,绿色海洋。傣家村寨,孔雀屏开,我心随孔雀之舞倘佯。
当你行走于彩云之南时,你才会真正意识到,祖国美丽的西南边陲是多么令人眷恋。心真的随着彩云飞翔了。
一路上,一种近乎神奇、神圣的人文景观,令人深深感动。那巍峨耸立起伏逶迤的云岭横断山脉所构成的大大小小、高高低低的山的雄峻和陡峭,每一条谷的幽深,每条江河湖“海”的碧波浩瀚与彪悍不羁,都有一种深不可测的神秘与沧桑感。
而我在半个多月的行走中,只是在国人最熟悉的也是最美丽的、最令人神往的几个城乡间,在彩云深处流连忘返。大理、泸沽湖、丽江、西双版纳不仅留下了我的足迹,更留下了几多思绪。
风花雪月皆有情
在昆明滇池边,我们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在我们身边纷飞捕食的红嘴鸥。这些从俄罗斯西伯利亚不远万里来春城过冬的鸥鸟有数万只,它们在岸边上下飞舞,从游人手上捕捉着食品,展现了人与鸟的亲密接触,场面煞是动人。
现在正是北方冰雪严寒的冬天。在这里,我们脱掉了厚厚的羽绒服换上春装。乘越野车从昆明到大理,使我大为惊讶的是,出了城不久,便进入了山区。我虽然知道云南是处于云贵高原,却不知云南几乎每座城池都是建在山与山之间的“坝子”上的。司机师傅说:我们所经过的是无量山系并非云南的高山区,到滇西北你再看高山吧。不过所见之山皆碧绿葱葱,一片苍翠。
一路上,我看到的另一种景象,便是见证了那变化多端的云。连地名都有云:彩云、祥云、西云……我们真是身处白云深处了。在山上你觉得自己是头顶云,脚踏云,腾云驾雾了。那祥云自由自在地在天上飘浮,彩云多缀在半空,似乎触手可及。有的如鳞片、如棉絮、如凤尾、如瀑布、如羊群……舒舒卷卷、自由自在、飘飘忽忽。真是风流云走,轻纱薄罗,依山体斜卷。倏忽间,横空飞行,光影斑驳。进大理城前,已近黄昏,霞光万道从丝丝缕缕的云中穿出,云似乎镶上了金红色边儿。真是瑰丽无比。那种空灵漂浮的浪漫最能感染旅人的心。
下关风,上关花,下关风吹上关花;
苍山雪,洱海月,洱海月照苍山雪。
这首诗是著名作家曹靖华对大理风光“风花雪月”的诗解。真是形象而深刻的概括。到大理第二天,我惊奇地发现,在这隆冬季节,满城许多高高的树上开着灿烂的粉红色的花。似桃花。但桃花是春三月才开呀!我惊奇地问当地人,答道:那是樱花。怎么冬天樱花会开?那是冬樱花呀!又见那些白族人家的白粉墙上爬满金黄色类似小喇叭的花朵。主人说,你若是三月来,会看到家家户户院内外和门前摆满了花。山茶花、白豆花、杜鹃花……山上山下,到处是花,那才美丽哪!至于下关的风,我倒没感受到,也许没到时候,也许因为北京的风也很凌厉。至于雪,在大理便是举目可望。那连绵百里的苍山十九峰,海拔在三四千米以上,山峰常年积雪。山峦间一片青黛色,苍翠蓊郁,它的奔泻而下的十八条清溪,流入洱海,成就了美丽的夜景——洱海明月。使我十分惊讶的是一个被雪山环抱的城市,却是花开如锦,温暖如春。难怪古人徐霞客都说它是“松荫塔影,隐现于雪痕月色之间”,真是人间美景。
对于大理的悠久历史和文献名邦之称,早有所闻。它早在西汉武帝元封二年就设为叶榆县。唐代的南诏国,宋代的大理国,至今均有遗址、遗物留存。现今的大理城为明洪武年间建筑的,城楼雄伟,市井俨然,苍山洱海,古朴幽深。所以大理几乎是天下每一个旅人梦想一游的地方。
到大理的第二天,当地的朋友便驱车陪我们绕洱海一周,让我们近距离地欣赏苍山和洱海的美景。清晨,朦胧的雾气还未散尽。远远望去,洱海当真如同大海一般浩瀚,一片铅灰色中透着蓝光。当朝阳升腾时,湖面波光粼粼。这个有二百四十多平方公里的高原湖,尽显其烟波浩淼的本色。果然是苍山的巍峨雄壮,洱海的妩媚秀丽,一望无垠。沿着洱海之滨,有一条绕湖而设的观海长廊和海滨大道。苍山为屏,玉海银苍,相互掩映,真是一幅天然的水墨风景画卷。
沿着洱海边和苍山麓及丘陵带都建起一幢幢美丽的具有白族建筑风格的大小别墅和民居。白族民居建筑很有特色,青瓦白墙,飞檐翘角,每幢山墙上都绘有线条简洁却十分雅致的图案。从远处看,在洱海边和苍山脚下闪烁着一颗颗白色的珍珠,煞是美丽壮观。在洱海的另一侧,我们看到了渔村和农村。渔民们悠闲自在地晒着渔网,路上,一匹匹小毛驴驮着果蔬,慢悠悠地前行,而主人却离驴儿数米远,慢悠悠地跟着。这大概是休鱼歇农时节吧。但田畦上却生长着绿油油的蚕豆苗儿。
在洱海岸边,有一个古老的小镇叫喜洲镇,是个最早的白族村,这里有热闹的小镇,有古色古香的典型白族民居群。我们直奔古民居老白族的宅第——严家大院。宅的原主人叫严宝成。他是民国时期龙云的部下,作过民国考试院院长。这座宅院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建成,虽不古老,但却体现了白族家居建筑的风格特点。“三坊一照壁”门楼“三滴水”,一进两院一天井。花园小巧玲珑。天井中种花养树,庭院显得恬静而幽雅。二层木结构的小楼,飞檐翘角,木雕精美。院内还有一花厅,正在举办白族古乐音乐会。处处体现出白族的民族风格。这里没有金庸小说中的侠义世界,却有着大理国和南诏国留下的璀璨文化和“文献名邦”的美称。
从古镇出来,直奔大理古城门。这应该是这座千年古城最具风采的建筑,它虽经过各朝各代,却仍挺立着,诉说着大理的古朴和沧桑。我们刚走进城楼,就被一群着各族鲜艳服装的小姑娘团团围住了,她们是要与我们合影。我自然高兴,但一问才知,每位姑娘与游人合影要收十元钱。我急忙退出包围圈,一手携一白族姑娘,一手拉一苗族姑娘,与她们在城门下拍了一张很有民族风情的合影(付款二十元)。苗族姑娘的百褶裙和白族姑娘帽上的“风花雪月”衬着背后的大理古城门楼,自是风情万种。
到大理来,大约无人不到迷人的蝴蝶泉看看。只是在这严冬季节,则空有蝴蝶之泉,却无千万只蝴蝶的聚会了。
蝴蝶泉公园很大。坐落在苍山云弄峰的神摩山下。尚未进园门,便见两棵高大的冬樱树,粉红色的花如云霞般灿烂。我们这些北方客都惊奇地围着樱花拍照。沿着一片竹林小路走到蝴蝶泉边,迎面只见一方用大石围起的大水池(泉)中竖起一块巨石,上书“蝴蝶泉”三个娟秀的红色大字。这是郭沫若题写的。此泉池面积达六十多平方米。泉水清澈见底,在石栏下面有五条龙在戏水,从龙口鼻中吐出了一串串水珠。泉池西北角有一棵千年合欢古树,每年春三月,花开满枝头,形酷似蝴蝶,发出异香,招来千万只蝴蝶,足须相连,结成一串串彩带。从树枝直垂泉池水面,五彩缤纷。郭沫若有诗为证:“蝴蝶泉头蝴蝶树,蝴蝶飞来十万数。首尾连接数公尺,自树下垂疑花序。五彩缤纷胜似花,随风飘摇朝复暮。蝶会游人多好奇,以物击之散还聚。”可惜,如此神奇景观未得见。在绿树红花的掩映下,各色鱼儿和白色的禽鸟在水中自在地游着。只见那水中倒映着蓝天白云及四周的参天古树,奇花异草,一时竟有如入仙境之感。一些过去只在书本上见到的植物:如曼陀罗、合欢树、悬钩子、冬樱、黄连木等,都在这里落地生根,真是万千植物的乐园。让我们乐而忘返。
蝴蝶泉又称“爱之泉”,至今还流传着不少爱情佳话:霞郎和雯姑,金花和阿鹏的影子,便倒映在清澈的泉水中了。从此便有了美丽的蝴蝶泉边蝴蝶会之恋。那“爱之泉”便不停地流到月牙潭、情人湖,流到浩瀚的洱海。
苍山脉脉,洱海苍苍,蝴蝶泉情悠悠,白族人待客的“三道茶”(一苦二甜三回味)的温馨……使我感悟:这一切不正是白族文化之本吗?
仙女湖,圣母山,摩梭人留恋在母爱间
走出大理,一种留恋情丝萦绕心头,但想到我们要去的是向往已久的女儿国——泸沽湖,心便又充满了憧憬。车最先路过的是宾川县。这里是水果之乡,沿途都是果园。金红色的蜜橘密密麻麻地挂满枝头,煞是可爱。司机师傅满面笑容地在丰硕的果实间采摘着,丰收的喜气感染着每个人。重新上路时,这喜气便被重重的山峰,艰险的山路吸走了。此时我们已行进在十万险山的横断山脉中了。沿途山连山,峰重峰,重重叠叠,弯弯曲曲,从谷底到峰巅上千米到数千米。从峰顶望谷底如同从飞机上俯瞰陆地。山村的房屋如火柴盒一般。车在盘旋的山路上行驶,且是连续的S弯道。开始我还数着经过的弯道,数到三百后便数不下去了。因为心情紧张,也因为山道之弯太多太险了,我的心已悬在空中。啊,前面又是一个急转弯,我们的越野车急刹车停下,呀,真悬!眼看着有四辆载重大卡车在弯道上左腾右挪地错车。窄窄的山道挤得无隙可挪。回头看那盘旋到谷底的山路,真是惊心动魄,险象环生,我惊出了一身冷汗。
我们看到在山峰与山谷之间,凡是有褶皱和山坳及小小峡谷平坝之地都种上了玉米之类的谷物及菜蔬。山民们一锄一镐精心地耕耘着小小的山地,这情景使我骤然想到:云南不是只有昆明湖的鸥鸟纷飞和大理的风花雪月,也不只是美丽的雪山绿色的古城丽江以及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孔雀和傣家风情。还有山民们在险山隙地间艰难地耕耘着。虽然如今生产方式有些“现代化”了,但是谁能改变这千万年生成的险山恶水呢?山民们祖祖辈辈,经历千百年的沧桑,以这个险山恶水为生命的母体繁衍着,世世代代,生生不息地把百万大山踏在脚下。而且能播种出生命的奇迹,那每一寸山地,每一粒粮食,每一株茶花,都见证着山民们的辛劳汗水。这该是怎样的坚韧。我望着险峻的群山和在山中耕种的山民们,油然而生出一种敬意。
不知经过了多少艰险的弯弯山道,又转过一个山垭口,豁然,眼前出现了奇迹。在一片蔚蓝的天空下面,群山围着一泓幽蓝幽蓝的湖水。“啊,太神奇了。简直是人间仙境!”我们都惊诧得目瞪口呆。真是此景只应天上有啊!如梦如幻,思绪如彩云飞腾在泸沽湖上空了。
我们走向湖边,只见那湖水仿佛凝脂般一波不兴。湖面一群群鸭鸥也像凝固在水面上了。那逶迤的群山一片黛青色,围着湛蓝的湖水,俨然是这仙湖的护卫。
越野车如我们心情一样,快速地奔向湖边的旅馆。这是一家走婚族的母系家族戈哲家经营的旅社。院内三面皆是二层木楼。我们住在二楼。房间如内地一般旅舍。二床一卫生间。一面窗正好朝向泸沽湖,真是太好了,我乐得竟欢呼起来。
泸沽湖坐落在青藏高原东南,摩梭人称为“谢纳米”,即母海之意。它在莽莽的横断山脉中段,海拔一般在两千五百至三千五百米。泸沽湖面五十多平方公里。湖面海拔两千六百九十米七,水深四十八米三。最深处九十米三。湖水宁静,有一种女性的温柔美,被称为与世无争的桃花源。这里千百年来生活着世间罕见的延续着母系氏族社会特点的摩梭人。人称“女儿国”。可以说,泸沽湖是人类母系氏族在地球上的最后遗迹。这里就连神话传说都赋予了女性的温柔、女性的魅力和母爱的光辉。母亲、外婆、祖母是摩梭人最崇敬最热爱的人物。
走近泸沽湖,犹如走近了历史的深处。
摩梭人具有悠久的历史。有文字可考的可以追溯到西汉元鼎六年(即公元前一一一年),迄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在这滇川交界的地方,他们世代繁衍生息着,从与世隔绝的土司统治的社会,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摩梭人从奴隶制社会一跃跨越了几个世纪,同全国人民一起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这种跨越并未改变女性为核心的社会结构。国家和社会尊重这种以女性为轴心的社会形式。但据说这种母系大家庭现在已有明显的变化。如今这里已出现了三种婚姻形式。即:阿夏婚(即走婚),阿夏同居婚和正式登记结婚。却仍以走婚为主,因而仍维系着母系家庭结构。
当晚,当地朋友请来三位风姿绰约的摩梭姑娘与我们联欢。她们穿着鲜亮的民族服装,个个生得漂亮。高高的个儿(大约都有一米七左右),头上配有珍珠链和美丽的绒花。上着一件编襟短衫,百褶裙有半边斜垂着。有点儿像古代女人的褶裙,很鲜艳。这就是她们的民族服饰。她们都会讲汉语,神采飞扬的模样十分可爱。三个姑娘,一个叫达巴·纳珠拉姆;一个叫阿瓦·彩丽卓玛;一个叫巴尔·卓玛拉措。多美丽的名字。在我们的邀请下她们用民族语言唱了两首民歌。一首是献给母亲的,一首是献给情人(阿夏)的。歌声嘹亮高亢,音调悠长,是纯粹原生态的;是那种能够穿透仙女山和母亲湖上空的云雾般高亢的原生态,非同我们在电视上看过的那些经过训练的原生态歌手的歌声,如同泸沽湖般悠远而绵长的真情吟唱。
入夜,我们在月光下的泸沽湖畔漫步,万籁俱寂,静谧得如同神话中的世界。这里没有城市的辉煌灯火,冬天的湖上也没有渔火。明镜般的湖面上只泛着粼粼的波光,偶尔能听到的鱼跃声和天籁声。我真切地感到,此生从未遇到这样古朴恬静的夜。我们在湖边流连良久。
晨曦中,我顾不上梳洗,急忙坐在窗前,目不转睛地观看泸沽湖。呀!湖上似乎起了风,湖水泛起轻微波浪。朝阳照在湖上,波光闪烁,湖面上几十只数百只黑色的野鸭次第飞来,在湖上随波嬉戏,还不时地潜水捉鱼。湖上有薄薄的雾霭,是泸沽湖这个睡美人蝉翼般的面纱。在银灰色的云间蓦地抖闪出一道灿烂的红光,云端的朝阳,四射的霞光,使湖边的母山瞬间明朗起来。
转湖回来,旅社的主人家已为我们准备好早餐。一杯酽酽的酥油茶,热气腾腾的馒头和面条。摩梭人制作的酥油茶有奶香和淡淡的碱膻味。这里是一大间祖母屋,是全家族的生活中心。在进门的长方形案上,卧放着一头腊好的肥猪(摩梭人每到年节杀猪后便剔出内脏和瘦肉,而后将整猪身腊腌,叫它猪膘。遇喜庆日或佳节切食之)。在锅庄的下方是房屋的中心——火塘。老祖母又是火塘的中心人物。此时,戈哲家的老祖母正在火塘边烤着馍。她已八十三岁,穿着一身深色的民族服装,白发包在黑色的头帕里,满脸皱纹留下了岁月的沧桑,她默默地为火塘加炭。我们向她问好,同她合影,她只是微微地笑着。这位老祖母是戈哲家劳苦功高受全家尊重的人。这家还有母亲、女儿、儿子、舅舅、外甥女等。全家都参加旅社的管理和劳动。是个典型的以母系血缘为核心的大家族。
当地朋友为我们请来一位向导。她是在泸沽湖边长大的摩梭姑娘,名叫格桑娜姆(汉名叫杨树梅),刚从大学林业系毕业。操一口纯熟的普通话,一脸纯朴,一脸真诚,真是位难得的向导。她亲切地拉着我走向泸沽湖边。因为是冬季,游人少,我们竟是泸沽湖的第一批游客。湖水仍是湛蓝,微波轻轻地拍着岸,好像在拍手欢迎我们。一排排的猪槽船横列在岸边,似乎在等待着我们。格桑娜姆请来了两位摇船的摩梭小阿哥。噢,好帅的小阿哥呦!执橹的小阿哥身着花缎子民族装,足蹬黑色马靴,头戴牛仔帽。掌舵的小阿哥身穿黑色毛衣外罩一件米色马甲,足下也是一双马靴,十分豪爽,英气十足。登上猪槽船,我们都被那神奇的湖水吸引住了。我惊讶这湖水竟然是透明的。在幽蓝的天空下,清晰可见湖底,靠岸的水中,长着头发般的植物,一群群小鱼儿穿游其间。我们伸手轻轻地抚摸着湖水。只觉得柔柔的,软软的,如同慈爱的母亲在轻抚她的婴儿。船渐行,水渐深,仍是那般清澈,那般幽蓝,鸥鸟在湖面上自由飞翔,鱼儿在水中自在潜游,远处飘来了渔歌……让人有一种幻梦般的感觉。真是如诗如画如梦啊!
顷刻,船划进阳光里,群山和岸上的森林都染上了橘红色,水也呈现出澄黄、橘红色。湖水尽染上朝霞,真是一幅美丽的朝霞图,我们看得目瞪口呆!“小阿哥,唱支情歌吧!”我们和摩梭人没有陌生感和间离感,自然亲切地邀请划船的小阿哥唱歌。于是,划船的小阿哥开口唱道“不管你从哪里来,来的都是客,玛达米”,“美丽的泸沽湖哟,善良的母亲站在湖边微笑。问阿妈为什么这么快活,她说,因为美丽的女儿已经长大成人……”“经历过千难万险忘却了,唯独忘不了母亲的恩情”,又唱“划船的小阿哥啊,阿妹初次来相会,小阿妹啊小阿妹,相会就是有缘分……”歌声甜蜜而悠扬。于是游人和阿哥互相拉歌,欢声高唱,此起彼伏。这纯情的歌声,溶进了清清的碧蓝的泸沽湖水中。摩梭人的歌,多半是献给母亲和情人的。摩梭人对母亲的爱是绝对的,他们歌颂母亲的神圣,他们认为那山,是母亲的灵;那湖,是母亲的魂。人们生活在博大的母爱中。在这里,人们,包括我们这些游人,都不自禁地深深陷入对母亲和女性的尊敬与颂扬之中。泛观今日之世界和社会,妇女大都属于附庸地位,只有在泸沽湖,女人才真正有一方属于自己的领地。在这里,我重温以母亲为轴心的氏族公社那种和谐、安泰、友爱的情感。我冒昧地问掌舵的小阿哥他家是否走婚家族,他很泰然地告诉我:他的父母是通过阿夏同居婚建立了新的家庭,他们兄弟姐妹也要走“阿夏婚”之路。我又问格桑娜姆(小杨),她说她家是阿夏婚的母系家族,父母不住在一起。母亲生了三个女儿。姐姐在外地已自主结婚,建立了家庭,妹妹在高中念书。自己在大学读书期间与学长建立了恋爱关系,准备明年结婚。这个母系家庭的女儿们已走上了另一条婚姻之路。这是部分摩梭人走向一夫一妻制的婚姻。不过,格桑娜姆说,她不仅尊重走婚的习俗,而且觉得泸沽湖摩梭人的社会民风十分淳朴。没有尔虞我诈,没有以强凌弱,特别对于妇女的尊重和爱护是真心诚意的。现在走婚的父母虽不在一家,但有的还是互有联系和互相帮助的。
这里还有一个“女儿国阿夏园”。是个观光、展览性质的摩梭人民居。形象地展示出摩梭人的走婚家族形式。这是座木质的二层楼房。有祖母的,母亲的,女儿们和舅舅们的房间。其中最醒目的是女儿的花楼,在花楼外墙上设有几个凹进墙体的脚窝,走婚的情人登上几级“脚窝”才能爬上花楼。这时姑娘正在窗内等待阿夏的到来。一夜男欢女爱,待到雄鸡报晓时,阿夏又要悄悄地从窗口爬出,回到自己的母家。花楼房内有一张红木的雕花床及被褥、梳妆等简单用品家具。经济情况较好的摩梭人家,每个女儿都有一间“花楼”。生儿育女,世世代代,儿女们就只同祖母、母亲、姨母、舅舅等亲人和乐融融地生活在一起。
近些年来,交通发达了,受外面世界的影响,商业之风也吹进这曾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摩梭人也经营商业、旅游业。打破了完全与世隔绝单纯从事农牧渔业的格局,发展了自己的经济。我们来到了环湖的商业区,仍觉得是那么恬静。木质的两三层小楼依山傍水,错落有致,很有民族风味。商品齐全,从日用品、食品到具有民族特色的各种小商品应有尽有。格桑娜姆说,商业街的房屋都是本地摩梭人盖的,但大部分出租给外地人。因为本地人没有外地外省人会经营,会赚钱。
从摩梭人的商业街归来,格桑女神山(狮子山)上祥云缭绕。夕阳在女神山上披上了金红色的晚霞。泸沽湖上金波与烟霞齐舞,如梦如幻。在那些山坡上或大大小小山峰平台上有经幡和红的、白的、蓝的三角旗随风飘动。昭示摩梭人对藏传佛教的信仰。
入夜,湖边本该进行的篝火晚会,因冬季客少被取消了。我静静地站在湖边聆听着,泸沽湖静得让你只听到了自己的呼吸声。天上挂着的繁星和月亮让你觉得是此生所见到的最明亮,最耀眼,离你最近的夜空。
这时,当地朋友邀我们去一个母系家庭作客。这是我十分向往的。我们踏着月光,沿着湖边来到一个叫“女儿风情园”的院落。这是个真实的女儿国。一个很大的四合院,有两幢木质的二层小楼。旅游季节这就是个初具规模的旅社。这个“女儿国”的女主人叫木日次拉措,只有四十六岁。我们一行进入她家的“祖母屋”,老少四位女子正在火塘边烤火。炊壶正蒸腾出朵朵热气。见到我们这些不速之客,主人毫不惊奇,热情地拉着我们坐在火塘边的沙发上。小姑娘是这家的女儿,热情地为每位客人送上一杯蜜水。屋里的三位中年妇女,有两位是主人木日次拉措的闺中密友,阿青卓玛和冰玛拉姆。她们从小在一起长大,现在各自经营一家旅馆。冬闲时每天晚上相聚,守在火塘边聊天。说说笑笑十分开心。有意思的是这不同姓氏的摩梭三姐妹都是走婚家族,而且都生有两个女儿,祖母已经不在世,也无兄弟和舅父。母亲们的阿夏都在另外的家庭。三姐妹都是各自家族能干的母亲。主持着一家的生产生活各种事宜。木日次拉措很能干,不仅经营着一家旅馆,而且干农活、划游船样样不落后。家里经济实力较殷实。这个大祖母房里有电视,沙发,几组大壁柜,桌椅等家具,都围着锅庄和火塘设置,外围似乎还有不少矮柜,墙上挂着大幅家族照片和画,房梁上垂挂着一串串腊肉。很温馨,很和睦,很欢乐的气氛环绕在大屋中。我坐在她们中间,她们异口同声地要我做她们家的祖母。木日次拉措不停地剥着她们自种的葵花籽仁,一把把地送到我手中。小姑娘不断地给我们添加蜜水。她们都能操着云南普通话同我们交谈,说说笑笑真像一家人。三姐妹都没上过学,基本上不认字。阿青卓玛身穿一件粉红色的马甲,笑呵呵地讲她做生意闹的笑话。她说,当初自己连十元和百元的票子都分不清,有一次一位客人结账时说自己没有带现金,要到镇上银行,把钱拨在她的账号上。她就不假思索地同意了。客人说:你不怕我跑了,骗你吗?她却回答说:我对你那么好,你好意思骗我吗?说得大家哄堂大笑。木日次拉措也说:“反正他们(客人)算对了就行,我相信他们。”“没受过骗吗?”我好奇的地问。“还真没受过骗。”“哈哈,那你们算是遇到好人了。”这些摩梭姐妹可真是桃花源中人哪。“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的格言,在这里似乎是多余的。多么纯真的摩梭人啊!
火塘里的炭火仍悠然的燃着,火光映在木日次拉措姐妹们那黝黑泛红的脸上,闪着极淳朴、极慈祥、极动人的母性光辉。于是我又大胆地问起她们孩子们的父亲的情况。她们毫不避讳,开朗地告诉我,孩子的爸爸有时过来看看 (不必早晚爬花楼),也给上学的女儿们交学费,也承担部分家务,但比他们作舅舅的责任小多了。三姐妹各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安排,她们已习惯了这种自由自在的生活,乐在其中了。我问她们是否会干涉未婚的女儿们走哪条婚姻之路。她们爽朗地说:“绝不干涉,那是女儿们的自由。”木日次拉措的二女儿冰玛拉姆也笑容可掬地望着我,这便是默契。我的心真切地被他们母性之爱深深感染了。就让这些女儿们、母亲们永远生活在这方快乐的母性天堂吧。泸沽湖不仅养育了一方幸福的女性,也会保护她们,正如那圣母山和母亲湖的传说。在现实中,我们中国这个大社会,女性大多虽已走出附庸地位,只有在泸沽湖,才真正体现了女性当家作主,家庭以女性为中心的特色。看来泸沽湖真是因摩梭女儿的爱情而美丽;女儿国因泸沽湖的美妙而神秘。我在想,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开放,随着现代文明的涌入,随着旅游事业的发展,摩梭人还会还能固守住“阿夏婚”和母系氏族社会的形态吗?我曾向已走出去读完大学的摩梭族姑娘格桑娜姆提过这个问题。她爽朗地说:那就要顺其自然了。她迷恋这个母系小社会的纯朴与安宁,但也不担心大社会的影响,相信该来的是挡不住的。摩梭姑娘杨二车娜姆不是都走到国外去了吗?也许,泸沽湖水依然长流,圣母山依然长青,天荒地老,母系家族祖母、母亲和女儿们会世世代代传承下去,因为这个“女儿国”具有最稳固和活力的社会形态;具有最纯洁、最和谐的家庭关系!这可能是许多年轻的摩梭人的心声。
不知不觉间,在拉措家说说笑笑两个多小时过去了。夜已深,不便再打扰,我们便起身告辞,拉措拉着我的手执意挽留,说:他们有公事的让他们走,你要留下来做我们的祖母,我们房间多着呢,一定要多多住些日子,能长期留下来最好,我们只让你快乐!其实,我也被她们的真诚所感染,想留下来,同这些纯真的摩梭女人一起生活几天,但女儿的行程已不能更改。只得怀着难以尽诉的深深眷恋和依依惜别的心情向她们告别。她们三姐妹及女儿拉着我们的手,一直送到“女儿风情园”的大门外,她们殷切地嘱咐:明年夏天可一定来呀!我的眼睛朦胧着雾霭。
多么可爱可亲纯真的摩梭女人啊!在她们中间,没有陌生感,没有时空差,也没有民族隔阂,只有熟稔、温馨和一种深深的恋情。
第二天清晨,当我们告别那悠静、清碧如镜的泸沽湖和可爱可亲的摩梭人时,远山已现出一抹朝霞,无限依依,心中满含感动与依恋。在我的大半生中,曾走过许多名城与名山大川,都不曾有过这样的眷恋之情。当越野车又上路时,只见泸沽湖水仍然是那样湛蓝,依然鸣奏着流韵天成的天籁之音;圣母山仍然亲密地环抱着母湖,摩梭人又划着他们的猪槽船,悠然地唱着渔歌,在湖上撒开了网。当车又转过那个山垭口时,泸沽湖远去了。再见啦,木日次拉措,再见了,阿青卓玛们!你们那清纯和温柔的母性目光将在我的心上永久留痕。
湿漉漉的丽江,小桥流水,古乐悠扬,纳西人家,城不设防
现在似乎全世界都知道,在中国的西南隅,有座七百多年的古城——丽江。人皆向往之。
一脚踏进丽江,有第一次进姑苏古城的那种水淋淋、湿漉漉的感觉。江南姑苏的水是湖水,它因有“十里楼台烟雨”而妩媚。同样是小桥流水人家,丽江的水却是来自五千五百多米的雪山——玉龙山。奔泻而下的雪水,水质清冽,穿街过巷环镇而流,可谓高原水乡了。在丽江无论怎么走,都走不出水的萦绕。而它的水,又与那“奔腾到海不复回”的长江连在一起。丽江,丽江,它是因美丽的金沙江而得名的。万里长江在那里转了个大弯,绕城而过直奔长江。
再有,姑苏无法相比的,那里有座很独特的大山——巍峨的玉龙雪山。这座山地处青藏高原西南部与横断山脉交接,它的十三峰如一道道屏障,由南向北排列,南北纵长三十五公里,东西横宽十二公里。最高峰达五千五百九十六米。山上常年积雪,是地球上离赤道最近的一座大雪山。古代旅行家徐霞客称赞:“漾荡众壑,领挈诸腾。”看来,丽江是深得“玉壁金川”之盛的。
古城的不设防——无围墙成为它的特色。传说是历代木姓土司怕木字加上框(围墙)便成了“困”字。故而不设城墙。其实是木氏的统治者利用了山川河流作为天然屏障。北有高不可攀的玉龙山,南有水流湍急的金沙江,岂不更胜于城墙。木氏土司十三代统治丽江四百七十多年。这样的不设防岂不更稳固。
这座古城始建于宋末元初。自明朝伊始,聪明的木氏土司积极向明王朝廷靠拢,南御大理、北拒吐蕃,自命木姓(包含明朝皇帝朱姓之意)。积极吸纳中原文化。我在来丽江之前,刚刚看过电视剧《木府风云》,不知剧情有多少源于历史真实,便向当地朋友咨询,恰好当场有一位中年男子说:“我就是木土司的第二十五代世孙。”他的名字叫木军伟。我一阵惊喜,真是太巧了。原以为他可以陪我们参观“木府”,但不巧,他第二天的日程已定。他说,没关系,木府有讲解员,比我知道的多。
第二天,我们就急于到木府参观。嗬,这么金碧辉煌!当我见到这个纳西王宫时,真是大吃一惊。这真是北京紫禁城的缩影。石牌坊、忠义坊、仪门、仿故宫金水桥的马鞍桥、守门的石狮子、照壁、亭台楼阁,在东西三百六十九米的中轴线上依次排列着,议事厅、护法殿、万卷楼、光碧楼,直至土司的后花园万古楼,一派的宫廷建筑风格,雕梁画栋,金碧辉煌!
电视剧中的木得,木增,历史上确有其人。木增是木氏土司统治时期的集大成者,是木府第十三任土司。他被纳西族百姓称为“木天王”,颇有人气。他十一岁袭任知府,任期长达二十七年,壮年引退。还是一位颇有成就的诗人。木增与明朝地理学家徐霞客交往密切。徐霞客在丽江期间曾要看看木府,但木增从未让徐霞客走进木府,大约是因木府建筑已严重“僭越”吧!这个木府到了清朝便“盛极而衰”,木氏土司的权威也日渐下降。那个“东壁图书照丽阳,湖边文笔碧霄翔……列岫层峦皆几案,行云流水尽文章……”(摘木增诗)的木氏王府势力已逐渐败落。繁华与专权已成为历史。
因为在丽江停留的时间太短,所以走到老街上总有迷路的感觉。它的街巷建筑和街道不像北方那样正东正西,正南正北。城中心有个四方街。由此呈放射状的街衢和道路四通八达,四方街仿佛是古城的心脏,它既是古城各条街道的终点,又是各条街道的起点。其广场又是古城的经贸中心,广场进口处,有几架老式的木制水车,标明它的古老。在一座古色古香的牌坊上有江泽民的题字:世界文化遗产——丽江古城。
白天从高处俯瞰这座古城,在蓝天白云、银雕玉壁般的千年冰峰玉龙山的映衬下,一片高低起伏的灰瓦屋顶,鳞次栉比;五花石的街道被水冲刷过后,总是湿漉漉、亮晶晶的。入夜,我们走过繁华的街衢,宫灯闪闪烁烁、迷迷离离、朦朦胧胧的光影,真让人有走进古代的感觉。我想,如果那里灯火辉煌,便不是丽江了。我不想进店铺买什么,更不想看那些五光十色的商品。就是想沿着水渠,踩着老街的五花石慢慢地走着,想着。仿佛我也走进了丽江那悠久的历史,仿佛似曾相识,仿佛从前我曾在这里住过。
丽江古城主体居民是纳西族人。据说古时纳西族是当地土著与北方南迁而来的其他民族融合而成。纳西族人精明能干,性格开朗,素有儒雅之风。他们踏踏实实地走过了历史,经过了历朝历代而兴旺不衰,这个不到三十万人的民族竟有自己的文化、文字和文明。
这座古城完整地将中国西南纳西族、汉族、藏族、白族等民族文化水乳交融,使儒、佛、道、东巴四教和谐并存。让它成为香格里拉式的人间净土。
在丽江博物馆,我看到了东巴的象形文字,具有浓厚的图文并茂的特点。除了甲骨文之外,我还未见过如此象形的文字。一个句子或一个段落就像一幅主观画。据说东巴象形文字是世界上仅存的仍在使用(某种特定领域使用)的象形文字。在我看来,每个字都是一幅图画,很生动。这是纳西族引以为荣的文化。
古城另一值得称道的重要文化品牌便是纳西古乐和白沙细乐。据说纳西古乐并非纯粹由纳西民乐创作而成。而是纳西民族在自己民乐的基础上,吸收了从明朝时期大量传播进入丽江的汉族音乐。白沙细乐原系纳西民族独创,但它却保留了中原地区流传的唐、宋词及元曲的音乐元素。离开丽江前夕,我们聆听了这美妙的音乐。这是专门的“大研纳西古乐会”。当大幕开启时,我为之一惊。因为“乐手”们大多是白鬓老者,各个身穿唐服,手持乐器(大部分是弹拨乐器)。最先出场的“报幕者”,是全世界都知名的纳西古乐的传奇人物(也是纳西古乐的保护者)宣科。他已八十岁,却十分健朗,是位学者型的人物。他用中英语介绍了纳西古乐的来历与影响。为纳西古乐的流传与弘扬光大鼓与呼。当地人说“没有宣科就没有纳西古乐的今天”。他带领那个“三老”(古老的音乐,古老的乐器,古老的艺人)乐队曾到英国及欧洲一些国家去演出。我静静地聆听着每曲古乐,顿觉有一种古曲遗风萦绕耳边。《木府风云》中那首《净土》就有纳西古乐的韵音。忽然,一位白发老人竟自弹自唱:“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这不是李煜的《浪淘沙》吗?原来这个“三老乐团”也熟悉唐、宋词和元曲等古曲。这古乐竟唤回了人们千年以前的回忆。真是太美妙了。这个几乎已被汉人遗忘的古音,竟被这个温厚的少数民族保存下来。我的眼湿润了。原来宣科苦心经营甚至是声嘶力竭鼓与呼的,是如此美妙的古乐。不仅应该保留下来,而且应该让它永远流传下去。但是,只靠这些七八十岁的老人,能传承下去吗?古乐在呼唤后继之人。
茶马古道悠悠马帮
比丽江古城还古老的是小镇束河古镇。朋友领我们来拜会这座古城的源头。这便是丽江源头的茶马古道第一驿站。
丽江的茶马古道,其历史和文化背景是极悠久、极艰险的古代连接现代的重要桥梁。是古时滇藏川贸易、物流往来的重要通道。也是建造与行走其间者作出重大牺牲道路。它修造在横断山脉的险山恶水之间,是在原始森林和险山恶水之间盘旋绵延的一条古老而神秘且有着众多人马牺牲的道路。它就是世界上地势最高、最险峻的经济、文化、宗教传播的茶马古道。
这条茶马古道,是靠山地之舟——马帮才运转起来的,马帮是高原上流动的希望。在江不能行舟,路不能通车的高山峡谷中,在鸟兽绝迹的峭壁悬崖上,从远古就有勇武之士,赶着马,驮着物资,在那危险的陡崖羊肠小道上穿行。不知有多少人和马葬身于这条古道。应该说,他们不仅踏破了千年的深山密林与风霜,也写就了这篇伟大的交通历史。
在丽江我访问了那个最古老的小镇。这里人称古道第一境,它是丽江新城与老城的分界处,也是古代南北马帮的驿站。马帮南来北往都要在这里休整,保养马匹交流货物。从北方从藏区来的马帮由此进城,而往大理方向去的马帮也由此出城。今日丽江能呈现出多元文化渗融共存,与“茶马古道”咽喉之地的历史地位密切相关。
在这个叫做束河的古镇,我看到许多古色古香的街道和商店。茶、玉制品、五颜六色的商品琳琅满目。一条永不枯涸的小溪沿着商埠货栈及各色民居潺潺流淌。其间有若干小桥分布其间。街两旁及桥畔,一家一户以自己家为店铺,招揽过往的商客入门,居民们都把自己各种小商品、时鲜水果等摆在路边叫卖。想必这也是古代茶马古道“第一街”情景再现。
随着当地朋友走出古镇一个出口。这里有一排木栅栏,且有一条道路通往镇外的“茶马古道”。一边是连片的农田,一边有大山和丛林。岁月沧桑,古道已隐于草木之中,而冥冥中萦绕耳际的马铃声,带出那份落寞情致。遥想着那曾飘洒在古道上的风霜雨雪,不禁黯然。
我们默默地从原路返回。在一个胡同口,见墙上挂一块牌子,指明对面院子是古代茶马古道上一位王姓马帮头(马锅头)的故居。我十分兴奋地一脚踏进门。这是个很典型的纳西族人古朴的小院。青石铺地,一个小天井,两层青砖小楼,院中有位老人坐在躺椅上晒太阳。一个小伙子在小楼廊前摆弄电脑。一位小姑娘迎上前问我们来意。“很想看看老锅头的故居啊。”姑娘操着普通话说,“欢迎,你们随便看吧,但不能拍照。”说完便走开了。我们登上二楼,这是几间木板间隔的房间,堆一些杂物,没有发现古时马锅头时期遗留的事物、资料或图片。一副对联迎在眼前:“古道情悠,岁月美丽。”显然,这不是供参观的展览馆,也不卖门票,自然,主人也没有解说的义务。但这个家族有几代人都是马锅头。就是说这个王姓家族几代人都在那古老的茶马古道上跋涉过。同行的当地朋友告诉我,当地马帮曾在只有二尺宽的山道上行走,马在深山的石板上竟留下二寸多深的马蹄印。深山洞穴中,有马帮留下的被烟熏黑的石壁,这些无数代的马帮风雨兼程,留下的不仅是马蹄印,也有森森白骨。我耳边仿佛响起那凄凉的马铃声。岁月悠悠,古道已渐隐于草木之中。
在小院里,我走到小伙子跟前,主动与他搭话,问他的祖辈马帮情况。他并不多言,只告诉我,他是王老马帮头的三十三世孙。而后语重心长地说:马帮是一种古老文化,不能只是“到此一游”而已。小伙子这句话让我颇感惊奇,是警告,还是提醒我不要只满足于“到此一游”?我说:“你这话我极赞同。”小伙子这才有遇知音之感。说,古代的马帮和茶马古道,是历史,是一种文化史,是值得研究和纪念的。他的祖辈就是从这悠久的历史文化中一路走来。他们凭着顽强不屈,凭着本能的韧劲,从前辈辟出的道路不断拓展,付出了无数的牺牲。他说,茶马古道上的每个石子都是文化,都是无数马帮们的汗水与鲜血铺就的。小伙子这一番话,让我沉思,让我满含热泪地告诉他和这老马锅头的小院,我会思考那个马帮文化的。
我们在返回驻地时,在一座山下堵车一个多小时。竟意外地发现,在那座青悠悠的山下崖边竟有一条斑驳细长弯弯曲曲的小路。一边是大山,一边是河水。当地人说,那就是茶马古道。我们仔细分辨,才发现那小路被杂草和青苔及乱石掩盖着,但仍能看出那里埋藏的马帮的沧桑岁月。此时我又想起老作家李纳大姐曾对我说过的故事。
李纳的故乡是云南路南县。她说她童年时,每听到小朋友们大呼大叫“马帮来啦”便非常兴奋,呼唤出男女老少的人群。孩子们大声数着马的数目,特别喜欢那匹带头马。高大、光滑、迈着坚实的步伐走在大队前头。额上挂一面镜子,在红缨中闪闪发光,像挂着绶带的将军。孩子们笑闹着,高声赞叹着,想唤起马锅头看自己一眼。大家巴望着没有尽头的马帮,马帮在人们心目中播下了神秘感。男孩们跟着马帮奔跑,一心想加入马帮,寻找赶马人的浪漫情调……可见马帮不仅给当地人们带来了神秘感,也带来了一种憧憬和希望。尽管这历史、这文化也给人带来了凄凉的回味。
哦!马帮,你的歌声在马背上流传,悠悠的马帮,古老的马帮,长长细细的山路,弯弯曲曲如同梦幻,几多期待,路途漫长遥远,不惧风雪严寒。你们的期待,你们的忍耐,你们的艰险奔波,你们的牺牲……你们可曾想过吗,那火塘温暖着你们的身心,那悠长的古道,筑就了未来。
程 豁:无祖籍山东莱阳,生长于辽河西岸的台安县。1948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转业后从事新闻记者,编辑工作四十余年。先后在齐齐哈尔日报、北京日报、中国煤炭报任记者、编辑、主人编辑、副刊部主任。致力于散文,报告文学创作。曾发表散文,报告文学作品数百篇。有七篇获省部文学奖。获中国当代散文集,载《中国散文学家大辞典》等。著有散文集《向太阳倾诉》、《心旅》等。现为中国煤矿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