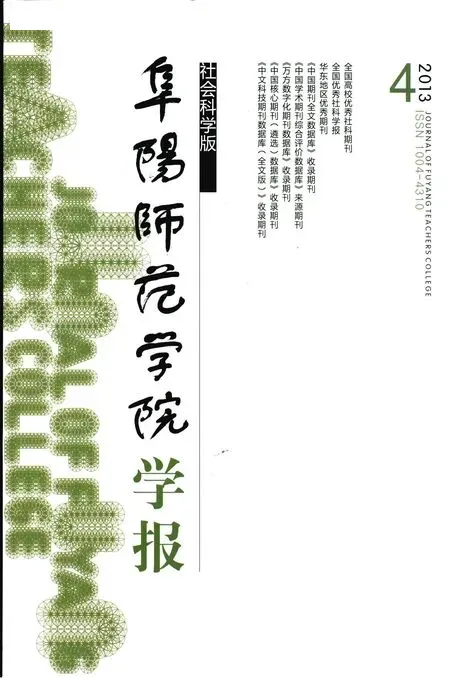浅谈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困境
2013-04-18陈连锦
陈连锦
(黎明职业大学人文系,福建 泉州 362000)
20 世纪80年代,受西方新历史主义的影响,中国文坛出现了刘震云、苏童、陈忠实等新历史主义小说家的创作。与传统历史小说的重历史真实,重正面、崇高人物的塑造,重主体意识比较起来,新历史主义小说在历史观、主体意识、人物形象、价值立场方面表现出与传统的历史小说创作十分迥异的一面,一度给文坛注入了许多新鲜的血液。但是,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偏离、缺乏理性制约的新历史主义小说创作很快在历史观、主体意识、人物形象、价值立场方面遭逢困境。困境引起转型,一些新历史主义小说家在发现西方新历史主义的不足之后,纷纷寻求新的适合本土的创作风格。
一、历史真实陷入虚无主义
传统历史小说表现的历史真实是客观的,作家们是按照历史的规律、历史的真实事件的记载来展开对历史的有序介绍,“作家所叙述的历史是严格按历史文献佐证的历史事实进行叙述,在尊重历史真实的前提下再进行合理有限的艺术想象和创造”[1],如《李自成》、《皖南事变》、《曾国藩》等,其主要人物与重大事件都是忠实于史料的。受西方新历史主义影响的新历史主义小说家们“不再向正史取材,不相信正史,不相信御用文人的话,宁可相信野史”[2],另外,他们认为历史是多元的,不可能存在真正的历史真实,任何历史真实都是个人化的阐释。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历史观没有整齐划一的历史观念,作家们用各自的兴趣来把玩历史,来呈现他们心中的历史真实。
在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中,严肃的历史完全变味了,成了一出闹剧,一出家族间争来抢去的历史嬉戏的闹剧;在刘震云的《故乡面和花朵》中,历史的真实只是个人对家乡的回忆;在莫言的《红高粱》中,历史真实只是个人的心理独特体验的呈现;在陈忠实的《白鹿原》中,阶级斗争的历史并不是作者表现的重心,历史成了白鹿两家三代人之间人性和人格方面的纠缠;在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中,小说对1942年发生在河南的自然灾害等历史事实做了多种可能性的猜测,小说的历史真实变成了语言的叙述性游戏。有评论认为,“这种勾兑的历史故事,根本无力更无意于贴近或承担历史史实,它不过是借助于年代不详和似真似幻的历史符号做虚构历史的话语游戏”[3]。但是,我们不难看到这样的现象,如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和陈忠实的《白鹿原》在摆脱了主流、正统的历史观之后,其实不自觉地陷了另外一种的个人主义的历史真实的表述。而且,他们强迫别人接受他们的这种表述。个人化言说的历史真实,让历史陷入了虚无主义的泥沼中。
一味地背离现实的想象力的发挥,毫无根据地虚构,这样的历史小说其实只是披着历史的外衣而已。历史小说除了要有历史真实的呈现之外,还应该有对历史规律、历史走向的把握。历史真实的呈现应该是以一定的历史真实作为依据的,作家可以有适当发挥的空间,但如果一味地质疑史载内容的真实性,那么,其创作势必会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迷宫,历史文学也将失去意义。如果缺乏对历史走向的体现,那样的创作肯定是经不起时间的考验的。
二、作家主体意识明显缺失
传统的历史小说中,作家肩负着民族、国家的代言人的重任,他们会在小说中极力呈现崇高的一面。革命历史小说中,文中的主人公为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等,他们尽管有细节上的不足,但是,他们为了国家和集体的利益,勇于牺牲自我,具有革命者的崇高气概。如《红日》、《红岩》、《青春之歌》等作品中,作者通过对崇高人物的宣扬来体现自己的价值观。而新历史小说中,作家主体的价值观已经弱化,作者作为历史的个性化的叙述人,他们无法与历史进行深层对话,对现实的批判力度也非常弱化。
在余华的小说中,主体的退隐是一个很明显的现象。小说的主人公不明确自己的人生目标,作者也无意要给他们找寻一条光明的道路。《十八岁出远门》中的主人公,那个不安世事的小伙子,当别人抢走他乘坐的车的东西时,他也加入到了抢夺的行列中。他似乎不知道自己远行能够做些什么,他只是漫无目标地漂在不属于他的人生航道上。
《活着》的主人公福贵,他的生活的重心似乎只有等待亲人的死亡。在亲人死亡的事实面前,福贵或许分不清是痛苦还是快乐的,或许他更多的是在庆幸亲人可以逃离现实苦难的漩涡,可他的苦难还在延续。对于他那无穷的苦涩和酸楚的慢慢岁月,作者为什么不给他一个光明的出路呢?这难道不是作者对代表过去年代的广大的人民群众的主体价值的忽视吗?或许,正如评论所质疑的那样,余华缺乏在农村的生活体验,所以他会让他笔下的农民长期隐忍地活着,不去寻找新的出路。
作为历史的存在,人既创造历史,也为历史所创造。从一个民族世代活动组成的历史长河中考察历史,我们可以发现,虽然作为个体,每个人或许都有这样、那样的明确目的,但从整体上看,历史却是盲目的。作为历史学家应该努力去挖掘在历史的规律背后的盲目性。人作为个体是有理性的、有目的的行为,但因为人类历史是盲目的、无理性的,所以人在总体上是无目的的、无理性的。在新历史小说中的主体不是努力去呈现个体的理性,相反,作家的主体意识却极力退隐。
在新历史主义小说中,作家主体意识的退隐也伴随着带来偶然性的张扬。小说中,历史的偶然性、随意性可以很容易地把人的理性、目的性的行为粉碎、挤压。《白鹿原》中鹿兆海和白灵靠投铜钱来决定参加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故乡天下黄花》中孙屎根本来想参加国民党,但因仇家先他一步加入了国民党,他便转向共产党,成为了革命者。
新历史小说往往过分强调历史进程中的不确定因素和偶然因素,使历史成为一个虚无的幻影和不可知物,从而使历史和自身都陷人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之中。新历史小说中意义缺失、主体意识弱化及现实批判立场的缺席都与自身的这种困境相关联。这样看来,新历史主义小说在摆脱历史决定论时又陷入了机械决定论。人的价值、人的意义在这种非人的历史观中被抛弃了。
三、人物边缘化造成历史欲望化
传统历史小说中的主人公或者帝王将相、或者有突出贡献的工人、农民等。他们总是神圣与崇高的化身。新历史小说呈现更多的却是处于社会底层的边缘人物。在边缘小人物的叙写中,小人物的卑琐的欲望成了作家们表现的中心。因此,在新历史主义小说中,我们看到了作者对土匪强盗、妓女等丑恶的事物持一种欣赏的态度。在莫言的小说《檀》中,一些民族英雄的壮举并未得到太多的表现,相反,一些妓女等不入流的事情却受到作者的追捧;在刘震云的《故乡相处流传》中,曹操、袁绍与刘表的战争的起因却被无情地书写为为了争夺一个寡妇,历史的神圣性遭到了无情的亵渎。
历史欲望化的书写,必然带来人的欲望被压抑时内心深处所产生的心理阴暗的书写。苏童的长篇小说《米》,小说中的主人公五龙,从农村逃到城市讨生活,到城市为了一个馒头被逼了叫人家爸爸,从此在的心中埋下仇恨,在城市里他疯狂地报复着那些曾经带给他们仇恨的人,连那些他最亲近的人,他也不放过,以致于他气死岳父,霸占自己妻子的姐姐,抢夺百姓财物等等。一个靠仇恨生活的人,在作家的笔下被没有受到太多的批判。在那冰冷的叙述背后,我们不得怀疑这样的小说创作中对边缘人物的罪恶的凸显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负面影响。王安忆的《长恨歌》中充斥王绮瑶一生的核心内容是物欲,小说通过对那个对城市里的霓虹灯、化妆品、楼房等物质着迷的女人的刻画,似乎又让我们回到了中国几十年的变迁前的对物质充满欲望,追求狂欢与享受的起点。
新历史小说中的边缘人物的日常生活中的吃喝拉撒、婚丧嫁娶、家族争端等成了历史叙述的重心,以往的政治事件的重心被完全取代。小说为政治服务的倾向被淡化,历史成了欲望化、世俗化的历史。当历史成了欲望的代名词时,历史的崇高感自然不再我们的记忆中闪现。新历史小说专意撰写“边缘历史”的做法,“不但使自身的价值陷入相对主义,而且最终陷入历史相对主义”[4]。
四、民间化价值取向的凸显造成批判精神的缺失
传统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喜欢从两个阶级、两种政治力量的角逐去构思情节,小说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权威历史话语固定模式。小说的目的是为了让读者接受主流意识形态化的历史观念,接受主流的价值观。如《红岩》宣扬的是革命道德品质的认识,而《红旗谱》宣扬的则是关于农村阶级对立的现象以及如何缓解阶级矛盾的知识。而新历史小说中,对边缘人物的凸显,民间的意识形态成为价值评判的主要指标。在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中,八路军的一次草率的伏击引来了日本兵的疯狂报复,面对日本的报复,村长在谴责日本兵的同时,也谴责八路军。在村长的眼中,如果没有八路军的草率伏击就不会日本人的报复,在这里,村长不是站在抗日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视野中,而是用民间的价值观来表达对战争的厌恶情绪,表达出对任何权力体制的怀疑。但这样的失衡民间价值观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却是非常明显的。有评论认为,“权力之所以能统涉人类历史,是因为它合人性,权力的本质是认同而不是暴力”[5]。客观地讲,权力是具有积极的意义的,它是多维多层的复杂关系的结果。单纯对权力进行否定,而不探讨权力之所以可以存在的深层原因,那是“将深度的历史表象化的肤浅行为”[5]。新历史小说中,以民间的价值取向作为评判事物的标准,忽略历史深层原因的探讨,除了增加一些对权力体制的怀疑外,并无法从根本上促进社会历史的进步。
在莫言的《檀香刑》中,杀人在晚清刽子手赵甲眼中,显然成了一种报效皇恩的神圣职业和艺术,杀人的丑恶行为已经被美化。作品中,作者对赵甲的才能虽然进行了极力肯定,但我们认为对赵甲的杀人行为等还是应该有起码的批判精神在内。
作者“用老百姓的思维来思维”并进而进行民间写作,这一点无可非议。但我们应该知道的是,文学作品应该承担着对美好事物、积极进取精神的宣扬,对丑恶事物的扬弃这一历史使命。而对民间价值取向的宣扬,对负面因素的不加批判的态度,无疑冲击了主流意识形态正面、崇高等的宣扬。当负面的情绪在一定范围里蔓延,无疑会削弱人们对事物是非的评判能力。
五、新历史主义小说的转型
新历史主义小说在经历了短暂的辉煌后,纷纷寻求更适合本土的创作资源。王安忆的《叔叔的故事》曾用解构、元小说、反讽和戏拟等叙述特征进行描写,但到了90年代之后,再也找不到用激进的方式进行创作了。她的《长恨歌》用一个女人的历史来影射上海这座大城市的变迁,用一个女人一生的浮沉来映射城市的衰荣。故事不仅好读,也具有浓厚的文化蕴涵。余华也一改《现实一种》等以往的冷漠叙述、历史的平面呈现等。他的《许三观卖血记》以好懂、耐读的风格形式出现在读者面前。他改变了过去把人物当符号的做法,又重新重视传统的故事与人物赋予他们丰富的声音和个性。在许三观等身上我们终于体会到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耐人寻味的精神世界和我们国民的劣根性等。余华开始用同情的眼看待世界,开始认真审视与回味这片使文学赖以生长的土壤。
新历史主义小说产生的困境,表层原因是因为新历史主义小说家在接受西方新历史主义理论本身存在理解偏差,深层原因是因为中国的新历史主义小说创作还缺乏适合西方新历史主义文化思潮等的土壤。新历史主义小说家在充分汲取异域营养和认识到异域的不足之后,他们开始重新向本土寻找并发现精神和现象的真实,从而建构有中国灵魂的文学。
[1]金汉.中国当代小说艺术演变史[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131.
[2]吴景明.论新历史主义小说对传统历史小说的反拨[J].长春师范学院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1):79-83.
[3]施津菊.新历史小说:从解构历史到游戏历史[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2008,(1):55-58
[4]胡健.肃穆与消解肃穆——从传统型历史小说到新历史小说[J].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J].2007,(6):121-124.
[5]刘川鄂,王贵平.新历史主义小说的解构及其限度[J].文艺研究,2007.(7):1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