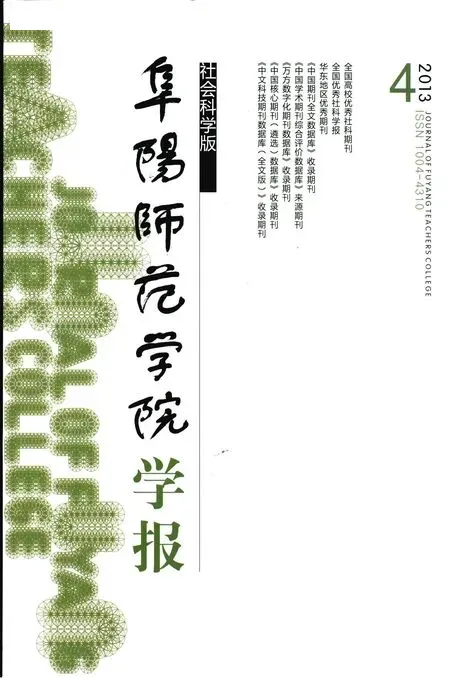论《牡丹亭》中杜丽娘的形象
2013-04-18张瀚池
张瀚池
(安徽大学历史系,安徽 合肥 230039)
汤显祖(1550—1616),字义仍,号海若、若士,又号清远道人,临川(今江西抚顺)人,明代著名文学家、戏曲家。生平创作诗文戏曲作品甚多,在中国乃至世界戏剧史上,可与关汉卿、王实甫诸家前后辉映,亦能和莎士比亚东西相望。日本学者青木正儿的《中国近世戏曲史》中曾提到“显祖之诞生,先于英国莎士比亚十四年,后莎氏之逝世一年而卒(据考证实为同年)。东西曲坛伟人,同出其时,亦一奇也。”[1]称汤氏为世界文坛的一颗璀璨明星实至名归。
在汤显祖为后世留下的卷帙浩繁的文学作品中,以“临川四梦”声明最高、价值最大,而四梦中又首推《牡丹亭》。《牡丹亭》全名《牡丹亭还魂记》,乃是汤显祖根据明代早期话本《杜丽娘暮色还魂》改编而成的。其剧一经问世,影响甚大,盛演不绝,刊刻不衰,时称“汤义仍《牡丹亭梦》一出,几令《西厢》减价”[2]。戏剧塑造了柳梦梅、杜丽娘、春香、杜宝等经典人物形象,而其中尤以女主人公杜丽娘的形象最为深入人心,数百年来牵绊住了无数青年男女、文人墨客,和崔莺莺、林黛玉等经典女性形象一道在古典文学画卷上留下了浓重一笔。
剧作第一出《标目》的开场词中“世间只有情难诉”一句,简明扼要地表达出了汤显祖所追求的“至情”理想,汤氏用笔为世人描绘出一幕轰轰烈烈、感天动地的爱情。整剧剧情梗概也在其第一出《标目》中有所说明,“杜宝黄堂,生丽娘小姐,爱踏春阳。梦感书生折柳,竟为情伤。写真留记,葬梅花道院凄凉。三年上,有梦梅柳子,于此赴高唐。果而回生定配,赴临安取试,寇起淮扬。正把杜公围困,小姐惊惶。教柳郎行探,反遭疑激恼平章。风流况,施行正苦,报中状元郎。”[3]杜丽娘、柳梦梅看似完满的结局,得来并非易事。作为一个生来便居于深闺中的少女,杜丽娘饱受封建伦常的荼毒,但既然是自然人,就不可避免的会萌生自然的情感。内心淳真性情的萌动和园中春日美景的感发,使她产生了强烈的自我意识,大胆地走出闺阁,去追求真挚的爱情和美满的婚姻。过程中对于几千年来被奉为圭臬的封建思想、贞节观念作出了彻底的扬弃,迸发出强烈的个性解放的思想光芒。
但是毕竟作者本人仍处在封建统治之下,思想里难免被打上了封建的烙印。体现在作品中,或多或少的流露出对于如何调和性与爱、情与理之间矛盾的乏术,有一定的局限性。本文试图在“至情”的氛围中探寻主人公杜丽娘自我超越的轨迹,了解其形象中的思想价值和艺术魅力;同时结合作者汤显祖及作品所处的时代背景,分析其形象的超越性和局限之所在;从而根据其典型的形象和内涵归纳出普遍的社会性和现实意义。
一、从自然真淳的封建闺阁少女到自我意识觉醒的反封建斗士
(一)传统闺阁中内心情欲萌动的少女形象
在作品的第三出《训女》中,女主人公正式登场,她是南安太守杜宝与夫人甄氏的独女,“才貌端妍,唤名丽娘,未议婚配,看起自来淑女,无不知书”[3];并且精巧过人,“长向花阴课女工”[3],是封建社会典型的大家闺秀。作为一名成长于官宦之家的闺中少女,杜丽娘侍父母恭顺谨严,待人老成持重,行事守节整齐,很符合封建伦常对女性的要求。然而即便如此的知书懂礼、精巧过人,杜丽娘似乎仍不能让双亲欣慰无憾。她的父亲杜宝时常感叹,“我比子美公公更可怜也。他还有念老夫诗句男儿,俺则有学母氏画眉娇女”[3]。这仅仅是因为丽娘身非男儿,于是父母只能退而求其次,希望她能贤德淑慧,他日觅得佳婿,光耀门楣。这样的男权社会的偏见,怎不叫人寒心!但面对一切的不平等,杜丽娘欣然接受,她似乎已经认同了传统封建制度下男尊女卑的认识,不见其叛逆斗争的思想印痕。第七出《闺孰》介绍了杜丽娘读书求学的情况,对于腐儒陈最良令她早起读书的要求,丽娘并无不满,只一句“知道了,今夜不睡,三更时分,请先生上书”[3];而淘气天真的丫头春香对先生“之乎者也”的说教表示不满时,丽娘温声制止,自己只一句“师父,依注解书,学生自会。但把诗经大意敷演一番”[3],一言一行表现出待上以敬、待下以宽的传统美德。杜丽娘很端庄,但似乎缺少了青春气息。
而事实并非如此,虽然杜丽娘被父母呆板僵化的封建传统价值观所束缚,可是在她封建闺秀的外表下,有着天性使然的热切情感。她天资聪颖、蕙质兰心,剧作中称她“男女四书”都已成诵,摹卫夫人的书法也几可乱真,这在提倡“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时代难能可贵,让她少受世俗的影响,保持一颗真淳之心。她热爱自然,也懂得欣赏自然之美,甫一出场便有“娇莺欲语,眼见春如许。寸草心,怎报的春光一二”[3]的赞叹。《闺塾》一出中,看似温婉的丽娘,其活泼自然的少女天性便借着春香的顽皮闹学表现了出来。对于父亲和先生将《关雎》理解为歌颂后妃之德的观点,丽娘也颇不认同,“关了的雎鸠,尚然有洲渚之兴,可以人而不如鸟乎”[3],在她看来这分明是一首热切的恋歌。此时的杜丽娘,心中已是情思萦绕,“圣人之情,尽见于此矣。今古同怀,岂不然乎”[3],她迫切的渴望有一个能够释放情感的天地。
而此时,又是“顽皮”的春香为她打开了通往这片天地的大门。“书要埋头读,那景致则抬头望”,“一生爱好是天然”的个性使杜丽娘再也按捺不住,迫切的想看看在春香口中“亭台六七座、秋千一两架;绕的流觞曲水,面着太湖山石”的花园是个怎样所在。于是她步出了深闺,第一次走进了真正的春天,也第一次感受到了自己那如春天般动人的青春,不由从心底生发出“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3]的喟叹。园中的春色是那样的美,“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残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贱”。“她懂得欣赏美,是出自于自身对美好事物的追求”[3],姹紫嫣红的鲜花,明艳动人的春色,如此美好的景致却少有人欣赏,她沉醉其中却又无限伤感。流连园中,丽娘因花动情,“遍青山啼红了杜鹃,荼蘼外烟丝醉软。牡丹虽好,他春归怎占的先”[3],春日将逝,园中群芳竞相怒放,唯牡丹迟迟未开。从花中,丽娘仿佛看到了自己——深居闺阁,空有青春美貌,却无人欣赏,时光流逝,青春虚度,怎不叫人黯然神伤。“她惋惜的不是三月残春,她惋惜的是眼看青春转瞬即逝,而她却无能为力,不能自主,感到自己生存的荒芜和生命的空虚”[4],心绪难平便再无意游园了,“观之不足他缱,便赏遍了十二亭台是枉然。到不如,兴尽回家闲过遣”[3]。观之不足、兴尽而归是假,融融春光触动了内心情愫才是丽娘由喜转怨的真正原因。寥寥数句,一个在封建伦常压制下苦闷和酸楚的闺中少女的形象跃然纸上。
在杜丽娘的心中,充满了对自然的热爱和对青春的向往,内心情感的激荡使她产生了对抗压抑自己已久的封建礼教的念头,而对抗之法便是一个“情”字。但是身处于男权社会中,她的力量毕竟太过弱小,现实中寻求而不可得,便只能寄“情”于梦中。梦境虚幻,情感却真,在梦中人性得到了最大程度的舒展。回归现实,情感依旧,为了维系这得来不易的“情”,她可以抛却生死,由情始杜丽娘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
(二)由本我层面的情欲激荡到自我意识的觉醒、迸发
“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提到人格的三个层面:本我、自我、超我。‘本我’是原始冲动、欲望以及被压抑的愿望的综合;‘自我’是在现实环境中由本我分化而来的,介于本我与超我之间,成为二者的协调者;‘超我’则是伦理、道德、社会规范等的汇集。根据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理论,‘本我’更多的受潜意识的支配,受人的原始欲望的牵引,倍受压抑,它却不安分,要求挣脱束缚;而‘自我’受意识的支配,受人的理性、情感的指引。”[5]通观《牡丹亭》可以看出,杜丽娘从一名待字闺中的封建大家闺秀,到有感于春日之景而内心情欲萌动,再到大胆地突破封建伦常的束缚,追求属于自己的爱情和幸福,这样的一条爱情道路正是她从本我层面的情欲激荡,转为认识自我,进而摆脱超我的束缚,使情感得以释放、人性得以舒展,完成自我意识的觉醒的过程。
汤显祖一心将杜丽娘塑造成为至情的化身,在他的笔下“天下女子有情,宁有如杜丽娘者乎”[3]。丽娘的这份情,是对长久以来压抑的欲望的释放,是对自我存在的认识,也是对传统贞洁观念的挑战。当然,现实中封建社会的强大仍是她无法直面的,在这强势的超我力量的压迫之下,她只能通过虚幻的梦境来挣脱束缚。梦境看似虚幻,对杜丽娘而言却很真实,从中她愈发的体会到了自身的意义和价值,懂得了“我”是一个独立存在的个体,“我”需要的是什么。正是这种对自我、对生命的体认,使得她由生至死、死而复生,在与命运的抗争中赢得了爱情。
在强烈的自我意识的指引下,杜丽娘和柳梦梅二人的爱情经历了感春生情、情欲萌动后梦中相识相恋;寻梦而不得,香消玉殒后一缕香魂不灭,人鬼相恋;死而复生后坚决捍卫爱情,有情人终成眷属这三个阶段。可以说,“穿越生死只为情”是这场感天动地的爱情的完美注脚。
(三)自我意识觉醒后的至情赞歌
《惊梦》一出是爱情的开始,游园后的杜丽娘,在大好春色的感召下,情欲激荡,“吾今年已二八,未逢折桂之夫;忽慕春情,怎得蟾宫之客”[3],“吾生于宦族,长在名门。年已及笄,不得早成佳配,诚为虚度青春,光阴如过隙耳”[3]。对于情感的强烈渴望,让她忘却了自我,昏昏然进入了梦境。在梦中她得以一会意中之人,与之共赴云雨,舒展了欲望、体验了爱情。这种朦胧的情感,一旦回归现实便被击得粉碎。惊梦而起反遭母亲的斥责,无奈的杜丽娘只能重回梦中寻求慰藉。于是便有了《寻梦》一出,丽娘进一步突破了封建伦理的束缚,更加热切的追求爱情。可梦终究是虚幻的,可以让她体会到真挚的情感,却无法给她梦想中的归宿。“问世间何物似情浓,整一片魂断心痛”,失望的情绪在现实中蔓延,丽娘因情致疾,日渐消瘦。可是已经体会到真挚情感的她,对自我有了全新的体认,她宁可用付出生命的代价抗争到底,也不愿屈从于现实,“这般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待打并香魂一片,阴雨梅天,守的个梅根相见”[3],她愿身后葬于梅边,以留存那份真爱。《写真》一出,她为自己描绘下了一幅二八春容,坚定的题上了“不在梅边在柳边”的诗句,完成了这份梦中的爱恋,慕色而亡。
从《冥判》到《回生》是人鬼相恋的阶段,此时的杜丽娘早已不再是那个情愫初生,从梦中寻找真情的懵懂少女。她觉醒的是那样的彻底,完全冲破了封建伦理道德的束缚,执着、热切地追寻着属于自己的爱情。在《冥判》中,已成鬼魂的她沉着应对,以自己感人至深的情打动了判官,从而有机会重返人间,完成那段未尽之情。《幽媾》一出,丽娘之魂回到旧时庭院,“魂随月下丹青引”,终于找到了她那“不在梅边在柳边”的梦中之人。深夜造访,为了不让意中人受惊,她谨慎的暂时隐瞒了鬼魂的身份。而在见到柳生以后,隐忍已久的情感再次得到了释放,二人互道衷肠,共度良宵,一切的世俗观念、伦理道德都荡然无存。随着二人逐渐情浓难舍丽娘决定向柳生表明身份,让他助自己还阳,以“早定夫妻百岁恩”。于是便有了《冥誓》一出,二人盟香为誓:“生同室,死同穴,心口不齐,寿随香灭。”[3]好在柳梦梅也是痴情之人,终不付丽娘之托,帮助她死而复生。到了这里,似乎这份经历生死的爱情可以完满了。
而事实并非如此,再世为人的杜丽娘,又一次身处封建伦理道德的规范之中,她必须直面现实,捍卫自己那得来不易的爱情。从《婚走》一出到剧作结束是爱情回归人世,有情人终成眷属的阶段。经历了天上人间、诸多磨难的杜丽娘虽然已和柳生私定终身,但为了让自己那脆弱的爱情能被世俗所容纳,不得不借助合乎世俗的手段——功名。当柳梦梅高中状元,二人终于得成佳配之时,父亲杜宝的阻挠却又使好事多磨。丽娘据理力争,希望自己的婚姻得到承认。甚至父亲提出:“离异了柳梦梅,回去认你”[3]的条件,她也不为所动:“叫俺回杜家,赸了柳衙,便作你杜鹃花,也叫不转子规红泪洒”[3],对爱情的那份追求和坚守,是其所具有的感人力量。在从生到死、由死复生,生生死死的爱情追逐中,杜丽娘谱写出“则普天下做鬼的有情谁似咱”[3]的爱情赞歌。
二、在自我的觉醒与超我的限制中挣扎的情理之争
(一)至情理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牡丹亭》的创作及其至情理想的产生并非偶然,可以说是明朝中叶以降思想解放思潮的产物,代表着明代文学的顶尖成就。宋明时期,理学一直居于正统地位,孔孟之书、程朱理学始终被统治者奉为圭臬,表现在选择人才上,依理学经典取士;社会生活上,极力倡导妇女贞洁观念。但是,到明朝中后期,随着封建制度的趋于没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发和市民阶层兴起,在思想领域心学异军突起,占据了文化宗主的地位,承袭王陆心学而来的一大批思想家,如徐渭、王艮、罗汝芳、李贽等人,形成了蔚为大观的晚明思想解放潮流。而这样一个反对伪圣贤、假道学,崇尚人性真情、追求思想自由的思想学术潮流,对文学艺术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具有追求独立性和主体性、肯定自我、表达真情的全新主题。体现在传奇剧创作上,便有了汤氏的《牡丹亭》。汤显祖将其对人生的体验和对身世的感怀倾注于作品中,其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赞美世间的真情、至情。正如他在作品《题词》中所言:“天下女子有情,宁有如杜丽娘者乎?梦其人即病,病即弥连,至手画形容,传于世而后死。死三年矣,复能溟漠中求得其所梦者而生。如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3]在这里汤显祖以其澎湃的情感为世人描绘出一幅真实的画卷,画中人杜丽娘成为了至情的化身,在她的身上既有传统古典女性的端庄之美,更具备了以灼热的情感反抗现实命运的一面。这样一个展现了崇高至情理想的女性形象,经过时间的涤荡仍旧明丽动人。
(二)无可奈何的情理之争
《牡丹亭》中所表达的至情理想具有超越时代的意义,杜丽娘自我意识的觉醒、以情反理的精神对封建传统伦理道德规范形成了冲击。但同时,“杜丽娘是一个矛盾的结合体,为爱情无法实现而坚强,又为爱情的有条件的实现下而顺服,人性的舒展与理学的压抑在她身上交织着,从而升华为经典。”[6]作为至情的化身,杜丽娘生生死死、天上人间只为追寻那份出自自然本性的“情”,而与之相对抗的则是维护伦常、抑制人性的“理”,情与理激烈斗争而又趋向调和。“在明代理学思想强化的特定时代,‘情’指的是生命的欲望、生命的活力和自然的状态;‘理’指的是社会生活构成秩序的是非准则”[7],二者中,“理”作为统治力量居于强势地位。因此作品尝试着跳脱出现实,将天然之情寄托于幻想、寄托于梦境,以避免情与理的直面对话。可一旦从梦境中醒来,回归现实,看似热烈的爱情瞬间变得迷失、彷徨。试看杜丽娘转生后的表现:为了门当户对、早成婚配,她鼓励柳生考取功名;当柳生助她重回阳世,欲与她成夫妻之礼时,丽娘提出“必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前日鬼也,今日人也。鬼可虚情,人须实礼”[3]。这全然不像那个坚毅勇敢、为了追求爱情不惜以生命相抗争的杜丽娘了,曾经对封建伦理道德彻底扬弃的她,也开始妥协了。
从幻境到现实,杜丽娘表现迥异,这表明在她坚定的反抗行动中亦包含了屈从。而伴随着这不经意的屈从,汤翁完美的至情理想,也从云端跌落尘埃。文学作品中,任何人物形象的塑造,都必须植根于其所处的特定的时代,且无可避免的包含作者的主观印迹。“虽然许多研究者都关注到杜丽娘作为女性身上所蕴涵的反抗性和进步性,并对此进行歌颂,但是汤显祖终究不能超越他自己所处的时代。他没有也不可能意识到,他笔下至美至善的杜丽娘独独缺少了最不该缺少的东西,那就是为自己的命运承担责任并付出努力的‘自我规定的意志’。”[8]情虽本乎自然,却离不开现实的土壤,二者互不相让、牵扯萦绕,形成了一种中和的状态。尽管如此,《牡丹亭》仍是一个美好的梦,她的出现使传统意义上的对爱情的追求和理解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洋溢着人性关怀的光辉。而从这个梦中向人们缓缓走来的杜丽娘完美地诠释了“情”的深刻意蕴。
三、杜丽娘形象的社会性及其现实意义
能够帮助人们选择创造自身生活的方式,是文学的本质功能之一,在这一点上,《牡丹亭》无论对当时还是对后世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一生四梦,得意处惟在《牡丹》”,作为汤显祖穷其心血之作,自问世伊始,《牡丹亭》和杜丽娘的形象在文学上和社会生活上都造成了不小的轰动。
在程朱理学盛行、封建伦理强势的时代,《牡丹亭》以赞美人性、歌颂真情的方式,全方位地展现了女性意识从觉醒到发展的过程,对世俗礼教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走在了时代的最前列。同时也为后世女性思想解放运动的兴起和女性主义文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男性的主体意识长期以来都居于主导地位,相对的女性的主体意识是那样的苍白无力。明清时期处于封建社会的末世,也是社会剧变的时期,产生于此时的《牡丹亭》有力地推动了女性主体意识的复苏。广陵才女冯小青身世命运凄婉,在读到《牡丹亭》后,深受杜丽娘形象的感染,对于封建社会下不合理的婚姻制度发出了凄美的不平之音:“冷雨幽窗不可听,挑灯闲看《牡丹亭》。人间亦有痴于我,岂独伤心是小青。”而在《红楼梦》中,众多妙龄女子特别是林黛玉身上所体现出的更为强烈的自我意识,正是由杜丽娘的至情理想沿袭、升华而成的。《红楼梦》第二十三回“《西厢记》妙词通戏语,《牡丹亭》艳曲警芳心”,其回目便直接把《牡丹亭》写出。黛玉在梨香院墙角外,只听墙内笛韵悠扬,歌声婉转,偶然两句吹到耳朵内,明明白白一字不落道:“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于是她止步侧耳细听,又唱道:“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只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在幽闺自怜”。黛玉仔细忖度,越发情思萦逗、如醉如痴,。第四十回中写黛玉在行酒令时随口说出“良辰美景奈何天”的句子,能脱口而出,可见黛玉对于《牡丹亭》的喜爱。而当宝钗听到了黛玉说出的酒令后,对黛玉进行了劝诫。能够一听之下便知是《牡丹亭》,说明宝钗也对这部在当时被视为禁书的作品颇有了解,也说明《牡丹亭》在当时的青年男女中相当流行。《牡丹亭》的思想性和艺术魅力在后世不断得到体现。
明清时期产生了众多传奇剧作,作为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一部,《牡丹亭》以其浪漫唯美的文字、瑰丽奇特的构思、热烈奔放的情感,对传统封建格局进行了颠覆性的挑战,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而我们也知道,一部伟大的作品,“并不是一个自身独立,向每一个时代的每一个读者均提供同样的观点和客体,也不是一尊纪念碑,形而上学地展示其超时代的本质”[9]。正相反,其丰富多彩、意蕴无穷的内容使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读者面对同一部作品时都会有不同的感悟,从而形成全新的影响和价值。因此,在当前的时代环境下,《牡丹亭》和杜丽娘的形象仍散发出夺目的光芒。
今天的人类社会,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禁锢思想、压制人性的封建礼教早已失去了生存的土壤。可是无论时代如何变化,人类对于爱情幸福的渴望和追求今古同怀,宣扬人性觉醒、展现时代方向、歌颂至美爱情的文学艺术将长盛不衰。正因如此杜丽娘这个人物形象和她对理想和爱情的执着追求,至今仍以其巨大的艺术力量震撼着我们的心灵。
[1][日]青木正儿.中国近世戏曲史[M].北京:作家出版社,1958.
[2]沈德符.万历野获编[M].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
[3]汤显祖.牡丹亭[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4]罗建新.“礼”与“理”的叛逆——兼论崔莺莺与杜丽娘的抗争形象[J].重庆交通大学学报: 社科版,2007,(7):62-69.
[5]胡佩霞.从女性人性价值的体认到人格价值的体认——杜丽娘与林黛玉爱情之比较[J].徐州教育学院学报,2006,(21):84-86.
[6]王治浩.杜丽娘的形象及其内涵[J].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17):69-71.
[7]杨艾明.《牡丹亭》情与理的冲突融合[J].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27):65-67.
[8]徐新敏.试论《牡丹亭》杜丽娘形象的多重意蕴[J].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7,(11):132-133.
[9]H.R 姚斯,R.C 霍拉勃.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M].周宁,金元浦,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