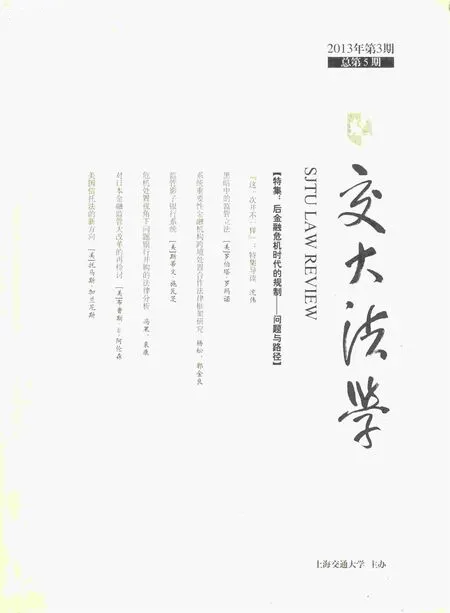美国信托法的新方向
2013-04-18托马斯加兰尼斯ThomasGallanis
[美]托马斯·加兰尼斯(Thomas P.Gallanis)*
徐 卫** 译
引 言
在信托法上,赠与人与受益人的权利之间存在一种紧张关系。一方面,赠与人的地位似乎至高无上。赠与人——信托法上即为委托人〔1〕See Uniform Trust Code§103(15)(amended 2004),7CU.L.A.414(2006)(“委托人,包括遗嘱人,是指设立信托或将财产交付信托的人”);Restatement(Third)of Trusts§3(1)(2003)(“设立信托的人即为委托人”).——制定信托条款〔2〕See Restatement(Third)of Trusts§4(2003)(其中对“信托条款”一词进行了界定).,因而有权决定受益人衡平权益的范围,并有权对信托管理中受托人的行为进行控制。的确,正如《财产法重述》(第三版)所指出,财产赠与转移法的组织原则即是在法律允许的最大限度上尊重赠与人的意愿。〔3〕Restatement(Third)of Property:Wills &Other Donative Transfers§10.1(2003).另一方面,也可以说受益人处于优势地位。在信托中,拥有信托所有权利益的仅是受益人而非委托人〔4〕See Restatement(Third)of Trusts§3(4)(2003)(“受益人是指信托持有的财产为其利益而存在的人”).(委托人有时也可能是受益人,〔5〕See id.§3comment d(“委托人或受托人,或者二者都可担任受益人;但唯一的受托人不可以担任唯一的受益人……”).但这里所说的委托人是指本来意义上的委托人)。受益人(而不是委托人)拥有信托财产衡平法上的所有权,这似乎应当限制委托人对信托的控制权。事实如此,《信托法重述》(第三版)强调说,“私益信托及其条款和管理必须有利于受益人的利益”。〔6〕Id.§27(2);See also Uniform Trust Code§404,7CU.L.A.484(2006)(“信托及其条款必须为受益人利益而存在”).
信托法“航行”于委托人控制与受益人控制“两级”之中,有时采取了有利于委托人的立场,有时则采取了有利于受益人的立场。
本文中,笔者将对我们当前的发展状况和未来走向进行讨论和规范分析。笔者指出美国信托法实施了几十年的“青睐”委托人之模式,目前正进入新的方向,重新主张受益人的权利和利益。笔者也认为这种新的方向是恰当的和值得欢迎的。
一、研究背景
依照顺序,首先应谈一下背景,因为一些读者可能不熟悉信托的基本结构。最清晰的信托定义是牛津大学伯纳德·卢顿教授提出的,他指出,信托“本质上是一种赠与,它分散在长远的时间维度之上,因而受制于管理体制的约束”。〔7〕Bernard Rudden,“Gifts and Promises.By John P.Dawson”,44Modern Law Review(1981),610(book review).信托财产的法律所有权从委托人转移给受托人,衡平法所有权从委托人转移给受益人。〔8〕Austin Wakeman Scott et al.,Scott and Ascher on Trusts,5th Ed.(New York:Aspen Publishers,2008),p.5(“受托人持有法律上的所有权,而受益人拥有衡平法上的所有权”).法律所有权与衡平法所有权的区分源自英国,在数世纪中,英国普通法法院认可受托人的所有权,而践行公平理念的衡平法院则依法执行受益人的权利。〔9〕有关概述,see J.H.Baker,An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Legal History,4th Ed.(London:Butterworths,2002),pp.290-293.19世纪,英国普通法与衡平法出现融合,〔10〕See T.P.Gallanis,“Victorian Reform of Civil Litigation in the Superior Courts of Common Law”,in C.H.van Rhee(Ed.),Within a Reasonable Time:The History of Due and Undue Delay in Civil Litigation(Berlin:Duncker &Humblot,2010),p.233,pp.243-244.但权利分割在信托概念结构中处于核心地位,考虑这一点对概念理解而言依然是准确和有益的。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本文讨论的信托是指通过财产赠与转移而设立的信托。这是卢顿教授把信托看作“本质上属于一项赠与”的含义所在。普通的信托产生于财产的非商业性转移,尤其是家庭中财产的转移。正如一位著名美国信托法学者约翰·朗拜因教授指出,“信托作为一种家庭财富转移的工具产生于中世纪末期。在转让者拥有大量财产或复杂家庭事务需要处理时,信托仍然是组织财富代际转移的特色化工具”。〔11〕John H.Langbein,“The Secret Life of the Trust:The Trust as an Instrument of Commerce”,107Yale Law Journal(1997),165.诚然,社会上也存在诸多的商业信托——养老金信托、共同基金、不动产投资信托、法律事务所信托账户等〔12〕See id at 167-78.——但美国信托法关注的一直是基于财产无偿转让而设立的信托。例如,美国法律学会在《信托法重述》(第三版)中将商业信托从计划方案的涵盖范围中剔除了出去,〔13〕Restatement(Third)of Trusts chapter 1,introduction note(2003).转而关注那种“作为家庭财产灵活、长期管理的工具”的信托。〔14〕Id.同样,笔者在此所谈的信托也是财产赠与转移给受益人的信托,其设立旨在进行(尤其是家庭代际之间的)财富管理。
在具有赠与性质的家庭信托中,很容易面临委托人的愿望和受益人的愿望之间的潜在冲突。在出现冲突时,法律须回答“这是谁的信托”这一基本问题。在我们国家的历史发展中,法律对这个核心问题给出了不同的回答。
在以下两种场合会出现委托人权利与受益人权利之间的紧张关系:信托存续期间(信托管理期间)中和信托结束(信托终止)时。在本文中,笔者将考察“信托管理”和“信托终止”两种情况,通过分析每种情况中的两个例子(共四个例子)来揭示笔者的主要论点。
二、信托管理
首先是信托管理。在信托管理过程中谁的意愿占主导地位:委托人还是受益人?前者设立信托并在信托文件中对其控制权进行了明确规定;后者是信托财产衡平法上的所有者。〔15〕在标准信托法上,三方当事人即是委托人、受托人和受益人。See id.§3.然而最近美国信托法中出现了另外一个角色:信托保护人。信托律师亚力山大·博韦和梅莉莎·兰格对信托保护人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定义:“信托保护人是指这样一个人(或委员会或实体),他不是受托人,但在信托中被授予了代替受托人相应权力的一些权力。”Philip J.Ruce,“The Trustee and the Trust Protector:A Question of Fiduciary Power.Should a Trust Protector Be Held to a Fiduciary Standard?”59Drake Law Review(2010),68n.1.信托保护人“在国际资产保护信托中被认为是一种有价值的工具”,从而逐渐进入国内信托之中。Id.at 78.关于信托保护人的学术分析,See id.;Gregory S.Alexander,“Trust Protectors:Who Will Watch the Watchmen?”27Cardozo Law Review(2006),2807;Jeffrey Evans Stake,“A Brief Comment on Trust Protectors”,27Cardozo Law Review(2006),2813;Stewart E.Sterk,“Trust Protectors,Agency Costs,and Fiduciary Duty”,27Cardozo Law Review(2006),2761.信托保护人如何纳入本文主题之中——或作为本文核心论点的进一步说明,或者作为相反趋势——要视信托条款和信托保护人的身份而定。正如斯迪克教授直言:“设置信托保护人可以是为了保护受益人的利益,也可以仅仅是出于保护委托人的意愿和计划的目的。”Stake,supra,at 2813.在受益人或受益人的代表人担任信托保护人时,信托保护人可能更加有助于信托受益人的利益而不是委托人的利益。相反,在委托人的代表人担任信托保护人的情况下,信托保护人可能有助于委托人的意愿或推定意图的实现,而不是受益人的意愿或利益的实现。
笔者在两个具体规则的探讨中考察这一问题。首先是关于挥霍条款的有效性及其范围的规则。所谓挥霍条款,即限制受益人转让其信托利益的条款。其次是管理偏离规则,此规则在信托文件的管理条款与受益人的最大利益发生冲突时开始发挥作用。
(一)挥霍条款
首先讨论挥霍条款的有效性及其范围问题。挥霍条款是由委托人(或委托人的律师)嵌入信托文件中的一种条款,该条款试图剥夺受益人将其衡平利益转让给第三人的能力,因而也剥夺了受益人的债权人追及该利益的权力。〔16〕See Restatement(Third)of Trusts§58comment a(2003)(“‘挥霍信托’是指限制信托受益人利益全部或部分自愿或非自愿转让的信托”);Austin Wakeman Scott et al.,supra note〔8〕,at 898-900(讨论挥霍信托).标准挥霍条款如下:“任何受益人对本信托的收入或本金享有的利益不得在预期支付中进行转让,不得以任何方式对受益人的债务和义务负责,并且不受查封和扣押的制约。”〔17〕Thomas P.Gallanis,Family Property Law:Cases and Materials on Wills,Trusts,and Future Interests,5th Ed.(New York:Foundation Press,2011),p.398.
这种条款有效吗?这一问题的回答将揭示本文核心“这是谁的信托”这一更大问题的许多信息。如果受益人的确拥有信托财产的所有权,那么必须知道,所有权的一个重要要素即是转让权,〔18〕See e.g.,Maxwell v.Moore,63U.S.(22How.)185,190(1859)(“如果拥有财产或对财产享有权利的人无权转让该财产,这与财产的本质是不一致的”);Dodge v.Woolsey,59U.S.(18How.)331,376(1855)(其中把可转让性看作财产“最基本的特性”).且伴随这种转让权,产生了支付债务的责任,我们拥有的财产才能被债权人追索。〔19〕See,e.g.,Broadway Nat’l Bank v.Adams,133Mass.170,174(1882)(“在我们的制度中,债权人可追索债务人所有的财产,除非存在法律上的例外……”).拥有可被债权人追索的财产并不必然是一种负担,相反可能还是一种利益。对于过去的债权人而言,它是一种负担,但对未来债权人而言,则是一种利益,因为它能让财产所有者用该财产做担保进行融资。对于这一观点的强调,See Thomas P.Gallnis,supra note〔17〕,at 219-220.另一方面,如果信托本质上是委托人的,那么委托人在挥霍条款中明示的意愿应当占主导地位。由此引申,受益人——甚至受益人的债权人——的权力则应退居次位。
在英国普通法及美国早期普通法中,现代的挥霍条款是无效的。〔20〕See Restatement(Third)of Trusts§58comment a(2003)(“英国法是不允许挥霍限制的……”);Austin Wakeman Scott et al.,supra note〔8〕,at 900(“英国法院一贯将限制受益人信托利益转让的条款认定为无效”).有关美国历史中 的 高超处理,See Gregory S.Alexander,“The Dead Hand and the Law of Trust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37Stanford Law Review(1985),1198-1200.这一规则由英国衡平大法官埃尔登勋爵在1811年布兰登诉鲁滨逊案〔21〕Brandon v.Robinson,(1811)34Eng.Rep.379(Ch.).中确立。该案中,史蒂芬·格姆通过遗嘱为其孩子设立了一份信托。后来他的一个孩子汤姆斯·格姆破产了。上述遗嘱中有一条规定是信托利益“不得赠与,转让或以其他方式让渡”。〔22〕Id.at 379.原告布兰登是债权人,被告鲁滨逊是受托人之一。埃尔登勋爵认为“反转让条款”无效:汤姆斯·格姆已经获得了信托中的利益,并且该利益在其破产后继续存在,〔23〕埃尔登勋爵指出,遗嘱人本来可以对利益施加一种限制(如为A生前或在其破产之前的利益),但遗嘱人没有这样做。用埃尔登的话说:“下述两种情况是存在明显区别的:将财产在某人破产之前分配给他和试图将财产给他以阻止其债权人获得财产上的任何利益(尽管该利益是他的)。”Id.at 380.因此该利益不能免除对债权人布兰登的支付。
19世纪末之前,布兰登诉鲁滨逊案规则在美国是一个占主导地位的规则。〔24〕Gregory S.Alexander,supra note〔20〕,at 1199(“19世纪上半叶,美国许多法院遵循了布兰登诉鲁滨逊案的规则”);Id.at 1202(“美国法院偏离布兰登诉鲁滨逊案规则……始于19世纪末并持续到20世纪20年代”).改变美国法律方向的司法观点是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1882年在百老汇国家银行诉亚当斯案〔25〕Broadway Nat’l Bank v.Adams,133Mass.170(1882).中的判决。该案涉及一份遗嘱。在该遗嘱中,遗嘱人为其兄弟查尔斯·亚当斯的利益设立一份遗嘱信托。遗嘱内容如下:
我将75 000美元交给我的遗嘱执行人……以此设立信托并进行投资……将其净收益每半年支付给我的……兄弟查尔斯·亚当斯。在查尔斯·亚当斯生前方便时将该等支付亲自交付给他。否则,应根据其要求或书面票据进行交付。无论哪一种情况,都不受其债权人的干预或控制,我的目的就是这些收益不得用于对受益人债权的支付。〔26〕Id.at 170.
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认为,在既定法律下,如果这种条款适用于财产从遗嘱人到查尔斯的直接赠与,该条款将是无效的:“普通法的规则是,一个人不能对财产的赠与或转让附加‘财产不得转让’的条件(仅此条件而没有其他条件),这种条件与赠与财产的性质相违背。”〔27〕Id.at 171.法院也承认,在英国和美国的多数规则中,同样的无效也适用于对信托利益的限制。法院的观点用其自己的话说就是:
当信托财产收益终生地支付给一个人(已婚妇女除外)时,衡平法上的终身财产可以由(受益人)转让,并在衡平法上承担(受益人)的债务,……(且)这一性质与财产不可分离,因此任何条款,无论是否明示,……都不能保护该财产免受其债务的负担。〔28〕Id.at 172.
那么,为何法院偏离美国的多数观点而主张委托人的挥霍条款有效呢?法院的答案指向了委托人的利益和权力:
信托的设立者是财产的绝对所有权人。他具有处分其财产的绝对权利,如通过完全的赠与将财产给他的兄弟,或通过施加他认为合适且不违反法律的约束或限制进行赠与……他的意愿应当被执行,除非这些意愿违背公共政策……
允许遗嘱人将信托财产收益上的合格利益支付给受益人,并防止受益人的浪费或不幸,对于这种做法,我们没有发现它违反良好公共政策中的任何原则。〔29〕Id.at 173.
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接受挥霍条款有效性的判决是相当有影响的,〔30〕See Restatement(Third)of Trusts§58comment a(2003)(“对于把挥霍信托视为美国普通法的一部分,可以举出的最有影响的案例是百老汇国家银行案”);Austin Wakeman Scott et al.,supra note〔8〕,at 902(“真正赞同对信托利益转让限制的主导案例是百老汇国家银行诉亚当斯案”).当今所有的美国司法区都认可挥霍信托。〔31〕N.Camille Varner,“Is the Dead Hand Losing Its Grip in Texas?:Spendthrift Trusts and In re Townley Bypass Unified Credit Trust”,62Baylor Law Review(2010),609n.89(其引述了每个州认可挥霍信托有效性的立法条例和司法判例).
但这个问题并没有结束,挥霍条款虽然有效,但并非总是完全有效。许多州通过立法对挥霍条款的有效性施加了限制,规定了受益人转让〔32〕Recall the point made in note〔19〕.及其债权人追索受益人信托利益的能力。〔33〕See Restatement(Third)of Trusts§58comment a(2003)(“许多州通过立法将挥霍信托法典化,少数几个州还明显地偏离了这里所讲的规则……即限制允许保护的范围……”).例如,纽约立法规定,债权人可以追索“超过维持受益人生活和教育所必须的那部分收益”。〔34〕N.Y.EST,Powers &Trusts Law§7-3.4,McKinney,2002.加利福尼亚法律对纽约的规定进行了修改,类似地允许债权人追及超过维持生计和教育所需的部分——但仅限于可支付总额的25%。〔35〕California Probate Code§§15306.5(b),15307(West 2002).许多州则采取了不同的立场,即认定某些债权人可以追及受益人的信托利益,即使其中存在挥霍条款。〔36〕《信托法重述》(第二版)包含了一个分款,该款列举了可追及挥霍信托受益人利益的“特定权利人类别”。Restatement(Second)of Trusts§157(1959).《信托法重述》(第三版)包含了一个类似但并不完全相同的条款。Restatement(Third)of Trusts§59(2003).根据多数观点,挥霍条款不能保护受益人的信托利益免受赡养费和子女抚养费请求权的追索。〔37〕Hurley v.Hurley,309N.W.2d225,227(Mich.Ct.App.1981)(“多数规则是,如果无明确地制定州法规定,以前夫为收入受益人的挥霍信托,其前妻可追索该信托收入以满足其赡养……或小孩抚养的需要”);see also Uniform Trust Code§503(b)(1)(amended 2005),7CU.L.A.525(2006)(“受益人的孩子、配偶、前配偶若拥有法院对受益人发布的有关抚育或赡养的判决或指令,挥霍信托条款对这些人不具有执行力……”);Restatement(Second)of Trusts§157(a)(1959)(“为满足那些对受益人可以执行的权利,允许受益人的妻子或孩子基于抚养或妻子基于赡养而追索信托受益人的利益”).1997年,密西西比州最高法院公布了一项(被《信托法重述》(第三版)的作者认为“获得广泛的好评”〔38〕Edward C.Halbach Jr.,“Uniform Acts,Restatements,and Other Trends in American Trust Law at Century’s End”,25ACTEC Notes(1999),101,108.)斯莱诉第一国家银行案〔39〕Sligh v.First Nat’l Bank,704So.2d1020(Miss.1997).的判决,该判决指出,挥霍条款不能保护信托受益人免除侵权之债的追索。〔40〕Id.at 1029.
在委托人的意愿及动机与受益人的所有者权利及责任之间,美国法律朝着更好地平衡二者的方向发展。百老汇国家银行案则允许委托人利用挥霍条款剥夺受益人自愿及非自愿转让其信托利益的权力。当前对挥霍条款的态度更加精细化,即确认越来越多的受益人须承担所有权义务的情形。〔41〕关于国内资产保护信托,很适当在此一提的是,在长期美国普通法中,若受益人同时是委托人,挥霍条款在牵涉此受益人利益时无效。See Restatement(Third)of Trusts§§58(2),60comment f(2003).尽管如此,目前有12个州通过立法认可自益资产保护信托,只是在具体规定上存在差异。See generally David G.Shaftel,“Comparison of the Twelve Domestic Asset Protection Statutes”,34ACTEC Journal(2009),293.因同一个人同时担任委托人和受益人两个角色,所以自益资产保护信托同时为委托人和受益人的利益而存在。对第三方债权人而言,无论其目的还是其意愿都被忽略。这些立法提出了一个令人关注的重要问题,由此激起了深刻的批评。See generally Restatement(Third)of Trusts§60comment f reporter’s notes(2003).
(二)管理偏离
在信托存续期间,若信托文件的管理性规定要求受托人以不符合受益人利益的方式采取行动,此时也会出现委托人与受益人的紧张关系,这是委托人与受益人在信托存续期间出现紧张关系的第二种情况。针对这一情况,存在一个规则——所谓的管理偏离规则〔42〕See e.g.,Thomas P.Gallanis,supra note〔17〕,at 536-539.不能把这个原则与相近似的衡平偏离原则相混淆,在后一原则中,如果发生了事先未能预料的情势,且修改信托条款与委托人的可能意图相一致,在此情况下即允许修改信托条款。See T.P.Gallanis,“The Trustee’s Duty to Inform”,85North Carolina Law Review(2007),1621.统一信托法既允许衡平偏离也允许管理偏离。该法第412(a)条是关于衡平偏离的规定,该条允许在特定情况下修改信托条款,但要求“在实际可行的情况下,信托条款的修改须与委托人的可能意图保持一致”。Uniform Trust Code§412(a)(2000).尽管如此,“如果根据现行信托条款,信托的持续将是不切实际的或是浪费的或者损害信托管理”,第412(b)条继续允许修改信托条款,这里并没有提到委托人的意图。Id.§412(b).《信托法重述》(第三版)中不存在与《统一信托法》第412(b)条直接对应的规定,根据《信托法重述》(第三版)作者的解释,而是采纳了重述之衡平偏离框架下的管理偏离规则。See generally Restatement(Third)of Trusts§66comment a reporter’s notes(2003).——即允许受托人偏离信托文件中存在问题的一些规定。不过,管理偏离的先决条件是什么呢?根据《信托法重述》(第二版),美国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当中的立场是:“如果因委托人不知或未预料的情势发生,导致遵从信托条款会挫败或严重损害信托目的的实现,法院则会指令或允许受托人偏离信托条款……”〔43〕Restatement(Second)of Trusts§167(1)(1959).在这一规则中,强调了委托人智识和意愿的重要作用。
与美国《信托法重述》(第二版)一致,委托人角色在“管理偏离”的典型案例即普利策财产案中表现显著。普利策财产案于1931年由纽约州纽约县的一个遗嘱检验法庭判决。〔44〕In re Pulitzer’s Estate,249N.Y.S.87(Sur.Ct.1931),aff’d mem.,260N.Y.S.975(App.Div.1932).该案是有关约瑟·普利策遗嘱的一个案例。约瑟·普利策是一位移民,后来成为美国最有影响的新闻工作者。〔45〕关于最近的传记,See James McGrath Morris,Pulitzer:A Life in Politics,Print,and Power(New York:HarperCollins,2010).他出版了《纽约世界》(其关联报纸是《周日世界》和《世界晚报》)和《圣路易斯邮报》两份报纸。《纽约世界》是他最喜欢的报纸。普利策通过努力将《纽约世界》打造成世界上读者量最大的日报。〔46〕关注普利策作为新闻出版商的相关传记,See George Juergens,Joseph Pulitzer and the New York World(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6).普利策在其临死时,将其持有的普利策出版公司(出版《圣路易斯邮报》)和新闻出版公司(出版《纽约世界》及其关联的《周日世界》和《世界晚报》)的股份设立了一份信托,并允许信托受托人出售前一个公司的股份,但后一个公司的股份不能出售。这份遗嘱相关规定如下:
我把圣路易斯普利策出版公司的股份通过遗赠交付给遗嘱执行人和受托人,授权他们随时及不定时地公开或私下以其认为最好的价格和条件出售和处置这些股份的全部或一部分,并以信托方式在相同信托中为受益人持有销售这些股票所得的收入。这种销售权不可解释为强制性规定,而纯粹是裁量性规定。但是,该销售权只限于圣路易斯普利策出版公司的股票,绝不能认为授权受托人销售或处置新闻出版公司(即“世界”报纸的出版者)的任何股票。特别指出,我责成我的儿子和后代们负有维护、发展和延续“世界”报纸(即维护和创立我为之耗费心血的事业)的责任,我把这些公司视为公共机构去努力创办和经营,希望他们遵循同样的精神去经营,着眼于更高目的而不是单纯地追求利润。我一直以来的愿望就是,永远秉承独立的精神经营这些报纸,并向社会公众及其官员代表灌输一种高标准和公共精神。我诚挚希望今后根据同样的原则运营这些报纸。〔47〕In re Pulitzer’s Estate,249N.Y.S.at 92.
不幸的是,《纽约世界》这份报纸变得无利可图,信托处于丧失其大量价值的危险境地。于是,受托人到法院申请批准偏离信托条款并出售股票。法院同意并允许出售股票。〔48〕Id.at 98(“因此我认为……遗嘱及其附件并未禁止受托人处置新闻出版公司的任何资产……”).那么法院是如何得出这一结论的呢?法院推理的核心是推测委托人的信托限制意图:如果普利策知悉这些股票价值将如此危险地贬损,他将如何去做?公正解读信托则会发现,普利策是相当自负的,他绝不会考虑到这一情况,〔49〕See id.at 92.(引述了信托自身中的表述。该信托认为普利策出版的几份《世界》报纸“源于远比单纯收益更高的动机”,那就是,在其毕生中“永远以独立的精神去经营”并希望该报纸“从今以后根据同样的原则进行经营”。)但是,为了获得正确的结果,法院在高度赞扬委托人商业判断的同时,进行了灵活地推理,法院说:
普利策先生的主要意图肯定是让其孩子持续获得相当收益的同时,让剩余受益人最终获得不受损害的本金。信托的永久存续和其孙辈们最终得到利益都是其目的之一。一个富有睿智和商业能力的人不可能纯粹为了虚荣,让凝聚其名誉和心血的报纸在整个信托财产遭受破产或清算毁损的情况下依然坚持经营下去。〔50〕Id.at 94-95.
确定委托人的限制意图是保存信托后,法院认为受托人有权力出售信托财产。〔51〕Id.at 98.
在现代信托法中,无需借助委托人的推测意图也可得到相同的结论。正如《统一信托法》第412条指出:“根据现行信托条款,如果信托继续存在将不切实际,或是一种浪费或者损害信托的管理,法院可以修改信托的管理性条款。”〔52〕Uniform Trust Code§412(b),7CU.L.A.507(2006).这里为何没有提及委托人的意图,其原因可以从《统一信托法》该条评论之中找到答案:
尽管委托人在确定信托目的时拥有相当的自由空间,但“信托具有服务于受益人利益的目的”这一原则禁止对信托财产使用施加不合理的限制。所有者对自己财产的使用具有任意的自由,但当该财产烙上了为他人利益而设立的信托之印记时,上述自由就不存在了。〔53〕Id.§412comment.
同挥霍条款的有效性与范围一样,管理偏离规则显示美国信托法的新方向是如何平衡委托人的意愿和受益人的所有权的。信托的管理最终必须有利于受益人的利益,受益人在信托财产上的衡平法所有权必须得到尊重。
三、信托终止
现在再讨论信托的终止。所有制作完善的信托都有关于信托自然终止的规定。例如,假若信托规定收益在A生前交付给A,剩余本金交付给B。那么在A的终生财产权结束时,信托即终止。不过,这里讨论的是通过受益人的自愿行为或通过反永久规则的运作而引起的信托提前终止。
(一)受益人的自愿行为
首先分析受益人自愿行为引起的信托提前终止。通过设立信托,委托人选择了给予受益人有限的衡平法利益,而不是赋予受益人对信托财产的直接所有权。那么受益人在何种程度上可以决定直接取得信托财产呢?
英国衡平法院1841年在裁决桑德诉沃捷案〔54〕Saunders v.Vautier,(1841)41Eng.Rep.482(Ch.).时即面临这一问题。遗嘱人理查·莱特将其在东方印度公司的所有股票为其孙侄子丹尼尔设立了一份信托。根据信托条款,利息、股息在丹尼尔年满25周岁之前积累起来,在丹尼尔年满25岁时,股票(包括利息和股息)直接交付给他。〔55〕Id.at 482.丹尼尔年满21岁时便向法院申请,要求立即占有这份财产。法院同意这一请求,认为丹尼尔无可争辩地被授予了利益,〔56〕“无可争辩地授予”的未来财产权益意味着不受禁止占有或受益的条件限制,一旦成为所有人的财产,也不受禁止其成为绝对所有权的限制。Restatement(Third)of Property:Wills &Other Donative Transfers§25.3 comment a(Tentative Draft No.6 2010).一旦其达到法律行为能力的年龄,即有权要求取得那份财产。桑德诉沃捷案的观点被理解为,在信托上享有衡平利益且有法律行为能力的全体当事人要求终止信托、分配信托财产时,信托可以提前终止。〔57〕Gregory S.Alexander,supra note〔20〕,at 1201.
1889年之前,美国法院通常遵循的是桑德诉沃捷案规则。〔58〕Id.;see also Austin Wakeman Scott et al.,supra note〔8〕,at 2207.(“美国的立场是,如果变更或终止信托会损害信托的实质目的,即使全体受益人同意,也不能终止或修改信托。这一立场直到19世纪后半叶才得到广泛接受。”)1889年,美国马萨诸塞最高法院判决了克拉佛林诉克拉佛林一案。〔59〕Claflin v.Claflin,20N.E.454(Mass.1889).该案基本案情如下:威尔伯·克拉佛林将其剩余财产设立了一份信托,指示受托人出售这些财产,并将收入的三分之一直接支付给他的妻子玛丽,三分之一的收入直接支付他的儿子克莱伦斯,另外三分之一收入以其儿子阿德尔伯特为受益人设立信托并按以下要求支付:1万美元在阿德尔伯特21岁时支付;1万美元在阿德尔伯特25岁时支付;剩余财产在阿德尔伯特30岁时支付。阿德尔伯特年满21岁不满25岁时,即向法院诉请终止信托并立即分配信托财产。根据桑德诉沃捷案规则,这一主张具有坚实的理由,但法院拒绝了他的要求,相反提到了该院七年前在百老汇国家银行案中的判决,强调说——这里引用克拉佛林案中法院的表述——“遗嘱人有权在处置财产时施加其认为适当且不与法律冲突的限制和约束。这种意愿应该予以尊重,除非这些意愿违反了某些实定法规则或与公共政策相违背。”〔60〕Id.at 456.正如法院在克拉佛林案中指出:
在原告年满25岁和30岁时将款项支付给他并未违反公共政策,或与授予原告的财产权不相符合,因而我们无法发现遗嘱人的要求不应予以执行。〔61〕Id.
克拉佛林诉克拉佛林案规则意味着:只有在下列两个条件都满足的情况下,自愿同意才可以提前终止信托:第一,全体受益人必须同意提前终止信托,并且都具有法律行为能力(正如桑德诉沃捷案所揭示的那样);第二,提前同意终止信托不得损害委托人设立信托的“实质目的”。〔62〕See Restatement(Second)of Trusts§337(1959).
在克拉佛林案之后的几十年当中,许多类型的信托都被认定包含了实质目的而坚不可摧。〔63〕关于一些案例的概要,See id.§337reporter’s notes.特别是,当信托中存在赋予受托人在收益和本金支付上具有裁量权的规定(以下简称为“裁量规定”)〔64〕Austin Wakeman Scott et al.,supra note〔8〕,pp.2223-2224(“当某一信托……属于裁量信托时,其受益人不能强制终止信托”).或者包含了挥霍条款〔65〕See id.§34.1.2,pp.2213-2215.时,都被认为包含了实质目的。由于几乎所有的现代信托都包含了裁量规定,并且大部分现代信托都包含了模式化的挥霍条款,因而在现代可以提前终止的信托数量实际上已经很少了。
但美国法律出现了新的趋势。《信托法重述》(第三版)和《统一信托法》在显著松动实质目的要件方面进行了突破。在此,有三点值得强调:
首先,单纯地存在挥霍条款不再“被推定为构成信托的实质目的”,〔66〕Uniform Trust Code§411(c),7CU.L.A.498(2006)(2004年修正案将其置于括号之中);accord Restatement(Third)of Trusts§65comment e(2003).正如《统一信托法》第411条评论指出:
有时将挥霍条款解释为构成一个实质目的,而不去探究委托人的意愿……这种结果问题重重,因为将挥霍条款置入信托文件常常是没有经过考虑的……(《统一信托法》的规定)并不否定这种可能性:让信托持续下去以确保挥霍条款的保护可能是特定委托人的实质目的。是否存在委托人的目的却是一个事实问题,需要根据整体情况进行确定。〔67〕Uniform Trust Code§411comment(amended 2004),7CU.L.A.500(2006).第二,单纯存在裁量规定不足以“认定或推定那种阻止全体受益人同意终止信托的实质目的”。〔68〕Restatement(Third)of Trusts§65comment e(2003).正如《信托法重述》(第三版)第65条评论指出:“裁量规定……可能只是代表委托人打算将其财产利益在各个受益人之间进行弹性分配,并非表示对某些事情的担忧或者禁止受益人共同终止信托的保护性目的。”〔69〕Id.
第三,即使法院认定一份信托能被证明实质目的的存在,法律也要求法院根据新的规则在实质目的与提前终止信托的理由之间进行权衡。如果法院“认定终止信托的理由……胜过实质目的”,则可提前终止信托。〔70〕Id.§65(2).简单而言,委托人的目的并非自动地超越受益人的目的。
如果回到本文中心的基本问题——“信托财产是谁的”——自愿行为提前终止信托的新规则显示,法律正从委托人的主导地位进行回调,进而朝着更加平衡地尊重受益人的权利和意愿的方向发展。这种新的平衡也体现在下面依据反永久规则终止信托的案例中。
(二)反永久规则
反永久规则旨在对赠与者在财产绝对所有权上施加约束进行期限限制。这一规则源自1682年衡平法院判决的诺福克公爵案。〔71〕Duke of Norfolk’s Case,(1682)22Eng.Rep.931(Ch.).不过,该规则的基本框架是150多年后才确立的。的确,正如世世代代的律师和法律学生所知,该规则由哈佛大学约翰·奇普曼·格林教授构筑而成。用他的话说:“如果可能的话,利益必须在不迟于信托创设时存活的某个人21年内给予,否则就不是真正的利益。”〔72〕John Chipman Gray,The Rule Against Perpetuities§201(2ded.1906).类似思路(但不完全相同)在该书1886年第一版中就已出现过。
始于诺福克公爵案并由格林教授构筑的上述规则适用于财产上的预期未来权益。〔73〕“预期”未来权益“受以前形式规定的条件的约束,而不受后来形式规定的条件的约束”。Restatement(Third)of Property:Wills &Other Donative Transfers§25.3comment a(Tentative Draft No.6 2010).起初,这个规则的影响主要体现于土地上的未来预期权益上。因为众所周知,英国早期的大部分财富是以不动产的形式体现的。〔74〕See Chantal Stebbings,The Private Trustee in Victorian Englan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6.随着时间的推移,财富的主要形式由不动产转向动产,即“金融债务”——或者按照罗斯科·庞德典雅的表述:“在商业化时代中,财富是由大量的承诺构成的。”〔75〕Roscoe Pound,An 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Law(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22),p.236.由于这些承诺越来越被置于信托之中,所以上述规则对它们也同样适用。〔76〕See Olin L.Browder,Jr.,“Trusts and the Doctrine of Estates”,72Michigan Law Review(1974),1509.
反永久规则要求:欲使预期未来权益有效,该权益就必须在某人生存期间加21年内确定地给予。这一要件的意义在于,信托利益不得无限期存续(持续为慈善目的持有的利益存在例外,〔77〕See Uniform Statutory Rule Against Perpetuities§4(5)(1990)(其对反永久统一制定法规则设立了一个例外:“慈善机构持有的预期财产利益……如果另一个慈善机构持有的利益先于该预期财产利益”);Restatement(Second)of Trusts§365(1959)(“即使依据信托条款某慈善信托将无限存续,该信托也并非无效”).举例来说,威廉·潘1704年藉助一纸宪章设立的信托至今仍有效存在。See generally Trs.of New Castle Common v.Gordy,93A.2d509,511-13(Del.1952)(其论述了信托设立历史发展中的法律问题).但这种例外不属于目前讨论的范畴)。
有必要搞清楚的是,这个规则是如何对信托利益进行时间限制的。在某一时点,信托设立时活着的所有人都会死亡。那时如果依然存在信托利益,这些利益将由信托设立时尚未出生或不确定的那些人持有。未出生或不确定的受益人的利益视受益人将来是否出生和确定而定。这样的利益可以为个人(如委托人年龄最长的曾孙)也可以为某一类人(如委托人的后代)设定。〔78〕See Restatement(Third)of Property:Wills &Other Donative Transfers S§13.1(a)(Tentative Draft No.4 2004).[“种类赠与(class gift)是把财产赠与依团体标签来界定的那些受益人,并且这些受益人是作为一个团体而出现的。‘作为一个团体出现’意味着……该种类成员通常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处在变动之中……”]无论哪一种情况,未出生或不确定受益人的利益就是不确定的,因而受反永久规则的约束。为了让这种利益有效,该规则要求这种不确定性须在信托设立时活着的某个人生前外加21年内加以确定。以“我的孩子”为剩余受益人设立的遗嘱信托即满足这个标准。在我自己生前外加瞬间时间(更不要说21年)内可以确定是否有、有多少以及哪些孩子将会出生(或由我收养)。但只要有孩子在我死亡时还活着(这是可能的),以我的曾孙为剩余受益人设立的遗嘱信托就不满足这个标准。这些孩子以后可能会生(作为父亲或通过收养)我的孙子,孙子以后可能会生(作为父亲或通过收养)我的曾孙。在此情况下,需要花比生前外加21年更长的时间来确定是否有、有多少以及有哪些曾孙将会出生或收养。〔79〕For purposes of the Rule Against Perpetuities,class gifts are governed by the“all-or-nothing”rule of Leake v.Robinson,(1817)35Eng.Rep.979(Ch.).这种不确定性太飘渺,因此,根据上述规则,这种利益是无效的。无效的后果就是无效利益从财产分配上剔除出去。〔80〕W.Barton Leach,“Perpetuities in a Nutshell”,51Harvard Law Review(1938),656.(“若某一利益根据反永久规则是无效的,此利益即从信托文件中剔除出去……遗嘱或信托文件中创设的其他利益即行生效,就如无效的利益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一旦信托中的所有利益都很飘渺以致被剔除出去,信托就不再存在。
反永久规则具有积极的价值。信托持有的财产以分割所有权的状态存在:受托人拥有普通法上的所有权,受益人拥有衡平法上的所有权。绝对拥有的财产(并非出现在信托中)是以不可分割的所有权而持有(绝对所有权)的财产。所有人拥有相当大的按照其喜欢的方式处分财产的自由。换句话说,委托人可以要求财产以信托的方式持有,但反永久规则对其进行了期限限制。一旦该信托根据反永久规则被迫终止,该财产即进入绝对所有权的状态。
路易斯·西梅斯教授是20世纪研究未来权益的一位著名教授,他强调了反永久规则的积极作用,他说:
当代成员与后代成员都有根据其意愿处理财产的愿望,反永久规则即在二者之间保持平衡。……这里的难题在于,如果我们放纵某一代人创设未来权益的愿望,其后代成员获得的财产将处于受限制的状态。因此,他们不能创设其希望的所有未来权益。或许他们甚至根本不能创设这种未来权益。故为了最大限度满足所有代际人的愿望,必须在当代人不受限制地通过遗嘱处分财产和后代人不受限制地处分财产之间保持合理的平衡。〔81〕Lewis M.Simes,“The Policy Against Perpetuities”,103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1955),723.有关对西蒙哲学观点的评判,See T.P.Gallanis,“The Rule Against Perpetuities and the Law Commission’s Flawed Philosophy”,59Cambridge Law Journal(2000),284.换句话说,反永久规则在委托人的意愿和受益人的意愿之间提供某些平衡。
美国有超过一半的司法区颠覆了这种平衡。19个司法区允许信托永久存续:或废除反永久规则,或使该规则成为任意性规定。〔82〕这些州包括:阿拉斯加州、特拉华州(动产信托)、哥伦比亚特区、爱达荷州、伊利诺伊州、肯塔基州、缅因州、马里兰州、密苏里州、内布拉斯加州、新罕布什尔州、新泽西州、北卡罗来纳州、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罗德艾兰州、南达科塔州、维吉尼亚州以及威斯康星州。另外,还有几个州修改了这一规则,允许信托视情况持续1 000年。〔83〕这些州包括:阿拉斯加州(有关特殊指定权的行使和终止)、亚利桑那州、科罗拉多州、特拉华州(关于不动产信托)、弗罗里达州、密歇根州、内华达州、田纳西州、犹他州、华盛顿州以及怀俄明州。
如何解释这种令人困惑的状况呢?答案在于联邦税法的漏洞和各州对信托业的推动。1986年,联邦代际转移税进行了改革。〔84〕See 26U.S.C.§§2601-2604(2006).代际转移税对持续一代以上的信托征收高额的税收,但也存在一个巨大免征额:2011年,代际转移税的免征额是每捐赠人五百万美元。〔85〕Id.§§2631,2010(c).用等于或低于免征额的财产设立信托即免征代际转移税,不管信托持续多长时间,也不论信托本金因投资而增加了多少收入。〔86〕See id.§§2641(a),2642(a).
在设计联邦代际转移税的免征额中,国会犯了一个基本的错误(尽管是可以理解的):它依赖于反永久规则——这一规则属于州法而非联邦法的一部分——来控制免征联邦代际税信托的存续期间。〔87〕美国法律学会持这种观点。《财产法重述》(第三版)第27章引言部分指出:“在代际转移税免征问题的规制中,国会依赖于州的反永久法来控制免征代际转移税信托的存续期间,从而将免征代际转移税信托的存续期限交到各州手中。然而,相比联邦财政收入的保护而言,一些州在发展州内机构受托人信托业方面表现了更大的兴趣。”Restatement(Third)of Property:Wills &Other Donative Transfers chapter 27,introduction note(Tentative Draft No.6 2010)(2010年5月由全体成员一致赞成通过).这个错误将免征代际转移税信托的存续期间交到州立法机构手中。在联邦体制下,州立法机构根本没有兴趣保护国家的财政收入,相反它可能有兴趣的是在自己的管辖区中吸引信托业和增加收入。1986年以后开始出现支持永久或近乎永久信托的运动,由于律师和银行机构了解到这一运动具有吸引信托业的潜能,该运动的发展得以突飞猛进。〔88〕See Max M.Schanzenbach &Robert H.Sitkoff,“Perpetuities or Taxes?Explaining the Rise of the Perpetual Trust”,27Cardozo Law Review(2006),2476-2478;Robert H.Sitkoff &Max M.Schanzenbach,“Jurisdictional Competition for Trust Funds: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Perpetuities and Taxes”,115Yale Law Journal(2005),359-363.根据永久信托运动,一些观察者认为反永久规则在国家层面上已经死亡。〔89〕See Austin Wakeman Scott et al.,supra note〔8〕,at 503n.16(其中引述了15篇讨论反永久规则没落的论文);See also,e.g.,id.§9.3.9,at 503(“可以斗胆地说,不管是好是坏,反永久规则当前正处于落寞之中”);Note,“Dynasty Trusts and the Rule Against Perpetuities”,116Harvard Law Review(2003),2609[其中提到“目前导致反永久规则死亡的王朝信托(the dynasty trusts)”].
借用马克·吐温的话说,反永久规则死亡的说法被极大夸大了。的确,该规则最近注入了新的活力并进行了重新改造。《信托法重述》(第三版)最后一章即对该规则进行了重构:从对飘渺地授予预期未来权益施加限制到对信托或其他财产赠与处分的存续期间施加直接限制。对于这种重构,美国法律学会是赞同的。〔90〕有关“改变此规则,要求在永久期间到来或终止之前终止信托”的问题,see T.P.Gallanis,“The Future of Future Interests”,60Washington &Lee Law Review(2003),559-560;Daniel M.Schuyler,“Should the Rule against Perpetuities Discard Its Vest?”56Michigan Law Review(1958),709.根据重构规则,反永久规则要求信托在最新设置的永久期间到来之日或到来之前终止。目前,这个期限是不超过转让者后两代的最后一位存活的受益人死亡时截止。〔91〕Restatement(Third)of Property:Wills &Other Donative Transfers§27.1(Tentative Draft No.6 2010).有一项是为低于30岁或30岁以下某特定年龄的受益人持有信托财产的规定。See id.§27.1(a).在上述期间内信托不终止者,将面临司法的调整以致其在该期间内终止。〔92〕Id.§27.2.
重构上述规则是为了更加直接地实现传统规则的目标,用《财产法重述》(第三版)的话说就是:
对死手控制保持合理限制的重要理由是,该限制可以强力控制被束缚的财产,促使其定期向活人进行转移,从而摆脱最初转让者施加在财产上的限制。活人然后可以根据其意愿使用该财产,包括根据新的规定用此财产再次设立信托。〔93〕Id.ch.27,intro.note.
《财产法重述》(第三版)所谓的比重重构比这一规则更进一步。该重述也表达了美国法律学会的官方立场,即认为允许设立永久或近乎永久的信托是欠考虑的:
最近立法运动允许设立永久信托或可存续若干世纪的信托,美国法律学会慎重地认为这是欠考虑的。
抑制死手过度控制的规则深深扎根于这个国家的历史和传统之中,并存在正当理由。2010年设立的存续360年的信托可以存续到2370年,并有100 000以上的受益人。2010年设立的存续1 000年的信托可能在3010年终止并有百万个受益人。没有转让者能有足够的智慧在这么大的时间跨度中为如此遥远且数量巨大的受益人做出正确的财产处分。在2010年设立的存期1 000年或360年的信托中,可以为持续到遥远未来的信托嵌入当前认为是灵活的条款。用更远的眼光来看待这一问题的话,可以考虑在1650年或更早时(即360年以前或更早以前)可以利用的在后代中控制家庭财富的工具。这样的工具在打字机出现之前首先采取的是不可撤销的限定继承的形式,后来限定继承变成可撤销,又采取严格处置的形式。如今这些工具早已不合时宜。如果说在360年或更早以前认为是复杂的工具今天看来是很原始的,那么有理由怀疑,今天看来是复杂的工具在360年或更长时间以后将被认为是原始的。〔94〕Id.
简单地说,在有关未来权益和永久规则的法律规制上,《财产法重述》(第三版)体现的新的方向就是,重新平衡信托委托人的意愿及利益与信托受益人的利益。
四、理论构架
在前面的讨论中,我们看到了美国信托法新方向的四个例证。这些例证综合起来反映了法律的一种动向:对委托人的偏爱进行适度回移,从而朝着越发认可受益人权利、责任和意愿的方向发展。
现将这种新的规则方向置于更大的理论框架之中。如果在普通法和衡平法之间划定不同的区域,信托法应有自己的位置,但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在财产法和契约法之间存在重叠。最近学者中一直在争论一个问题:信托是接近于财产权还是接近于契约?〔95〕关于该争论的叙述,See Robert H.Sitkoff,“An Agency Costs Theory of Trust Law”,89Cornell Law Review(2004),627-633.契约论学者把信托看作主要是委托人和受托人之间的一种契约,受益人则处于类似于契约第三人的地位。〔96〕See e.g.,John H.Langbein,“The Contractarian Basis of the Law of Trusts”,105Yale Law Journal(1995),627;See also Robert H.Sitkoff,supra note〔95〕,at 647(其用“剩余索取权人”这一组织法上的词语来形容信托受益人).颇有影响的契约论学者约翰·郎拜因教授宣称:“委托人和受托人之间的交易在功能上与现代第三人利益契约已无明显区别,信托就是契约。”〔97〕Id.John H.Langbein,627.相反,财产权论学者则把信托及受托人角色看作本质上是“以财产权为基础的”:〔98〕Gregory S.Alexander,“A Cognitive Theory of Fiduciary Relationships”,85Cornell Law Review(2000),768;See also Tamar Frankel,Fiduciary Law(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p.233(其把受托人—受益人之间的关系看作是“以财产为基础的”).信托是源自转让或赠与的一种财产权安排,它不是契约。〔99〕Restatement(Third)of Trusts§5(ⅰ)comment i(2003);Restatement(Second)of Trusts§197 comment b(1959).
在此问题上,笔者属于财产权论者之阵营。〔100〕See e.g.,T.P.Gallanis,supra note〔42〕,1621.(“现代受信管理法对委托人的契约权力施加了物权上的限制。在不可撤销信托中,法律虽然赋予了委托人控制受托人行为的巨大空间,但这并不能免除受托人为受益人利益管理信托的核心责任。”)尽管如此,需强调的是,这些立场并不是“全有全无”式的:〔101〕还有一种观点,即批判契约主义但其本质上大概也不属于物权主义派。这种观点由梅兰妮·莱斯利教授提出。他认为,将受信义务看作任意性规则会弱化其道德力量,并造成其内容难以把握。Melanie B.Leslie,“Trusting Trustees:Fiduciary Duties and the Limits of Default Rules”,94Georgetown Law Journal(2005),89.在上述争论中,参与者都承认信托结合了契约和财产权的特点。〔102〕John H.Langbein,supra note〔96〕,at 669(“信托是契约和财产权的混合物,承认其契约要素并不要求无视那些优势显著的财产权成分”);See also Robert H.Sitkoff,supra note〔95〕,at 633(“如同其他组织法一样,信托法将对人特性与对物特性进行了精细的融合”).只是学者在阐述各自立场时更加突出和强调信托的契约或财产权因素而已。
在契约论—财产论的轴心上,一个人采取何种立场通常会影响其对信托法中任意性规则和强制性规则作用的看法。除相对少数的情况之外,契约论学者常常偏爱于任意性规则,从而给予委托人最大限度的灵活性以使其在制订信托条款时与受托人讨价还价。〔103〕Robert H.Sitkoff,supra note〔95〕,at 624.(“这篇文章的基本观点是,法律在将管理权授予受托人、剩余权益赋予受益人时,应当降低其中的固有代理成本。但降低成本必须与委托人的事前指示相一致。”)See also John H.Langbein,“Mandatory Rules in the Law of Trusts”,98Northwestern University Law Review(2004),1126.(“信托法基本上全部由任意性规则构成。强制性规则几乎不会干预普通的实践。”)
持财产权论的学者通常更愿意使用强制性规则,这些强制性规则会忽略委托人的意愿以保护受益人持有的财产权利。〔104〕这对英国信托法而言特别正确,英国信托法即把信托看作是一种“财产权关系”。John Mowbray et al.,Lewin on Trusts,18th Ed.(London:Sweet &Maxwell,2008),p.7(指出“在宽泛意义上,信托受益人权利的所有权本质是对受托人主张所有权救济的核心”);See also David Hayton et al.,Underhill and Hayton:Law of Trusts and Trustees,18th Ed.(London:Butterworths Law,2010),p.19(其提到“传统上强调信托的所有权本质”);J.E.Penner,The Law of Trusts,7th Ed.(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p.39(“不幸的是,信托的‘债务’层面之见解有时依然是令人困惑和头痛的问题……”).需要强调的是,英国法对受托人施加了一种强制性义务,即告知受益人有关信托及其管理的情况。See David Hayton,“The Irreducible Core Content of Trusteeship”,in A.J.Oakley(Ed.),Trends in Contemporary Trust Law(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53(“受托人的有些责任对于信托的存在而言是基本的,对此委托人不能……免除”).在美国,《信托法重述》(第三版)和《统一信托法》将受托人的告知义务看作是强制性义务,但许多州在通过统一信托法时拒绝采纳这一规定,而是将告知义务构筑成任意性规则,从而委托人可以拒绝适用;统一法律委员会屈于现实,将《统一信托法》中与此相关的规定置于括号之中。See Uniform Trust Code§105(b)(8),(b)(9),7CU.L.A.429(2006)(其将下列义务视为强制性义务,即“告知合格受益人……信托的存在……及其有权要求受托人报告……的义务”以及“对(合格)受益人要求……受托人提供报告及其他合理的、与信托管理相关的信息……进行披露的义务”);id.§105comment[其揭示了2004年修正案将(b)(8)和(b)(9)分款置于括号中的意义,即表示在此问题上“难以期待统一”];Restatement(Third)of Trusts§82comment a(2)(2003)(“向某些受益人提供信息的义务……在某种程度上或短期内是不会彻底免除的,这会不适当地干预信息要求的实效或基本目的”).展开来说,契约论学者强调委托人的目的,财产权论者则强调受益人的财产权利益。
相对美国信托法而言,英国信托法较为一贯地(一直是并且继续是)持财产权论立场。〔105〕参见上注。回到前面所谈的四个例证:英国法依然遵循桑德诉沃捷案规则,允许全体受益人的同意而提前终止信托;〔106〕See John Mowbray et al.,supra note〔104〕,at 850-853.英国从来不认可挥霍信托;〔107〕挥霍信托包含了利益转让“禁止限制”的挥霍条款。关于“禁止限制”(disabling restraints)与“没收限制”(forfeiture restraints)之间的区别,see Restatement(Second)of Property:Wills &Other Donative Transfers§3.1,3.2(1983).转让的禁止限制在英国是不允许的。See John Mowbray et al.,supra note〔104〕,at 177-1778,1184.英国法认可没收限制——例如,关于破产、清算的转让——在此情况下,受益人的利益视所述事件的发生进行转让或剥夺。See id.at 181-86.有一个例子即所谓的“保护信托”,目前出现在英国制定法的一个注脚中。Id.at 186-190.英国法赞同管理偏离规则,而不探究委托人的推测意图;〔108〕See Variation of Trusts Act,1958,6 &7Eliz.2,c.53,§1(1)(U.K.);Trustee Act,1925,15 &16 Geo.5,c.19,§57(1)(U.K.).有关讨论,See John Mowbray et al.,supra note〔104〕,at 1858-1861,1867-1868,1878-1879,1892.英国保留了反永久规则(目前以立法的形式体现),〔109〕See Perpetuities and Accumulations Act,2009,c.18(U.K.).因而禁止永久或近乎永久信托的存在。
在契约论和财产权论的轴心上,美国法当前位于何处又向何处发展呢?
五、结论
19世纪末及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当中,美国法朝着契约主义和偏爱委托人的方向发展。然而本文所举例证显示,因美国信托法要在委托人意愿和信托受益人财产权之间实现平衡,钟摆目前正向中间位置回摆。钟摆的这种运动方向可从现代对挥霍条款、管理偏离、克拉佛林规则以及反永久规则的立场中得以探知。然而需要强调的是,钟摆只是朝着中间方向回摆,而不是超越这一位置。信托文件中体现的委托人的意愿依然具有很大的反响力,且事实的确如此。“赠与转让的美国法组织原则是在法律允许的最大范围内尊重赠与者的意愿。”〔110〕Restatement(Third)of Property:Wills &Other Donative Transfers§10.1(2003).美国信托法源自英国信托法,但美国信托法没有采纳英国信托法的财产权主义立场。尽管如此,在委托人意愿和信托受益人的利益和权利之间重新取得平衡,这既是恰当的也是值得欢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