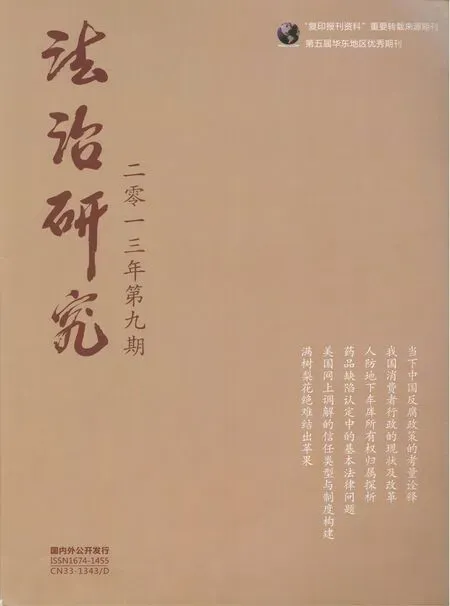药品缺陷认定中的基本法律问题*
2013-04-18张建平
张建平
药品具有公共性、危险性、政府管制性等特征,其生产上市经历了系统的科研论证以及严格的行政审批,因此,认定药品缺陷需要比普通产品更为审慎。在西方产品责任法中,药品缺陷的认定规则也更为特殊。然而,受种种因素制约,我国的缺陷药品责任仍然处于“初级阶段”。这种初级阶段表现为,在司法实践中,不论是律师还是法官,仍旧在一些基础问题上存在疑问:例如,药品质量合格是否构成缺陷;发生药品不良反应,企业是否可以免责;经过检验符合国家标准,药品是否存在缺陷;企业符合药品监督管理所有规定,是否需要承担民事责任等等。上述疑问在龙胆泻肝丸系列诉讼①2005年,龙胆泻肝丸系列诉讼——“李玲诉北京同仁堂案”、“王春华、冯萍萍诉北京同仁堂及同仁堂中药二厂案”、“李树花诉北京安定医院和同仁堂案”均被驳回起诉,原因包括“不足以证明其服用的龙胆泻肝丸是北京同仁堂生产的”、“龙胆泻肝丸的生产和销售均经国家主管部门批准的”。、奥美定系列诉讼②自隆胸产品奥美定1999年获批进入市场,相关的诉讼就没有停止过。但由于生产企业吉林富华公司持有两张王牌——医疗器械注册证和检验报告,截止2006年国家药监局撤销其产品注册证,消费者无一胜诉。以及减肥药曲美召回“拒赔门”事件③2010年,国家药监局正式叫停曲美等15种含有西布曲明的减肥药。减肥药曲美减肥胶囊,被生产商太极集团召回。该集团认为,西布曲明胶囊是2000年经正式依法注册、生产质量完全符合国家标准的合格产品。所以对此前长期服用曲美的消费者没有赔偿计划。上,表现得尤为典型。而类似疑问,在普通产品责任中也屡见不鲜。
由于我国现行的民事立法没有相关的明确规定,加之问题本身牵扯行政规制与民事侵权、横跨法律与技术领域,因此在实践中长期难以得到有效解决。在药品责任诉讼中,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是否立案或者驳回起诉,因此是不可忽视的“大问题”。本文拟从药品缺陷认定的基本问题(药品缺陷与药品质量;药品缺陷与药品标准;药品缺陷与药品监管)入手,进行系统地梳理和剖析,力求在药品缺陷,乃至产品缺陷的认定前提上,恢复“常识性”认识。
一、药品缺陷与合格药品
(一)产品缺陷的本质是产品的安全性问题
根据侵权法和产品责任法的基本理论,产品缺陷是指产品存在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不合理危险,即产品不具备相应的安全性。世界各国立法及相关公约对此虽然表述各异,但其都与产品的“不安全性”或“危险性”相关。我国《产品质量法》第46条也明确了这一点。
产品缺陷的本质是产品的安全性问题。产品责任制度的出现,源于产品工业化时代出现的无法避免的潜在大规模风险。作为侵权法中的制度性安排,产品责任制度就是对于这种风险的法律防范和司法救济。产品缺陷的核心是对于产品危险性或者安全性的评价,而不是产品质量的优劣问题的评判。
我国国家标准GB/T19000:2008(等同于国际标准 ISO90001:2008)对“质量”定义为:“一组固有特性,满足要求的程度。产品的固有特性包括物质特性、感官特性、时间特性、人体工效特性、功能特性等,而安全性只是众多质量特性之一。”
产品质量与产品的安全性区别在于:(1)地位不同。两者为种属关系,前者包含后者。(2)标准不同。产品质量存在合格产品与假冒、伪劣产品之分,而合格产品甚至存在优、良、中、合格等不同等级。但从安全性角度来讲,产品只存在有缺陷、无缺陷的两种分法。(3)特征不同。产品质量内涵广泛,具有时效性、相对性的特征,而产品的安全性内涵固定,具有绝对性特征。
必须注意的是,不能用产品质量取代产品的安全性。产品的质量与安全性是密切联系但是又不能完全等同的两个概念。合格产品甚至优质产品不等于没有缺陷的安全产品。由于评判产品是否合格的质量指标,限于科技水平、检验效率、标准设计目标等原因,不一定涵盖所有的安全性指标。《食品安全法》代替《食品卫生法》即是明证。“卫生”和“安全”两词之差,反映了食品领域从满足温饱到保障安全之间法律制度的变迁。
我国目前没有独立的产品责任法。相关的法律渊源散见于《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而《产品质量法》最为集中。但是,《产品质量法》本质上是产品质量管理法。1993年《产品质量法》的出台是为了解决产品质量差的突出问题,而2000年该法的修订则重点强化了质量约束机制和监管手段、制裁力度④苟铭:《法治的力量——就〈产品质量法〉颁布10周年访国家质检总局法规司司长刘兆彬》,载《中国质量技术监督》2003年第3期,第161~162页。,重点均不在于产品侵权责任。
《产品质量法》的第四章“损害赔偿”部分继承了《民法通则》第122条“因产品质量不合格造成他人财产、人身损害的,产品制造者、销售者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沿袭的是产品质量责任的立法思路,并未区分产品安全责任和产品质量责任。新制定的《侵权责任法》单立了第五章“产品责任”,可惜关于何为缺陷,具体条款上并无新的突破。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立法还是司法领域,已经注意产品责任与产品质量责任的界限。国内相关的立法释义,大量的学术论文、硕士博士论文,以及产品责任司法判例,不断反复论证合格产品的产品责任问题。
(二)合格药品也可能是缺陷药品
按照世界各国的立法和民法理论,产品缺陷一般分为设计缺陷、制造缺陷、警示缺陷。药品也不例外。药品的制造缺陷一般即药品存在质量问题。但药品即使质量合格,也可能存在安全隐患。现有的部门规章认可了这一点。根据2007年12月10日国家药监局令发布的《药品召回管理办法》,药品召回的适用对象是已上市销售的存在安全隐患的药品(以下简称“问题药品”)。安全隐患,是指由于研发、生产等原因可能使药品具有的危及人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不合理危险⑤根据药品安全隐患的严重程度,药品召回分为:(1)一级召回:使用该药品可能引起严重健康危害的;(2)二级召回:使用该药品可能引起暂时的或者可逆的健康危害的;(3)三级召回:使用该药品一般不会引起健康危害,但由于其他原因需要收回的。。可以看出,安全隐患基本上涵盖了药品缺陷,问题药品其实涉及到了存在设计缺陷、警示缺陷的药品。而药品召回制度在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已实施多年,上述规定已基本成为国际惯例。
具体来讲,如果在药品的有效成分的筛选与确定、给药剂量的确定、适应症与功能主治的确定、内包装材料和容器的选择、储藏的设定等方面存在问题,药品可能存在设计缺陷;如果对药品的适应症、用法用量、药品的不良反应、禁忌、注意事项、药物相互作用没有作出充分合理的说明,药品可能存在警示缺陷。
因此,合格药品仅仅表明药品质量检验合格,无法排除药品所有的危险性,即无法排除药品缺陷的存在。
(三)药品不良反应不是避风港
药品不良反应是指合格药品在正常用法用量下出现的与用药目的无关的或意外的有害反应。⑥2004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令第7号发布《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和监测管理办法》第29条(一)。其基本要素包括药品质量合格、合理用药、超出预期、损害后果、因果关系五个要素。但无论是医药行业内,还是司法界,很多人误认为药品不良反应是可以免责的,代表性理由分别有:(1)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的原因是复杂的,完全避免是不可能的,缺陷的概念用在医药上是模糊的。⑦李应兰、吴忠豪:《试论药物不良反应的责任和法律义务》,载《中国药事》2000年第2期,第91~93页。(2)药品不良反应是限于科技水平所不能解决的问题,按照法定概念,一经鉴定为药品不良反应,实际上已经排除了人为过失或过错;药品生产或经营者只要没有过错,一般而言不必承担法律责任。⑧孙骏、卢军锋:《试述药品不良反应的法律责任》,载《江苏药学与临床研究》2004年第12期,第12~14页。(3)单纯的药品不良反应根据现行法律可以免责,应通过医疗保险或基金给予受害者补偿。⑨田侃:《药品不良反应的法律责任》,载《中国执业药师》2005年第1期,第12~14页。
本文认为,药品不良反应概念的前提是合格药品。正如前文所述,药品合格基本否认了制造缺陷的存在,但无法排除设计缺陷、警示缺陷的可能。某些药品不良反应恰恰可以通过药品合理的设计、充分及时的警示来避免:(1)药品中的某种成分可以替换为更为安全的成分。旧版龙胆泻肝丸所含的“关木通”是马兜铃属植物关木通,所含的马兜铃酸在体内积蓄会引起慢性肾功能损害、肾衰竭甚至死亡等严重药物不良反应。1985版《中国药典》中,龙胆泻肝丸的成分木通药材栏目只有“川木通”和“关木通”;1990版《中国药典》将“木通”改为“关木通”;2003年国家药监局发出通知,取消关木通药用标准,要求生产企业将关木通替换为“木通”(木通科)。(2)药品生产工艺的改进可以减少药物过敏反应的发生。研究认为,青霉素过敏反应的过敏原是制剂中的高分子杂质,减少青霉素过敏反应的关键是提高产品纯度,结晶工艺条件是提纯和去除致敏性高分子杂质的关键。青霉素生产工艺虽然相同,但生产厂家技术水平不同,其质量亦有差别。⑩任吉民、李雅琳:《青霉素过敏反应研究近况》,载《中国药房》2003年第14卷第 4期,第250~251页。(3)药品说明书中根据药学研究及时添加警示语。2006年,鱼腥草注射液等在临床中出现了过敏性休克、呼吸困难和重症药疹等严重不良反应,甚至有死亡病例报告。同年11月3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出通知,修订鱼腥草注射液(肌内注射)说明书。在新修订的说明书上,警示语“警告本品可能导致严重过敏反应”被标在了药品名称、成分、功能主治等信息前。
从总体上来说,药学史就是药品不良反应的发现史。对于具体某个药品来讲,通过合理的设计、及时的警示,甚至质量标准的提高,某一项不良反应可以也是应当避免的。近几十年的药学发展史,是逐步提高药品安全性、有效性的历史,也是药品不良反应的监测、控制和防范史。
1957年~1961年发生波及17国的“反应停事件”,因孕妇广泛服用止吐剂“反应停”而产下一万多例“海豹肢畸形”胎儿。1957年所涉药物首先在德国作为镇静安眠剂应用于妇女妊娠呕吐的治疗。由于当时药品临床研究和审评的要求不高,该药属于政府审批的质量合格药品。但该药存在明显的设计缺陷,制药企业对动物实验不够深入,并未发现该药致畸作用的孕后敏感期。1961年年底,联邦德国亚琛市地方法院受理了全球第一例控告“反应停”生产厂家的案件,7名工作人员因为在将“反应停”推向市场前没有进行充分的临床实验以及在事故发生后试图向公众隐瞒相关信息而受到指控。1970年4月10日,原被告双方在法庭外达成了和解,生产厂家同意向控方支付总额1.1亿德国马克的赔偿金。1971年12月17日,联邦德国卫生部利用赔偿款项专门为“反应停”受害者设立了一项基金。此后数年间,联邦德国有2866名“反应停”受害者得到了应有的赔偿。⑪参见文执:《反应停:五十年恩怨》,载《科技文萃》2003年第3期,第174~176页。
跨国医药巨头面对新药不断披露的严重不良反应胆战心惊,生怕官司缠身;而在我国则区别对待,连一声道歉都没有。⑫2007年,美国制药巨头默克公司支付48.5亿美元赔偿金,通过和解协议了结美国近5万宗与止痛药“万络”有关的诉讼。中国有超过200万的患者服用过此药,北京一律师事务所尝试召集20万“万络”使用者索赔,但无果而终。这充分表明了中西药品侵权法律制度上的巨大差异。药品不良反应不是药品缺陷的避风港。现有科技水平条件下能够避免而未能避免的药品不良反应,实质就是缺陷药品的侵权事实。因此,药品不良反应不排除侵权责任。
另外,对于现有科技水平条件下无法避免的药品不良反应,构成产品责任中的发展风险抗辩(或科技水平抗辩),可以免除侵权责任。受害人的救济问题,则可以通过设立类似北欧、日本、我国台湾地区的药害救济制度⑬瑞典分别于1975年、1978年实施了病人伤害保险制度和药物保险计划。日本通过1977年《医药品副作用被害救济基金法》创设了独立基金救济制度。丹麦于1995年颁布了《丹麦药品伤害赔偿法》,建立了处方药不良反应国家补偿制度。我国台湾地区亦于1999年发布实施“药害救济要点”,2000年正式实施“药害救济法”,建立了专门的药害救济基金制度。来解决。
二、药品缺陷与药品标准
(一)药品标准是最低安全标准
药品标准是对药品的质量指标、检验方法以及生产工艺等的技术要求,是药品生产、供应、使用管理部门评价药品质量的法定依据,属于强制性标准的范畴。虽然是技术性规范,但药品标准实际具有与法律规范同等的地位和效力。除了中药饮片和中药材还存在地方标准外,我国所有药品必须遵守国家药品标准。国家药品标准一般分为《中国药典》、局颁或部颁标准、药品注册标准。
药品注册标准是国家药监局批准给申请人特定的药品标准,可理解为企业标准,包括新药、仿制药等等。目前存在的问题是:(1)新药注册标准有漏洞。该标准由生产企业或药物研究机构起草,要进行原材料的选择、工艺研究、药品质量的确定等整个过程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制定药品的质量标准。但新药注册标准的起草中,生产企业往往会设计对自己有利的指标体系来逃避监管,药品审评由于人力、精力限制和外来因素影响,不一定会发现标准文本中的安全风险。(2)仿制药注册标准有局限。仿制药注册经审批后,药品标准按照已有国家标准执行;对国家标准进行了提高或修改的,申请人提交药品标准草案,经批准成为正式注册标准执行;该注册标准不得低于已有国家标准。我国国家标准的局限性整体决定了仿制药注册标准的安全风险。
随着我国医药工业的不断发展,我国早期制定的国家药品标准已严重滞后于药品生产现状和药品检验工作发展的实际,一些药品标准已不足以控制药品的质量。2004年国家药监局发布《提高国家药品标准行动计划》,该计划明确指出,现有药品标准存在的问题包括:(1)中成药国家标准:囿于历史缘由,采取“先整顿后提高”,中成药部颁标准多数难以控制其质量;相当数量的品种无专属性鉴别,更无含量测定,缺乏对有害重金属、砷盐限量要求,功能主治不规范(功效描述用词欠妥;病症不分,中西医名称混用;过于宽泛,与临床脱节;禁忌、不良反应和注意注明事项不够全面)。(2)化学药品国家标准:检测方法陈旧,不能准确测定有效成分或监控杂质含量;近年来已广泛应用的检测项目不全,如“有害残留溶剂”、“细菌内毒素”等在大多数标准中均未设立;质量控制指标过低;中西药结合药品需重新评价且质量控制水平偏低。(3)生物制品标准:部分制品工艺落后,有效成分不明确;生产用原辅料未确立质量控制指标;检测方法不完善。(4)辅料标准:《中国药典》收载标准品种较少,有的标准质量难以控制。⑭参见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提高国家药品标准行动计划的通知》(国食药监注[2004]35号),2004年2月12日。
从药品标准体系而言,基本没有形成体系,多是单纯就药品标准谈药品标准,致使药品标准的责任主体不甚明确;药品标准与药品监管链各环节断裂。⑮姜红:《药品标准的解析与药品标准体系的重构》,载《中国药品标准》2008年第3期,第186页。不同的药品标准分属于不同的技术机构管理。《中国药典》、局颁标准等属于国家药典委员会管理,药品注册标准由国家药品审评中心管理(注册标准不对外公开),进口药品标准由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管理,地方药品标准由各省药监局管理。因为缺乏相应沟通交流机制,因此出现同一品种不同国家标准的现象;再加上不同标准之间地位功能和执法方面界定不清,不利于审评和监管工作的开展。⑯胡春丽、张珂良、汪丽从:《从中美两国药品质量标准现状看我国药品标准管理存在的问题》,载《中国药事》2012年第4期,第330页。
因此,现行的药品标准,无论从药品标准确立、发展水平,还是标准的管理体制上,并不能完全保证药品的安全性。从性质上来说,药品标准是药品质量标准而不是药品安全标准,它仅仅反应了药品的质量控制水平。而药品安全性,并不是药品标准设定的全部目标。有效性、质量可控性、实用性、经济性也是药品标准的评判指标。国家药品标准行动计划,是国家根据药品监管的形势需求,借助标准提升的杠杆效应,逐步提高公众用药安全水平,实现医药产业结构调整,形成以标准促进用药安全,以标准支撑行业监管,以标准引导产业发展的工作格局。⑰于江泳、余伯阳、钱忠直:《试论国家药品标准提高工作》,载《中国药事》2011年第10期,第957页。可以看出,药品标准被同时赋予了监管政策、产业调控等诸多功能,而用药安全在药品标准中究竟占多大权重,恐怕还要考虑某个时期行业实际、监管形势。药品标准只是根据药学科学、临床医学、临床药学以及制药工业的水平,在产业利益和消费者利益之间所选取的分配优势的分水岭。⑱宋华琳:《论政府规制与侵权法的交错——以药品规制为例证》,载《比较法研究》2008年第2期,第42页。
某种意义上,药品标准构成了药品规制的起点,给予了各项医药政策一个最基本的“阈值”⑲宋华琳:《中国药品标准法律制度的发展与完善》,载《中国处方药》2008年第7期,第49页。。国家药品标准仅仅是药品标准的最低要求,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各方力量综合权衡后的产物,它是用药安全的起点而不是终点,是目标之一而不是全部目标。
(二)符合强制标准与产品缺陷
我国《产品质量法》第46条规定:“本法所称缺陷,是指产品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产品有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是指不符合该标准。”上述规定与世界其他国家规定区别在于,在不合理的危险的定义之外,增加了强制性标准。实践中,该条款产生了众多的歧义和争论,符合标准是否构成缺陷也往往判决不一。
本文认为:上述第46条前半句话是关于产品缺陷的定义,而后半句话是关于不符合标准即认定为缺陷的转介条款,在缺陷判断中引入了技术标准作为判断依据。一般来看,不符合标准即认定为缺陷,没有争论。但符合标准是否不存在产品缺陷,产品质量法没有给予明确。从逻辑学上来讲,也不能推导出来。
根据上述第46条可以确定的命题(AB)是:“如果产品不符合强制标准,则存在缺陷。”该命题的逆命题(BA)是:“如果产品存在缺陷,则不符合强制标准。”该命题的否命题(-A-B)是:“如果产品符合强制标准,则不存在缺陷。”该命题的逆否命题(-B-A)是:“如果产品不存在缺陷,则符合强制标准。”
逻辑学常识告诉我们:原命题真,它的逆命题和否命题未必真;原命题假,它的逆命题和否命题未必假;互为逆否的两个命题,同真同假。即,上述第46条的AB命题成立,-B-A成立,BA、-A-B命题不一定成立。因此,对于《产品质量法》产品缺陷定义的解读,在逻辑学上普遍混淆了逆否命题与逆命题。
产品质量法的立法原意应当是,产品标准只是产品缺陷认定的一般标准但不是唯一标准。产品不符合强制标准,则不具备最低的安全性,因此存在缺陷;但产品符合标准,不等于产品具备所有应该具备的安全性,因此不排除缺陷的可能。强制性标准,只是产品缺陷的判断参考之一,而不是全部。在《侵权责任法》未来的司法解释中,为避免对《产品质量法》的继续误读,应当明确强制性标准的参考价值而不是决定地位。
(三)药品检验不是认定缺陷的唯一手段
药品检验分为企业自行检验和行政监督检验。⑳根据检验目的、适用对象和处理结果不同,药品的行政监督检验可以分为以下几类:(1)抽查检验:分为国家和省(区、市)两级;(2)注册检验:包括对申请注册的药品进行的样品检验和药品标准复核;(3)上市检验:三类药品(规定的生物制品、首次在中国销售的药品、其他药品),在销售或者进口前的强制性检验;(4)批签发:生物制品,每批药品上市时均进行强制性检验;(5)口岸检验:口岸药品检验所对进口药品依法实施的检验。不论哪一种检验,一般都必须采用国家药品标准作为检验指标。药品检验的结果是药品质量是否合格,但不能判定药品是否存在缺陷。
如前文所述:药品标准不是判断药品安全性的唯一依据。药品检验不合格,不等于绝对存在安全性问题(如药品成分有效性不足,药品标签未标明批准文号等等,药品内包材不符合规范等等);反过来讲,药品检验合格并不能等于药品不存在安全性问题。
药品检验在认定药品缺陷上的局限性在于:第一,药品检验是一项专业化的技术性工作,必须完全按照检验流程、药品标准来进行,是基于样本、数据、指标所进行的程式化工作,是基于仪器、数据的技术判断。现实中专门针对药品检验标准的造假,药监部门依法检验时难以查出,从而出具了合格报告,使假药逃脱监督,使合格报告成为假药的护身符。㉑参见王霞:《王国治:针对药品检验标准的造假行为不容忽视》,载《中国医药导报》2009年3月第6卷第9期,第2页。第二,药品检验指标是依据药品标准的,而标准本身具有局限性,不能穷尽安全指标。2012年毒胶囊事件前,药品检验中的铬含量标准不完善,正如2008年三鹿奶粉事件前奶粉中不存在三聚氰胺的检验标准一样。基于检验效率的考虑,药品标准不需要也无法穷尽所有的有毒有害物质指标,只能关注风险较大的、发生频率比较高的有毒有害物质。第三,药品检验的目的主要不是评价药品的安全性,而是控制药品质量。其重点在于药品是否符合质量检验指标,是否掺杂、掺假;假如现行药品标准有漏洞,检验方法可以改进㉒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第58条:“对有掺杂、掺假嫌疑的药品,在国家药品标准规定的检验方法和检验项目不能检验时,药品检验机构可以补充检验方法和检验项目进行药品检验;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后,使用补充检验方法和检验项目所得出的检验结果,可以作为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认定药品质量的依据。”,关注的也仅仅是药品的制造缺陷而已。
从根本来讲,药品是否具有缺陷,是一项常识性判断而不是技术性判断,需要依赖技术但不是完全信赖技术。药品检验不是也不应成为药品缺陷认定中的唯一手段,否则在药品缺陷认定上,技术判断会取代事实判断。因为,任何司法审判,不论是刑事案件还是侵权案件,技术性要素、科技发展水平都仅仅只是法官审判中的诸多考虑要素之一。技术上无法解决的问题,司法审判中仍然需要给出明确的结论,这需要法官的自由心证和良知,以及对于公平正义和社会公共政策的把握。
三、药品缺陷与药品监管
(一)药品监管无法消灭药品缺陷
我国现行的药品监督管理手段包括药品评价、药品注册、生产经营许可、现场检查、抽查检验、药品认证、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立法等等。在提高药品质量、保证用药安全方面,药品监管功不可没。但是药品监管并不能排除所有的药品缺陷。原因在于:
第一,药品监管的目标是防范风险而不是消灭风险。药品的安全风险是与制药工业的大规模发展密切联系的,药学技术在防范风险的同时也在产生风险。正因为如此,才产生了药品规制或称之为药品监管。药品监管的目标从来不是消灭风险,而是将药品的风险控制在可接受程度范围内,是在用药安全和产业发展之间寻找合适的平衡点。虽然民众对于药品安全事件是“零容忍”,但风险控制的实际效果,不仅与科技水平、人员素质相关,也与一国的政治格局、药品监管体制密不可分。在全球,药品风险是无国界的,但药品安全水平却是不均衡的。
第二,药品审评只是初期的风险评估。风险评估、风险管理、风险交流通常被视为风险分析框架的基本组成。㉓沈岿:《风险评估的行政法治问题——以食品安全监管领域为例》,载《浙江学刊》2011年第3期,第18页。药品上市前的药品审评即风险评估,是药品风险控制的起点。药品审评的内容是药物上市申请中风险-效益比,这非常类似于药品缺陷的判断。但药品审评的结论不能取代药品缺陷的认定。
我国药品审评工作的质量,目前既受到人员严重不足的制约,也受企业研发水平、申报资料规范化程度、医药企业的诚信度、社会公众的文化认知程度等因素的影响。㉔李国庆:《药品审评的改革实践和今后的工作思路》,载《中国食品药品监管》2011年第8期,第21页。即使不受这些因素影响,科学和专家也具有内在局限性,表现在药品审评领域:临床实验病例数少、研究时间短、试验对象范围较窄、用药条件控制较严、研究目的单一㉕主要考察药品的疗效,未列入的试验内容一般不予考虑。,导致发生率较低、潜伏期长、特殊人群的药品风险、药物相互作用等均无法识别。
药品监管是一系列的药品风险管理过程。药品不良反应监测、药品召回、药品上市后的再评价与淘汰、药品注册与许可、行政处罚等,均为药品上市后风险筛查与控制的具体手段。因此,药品审评中的风险-效益权衡仅仅是起点,无法完全消除药品缺陷,不能以药品上市前药监部门药品审评的结论作为药品不具有缺陷的理由。
第三,独立、中立、科学的药品监管机制尚待加强。我国的药品监管机构,经历了转型期的独立规制机构面临的普遍性困境:1998年以前,卫生部主管药品监管;1998年国家药监局成立,为国务院直属机构,逐步建立半垂直管理体系;2008年以后,国家药监局改由卫生部管理,地方政府分级管理;2013年,组建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重归国务院直属机构。而药品监管理念也经历了“监帮促”到“科学监管”的过渡。㉖两种理念的区别,关键在于处理三个关系:政府与企业、监管与服务、商业利益与公众利益的关系,参见《吴仪在全国加强食品药品整治监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07年2月8日,http://www.gov.cn/wszb/zhibo9/content_521888.htm。而郑筱萸案件,凸显出药品监管者存在被被监管者俘获的机会和事实。
就目前的药品规制而言,规制的中立、科学、透明和可问责机制,都有待于继续加强;规制的激励机制不足,使得规制政策执行受阻;规制机构裁量权过大,缺少明确的裁量基准,缺少对规制者权力的制约;未能建立规制影响评估制度,在形成规制决策时,缺少对替代方案的考虑,以及规制风险和收益的评判。㉗宋华琳:《政府规制改革的成因与动力——以晚近中国药品安全规制为中心的观察》,载《管理世界》2008年第8期,第50页。
因此,无论从药品监管的宗旨,还是监管机构的现状来说,药品监管无法防范所有的药品安全风险。即使对于世界药品监管的楷模——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药品零缺陷,也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从本质上来讲,药品缺陷的民事责任主体是药品生产企业,而不是药品监管机构。药品监管后的无法回避的“残余风险”,是各国侵权法和社会保障需要共同解决的问题。但在我国,缺陷药品所致损害往往没有主体承担责任,出现了“有组织的不负责的社会”㉘刘铁光:《风险社会中技术规制基础的范式转换》,载《现代法学》2011年第4期,第70~71页。现象,其原因一方面在于药品不良反应救济制度的缺失,另一方面恐怕在于司法实践中,对于(行政)法律法规、技术标准的过度依赖。㉙参见赵西巨:《论我国立法和司法对法定外在标准的过度依赖——以我国医疗损害责任鉴定与诉讼实践为例》,载《证据科学》2012年第20卷(第3期),第297~312页。文章认为,我国在一些关键性法律问题(如医疗过错)的立法、司法和学术阐释上有一种过于依赖法律法规和行业标准或规范来定夺的倾向;立法将法律法规、行业标准和诊疗规范这些外部标准推到了至尊甚至绝对的地位,而忽略了对相关问题本身及其内在因素的考察;司法者利用来自医疗专家层的鉴定来判案成为我国医疗纠纷中法院和法官的一种保护机制,对外在标准的依赖降低甚至转移了法官裁判的风险。
(二)行政义务无法替代民事义务
药品恐怕是民用产品中行政管制最为严格的一类产品,在药品侵权诉讼中,药品监管与侵权责任往往相互影响。其中,药品生产企业行为合法合规、通过药品注册审批并符合国家标准的事实,似乎是药品侵权诉讼中非常有力的辩解。
药品生产企业完全遵守药事法规,是否不需要承担民事侵权责任?现行《药品管理法》就存在这样的疑问。该法中唯一的民法规范——第93条规定:“药品的生产企业、经营企业、医疗机构违反本法规定,给药品使用者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该条“赔偿责任”无非是产品责任和医疗损害责任两种。按照我国《侵权责任法》,产品责任适用无过错责任,医疗损害责任适用过错责任(过错推定)。但按照该条款,是否可以理解为只考虑当事人是否合法而不考虑过错(或者产品缺陷)?本文认为,这种理解是错误的。行政违法不同于民事违法,行政义务也有别于民事义务。
首先,“违法性”概念在民法和行政法上有差别。在民法上,违法性与过错是相互区别但又纠缠不清的两个概念。严格来说,违法性是德国侵权法独有的概念,有结果不法、行为不法之分,内容包括权利侵害、违反保护他人的法律、违背善良风俗。我国《侵权责任法》作出了以过错吸收违法性的制度选择,没有采纳所谓违法一词。有学者认为:违法性不宜作为独立的责任构成要件;违法行为是严重的过错行为,但过错又不限于违法行为,过错的概念要比违法行为的概念在内涵和外延上更为宽泛,应当采用违反注意义务作为统一的标准来判断过错。㉚王利明:《我国侵权责任法采纳了违法性要件吗?》,载《中外法学》2012年第1期,第5~17页。
在行政法上,违法行为包括行政主体的违法行为和行政相对人的违法行为,此处讨论的主要是行政相对人的违法行为;其违法性并不以过错为要件,判断依据比较明确,就是行政义务。
其次,违反行政义务不等于违反民事义务。药品管理法本质上属于专门行政法,是国家对于药品行政管理的专门立法。药品行政相对人的行政义务按照来源分为两类:药品管理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㉛如《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即GMP)、《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GSP)以及国务院、国家药监局的相关规定。中强制性规范所确立的义务;药品监管机构相关的具体行政行为(如药品注册,生产、经营中的行政许可文件,行政处罚,行政强制以及其他行政决定、命令)确定的具体义务。
侵权法中的一般注意义务是一个基础性的概念。其中的法定注意义务,来源包括法律规范(法律、法规、规章、技术归责和安全标准)、准法律规范(习惯、惯例、常理)㉜廖焕国:《论法定注意义务的成立》,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 6期,第44~50页。。但法定注意义务无法代表所有的民事注意义务。例如基于药品安全的注意义务,药品相关的法律规范和药品标准,原则上仅仅是一种最低的注意标准而非全部。不当行为的认定完全交给立法者并以法不禁止即许可为理念的侵权行为法,无异于以违反人权的方式认可了法律漏洞的存在。㉝[德]冯·巴尔:《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下册 )》,法律出版社 2001年版,第 296~297页。美国药品侵权诉讼的实践表明,大量经过FDA合法注册审批并且检验合格的药品,仍然要面对产品责任诉讼的考验。
药品的民事注意义务和行政义务不同点在于:第一,前者内涵宽泛,基于不伤害他人的原则而生;后者具体而明确,基于服从现行的药品监管秩序。第二,前者带有一定伦理色彩,后者更具有技术特征。第三,前者保护的是个体的用药安全和人身利益,义务标准的设定基于个案的情况考虑;后者保护的是国家的药品管理秩序以及相应的公共整体利益,义务标准设定考虑整体用药安全、行业发展和技术进步。第四,前者往往是药品损害结果发生后,法官裁决中进行的回溯性具体个案判定;后者是药品监管机构对于药品风险的普遍性、全程性管理,重视事前的风险控制。第五,前者着重于纠纷解决、私权救济,违反义务后果主要是赔偿责任;后者着重于加强药品监督管理,保证药品质量,违反义务后果主要是行政处罚而不是损失赔偿。
至于如何确定药品生产企业具体的民事注意义务,这已经超出了笔者的能力范围。㉞产品生产者的民事注意义务与产品缺陷是何种关系,产品缺陷的注意义务是否与过错相关,严格责任在此如何定位,都是值得推敲的问题。可以明确的是,民事注意义务应当由法院基于个案细节合理界定。危险的可预见性、危险的邻近性和政策评价三要素㉟廖焕国:《论一般注意义务的成立》,载《求索》2008年第12期,第128~129页。值得关注。
最后,行政合法与民事合法不能混同。从逻辑学上讲,《药品管理法》第93条并不能推导出“合法免责”的结论,理由与《产品质量法》第46条一样。从命题——“违法,承担赔偿责任”成立,无法推导出否命题——“合法,不承担赔偿责任”。
药品行政义务确立的两大依据,药品强制性规范与具体行政行为,其功能是行政管理而不是民事裁判,无法替代所有民事注意义务。遵守了法定注意义务,并不意味着行为是正当的和可接受的。行政合法条件下遗留的药品安全风险,仍需相对人承担民事责任,而不是药监机构,否则药监机构不得不对所有的药品安全承担不合理的责任。
因此,国家药监局反复强调:食品药品安全,地方各级政府负总责、监管部门各负其责,企业是第一责任人;任何一个产品的质量都不是检查出来的,而是生产出来的。㊱参见人民网前方报道组:《邵明立:企业是药品安全责任体系的第一责任人》,载人民网2008年3月16日,http://npc.people.com.cn/GB/28320/116286/116574/7005284.html,2013年4月6日访问。同样的说法见于《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药品安全监管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07]18号)。针对药品安全事件中“监管不力”的指责,“企业是第一责任人”也包含了一种提醒。国家药监局的相关部门规章也明确了行政义务不同于民事义务、行政责任不能代替民事责任:(1)2006年国家药监局发布的《药品说明书和标签管理规定》第14条规定:“药品生产企业未根据药品上市后的安全性、有效性情况及时修改说明书或者未将药品不良反应在说明书中充分说明的,由此引起的不良后果由该生产企业承担。”虽然药品说明书和标签是国家药监局核准后合法使用的,但企业仍然需要不断承担注意义务。(2)2007年《药品召回管理办法》第29条规定:“药品生产企业召回药品的,不免除其依法应当承担的其他法律责任。”这里的法律责任,其实就是缺陷药品的侵权责任。
是否符合药品法律法规、药品标准,是药品缺陷判断的相关性证据,但不是决定性的证据。如果认可了“行政合法——民事免责”,将会导致行政义务取代民事义务,违法认定取代缺陷认定,药品规制取代侵权裁判。产品缺陷认定根本上是民法的问题,是法官的权力,药品的特殊性并不能改变这一点。药品的行政监管、药品的技术标准、检验报告,是认定药品缺陷的证据而不是全部。司法作为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对于生产者是否履行了民法安全注意义务,才是最具有发言权的。不需要担忧药品侵权完全演化成为结果责任。毕竟,科技水平抗辩、因果关系证明等,都是药品侵权责任成立的不利条件。
至于药品缺陷的认定方法与标准,大量的美国药品责任判例,美国《侵权法重述》中的专门论述㊲详见美国《侵权法重述(第二版)》402A评注项k、《侵权法重述(第三版):产品责任》§6。,各国产品责任理论中的判断标准,提供了丰富的法律资源;而我国药品审评、药品再评价以及药品召回的实践经验和研究成果,则提供了大量的技术支持,在此本文不作详细论述。
四、结语
这些长期以来困扰药品责任的关键问题,也不仅仅存在于药品领域,具有政府管制色彩的其他产品领域,如医疗器械、食品、化妆品,同样存在。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产品缺陷并不是产品的质量问题,而是安全性问题;强制性标准仅仅是产品安全性的最低要求;行政义务并不能替代生产者的全部安全注意义务。
民法中的转介条款,其实也是本文触及到而未来得及深入的另一个问题。药品产品责任中不可避免要引入药品行政法律渊源,但行政法仅仅是处理药品责任问题的工具。法院在民事审判中不能无视行政行为的存在,不能完全否定行政行为的拘束力,不能总是抛开行政行为而直接对相关的争议作出裁判;但这种拘束力不是绝对的、单一的、“自我确认”的,而是相对的、多样的、情境性的。㊳何海波:《行政行为对民事审判的拘束力》,载《中国法学》2008年第2期,第112页。产品责任诉讼中,行政法资源的引用,固然可以减轻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和降低法官的裁判风险,但对于行政法资源的过度依赖和盲从也是需要警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