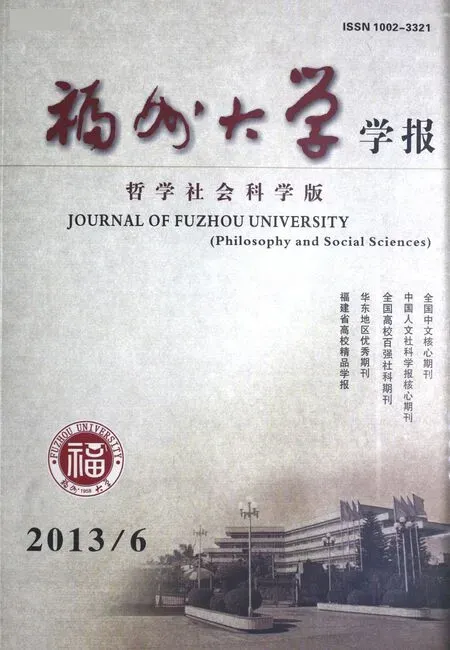六朝时期东南地区族群关系综说
2013-04-18林校生
林校生
(宁德师范学院经济管理系,福建宁德 352100)
六朝时期东南地区族群关系综说
林校生
(宁德师范学院经济管理系,福建宁德 352100)
受地形地貌大势和中古气候变迁的影响,六朝成为中国历史上继秦朝之后又一个大移民时代。秦朝大移民主要指其规模大(数量、距离),“政府操作”刚性大;六朝大移民的特点则是时间延续性长,对政治体制和族群关系影响巨大而深远。就东南族群关系而言,当时南渡、土著人口的“蛮化”和南方蛮族、“蛮区”的汉化两种倾向相互纠叠,闽中地区则直到隋唐时期非汉族群的势力依然十分强大。研究这一时期东南地区包括闽中一带的历史,对此亟当给予应有的关注。
东南地区;闽中;非汉族群
六朝时期中国北方、南方的少数民族构成都相当复杂,姑且以“胡”“蛮”分别作为北方和南方少数民族的总称。本文试图综合各家新锐之见,以南、北中国胡、汉、蛮交错下的总体族群形态为背景,讨论这个时期东南地区的族群关系和族群结构,又以东南族群形态为参照,粗窥六朝隋唐闽中族群拼图的初步轮廓,蒐求不免浮光掠影,引述不免断章取义,间夹己见,亦未必有当。统祈读者雅正。
一、“胡人汉化倾向”和“汉地胡化倾向”
关于三至六世纪中国历史有种种解释范式,这里只说韩国朴汉济的侨民体制论,它包括当时北方的“胡汉体制”和南方的“侨旧体制”。所谓胡汉体制,乃指“并存在同一地区和统治体制下的胡汉两个民族,在形成统一文化体制过程中的互相冲突、反目和融合,即以胡汉问题为基轴的一切社会现象”;也就是说,“胡汉关系是构成这一时代的基本骨架。”所谓侨旧体制,乃指“东晋、南朝时代南方的北来侨民成了主导历史的势力”。[1]朴汉济认为,“特别应该强调的是,南北方人口所具有的移(住)民独特的性格,‘背井离乡之人’所具有的独特的情感引发的团结力,是使他们能够主导南·北朝社会的最大的动力。这样,从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历史由脱离故乡人即‘侨民’所主导的这一事实,就可以在整体上充分掌握和理解南·北朝历史的框架,进而将五胡·北朝的‘胡汉体制’与东晋、南朝的‘侨旧体制’统一起来,并将这个时代以‘侨民体制’名称重新组合。”[2]
这种说法在中国大陆学界颇得呼应。例如,胡阿祥便很赞同朴汉济的主张:“错综复杂的东晋十六国南北朝史,其关键线索,在北方为胡汉问题,在南方为侨旧问题。所谓‘胡’,乃三国西晋时代不断内徙及十六国北朝时代先后入主中原的非汉民族,所谓‘汉’,即十六国北朝时代北方之汉族士民;又所谓‘侨’,主要指西晋永嘉乱后不断南徙的北方官民,所谓‘旧’,主要指南方土著。胡汉之间、侨旧之间既颇多矛盾,又有各种形式的合作。胡汉之间因有矛盾,引起了大量北方人口的侨流南方,侨旧之间因有矛盾,促成了东晋南朝侨州郡县的大量设置;胡汉之间、侨旧之间又有合作,从而十六国北朝得以立国于北方,东晋南朝得以立国于南方。”[3]上述引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朴汉济“胡汉、侨旧体制”论的一个很精到的概括。
对当时的北中国的民族纷扰,一般描述为:胡族内迁,胡汉杂居,主流是汉化,支流是胡族保留部分传统特征,汉族也受其若干影响,有时出现胡化现象。现在看来,这样的描述,诚如朴汉济、川本芳昭所指出的,对胡族历史表现的地位和影响估价很不充分。笔者在“胡人汉化”后面加了“倾向”二字,并以“汉地胡化倾向”说明历史同一进程的另一面相。
所谓胡人汉化倾向,在政治上的一个突出表现是“五胡各族建立的王朝都追溯王室的渊源,例如,慕容氏自称为黄帝有熊氏,姚氏自称为帝尧有虞氏等。北魏为了教育鲜卑族,编撰了以构成汉族文化核心的孝道为内容的《国语孝经》;有些非汉族的统治者到了东晋时代仍持有晋朝臣下的观念,这些非汉族并不认为自己与汉族的世界观有矛盾,这是值得注意的现象”[4]。它在社会生活上最重要影响的最深远的表现,当然是胡汉通婚。由此也会引出制度上的一系列变化。
所谓汉地胡化倾向,则是中原地区在五胡成为支配民族的形势下,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必然普遍受到胡风的浸染。
北方族群关系情况不是本文讨论的对象,这里只是作为东南地区族群关系的背景而简略述及。
二、南渡、土著人口的“蛮化”和南方蛮族、“蛮区”的汉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南方的“蛮化”现象,特别是这种“蛮化”在历史长段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在川本芳昭之前,似乎不见明言(类似的意思也有一些)。川本芳昭强调“一个与秦汉时代完全不同的崭新的‘中华’世界就是在当时这种胡化、蛮化和汉化同时进行的过程中形成的”。他把胡、汉、蛮作为三大对等的族群力量来考虑,恐怕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回答,但已经给笔者很大启发。
《魏书》卷九六《僭晋司马睿传》对南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现状有一个有所隔膜而又不失真实的概述:
春秋时为吴越之地。吴越僭号称王,僻远一隅,不闻华士。……晚与中国交通。俗气轻急,不识礼教,……地远恃险,世乱则先叛,世治则后服。秦末,项羽起江南,故衡山王吴芮从百越之兵,越王无诸身率闽中之众以从,灭秦。汉初,封芮为长沙王,无诸为闽越王,又封吴王濞于朱方。逆乱相寻,亟见夷灭。汉末大乱,孙权遂与刘备分据吴蜀。权阻长江,殆天地所以限内外也。叡因扰乱,跨而有之。中原冠带呼江东之人,皆为貉子,若狐貉类云。巴、蜀、蛮、獠、溪、俚、楚、越,鸟声禽呼,言语不同,猴蛇鱼鳖,嗜欲皆异。江山辽阔将数千里,叡羁縻而已,未能制服其民。
这里给我们特别震撼的印象,当时的南方其实是一片广大的蛮夷之地。所以,周一良作《南朝境内的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陈寅恪作《<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唐长孺作《孙吴建国及汉末江南的宗部与山越》,三位魏晋南北朝史的大家对此都很关注。[5]
这从孙吴进入江东必须长期的、大规模的攻打山越以掳获兵员和劳动力,从西晋末賨人李特领导四川巴氐人为主的民变,蛮酋张昌领导荆楚地区各族反晋,已可一斑窥豹。至于南方少数族群的人口数量,史无明言,各家提供的数字,从白翠琴估为一百万以上,到张泽洪估为八百万以上,相差巨大,都是种种推测。[6]据朱大渭估算,南方主要的三大支少数族(蛮、僚、俚)人口可占国家掌握总人口的一半以上。鲁西奇也说:“南北朝时期,长江中游及其周围地区的蛮民户口数,当远远超越同一地区著籍的华夏户口数。”[7]种种数据都可供参考,有一点差可达成共识:六朝时期土著族群分布很广,许多地方汉族人倒是少数,面临这样的族群格局,当时的“少数族”固然在“汉化”,而相当一部分很早就从北方迁来的汉族人口,在蛮夷包围下的“在地化”过程中,“化人”的同时也在“被化”,所以“中原冠带呼江东之人皆为貉子”。对于福建来说,就是同时存在“山越化(闽越化)”和“汉化”两种趋势的交叠。
面临这样的族群格局,相当一部分很早就从北方迁来的汉族人口,在蛮夷包围下的“在地化”过程中,能“化人”者少,而“被化”者多,所以“中原冠带呼江东之人皆为貉子”。
又,《宋书》卷九七《夷蛮传》载:
荆、雍州蛮,盘瓠之后也。分建种落,布在诸郡县。荆州置南蛮、雍州置宁蛮校尉以领之。世祖初,罢南蛮并大府,而宁蛮如故。蛮之顺附者,一户输谷数斛,其余无杂调。而宋民赋役严苦,贫者不复堪命,多逃亡入蛮。蛮无缓役,强者又不供官税,结党连郡,动有数百千人,州郡力弱,则起为盗贼,种类稍多,户口不可知也。
这也是“蛮化”的一种类型。
“这一时期的蛮酋大体有两类:出自汉人而统领蛮民的蛮酋和出自蛮人的蛮酋。”刘宋时期有司马黑石、夏侯方进成为西阳五水蛮的酋领,还有庞孟虬逃入义阳蛮中,司马楚之逃入竟陵蛮中,等等。[8]形势变化了,蛮酋也可能踏上归附的道路,于是有左郡、左县的设立。按照当时通例,左郡、左县的守令都以蛮族首领充当。这是南方蛮夷势力强盛对行政体制的影响。
以上所述,从另一方面看,又包括了南方蛮族、“蛮区”汉化的内容。
三、南方的侨、旧问题
异民族对所征服地区的治理,必然发生诸多新旧人口间的冲突和妥协。实际上这种情形也会发生在同一民族内部。这里的侨旧问题,便主要是指汉族内部的南北、主客间的对峙、隔阂、紧张、适应和归合。
1.蜀汉的主、客纠葛
《资治通鉴》卷六七建安十九年载:
诸葛亮佐备治蜀,颇尚严峻,人多怨叹者。法正谓亮曰:“昔高祖入关,约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据一州,初有其国,未垂惠抚;且客、主之义,宜相降下,愿缓刑驰禁以慰其望。”
胡三省注:
以亮等初至为客,益州人士则主也。
法正劝谏诸葛亮的话,涉及蜀汉史中的一个重要症结。王仲荦认为蜀汉政权是由三股政治势力组成的,即益州土著地主集团、刘焉刘璋父子为首的、以东州兵为主要武装力量的外来地主集团和刘备为首的以“京曹群士”为主的外来集团。这三股政治力量形成错综复杂的主客新旧矛盾。[9]田余庆认为,蜀汉政权中新与旧、客与主的分野主要是刘备和刘璋两个营垒。“其时蜀国臣僚中的政治纠纷是由‘新旧’、‘客主’分野之势演化而成。‘旧’和‘主’,指刘璋部属;‘新’和‘客’,指刘备由荆入蜀所领人物。刘备占领成都,喧宾夺主,主客地位颠倒,蜀史中一大公案,由此产生。……刘备死后,诸葛亮用以治蜀的臣僚,主要是分化刘璋旧属,或吸收,或排抑,使随刘备入蜀居于少数地位的人,同刘璋旧属居于多数地位的人,即所谓新旧两方,逐渐熔融而成。……(直到)李严废徙,这一新旧冲突过程始告结束。”
田余庆进而指出,蜀汉史中还有一些表面看不明白的孤立事件,也可以从上述客主新旧关系中求得解释。例如,建安二十四年群下推举刘备为汉中王的《上汉帝表》(李朝),结尾署名次序,以马超冠首,许靖、庞羲、射援都列名诸葛亮之前。这是由于“刘备以宾客之分而得益州,地盘、营垒骤然扩大,但是作为核心、作为基干的刘备嫡属,尚不足以稳居主导,控制局面。”[10]
田余庆强调巩固新人地位,协调新旧关系,是诸葛亮用人的核心问题,其实,不同时代、不同地区只要发生外来人治理,就几乎都要碰到类似的棘手事。孙吴长期、艰难的建国历程,也充满了不同地域势力先来后到间的冲突和磨合。
2.孙吴的南、北代易
《吴志·孙权传》载其即位时的形势:
是时惟有会稽、吴郡、丹杨、豫章、庐陵,然深险之地犹未尽从,而天下英豪布在州郡;宾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为意,未有君臣之固。
这里的“英豪”,指的是“布在”江东各个州郡有名望、有实力的文武世家,是民间社会力量的代表;“宾旅寄寓之士”,指江东全部的北来流寓之士,其中当包括随孙氏渡江的已有君臣之结的淮、泗武人集团,所谓“以安危去就为意,未有君臣之固”者,则主要是孙氏幕下、幕外的北来文士。主、客两种势力之间必有利益冲突,但孙吴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又必须以他们的一定程度上的合作为基础。从纵向发展的角度来观察,前一时期自是由北来的势力在主导,随着时间推移,流寓人物日渐凋零,本土势力的作用越来越强,越来越成为主角,这便是学界习称的孙吴政权江东化。魏蜀吴三国中,孙氏从攻占吴、会到正式称帝迁延时日最长,田余庆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它与江东诸大族关系需要一个比较长的调整过程。[11]江南地区的世家大族根基深厚,力量强盛,本当成为孙吴建国的主要柱石;而孙氏出自富春的寒门,“孤微发迹”,又是袁术的部曲,双方关系却甚是紧张。孙策经营扬州,最早靠的是从袁术要来的孙坚余部“淮、泗之众”,这自然引起江东大族的抵制。他们一时成为孙策经略江东的主要敌手,于是有“孙策平定吴会,诛其英豪”(《吴志· 孙韶传》注引《会稽典录》),直到孙权继位的前数年,余波犹在。
高敏肯定田余庆《孙吴建国的道路》一文“甚具说服力”,又补充论证了田文“未予以充分注意”的“北方地主集团与江东地主集团之间的矛盾斗争”问题,指出:
因为孙坚、孙策系依靠淮、泗武人集团而起家,又得力于北方流寓士人地主参谋献策。故孙权统事之初,军政大权几乎完全掌握于淮、泗武人集团及北方流寓士人地主集团之手。在孙权平定山越和拓土开疆的过程中,孙氏宗亲逐步成了世袭领郡与世袭领兵的世官、世将集团,而且大都享有奉邑、封爵和自置长吏的特权,由于两个集团之间不断存在着矛盾斗争,迫使孙权不得不依违于两个集团之间,从而初步形成了与北方地主集团平分秋色的局面。直到建安末年淮、泗武人集团的一些代表人物如周瑜、程普、吕蒙、鲁肃等人才先后去世,这就决定了在建安年间孙权既无法完全任用江东地主,也规定了他无法彻底摆脱淮、泗武人集团及北方流寓地主的影响。因而在黄武年间,仍需要用北海人孙邵为丞相。直到孙邵死后,他才有可能用顾雍为丞相,完成用人江东化的过程。故孙吴政权割据最早而称帝最晚,应当说同他需要较多时间以缓解北方流寓地主集团同江东地主集团之间的矛盾斗争有一定关系。[12]
高文对于我们更全面地了解孙吴政权存续过程中外来势力与地方实力派的矛盾关系及消长过程是有帮助的。
3.东晋的新、旧冲突
江东士族对司马睿政权的态度,初时颇为抵触。西晋平吴后,江南叛乱屡起。《晋书》卷五二《华谭传》载晋武帝曾问广陵人华谭说:“吴蜀恃险,今既荡平。蜀人服化,无携贰之心;而吴人趑睢,屡作妖寇。岂蜀人敦朴,易可化诱;吴人轻锐,难安易动乎?”华谭在答话中也有“殊俗远境,风土不同,吴阻长江,旧俗轻悍”的说法。《晋书》卷八六《王导传》载:“会帝(司马睿)出镇下邳,请导为安东司马。军谋密策,知无不为。及徙镇建邺,吴人不附。居月余,士庶莫有至者,导患之。”
有鉴于此,王导为政实行了“以清静为政,抚绥新旧”的指导方针。《资治通鉴》卷八六晋怀帝永嘉元年载:“王导说睿:‘谦以接士,俭以足用,以清静为政,抚绥新旧。’”胡三省注:“新,谓中原来者;旧,谓江东人。”这一政治方针取得了显著的效果,陈寅恪《述王导之功业》有很深入的分析,此不复赘。总的说来,朝廷对北方移民优惠颇多,时间长了,对南方人口的生产、生活有负面冲击,对国家财税也有消极影响,于是便有从侨置到土断的政策调整。[13]
这种土著者与外来者的冲突,特别是土著菁英与外来权贵在仕途上的冲突,直到南朝犹余响不绝,《南齐书·文学传·丘灵鞠》便是史家反复引用的生动例子。
相对而言,关于汉族的历史记载远比少数民族丰富得多,六朝汉族土客之争的文献材料对我们了解和认识当时非汉族群之间以及汉族与非汉族群之间多种面相的复杂关系提供了很好的参照。
四、六朝隋唐时期闽中族群关系粗估
今人对古代闽中居民的族群性质的理解,可说是两端比较一致:西汉以前,这里是非汉族群(闽族、越族、闽越族或南岛语族)的世界,宋代以还则已成为汉族人绝对主导的的世界。但对这两端之间的族群结构情况的判断,则分歧甚大。《史记·东越传》载:西汉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平定闽越国东越王余善之乱,“於是天子曰:东越狭多阻,闽越悍,数反覆,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间,东越地遂虚。”(《汉书·闽粤传》同)不少学者以此相信汉武帝已将当地百姓全部迁至江淮之间,使那里成为一片“无人区”。笔者以为,结合当时国家动员能力和福建地理条件两方面来考虑,这是根本做不到的。例如,东汉末,中原士族许靖避乱会稽,孙策渡江,他从会稽逃难,说自己是“浮涉沧海,南至交州。经历东瓯、闽、越之国,行经万里,不见汉地”。[14]所以,孙吴确立对闽中的统治,“福建的民族结构已以汉族为主了”[15]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六朝闽中的族群结构,和整个中国南方的族群结构紧密相关。
仿照周一良、吕春盛的划分办法,[16]六朝时期福建或福州地区的居民也可以分成三大类别。一类是西晋永嘉之乱以后迁来的侨人,但没有什么士族大姓。再一类是吴人,他们有的是从周边浙、赣等地迁入的,有的是已经相当汉化的土著。这两类,人数都不多,政治影响也小。第三类为非汉族土著,是闽中的基本居民,依时间推移,其族群特色又有一些不同的表现。以下略分三个阶段简单介绍。
孙吴时期,闽江流域也山越广布。《三国志》卷六十《吴书·贺齐传》载:
侯官既平。而建安、汉兴、南平复乱,(贺)齐进兵建安,立都尉府,是岁(建安)八年也。郡发属县五千兵,各使本县长将之,皆受齐节度。贼洪明、洪进、苑御、吴免、华当等五人,率各万户,连屯汉兴,吴五六千户别屯大潭,邹临六千户别屯盖竹,同出馀汗(笔者按:汗当作干)。……(贺齐连大破之),凡讨治斩首六千级,名帅尽擒。复立县邑,料出兵万人,拜为平东校尉。
《贺齐传》记事可能存在夸饰,但即使缩水一半,三县山越反抗力量也有三万户以上。孙吴要在江东立稳脚跟必须长期地、大规模地攻打山越以掳获兵员和劳动力,其时对山越的处置严重关乎国家政权的安危,不必多说。
晋宋之交,卢循所部基本上都属东南沿海的少数族群,史家记录了其中两支族群的信息。《资治通鉴》卷一一五晋义熙六年(410)载何无忌参军殷阐语:“(卢)循所将之众皆三吴旧贼,百战馀勇,始兴溪子,拳捷善斗,未易轻也。”始兴郡治在今广东韶关,溪子是对溪族的鄙称,溪作为族称也写作“谿”“傒”“奚”。溪族大多以渔猎为业,陈寅恪认为实际上就是《后汉书·南蛮传》中的盘瓠种蛮。现在学界多将盘瓠蛮指为畲族先民的一支。
溪族之外,还有蛮蜑。《三山志》卷六载,福鼎桐山、沙埕港有白水江,并引《太平寰宇记》卷一〇二记载,“白水郎,夷户也,亦曰游艇子,或曰卢循余种”。他们“举家聚止于一舟,寒暑食饮疾病婚娶未始去”。今天福鼎沙埕港、霞浦三沙湾和蕉城三都澳一带的群众中,还流传着“白水郎”的故事。明末清初的顾祖禹也说到:“今泉州夷户有曰泉郎者,亦曰游艇子,厥类甚繁,其居止常在船上。船之式,头尾尖高,中平阔,冲波逆浪,都无畏惧,名曰了鸟船。”福州疍民来源纷杂,其中也有卢循残部下江海而入蛋(疍)家者。今长乐县筹东村的卢姓疍民便归宗于卢循。
梁陈之交,江左社会激烈动荡,大量原来不得居于社会上层更无缘预闻国家大政的岩穴村屯之豪乘势竞起。据查考,他们大抵都是非汉族土著。[17]一度雄霸晋、建二郡的陈宝应也不例外。《陈书》本传称“陈宝应,晋安侯官人也。世为闽中四姓”。又引朝廷讨伐的“尚书符”说:“案闽寇陈宝应父子,卉服支孽,本迷爱敬。梁季丧乱,闽隅阻绝,父既豪侠,扇动蛮陬,椎髻箕坐,自为渠帅,无闻训义。”这里的“卉服”,是用絺葛做的衣服,《尚书·禹贡》、《汉书·地理志上》都有“岛夷卉服”的记载,所以一般用以借指边远地区的或岛居的少数族群。再叠用“蛮陬”、“椎髻箕坐”、“渠帅”乃至“无闻训义”,也都是强调其作为少数族群在地理区位、生活习俗、首领称谓和文化教育等方面的特征。虽然陈霸先曾经一度接纳陈宝应为宗室成员,但这是一种政治行为,在姓氏源流上则做不得真。况且,陈霸先本人家世也有造假之重大嫌疑,《南史·陈高祖本纪》说他“其本甚微,自云汉太丘长寔之后也”。甚至有学者从其好武、业渔、信奉天师道而推测他出自溪族。[18]
应当补充说明的是,对六朝时期闽中族群结构的这种认识,可以得到唐代 以还福建族群状况一些散见文献资料和学者相关研究的佐证。
福建唐代的实际族群状况和学界的研究推断,问题比较复杂,这里只能简单介绍笔者关注到的几家学术观点。
1.川本芳昭引用《元和郡县志》卷二九“江南道福建观察使·福州尤溪县、古田县、永泰县”条记载,认为福州辖下尤溪县、古田县、永泰县到开元年间还有非汉族群聚居的“洞”存在,这些县皆“开山洞置”;引用《重纂福建通志》卷二三“坛庙·漳州府·漳浦县”和《舆地纪胜》卷一三一“福建路漳州·官吏·陈元光”条的记载,考察唐代新设漳州地区的情况,认为史料反映了唐代福建南部的“开拓”历史,表明该地直至唐代仍保留浓重的蛮地特色;引用《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九“江南道福建观察使·汀州”关于开光龙洞而新设汀州的记载,考察黄连洞的蛮族,指出唐代闽西的情况与前闽南漳州的情况相似。[19]
2.谢重光著文节引康熙版《漳浦县志》关于陈元光把漳州作为自己世袭领地的记载,又引《新唐书·地理志七》概括羁縻州的若干特点,指出当时的漳州地区是刚刚归附朝廷的蛮夷之区,陈元光又是土著首领身份(谢重光有多篇文章讨论陈元光的身份),自武则天垂拱二年(686)到唐德宗贞元(785—805)初的一个世纪中,州政一直掌握在陈氏家族手上,陈元光、陈珦、陈酆、陈谟四代相继任漳州刺史,这种情势皆与羁縻州的制度相合。[20]
3.佐竹靖彦在川本芳昭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考察研究,从政区设置动因切入,对唐宋时代福建地区的激烈变化提出如下论断:
从福建新县与旧县的设置情况来看,支撑福建东南部汉族居住地的形成和发展的,是通过海上交通与浙东、广东等地的连接;而支撑西北部汉族居住地的形成与发展的,是与江西地区的连接。也就是说,汉族的移居是以通过海上交通连接浙江东南部边境的福州,以及通过陆路连接江西东部边境的建州为中心展开的,随着唐朝中期不少新县的设置,至此为止各自在西北部和东南部分别居住的汉族地域连成一片,西北部的山岳地带出现了汀州,由于汀州与漳州相连,形成了汉族居住圈将原住民居住地包围在内的格局。亦即可以说在唐朝中期,福建基本上完成了汉族进出据点的设立。唐开元时期的新县,是为了把剩下来的原住民居住地区包围起来而设置。此后,从唐中期到唐末,汉族迁入后分布在从建州经由古田县到福州的交通线上,以及从建宁到宁化之间,当时被称为黄连洞的广大少数民族居住地区。该地区的北半部大致在唐末汉化,和原住民对峙的前沿地带移至宁化南部的潭飞礤。……另一方面,五代宋初的新县,围绕建州、福州、泉州周围而设置,而且全部都是由镇、场升格而成,与区域商品流通有着密切的关系而获得发展,终于迎来了宋代福建地区科举及第者占绝对多数的福建社会成熟时期,而支撑民众日常生活的商业流通网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1]
这个结论,有力地印证了六朝时期广大东南地区尤其是闽中一带基本上只能是蛮夷之土。而人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误判实亦迁延久远,何以致此,尚可继续推究。
五、余话:研究视角的变换
在吸纳彭兆荣、鲁西奇等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2012年陈支平写了多篇文章论及东南社会的族群结构问题,它们的一个共同的致思取向,即警觉到“由于受到百余年来西方文化导向以及国内外政治因素的影响,中国南方民族史研究形成了一系列的思维惯性,这种思维惯性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中国南方民族史的原有形态”。他指出:
北方汉民族的南迁,一方面给东南地区带来了先进的社会形态与生产方式,促进了南方地区的开发;另一方面,也在这一代代的汉民后裔的文化意识中,积累了向往北方汉民族核心的牢固意识。再加上长期以来北方南迁汉民在东南地区的繁衍生息、兴衰存亡的艰难历程,促使这里的汉民形成了攀附中原世家望族的社会风气。于是,向往中原核心的文化边缘心态便在东南地区的汉民族意识中世代相传、牢不可破。[22]
随着北方南迁的汉民在东南地区迅速蔓延并且取得主控权之后,残留在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如畲族、疍民,以及唐宋以后从波斯海地区东来的阿拉伯人的后裔,逐渐受到汉民的影响以及其生活环境的需求,也不得不把自己的祖先,攀附在中原汉民的世家望族之上。[23]
在族群认同上,陈支平举了疍民的例子。千余年来疍民都生活在江湖漂泊的木船上,与一般的汉民及其他族群的生活方式有着显著的不同,但因他们曾经被视为“贱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国家民委开展民族识别的时候,他们一致请愿声称自己是汉族,千万不要把他们当做少数民族。时至今日,这支货真价实的东南土著少数民族,从浙江沿海南下福建闽江、九龙江及其沿海,一直到珠江三角洲流域,已经消失在汉族的大众之中。另外,我们知道,这方面畲族祖先传说也有很典型的表现。
考察中国南方的语言问题,也会遭遇类似的情形。以前往往片面强调闽方言是中原古音的活化石,但实际上南方汉语的形成既非完全土生土长,也非完全由北方迁入,而是一个多元结构。邓晓华追溯中古时期南方语言的建构变迁,指出:
先汉以前(即秦汉以前),南方与北方,南方各区系之间的语言文化交融已很频繁,例如闽越、吴越与楚关系密切,反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特点。秦汉时期,随着汉人中央政权的确立,南北关系实质上表现为一种“中心—边缘”、“华夏—蛮夷”、“中央—边陲”的关系。此时的南方土著更多的是在文化和政权上认同北方,随着六朝、唐宋时期大量的北方移民迁移南方,南方民族成分结构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大量南方土著变成南方汉人。但这并非意味北方汉语消灭或同化了南方土著语言,而是南北族群经过长期的语言文化的互动过程,从而形成独具特色的古南方汉语。[24]
最近邓晓华与台湾学者王士元合著的《中国的语言及方言的分类》第五章“闽、客方言的发生学关系以及历史层次问题”作出五点结论,有比较全面的说明:
例如,“闽客语都有一批最常用口语词与南方土著民族语包括南岛、南亚、苗瑶、壮(僮)侗语同源,这批词汇是闽客语不同于其他方言的基础。”
又如,“从空间层次看,闽语的南岛语成分多,客语的南岛语成分少;闽语中的苗瑶语成分应是来自客、畲语。”
又如,“闽语中的吴语成分并非都是‘中原汉人南迁路经吴地杂染吴音,后带入闽语’,闽吴互动自周代即始,由来久矣。”
又如,他们通过比较斯瓦迪士的前100词表和后100词表,指出“闽客语的语言性质确为汉语无疑,但是在闽客语的整个形成过程中,与非汉语发生极其密切的互动关系,闽客语的非汉语成分应该得到正确地对待和描述。……闽、客方言的形成是不同时期的北方移民语言与土著居民语言长期‘交互作用’的结果。……闽语实际上是一种古汉越语混合‘方言’。客话音韵系统来自宋代北方汉语,而口语系统的词汇则是汉语和苗瑶壮侗语混合的。”
因此,“使用人类学的族群互动和文化交互作用圈的理论可以正确解读闽客语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混合特性”。[25]
语言学家的这个论断,对我们把握古代福建真实的族群格局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前文所引各家的具体案断,未必都确凿不可移易,但就福建历史而言,学界以往对于中原“规模移民”的规模和开始时间,对于中原文明较之南方本土文明的先进性,对于北方农耕文化(亦即南迁移民的原乡文化)包括儒家文化、宗族文化的影响,往往估计过高,而对于闽地本土文化的发展水平、历史表现、现今遗存、转换形态和实际影响,则多有忽略之处,这实在值得我们深长思之。
当然,以上所述六朝(乃至隋唐)时期的族群分别是相对的,我们判断一个或一群人属于非汉族土著,并不意味着他或他们身上就完全没有受汉族影响的文化印记;同样的,这里的汉族其实也是在迁入地广受周遭异族群的渗入和影响而不断变化的巨大族群体,实际上已成为与汉代迥然有异的“新汉族”。这个认识应当贯穿到我们对整个历史时期南方包括闽中族群状况的判别。
注释:
[1]朴汉济:《北魏王权与胡汉体制》,《中国史研究的成果与展望》,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88页;《“侨旧体制”的展开与东晋南朝史》,《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1-39页。
[2]朴汉济:《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而提出的一个方法》,《中国前近代史理论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57页。
[3]胡阿祥:《魏晋南北朝史十五讲》引言,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年,第3页。
[4]川本芳昭:《论汉唐时期以中国为中心的“交流与变迁”》,复旦史学集刊第一辑《古代中国:传统与变革》,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4-35页。
[5]周一良:《南朝境内的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七本第四分,1938年;陈寅恪:《<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二本第一分,1944年;唐长孺:《孙吴建国及汉末江南的宗部与山越》,《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上海:三联书店,1955年。按,据唐书后的跋语,其文也原是“解放前的旧作”。
[6]参见白翠琴:《论魏晋南北朝民族融合对汉族发展的影响》,《民族研究》1990年第3期;张泽洪:《魏晋南朝蛮、僚俚族对南方经济发展的影响》,《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
[7]见朱大渭:《南朝少数民族概况及其与汉族的融合》,《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1期;鲁西奇:《释“蛮”》,《文史》2008年第3辑,第67页。
[8]谷口房男:《南北朝时期的蛮酋》,谷川道雄主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学的基本问题》,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
[9]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78-84页。
[10]田余庆:《蜀史四题》,《文史》第35辑,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
[11]见田余庆:《孙吴建国的道路》,《历史研究》1992年第1期;《暨艳案及相关问题》,《中国文化》1991年第4期。
[12]高敏:《试论孙吴建国过程中北方地主集团与江东地主集团之间的矛盾斗争》,《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4年第1期。
[13]侨置,我国古代政权在战争状态下,政府为招徕移民,仍用其旧名为其设置州、郡、县。东晋时期,北方大片沦陷,南方大量设置侨郡侨县,一直延续到南北朝。土断,主要是东晋、南朝整理户籍及调整地方行政区划的政策。其主要精神是整理(省并、改属、割实)侨郡、侨县,将大量的流移与侨寓人口,在所居郡县编入正式户籍;其原籍北方的侨流大部分注籍侨州郡县,成为白籍户,享受优复待遇;另有一些“无贯之人,不乐州县编户者,谓之浮浪人,乐输亦无定数,任量,惟所输终优于正课焉”(《隋书·食货志》)。
[14]《三国志》卷三八《蜀书·许靖传》,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第964页。
[15]见黄公勉:《福建历史经济地理通论》第二章“历史人口”,福州: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年,第49页。黄氏并且认为“这是福建历史上民族结构变化的一个重大问题”。
[16]周一良《南朝境内的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最早提出南朝境内侨人、吴人、南方土著三分法,但对三种人的界定尚不尽妥帖,吕春盛对此略有补正,见《陈朝的政治结构与族群问题》第一章导论,台北:稻乡出版社,2001年,第7-10页。
[17]见陈寅恪:《<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金明馆丛稿初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113-119页;吕春盛:《陈朝的政治结构与族群问题》第四章第一节,台北:稻乡出版社,2001年,第121-130页。
[18]见朱大渭:《梁末陈初少数民族酋帅和庶民阶层的兴起》,《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346-347页。
[19]前揭复旦史学集刊第一辑《古代中国:传统与变革》第39-40页。详见川本芳昭:《六朝时期以蛮族问题为中心的各地状况》,《史渊》第132辑,1993年,第83~88页;《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民族问题》,汲古书院,1998年版,第505-511页。
[20]谢重光:《漳州初建时期实行羁縻州制说》,《陈元光与漳州早期开发史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第119-139页。
[21]佐竹靖彦:《唐宋时期福建的家族与社会——山洞与洞蛮》,东京都立大学《人文学报》227期历史学编,1997年。转引自前揭复旦史学集刊第一辑《古代中国:传统与变革》第40-41页。
[22]陈支平:《从历史向文化的演进:闽台家族溯源与中原意识》,《河北学刊》2012年第1期。
[23]陈支平:《回归学术主体性:东南民族研究的三个省思》,《思想战线》2012年第1期。
[24]参见邓晓华:《南方民族语言的起源与形成》,陈支平、邓晓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南方民族的起源与形成》最终成果下编,未刊稿,转引自陈支平:《中国南方民族史研究的逆向思考》,《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25]邓晓华、王士元:《中国的语言及方言的分类》,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40-141页。
[责任编辑:余 言]
本刊声明
为扩大本刊及作者知识信息交流渠道,加强知识信息推广力度,本刊已许可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在CNKI中国知网及其系列数据库产品中,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同时本刊已入编“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等数据库。凡在本刊发表的论文都将自动进入以上电子出版系统,本刊同时获得所刊发论文的电子版本和信息网络的使用权。作者著作权使用费与本刊稿酬一并支付,不另计酬。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的行为即视为同意本刊上述声明。
迄今为止,本刊从未与任何单位、个人订立任何形式的合作用稿协议,从未委托任何网络中介承应合作发表论文事宜,凡有此类约稿、征稿、组稿信息均为诈骗信息,请勿上当受骗。本刊欢迎作者、读者监督、举报此类虚假信息。本刊保留追究任何损害本刊学术声誉不法行为者的权利。
福州大学学报哲社版编辑部
2013年11月
K203
A
1002-3321(2013)06-0069-08
2013-08-30
福建省服务海西建设重点项目(2010H204)
林校生,男,福建宁德人,宁德师范学院经济管理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