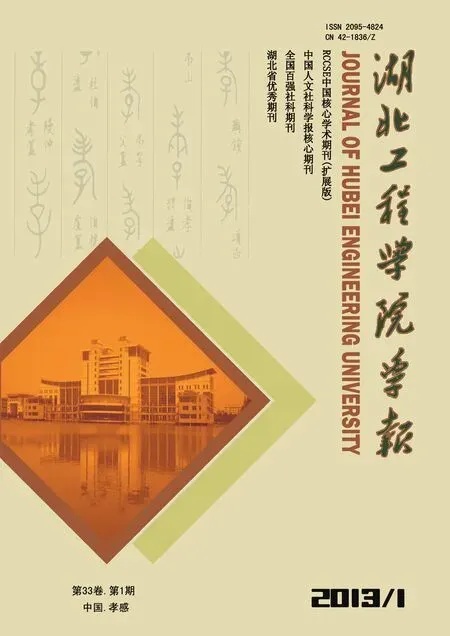论因牵连他国而构成国家责任的行为
——以联合国《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为线索
2013-04-13张磊
张 磊
(1.华东政法大学 国际法学院;2.复旦大学 法学院,上海 200042)
一、国家责任及其构成要件
所谓国家责任(State Responsibility),是指国家就其国际不法行为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所谓国际不法行为,是指国家所做出的违背国际义务的行为的总称。[1]143国际不法行为是引起国家责任的根据和前提。
关于国家责任目前尚不存在一部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国际公约,然而国际社会以往曾经多次试图将国家责任问题编撰成为一部国际法典。例如国际法学会(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Law)在1927年通过一项题为 “国家对在其领土内外国人的人身或财产造成损害所负国际责任的草案”(Draft on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y of States for Injuries on Their Territory to the Person or Property of Foreigners)的决议,但真正对国家责任问题开展系统和全面编撰工作的是国际法委员会。国际法委员会早在1949年第1届会议上就将国家责任问题列为其优先编撰的项目之一。于是,从1956年起,先后任命了加西亚·阿马多尔(Garcia Amador)、罗伯托·阿果(Roberto Ago)、威廉·里普哈根(Willem Riphagen)、加埃塔诺·阿兰焦·鲁伊斯Gaetano Arangio Ruiz以及詹姆斯·克劳福德(James Crawford)五位特别报告员开展研究,并向国际法委员会提交报告。最终在2001年国际法委员会第53届会议上,一份比较完整的《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二读)》(Draft articles on Responsibility of States for Internationally Wrongful Acts,以下简称《责任草案》)得以通过。同时获得通过的还有《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评注》(以下简称《责任草案评注》)。《责任草案》的完成及其在联合国大会的通过代表着国际法委员会超过40年工作的顶峰,它是迄今在该领域最为权威的国际法文件。
根据国际法,要构成国家责任需要具备两个方面的条件:第一,主观要件,即某一行为可以归因于国家而被视为国家行为;第二,客观要件,即该行为违背该国的国际法义务。[1]144其中,国家责任的主观要件一直是理论和实践中的难点。这是因为所谓的“国家行为”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必须以一定的代表国家的个人或团体的行为表现出来。例如国家侵害他国外交代表尊严的行为一定是代表该国的某个人或某个机构所做出的侵害行为。但不是任何个人或团体的行为都可被视为国家行为,所以国际法需要运用“归因性”来明确哪些个人或团体的行为可以归因于国家而由国家承担法律责任。然而,现实情况是异常纷繁复杂的,而构成国家责任的后果又是非常严重的,因此任何国家都会在国家责任问题上锱铢必较。这就使该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中长期存在各种各样的争议。一般而言,我们可以将国家责任的主观要件分为两个方面——可单独归因于国家的行为和因牵连他国而归责于国家的行为。前者较为简单,而后者(因牵连他国而构成国家责任的行为)则是争议较为集中的议题,历来是难点中的难点。国际法委员会在《责任草案》中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相关思路。以《责任草案》为线索,我们可以将因牵连他国而构成国家责任的行为分为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讨论。
二、援助或协助另一国实施国际不法行为
《责任草案》第16条规定:“援助或协助另一国实施其国际不法行为的国家应该对此种行为负国际责任,如果:(a)该国在知道该国际不法行为的情况下这样做,而且(b)该行为若由该国实施会构成国际不法行为。”[2]5在国际实践中,向另一国提供“援助或协助”(Aid or assistance)进而承担国家责任是一种比较常见的现象,尤其是在战争法中,正如伊恩·布朗利教授所言:“对违反中立和实施侵略的国家提供各种形式的协助原则上会导致共同责任。因此在一些条约关于侵略的定义中包含有对‘侵略者的协助’就不足为奇了。”[3]然而,此处国际法委员会所规定的第16条比以往更为精巧。
笔者注意到,在1999年《关于国家责任的第二次报告(增编1)》中,曾经将该条文表述为:“一国对另一国的援助或协助,如经确定是为了使另一国实行国际不法行为,则该项援助或协助本身构成国际不法行为,即使该项援助或者协助,单独来看,并不构成对国际义务的违背。”[4]6从前后两个条文的对比我们能够看出以下两个问题。从这两个问题,我们可以体会到该第16条确实精巧。
第一个问题是,《责任草案》第16条对援助国 “主观方面”的要求有所弱化,即它规定援助国应当“知道”被援助国所实施的是国际不法行为。而之前的条文对主观方面的要求不仅仅是“知道”,而且要达到“积极追求”的程度,即“是为了使另一国实行国际不法行为”。第16条降低了主观方面的门槛无疑是正确的,因为这样可以将这样一种重要情况纳入国家责任的范畴,即援助国明知自己行为可能导致的结果,但放任这种结果发生。
第二个问题是,《责任草案》第16条规定援助国行为本身也是违反其所承担的国际义务的,而这与之前的条文恰好相反。之前的条文实际上是扩大到“即使该项援助或者协助,单独来看,并不构成对国际义务的违背”。这一变更也是明智的。一方面,如果被援助国违反的是一项国际习惯法,那么援助国的行为不存在“单独来看,并不构成对国际义务的违背”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维也纳条约法公约》(Vienna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reaties)第34条规定:“条约非经第三国同意,不为该国创设义务或权利。”第35条规定:”如条约当事国有意以条约之一项规定作为确立一项义务之方法,且该项义务经一第三国以书面明示接受,则该第三国即因此项规定而负有义务。”[5]这就是说,如果被援助国对第三国负有一项条约义务,而援助国不受该条约义务的限制,除非援助国明示接受该义务,否则援助国帮助被援助国违反该义务的行为并不抵触《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因此,相比之前的条文,《责任草案》第16条在国际法上更加有理有据。
此外应当注意的是,援助国的行为应当达到怎样的程度才能引起国家责任。一方面,“没 有任何规定要求该项援助或协助对该国际不法行为的实施而言必须是不可或缺的,光是大大 促成该行为就已经足够了。”[6]149另一方面,援助国所提供的帮助应当具有针对性,即针对具体的国际不法行为,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援助,例如两国之间达成全面的经济援助协定就不属于《责任草案》第16条的范畴。
三、指挥或控制另一国实施国际不法行为
《责任草案》第17条规定:“指挥或控制另一国实施其国际不法行为的国家应对该行为负国际责任,如果:(a)该国在知道国际不法行为的情况下这样做,而且(b)该行为若由该国实施会构成国际不法行为。”[2]5可说这几乎是第16条的翻版,但是在第17条中我们应该更加侧重对“控制”一词的把握。
詹姆斯·克劳福德认为这种指挥或控制关系在历史上主要体现在三种特殊的国家关系中:第一,国际附属关系,特别是“宗主关系”和国际保护关系;第二,联邦国家与保留了自身的国际人格的联邦成员国之间的关系;第三,领土占领情况下占领国与被占领国之间的关系。但他也同时指出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国际关系的发展进一步限制了该条款的范围。几乎毫无例外,旧的国际附属关系已经结束,例如在阿拉伯半岛受英国保护的国家。余下的国家大多数已经改组了,以便缩小或者消除不确定性或附属性,例如意大利与圣马力诺、瑞士与列支敦士登、新西兰与西萨摩亚的关系式以代表性为基础,并不涉及受代表国家的指挥或控制的任何法律权利。[4]15
此外,应当注意的是,要使控制国承担国家责任,光有存在控制关系的事实是不够的,还必须有控制国实际利用自身控制地位的行为。例如“在道尔斯特与雅努塞克诉法国和西班牙案(Drozd & Janousek v.France and Spain)[注]这是一个由欧洲人权法院审理的一个案件。该案原告道尔斯特与雅努塞克声称自己在安道尔公国的法庭上没有收到公正的审判,并认为法国和西班牙应当在国际法上为安道尔的这种行为负责,因为根据法国和西班牙签订的和约,两国对安道尔都有宗主权。法庭认为相关行为并不能归责于宗主国,因此,对本案不享有管辖权。中,欧洲人权法院的多数意见认为,法国无须对安道尔法庭的判决负责,除非法国本身参加做出判决,或者后来赞同和公然拒绝司法”[7]。简言之,既有法律事实,又有法律行为,才能构成国家责任。
四、对另一国实施胁迫的行为
《责任草案》第18条是一条需要颇费思量的条文,它规定:“胁迫另一国实施一行为的国家应对该行为负国际责任,如果:(a)在没有胁迫的情况下,该行为仍会是被胁迫国的国际不法行为,而且(b)胁迫国在知道该胁迫行为的情况下这样做。”[2]5
笔者之所以称其颇费思量,是因为该条有一个用意很深的(a)款。《责任草案评注》对此解释道:“按照第18条承担的责任还有一个条件,即胁迫国必须意识到如果没有胁迫也会引起被胁迫国之行为的不法性的情况。”[6]157然而《责任草案评注》之前又称:“为了第18条的目的,胁迫与第23条所指的不可抗力具有同样的基本特性。必须有迫使被胁迫国意志屈服,除了遵守胁迫国的意愿之外别无选择的行为,才符合第18条的规定。”[6]156
或许有人会产生这样的误解:既然被胁迫国的行为是被逼到走投无路才做出的,那么怎么会假如不存在胁迫,仍然会引起被胁迫国做出不法行为呢?这要从两个方面来正确理解(a)款的准确含义:第一个方面,该款所谓假如不存在胁迫,仍然会出现的东西,不是被胁迫国的“行为”,而是该行为的“不法性”;第二个方面,《责任草案评注》认为:胁迫与第23条所指的不可抗力具有同样的基本特性,而“胁迫行为等同于不可抗力意味着:在适用第18条的大多数情况下,可以解除受胁迫国对受害第三国承担的责任。……等同于不可抗力的胁迫可以成为解除对受胁迫国的一行为之不法性的原因。因此,第18条没有在起首条款中将该行为称为‘国际不法行为’”。[6]156-157于是,我们将两个方面统一起来,国际法委员会在(a)款中的准确含义是:由于胁迫等同于不可抗力,所以胁迫是解除不法性的情况之一。于是,要使胁迫国承担第18条的国家责任,就必须满足:假如被胁迫国出于胁迫以外原因仍然实施了相同的行为,这一行为仍然具有不法性。这就将这样一种情况从第18条中剔除出去了,即除了胁迫外。被胁迫国行为的不法性被其他免责事由解除,例如即使一国在没有受到胁迫的情况下对外国人的财产实施了征用,但该征用因“危难”(例如为拯救公民生命)而免除责任。那么在此情况下,即使加上了胁迫,胁迫国也并不因此承担国家责任。
此外,还有两个比较重要的问题:第一,第18条的“胁迫行为”是否包括“合法胁迫”。法国指出:“胁迫”一词含义过泛,应限于违反国际法的胁迫。[8]78然而,国际法委员会却没有采纳法国的意见。笔者认为,这是明智的——第18条应当包括合法胁迫的行为,即胁迫国的胁迫行为可能并不违反其承担的国际法义务——第18条关心的只是胁迫行为能否迫使他国实施国际不法行为,这是因为“胁迫国对第三国的责任不是来源于它的胁迫行为,而是来自被胁迫国所实施的不法行为”。[6]156第二,我们发现在第16、17条都出现的措辞——“该行为若由该国实施会构成国际不法行为”——在第18条中却不见了,这就说明即使被胁迫国所违反的国际义务并不约束胁迫国,胁迫国仍然要为被胁迫国的行为承担责任。理由非常简单,因为被胁迫国由于胁迫因素的存在(等同于不可抗力)而被免除国家责任,假如胁迫国依旧能够主张不受被违反国际义务的约束而免责的话,那么就没有国家来承担责任了。
作为主权国家,各国都会不遗余力地避免构成国家责任。国家责任制度的核心是主观要件,而因牵连他国而构成国家责任的行为又是主观要件中最为复杂和最富争议的问题。以《责任草案》为线索,我们可以将该问题进行系统的梳理,同时对规则细节进行深入推敲。只有将细节问题分析透彻,国际社会才有达成协调意志的可能性。而本文的目的即使对该规则的细节进行评述,为国际公约的制定提供理论基础。
[参 考 文 献]
[1] 王虎华.国际公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2] U.N.Doc.A/RES/56/83.
[3] Ian Brownlie,State responsibility[M].Londou: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3:190.
[4] U.N.Doc.A/CN.4/498/Add.1.
[5] 周洪钧.国际公约与惯例:国际公法卷[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487-488.
[6] James C.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s ar-ticles on state responsibility:introduction,text,and commentaries[M].Londou: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
[7] Council of Europe ed.Yearbook of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1992, Vol35),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1995:160-163.
[8] U.N.Doc. A/CN.4/488: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