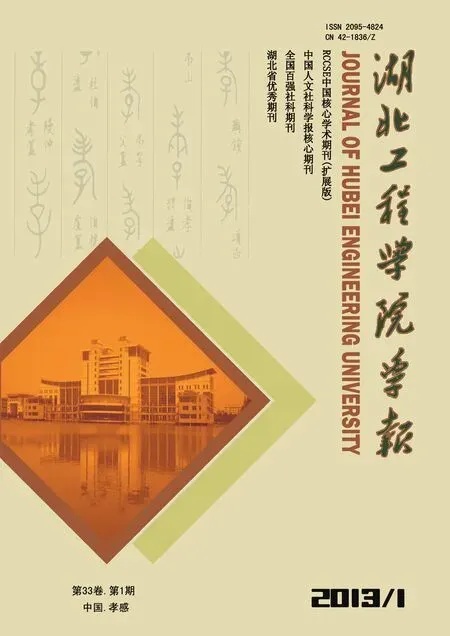法国现当代汉学与鲁迅
2013-04-13张静
张 静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编辑部,北京 100872)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文化巨人,海外汉学对于中国的研究大都以鲁迅作为先导。鲁迅的著述与思想,已成为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被广泛译介到世界各国,在异域文化中绽放文学生命。
在海外汉学研究中,以法国汉学与鲁迅最有不解之缘。
其一,鲁迅的文学活动是从翻译介绍法国作品开始的。鲁迅有着内容丰赡的翻译作品,“他在此处(翻译)所花的时间,比自己的创作要多得多”[1]。从1907年写《摩罗诗力说》算起,直至逝世前翻译果戈理《死魂灵》,30年间他从未停止过外国文学的翻译和介绍工作。1903年,他翻译了凡尔纳的科幻小说《月界旅行》、《地底旅行》和雨果的《随见录》中的《哀尘》。
其二,法国是欧洲翻译和介绍鲁迅著作的文化重镇。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鲁迅在法国的译介历程已经历了80余年,其小说和杂文、散文诗都被陆续译成了法文。
一、鲁迅在法国的译介(20世纪20年代-70年代)
中国现代文学在海外的传播以鲁迅为先驱,肇始于罗曼·罗兰对鲁迅的推崇。 1926年,《阿Q正传》由留法学生敬隐渔翻译成法文,巧合的是,敬隐渔也是将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介绍到中国的译者。罗曼·罗兰为向《欧罗巴》推荐《阿Q正传》而写信给该刊编者巴查尔什特,信中对《阿Q正传》评价道:“这篇故事的现实主义乍一看好似平淡无奇。可是,接着你就会发现其中含有辛辣的幽默。读完之后,你会很惊异地察觉,这个可悲可笑的家伙再也离不开你,你已经对他依依不舍。”[2]正是出于对现代中国文学天才的欣赏,经罗曼·罗兰推荐,《阿Q正传》分两期发表在巴黎《欧罗巴》(Europe)刊物上,这之后鲁迅译介便一步步进入法兰西语境。
沿着罗曼·罗兰以及一批留法学生以探求鲁迅为代表的译介取向,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有一批留在中国的法国和比利时传教士为法国引进鲁迅作品作出了贡献,像文宝峰、范伯旺、布里埃和明兴礼等都活跃在鲁迅研究的前沿。代表作如布里埃的《人民作家鲁迅》(法文版《震旦大学通报》第七卷第一期,上海,1946年)、范伯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鲁迅及其作品》(斯科特书局,北平1946年版)、明兴礼以《中国现代文学:作家时代的见证人》为题的论文,于1942年获得巴黎索邦大学博士学位。可贵的是,他们长期在中国传教,拥有第一手资料,这就使他们的研究成果大大突破了20年代拓荒者粗浅的介绍层次,鲁迅在法国的形象日趋饱满。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政治原因影响了世界文化格局的发展和法国汉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译介研究,巴金、茅盾、老舍、沈从文等现代大家在法国鲜有认知。在此种沉寂局面中,却仍然孕育着鲁迅研究发展的态势。此种发展一是因为鲁迅的作品大多为短制的精品,适于国外译介,二是因为法国的一些著名刊物保持罗曼·罗兰开拓的译介鲁迅的传统,陆续刊载鲁迅作品。比如《欧罗巴》文学月刊,这家在欧洲享有盛名的文学刊物,于1953年推出中国新文学专号,介绍了鲁迅的《药》,汉学家如艾丽斯·阿尔韦莱(Alice Ahrweiler)、克洛德·罗阿(Claude Roy)等人都写了专论。同时,巴黎联合出版社推出了“认识中国”丛书,内有鲁迅《阿Q正传》全译本,克洛德·罗阿为法译《阿Q正传》写序,称鲁迅这部小说是“震撼心灵的杰作,深深拨动了西方读者的心弦”[3]序言Ⅴ。此后,随着中法两国关系的日趋发展,特别是1964年建立了外交关系之后,两国间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法国汉学界运用此良机,一方面更新自己的知识,努力熟悉新中国、新文学;一方面花大力气培养新生力量。法国一些研究鲁迅的专家,如米歇尔·鲁阿、弗朗索瓦·于连、保尔·巴迪等,都是本时期先后接受汉学训练,经过磨砺而成才的。他们相继成长,无疑为日后法国研究鲁迅增添了新的活力。
20世纪70年代,因法国先锋刊物“太凯尔”(TelQuel)杂志社成员访问中国后陆续推出“中国专号”,被毛泽东喻为“新文化旗手”的鲁迅遂被法国文艺界塑造为“文化偶像”,因此,70年代上半期开始形成了法国介绍鲁迅的热潮,对鲁迅的研究更为规模化和学术化。从规模上来说,研究者们运用多种途径,比如文字译介、戏剧、观摩会、宣讲会等。就译述而言,从1970年起,法国几乎每一年都有鲁迅的译作问世。举其要者如:1970年《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内收鲁迅三篇杂文);1972年《如此这般》杂志发表了《为了忘却的纪念》、《对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译文;1973年《这样的战士·鲁迅诗歌、杂文选》出版;1975年《阿Q正传》重译本问世,同时据此改编的话剧《阿Q》在巴黎公演,《野草》全译本出版;1976年《鲁迅杂文选》两卷集、《朝花夕拾》法译本流传;1977年《论战与讽刺·杂文选译》出版;1978年《华盖集》法译本首版;1979年《故事新编》重版等。这些译文已不限于鲁迅的小说,扩大到包括他的诗歌、杂文在内的全部创作,其翻译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在法国汉学史上实属空前。从学术水平上看,此期的鲁迅研究由以往零星、随感式的介绍向系统研究转换。比如法国著名的鲁迅研究专家米歇尔·鲁阿(Michelle Loi)夫人,她为近现代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尤其是鲁迅在法国的推广传播起到了先锋作用,促使鲁迅在法国的译介达到一个高潮。鲁阿夫人原先教授了十多年的古希腊文、拉丁文和法文,驱使她专攻汉学研究中国的唯一原因是鲁迅。她非常崇敬鲁迅,她说:“中国并非一直是我从事教学和研究的中心……可是当我把兴趣转向中国的时候(早在去中国之前),我真想不到这个后来引起我兴趣的新的‘中心’,这个如此强烈地震动我自己生命的‘心’,竟是一个当时我几乎还未闻其名的作家:鲁迅。今天我仿佛觉得我早就很熟悉他……我想,为了使得我周围的青年学会了解鲁迅,像我那样认识鲁迅,我不能不做点什么。”[4]从70年代初起,鲁阿夫人就致力于鲁迅作品的翻译和介绍,尤其集中翻译了大量散文及杂文,曾先后出版过《革命文学》、《这样的战士》(鲁迅诗歌、杂文、散文选译)、《门外文谈》、《论战和讽刺》(内收《春末闲谈》、《无声的中国》等三十篇杂文)、《中国的语言和文字》、《鲁迅诗歌》、《妇女们非人的命运》(鲁迅小说杂文选译)等鲁迅作品译文单行本,撰写过《鲁迅》、《议谈点鲁迅》等多篇文章,为法国人认识这位“中国贤智”作出了可贵的贡献。由于她的积极倡导,由于她和其他汉学家的共同努力,在法国掀起了一股介绍、学习鲁迅的热潮,造成了一种“鲁迅奇观”。鲁阿夫人对于鲁迅的研究侧重关注鲁迅在革命战斗性和政治实践性上的关注,在她撰写的一系列文章中,基本都是围绕鲁迅作品的教益和现实意义展开,认为鲁迅是“我们时代的三四个最伟大的战斗的知识分子之一”。[注]鲁阿夫人认为鲁迅在“左联”内部的思想斗争所采取的立场,犹如法国伟大诗人保尔·艾吕雅之于保尔·尼赞,德国布莱希特之于卢卡契,意大利的葛兰西之于陶里亚蒂,称鲁迅是这三四个最伟大的“战斗的知识分子”之一。在她的研究著作《论战与讽刺·前言》中,作者以《诞生在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如何解放妇女》、《为了左翼作家的团结》、《反对人道主义》、《战斗的知识分子的活生生的榜样》、《文学与革命》等21节的篇幅,全面论证了鲁迅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对法国读者全面认识鲁迅的战斗实践和艺术实践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3]序言Ⅶ为了使法国青年了解和认识这位中国近代思想先驱,她1977年与巴黎第三大学于如伯教授组建了巴黎“鲁迅翻译中心”,决心把鲁迅的全部著作系统介绍到法国,翻译出版了鲁迅的《坟》等杂文集。由于他们的努力,法国的鲁迅研究得以持续、稳步地向前发展。
二、弗朗索瓦·于连——回到作品本身
从法国学术化研究来看,一些后起的学者突破了传统对鲁迅思想政治考察的研究方法,对鲁迅的具体作品本身作出全面阐释和分析。弗朗索瓦·于连是其中突出的代表,他率先提出了以回到作品本身的方式研究鲁迅。于连是现今法国著名汉学家,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1972-1977),曾在北京和上海大学留学(1975-1977),1983年获法国文学博士学位,曾任法国汉学学会会长(1988-1990)、巴黎国际哲学院院长(1995-1998),现为巴黎第七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教授、系主任,兼任法国当代思想研究中心主任、葛兰言研究中心(Centre Marcel Grant)主任,创办比较诗学杂志《远东-远西》杂志。主要从事中国传统文学、跨文化与欧洲的研究。[5]
值得一提的是,于连通过对鲁迅的学习和研究才渐渐产生了对中国文学研究的兴趣。他觉得鲁迅是“最有意思的作家,他的作品言简意赅,充满机敏智慧,直至隐晦难懂,他处于古典中国与现代中国的过渡阶段。鲁迅在当时既是惟一可接触的又是值得研究的作家。”[6]73另外,让于连觉得难能可贵的是,鲁迅还读过尼采、弗洛伊德、马克思、欧洲浪漫派诗人的作品,这是让于连感到很有意义的方面,他成了连接东方和西方的桥梁。于连认为,“鲁迅的一生就是一堂公开的汉学课,因为他极富有传统中国-现代中国、远东-远西的过渡性色彩。”[6]74鲁迅本人出身书香门第,但东渡日本学了西方知识。在日本,他接受了欧洲思想教育。明治维新时代,欧洲思想系统地传入日本远胜于中国:中国翻译的大部分欧洲概念都是通过日语进行的。鲁迅后来弃医从文,拿起手中的笔投身于思想意识的战斗。这些都对于连触动很大。
于连的研究重在突破前人研究的局限和单一,真正开始“让鲁迅自己说话”。他翻译了鲁迅的《朝花夕拾》、《华盖集》等文集,还撰写了《鲁迅:写作与革命》)的博士论文。论文研究的重点不是考察如鲁阿夫人关注的“革命性”——那个时代的革命斗争内部重建意识形态的介入,而是为了考察鲁迅“写作”的能力。他从鲁迅作品本身探寻“真正的鲁迅”,就鲁迅《故事新编》中的《补天》,《呐喊》中的《狂人日记》以及《华盖集》、《野草》、《朝花夕拾》中的作品进行“双重破译”,即本文的破译和背景的破译,从作品原有的内容中去考察作品自身不可剥夺的思想深度,去发现鲁迅在创作手法上的“间接批评技巧”。
在研究鲁迅的方法上,于连提出了“差异化比较”。于连认为,长期以来学界总习惯于对鲁迅其人其文的革命特质作单一的解释,而忽略作品本身的分析。更有甚者将鲁迅研究导向政治实用主义:“把鲁迅视为革命思想的确切体现者(如鲁迅是‘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反修战士;鲁迅斥责狄克;鲁迅提倡学日语;鲁迅赞成向西方开放)”,这就势必使鲁迅的作品失去它可靠的内在含义,“鲁迅就不得不沦为为意识形态服务的木偶”。另外,于连认为,中西文化差异和思维方式的不同,也促使学者应该从多元视角和差异化角度研究鲁迅。异国文化的差异性和特殊性,必然会带来研究方式的不同,这种差异有助于重新审视本国文化,比如于连从希腊哲学的角度转而研究中国思想,正是一个反思西方传统的全新角度,也是解构西方文化的有效途径,这也是于连不同于法国其他著名汉学家比如艾田蒲(Etiemble)等的独特之处。
难能可贵的是,于连总结出了贯穿鲁迅创作风格的主旨:认为鲁迅的创作异彩纷呈,但透过其创作的多样性,贯穿着一个基本的共同点,那就是象征主义。
于连撰写的《作家鲁迅:1925年的展望,形象的象征主义与暴露的象征主义》一文[注]1981年在鲁迅百年诞辰之际,法国汉学研究会组织纪念研讨会,于连在会上宣读论文《作家鲁迅:1925年的展望,形象的象征主义与暴露的象征主义》。论文内容参见钱林森:《法国汉学家论中国文学——现当代文学》,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年,第32-34页。,对鲁迅的散文诗集《野草》和杂文集《华盖集》进行了象征主义分析,是法国汉学界研究鲁迅的佳作。于连认为,鲁迅的象征手法是通过对立和矛盾手法来体现的,贯穿于其所有的作品,但每个作品的表现象征主义的形式又千差万别。比如散文诗《野草》是一种形象的象征,整个环境的描写是虚构甚至是梦幻,通过环境的象征使人感受压抑和窒息,借之矛盾的、不相容性的景物(《秋色》中的枣树与天空,《死火》中的火与冰等)等的描写,造成一种紧张、窒息的背景气氛,沉重地压抑着作品中的自我,不堪忍受的自我形象就在这种令人困扰的景物描写中鲜明地表现。这种环境描写无疑是作家强烈体验过的心理经验的直接投射。比如《求乞者》(《野草》集),他写道:
我顺着剥落的高墙走路,踏着松的灰土。
另外有几个人,各自走路。
微风起来,
露在墙头的高树的枝条带着还未干枯的叶子在我头上摇动。
微风起来,四面都是灰土。[7]
破败的泥墙灰土,由景物描写而表现出来的主题再现在整个场景之中。只存一堵颓垣断壁,成了虚空世界的象征。而风是这个场景中唯一运动着的有活力的因素,但是也只是除了掀起灰土这一断墙的残留物之外,再也无所作为。这种环境使读者蓦然感受出作者行走其中的绝望和难以忍受,于是将作者个人陷入囹圄和中国社会陷入困境的不安联系起来。
而杂文集《华盖集》运用的象征则是“论战性的象征”,是从社会现象出发而发掘象征意义,类似于罗兰·巴尔特的《神话学》。从具体经历过的细小的事件入手,发掘出一般人不能发现的象征含义,把它系统地纳入到思想背景中去,在赋予它们以一种象征意义的同时,又赋予它们以一种社会意义。不过巴尔特把符号学的总体视为明晰的体系,而鲁迅的象征基本上是追求暗含的境界,符号的含意全在言外,一如神秘莫测的影子。于连最后指出,如果说,《野草》中用形象表现的象征主义,可能受到了西方的影响,受到了现代诗的影响,受到柏格森、特别是弗洛伊德的新世界观影响,那么,杂文所表现的风格技巧更体现了真正的中国传统(即孔夫子赞同的春秋笔法、微言大义);这种情况下,象征色彩愈加浓厚,因为它以隐秘方式表现出来更具有化腐朽为新知之感。这种感觉随时都会使读者偏离习以为常的观念而探寻新的认知。
于连选择了《华盖集》里的《长城》[注]参见法文版鲁迅《华盖集》,弗朗索瓦·于连译自中文,洛桑,Alfred Eibel出版社,1978年,第134页。来说明鲁迅的象征手法:
伟大的长城!
这工程,虽在地图上也还有它的小像,凡是世界上稍有知识的人们,大概都知道的罢。
其实,从来不过徒然役死许多工人而已,胡人何尝挡得住。现在不过一种古迹了,但一时也不会灭尽,或者还要保存它。
我总觉得周围有长城围绕。这长城的构成材料,是旧有的古砖和补添的新砖。两种东西联为一气造成了城壁,将人们包围。
何时才不给长城添新砖呢?
这伟大而可诅咒的长城![8]
于连认为,鲁迅这篇《长城》写于1925年,它表达了鲁迅对传统中国文化的立场:讽刺、模棱两可,一种复杂的象征手法,逐步改变文本,直到走向完全的反面——从“伟大”变得“令人诅咒”。而填补维护传统文化的砖的形象是保守势力的象征,它们企图以思想意识的填补来维护传统文化和传统社会。
于连的这篇论文《作家鲁迅:1925年的展望,形象的象征主义与暴露的象征主义》是有感于有些法国研究者例如鲁阿夫人对鲁迅作品过分注重其政治上实用主义偏向而发的,凝聚了作者对鲁迅研究的独特性思考,是严格意义上从文学本身出发、回到作品本身中去分析的可贵实践。
三、当今法国鲁迅译介(20世纪80年代至今)
在译介方面,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法国共出版鲁迅译著10部左右,主要集中在小说上,比如1981年,法国斯多克出版社出版《狂人日记-阿Q正传》,并于1996年再版;同年,巴黎卫城出版社出版杂文集《坟》;1985年,法国信使出版社出版由鲁阿夫人及其小组翻译的5篇鲁迅的短篇小说及杂文合集《女性不公正 的生与死》;1995年,法国米歇尔出版社出版小说集《呐喊》等。值得一提的是,这其中,由鲁阿夫人翻译组织的译著有7部,其本人作为巴黎第八大学教授,曾于1985年3月来华访问,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签订法文版《鲁迅全集》(1981年)的工作协议书,并与复旦大学鲁迅研究室人员座谈鲁迅著作的研究和翻译问题,同时还访问了西北大学鲁迅研究室,与之建立工作联系,为《鲁迅年刊》撰稿。2004年是中法文化交流年,法国出版界重点推出了鲁迅小说《彷徨》的法译本。法国巴黎高师出版社和友丰出版社都做了重点宣传。2010年,巴黎高师出版社又推出了小说集《呐喊》。可见,法国对鲁迅的翻译重点在其小说,并存在多次复译现象,而对鲁迅散文尚开掘不够。
沿着20世纪80年代弗朗索瓦·于连回到作品本身的研究趋势,当今法国汉学界对于鲁迅的关注已经落实到对文学性以及叙述风格的研究。例如巴黎高师版《彷徨》的译者赛巴斯蒂安·韦(Sébastien Veg)[注]Sébastien Veg,中文名为王剑或者魏简,男,1976年生于美国纽约,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并于2004年在法国普罗旺斯大学比较文学专业获博士学位,2006年至今,为法国现代中国研究中心(CEFC,香港)研究员。通晓中文,与国内鲁迅研究者交流颇多。,是现阶段鲁迅研究的中坚力量,他写于《彷徨》法译本后记的文章《彷徨与出路》展开了对鲁迅的新思考,既是对20世纪法国“鲁迅热”的回顾与反思,又是对前辈学者研究鲁迅成果的发展。这篇后记通过对鲁迅的文本分析,总结出鲁迅的彷徨具体展现在六个方面:政治彷徨,历史彷徨,回忆的模糊性,现代性的冲击,情感浪漫主义和政治浪漫主义,孤独与伦理。同时认为《野草》中的《希望》一诗总结了《彷徨》所有的主题:求索询问、过往、黑暗、浪漫主义的并与希望相关的幻想。这种主题与卢卡奇式整体性的努力大相径庭,恰恰是一种碎片伦理的开端,某种程度上,与20世纪中后期法国后结构主义者有着暗合的思维。他的另一篇力作《从无政府主义到民主:鲁迅五四时代的小说》就主张鲁迅的创作源泉是一种民主的无政府主义精神——强调个人发展、思想独立自由、主张用教育改变社会——而不是对政治制度的革命。他认为鲁迅用文学写作正是体现了这种无政府主义精神——用写作这种完全个人的行为来打破规范,促进社会民主化,同时避开政治制度的变革。可见,Sébastien Veg对鲁迅的分析已经与前辈鲁阿夫人等关注“战斗性”大相径庭。
无疑,21世纪以来的鲁迅研究者,更能以理论化、文学化的观点,带着更具现代性乃至后现代性的观点来看待鲁迅作品,也更具包容性和拓展性,这些都为鲁迅研究在法国的新发展开辟了新的领域。
[参 考 文 献]
[1] 孙郁.鲁迅的译介意识[M]//鲁迅跨文化对话纪念鲁迅逝世七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40.
[2] 米歇尔.鲁阿.罗曼·罗兰与鲁迅[J].中国比较文学,1984(1):9.
[3] 钱林森.法国汉学家论中国文学——现当代文学[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4] 米歇尔.鲁阿.向新的高度攀登,我们会看得更远——鲁迅所教给我们的[M]//鲁迅研究年刊.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407.
[5] 乐黛云,李比雄.跨文化对话·17辑——“中法文化年”专号[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138.
[6] 弗朗索瓦·于连,狄艾里·马尔塞斯.(经由中国)从外部反思欧洲——远西对话[M].张放,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
[7] 鲁迅.鲁迅经典全集[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8:236.
[8] 王富仁, 沈庆利.新版鲁迅杂文集·华盖集·而已集[M].张中良,校注.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