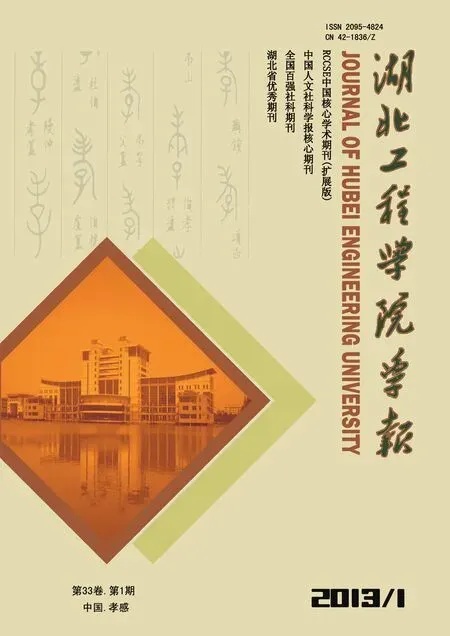“身外青春”:鲁迅散文的一个精神向度
2013-04-13王吉鹏
王吉鹏,杨 丽
(辽宁师范大学 研究生院,辽宁 大连 116029)
鲁迅在1925年1月1日“因为惊异于青年之消沉”[1]365而写的散文诗《希望》中说到:“我早先岂不知我的青春已经逝去?但以为身外的青春固在……”[2]181鲁迅把青年看成自己的“身外青春”,对“身外青春”的关注一直是鲁迅的一个精神向度。本文以鲁迅散文为研究对象,探讨鲁迅对“身外青春”的各种不同态度,从而展示一个伟大灵魂的侧面。
一
鲁迅在散文《藤野先生》一文的开头,这样描写了日本东京一个公园的场景:
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上野的樱花烂熳的时节,望去确也像绯红的轻云,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2]313
日本的国花樱花开放在春季,当其盛开得娇艳动人,缤纷烂漫时,“望去确也像绯红的轻云”飘在朗朗的天际,煞是美艳!东京市民会络绎不绝地前来观赏。赏花的人群中总也少不了清国留学生,且是“成群结队”相伴而行。这些留学生也形成了一道“风景线”。头顶上盘着犹如“富士山”般“高高耸起”的辫子,也有解散了辫子头发盘得平的,像是小姑娘的发髻一般“油光可鉴”。辫子作为民族压迫、民族屈辱的象征,鲁迅对其深恶痛绝。而有些留学生却怯于剪掉,不以留辫为耻,反以为荣,可见身上的封建思想与落后意识并未根除。鲁迅选择毅然决然剪掉辫子,并说“我的爱护中华民国……大半正为了使我们得有剪辫的自由”[3]576。清国留学生在东京的这种“附庸风雅”与“丑态”让鲁迅感到厌恶——“东京也无非是这样”!
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内忧外患,派遣留学生出国留学的初衷是要学习他国的先进科技知识,来探索本国的近代化之路。有些青年却把宝贵的青春挥霍在消闲娱乐上,“赏樱花”“学跳舞”“燉牛肉”。而鲁迅“除学习日文”就是“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演讲”[3]578。正值青年的鲁迅,没有将自己的青春置于身外来挥霍享受,而是积极向上,谱写着青春的乐章。1903年鲁迅在《自题小像》中曾表明过心迹:
灵台无计逃神矢,
风雨如磐暗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
我以我血荐轩辕。
鲁迅看到清国留学生的种种“丑态”,心里备受刺激,遥想故国飘摇不定的现状,又目睹同来的留学生沉醉于异国风情,心里难免会生出失落之感。
面对一道而来的青年人的醉生梦死与消闲享受,鲁迅心里多少有些心灰意冷,“到别的地方去看看,如何呢?”[2]313鲁迅禁不住发出这样的感叹。在弘文学院毕业后便决定前往仙台的医学院去学习。“仙台是一个市镇,并不大;冬天冷的厉害;还没有中国的学生。”[2]313鲁迅选择到仙台这样一个条件一般的学校学医,一方面要通过学医来救国,另一方面似乎是厌倦了与盘着富士头的清国留学生在一起,而要找个清静的地方去充实自己。鲁迅在东京学习的两年间没被享乐的“同仁”所“同化”,依然坚定地保持着自己的方向,寻求着自我所心向往之的彼岸。事实上,鲁迅在仙台时也没有完全割断与中国留学生的联系,除了经常通信外,还与许寿裳等人时而聚会,与范爱农等人有接洽,和这些志同道合的青年互为勉励,共同进步。鲁迅不仅让自己的青春不留白,同时也关心着其他青年人的发展。
在散文《范爱农》中,两人在后来“冰释前嫌”的回忆中叙说了一段误会。当时鲁迅作为留日的学长,去横滨接前来留学的范爱农及其同伴,在关检时,看到范爱农皮箱中装有其师母的“绣花的弓鞋”,这引起了鲁迅的不满,“心里想,这些鸟男人,怎么带这东西来呢”[2]323,无形间造成了二人之间的隔阂。虽然是一场误会,但从侧面看到了鲁迅的秉性,他不满青年人的自我腐化和堕落,希望他们能够珍视出国学习的机会,以待学有所成为国家做出自己的贡献,这也正是鲁迅青年时期的人生目标。鲁迅重视青年人的发展,后来在杂文《北京通信》中提到“但倘若一定要问我青年应当向怎样的目标,那么,我只可以说出我为别人设计的话,就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我之所谓生存,并不是苟活;所谓温饱,并不是奢侈;所谓发展,也不是放纵。”[4]52在基本生存保证的前提下,青年人不能只顾一己的奢靡享乐,而是要求发展,这发展也决非无尽地放纵自己。青年人要清楚自己的身份以及肩负的使命,要在不断的学习中提升自己,为改造社会添砖加瓦。“自然,这,是很幼小的。但是,惟其幼小,所以希望就正在这一面。”[1]316
二
这些不肯涂脂抹粉的青年们的魂灵便依次屹立在我眼前。他们是绰约的,是纯真的,——阿,然而他们苦恼了,呻吟了,愤怒,而且终于粗暴了,我的可爱的青年们!”[2]228
是的,青年的魂灵屹立在我眼前,他们已经粗暴了,或者将要粗暴了,然而我爱这些流血和隐痛的魂灵,因为他使我觉得是在人间,是在人间活着。[2]229
这是1926年4月10日鲁迅在《一觉》中对觉醒青年的一段描述。鲁迅在《〈野草〉英文译本序》中说“奉天派和直隶派军阀战争的时候,作《一觉》”[1]365。此外,此时距离“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不久,面对军阀无休止的混战,目睹爱国青年的惨遭杀害,鲁迅心中充满血和泪。在整理青年文稿的过程中,“绰约的”“纯真的”“不肯涂脂抹粉的”沉默的青年们终于“苦恼”“呻吟”“愤怒”“已经粗暴”或者“将要粗暴”了,这是多么的振奋人心!鲁迅已按捺不住心中涌起的波澜,高呼“我的可爱的青年们”。部分青年在鲁迅的支持下坚持从事文艺活动,在“一片沙漠里”终于涌现出《浅草》和《沉钟》。尽管《浅草》“经了几乎致命的摧折”在短短的3年内便名存实亡,随后的《沉钟》也在“这风沙澒洞中,深深地在人海的底里寂寞的鸣动”,但是它们已“开一朵小花”,并且“拼命伸长”自己的根去吸取地泉,“造成碧绿的林莽”,方便人们“休息”。这种坚持与拼搏深深触动鲁迅心灵,“我爱这些流血和隐痛的魂灵”,这宛然让人感到“生”的存在,觉得是“在人间活着”。鲁迅赞扬与期许这种精神,因为他们是被斗争的“风沙打击得粗暴”的灵魂,他们身上有着顽强的生命力与持久的战斗力。
1925年4月23日,鲁迅曾在《死火》中通过奇幻的梦境方式,展现了自己的战斗精神追求。他梦见自己在“冰山间奔驰”,虽然寒风凛冽刺骨,“我”也坚忍地坠入冰谷去寻找“死火”,那象征着抗争与进步的火种。“我”渴望它重新燃起,并且“永不冻结”“永得燃烧”。[2]201现实的残酷终究难逃“烧完”的宿命,与其“冻灭”不如奋战后“烧完”,便勇猛地跃出冰谷口外,虽然“我”被碾死在象征反动势力的“大石车”下,但“我”为救出革命的火而欣喜。青年人也是这“死火”的组成部分,鲁迅不惜以自我牺牲的代价来唤醒青年,可见其人格的高尚。
鲁迅生活在一个“风雨如磐”的时代,一个被“因袭的重担”压得喘不过气来的中国,又深受进化论的影响,“总认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1]5因此坚信青年人是未来的希望。当看到消沉的青年时,鲁迅直言不讳表达着不满:“现在青年的精神未可知,在体质,却半还弯腰曲背,低眉顺眼,表示着老牌的老成的子弟,驯良的百姓”。[5]251鲁迅敏锐地感知到青年中普遍存在着的颓废心理和虚空的苦闷,意识到应该唤醒青年人的觉悟,并鼓舞青年人正视现实,重拾失去的自信力,奋起与黑暗抗争!在《灯下漫笔》中,鲁迅大声呼喊:“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5]229面对复杂的社会环境,青年们必须勇敢地担负起身上的使命,“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1]15虽然赞赏“愤怒而粗暴的魂灵”,但即使做不到,也“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以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5]341。鲁迅用自己的温热,带领青年走出“冰谷”,使其“永不冻结”“永得燃烧”!鲁迅把促使青年人的觉醒当作己任,且不惜以牺牲的代价对青年人进行积极引导,热情指点,使他们得以沿着正确的路径成长和发展。
三
是的,但素园却并非天才,也非豪杰,当然更不是高楼的尖顶,或名园的美花,然而他是楼下的一块石材,园中的一撮泥土,在中国第一要他多。他不入于观赏者的眼中,只有建筑者和栽植者,决不会将他置之度外。[3]70
得到鲁迅这样肯定和赞赏的不是别人,正是韦素园,一位不求名利、踏实肯干、不尚空谈的进步青年。韦素园原系未名社成员,1932年不幸以三十岁的盛年因病去世。鲁迅在为他写的“墓记”中,悲叹“宏才远志,厄于短年”[3]64。不久又在散文 《忆韦素园君》 一文中详尽地记叙了二人的交往,表达了对他优秀品格的赞佩。
从鲁迅深情款款的回忆中,我们看到韦素园身上那种“愿意切切实实的,点点滴滴地做下去的意志”,以及那种办事“认真”,虽然“穷着”和“生着病”而仍旧坚持工作、“拼命的对付着内忧外患”“认真而激烈”个性。韦素园忠厚踏实,不求闻达,活着时“在默默中生存”,死后“在默默中泯没”,鲁迅把他比作是“楼下的一块石材,园中的一撮泥土”,认为“在中国第一要他多”。韦素园勤勤恳恳地做了许多对革命文艺事业发展有帮助的工作,“在默默中支持了未名社”,使译作“在文苑里却至今没有枯死的”,因此“是值得记念的青年”。鲁迅对他身上的优秀品质在回忆的“小事”中进行了细致的描写,给予充分的肯定与高度的赞扬,是因为他是建筑者、栽植者,而不是一个模仿者、跟随者,他理应是青年们仿效的楷模。韦素园“并非天才,也非豪杰”,但与当时存在的只知自我的青年相比较,他的确是值得赞赏的。而在饱含深情的文字之外,我们也同样看到了一向不喜欢空谈的鲁迅,他的一生也是在勤奋不息、努力耕耘、埋头苦干中度过的,二人的精神有相合之处。
鲁迅很赞誉韦素园身上那种“不怕做小事业”的“泥土”精神。在1924年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友会上的演讲中就强调“泥土和天才比,当然是不足齿数的,然而不是坚苦卓绝者,也怕不容易做”[5]177,正是指出这种精神的可贵性。鲁迅在对青年的做事态度上呼唤“泥土”精神,特别赞赏“肯做苦工”,“切切实实的,点点滴滴的”做“小事情”的年轻人,因为“似乎大家都可以做”且“中国正需要”。但鲁迅也很清醒地看到在当时的中国,“求虚名”的青年也大有人在,而甘愿做小事情的青年人则十分稀少。在后期看到青年人逐步摆脱浮躁时,他会感到由衷的欣喜,并会迫不及待地写信告诉给老朋友“近来有一些青年,很有实实在在的译作,不求虚名的倾向了,比先前的好用手段,进步得多……”[6]59。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中也赞扬这种“埋头苦干的人”,他们可以称之为是“中国的脊梁”,现在的社会也并不缺少拥有这种品质的人,“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3]122踏实肯干的青年才是社会所需要的人才。
鲁迅在回忆韦素园时提到了他的一个致命伤——“他太认真”,“一认真,便容易趋于激烈,发扬则送掉自己的命,沉静着,又噬碎了自己的心”[3]66,这是对韦素园“太认真”的一种惋惜。而当看到中国人的“不认真”时,又表现出了别样的态度。中国人把“一切事”都看作“不过是一出戏,有谁认真的,就是蠢物”。[4]345鲁迅看来,“不认真”是中国国民性的一个固有弱点,他曾发出号召要向自己的“敌人”——日本学习那种凡事认真的精神。对鲁迅来说,认不认真,同样是关系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前途与命运的因素。这似乎与韦素园的“太认真”矛盾,其实不然。正因为“认真”二字在鲁迅心中有极其重要的分量,所以会对韦素园的“太认真”表现出欣赏,为失去这样的青年而惋惜。鲁迅对韦素园这样默默无闻,踏实认真的青年可谓是赞赏有加,通过他勾勒出了有为青年的轮廓。
四
我平素想,能够不为势利所屈,反抗一广有羽翼的校长的学生,无论如何,总该是有些桀骜锋利的,但她却常常微笑着,态度很温和。待到偏安于宗帽胡同,赁屋授课之后,她才始来听我的讲义,于是见面的回数就较多了,也还是始终微笑着,态度很温和。待到学校恢复旧观,往日的教职员以为责任已尽,准备陆续引退的时候,我才见她虑及母校前途,黯然至于泣下。[4]291
刘和珍,没有“桀骜锋利”的外表,而是始终“微笑着”“态度很温和”,是一位追求新知的女性,富有正义感,敢于反抗“广有羽翼的校长”,不因势利强大而屈服,并时时担忧母校的前途。这样一位在思想上、行动上都进步的青年,却被“虐杀”在棍棒刀枪下,在如花灿烂的年纪!1926年3月18日,北京发生一件凶残的血案:段祺瑞政府派卫兵用步枪大刀,在国务院门前包围虐杀了徒手请愿,意在援助外交的市民和学生,死伤人数众多,事后被污蔑为“暴徒”,女师大学生刘和珍和杨德群在此事件中惨遭杀害。鲁迅一直不赞成学生请愿的事宜,但也万万没料到会有如此“喋血”的惨案发生。已经“出离愤怒”的鲁迅看到了为中国而死的青年,在“悲哀与尊敬”的心绪中感到“有写一些东西的必要”。可面对国民党政府的暴行“实在无话可说”,惨象和流言实在让人忍无可忍,呼喊“我还有要说的话”!“沉勇而友爱”的革命女青年在“弹雨中互相救助”“殒身不恤”,是多么“惊心动魄的伟大”!这些女性冲破几千年的桎梏,做事“干练坚决”“百折不回”,是新女性的代表,鲁迅真诚的毫无掩饰表达着对她们的赞扬。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真的猛士”是为革命而牺牲的烈士,同时也是鲁迅自身及对青年的期许。存活的有志青年要化悲愤为力量,继续顽强不屈地与黑暗现实作斗争。先驱者的死是要显示未来的希望的。“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4]290鲁迅对青年寄予希望,激励着他们向着光明的未来勇敢前行,鲁迅的革命姿态也尽显其中。
鲁迅目睹了一次次青年的被屠杀,层层淤积起来的青年人的血,使其极度悲愤,并沉重地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不料积习又从沉静中抬起头来……”[1]500鲁迅一贯的战斗精神让其将悲愤凝于笔端,记录下另一位革命青年——柔石。 他的家乡,是台州的宁海,这只要一看他那台州式的硬气就知道,而且颇有点迂,有时会令我忽而想到方孝孺,觉得好像也有些这模样的。[1]476
柔石做事坚决干练,遇到挫折勇于面对,身上有台州人特有的“硬气”;“迂”气如方孝孺,是其不屈不挠秉性的体现。他善良真诚,不怕死,且惊疑于世间居然有人“卖友”“吮血”,坚信“只要学起来”就没什么不可能。这样一位青年,在1931年2月7日国民政府的反革命的文化“围剿”中被秘密枪杀,遭此命运的还有其战友,他们是被人们永远铭记的“左联”五烈士!他们为追求自由,生命与爱情皆可抛弃。
“原来如此!……”恍然大悟后,是无尽的痛心和悲愤。国民党政府的罪行已无可计数,面对为革命献身的年轻战士接连遇害,鲁迅在激愤的同时也对他们充满了赞许。“我不如忘却”,但又说“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1]502革命者的崇高品质和战斗精神将会永远铭记在人民心中。“夜正长,路也正长”,黑暗的统治在继续,奋斗不息的步伐也不会停滞,我们当以十足的勇气来面对。不能忘却的继续前赴后继,以昂扬斗志前行。
鲁迅赞扬牺牲者无畏的品格,但他心里并不希望青年人作无谓的流血牺牲,他也从不鼓动青年用自己的热情去硬碰残暴的当局。他不赞成学生请愿游行,一方面是他对国民党政府的残暴有充分的认识,另一方面是出于对青年人生命的珍爱,他期望青年们能够更好地生存与发展,因为青年是未来的希望。而“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4]378,因此鲁迅对因自己的号召而使青年人牵连受害的事件表现了深深的自责。因民间讲究虾越鲜活,吃的人便越高兴,越畅快,他说,“我就是做这醉虾的帮手,弄清了老实而不幸的青年的脑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觉,使他万一遭灾时来尝加倍的苦痛,同时给憎恶他的人们赏玩这较灵的苦痛,得到格外的享乐。”[4]474鲁迅对青年的态度有时是矛盾的,既希望看到青年勇猛奋起抵抗黑暗,又害怕青年因这勇猛而牺牲。这也就是鲁迅为什么时常要对青年发出自己的意见和看法又怕因此“毒害”了青年的缘故。
鲁迅散文的精神世界是一片幽幽深谷,而对“身外青春”的关注又是其散文的一个精神向度。鲁迅把大量的心血倾注在青年身上:他率直地对醉生梦死的青年表达着不满,发自内心地对踏实肯干的青年给予着赞扬,他为革命事业唤醒与培育了众多的英才,同时又为因此牺牲的青年感到痛心与惋惜,但依然始终如一在青年身上寻找着生命的能量。我们从鲁迅对“身外青春”的各种不同的态度中窥见鲁迅散文的精神向度,借以这扇窗户,来感受鲁迅的人格风范和思想力量。
[参 考 文 献]
[1] 鲁迅.鲁迅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2] 鲁迅.鲁迅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3] 鲁迅.鲁迅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4] 鲁迅.鲁迅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5] 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6] 鲁迅.鲁迅全集:第1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