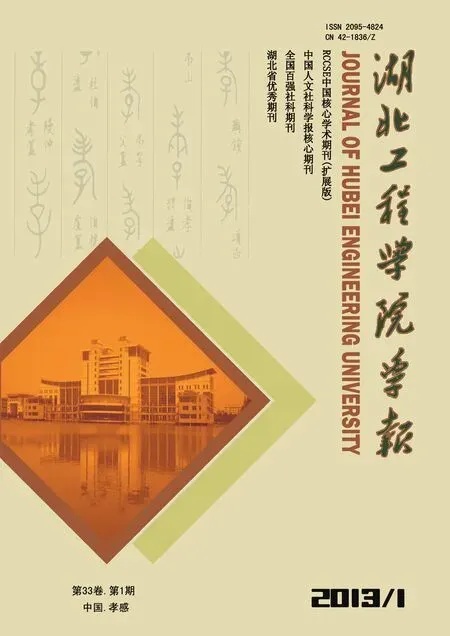伦理与实践:魏晋南北朝孝道述论
2013-04-13王仁磊
王仁磊
(河南师范大学 图书馆,河南 新乡 453007)
中国儒家的传统观念认为,“孝”至少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尊敬父母,这主要是精神层面的要求;二是赡养老人,即尽可能地去满足老人的物质需求。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不可分割。本文即从这两个方面对魏晋南北朝的孝道略加探讨。
一、尊敬父母
孝观念是中国家庭伦理的核心。从汉代开始,“孝”已经在朝廷政治与社会伦理中处于核心地位。魏晋以来,政权更替频繁,一些靠篡夺而上台的当权者忌讳言忠,所以他们更加强烈地标榜“以孝治天下”,甚至出现了“孝先于忠”的独特现象。[1][2]在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和朝廷的大力提倡下,孝道伦理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较好的实践。
1.孝道伦理。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玄学思潮盛行一时,但对广大家庭影响最深的还是儒家思想。在绝大部分家庭中,孩子从小就接受了孝道教育。有些孩子从三四岁就被父母教以《孝经》,当时人认为:“读此一经,足为立身之本。”[3]196文献中记载了许多这一时期懂得孝敬父母的小孩子。“陆绩怀橘”讲的就是一个小孝子的故事。据史书记载:“绩年六岁,于九江见袁术。术出橘,绩怀三枚,去,拜辞堕地,术谓曰:‘陆郎作宾客而怀橘乎?’绩跪答曰:‘欲归遗母。’术大奇之。”[4]1328东晋道士吴猛少时的事迹也很典型:“少有孝行,夏日常手不驱蚊,惧其去己而噬亲也。”[5]2482为了不让蚊子去叮咬亲人,任凭蚊子来咬自己。南朝的冯道根也是一位小孝子:“少失父,家贫,佣赁以养母。行得甘肥,不敢先食,必遽还以进母。年十三,以孝闻于乡里。”[6]286-287
孝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东汉末年,司马芝少年时“避乱荆州,于鲁阳山遇贼,同行者皆弃老弱走,芝独坐守老母。贼至,以刃临芝,芝叩头曰:‘母老,唯在诸君!’贼曰:‘此孝子也,杀之不义。’遂得免害”[4]386。就连盗贼对孝子也很敬佩,足见孝的影响力之大。甚至因孝敬父母而犯了罪,也会得到官府或他人的原谅。西晋时,“(范)乔邑人腊夕盗斫其树,人有告者,乔阳不闻,邑人愧而归之。乔往喻曰:‘卿节日取柴,欲与父母相欢娱耳,何以愧为’”[5]2433。范乔原谅了为二亲节日取暖而盗伐其树的邑人。北魏北新侯安同的长子安屈,在明元帝时典太仓事,“盗官粳米数石,欲以养亲。同大怒,奏求戮屈,自劾不能训子,请罪”。而明元帝却“嘉而恕之”,并下诏“长给同粳米”。[7]713为了养亲而犯罪,不但没有被处罚,还得到了最高统治者的嘉奖,其原因就是孝。
其实,除了统治者的倡导,孝也是善良的人们发自内心的自然之情。东汉献帝兴平(194年-195年)年间,京兆新丰人鲍出冒死从“啖人贼”手中救回母亲,史家赞扬其曰:“至于鲍出,不染礼教,心痛意发,起于自然,迹虽在编户,与笃烈君子何以异乎?”[4]553-554可见孝行被认为是人的本能。
2.尊严与避讳。西汉思想家、政治家董仲舒把儒家的伦理思想概括为“三纲五常”,其中之一就有“父为子纲”。他在《春秋繁露》中指出:“父者,子之天也。”即强调了父尊子卑的理念。因此,儿子要顺从父亲,并要竭力去维护父亲的尊严,这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魏晋南北朝时期,“三纲五常”思想仍然统治着人们的头脑。在父亲的尊严遭到挑战时,孝子们总是要竭尽全力去维护。东吴名臣诸葛瑾(字子瑜)面长似驴,有一次孙权大会群臣,想借此捉弄一下他的儿子诸葛恪,“使人牵一驴入,长检其面,题曰诸葛子瑜。恪跪曰:‘乞请笔益两字。’因听与笔。恪续其下曰‘之驴。’举座欢笑,乃以驴赐恪”[4]1429。诸葛恪既在群臣中维护了父亲的尊严,又没有得罪于皇帝,还赢得了一头驴,可谓是一举三得。
对父亲尊者地位的维护还表现在不拿自己和父亲对比,即使是别人这样做了,自己也要去声明子不如父。刘宋时有这样一则故事:“(张)敷小名查,父邵小名梨,文帝戏之曰:‘查何如梨?’敷曰:‘梨为百果之宗,查何可比。’”[8]1396张敷巧妙地化解了宋文帝的戏弄。与此相比,南齐王慈的回应可谓是更高一筹。王慈小时候与从弟王俭共同练习书法,“谢凤子超宗尝候(慈父)僧虔,仍往东斋诣慈。慈正学书,未即放笔,超宗曰:‘卿书何如虔公?’慈曰:‘慈书比大人,如鸡之比凤。’超宗狼狈而退”[9]606。王慈既对谢超宗的对比做了解释,又回应了他对父讳的违犯。
魏晋南北朝时期继承了先秦以来“为尊者讳”的传统,尤其是世家大族特别重视避讳,这也体现了孝道伦理。即使是任官也要避父讳,西晋已有“故事,父祖与官职同名,皆得改选”[5]1534的惯例,到了东晋南朝,甚至字同音异者也要避讳。如东晋时,“将征苏峻,司徒王导欲出(王)舒为外援,乃授抚军将军、会稽内史,秩中二千石。舒上疏辞以父名,朝议以字同音异,于礼无嫌。舒复陈音虽异而字同,求换他郡。于是改‘会’字为‘郐’。舒不得已而行”[5]2000。王舒任官避父讳,将会稽改为了郐稽,这样一来字和音都不相同了。他人犯父讳也要给予坚决的回击,以维护父亲的尊严。如东晋时,“庾翼子爰客尝候(孙)盛,见(其子)放而问曰:‘安国(盛字)何在?’放答曰:‘庾稚恭(翼字)家。’爰客大笑曰:‘诸孙太盛,有儿如此也!’放又曰:‘未若诸庾翼翼。’既而语人曰:‘我故得重呼奴父也’”[5]2149。在当时,不避父讳则会同不孝之子一样遭到别人的嗤笑和鄙视。南齐时,何昌宇曾任吏部尚书,“尝有一客姓闵求官。昌宇谓曰:‘君是谁后?’答曰:‘子骞后。’昌宇团扇掩口而笑,谓坐客曰:‘遥遥华胄’”[9]795。
3.孝感故事的出现。魏晋南北朝时期,“孝感”观念兴起,出现了大量的孝感故事。继后妃之后被列为《晋书》列传之首的孝子王祥,就有“卧冰求鲤”和“黄雀入幕”两则孝感故事。王祥的继母朱氏是一个苛刻的女人,“常欲生鱼,时天寒冰冻,祥解衣将剖冰求之,冰忽自解,双鲤跃出,持之而归。母又思黄雀炙,复有黄雀数十飞入其幕,复以供母。乡里惊叹,以为孝感所致焉”[5]987[注]史书中对王祥的孝感故事多有记载,如《三国志》卷18《魏书·吕虔传》注引孙盛《杂语》曰:“祥字休徵。性至孝,后母苛虐,每欲危害祥,祥色养无怠。盛寒之月,后母曰:‘吾思食生鱼。’祥脱衣,将剖冰求之,少顷,坚冰解,下有鱼跃出,因奉以供,时人以为孝感之所致也。”到了唐初官修《晋书》时,对王祥的孝感故事做了总括性的描述,即为文中所引。。有些孝感故事则与父母的疾病有关,这反映了子女的孝心和古人缺乏医学知识的无奈。南齐永元(499-501年)初,“(庾黔娄)除孱陵令,到县未旬,(父)易在家遘疾,黔娄忽然心惊,举身流汗,即日弃官归家,家人悉惊其忽至。时易疾始二日,医云:‘欲知差剧,但尝粪甜苦。’易泄痢,黔娄辄取尝之,味转甜滑,心逾忧苦。至夕,每稽颡北辰,求以身代。俄闻空中有声曰:‘征君寿命尽,不复可延,汝诚祷既至,止得申至月末。’及晦而易亡,黔娄居丧过礼,庐于冢侧”[6]650-651。萧梁时,“(陆)襄母年将八十……尝卒患心痛,医方须三升粟浆,是时冬月,日又逼暮,求索无所,忽有老人诣门货浆,量如方剂,始欲酬直,无何失之,时以襄孝感所致也”[6]409。有些孝感故事似乎与道教的神仙灵药思想有关。萧梁处士,“后于钟山听讲,母王氏忽有疾,兄弟欲召之。母曰:‘孝绪至性冥通,必当自到。’果心惊而返,邻里嗟异之。合药须得生人葠,旧传钟山所出,孝绪躬历幽险,累日不值,忽见一鹿前行,孝绪感而随后,至一所遂灭,就视,果获此草。母得服之,遂愈。时皆叹其孝感所致”[6]740。有些孝感故事与儒家思想密切相关。如陈朝时曾为太子洗马的徐份,“性孝悌,(父)陵尝遇疾,甚笃,份烧香泣涕,跪诵《孝经》,昼夜不息,如此者三日,陵疾豁然而愈,亲戚皆谓份孝感所致”[10]。北朝同样有孝感故事。如北魏时人陆政,“性至孝。其母吴人,好食鱼,北土鱼少,政求之常苦难。后宅侧忽有泉出而有鱼,遂得以供膳。时人以为孝感所致,因谓其泉为孝鱼泉”[3]557。历仕萧梁和北周的柳霞,“其母尝乳间发疽,医云:‘此病无可救之理,唯得人吮脓,或望微止其痛。’霞应声即吮,旬日遂瘳。咸以为孝感所致”[3]767。
这些孝感故事以母子孝感故事居多,父子孝感故事则较少,这其实同中国古代的孝行故事在整体上是一致的。有研究表明,从两汉时期开始,以“孝子养老母”为题材的孝行故事已经成为中国孝行故事的一种固定模式。魏晋南北朝时期当然也不例外,但孝感故事在这一时期才大量出现。值得注意的是,南朝特别是萧梁以降,孝感故事明显增多,并且常常与佛教信仰相联系。这应该与南朝一些君臣崇信佛教特别是梁武帝佞佛有关。如曾任萧梁守吏部尚书的褚翔,“少有孝性。为侍中时,母疾笃,请沙门祈福,中夜忽见户外有异光,又闻空中弹指,及晓疾遂愈,咸以翔精诚所至焉”[6]586。又如孝子刘霁,“母明氏寝疾,霁年已五十,衣不解带者七旬,诵《观世音经》,数至万遍,夜因感梦,见一僧谓曰:‘夫人算尽,君精诚笃至,当相为申延。’后六十余日乃亡”[6]657。豫章南昌人滕昙恭,“年五岁,母杨氏患热,思食寒瓜,土俗所不产,昙恭历访不能得,衔悲哀切。俄值一桑门问其故,昙恭具以告。桑门曰:‘我有两瓜,分一相遗。’昙恭拜谢,因捧瓜还,以荐其母。举室惊异。寻访桑门,莫知所在”[6]648。这些与佛教有关的孝感故事,或是在老人生病时请沙门祈福,或是孝子口诵佛经,或是遇桑门帮助,反映了南北朝时期佛教对人们家庭生活的影响之深。
对于这些孝感故事,有学者认为,其可信度和奇迹出现是否真为诚孝感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即使这些故事都是出于编造,亦仍具有家庭历史发展的重要标志性意义,标志着‘孝感’观念的兴起。从此,这个观念一直镶嵌在国人精神灵魂的最深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演变,有着十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11]我们知道,魏晋以降,从印度传来的佛教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到了南北朝时期,更是成为了社会的普遍信仰,对上至帝王将相,下至普通百姓的生活都有一定影响。源于中国本土的道教在这一时期也逐渐兴起,对社会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它们的影响不断扩大,从而大大改变了儒家伦理统治下的社会各阶层家庭的生活面貌。笔者认为,孝感故事的出现,正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儒、释、道思想及其融合在家庭这一层次的社会组织中的体现。
4.不孝之子。虽然社会提倡孝道,但总是有那么一部分人不守孝道,成为了不孝之子。这样的人从皇帝到百姓都有。南朝刘宋的前废帝就是一个不孝之子。史书记载:“初太后疾笃,遣呼帝。帝曰:‘病人间多鬼,可畏,那可往。’太后怒,语侍者:‘将刀来,破我腹,那得生如此宁馨儿!’”[8]147不孝皇帝差点儿把太后气死。南齐时,“秣陵朱绪无行,母病积年,忽思菰羹,绪妻到市买菰为羹欲奉母,绪曰:‘病复安能食。’先尝之,遂并食尽。母怒曰:‘我病欲此羹,汝何心并啖尽。天若有知,当令汝哽死。’绪闻便心中介介然,即利血,明日而死”[9]1815。虽然故事情节未必真实,但像朱绪这样的不孝之子毕竟是存在的。诚然,穷苦人家的子女未必能够满足父母的物质需要,但富人倘若也是如此的话,就不只是吝啬了,那就是不孝。北魏平昌太守崔和就是这样的不孝之子,史称其“家巨富,而性吝啬,埋钱数百斛。其母李春思堇,惜钱不买”[7]634。
《孝经》有言:“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法律对不孝也是要治罪的,如《魏律》、《晋律》和《北魏律》中都有相关的规定。刘宋时,“安陆应城县民张江陵与妻吴共骂母黄令死,黄愤恨自经死”[8]1534。后虽遇赦,不孝之子张江陵仍被枭首,其妻吴氏免死补冶。如王华孙王长在宋明帝泰始二年(466年),“坐骂母夺爵”[8]1678。在这一时期,不孝可以作为政敌之间攻讦的借口,甚至可以成为废除皇帝的理由。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孝在这一时期地位之重要。
二、赡养老人
尽可能地去满足父母物质上的需求,使他们老有所养、病有所医,是子女们应尽的孝道。为了做到这一点,普通家庭的子女们可能要更加努力地去劳动,或是耕种土地,或是受雇他人,或是代人抄书,等等。有些人家的子弟,为了养亲而出仕,因为在当时,做官特别是地方官可以获得较为可观的收入。西晋时,王长文原是一个“州府辟命皆不就”,“闭门自守,不交人事”[5]2138的隐者,但因为家贫,为了养亲而出仕。有人问他:“前不降志,今何为屈?”他的回答是:“禄以养亲,非为身也。”[5]2139太原中都人孙盛也是这样的一位孝子:“起家佐著作郎,以家贫亲老,求为小邑,出补浏阳令。”[5]2147当然,如果家庭经济条件不差,足以养亲的话,孝子们会选择在家侍养而不出仕。如魏晋时的大孝子王祥就对其继母甚孝,“供养三十余年,母终乃仕,以淳诚贞粹见重于时”。[4]541即使有人推荐为官,孝子们也往往会以“母老疾笃,故无心为吏”[5]1434一类的话来推辞。许多在职的官吏也会因赡养老人而罢官归家。如北魏时曾任太尉长史的崔季良,“及(父)秉还乡,季良亦去职归养”。[5]1106
当时的律令规定:“八十者,一子不从政;九十者,其家不从政。”[5]1398当老人年满八十时,至少要有一个儿子(通常情况下应是嫡长子)在家中侍养老人,而老人年满九十,其所有的儿子都要在家供养老人。当籍注年龄与实际年龄不同时,如果籍注年龄大于实际年龄,孝子要按籍注年龄辞官。如刘宋时的孝子何子平,“母本侧庶,籍注失实,年未及养,而籍年已满,便去职归家。时镇军将军顾觊之为州上纲,谓曰:‘尊上年实未八十,亲故所知。州中差有微禄,当启相留。’子平曰:‘公家正取信黄籍,籍年既至,便应扶侍私庭,何容以实年未满,苟冒荣利。且归养之愿,又切微情。’觊之又劝令以母老求县,子平曰:‘实未及养,何假以希禄。’觊之益重之。既归家,竭身运力,以给供养”[8]2257-2258。反之,如果是实际年龄大于籍注年龄,作为孝子,又要按实际年龄归养。同是刘宋时期的张岱就是如此:“母年八十,籍注未满,岱便去官从实还养,有司以岱违制,将欲纠举。宋孝武曰:‘观过可以知仁,不须案也。’”[12]
由于统治阶级对“孝”的提倡以及法律上的强制规定,儿子在家供养老人的现象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普遍存在,形成了供养型家庭。在这种家庭中,老人(父母都在世或一人在世)身边至少有一个儿子及其家庭,即为社会学上所说的主干家庭,有时还可能包括其他儿子及其家庭,组成了联合家庭。秦商鞅变法“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13]的法令,秦汉时期一直存在。东汉后期以来,父子兄弟同居的大家庭逐渐增多,在曹魏“除异子之科”[5]925法令实行之后,主干家庭和联合家庭更是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而且尤以北朝为最。在北朝,已婚的兄弟们共同养老而不分家的情况比较多。如北魏时,“东郡小黄县人董吐浑、兄养,事亲至孝,三世同居,闺门有礼”[7]1884。而在南方,供养型家庭的规模可能要小些。据《宋书·周朗传》记载:“今士大夫以下,父母在而兄弟异计,十家而七矣。庶人父子殊产,亦八家而五矣。”这反映的应该是南朝家庭的实情。
[参 考 文 献]
[1] 唐长孺.魏晋南朝的君父先后论[M]//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北京:中华书局,1983:233-248.
[2] 胡和平.浅议“魏晋以孝治天下”[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4):68-71.
[3] 令狐德棻.周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1.
[4] 陈寿.三国志[M].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1982.
[5] 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6] 姚思廉.梁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7] 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8] 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9] 李延寿.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0] 姚思廉.陈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336.
[11] 张国刚.中国家庭史:第1卷[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465.
[12] 萧子显.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580.
[13]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22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