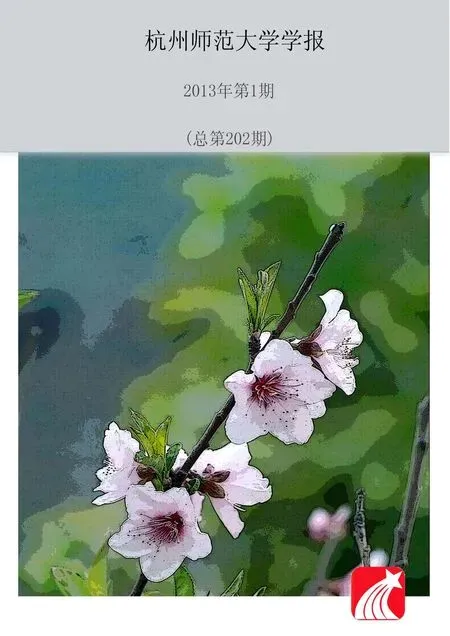析布尔迪厄的艺术理论
2013-04-13陆扬
陆 扬
(复旦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433)
析布尔迪厄的艺术理论
陆 扬
(复旦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433)
布尔迪厄的《区隔》要求学者走进厨房,在食物色香味的调配中培养基本审美趣味。这并不仅仅是一个隐喻。他判断工人阶级和知识阶级生活习性的不同导致艺术趣味的不同,亦是立足于这一趣味不平等的法理认知。由此来看摄影的“大众美学”, 或可见出学院派再是有心在仪式化上做文章,没有雄厚的受众基础,以及引领时尚的先锋意识,任何一种新兴艺术修成圆满功德谈何容易。而在社会分工日益细化的今天,我们更需要一种整体的而不是支离破碎的人文关怀。
布尔迪厄;《区隔》;艺术场;审美;康德
一 从口味到趣味
“趣味”(test)一语的原初含义应是口味,它是人类最古老的感觉之一。当口味发展到趣味,这意味着当中的感性因素渐行渐远,理性因素占据了上风。但是趣味不但因人而异,各不相同,就是阶级与阶级、阶层与阶层之间,也多有差异。布尔迪厄在他的名著《区隔:趣味判断的社会批判》一书中,通过大量数据分析,得出缘因文化资本,导致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艺术趣味判然有别的结论。《区隔》开篇就宣布,文化商品的经济有其特殊逻辑;而社会学,便是不遗余力,说明文化商品的消费者及其趣味是在何种条件下产生,与此同时,描述占有我们叫做艺术作品那类东西的不同方式,及其背后的法理体制。他给文化下了这样一个定义:
除非“文化”一语在其限定的、通常使用的规范意义上,回归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同时对最精致对象的苦心经营的趣味,重新同美食风味的基础味觉联系起来,我们便无以充分理解文化的种种实践。[1](P.1)
这里可以见出布尔迪厄典型的后现代治学立场,即不以文化为图书馆中的高头讲章,要求文化的研究走出殿堂,走进厨房,在食物色香味的调配中培养出最基本的审美趣味。很显然,这是宏大叙事消解之后的后现代的方法。
从食物的口味来培养趣味,就算不过是个比喻吧,这听起来也完全是现代美学的一种倒退。美学不就是要求摆脱声色感官的快感,把它们升华到精神的层面吗?这是康德的传统。但是布尔迪厄明确表示反对康德美学的审美非功利观点,反对康德主张艺术快感不涉及任何功利目的的立场。反之他认为审美感知必包含两个部分,一是工人阶级的大众趣味,在不无粗鄙的声色犬马中得到快乐,二是独立于感官诱惑的那一种冷静快感,那是权贵阶级维护自身特权的手段。故而在文化消费中出现的趣味分歧,追究到底,是现代社会错综复杂的阶级分歧,演绎到了艺术和文化的领域。所以康德美学绝不是一种天真无邪的趣味理论,而是丝毫不爽的阶级斗争的产物。用布尔迪厄本人的话来说,那就是每一个阶级群体,都有它自己的艺术家和哲学家、报纸和批评家,一如它拥有它自己的发型师、室内设计师和裁缝。
但是布尔迪尔还真不是仅仅是在比喻说法。在《区隔》的第三章“习性与生活方式的空间”中作者指出,在食物领域,社会等级的区分通常与收入直接有关。但是收入的差异掩盖了背后另一种更隐秘的差异,那就是文化资本富足、经济资本稍有不足的群体,同反过来经济资本富足,文化资本稍有欠缺的群体,他们的食物趣味,是恰如其反。布尔迪厄发现,当某人社会地位一路上升的时候,他收入中食物开销所占的比例,会一路下降。或者在其食物开支中,消费在高脂肪食物,诸如通心粉、土豆、豆子、培根、猪肉,以及红酒一类食品上的费用,会有所下降。反之易消化、低脂肪食物,如牛肉、小牛肉、羊肉、羔羊肉,特别是新鲜水果和蔬菜上面的开支,会随之上升。这里面的差别就在于口味。所以领班的工资虽然普遍高于白领职员,他的口味或者说趣味,还是“大众”的工人阶级趣味,反之白领们的口味大异其趣,比较接近教师们的口味。布尔迪厄这里的意思是,当我们高谈趣味判断无标准、非功利的时候,不要忘了,其实它是来源于生活的必然。
趣味一旦同必需结缘,布尔迪厄指出,那只能是生活方式“本身”的基础所在。换言之,那趣味着实贫乏得可怜。一些人身上的荣耀标记,在另一些人身上就是耻辱。他引了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分工和工场手工业》一章中的这一段话:“正像耶和华的选民的额上写着他们是耶和华的财产一样,分工在工场手工业工人的身上打上了他们是资本的财产的烙印。”[2]进而指出,这里马克思所说的“烙印”,说到底也就是生活方式。正是在生活方式里,被剥夺阶级立马就暴露了自身。他们除了技术之外一无所有,而技术在讲究知识和风度的趣味市场里,一文不值。用流行的话说,他们是不懂得如何生活和休闲的人。他们的精力和财力大都耗在食物上面,面包、土豆、肥肉,偏爱高脂肪的油腻食品。吃得庸俗,喝得同样庸俗,比方说葡萄酒。舍不得在衣着和化妆品上面过多消费。至于休闲,他们会开着雷诺5和西姆卡1000这类平价汽车,假日里面一头扎进堵车大军出去远足,在高速公路边上野餐,在拥挤不堪的野营地支起帐篷,认真把文化产业工程师们预先设计好的休闲项目,逐一品尝过来。一切皆为事出必需,又属必然。
二 习性和趣味的不平等
那么,什么是“习性”? 布尔迪厄明确反对以想象力和理解力神秘结合来解释审美现象的康德美学,认为审美活动事实上不可能独立于外部世界的影响。但是人类的审美和文化活动是不是完全可以由阶级区分这类外部因素来加以说明,反过来将康德传统的主体意识一笔勾销?布尔迪厄的回答是否定的。他的“习性”(habitus)概念正是在这一背景上提出的。什么是习性?据布尔迪厄的解释,“习性”就是社会生活和个人情志双向作用下来,集聚在个体和群体身上的总体持久性情。它是特定的阶级与文化使然,涉及同一阶级共享的价值观念和生活体验。如布尔迪厄认为,工人阶级的习性说到底乃是生活必需资料匮乏的结果:
习性是由必然性构成的一种德行。这个基本命题在工人阶级身上表现得再清楚明白不过,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必然性包括这个词通常所指的全部含义,即是说,必需品不可避免地给剥夺一空。[1](P.372)
所以必然性逼迫之下产生的趣味,必然就是形似穷凶极恶的物质追求,它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性情,足以同革命的意愿声气相求。由是观之,社会阶级的界定,就不光取决于其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同样取决于“通常”联系着这一地位的阶级习性。布尔迪厄特别指出,“通常”这个词在这里,可是有着大量统计数据支持的。由此可见,“习性”概念的提出,可以说一方面是跳出了结构主义见物不见人的局限,一方面又避开了高扬主体,视艺术家为造物主的浪漫主义窠臼。
工人阶级的生活方式体现的是粗鄙习性,那么当代技术社会的中坚,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一代“技术”阶层,又当何论?布尔迪厄指出,同他们的长辈一样,这些年轻人阅读科学和技术著作,不过比较起来看,他们的趣味会分出一点给予哲学和诗歌。同长辈相似,他们也不是博物馆的常客,不过假若要去,他们通常会去现代艺术博物馆。这一倾向在出身中产和上层阶级的技术青年中,尤其明显。他们大都知道一大堆音乐家和作曲家的名字,醉心现代艺术和哲学,也经常造访影院。但是年轻一代技术阶层与其父辈,不论是原本就出身小资的小资也好,抑或从工人阶级当中脱颖而出的小资也好,最大的不同在布尔迪厄看来,还是在于他们的外表特征,即服饰和发型传达的符号信息。简言之,年轻一代接近学生风格,追逐时尚,张扬个性;他们的父辈则偏爱“稳重得体”,抑或“适合身份”的服饰,那正是事业有成的小资们的典型选择。
小资们的趣味应该是比较典型的艺术趣味。但是艺术趣味,同样也体现在商品上面。不同趣味的消费群体,可以决定商品的不同地位。对此布尔迪厄说:
根据人们的趣味来做选择,这也是一个鉴别商品的过程。商品客观上是跟人们的社会地位同步的,它们“并肩而行”,因为它们在各自的空间里面,大体是处在相同的位置,不论电影还是戏剧,卡通还是小说,服饰或者家具,选择总是由机制来帮助完成的——商店、剧院(左岸抑或右岸)、批评家、报纸、杂志——它们本身是根据其在一个特定领域中的地位,来得到定义的。而这个领域的确定,依据的又是相似的原则。[1](P.233)
即便如此,布尔迪厄表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实际上也是无所不在,涵盖了文化实践和符号表征的所有领域,包括衣着、体育、饮食、音乐、文学、艺术等等一应各方各面的趣味偏好。这里的关键词还是“趣味”。虽然,艺术和文化消费本身并不生产阶级不平等,但是社会主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正是在文化和艺术的消费中彰显出自己的阶级符号,故而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完成了社会秩序的再生产。这一点上布尔迪厄应有似于福柯,视权力无所不在渗透到认知表达的每一个角落,即便是想当然甚至天衣无缝的观念,背后也是潜藏着视而不见的权力阴谋。虽然,在布尔迪厄看来,这无孔不入的权力计谋,更多地同经济和政治力量纠结在一起,故此是更多地在出演一种趣味不平等的合法化功能。
《区隔》中布尔迪厄引了马克思的这一段话:
人类首先被看作是私有财产的拥有者,即是说,一个排他性的拥有者,他的排他性的所有权一方面使他保有了他的个性,一方面也使他与其他人分别开来,同时也联系起来……私有财产是人类个人的、独特的,从而也是本质的存在。[3]
对此布尔迪厄的评价是,占有绘画这样的艺术作品,即具有物质形式的符号对象,就是肯定自己是对象独一无二的拥有者。与此同时,肯定自己排他性地拥有对象权威趣味的判断资质,由此转化为一种具体否定,否定一切不足以拥有这件作品的人,他们或者是财力不够,或者是品味不足,或者纯然是缺乏倾家荡产来获得它的强烈动机。文化和艺术作品的消费,由是观之,自然同样是缘起于这一类自由财产的绝对拥有欲望。
三 艺术的场
由此我们可以来看布尔迪厄的艺术观念。言及艺术与文化的关系,布尔迪厄指出,如果你仔细“阅读”一件艺术作品,就会发现,艺术品的消费不过是制码和解码复杂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故观看(voir)的能力,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也就是知识(savoir)的一种功能。艺术作品只有对于那些具有文化底蕴,懂得怎样制码和解码的人,才有意义。无论是绘画还是音乐,一个时代、一个流派、一位艺术家的特定风格,充分的专门知识积累,是审美快感的必要条件。否则,所见所闻不过是色彩、线条、声音和节奏的大杂烩而已。这意味着同艺术作品的相遇,并非想当然的那种“一见钟情”,而是一种移情的过程,这个过程中的认知能力,保证了解码活动的顺利展开,惟其如此,我们才能得到审美快感。
由此可见,布尔迪厄的理论中,艺术和社会生活的其他符号层面一样,难分难解地交织着我们生存的物质条件,两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能分隔成彼此对立的两元。他本人的一个核心概念“场”(champ),也正是基于这一认知提出的。据他解释,一切社会结构的形成,都取决于一系列场域的等级组合,诸如经济场、教育场、文化场、政治场等,其中每一个场域都有自己的功能法则,以及与其他场域之间的独特关系。换言之,除了经济和政治这两个基础场域本身之外,每一个场域既有独立于政治和经济的自足性,又具有与其他场域同源同构的相似性,虽然它们等阶高低各不相同。布尔迪厄在他的《福楼拜与法国文学场》一文中,给他的“场”下过这样一个定义:
我说的“场”是什么意思?我使用这个术语,是说一个场域就是一个分离出来的社会宇宙,它具有自身的独立于政治和经济的功能法则。作家的生存无论在实际上还是在观念上,与作为一个自足宇宙,被赋予评价行为和作品特殊原则的文学场的存在,是不可分割的。[4](P.163)
所以在布尔迪厄看来,理解福楼拜或波德莱尔,或者以及大大小小任何作家,首先就要去了解作者是处在什么样的社会条件之中,因为作家的创作与“文学场”游戏规则的不断更新,是难分难解地纠缠在一起的。但是反过来看,文学场和艺术场一样,它们越是遗世独立,就越是紧紧牵擎着社会结构中无所不在的经济和政治游戏,诚如布尔迪厄本人所言:
文学和艺术场的特殊性在于这一事实,那就是它越是自足,即是说,越是彻底完全履行它作为一个场域的自身逻辑,就越是趋向于搁置抑或颠倒无所不在的等级原则。但与此同时,不管它独立到什么程度,它依然受制于经济和政治利润的相关法则,后者是始终包围着它的场域。[4](P.39)
故而以文学和艺术场为例,根据布尔迪厄的演绎,我们可以发现它是处在权力场的框架里面,这导致文学和艺术再是呼吁独立自足,总还是跳不出以阶级关系为标志的那个更大的经济和政治场域。这就是场域“等级化”的含义。
就艺术作品而言,布尔迪厄指出,只要它们是被懂得如何鉴赏它们的受众根据社会惯例来认知和欣赏,那么它们就是符号的客体。故而文学和艺术的社会学,不能仅仅把它的研究对象看作物质生产,同时也必须视其为一种符号的生产,即是说,同时认可作品的信仰、意义和价值生产,由此被纳入研究视野的,不仅仅是作家和艺术家,同样也包括批评家、出版商、画廊经纪人等一系列中介,正是他们合力给消费者生产了艺术作品的认知和娱乐功能。这些中介当中,布尔迪厄最为看重的是教师和家庭。特别是家庭,布尔迪厄认为它在文化资本形成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我们一旦明白这一点,就不会简单将人的音乐和绘画才能,一股脑儿归结为教育之功。教育也是资本,但是教育资本说到底,依然是一种势必要依赖家庭背景的文化资本,因为孩子能够上什么学校,很大程度上也还是取决于他的家庭出身。
四 摄影的“大众美学”
布尔迪厄早在1965年就发表过论摄影的专述。他指出,传统认为摄影的功能就是记录,而不是阐释,其精确性和忠实性,都是无可置疑的。但是这里存在偏见,事实是摄影捕获的只是现实的一个图像侧面,而且是经过精心选择的,而对客体其他方方面面的许多特质,一概忽略不计。摄影历来以“真实”和“客观”著称,仿佛是一种记录客体的“自然语言”。布尔迪厄强调说,这是将摄影定位在模仿艺术上面,在更深层次上看,只有最天真的“现实主义者”,才会仅仅看重事物的外表真实,反之视而不见时时在定义客体社会功能的规范系统。
那么,什么是摄影中的“自然”?我们可以从姿势说起。摄影中讲究姿势。姿势的意义又是什么?对此布尔迪厄指出,姿势对于摄影而言,其意义只能在一个特定的符号系统中来加以理解。摄影一般拍摄人的正面像,对象站在照片当中,距离适中,表情严肃,保持静止状态。这一切说它什么都行,就是很难说是事出“自然”。特别是摄影师不时会上来纠正姿势,还要换上新衣服,摆好姿势不希望被人骚扰。这一切都足以说明,摄影中的姿势,其意义是尊重自己,同时也希望得到别人的尊重。但是尊重依然并不等于“自然”。布尔迪厄发现,事实是你越是让摄影对象“自然”一点,对象越是显得手足无措,“自然”不起来,因为他心里没底,不知道自己上不上相。所以最好的希望,也就是企达一种模拟的自然,类似戏剧里的造型。不仅如此,许多业余的摄影家,还不遗余力逼迫他们的模特儿扭姿作态,摆出“自然”姿势。这同样说明,“自然”其实是一个文化理论,捕捉“自然”,必先创造出“自然”来。
布尔迪厄认为,对于工人阶级来说,摄影的艺术价值就属于上述之天真的现实主义一类,比如巴黎的工人会说,这妞长得匀称,真是个美女,美女总是上镜。在布尔迪厄看来,这差不多就是呼应了两千多年前柏拉图《大希庇阿斯》中,诡辩学者希庇阿斯面对苏格拉底的诘问,信口开河回答美是什么,“我会告诉他美是什么,他一定驳不倒我!说实话,苏格拉底,美就是一个漂亮的姑娘”。由此来看工人阶级的大众摄影趣味,很显然与康德美学是适得其反。康德美学倡导“非功利”、“无目的”,但是工人阶级的大众摄影大都有相当明确的目的性——并不是一切对象都能入照。他们会说,“这玩意儿不能照”,“这哪像照片”,这当中的取舍标准,多为文化的和伦理的考量,同纯粹的审美趣味往往关系不大。针对康德美学非功利无利害原则,布尔迪厄指出:
与此相反,工人阶级期望每一幅图像都能确切无疑地实现某一种“功能”,但凡一个符号总能明确表达某一种道德规范,符合其相关判断的话。不管是赞扬还是谴责,他们的欣赏总是指向一个以伦理为其原则的规范系统。故此,一个士兵尸体的摄影可能引发的不同判断,其矛盾不过是表面现象,即仅见于他们的个人所好。[5](P.170)
布尔迪厄指出,比如他们会很干脆地说,这不美,我不喜欢。或者说,我从道德角度反对死尸的照片,这类题材除了职业军人谁都不会感兴趣。还会说,这是战争摄影,我热爱和平,我讨厌它。当然也有喜欢这张照片的人,他们也许会说,那是战争残酷的记录,适合用来做宣传。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由此布尔迪厄得出的结论是,这些互为冲突的不同判断,指向一种能指总是绝对服从所指的美学。这种美学在摄影中尤其如鱼得水,因为摄影作为一门图解和再现的艺术,可以还原到摄影者选择拍摄的对象上面,通过肯定或者否定的情感表达,来展示作品的道德内涵。所以,摄影指向的美学,绝非康德美学的非功利原则可以概括,因为它说到底还是社会性很强的“功能”美学。
如上文工人阶级这样,比照作品的道德内涵来做出判断,用布尔迪厄的术语来说,是属于“野蛮趣味”一类。因为他们总是孜孜以求一些客观原理,惟其如此,才能放心给出自己的充分判断。而这些客观原理的获得,似乎又非走进学堂接受教育,无从觅得。这样用普遍原理来包容个别的和特殊的审美趣味,只能说是在向正统文化献媚,从而反过来映照出自己在文化上的被剥夺状态。布尔迪厄说,此种“野蛮趣味”也是“大众美学”的趣味,摄影在阐释此种趣味和美学方面,可谓是得天独厚。
将摄影定位在阐释“大众美学”的典型艺术,这个判断是不是过分了?布尔迪厄对此的解释是,在一个特定的社会,一个特定的时刻,诸如戏剧、体育、演唱会、诗歌、室内乐、歌剧等等,并不是所有的文化产品都一样高贵体面,一样具有同等级意义的。换言之,以上各门各类文化和艺术形式,是根据一个独立于个人趣味的等阶组合起来的,在这个等阶的背后,矗立着正统文化的合法性。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对于正统文化圈子外部的艺术,消费者自可自由定夺,随心所欲给出自己的判断;反之身处正统文化领域内部,消费者就不得不小心翼翼,用一种仪式的态度,按照客观标准来做出判断。故此爵士乐、电影和摄影,由于它们本身对仪式无多要求,不幸就是徘徊在了正统文化门外。
基于这一认知,布尔迪厄将艺术分为三个门类:其一属于正统文化,它们是音乐、绘画、雕塑、文学和戏剧,那是学院派的领地;其二属于正在竞争进入正统文化的领域,它们是电影、摄影、爵士乐和餐厅歌曲,那是批评家和俱乐部的天地;其三是跟正统文化偶尔相关的门类,它们是时装、化妆品、室内装饰、烹饪、运动以及其他日常生活中的审美行为。具体而言,正统艺术无论是绘画、雕塑还是文学等,均由学院培育出了相关的理论体系,承担着经国济世或者心灵陶冶的神圣使命,不但要有兴趣,而且要有技巧。这都需要天长日久的方法训练。不过在布尔迪厄看来,学院垄断的结果,无非是殚精竭虑张扬它们合法权威的外部特征,这也导致教授们每每是言不由衷,看上去是众声喧哗,实际上是千篇一律,只是偶尔会论及一些半业余的团体,诸如爵士圈和电影俱乐部。
这样来看摄影,它是处在上述法理等阶的中段,介于“庸俗”和“高雅”趣味之间。既有大众市场,又有精英垂顾。这也反而使它的地位显得尴尬,特别是在特权阶层当中,怎样定位摄影常常使人为难。一些虔诚的拥趸处心积虑,意欲确立摄影的充分完全合法艺术地位,可到头来总是徒劳无功,这也说明社会上抵制摄影进入正统艺术的惯习,不容小觑。这样来看摄影的“大众美学”维度,说到底还是应当在社会之中来寻找根源。故此:
如上所述,对于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来说,摄影实践所表达的美学与摄影评论一样,是显示了一种“精神气质”(ethos)的维度,故而浩瀚无边的摄影作品,其美学就能在自身不被因此贬值的同时,合法地还原到生产了这些作品的集团,以及这些集团如何赋予作品以功能、授予作品以意义的社会学上面,显而易见的也好,特别是隐而不见的也好。[5](P.178)
这是说,摄影家孜孜矻矻建构自己的美学理论,力争在正统艺术中赢得一席之地的努力,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应当说布尔迪厄的上述判断我们并不陌生。就电影、摄影、爵士乐和餐厅歌曲这四种半个世纪之前布尔迪厄判定是在正统艺术边缘上游荡的艺术或者准艺术形式而言,电影以它第一等的拟像技术和受众趣味的突飞猛进,在我们今天这个图像和传媒时代里,早已成为正统艺术中舍我其谁的新贵;爵士乐一半成了怀旧的点缀,它的商业效果明显盖过了艺术效果;餐厅音乐似乎也看不出有多大长进。那么摄影呢?我们发现它的地位仍然是尴尬的。多年以前,国内一家著名媒体曾经开辟“摄影文学”周刊,虽然不过是四个版面一张精美印刷的报纸,可也连篇累牍,邀请文艺名家疲劳轰炸,期望效法当年莱辛《拉奥孔》中诗与画的辩证,通过与文学联姻,让画面开言复让故事定格,来力推摄影进军正统艺术。但是资金链一旦断裂,它马上悄无声息,无疾而终。这里面的因缘倒未必是布尔迪厄所说的摄影不够“仪式化”,事实是学院派再是有心在仪式化上做文章,没有电影这样雄厚的受众基础,以及引领时尚的先锋意识,任何一种新兴艺术修成圆满功德,又是谈何容易。这也再一次回到了摄影的“大众美学”的话题。
《区隔》的英译者理查·奈斯(Richard Nice)在其译序中指出,该书的形式是“非常法国化”的,即是说,文化生产的典型表达方式,总是取决于它产生于中的市场法则。这应是打破了知识世界的一个禁忌。但是,当《区隔》将知识产品及其生产者同它们的社会生存条件联系起来,说明它终究还是不敢忽视知识产权的法则,将曾经灵光萦绕的艺术,简单视作科学对象。盖言之,布尔迪厄是通过分门别类区隔阶级趣味,殚精竭虑来对康德判断力批判中留下来的老问题,做出科学主义的答复。问题是,当今天过于早熟的劳动分工将人类学与社会学分隔开来,进而又分出知识社会学、文化社会学,甚至饮食社会学、体育社会学等等,我们是不是更需要一种整体的,而不是支离破碎的人文关怀?换言之,背靠社会等级的区分来阐释趣味,是不是在走向有异于康德美学的另一种理性中心主义?
[1]Pierre Bourdieu.Distinction:ASocialCritiqueoftheJudgementofTaste[M]. Richard Nice tran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4.
[2]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399.
[3]Karl Marx. “ExceptsfromJamesMill’sElementsofPoliticalEconomy”inEarlyWritings[M].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4.266.
[4]Pierre Bourdieu.TheFieldofCulturalProduction:EssaysonArtandLiterature[M]. Randal Johns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5]Pierre Bourdieu. The Social Definition of Photography[C]//J. Evans, S. Hall.VisualCulture:TheReader. London: Sage, 2009.
OnBourdieu’sTheoryofArt
LU Ya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Bourdieu’sDistinction:ASocialCritiqueoftheJudgmentofTastecalls on scholars to walk into the kitchen and develop a basic aesthetic taste in the smell and color of food. This is not only a metaphor. Bourdieu concludes that the difference of life habit between the working class and the intellectual class leads to their different tastes for art, which is cognitively founded on the principle of taste inequality. Therefore, in terms of “popular aesthetics” in photography, though the academism artists intentionally focus on its ritualization, any new form of art, without a strong audience base and an avant-garde awareness of leading the trend, is difficult to succeed. Within the present context of increasingly refined social division of labour, what we need more is a holistic kind of humanistic concern, rather than a fragmented one.
Bourdieu;Distinction:ASocialCritiqueoftheJudgmentofTaste; field of art; aesthetics; Kant
2012-12-23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研究”(11BKS01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陆 扬(1953-),男,上海市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艺学和文化研究。
I0-05
A
1674-2338(2013)01-0062-06
(责任编辑吴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