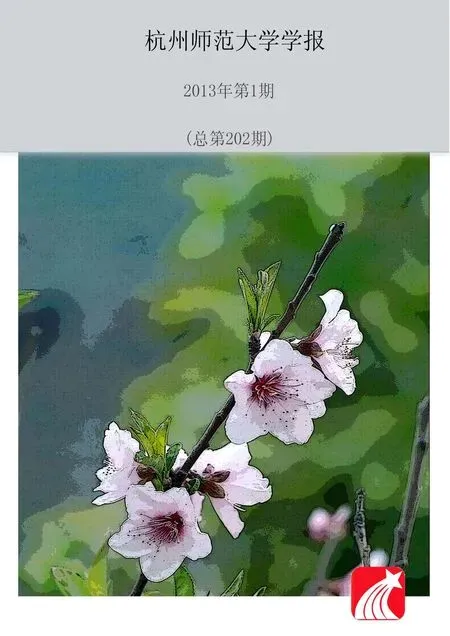光荣的毁灭:另类新闻人伊罗生
2013-04-13张威
张 威
(山东大学 威海环境新闻与国际传媒研究中心,山东 威海 264209)
光荣的毁灭:另类新闻人伊罗生
张 威
(山东大学 威海环境新闻与国际传媒研究中心,山东 威海 264209)
美国记者伊罗生在20世纪30年代上海中共宣传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 他是左翼刊物《中国论坛》的主编。由于与当时的中共领导在斯大林问题上的激烈争执,伊罗生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托洛斯基分子,有关他的研究也一直被视为禁区。新发现的史料证明,伊罗生当年只是一个具有左倾思想的对斯大林持批判态度的热血青年,他与托洛斯基没有任何组织上的关系。他的革命与宣传的辩证新闻思想在中国新闻发展中作出了积极贡献。
伊罗生(Harold R Isaacs);《中国论坛》;中国新闻史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来华采访的诸多美国记者中,伊罗生(Harold R Isaacs,1910-1986)*Harold R Isaacs的中译名还有艾萨克、艾萨克斯。也许并非出类拔萃之辈;在大陆出版的中国新闻史教科书里,他也多被忽视。然而这名被屏蔽多年的所谓“托洛斯基分子”在30年代上海中共宣传史上却占据着重要位置,他曾是左翼重要刊物《中国论坛》的主编。1938年,他的著作《中国革命的悲剧》[1]与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先后在伦敦出版,几乎同时吸引了国际中国学界的注意。然而,伊罗生没有斯诺那样的好运,这个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系的才子在中国的辉煌只有短暂的一瞬——他1930年来到上海,1934年离开北平返回美国,1944年再次以记者身份到重庆采访,最后被国民党政府驱除出境。*1944年,伊罗生以美国《新闻周刊》记者身份到中国采访,在重庆曾采访蒋介石与美国史迪威将军事件,遭官方检扣。伊罗生曾发电报要求美国政府出面干涉。1945年2月前后,董显光领导的国际宣传处吊销了一些美国记者的执照,对伊罗生作出“暂停发电”的处分,伊罗生随后回国。见国际宣传处关于美国记者在华活动的往来文函,南京:第二档案馆。1980年,当伊罗生几乎被忘却的时候,在老友宋庆龄的邀请下,他重返中国。而在此之前,他是被排斥的“对中国不友好”的美国记者,在与鲁迅、宋庆龄的合影中,他的形象甚至被删除,个中原因,大多在于他的特立独行,以及他与30年代中共领导人在斯大林问题上的激烈争执。
在《中国论坛》事件50年后,研究伊罗生的禁区被打开了,他的面目开始清晰起来。伊罗生本人、他的同时代人以及他的研究者都对过去的历史进行了种种描述。一些敏感的仍在考证的问题集中在如下方面:伊罗生是共产党员吗?他是托洛斯基分子吗?他在《中国论坛》事件上扮演什么角色以及他在中共早期革命宣传方面占据何种地位?
伊罗生与当时中共领导人的冲突集中在革命宣传的真实性问题上,在冲突的高峰期,后者要求前者在《中国论坛》上发表拥戴斯大林的文章,但被拒绝,伊罗生由此被解职,也同中共彻底决裂。作为一个共产主义革命的狂热追求者,伊罗生的理想和现实、新闻道德和革命事业发生了严重的冲突。
伊罗生是一个独立思考的另类新闻人。在中国新闻史上,这类新闻人偶尔浮现,比如储安平和萧乾,但在战争年代来华的美国记者中,伊罗生却是绝无仅有的一例。
寻求理想和进入中共视野
1930年年末,20岁的伊罗生初到上海,这时的他并无鲜明的政治倾向。和斯诺不同,他并非为工作而来;和史沫特莱也不同,他并非为推行某种政治事业而来。作为曼哈顿地产富商的儿子*兰德的著作China Hands被李辉、应红译出,更名为《走进中国》,其中说伊罗生是“曼哈顿西区上流社会的孩子”(见该书78页),有误,对照原文:“a child of the Upper West Side of Manhattan”,其中的“Upper”并非指上流社会而是指曼哈顿上西区,介于中央公园和哈德逊河之间,第59大道西大街以北。参见Peter Rand原书,第81页。,伊罗生衣食之虞。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时曾研究过中国历史,也在《纽约时报》当过实习记者,到中国来无非是想增加一些采访经验。当然,作为那个时代的激进青年,他崇拜社会主义,尤其欣赏诺门·托玛斯(Norman Mattoon Thomas ,1884-1968)*诺门·托玛斯,美国著名的社会主义运动领导人,在20世纪20年代曾三次任纽约市长,是著名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他也崇拜一些具有反帝国主义倾向的记者,如密勒(Thomas Millard,1868-1942)、佩佛(Nathaniel Peffer,1890-1964)、摩尔(Parker Moon,1892-1936) 等。[2](P.91)*密勒是近代著名美国记者,曾在上海创刊《密勒氏评论报》,被誉为“中国的美国新闻之父”,为民国政府首位美国顾问。佩佛为近代美国著名记者,《纽约论坛报》驻远东记者,在中国逗留了25年。摩尔时为哥伦比亚大学助理教授、《政治科学季刊》主编,有许多反帝国主义的著述。到上海不久,他先后在《大美晚报》(ShanghaiEveningPost&Mercury)和《大陆报》(ChinaPress)任记者。他的同学、同样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的董显光当时在《大陆报》任主编,两人相处融洽。但是董并没有留住伊罗生,后者觉得上海憋气,工作也很沉闷。他很瞧不起那些美国记者,说他们是“庸常之辈”。[2](P.95)4个月后,伊罗生从《大陆报》辞职,准备和他新认识的朋友格拉斯(Frank Glass )去遨游长江。
然而,伊罗生离开《大陆报》的真正原因是,他在短暂的上海期间,认识了一些左翼分子,其中包括中国历史学家陈翰笙、美国记者史沫特莱以及美国托派组织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格拉斯。这些人的激进思想深深影响了他。当时,史沫特莱是上海西人圈子中的核心人物,她曾为宋庆龄工作,这使她能将一批西方人特别是新闻记者引荐给宋庆龄,其中包括斯诺、海伦、艾黎、格拉斯和伊罗生。 关于史沫特莱的影响,伊罗生在30年代给他未婚妻维奥拉的信中有所表白,他说他结识的史沫特莱是一个“著名的燃烧的女共产党人”,经常给他发一些政治宣传品。[2](P.87)
有关伊罗生卷入《中国论坛》的细节尚待发掘,但多种史料表明,当时,宋庆龄等人正想在法租界办一个左翼刊物,以发出反对国民党右派的声音。宋希望刊物的主编由外国人担任,这是因为外国人在中国享受特权,可以避免当局的某些迫害。但这个主编不可能由激进的带有共产国际特殊使命的史沫特莱一类人担任。伊罗生适时地出现在他们的视野中。很可能史沫特莱和格拉斯早就看中了伊罗生。格拉斯回忆说,他和史沫特莱曾约伊罗生去上海惠中饭店(Palace Hotel)喝茶:
我们谈了很长时间,他(伊罗生)富于冒险精神,机敏的头脑,很强的理解力,是个好记者,好的观察家。但他头脑里没有任何原则。他是个小资产阶级的大学生。尚未成熟但具有很强的信念。史沫特莱问伊罗生:“你对自己怎样看?你有什么动机?有什么目的?你的立场是什么?”他回答说:“我没什么主义。”她说:“我会给你一个主义。”她真的这样做了。[2](P.88)
史沫特莱精心安排了“革命的同情者”伊罗生与宋庆龄会面,使他得以顺利掌管《中国论坛》,[3](PP.60-61)这个激进分子对20岁的伊罗生的冲击是巨大的,在短暂的时间里,史沫特莱令这个曼哈顿地产商之子对她推行的共产主义充满敬仰,伊罗生说:
我接受了一种新影响,它刺激着我进一步发展,其中的某些动力是史沫特莱,她唤起了我精神中的某些尚未发挥出来的部分。[2](P.87)
在这次谈话的两星期后,伊罗生和格拉斯开始了长江之旅。出发前史沫特莱还特地为他们壮行。在旅途中,两位青年耳闻目睹了中国的悲惨现实。伊罗生感触颇深。比他大15岁的格拉斯更为成熟,他告诉伊罗生要怀疑一切,不要轻信任何教条,与此同时,他也给伊罗生灌输了反斯大林的思想。
与格拉斯的交往和这次旅行给伊罗生带来了根本的变化,他回忆说:
我相信我已结束了盲目的生活,这种变化只因格拉斯简单的一句话……“你不可能骑在篱笆上,你不可能永远是一个旁观者。”[2](P.93)
我不能再徘徊了。我谈得太多了,我必须行动。我要抛弃中立,不当寄生虫,不当空谈的赤色分子。[2](PP.93-94)
现在不是我怎样生活,而是怎样投身于历史……在上海,这是投身于这个戏剧化的时代的机遇。[3](P.13)
在谈到他最终卷入《中国论坛》时,伊罗生提到了自己的心境:
那些暴露、耸人听闻、惊讶和遭遇,在那乱哄哄的几个月中的所见所闻向我冲来。当我在上海见到的那些共产党朋友提出我应当办一份自己的报纸时,我欣然同意了。[3](P.13)
一个富有争辩性的问题是伊罗生当时的身份,他究竟是否为美国共产党员,是否为美国共产党派来支援中国革命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唐宝林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说:
1930年,两个美国人先后来到中国。哈洛特·伊萨克,中文名字叫伊罗生,1910年出生于纽约的一个犹太人家庭,美国共产党员,1930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在《檀香山广告报》任职……[4](P.104)
与伊罗生当年在上海相熟的夏衍也说“他(伊罗生)是美国共产党派来的,同情中国革命……”[5](PP.267-268)
夏衍没有提出证据。唐宝林的根据来自于原中国托派中央委员王凡西(1907-2002)*王凡西,中国托派领导人之一,著有《双山文集》,20世纪40年代后一直流亡海外,逝于伦敦。,而王的说法是从哈佛大学图书馆保存的“托洛斯基档案”中获得的。[4](P.104)上述人均未展现原档的风貌,而伊罗生本人则斩钉截铁地加以否定。1980年伊罗生访问中国时,翻译何滨曾问伊罗生当年在上海时是不是共产党员,伊罗生毫不犹豫地说:“不是。”[6](P.54)20世纪90年代初,俄罗斯档案馆对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一些历史档案解密,这使人们能窥探当年的某些秘密。共产国际执委会驻中国代表米尔顿·赖安在《关于艾萨克斯的书面报告》中指出:艾萨克斯1931年出现在上海,“据我所知,他当时还不是共产党或者法国共产党党员”。[7](P.249)*《赖安关于艾萨克斯的书面报告》,1936年9月7日于莫斯科,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5卷。值得指出的是,上述文献资料的初始编者——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研究员认为,“艾萨克斯曾是美国共产党员”,但没有说明证据。
关于伊罗生卷入《中国论坛》的内情, 赖安说:“艾萨克斯是通过宋庆龄参加《中国论坛》出版工作的,作为《中国论坛》的编辑,这个美国人可以更好地为中国共产党所需要的杂志提供‘保护’。他也因此从党那里领到了出版和印刷《中国论坛》的津贴。”[7](P.249)但是共产党并没有资助伊罗生本人,他当时在法国哈瓦斯通讯社任翻译,他能养活自己,并因能保持“独立”而感到骄傲。[3](P.13)
伊罗生在1980年访华时直率地表明,他编《中国论坛》是共产国际的安排,他之所以能以非党员的身份编辑这份共产国际的杂志是由于“史沫特莱的介绍”。[6](P.54)共产国际有关文件也证明了《中国论坛》多次得到该组织的资助。[8](P.135)*1932年4月,共产国际同意资助《中国论坛》500美元,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第234号记录》,1932年4月9日。王明和康生1934年4月9日起草的《关于〈中国论坛〉性质的建议》指出,该刊“应与中共中央局有联系并由该局领导,但它不应具有公开的共产主义性质,而按其方针应该是反帝反法西斯的刊物”。[8](P.115)*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第368号记录》,1934年4月11日,莫斯科。
除了史沫特莱和格拉斯,宋庆龄对伊罗生卷入《中国论坛》也起到了关键作用。伊罗生不仅仰慕宋庆龄,甚至还暗恋过这位美丽高贵的孙夫人。[3](P.71)*伊罗生在他的《重返中国》中提到了他对宋庆龄的一往情深。1980年,他在北京受到了宋庆龄的款待,临走时,伊罗生向宋鞠躬说:“知道吗,有一件事我一直保留并珍视,从上海的岁月至今,是我对你的爱。”宋庆龄用一种看不懂的表情望着他,半闭着眼睛,用柔软而略带沙哑的声音说:“我很荣幸。”见Harold R. Isaaces, Re-encounters in China,p.71。宋庆龄在保持矜持的同时,对伊罗生表示欣赏和信任。[7](P.249)*据赖安说,宋庆龄对伊罗生曾有过怀疑,赖安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上说:“关于艾萨克斯不可靠的最初警告是来自宋庆龄,她曾详细地把她同艾萨克斯的谈话告诉了我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从这些谈话中可以看出,他在努力用托洛斯基的思想说服她。”见《赖安关于艾萨克斯的书面报告》。她不仅首肯伊罗生任主编,而且将他发展成为中国人权保障同盟组织里的中坚分子,委以重任,在伊罗生与中共发生冲突后,宋对他仍然关心信任。[3](P.66)*据伊罗生回忆,《中国论坛》事件后,他曾去向宋庆龄告别,宋对他说要“小心那些共产党,他们什么都做得出来”。见Harold R. Isaacs, Re-encounters in China, p.66。1980年,宋庆龄力排众议,邀请伊罗生访华并设家宴招待,这都表明建立在30年代的信赖和友谊在二人之间仍不断延续。
革命与真实
《中国论坛》在中共早期宣传史上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在1927年“四·一二”大屠杀后,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国统区的革命刊物几乎销声匿迹,唯《中国论坛》独树一帜,仍然坚持发出反对派的声音。尽管年轻的无党派人士伊罗生崇尚共产主义,希望帮助共产国际、中共以及中国革命,但他仍然保持着独立的立场,并以此为荣,他在《中国论坛》发刊词上说:
《中国论坛》全然不是任何政党或团体的喉舌……它将是在中国发表受到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国民党的报纸压制、漠视、歪曲的消息和言论的载体。*The China Forum, January 13,1932.该宣言还宣称:“中国与其他动摇的世界一起为生存而斗争……在这些斗争的每个环节,蓄意或制造的欺骗、歪曲、删改是整个中国报刊——外语或中文——的特点。那些具有话语权的人统治了新闻界,其他的声音被压制或被迫改变。《中国论坛》不采取虚幻的中立。在一个垂死的制度和新生力量的冲突间没有倾向性是傻瓜、骗子或他们的三位一体。《中国论坛》是发表新闻和意见的载体,因为新闻和意见目前没有发表的阵地,一些版本无法刊登。《中国论坛》要冲破谎言、歪曲和噤言。”
《中国论坛》最初出版为8页英文小报,后来以中英两种文字出版,刊登新闻与评论,主要报道中国学生运动、苏维埃地区以及白色恐怖的消息,并反映工人的呼声。*关于《中国论坛》的内容介绍,见Harold R. Isaacs, Re-Encounter in China,p.30。1932年1月13日出版的首期以 “五名年轻作家被国民党屠杀”为通栏标题,其下刊登了左联五烈士的消息和他们的照片,以及各界人士抗议国民党暴行的消息。第二期刊登的是胡也频和其他进步作家的短篇小说英译。第三期 (1932年1月28日)为日军进犯上海闸北的消息。在该刊存续的一年中,伊罗生开辟“观察家”专栏,请史沫特莱、陈翰笙等人撰稿,还刊登了鲁迅、丁玲、茅盾等进步作家的作品。1932年5月,《中国论坛》出版了一期特刊,标题为“国民党反动的5年”。
《中国论坛》上的文章,很多内容是关于中国监狱的状况、政治犯、非法审判、大屠杀和流放的报道,比如,遭受国民党独裁政权迫害的丁玲、被杀害的柔石等“左联”五烈士,以及国际著名民主人士牛兰夫妇(Noulenses)事件*牛兰夫妇是20世纪30年代共产国际与中共的联络人,当时以国际民主人士身份出现。及其反响,这些都是《中国论坛》上的热点。消息来源大多出自中共地下党员。这些人在街头小巷与伊罗生见面,向他传递消息。伊罗生从不知道这些人是谁,他与党的地下组织不直接打交道,甚至不知道共同执笔“观察家”专栏的陈翰笙是一名共产国际的成员(与后面对陈的介绍有矛盾)。上海的共产国际代表通过通讯员与他联系,这些人的真实姓名对伊罗生也是保密的。这种隐秘的工作性质,反倒进一步激起了伊罗生的兴趣。
由于刊载异见和一些被国民党当局封锁的消息,《中国论坛》曾发行到3000多份,产生了较强的影响。就连最后反对该刊方针的《红旗》也承认:该报“各地有代表处,且有‘读联会’的组织”,“能够在青年获得影响”,因为“广大群众的拥护和革命团体的帮助,(它)逐渐成了群众刊物”。[9]《中国论坛》将国民党的白色恐怖、迫害革命者和进步人士的情况采写成英文消息,影响了国际友人和西方世界,欧美有影响的民主人士爱因斯坦、肖伯纳、罗曼·罗兰曾根据这些消息在致国民党的抗议信上签字,形成了对国民党政府具有威胁的国际舆论。
在《中国论坛》取得成就的同时,共产国际和中共开始加强其控制影响。这对具有自由主义独立思想的伊罗生来说是一个挑战。1932年10月,一度为中共总书记的陈独秀被国民党逮捕。陈此时已经成为中共左派的反对派,他正面临中共和国民党的双重打击。1933年,中共中央苏区机关报发表文章对陈独秀的被捕讽刺挖苦,并要求《中国论坛》也如法炮制,但遭到伊罗生的拒绝。他在1934年5月写就的《我与中国斯大林分子决裂》中对曾经领导过他的某要人说:
当你要我书写并发表一个对陈独秀的诽谤性攻击的时候,我低调地拒绝了。陈当时被国民党判处13年监禁。你的要求是具体的。我不想谈陈独秀怎样从1927年中共的领导人变成1933年中国反对党领导人,我只打算将那些卑鄙的罪名串在一起,去解释为什么国民党甚至去监禁左翼的领导人。正如你所知道的,我从未写过或发表过这篇攻击性文章。[10](PP.76-78)
在这篇公开声明中,伊罗生没有明确指出“你”的身份,但根据当时的情况,这个“你”很可能是指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上海远东局书记埃韦特。
1933年11月,福建事变爆发,伊罗生前往实地采访,但中共左倾领导人不准伊罗生发表他据实采写的文章,而要根据党的口径来描写,遭伊罗生再次拒绝,他指出:
你要求我……代你写一篇对左翼反对派毫无根据的诽谤性攻击文章……你指责在福建,在陈铭枢和蔡廷锴组建的新政府中,存在明显的托洛斯基派……要求我将年轻的激进分子之一胡秋原写成一个托洛斯基派的领导者……我左右为难,要么按你的要求去写一个符合你要求的谎话,要么按我的愿望将左翼对福建政权的真实态度写进去。考虑再三,为了防止我们的关系破裂,我采取了折衷的态度,两者都不写……[10](PP.76-78)
还有一些事情令伊罗生反感,那就是为了政治目的而无视现实,任意编造,比如他曾被某领导要求将1月发生的工人罢工改到2月,夸大参加罢工的人数和工人的政治觉悟等。他理所应当地拒绝刊登此类消息。在对共产国际的态度、歌颂苏联的建设成就以及对斯大林的宣传方面,伊罗生与中共领导的矛盾逐渐加深,最后终于决裂。在1933年11月俄国社会主义革命16年纪念日时,伊罗生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没有提到“我们伟大的、敬爱的领袖斯大林”,于是,伊罗生被叫去谈话,并被勒令发表一篇补偿文章赞颂斯大林。伊罗生拒绝了。[3](P.31)他说:
我必须拒绝那些令人恶心的奉承斯大林的言语,以及对斯大林政策不加批评的全盘接受,这是世界共产党报刊的特点……这与国际共产主义的早期传统和感人至深的正面形象大相径庭……我必须拒绝,简言之,我不能以革命的名义做一个妓男。[10](PP.76-78)
伊罗生与共产国际、中共的矛盾逐渐升级,以至周恩来出面批评伊罗生。[4](P.113)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发表文章指责伊罗生利用《中国论坛》偷运托洛斯基主义,文章说:“揭破《中国论坛》上托洛斯基的观点,反对伊罗生的一切阴谋,坚决纠正《中国论坛》上的一切错误,彻底改造它,使它成为真正的革命刊物……”[9]
伊罗生明确表示了自己的立场:要么按既定风格继续出版刊物,允许他发表不同意见;要么全面开放专栏,自由讨论;要么主要发表中共的新闻和观点,但保留他的批评权利。[10](P.77)
伊罗生的同情者和支持者格拉斯立即将《中国论坛》濒临危机的消息通知了在挪威避难的托洛斯基,后者建议他们以左派反对派的精神出版一期战斗性的休刊号,来一个“光荣的死亡”。*“Trotsky to Frank Glass”, 29 January, 1934, Trotsky Papers Cataloging Records (MS Russ 13.11), Houghton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然而托洛斯基的建议尚未抵达(上海)时,《中国论坛》就已经停刊了,时间是1934年1月13日。这个短命的刊物存活了2年,共出版39期。伊罗生回忆道:
所有的支持突然间被收回了,就连对那些为本刊工作的勇敢的年轻同志——他们冒着风险翻译和发行本刊——连道声再见的机会都没有。我从来都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包括那个对我有特别帮助的人,我们一起工作和生活了好几个月。他握着我的手,泪流满面,他对我说再见,还说:“我绝不相信你是反革命!”[2](P.31)
《中国论坛》的突然停刊令共产国际非常恼火。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上海远东局书记埃韦特在1、2月间两次致电莫斯科,声称《中国论坛》需要继续办下去,需要编辑,要正在那里写书的史沫特莱立即赶赴中国。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决定责成王明和米夫研究出编辑部名单,随后决定派史沫特莱去中国任主编,但这个计划最后未能完成。[11](P.104)史沫特莱对格拉斯和伊罗生的托洛斯基倾向极为愤怒,她甚至在报纸上公开指责伊罗生是“帝国主义间谍”。[2](P.31)
既然伊罗生在《中国论坛》的出版宣言中表明自己要“冲破谎言、歪曲和噤言”,那么他就不能不身体力行。1934年3月,他告别上海,来到北平,开始了《中国革命的悲剧》的写作。临走前夕,鲁迅为他设宴饯行。*伊罗生事后才领悟鲁迅送行的意义:“这件小事之所以重要,乃是因为它让我们看到鲁迅是怎样的一个人。当时……我已经停止和所有的共产党朋友往来,他们也不再理睬我,也就是说断绝了一切个人关系。然而,尽管鲁迅当时很接近在上海的共产党员,……但还是如此礼遇于我……这样一个小小友谊行为其实有很重的政治和个人行为分量。”参见Harold R. Isaacs, Re-Encounters in China,pp.115-116。
结 语
许多人认为伊罗生是托派分子。其中的一个例证是当年中国托派领导人王凡西,他在《双山回忆录》中说“由于中共要他写文章攻击陈独秀,并且供给他一些虚拟的材料,要他诬蔑中国托派,使他发生反感,并逼他变成了托派”。[12](P.54)另一个例证是托洛斯基曾给伊罗生所著《中国革命的悲剧》撰写序言。但是伊罗生本人完全否认自己是托派,而且最恨别人说他是托派。[12](P.52)兰德认为,至少在编辑《中国论坛》期间,伊罗生没有受到托派的影响,因为当时中国的托派分子正在被监禁。但是,兰德倾向于同意这种观点——是“中共让伊罗生发表批判托派的文章,遭到拒绝后,使伊罗生站到了托派的阵营”。
伊罗生在回忆录中说,1930年他到了中国后,由于史沫特莱和格拉斯的推荐,他开始关注马列主义,其中也包括斯大林主义和他的反对派托洛斯基主义。但若干年后,当他系统地研究共产主义的历史之后,他对斯大林主义和托洛斯基主义统统采取了排斥的态度,并不惜与格拉斯决裂。[2](P.29)1950年,当《中国革命的悲剧》再版时,伊罗生撤下了托洛斯基写的序言。
伊罗生受过托洛斯基影响是毫无疑问的。但显然,他接受托洛斯基思想是因为其中有他认为可贵的东西,即托洛茨基象征的是那种还有思想和理想活力的革命,它的对立面斯大林主义,就是败死的革命,是腐败的权力、专制和暴政。[13](PP.161-274)伊罗生根据自己的观察,一直认为斯大林的瞎指挥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损失,为了寻找证据——斯大林有关中国问题的一篇讲话,他曾执着地在英国、美国的图书馆搜寻,终于查到了那个斯大林企图销毁的文件。[2](PP.127-131)
伊罗生回到美国后成为著名的《新闻周刊》(NewsWeek)记者,他于1944年重返中国,曾试图加入美国记者西北访问团,采访革命圣地延安,结果被中共拒绝。由于他的历史问题以及报道中的进步倾向,他于1945年被国民党驱逐出境。伊罗生在50年代成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国际问题研究员,之后,他曾多次尝试访问中国,但均被中国官方回绝。1974年,宋庆龄曾提出邀请伊罗生访华,却被一个“比她更有权势的人”告知“伊罗生是叛徒,不应当邀请他来”。[3](P.41)直到改革开放后的1980年,当许多历史问题平反后,伊罗生才得以重返中国。
在生命中最后一次对中国的访问中,伊罗生又发现了“假新闻”。这个“假新闻”是1933年肖伯纳访华时的一张合影,背景为宋庆龄上海寓所花园,其中有史沫特莱、肖伯纳、宋庆龄、伊罗生、蔡元培、林语堂和鲁迅共7人。令伊罗生不解的是,在英文版《中国文学》刊登的照片上,他和林语堂的形象消失了。伊罗生一下就悟到了其中的玄机:他和林语堂被认为是问题人物,被删掉了。伊罗生写道:
我凝视着这张照片, 它的冲击强烈而缓慢。许多事情已使这次旅行处于一个时间容器中,我的重返中国跨越了广阔人生的间隔……在我面前的这张照片里,我23岁的形象不见了,一起逝去的还有我的青春,在这,70岁的我,凝视着那片虚空,我知道对于我从前的朋友而言,我确实早已不复存在了……[3](PP.128-132)
在那个变革的时代,“真实性”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正同时在中国接受反省。伊罗生访问上海鲁迅纪念馆时,在纪念馆的墙上再次见到那张未经篡改的肖伯纳访华照片,照片上面有他和林语堂等共7人,但照片说明却写道:史沫特莱、肖伯纳、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伊罗生写道,上海鲁迅博物馆接待人员曾与他一起合影,他要求在照片背面注明所有人的名字,而“不是‘某某等’”。在场的人发出一阵“会心的大笑”。 若干年后,这张照片已在各出版物中以原有风貌发表,并附有合影的全部人名,包括“美国记者伊罗生”的字样。见Harold R. Isaacs, Re-Encounters in China,pp.128-133。——他的名字还是被删掉了。
自1980年中国之行后直到他逝世,伊罗生没有再访问中国。在中国新闻界,他似乎是一个被淡忘的美国记者。然而,伊罗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新闻实践以及他对“宣传”与“真实性”的质询和挑战确立了他在中国新闻史上的独特地位,他倡导的“宣传也要讲求事实”的观点已在今天的中国得到了充分认可。
[1]Harold R. Isaacs.TheTragedyoftheChineseRevolution[M]. London: Secker & Warburg,1938.
[2]Peter Rand.ChinaHands,TheAdventuresandOrdealsoftheAmericanJournalistsWhoJointedForceswiththeGreatChineseRevolution[M].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1995.
[3]Harold R. Isaacs.Re-encountersinChina:NotesofaJourneyinatimeCapsule[M]. New York: M.E.Sharpe,Inc.1985.
[4]唐宝林.伊罗生与中国论坛[J].近代史研究,1995,(6).
[5]夏衍.懒寻旧梦录[M].北京:三联书店,1985.
[6]黎辛.我常想起伊罗生[J].百年潮,2001,(8).
[7]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5卷[G].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
[8]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3卷[G].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
[9]坚决反对《中国论坛》上偷运反革命托洛斯基主义私货(提纲)[J].红旗周报,1934,64.
[10]Harold R. Isaacs. I Break with the Chinese Stalinists[J].NewInternational,1934.
[1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4卷[G].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
[12]徐贲.红潮往事:告别“党人革命”[M]//在傻子和英雄之间.广州:花城出版社,2010.
GonewithGlorious:HaroldR.Isaacs,aUniqueJournalist
ZHANG Wei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Shandong University at Weihai, Weihai 264209, China)
Harold R. Isaacs, an American journalist, takes a unique position in the publicity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Shanghai during the 1930s. He was the chief editor of theChinaForum, a left wing periodical. Isaacs was announced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s an unwelcome Trotskyist due to their disputes on the Stalin issues. Studies on Isaacs have remained as a taboo. This paper discusses Isaacs’ background and his journalism thought on revolution and propaganda which is regarded as a valuable contribution towards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journalism.
Harold R Isaacs; theChinaForum; Chinese journalism history
2011-09-20
张 威(1954-),男,湖南长沙人,山东大学威海环境新闻与国际传媒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G214.2
A
1674-2338(2013)01-0119-07
(责任编辑吴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