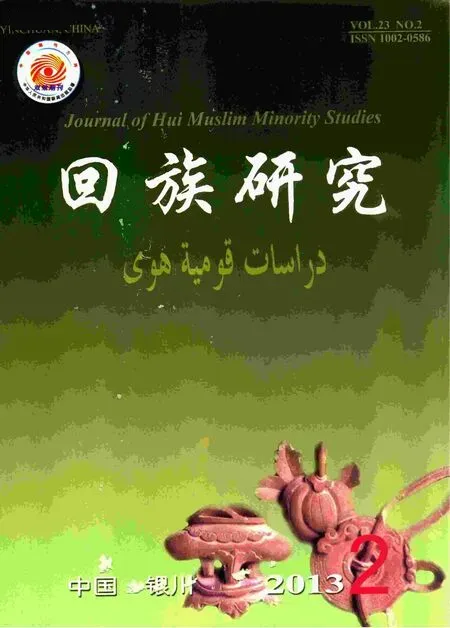明代宦官与清真寺
2013-04-12丁慧倩
丁慧倩
(中央民族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北京100081)
学术界对明代宦官社会活动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他们的佛教信仰及其创建、参修的各种寺庙,如何孝荣、程恭让和台湾学者陈玉女等人的研究①,集中讨论了宦官崇信佛教的原因、兴建寺院的活动,以及宦官群体的加入对北京佛教发展的影响。赵世瑜《黑山会的故事:明清宦官政治与民间社会》一文则从社会史的角度探讨了明清京师宦官与京师民间社会的关系②。上述研究涉及了宫廷、宦官与民间社会,将明代宦官的探讨引向社会史的研究方向。
在明代宦官参修的各种庙宇中,清真寺是较为特殊的一种。伊斯兰的信仰通常与固定的人群相结合,其社会影响力辐射特定的范围。本文将从清真寺碑刻入手,对宦官参修清真寺的原因、目的及宦官与清真寺的关系作初步的讨论。
一
明代宦官参与修建清真寺的活动始见于南京。据宣德五年(1430年)七月《敕郑和重建礼拜寺》记载,郑和因南京城内三山街礼拜寺被焚,“欲要重新盖造”,宣德皇帝以为“尔为朝廷远使,既已发心,岂废尔愿,恐尔所用人匠及材料等项不敷,临期误尔工程,可于南京内官监或工部支取应用,乃可完备,以候风信开船”③。郑和重修的三山街礼拜寺即净觉寺,创建于洪武年间,其创建的历史与明初安置归附回回人有直接的关系。据弘治五年(1492年)《南京敕建净觉、礼拜二寺碑记》记载,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西域鲁密国人亦卜剌金、可马鲁丁等人因明朝“为征金山、开元地面,遂从金山境内随宋国公归附中华”。他们内附后,“钦蒙高帝喜其宾服,钦赏纻丝银钞等物,着落礼部给与脚力,前往永平府搬取家小赴京居住”,从此被安置在南京,并敕建两座清真寺,“将可马鲁丁等五户分在望月楼净觉寺居住,子孙习学真经,焚修香火,祝延圣寿,寄籍江宁县,优免差役”。永乐三年(1405年),“内钦取四户上京,着在四译馆教习子孙,至今优免差役”,其余的回回人,“见存九户,在此习学本教,祝延不缺,节奉礼部札副”[1](P292)。到了宣德年间,净觉寺被火烧,郑和又以“祈保下番钱粮人船”的名义重修该寺。
明代宦官修寺的记载更多地出现于京师、北直隶及北部沿边墙地区。北直隶真定府定州清真寺创建年代不详,据该寺所藏元明碑刻记载,清真寺曾于元至正年间重修。明弘治年间,武平伯陈勋途径定州拜谒礼拜寺,得知本地教众有修寺意愿,但经费不足。陈勋回京后到敕赐普寿寺向“教之缙绅士大夫”募款,筹得“数百金”交于定州“当事者”。尔后,定州教众请陈勋代请敕额,“陈公未及行而殁”,其弟陈熹袭爵后,想继其兄志,为定州寺请敕额,遂与礼部侍郎张昱相商:“定寺敕额,先兄有志于请求而未逮,吾欲有以成之,可乎?”张昱回答说:“敕命未易得。予职宗伯也,天下寺院皆其所司,予且额之。”张昱为定州寺题匾“清真礼拜寺”。并“移檄定州卫,命择郡之谨厚有学行者三人以领其事,并查勘得寺原系古刹,仍给札副住持,以荣之焉”。从该碑碑阴题名中可以看出,参与本次修寺的人士以军官居多,除武平伯陈勋和陈熹外,还有保定副总兵张勇,都督同知马澄,大兴卫百户马佐、马继祖,密云右参将杨恭,锦衣卫指挥马让,金吾卫指挥田艾、穆高,旗手卫指挥梁右、肖钗,锦衣卫千户马仁、杨全、马良俊等人。文职官员有鸿胪寺卿舍诚、鸿胪寺序班王景、马谏、中书舍人吴卿。内官则有来自御马监的太监马臣、李洪、倪英、马敬和尚衣监的太监何江、丁俊、桑尕等七人④。
山西大同清真寺建于永乐年间,“至成化初,挥使王公信、杨公义,教人马俊、马永等,由钦差镇守太监覃公玑、总镇彰武伯杨公信、抚院王公越、暨阃帅毕公瑛、郡伯郝公渊,捐俸鸠工,大恢其制,革故为新,允可瞻礼矣。”嘉靖元年,都督詹升、武平伯陈勋、总镇麻循等人重修。万历年间,总镇马兰溪、麻西泉、马崇斋、马慎斋等人又多次修缮⑤。碑文中的镇守太监覃玑在天顺年间为镇守辽东左少监⑥,到成化时已出镇大同:
丁卯,镇守大同左少监覃玑奏:达贼大势入境,官军分为四路,都指挥李恺等为左哨,都指挥马仪等为右哨,修武伯沈煜、都督佥事张瑀由中路,臣偕都御史王越等随后策应,屡与贼战,杀败贼众,生擒一十二人,斩首二十七颗,获鞍马一百二十匹,弓箭什物无筭。诏覃玑等三员俱升一级,沈煜等三员宜从厚赏,余官军升赏有差[2](P856)。
到了成化三年(1467年)七月,覃玑因有功进官一级,由从四品左少监,升为正四品太监⑦。《明宪宗实录》成化五年(1469年)六月丙子条提到覃玑时已称其为“太监”⑧。此外,引文中的都御史王越,即前碑文中一同修寺的抚院王越。据《明史》记载,王越为河南浚县人,景泰二年(1451年)进士,天顺七年(1463年)升任右副都御史,接替前任韩雍巡抚大同⑨。在《明宪宗实录》中,王越的名字经常与覃玑一同出现。
成书于宣德年间的《宁夏志》记载,该地有“回纥礼拜寺,永乐间御马少监者哈孙所建”[3](P107)。这个回纥礼拜寺即为清真寺。御马监在明代可视为内廷的武职衙门,肩负出镇诸边及各省的职责。引文中没有说明哈孙修寺与其御马少监身份之间的关系,其名亦不见于宣德《宁夏志》和嘉靖《宁夏新志》对永乐年间宁夏镇守内官的记录⑩,其具体生平有待考证。
二
明代京师的清真寺保存有大量宦官参与修寺的记载。北京牛街礼拜寺在弘治九年(1496年)曾进行增修,从碑文可辨识部分中可以看到“内府酒醋局右□使杨公永”的字样,该碑题名中也有尚衣监太监刘昇、钦差提督鞍轡军器二局司设监太监何江、尚膳监太监张钺的题名,而杨永在题名中的官职已变为都知监太监⑪。
阜成门外三里河永寿寺坐落于西三里河村。据明天启四年(1624年)《重修清真寺碑记》记载,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本教司礼监秉笔太监李寿,锦衣户侯董应元协内外官庶教众,各捐己资,易得阜城关外三里河翁僧荒堂一区,遂营筑坛宇,择任住持”。到天启三年(1623年),又有“钦差提督城内外禁门地方巡城点军司礼监文书房太监金良辅,复虔诚妆修”[4](P152)。可见永寿寺的修建过程与宦官有密切的关系。李寿作为司礼监太监,其事迹见于刘若愚的《酌中志》。刘若愚称“司礼监随堂李太监寿者,京都人,西域苗裔,嘉靖四十一年选入,历任司礼监监官”[5](P193)。《酌中志》中对李寿“西域苗裔”的描述与碑文中“本教”的记载相合,既可确定李寿的族属来源,又说明了他穆斯林的身份。依据刘若愚的记载,李寿任司礼监监官时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主持了选录新宦官的差事,这中间就有刚刚入宫的刘若愚。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李寿因在处理福王朱常洵选妃的事件中有出色表现而得到总理婚典的太监陈矩赏识,得以升为随堂太监。不过,李寿升职不久便“一疾令终”,他并未出任过碑文中所说的司礼监秉笔太监。《酌中志》中另一处提到李寿的地方也称其为“随堂”[6](P32)。与碑文相比,刘若愚的记载应更为准确。
王东平、马明达两位先生在考证李寿生平时,都引用了《明神宗实录》万历十四年(1586年)二月辛未条的记载:
内旨传礼仪房供事锦衣卫指挥佥事可贵等六员,各升同知、佥事有差;礼仪房应役写字催事锦衣卫衣左等所冠带总旗李寿等八十余员,各升级有差,下兵部⑫。
这段引文中的李寿虽然供职于司礼监下属的礼仪房,但其世职应为锦衣卫衣左所冠带总旗,他这次升迁也是由兵部操作的。明代上十二卫中,锦衣卫与宦官的联系最为密切。例如东厂由最得宠的宦官提督,厂之属员悉取于卫,锦衣卫官员则常常由掌握东厂的司礼监太监私人出任[7](P227)。《明史》记载:“礼仪房,提督太监一员,司礼掌印或秉笔摄之,掌司、写字、管事、长随无定员。掌一应选婚、选驸马、诞皇太子女、选择乳妇诸吉礼。”[8](P1822)说明礼仪房通常由司礼监掌印或秉笔太监出任提督太监。锦衣卫官员参与礼仪房的事务,主要体现在“选择乳妇”的职能上。《明孝宗实录》弘治十一年闰十一月乙酉条记载:
国朝有礼仪房之设,先于京县、五城兵马司及金吾等二十八卫,择取乳妇预餋其中,以俟应用。初以锦衣卫千户一员管辖。近千户黄英以太监李广传升本卫指挥,遂恃势科扰军民,请革退,止令各卫以千户轮直管事[9](P2518—2519)。
《万历野获编》对礼仪房也有专门的记载:
都城内礼仪房者,俗号奶子府。每四仲月,各坊报少妇初孕者名奶口,验其年貌,辨其乳汁,留以供禁中不时宣索。每至期尽,而内无所召,则遣出再选。董其事者为锦衣缇帅,有掌房,有贴房,其体貌稍亚于两镇抚司,亦得门棍传呼[10](P1420)。
《万历野获编》中的“锦衣缇帅”即指锦衣卫指挥使。可见,两段引文都明确指出由锦衣卫官员管理礼仪房乳妇。锦衣卫千户黄英因太监李广的关系得以升任指挥使,说明宦官与锦衣卫之间联系密切,李广获罪后,黄英自然受到牵连。不过,锦衣卫与宦官毕竟是两个系统,本文讨论的内臣李寿应与锦衣卫李寿是两个人。
在李寿之后修寺的金良辅也出现在《酌中志》的记载中。金良辅为北直隶人,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入宫,泰昌元年经魏忠贤奏升司礼监,“任文书房,良辅,正阳等门提督”[11](P89)。《明熹宗实录》《崇祯长编》及《明史纪事本末》中均称金良辅为“九门提督太监”或“提督九门太监”⑬。《酌中志》将金良辅的简单传记收入《逆贤羽翼纪略》中,说明金良辅为魏忠贤党人。为金良辅修寺一事撰碑的“赐进士第文林郎山东兖州知曹县事石三畏”[4](P152),在魏忠贤得志之后成为其“十孩儿”之一⑭。
1955年8月,阜外三里河村居民马文林房下发现古墓一座,石碑一个,即明天启五年(1625年)《金氏宗图碑》。该碑碑额及碑阴刻有阿拉伯文,说明墓主人和立碑者的穆斯林身份,而立碑者正是前文修寺的太监金良辅。碑文汉文部分如下:
天顺元年,曾祖金承恩因英宗睿皇帝,口北回京登极叙劳有功,升锦衣卫正千户……
祖金奉,侍卫将军,有功历升锦衣卫副千户……
父金鳌,锦衣卫冠带总旗,西司房管事……
钦差提督正阳等九门并永定等七门及皇城四门京城内外禁门地方巡察官军司礼监管文书内官监太监金良辅
锦衣卫冠带总旗,东司房管事金良弼
天启五年岁次乙丑孟□吉旦建立[4](P171—172)
这块《金氏宗图碑》立于明天启三年(1623年),暨重修永寿寺后的第三年。从碑文追溯的祖先事迹看,金良辅出身于世袭军户家庭,他的曾祖金承恩在英宗复辟后得以晋升为锦衣卫正千户,祖父金奉也因功升锦衣卫副千户。金良辅的父亲为锦衣卫冠带总旗,其兄弟金良弼也是锦衣卫冠带总旗,可以推断其家世袭锦衣卫冠带总旗之职,而金承恩的锦衣卫正千户和金奉的锦衣卫副千户均为流职。金奉在升任锦衣卫副千户之前为侍卫将军,据《明会典》记载:“凡锦衣卫侍卫将军,自为一营,遇下班之日,照例操练,从管领侍卫官提督。”[12](P1119)金鳌、金良弼于东西司房管事,这是二人在锦衣卫中的职务。《万历野获编》在论及厂卫关系时提到东西司房的职能:
东厂能得之内廷,因轻重上下其手;而外廷间有一二扞格,至本卫则东西两司房访缉之,北镇抚司拷问之,锻炼完密,始入司寇之目[13](P1402)。
《金氏宗图碑》中对金良辅职务的描述,除了史籍所见的提督九门、司礼监管文书房之外,还提到了内官监。司礼监的文书房掌收通政司每日封进本章、会极门京官及各藩所上封本。内官监掌管营造宫殿陵寝及经办妆奁器用等事,同时还有管理外厂及藩王修建府第等外差。相对于司礼监“二十四衙门之首”的尊贵地位,内官监仅管营造工程,地位一般。《金氏宗图碑》刻于天启二年,而《酌中志》写于崇祯二年至十四年(1629—1641年)。刘若愚仅记录了金良辅升入司礼监的时间,“泰昌元年冬,逆贤奏升司礼监,任文书房”[11](P84),没有提到其在内官监供职的情况,因此,我们不大清楚金良辅碑文题名中将司礼监与内官监并书的原因。
金良辅于天启三年修寺的举动与其家族墓地坐落于三里河有直接的关系,金良辅死后是否也葬于此地已难于稽考。
三
从地理位置看,明代的定州、大同、宁夏都位于北部边墙沿线。定州、大同两寺的例子说明一直有武职官员参与修寺活动,这与其都地近边墙,具有军事防御价值,卫所、军镇分布其中有直接的关系。定州所处的真定府位于太行山东麓的冲积平原上。《读史方舆纪要》称真定府“控太行之险,绝河北之要,西顾则太原动摇,北出则范阳震慑”[14](P589)。真定府在内三边长城一线,紧邻保定,而定州位于真定府北部,其辖境北与保定府相接,军事价值一目了然。大同的北部和西北部直接面对蒙古部落,从大同南下即可抵达直隶,直逼京师。大同又处于山西北部大同平原上,“东至枳儿岭,西至平虏城,川原平衍,故多大举之寇”[15](P2435),故此大同的防御位置相当重要,大同府、大同诸卫、大同镇等建置犬牙交错。由于定州、大同在明代长城防御体系中的地位,因而两地都生活有大量军户。宁夏作为陕西三边四镇之一,也是著名的边塞重镇,“今三边既为中国所有,而宁夏居中,适当喉噤之地”⑮。明代的宁夏只有军卫建制,没有民政体系,不设府州县,居民以宁夏诸卫旗军舍余为主。
明代京师内外也是卫所军士驻防的重点地区。今北京市各清真寺所存明代碑刻中可见大量军卫武官的名字⑯。以牛街礼拜寺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敕赐礼拜寺记》为例,该寺敕名由都指挥詹昇题请,参与此次修寺者多为武职官员:
京城西南巡捕把总都指挥同知杨应瑞
原任内西巡捕把总都指挥同知杨胜宗
神枢五营把总指挥佥事张肃振
金吾右卫管卫事指挥佥事……
五军一营右哨千总指挥佥事……
济阳卫亲军掌印世袭指挥使……
鹰扬卫后所掌印百户……
昭陵卫见任实授百户……
济阳卫见任百户……
锦衣卫实授百户……
锦衣卫镇抚司指挥使……建造
锦衣卫见任百户 马化龙 郑凤
锦衣卫管带……[14](P60)
目前,我们很难一一考订参与清真寺修建的卫所军官是不是回回人,但明代都司卫所中确有大量回回军户存在,如碑文中提到的回回人武平伯陈勋家族、大同麻氏家族均为卫所军户。陈勋先世陈友出身于骁骑右卫,麻西泉(即麻贵)则世为大同右卫人。分散于各地卫所之中的回回人,在其驻地创建或参修清真寺,以实践自己的信仰。定州修寺碑中题名的几位宦官,与定州本地军民回回人的宗教生活很难发生直接的联系,他们的参与更多是共同信仰的驱动。像大同镇守太监覃玑这样在边镇重地参与修建清真寺的宦官,本身未必是伊斯兰教的信仰者,他们参修清真寺的活动源于其镇守京师外缘或监工在外的身份。与之相类似,郑和参修南京清真寺不仅发端于自身的信仰,还是其下西洋活动的一部分,他的举动代表了这只庞大队伍中伊斯兰教信仰者的愿望和需求。早在永乐十五年(1417年),郑和就在第五次出使途经泉州时拜谒了灵山圣墓:
钦差总兵太监郑和前往西洋忽鲁谟厮等国公干,永乐十五年五月十六日于此行香,蒙灵圣庇佑。镇抚蒲和日记立[16](P55)。
出于同样的目的,郑和在出使西洋途中还多次参与对妈祖的祭祀活动,由此表达官方对妈祖庇佑海运神力的认可⑰。宦官作为天子近侧之人,他们透过介入各种地方神的信仰活动,沟通地方社会与国家中枢之间的关系,其政治目的远远大于宦官自身的信仰动因⑱。
京师宦官与京师民间社会的关系更为直接。从大量庙宇的存世碑刻可以看出,宦官组成香会组织参与各种寺庙的祭祀活动,宦官政治以民间的造神和拜神的方式表达出来,同时,宦官也成为沟通宫廷与民间社会的特殊中介⑲。京师回回宦官亦通过信仰的方式参与回回人社会的日常生活。例如前文提到的金良辅先修永寿寺,后修家族墓地,将其自身的宗教信仰、家族先辈的纪念活动与清真寺的整修维护结合在了一起。
三里河永寿寺地处阜城门外。明清时期北京城西部的阜城门、西直门外不仅有大量私人墓地,而且还有多处义冢,其中包括两处官置漏泽园。据《宛署杂记》记载:
义冢,西直门外一所,计八十亩,系官置漏泽园……。七贤村一所,计八十六亩……东至千户马雄,南至大道,西至王家庄,北至张内相。阜城门北岔路一所,计十五亩……东北俱至道,南至卖主,西至耿家坟。阜城门外北岔路一所,计八十亩,系官置漏泽园。东北俱至道,南西俱至各家坟。阜城门外马家庙后一所,计五十亩……东南北俱至道,西至王内相也。阜城门外北岔路一所,计一千四百畦,先年包都司施。东西北俱至小道,南至各家坟。阜城门外南岔路一所,计一千二百畦……东北俱至道,南至各家坟,西至沟[17](P286)。
1938年《回教月刊》上发表的唐宗正《北京市清真寺调查(之三)——阜外三里河清真寺》一文称三里河永寿寺是“负有监护回教公墓使命之礼拜寺”,寺之周围有大量回回坟墓。
本村回民住户只不过四十余家,生活状况,以养驼、养鸡、养鸭及种菜园、务农等,间亦有代坟户看管茔地者。平日仰仗回教坟墓为生,遇有死亡之家,彼可代为抱坑破土(回教人俗称打坑),俟葬仪日并可代为填土葬埋,及葬后拍坟等工作,且任日后照料修理打扫等事项。其所得知代价,除遇坟户落丧即游坟事临时给以酬金外,并将彼所看管之坟地令其免租耕种[18](P442)。
除了守坟之外,永寿寺附近还有一些经师散居,他们“对本地私茔公墓所在地颇为熟悉,每遇葬埋亡者及平日游坟之教民,均由经师指导方式,引领地界,并代丧家诵经、祈祷等事”[18](P439)。
日本学者田坂兴道曾提出回回人可能在明朝就开始在此地营建坟墓,“景泰年之前及更早在阜城门外(可能就是今三里河)回教徒专用墓区已经相当大,并且是北京最主要的回教墓地”⑳。田坂兴道的推测不无道理。三里河除了出土金良辅家族的墓碑之外,此地还有晚明清初伊斯兰经学家王岱舆、晚清学者马邻翼、经师王友三、王浩然,以及马福禄、马福祥及其部下等人的墓。唐宗正称这里的坟墓多为牛街之教民。可见三里河永寿寺很可能是因回回坟茔集中而修寺,以寺守坟。
综上所述,明代参修清真寺的宦官并不一定都是回回人,有相当一部分宦官参与清真寺的活动是出自明确的政治目的。作为信仰者介入清真寺修建的回回宦官,则是明代清真寺活动的重要支持力量。透过清真寺碑刻,我们得以看到日常生活中的宦官与回回民间社会之间的互动。
注释:
①详见何孝荣:《明代宦官与佛教关系》,《南开学报》,2000年第1 期;程恭让:《明代太监与佛教关系考述》,《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3、4 期;陈玉女:《明代二十四衙门与北京佛教》,台湾如闻出版社,2001年;何孝荣:《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研究》,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7年。
②⑲参见赵世瑜:《黑山会的故事:明清宦官政治与民间社会》,载《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
③(清)孙可庵:《清真教考》,《四库未收丛刊》第十辑第十册,第116 页。又见《回族和中国伊斯兰教古籍资料汇编》第二十四册,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
④明正德十六年(1521年)《重修清真礼拜寺记》,余振贵、雷晓静主编:《中国回族金石录》,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7 页,碑文文字和标点均有校注、调整。
⑤碑文内容及考释,参见杨大业《大同清真大寺明天启二年碑文考释》,《第二次回族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汇编》,2006年。文中作者考证《中国清真寺女寺史》附录中收录的碑文“钦差镇守太监谭公(尧)、(总)镇彰武伯杨公(寅)”一句,应为“钦差镇守太监谭公(玑)、(总)镇彰武伯杨公(信)”。笔者认为作者补入的内容是正确的,但参照原碑,“谭”字应为“覃”字,这也和《明实录》中对大同镇守太监覃玑的记载一致。
⑥参见《明英宗实录》卷310,天顺三年十二月乙亥,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6520 页;《明英宗实录》卷321,天顺四年十一月庚寅,第6671—6672 页;《明英宗实录》卷351,天顺七年四月癸酉,第7052 页。
⑦《明宪宗实录》卷44,成化三年七月辛巳“赏大同有功官军八百六十员名,彩缎、白金、布绢有差,其镇守少监覃玑等进官一级,总兵官修武伯沈煜、赞理军务都御史王越等,赏赉视常例有加。”第911 页。
⑧《明宪宗实录》卷68,成化五年六月“丙子录大同杀贼功升奉御张普林、都指挥佥事张瑛,俱一级;赏太监覃玑、韦正、彰武伯杨信,银十两,彩缎三表里;都督佥事徐恕、右副都御史王越,银五两,彩缎二表里;都指挥以下官及旗军人等共三千八十六员名,各升赏有差。”第1360 页。
⑨《明史》卷171《王越传》,“七年,大同巡抚都御史韩雍召还,帝难其代,喟然曰:‘安得如雍者而任之?’李贤荐越,召见。越伟服短袂,进止便利。帝喜,擢右副都御史以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4570—4571 页。《明英宗实录》卷354,天顺七年七月壬子“升山东按察司按察使王越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第7088 页;《明英宗实录》卷355,天顺七年闰七月“己未命右副都御史陈价巡抚宁夏,王越巡抚大同”,第7092 页。由此可知王越由韩雍推荐,于天顺七年七月升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转月接替韩雍巡抚大同。
⑩参见(明)朱旃撰,吴忠礼笺证:《宁夏志笺证》,第148—149 页;(明)胡汝砺编,管律重修《嘉靖宁夏新志》,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15—116 页。
⑪《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53 册,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47 页。另可参见王东平《明碑所载官员助修北京清真寺考》,《史学史研究》,2010年第1 期。
⑫《明神宗实录》卷171,万历十四年二月辛未,第3098 页。参见王东平《北京三里河清真寺〈重修清真寺碑记〉笺证》,《回族研究》,2008年第2 期;马明达《北京三里河明刻〈重修清真寺碑记〉初探——略论明代宦官群体中的伊斯兰教徒》,《回族研究》,2011年第3 期。
⑬参见《明熹宗实录》卷73,天启六年闰六月辛亥,第3540 页;此处为“九门太监”,《明实录》附录《崇祯长编》卷2,天启七年十月丁巳,第77 页;《明史纪事本末》卷71《魏忠贤乱政》,丛书集成初编本第10 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1 页。
⑭《明史·石三畏传》卷306,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7857—7858 页。至于石三畏是否为回回,学界颇多争论。杨大业认为石三畏是回回;王东平认为其族属有颇多疑点;而马明达则明确提出石三畏不是回回。参见杨大业:《明清回族进士考略·直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1年;王东平:《北京三里河清真寺〈重修清真寺碑记〉笺证》;马明达:《北京三里河明刻〈重修清真寺碑记〉初探——略论明代宦官群体中的伊斯兰教徒》。
⑮(明)霍冀:《九边图说·宁夏镇》,转引自彭勇:《明代北边防御体制研究——以边操班军的演变为线索》,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93 页。
⑯参见王东平:《明碑所载官员助修北京清真寺考》,《史学史研究》,2010年第1 期。
⑰参见张桂林:《郑和下西洋与妈祖》,《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2 期;蒋维锬:《明永乐至宣德间的太监外交与天妃崇拜》,《莆田学院学报》,2004年第6 期;王元林:《天妃、南海神崇拜与郑和下西洋》,《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 期。
⑱邱树森以伊斯兰教中国化的视角解释元初的蒲寿庚、蒲师文父子和明初的郑和参与妈祖信仰活动的原因,与笔者从政治的角度看待这一问题不同。参见邱树森:《妈祖现象与伊斯兰教的中国化》,《宁夏社会科学》,1997年第3 期。
⑳[日]田坂兴道:《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入及其发展》(中国にぉける回教の傳来とその弘通)下卷,东京:东洋文库论丛(第43),1964年,第1110 页,转引自王东平:《北京三里河清真寺〈重修清真寺碑记〉笺证》,第106 页。相关史料有:《明英宗实录》卷266,景泰七年(1456)五月丁丑“撒马儿罕等地面使臣指挥马黑麻舍力班等,请游在京诸寺及出阜城门外祭扫祖坟,从之。”第5647 页。《明英宗实录》卷199,景泰元年12月辛卯“礼部奏脱脱不花王男也先猛可的正使苦秃不花等告要游看寺宇,副使兀马儿要阜城门外祭墓,并求朱红描金马鞍座及减金鞍镫,皆从之。”第4232—4233 页。其中副使兀马儿之名,可能与赛典赤之名乌马儿为同一词,意为“长寿”。因无其他旁证,此处存疑。
[1]冯今源.中国伊斯兰教碑文选注[A].冯今源.三元集[C].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
[2]明实录·宪宗实录:卷四二·成化三年五月丁卯条[M].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3](明)朱旃.宁夏志笺证[M].吴忠礼,笺证.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
[4]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59 册)[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
[5](明)刘若愚.酌中志:卷二二·见闻琐事杂记[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
[6](明)刘若愚.酌中志:卷五·三朝典礼之臣纪略[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
[7]栾成显.论厂卫制度[A].明史研究论丛(第一辑)[C].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
[8]明史:卷七四·职官三[M]北京:中华书局,1974.
[9]明实录·孝宗实录:卷一四四·弘治十一年闰十一月乙酉条[M].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10][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一·禁卫·礼仪房[M].台北:台湾伟文图书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
[11](明)刘若愚.酌中志:卷十五·逆贤羽翼纪略[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
[12](明)申时行,等.明会典:卷二二八·锦衣卫[M].北京:中华书局,1989.
[13](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一·禁卫·锦衣卫镇抚司[M].台北:台湾伟文图书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
[14](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一四·北直五[M].北京:中华书局,2005.
[15](明)陈子龙,等.明经世文编:卷二三二·许恭襄边镇论·大同[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6]泉州伊斯兰教石刻[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
[17](明)沈榜.宛署杂记:卷二十·志遗五[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
[18]唐宗正.北京市清真寺调查(之三)——阜外三里河清真寺[A].李兴华,冯今源.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选编(1911—1949)(上册)[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