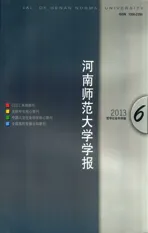比较叙事学视域下的《铁皮鼓》与《古炉》
2013-04-12王振军
王 振 军
(河南科技学院 文法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0)
比较叙事学视域下的《铁皮鼓》与《古炉》
王 振 军
(河南科技学院 文法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0)
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和中国作家贾平凹的《古炉》存在着文学精神上的相通性。两部小说虽然诸多方面表出显而易见的差异,但在另类(侏儒与儿童)叙事人物、独特的叙事视角、分裂的叙事声音,表现人性的复杂,追忆民族历史、反思人类灾难等方面,两位作家在进行着跨越时空的对话。这种对话也有着小说发展演变史的意义,在其叙事创新中显示了一种共通的世界文学精神。
比较叙事学;《铁皮鼓》;《古炉》;小说精神
1959年秋,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与读者见面,1999年格拉斯因《铁皮鼓》荣获诺贝尔文学奖,2011年1月,中国作家贾平凹的新作《古炉》出版,当年就引起中国评论界的极大关注,甚至有学者把《古炉》称为“一部‘伟大的中国小说’”[1]。值得关注的是韩鲁华在论及《古炉》时曾谈到自己是把《古炉》与世界经典如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红》等进行比较阅读的,比较性阅读给韩鲁华带来的印象是:虽然这些作品的“差异性也是非常大的,但是,它们之间似乎共同贯通着一个旷古的声音。”它们存在着文学精神上的相通性。“贾平凹似乎是在进行着与世界文学艺术精神打通的探索”[2]。所谓世界文学艺术精神在我看来应该表现为宏阔的艺术视野,深广的社会历史意蕴,悲天悯人的人文精神,对人类之真实存在状态的拷问,当然也应表现为审美判断的多义性和艺术创新上的时代共通性。就格拉斯的《铁皮鼓》和贾平凹的《古炉》来说,至少可以看到在另类(侏儒与儿童)叙事人物、独特的叙事视角、分裂的叙事声音,表现人性的复杂,追忆民族历史、反思人类灾难等方面两位作家在进行着跨越时空的对话,虽然贾平凹明确说自己没有读过《铁皮鼓》[3],但正是如此才更显两位作家在追求世界艺术精神上的可贵与一致。
一
《铁皮鼓》的故事时间起于1899年,终于1953年,经历一战、二战和战后德国的经济萧条等三时期。叙事人是一个有特异功能的侏儒奥斯卡,他两年前涉嫌一桩杀人案被关在疗养与护理院(精神病院的婉称)里,躺在白漆金属病床上写供认状,小说有两条线索,一条是奥斯卡从外祖母的四条裙子开始追忆自己的一生,一条写自己在疗养院的生活,两条线索最后合二为一,经过两年的调查后真相大白,奥斯卡在他三十岁生日时被无罪适放。《古炉》按冬—春—夏—秋—冬—春的时间顺序分为五部,故事时间起于1965年,终于1967年。《古炉》的叙述者是一个全知全能的叙述者,但借用了一个想长而长不大的的儿童为叙事视角,以这个出身不良、倍受欺侮的儿童的目光,观察发生在中国西北内陆一个叫古炉的村庄里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农民们鸡堆狗碎的生活,邻里之间的恩恩怨怨,乡村干部腐败专权,“文革”爆发的第一年古炉村两个团伙之间惨烈的武头场面。
两部小说在诸多方面都表现出显而易见的差异:一部是“二战”结束、整个文坛沉寂多年之后德国第一部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小说,一部是新世纪之初正当中国长篇小说创作呈现繁荣之势时的优秀之作;一部是以德波边境的但泽——一个先属波兰,后被俄、奥、普瓜分,再被国联托管,又被德国侵占,战后归还波兰并改名格但斯克的小城镇——为背景,反思法西斯势力何以能在德国抬头的小说,一部是以象征中国(China)的一个叫古炉的小山村为背景,从人性的深度追问“文革”何以在底层中国爆发的文革记忆小说;一部是继承了伟大的欧洲传统,具有流浪汉小说特征的黑色幽黙小说,一部是植根乡土中国,回到民间,还原琐碎的日常生活的中国传统小说;一部是时间跨度为五十四年,有着清晰的情节线索、空间位移的又被称为现代主义的小说,一部是时间跨度只有不足两年,事件只在古炉发生与发展,情节被大量的细节填充,被称为最真实的现实主义小说,等等。然而,比较性的阅读又让人时时感觉到《铁皮鼓》与《古炉》在某些地方有一种精神上的一致性和相通性,这种一致与相通主要表现在为拯救叙事(小说)而进行的叙事创新上,我们需要首先讨论《铁皮鼓》和《古炉》的叙述人、叙事视角和叙事声音,进而再看它们的小说演变史意义。
众所周知,在欧洲,经典现实主义小说中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叙事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直到西方现代主义小说出现之后,第一人称叙事才逐渐成为主流。但是就《铁皮鼓》而言,它是一部无法定位的小说,“人们可以用诸如现实主义小说、超现实主义小说、荒诞小说、黑色幽默小说、历史反思小说、现代流浪汉小说、(反)教育小说、童话小说、戏仿小说、互文小说等各种名称称呼它”[4]。《铁皮鼓》的叙述人既不是单一性的第一人称叙述或第三人称叙述、也不是多位叙述人轮流叙述的多叙述人模式(如《喧哗与骚动》《我的名字叫红》),而是第一人称、第三人称同一又分裂的混合性叙述,这是遍观西方小说而绝无仅有的。可以先读其中的一个片断:
这时,罗丝维塔一边热乎乎地捏住我的双手,抚摩着,一边启动地中海小嘴,开始了一席谈话。这是直接讲给我听的,甜蜜地灌进了奥斯卡的耳朵,随后又谈了些实际的事情,接着话又变得更甜蜜,封住了我的一切顾虑和逃跑的企图。我们到了帝国殖民区,朝妇科医院方向驶去。拉古娜告诉奥斯卡,这些年里她一直想着他,她还一直保存着我在四季咖啡馆里唱碎并奉献给她的玻璃杯。[5]308
这是奥斯卡离家出走后巧遇师傅贝布拉,之后他和另一个侏儒女相会交谈的场景,开始是以第一人称我的口吻讲罗丝维塔对我甜言蜜语,然后毫无征兆地变为第三人称,说罗丝维塔的话语灌进“奥斯卡”的耳朵,之后又突然回到第一人称叙述,在本节的最后,甚至一句话中就包含一次叙述人称的转换,且转换并无突兀感和阅读上的不适感。
叙述人称的不断转换在《铁皮鼓》中是贯穿始终的,这种双重叙述人称共存的叙事手法使小说具有了复调小说的性质。小说以第一人称叙事时,叙述人是以极为冷漠的口吻,采用叙而不议的姿态叙说自己的经历,眼看着妈妈、马策拉特、布朗斯基之间畸形的关系他是冷漠的,比他年龄小但比他个子高的几个孩子强逼他喝下和着砖末、青蛙和儿童尿的“佳肴”时他是冷漠的,妈妈躺在一头大一头小的棺材里被送进墓地还是冷漠的,甚至一些令人恐怖的死亡场的叙说也是极端冷漠无动于衷的,如蔬菜商格雷夫用七十五公斤土豆自杀,水晶夜纳粹分子袭击犹太人马库斯的商店致其身亡,布朗斯基——他可能的父亲在德国突袭波兰时中弹而死,马策拉特——他名义上的父亲在苏军面前吞下纳粹党徽而死,几个年轻的修女在海边给收养的孤儿捡拾贝壳和螃蟹,被疑是盟军的间谍被党卫军射杀,等等。
第一人称的奥斯卡是事件的亲历者,但也是一个具有荒诞色彩的叙述者,“我”好像一架架在奥斯卡头的摄像机,纯然客观的记录下“我”眼中所看到的一切,不动声色,不加评论,不言是非,不显好恶。同时,另一个第三人称叙述者又如影随形式的时刻跟随着“我”,他既站在奥斯卡背后看奥斯卡,又超越奥斯所处的时空位置看世界,把“我”作为故事人物,叙说“我”行动,于是作为叙述人也是小说主人公的奥斯卡被下降到一个被叙述客体的位置。“在这里叙述者同时具有了两双眼睛:奥斯卡具有‘看清四周’的横向视野,他可以扫视自己置身其中的环境中,随历史的潮流而动,从而成为历史的见证者;格拉斯则以旁观者的身份处于事外,他可以进行纵向与客观的反思”[6]。于是,同一个叙述者裂变为两个叙事主体,他们都有独立意识,都有权表述自己的意见,发出自己的声音,以各不相同的视角、声调、语气、思想、意识表述各自眼中的世界,在两个叙述者之间形成相互邀约、交流、对话、协商、互渗、矛盾、融合、置疑的话语张力。格拉斯自己也曾谈到两个叙述人交替并置的意义,他说:“我构想出一个枝繁叶茂的家庭,我与奥斯卡及其亲友们争论不休……我试图为奥斯卡这个孤僻的怪人配备一个邪恶的小妹妹,然而我的企图在他的抗议下破产了。”[7]格拉斯的回忆一方面说明他是在有意识地让两个叙述人同时在场并让他们之间发生潜在的“对话”,另一方面也说明第三人称叙述人某种程度上代表了自己的声音,虽然一般的叙事学研究都把作者与叙述人看成是两个不同的小说构造者。
二
《古炉》采用的是传统小说的全知全能的叙事模式,从这一点人看,《古炉》与《铁皮鼓》似乎并没有可比性,但文学文本往往在没有交集的地方可能隐含着某种艺术追求的一致性和艺术精神的沟通性。
《古炉》的叙述人是一个名叫夜平安的十三岁的儿童,但人们只把他呼为狗尿苔,他无父无母,是蚕婆到镇上赶集时从路边捡来的,也或许是别人捡来送给蚕婆的,他“眼珠子突”、“肚子大腿儿细”、“乍耳朵”并且长得只有“毯高”,他是“侏儒,残废,半截子砖,院里卧着的锤布石”[8]336。他的爷(蚕婆的丈夫)解放前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后来跑到台湾,狗尿苔和婆成了反革命家属,他在村里地位低下,和地主分子等同,人们可以呵斥他、取笑他、歧视他,也可以随意的指使他,他经常被人呼来呵去的跑跑腿送个口信,拿拿火绳点个旱烟,他受人欺侮却不能反抗,麻子黑用腿跨过他的头他也只能心中恨恨然,秃子金骂他是伪军属稍有表示却招来一记耳光。狗尿苔又是善良的,守灯不待见他,他没有告发守灯破坏天布家的藤蔓根,牛路背叛他,他仍愿意和牛路玩,天布在霸槽大的坟上钉木橛子,他给悄悄的拔出来,杏开看不起他,他还愿意把家里的老母鸡杀了给杏开补身子,支书没给过他什么好处,当支书被关押时他给支书去送饭,榔头队和红大刀队武斗开始了,他不参加任何一派,却给他们通风报信,谁有麻烦就帮助谁,谁处弱势就同情谁,灶火把主席像倒挂在扁担上,他用儿童式的机智让灶火躲过杀身之祸,磨子身负重伤,他冒险帮助红大队把磨子救出,“榔头队”与“红大刀”拔剑驽张,眼看一场血腥恶斗就要爆发,不知又有谁会死于非命,他掀下蜂箱,自已被蜇的满脸红肿化解武斗,等等。贾平凹还赋于狗尿苔灵异的功能,他可以与山川交流,与大地沟通,与禽鸟为伴,与豕狗为伍,能听禽言,能懂兽语,特别是狗尿苔有一种奇异的嗅觉,能嗅出古炉村将会发生的大事,“令他也吃惊的是,他经过麻子黑的门口时闻到了那种气味,不久麻子黑的娘就死了,在河堤的芦苇园里闻到了那种气味,五天后州河里发了大水。还有,在土根家后院闻到了一次,土根家的一只鸡让黄鼠狼子叼了,在面鱼儿的身上闻到了一次,面鱼儿的两个儿子开石和锁子红脖子涨脸打了一架”[8]8。
贾平凹让狗尿苔生活在古炉村,让狗尿苔具有追逐热闹的性格,凡是有家长里短、鸡鸣狗盗、打架斗殴、吃喝拉撒、调笑取乐、婚伤嫁娶、生老病死发生的地方就会有狗尿苔的身影,《古炉》以狗尿苔为视角,以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叙事,古炉村发生的一切,从庸常沉闷、贫困琐碎的日常生活,到血腥的武斗场面都透过他的儿童视角得到了观察,儿童视角造成一种叙事的客观化,使作者不再以成人化的目光看世界,不再以理性的意识去评论小说人物和他们的言行,作家自觉的隐退造成一种客观化叙事效果,儿童视角在使叙事回归本真的生活中起到意想不能的作用,“儿童作为社会的边缘人物,在认知上具有感性、真实、原生态的呈现特点,也即巴赫金所说的‘不理解’认知特性。以这种非群体的、非社会化的极具个性化的限知视角叙述‘文革’是作家在策略上的有意‘撤退’,叙述视角由理性的、社会化的成人智性反思到感性的、个人化的儿童限知叙述,这是叙述载体的弱化,这种弱化消弭了小说叙述中成人的带有功利的、全知式的‘文革’叙事,而注重发挥儿童视角的呈示功能”[9]。
当众多评论者对贾平凹另类(疯傻)视角给以叙事创新意义的评价时,贾平凹也受到一些批评,如欧阳光明认为《秦腔》中的引生和《古炉》中的狗尿苔以非理性的眼光和超常的能力,打碎了笼罩在正常世界之上的光环,“对于书写世界的‘真实’,无疑有巨大的帮助。”但也正因为狗尿苔是心智低能、缺乏正常理性思维能力的畸形儿,无力担当表现社会历史变迁的重大任务,贾平凹“形而下思考的畸形发达,以及形而上思维的严重缺乏,严重阻碍了小说思想境界的提升”[10]。笔者所做的不是作孰是孰非的判断,而是在不同的评判中寻找出贾平凹叙事的意义。
在《秦腔》与《古炉》中,贾平凹以疯傻人引生和狗尿苔作为叙事人或以之为叙事视角,如果把他们的叙事等同于作者的叙事,得出上述结论似乎也不无道理,但欧阳光明在谈叙事视角时一方面没有辨析第一人称体验视角与第一人称回顾性视角的区别,另一方面在谈论视角转换时也不应忽视和叙事视角密切相关的叙事声音这一叙事学概念。引生在讲故事时如果采取当下在场性的体验视角,当然会出现叙事的“严重漏洞”,如果采用的是事后追忆式的回顾视角,则引生的叙事就是合理的,其叙事并不是“视角误用”现象。当然,我们在这里重点讨论的不是视角问题而是叙事声音问题。自从巴赫金从话语层面上提出声音概念后,对声音的讨论就不绝于耳,詹姆斯·费伦认为声音“既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个体现象”[11]。在小说叙述中作者、隐含作者和叙述人都可以通过某种语气、语调或其他手段传达出某种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也可以在相同的语气、语调中传达不同的思想观念,兰瑟则把社会诗学意义的声音和叙事学意义的声音结合起来,叙事声音是“指叙事中的讲述者,以区别叙事中的作者和非叙述性人物”[12]3。而女性主义声音是“那些现实或虚拟的个人或群体的行为,这些人表达了以女性为中心的观点和见解”[12]4。兰瑟认为两种声音在小说叙事中有时是可以重合的。贾平凹运用了引生与狗尿苔这样的疯傻型叙事者目的就是要造成作家隐退的客观化叙事效果,兰瑟所认为的两种声音的重合显然难以做到,但通过疯傻者的叙事声音传达出作者与隐含作者的意识形态声音是完全可能的。
《古炉》以狗尿苔为视角,从狗尿苔对麻子黑、秃子金的愤怒、对水皮的反感、对霸槽的追随、对杏开的帮助、对善人的亲近中我们可以推想,如果贾平凹同时以狗尿苔作为叙述人,就不可能实现小说叙事的客观化,但妙的是作者选用侏儒视角的同时又把叙事的权利交给全知全能的叙述人,实际上造成了叙事视角与叙述人的分离,这样就有可能让叙事者站在狗尿苔背后、置身故事之外以一种客观冷静的姿态叙述故事。不过,叙述人的客观冷静并不代表作者的毫不介入,贾平凹正是不满足于人们对“文革”的遗忘,也“不满意曾经在‘文革’后不久读到的那些关于‘文革’的作品,它们都写的过表象,又多形成了程式”[13]。他要写出对“文革”的乡村记忆,那是一个有着纯朴古风的小山村,也是包含一切人性之恶的小山村,饥饿贫困、庸常自私、小仇小恨、争强好胜、委琐凶狠、压抑沉闷,等等。本是自上而下的“文革”在这个封闭的小村庄一旦遇到一点点火星就迅速点燃并演变成一场血腥的武斗。贾平凹并没有以政治正确性的姿态评说“文革”,也不是如伤痕文学那样以善恶二元对立的观点否定“文革”,而是回到民间,沉入底层,解剖“文革”之所以在中国社会最底层发生的人性根源,可以说在客观化的叙事中潜隐着贾平凹反思文革的声音,那是一个有良知的作家发出的深沉的理性之音,是超越“文革”本身的对人类生存境况反复追问的“形而上”之音。
同样的声音在《铁皮鼓》中也暗含着,并且《铁皮鼓》的叙事声音与作者的意识形态声音实现了意想不到的重合。第一人称叙述者是以极端冷漠、超然事外的口吻把悲剧性的事件给予喜剧化处理,从而使《铁皮鼓》具有荒诞色彩,一个只有九十公分高的侏儒却有着超常的智慧和唱碎玻璃的本领,穿着时髦的阔太太被奥斯卡的声音吸引把手伸入橱窗行窃,场面盛大的纳粹集会被奥斯卡的鼓声敲成了滑稽可笑的舞会,小市民出身的马策拉特一件一件地穿上党卫军服装后洋洋得意,等等。格拉斯营构小说的荒诞感是要在荒诞中直逼生活中固有的真实,它的深刻之处在于作者并没有象多数人那样从外部寻找战争的原因,而是从解剖人的灵魂入手,从人性的深度出发,真实地揭示出了趋炎附势、盲目追随、自私狭隘的民族劣根性,并认为这才可能是引起战争的根源所在,因而战争之后对德国民众来说重要的不是发展经济,而是重建精神家园。所以,在洋葱地窖里,原来那些靠切洋葱头刺激落泪(这是多么无聊多么荒诞啊)的顾客,听着奥斯卡的鼓声终于离开洋葱哭泣出来了,这是“体面的哭泣,无碍的哭泣,自由地把一切都哭出来。这里江水滔滔,泛滥开去。这里在下雨。这里在降露水”[5]506。这里,作为奥斯卡声音终于脱掉冷漠的面纱和第三人称叙述人的声音及作者格拉斯的声音融合在一起。
三
如果把《唐吉诃德》作为西方长篇小说成熟的标志的话,从这部“伟大的欧洲小说”问世到现在,西方小说走过了整整四百年的历程,其间经历了诸如流浪汉小说、教育小说、哲理小说、对话体小说、书信体小说、诗体小说、复调小说、意识流小说、表现主义小说、新小说、黑色幽默小说、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等众多的小说体栽和小说类型的探索与创新,各种小说艺术手法的运用也几乎遍备,从小说叙述人上有第一人称叙事、第三人称叙事,单一叙述人叙事、多叙述人叙事多等各种类型,从叙事视角看又有全知视角、选择性全知视角、戏剧式或摄像机式视角、第一人称回顾性视角、第一人称见证人视角、固定人物有限视角、变换式有限视角、多重式人物有限视角、第一人称体验性视角等多种[14]。
叙事声音也经历了由显到隐的演变。浪漫主义作家要在他们的小说中彰显一个无处不在的自我,作家会在他们的小说中时时露面,不时的把他的主人公凉在一边,自己跳出来发表一通议论,如《少年维特之烦恼》《忏悔录》《悲剧世界》《唐·璜》《叶甫盖尼·奥涅金》。现实主义虽然以真实再现社会生活的原则,希望他们的小说成为一部社会风俗史的记录,但由于他们的良知、道义以及他们自觉的社会责任意识,他们总是忍不住在小说中现身。自然主义反对作家在作品中露面,反对作家进行直接的主观抒情、议论和道德评价,主张用纯然客观的真实描写达到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但只要读一读《包法利夫人》《娜娜》《漂亮朋友》就会感到作者还时不时地隐藏在文本的某一个角落里。现代主义小说家则要么让小说人物的意识取代作者的喋喋不休,要么如摄像机般的叙事手段实现作家的彻底隐退,要么用象征、荒诞的手法把作者隐藏在文本背后。
至此,各种可能的叙事策略——作家隐退也好,纯然客观也好,主观真实也好,人称变换也好,视角选择也好,叙事声音的显隐也好——似乎都已用尽。小说就是讲故事,从“讲什么”上说,小说是一个永远没有完结可能性的文学类型,但从“如何讲”上,小说似乎走到了尽头,以至于有人发出小说终结论的惊呼。但中西小说的发展现状又令人信服的说明终结论最少在目前来说是杞人忧天之举,这或许是《铁皮鼓》和《古炉》给叙事学和小说文体发展史的启示。当众多作家在从技术层面上寻找最恰当的小说叙述人(第一人称、第三人称、多人称)和叙事视角的时候,一些作家已然发现它们是可以和叙述者的身份、地位、个性特征、身体状况相联系的,小说的发展演变史有一个显而易见的线索,小说家们一直在努力实现作家的隐退(前文对叙事声音分析说明作家的绝动隐退是很难做到的),作家的隐退当然可以通过技术性略策实现,除此之外由什么样的人来叙述也是一条值得探讨的路线,如《铁皮鼓》与《古炉》,或者采用怪诞的侏儒作为叙述人,或者以儿童为叙事视角,目的都是要加大作者与叙事对象之间的距离,通过作家的有意“撤退”造成两者间的疏离感,形成客观冷静甚至漠然的叙事效果。这样的叙事学创新如果是《铁皮鼓》与《古炉》所独有,某种程度上说也并不值得给予极高的评价,因为它们作为个案很难说表现共通的世界文学精神,但是如果读一读《喧哗与骚动》《我的名字叫红》等小说,我们就会有一个基本的感受:这些作家在反映时代的精神风貌,追索人类共同的精神状态,叩问人类本真的存在价值时,存在着精神上的一致性,与此同时,他们还在思考着故事“如何讲”的问题,还在探索着小说这种未完成的文体如何走下去的道路问题,这是不是一种“小说精神”,进而是不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世界文学精神?
[1]王春林.伟大的中国小说(上)[J].小说评论,2011(3).
[2]韩鲁华,储兆文.一个村庄与一个孩子——贾平凹《古炉》艺术论[J].小说评论,2011(4).
[3]贾平凹,韩鲁华.一种历史生命记忆的日常生活还原叙事——关于《古炉》的对话[J].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
[4]周红红,徐谨.论《铁皮鼓》的叙事伦理[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11(2).
[5]君特·格拉斯.铁皮鼓[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6]王光利.《铁皮鼓》的荒诞与真实:一个多声部叙事交响的象征世界[J].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11(12).
[7]格拉斯,贺骥.回首《铁皮鼓》[J].世界文学,2002(2).
[8]贾平凹.古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9]沈杏培,姜瑜.叙述之轻与生存之重:新时期“文革”小说的另类叙事[J].艺术广角,2005(6).
[10]欧阳光明.论贾平凹后期长篇小说的叙事视角[J].当代文坛,2012(3).
[11]詹姆斯·费伦.作为修辞的叙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9.
[12]苏珊·S.兰瑟.虚构的权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13]贾平凹.长篇小说《古炉》后记[J].东吴学术,2010(创刊号).
[14]申丹,王丽亚.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95—97.
[责任编辑海林]
I106.4
A
1000-2359(2013)06-0169-05
王振军(1969-),男,河南卫辉人,河南科技学院文法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文艺理论与外国文学研究。
2013-07-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