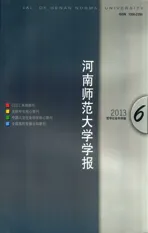论孔子山水思想中的仁学内涵
2013-04-12徐仪明
徐仪明,蒋 伟
(湖南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湖南 长沙410081)
《论语·雍也》中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这是孔子关于山水的经典名句。“山水比德”也成为学术界对孔子山水思想的一个基本定论。以水比智者的“动”与“乐”,以山比仁者的“静”与“寿”,已成为一些研究者的思维定势,他们围绕着“知者何以乐水”、“仁者何以乐山”作了许多自问自答的分析,似乎进入了一个思维误区:“知者”只“乐水”并不“乐山”,“仁者”只“乐山”而不“乐水”。究其原因,是对孔子“仁”的思想认识得不够全面深刻。孔子的山水观虽然谈到了智,但其中“仁”是最主要和最根本的。如果将“知”和“水”、“仁”和“山”分开,则是对山水中“仁”这一核心思想的忽略。所以,从“仁学”的视角对孔子的山水思想进行深入探析,理应是理解孔子山水思想的恰切的方式。
一、“仁学”:孔子山水思想的核心内涵
正如“道”是老子思想的核心内涵一样,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因为,“在孔子以前,‘仁’与其他道德修养是平行并列的,而孔子将‘仁’提升而成为贯穿一切道德修养之中的一条主线,从而使‘仁’具有‘统摄诸德’的功能和特点”[1]。在《论语》499节中,有58节讲到了“仁”,共出现了109次。每一次谈论“仁”的时候,由于所面对的对象、时间空间、谈论的角度及当时的心境情绪的不同,对“仁”的解答也有所变化。正如孔子观水时所云“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仁”在孔子思想中作为一个重要的部分,就像水一样,处于一种动态的变化状态,所以才有“克己复礼为仁”、“仁者爱人”、“仁者无忧”等等。徐复观早就注意到了仁的多样性特征,他说:“就仁的本身而言,它只是一个人的自觉的精神状态,并且这种自觉的精神状态又可以有许多层次和方面。”[2]“山水之乐”,就是“仁”的一个精神层面。“仁者”应该是既“乐山”又“乐水”的。何谓君子?“君子”就是“仁者”。孔子说:“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五者”就是指“恭、宽、信、敏、惠”,在这五项德行中,“敏”和“惠”都属于“知”的范畴,这说明,孔子的“仁者”涵纳了“知者”的智慧和能力。孔子的“仁”与“知”不是并立概念,而是相容概念。“知”和“仁”具有内在统一性,“知”是包含于“仁”的一个品格。因此,孔子的山水思想的核心内涵仍然是“仁”。
仁者为什么会喜爱山水呢?冯友兰先生说过:“孔子认为,人必须有真性情,有真情实感。这就是‘仁’的主要基础。”[3]杜维明先生在分析儒家知识分子时作了如下阐释:“人是情感最为丰富的动物,天赋有着最敏感的身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万事万物皆体现于感情之中,对于人而言不仅可能,而且也必然是人才克臻于此。”[4]不管是理性思维,还是道德修为,都不可能是一种纯抽象的过程,必定会包含着个人自我的情感取向。情是人的情感,是天所赋予人的自然之性。孔子把仁的基础建立在真实的情感心理上,认为在仁的人格构成中是不可能脱离真实的情感世界和现实生活的。“仁者,人也”(《中庸》),“仁”应该是人的真性情的流露,而后才有“仁”的品质。因此,孔子的山水观并不是偶然的现象,他摆脱了宗教神学的从信仰出发来崇拜山水,而从人的内在要求出发来看待山水,并高度重视发挥审美和艺术对个体情感心理的感染愉悦作用,通过个体对山水审美的心理欲求和社会的伦理规范两者的交融统一,来宣扬“仁”。“孔子认为要使人们实行‘仁’,最重要的是要使‘仁’成为人们内心情感上的自觉要求,而不是依靠外部强制”[5]。对此,孔子曾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雍也》)作为仁者,知道什么是仁,不如喜好仁,喜好仁,又不如以仁为快乐。按照孔子提倡的“成于乐”的观点,“成”乃完满、完善之意,“成于乐”就是境界升华、道德完善在于乐,正如东晋李充在《论语注》中所诠释的:“好有盛衰,不如乐之者深也。”“好”可以只是出于一时的兴趣,不如“乐”的深沉持久,因为“乐”是内心情感的要求和满足,不会因其他因素而改变。因而,仁者在山水之乐中使道德境界得到了升华与完善。《论语·里仁》中有一段孔子论仁的话,不常被人注意,其实对“仁”与“乐”的关系说得很清楚:“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乐”使外在的规范最终转化为内在的心灵的愉快和满足,外在和内在、社会和自然在这里获得了人的统一,这也就是“仁”的最高境界。它不只是认识、语言,不只是规范、善行,而且是美,是艺术。儒家对人作了过分狭隘的规定,把宗法社会的伦理道德定为“人之本”,也就对山水与人的关系作了限定,如“遍予而无私,似德”、“所及者生,似仁”之类;因为儒家总要规定人,并且按仁的要求规定人,也包括人的审美活动,即便是对自然山水,也打上了仁的意识和理性的烙印,所以山水之美的本质也就只能是“仁”。“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仁是内容,是实质,仁与山水之乐的关系也是如此,仁是山水之乐的内容、实质,乐是仁的表现形式。此时山水实质上就是人的道德品格的象征物,这正是伦理人格在对自然山水的观照中所进行的一种审美。“乐者为同”(《论语·乐记》),仁者的精神状态是“天下归仁”(《论语·颜渊》)、“浑然与物同体”(程明道《识仁篇》),就是山水之美与仁德之美通过“乐和同”,自然而然地融和统一。
孔子所以特别热爱山水,也正是因为在山水中体味到“仁”。乐山乐水实际上是“乐仁”,在山水审美中把握到了最深的道德境界。正像王国维所说的“以我观物,故物物皆着我之色彩”,孔子赋予了山水以“仁”的色彩。
二、模山范水:孔子向仁的道德修养
孔子其实是把“仁”作为一种很高的道德修养境界的。如前所述,孔子山水思想的核心是“仁”,孔子对山水的钟情并不是山水本身,而是侧重于其中的寓意和“仁”的联系,通过欣赏自然山水来发现山水中的寓意,激发起生命的情趣,找寻一种审美的修养方法,同时获得精神上的愉悦,通过模山范水来完善仁者的道德修养,从内心唤起仁性的完美。从知行合一的角度来看,仁作为孔子的道德本体,需要主体从仁的概念桎梏中解放出来,自觉愉悦地践行仁,由知行合一上升到乐行合一。山水之乐就体现了这种“与仁处之”的精神境界与行为模范。山水之乐并不是简单的娱乐,而是仁者的修身方式。“从另一种意义上谈论人的存在问题,即人作为人而言,首先是有情感的动物,就是说,人是情感的存在”[6]。“为仁由己”,在仁学实践的过程中,是不能只满足于抽象的理性思辨的,至高的仁应该显现出活生生的、具体的心情愉悦,才能真正地得以落实,才能将人伦教化的义务化为人们情感的自发需求。
按照李泽厚实践理性的观点,孔子的“仁”也要通过行为的实践来养成。“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尔》)。首先要乐于仁,才能在具体生活中释放仁性而进入一个真实和快乐的生存世界。“乐由中出故静”(《礼记·乐记》),其“静”即是孔子山水思想中的“仁者静”之“静”的义涵。这说明“乐”可以提升人,促使人进入仁的境界。对于个人而言,只有行到乐处,才会自觉自愿地发生出合于仁的行为。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论语》中多处使用“乐”字,才有“回也不改其乐”,“乐亦在其中”的“仁乐”,“山水之乐”将内心意志的愉悦与道德内涵的提升融合于山水之中,将山水之乐成功地转变为个体践行的充实与快乐,并使这种快乐成为仁的一种必要的构成特质,山水之乐对激发道德、践行道德具有特殊功能。其次,“仁也者,仁乎其类者也”(《吕氏春秋·爱类》)。面对山水,要观察山水的特质,体验人生的道德意义,并自觉地去完成“仁”的自我构成。乐山乐水乃是“志于仁”,通过对山水的特征来反观仁的行为,去贴近心中之于仁性的召唤,进一步完善仁所需要的心理构成,使之朝着仁的实践与完成方向发展,即“苟志于仁”(《论语·里仁》)。自觉地乐于仁是一以贯之仁的最好的实践。孟子对孔子乐水作了进一步阐发:
徐子曰:“仲尼亟称于水,曰‘水哉,水哉!’何取于水也?”
孟子曰:“源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尔。苟为无本,七八月之间雨集,沟浍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声闻过情,君子耻之。”(《孟子·离娄下》)
这一段阐述了孔子对水的特质的描绘。美国学者艾兰说:“在这段文字中,有源的溪流是与自天而降的雨水相比较而言的。雨水无本无源,充溢于灌溉庄稼的沟渠,滋润禾苗,但很快便会挥发干涸,而有泉水则不断流淌。据孟子所说,孔子从这种自然现象中悟出一条道理:荣誉如果得不到人的内在道德资源的支持,就像不能连续流涌的水流,眼见干枯,这使君子感到耻辱而非荣耀。”[7]这里对孔子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之说作了发展。孔子“观水”,并不是对水的科学考察,不是要观测水文、水质,而是要从水的形态获得某种人生的心理体验,仁者就应该像水一样持之以恒,而不是表面上的风光,华而不实是仁者所不耻的。对此,孟子又加以补充:“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孟子·离娄上》)这样的“观水”之“术”,就是把水的某些形态特征同人的某些精神特征联系起来,从而获得一定的人格体验。后来朱熹有感于孔子的“观水”之“术”写了一首诗:“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汉代的刘向《说苑》对孔子乐山作了仔细的论述:
“夫仁者何以乐山也?”
“夫山,巃嵷礧嶵,万民之所观仰,草木生焉,众物立焉,飞禽萃焉,走兽休焉,宝藏殖焉,奇夫息焉,有群物而不倦焉,四方并取而不限焉。出云通气于天地之间,国家以成。是仁者所以乐山也。《诗》云:‘泰山岩岩,鲁候所瞻。’乐山之谓也。”
山“立于天地之间”,即阴与阳之间,有如天地之大德,生发万物。如此的特殊地位使它成了一切秩序的映象和模范,就像仁者在社会伦理关系中的地位一样。
山水如何激发仁者的人格精神呢?对于这个问题,古人早已有明确的认识:“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礼记·乐记》)人性一片纯真、纯善,在无外物扰动人心时,并无欲之动。性是“自本自根”的自然而感,其“感于物”而“动”,王夫之说:“形于吾身之外者,化也;生于吾身之内者,心也。相值而相取,一俯一仰之间,几与为通,而悖然兴矣。”(王夫之《诗广传》卷二)当山水形貌与主体之心相接通,才能产生美的感受,即“缘心感物”。许慎《说文解字》云:“感,动人心也。”所以“感”为心有所动之义,“感物”,就是在审美对象的触发下,主体心有所动,在观赏山水时有感而动,把生命向仁性上升,向纯净而无丝毫人欲烦扰夹杂的人生境界上升。如此,道德便成为一种情绪,成为生命力的自身要求。人顺其情绪的要求产生的审美活动是快乐的,由这种乐出发的道德也是美与仁的大融合。所以孔子便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成”是圆融,在仁与美的圆融中,仁不是作为一个标准规范去追求,而是一种审美的享受。仁的境界有同于山水之乐的境界了,“仁”已渗入到个体的人格之中。
人的道德性存在脱离不了真实感情存在的生命个体。从人的感情需要来说,乐可以缓和对道德的认识、学习、实践的生硬感,而从道德的内在情感来促发仁性的生成,达至一个圆融的世界,则体现了一种生命和谐的情感,使仁性道德得以最大程度地发挥。只有由内发出的乐仁,才会有自觉的习仁践仁的行为发生,并自觉地朝着仁性的目标去行为。
三、山水审美:仁性的升华
在中国思想史儒道互融的历程中,儒家入世,道家出世,其融合之处就体现在对山水的共同审美上实现了殊途同归的契合。“四海之内,其性一也”(《性自命出》),由于人的相同的感觉器官构成了共同美感的生理基础,所以对山水的审美也具有共同性,“山水质有而趣灵”,故而能体会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庄子·知北游》)的境界。从山水中获得的极高审美境域就是儒道在实现人生的价值与追求生命的意义的过程中共同的情感体现。“万物生意最可观,此元者善之长也,斯所谓仁也”(《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仁是最真实的情感,它源自自然界的生命创造,同时,仁也是一种能激发生命的活动。仁是本,“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仁”作为人之本性,是可以超越于人而达至世界万物的终极境界的。借鉴朱熹的话“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语类》卷一),它是一个“极崇高而又切实的生活理想,不玄远,无神秘”[8],便是程颐所说“仁与天地万物一物也”(《遗书》卷十一)的天地境界。
一般而言,儒家将审美价值等同于伦理价值,注重审美的教化作用,即所谓“成教化,助人伦”。“孔子追求的是一种社会中的道德境界,而庄子追求的则是一种哲学中的天德境界,这两种不同境界的相同之处,即都是高级的精神境界,并且都是从自然或山水中体验而来”[9]。从《论语》中记载的孔子与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谈人生理想时的态度可以看出孔子的山水境界,当曾皙说:“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与”乃嘉许之意。孔子对几个弟子的回答都不置可否,唯独对曾点的回答表示感慨与赞叹。古今对此异论纷纭,因为孔子的仁学一般是强调人世现实,偏重与伦理道德的结合,而且,“由于实践理性对情感展露经常采取克制、引导、自我调节的方针,所谓以理节情,‘发乎情止乎礼义’,这也使生活中和艺术中的情感经常处在自我压抑的状态中,不能充分地痛快地倾泄表达出来”[10]。但在这里,孔子发出了“吾与点”的感叹,“山水比德”的思想似乎减弱了。这说明,只有置身于山水中,孔子才可以暂时释放具体生活中的理性之思而进入一个单纯、愉快和自由的天地境界,摆脱“克己复礼”的行为约束,通过置身于对“仁”的更有意义的领会而进入到真情畅遂、一片天机的境界,此种山水审美境界与孔子的道德境界融合为一种天地境界,这是人生最高的境界——与道合一的境界。一个人的精神,沉浸消解于最高的审美境界之中时,是“初无舍己为人之意”,是“不规规于事为之末”,超越功利欲望,达到“物我合一”、“物我两忘”的天地境界,也即朱熹描述的“人欲尽处,天理流行,随处充满,无稍欠缺”(《朱子集注》)的境界。因为“在我国传统思想中,虽然老、庄较之儒家,是富于思辨的形上学的性格;但其出发点及其归宿点,依然是落实于现实人生之上”[11]53。古人在山水中所表现的“出世精神”,实际上是“入世情结”的延伸与转型。出世是为了更好地实现现世不能达成的愿望与梦想,终在天人之际。中国人从未将此岸与彼岸看得泾渭分明,而是把世界当作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出世与入世,貌似南辕北辙,但实际上,两者却有着共同的落脚点,有着共同的出发点和共同的归宿——自然山水。
山水本身并没有先验的道德性质,是孔子赋予了山水以“仁性”。这种“山水比德”的思想摒弃了枯燥的道德教化行为,而具有审美性灼灼光华的感性特征。与道家的山水思想不同,孔子并没有为追求玄远而超越现实生活,而是追求生命存在的真实意义,自然而然地顺应“仁”的要求。因为“仁对于一个人而言,不是作为一个标准规范去追求它,而是情绪中的享受。这即是所谓快乐的乐(洛),以仁德为乐(洛),则人的生活,自然不会与仁德相离而成为孔子所要求的‘仁人’”[11]39。在山水审美的过程中,乐与仁的会通统一,便超越了儒家一般的人伦关系。在对山水的审美体验的刹那,仁性得以呈现。理性与审美的自然交融亦是彰显仁性的一种方式。
[1]陈鼓应.老庄新论(修订版)[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2]徐复观.中国仁性论史(先秦篇)[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81.
[3]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149.
[4]杜维明.道、学、政——论儒家知识分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103.
[5]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117.
[6]蒙培元.情感与理性[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24.
[7]艾兰.水之道与德之端——中国早期哲学思想的隐喻[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46.
[8]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2.
[9]陈池瑜.孔子的山水比德思想及对中国山水艺术的影响[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2).
[10]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37-38.
[11]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