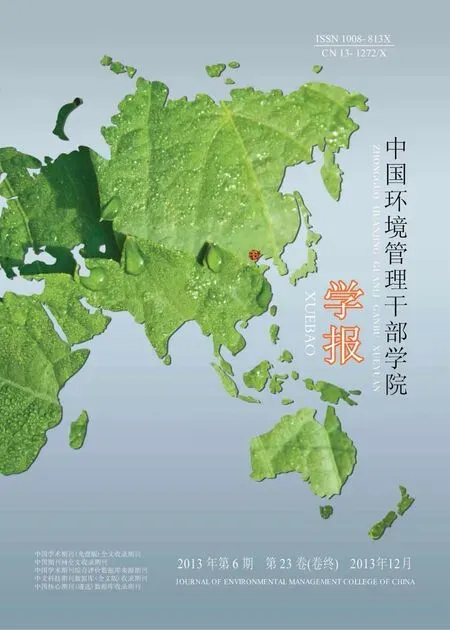基于人的自私性的生态哲学分析
——论生态问题
2013-04-12陈浩
陈 浩
(南京大学 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生态问题非人类社会天生的问题,追溯历史,这个幽灵在工业革命时就开始浮现了,但人类并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或敏锐觉察到它在未来会肆虐起来。尽管东西方很早就有关于自然保护的著作与思想,但直到1962年卡逊的《寂静的春天》问世(如一颗重磅炸弹抛向自我感觉良好的人类社会),才广泛激起一种深度的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忧虑,生态问题受到了全球前所未有的关注。这种关注从生物学、生态学、环境学延伸到经济学乃至整个文化与思维层面。或说,卡逊的书是对人类自我满足情绪的理性批评,她将人们带回到现代文明丧失的基本观念:人类与自然环境相互融合[1]。到1972年《增长的极限》发表,人们的关注扩展到全球性问题:人类发展的困境。它指出在高增长、高污染、高消耗下经济增长存在极限,并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模型的雏形[2]。后来环境与发展大会召开,人类社会从各方面反思自己,开始政府决策、利益集团及民间力量之间的博弈。最终上述问题在哲学上被剖析,生态哲学应运而生,反思更深刻和富有一般指导意义。它重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地关系),反思既有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乃至整个生产方式[3,4]。而人是最核心的,因此对人自身特性的辩证解析或可解释和帮助解决生态问题。
1 自然观与生态哲学概述
1.1 自然观的演化
对自然的认识和看法构成了自然观,如何看待自然和人的关系是生态哲学避不开的基本问题。历史上,人类的自然观经历了崇拜、适应、征服三个主要阶段[4],现在趋向和谐共处的观点。重大转变有两次:工业革命后是“向大自然宣战”,大自然仅是人类征服与控制的对象[1],自然的价值趋附于人类的利益[4];20世纪前期出现的全球问题及绿色运动促成了当代人的生态意识[5],要求“善待自然”。这些转变是人对人地关系的认识变化,更是人对自身的定位变化,体现了人的复杂性和能动性。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清晰地展示了人类自然观的变化,并告诫“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6]。这种告诫是富有远见的,但没有引起当时社会的关注,因为世界正处在资本主义的扩张与掠夺中。
1.2 生态哲学的思考
生态哲学是人类对人地关系和人人关系的反思,考察对象是生态问题与生态系统,包含人、自然及社会。包庆德认为生态哲学既是现实生态问题的深层哲学思考,又是对生态分支学科哲学底蕴的揭示和扬弃,可为人、自然及社会综合优化发展提供一般思路和方法论[3]。这种思考直接扩展到人类的生产方式、技术文明与人文关系上。美国环境伦理学家罗尔斯顿提出地球是人生存的“家园”,应承认其自然价值;单纯以人为中心作环境决策,会发生只求短期效益的弊病[7]。而笛卡尔—牛顿的传统哲学强调主—客二分,人类为中心,实行一种实际上“反自然”的社会—经济—消费生活[8]。因此具有可持续发展思想倾向的生态哲学可指导人类实践转向。但陈红桂认为生态哲学自身存在的缺陷和矛盾,使之无法彻底澄清发展过程中理论与实践的困惑[9]。如此,关于发展的哲学从传统的绝对人类中心主义走到生态哲学的自然中心主义,走到当下的相对人类中心主义。
在生态哲学上,马克思主义被给予很大关注。他把生态问题看作通过人的实践活动而历史生成的关系性存在,认为只有在实践所建构的关系性存在中,人与自然“才彼此密切地关联着”,“自然的历史与历史的自然”才达到了高度的统一[4]。在北美,这是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生态哲学),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文化和价值联系[5]。
然而,上述研究都是在大的层面上展开,认识到人的核心作用,都围绕人地关系,而很少有人从更小的尺度人性层面考察之。马克思论证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时,正是从人性出发,论证要使人的本质力量得到充分的自由发展就必须消除私有制[10]。
2 生态问题的哲学分析——基于人的自私性
2.1 人性问题——人的自私性
东西方在各自早期文明已探讨人性的问题,各种学说组成了“人性论”。朱光潜认为人性是人类自然本性[10]。人性具有客观存在性,而且是具体的,它必然影响着具体的行为人。那么,人性是单一的吗?不是。古今关于性恶性善的争论可证明它至少分为两大面。实际上,人性是复杂的,对人性低劣与高尚的认知也在演化。这里要探讨的是人性一个更小的方面:自私性。它主要体现在自身利益优先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原则上,具有强烈的排他性或异己性,带有短视性。它包含两层含义:人对自然的自私性和人对人的自私性。个体具有的自私性,在市场经济下无所不在,当这种特性借助资本、技术、权力等“武器”后便膨胀起来,表现出强烈的物质欲和占有欲。这是出现生态问题的最基础的原因。
2.2 资本的激发和漠视自然的原因
资本主义扩张的历史也是人的自私性膨胀的历史。在人类自私性扩张的路上,资本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首先,传统哲学理论带有对自然的偏见,导致主、客体分离,产生人类中心主义。但过去因为社会生产力不发达,人们并没有把普遍的偏见扩大化,因此整个王权时期生态问题并不严重。而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开始了原始积累。在自由市场阶段,市场主体自由逐利,资本的本性也反映了人的本性。马克思认为资本的本性是追求利益最大化和体现人人关系的社会本性,在这种资本逻辑下,自然环境只作为资本的要素服从于其增值的逻辑[4]。周志山认为资本主义发展史是一部资本在全球的扩张史,也是一部掠夺性开采自然资源与破坏生态环境的历史。在此,资本首先极大激发了人类的贪婪、占有欲、虚荣等自私性的成分。有人形容,尽管个体批判君主专制,但若给其足够的手段和恰当环境,他也极可能成为专制君主,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其次,在人类中心主义思潮下,资本刺激人类掠夺自然,加剧了人地关系的对立,同时也加剧了人人关系的对立。人地关系被看作人人关系的基础,对自然的漠视也深刻寓含在人与人之间对抗的、不平等的社会关系中。人在逐利上的天然利己性使其无法关照到其他人,更无法关照到“没有感情和知觉”的自然环境。因此,这也决定了人对自然的关系的反思必然在对人人关系的反思之后才可能比较顺利和深刻地展开。事实上,19世纪甚至更早人人对立关系的改善就大规模开始了,到20世纪中期人类对自然的漠视开始被根本性扭转,逐渐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全民共识。
最后,在自由市场阶段后出现国家资本主义,人的自私性便不再是个体的事情了,开始以一个群体或者集团的名义对外扩张。从环境意识上看,它是已出现环境觉醒的发达国家或优势地区向还挣扎于旧体制或温饱线的国家和地区的扩张,伴随经济全球化出现生态问题的全球化。这是一种群体自私性。
2.3 不同尺度的自私性与生态环境问题
2.3.1 个体层面上
在市场经济发展初期,个体自私性在经济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上扮演了重要角色。粗放的生产方式下,人们各顾自身利益,向自然索取生产要素。19世纪的西欧和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都处于个体经济发展-积累阶段,给资源与环境带来巨大的压力。人们执迷于自我财富的追逐与膨胀,很少考虑对自然的影响。这是个体自私性扩张时相对不受约束的阶段。这时的生态问题应该是局部的和地方性的。
2.3.2 社会层面上
个体的物欲被激发后,逐利成为一种社会风气,那么又反过来加深个体印象。当群体的自私性在对自然关系上显著起来时,全民运动式地掠夺资源便对环境造成极大的破坏性。如欧洲殖民者涌入美洲,掠夺当地资源以致森林锐减、灾害肆虐;中国20世纪后期各地掠夺式发展,造成水污染严重。上述影响常造成区域性环境灾难,具有长期性甚至不可逆转性。此外,社会生活与消费方式的影响不容忽视。数据显示[11],20世纪末美国人口只占全球人口的4.7%,却消耗40%的石油、36%的天然气、46%的铝等,排放30%的废气,产生70%的固体废物,是当之无愧的“头号能源消耗大国”和“头号污染大国”[12]。这种消费方式不可普及,是地球无法承受的,实质是发达社会维持自身享受而对发展中社会不平等的剥削,进而造成资源输出地对当地环境的自私。
2.3.3 国家层面上
它表现为政府对内和对外的自私性。对内上,政府也是市场参与者,也有自己的利益。布坎南认为政府决策者如同经济人一样是有理性的、自私的人,他们在政治市场上追求自己最大的利益——政治利益[13]。政府一方面作为环境保护的领导者,另一面也跟其他利益主体进行博弈,在巨大的经济效益面前就可能妥协。私有制从制度上认可了人的自私性,但无法调和不同利益体之间的矛盾。尽管面对自然,人类有共同利益;但当代全人类分化为具有不同背景的国家与民族,存在着不同的特殊利益。在共享有限的地球资源中,不同利益主体发生矛盾和冲突时,“国家民族利益优先”仍是当代处理国际事务中的一条基本原则[4]。如美国先用别国的资源,又不愿为其环境问题买单。这是全球生态问题难以协同解决的直接原因。
3 人性的拷问与环境伦理观
不可否认,一切生态问题实质是人的问题。人地关系的失调实际上是人与人关系的失调[4]。周志山认为在私有制占主导的社会里,“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人类整体中心主义”必然表现为彼此矛盾的个人利益、群体利益或个人主义、群体主义,背后存在着以国家利益为主导的“力量较量”或“强权逻辑”,导致社会关系的不公。这是造成人地关系紧张和对抗的根本原因,要从人自身特性进行反思。人性层面上,消除人的自私性是不可能的,个体对衣食住行的需求构成了他的生物基础,而纵欲主义已经被历史的实践否定,因此容忍个体适当的自私性是必须的。这就要求从反方向对人们进行道德和伦理的教育。文化层面上,既有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也存在缺陷。既然绿色文明成为诉求,就必须首先普及到思维领域,提倡绿色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
环境伦理学即从道德层面研究人类与环境之间的伦理道德行为关系。在东方尽管古人提出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但不深刻,而且是从统治者的角度来认识,是朴素的环境伦理。而对绝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促成了生态哲学,从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观及方法论上进行革新,认为主—客体是辩证统一的,不是谁屈服于谁。这一点讲,生态问题也是主、客体分离的结果,在技术、资本等刺激下,主体欲望膨胀而使其忽略了二者的关联性。莱奥波尔德很看重情感在维系人类与大地间关系的中介作用,其《大地伦理学》被认为是现代伦理学的经典之作[14]。他强调人对自然的伦理和道德情感,自然作为客观存在具有其自身价值,但在探讨人与自然的伦理道德关系上产生了分化。值得肯定的是环境伦理学的出现是人类对人地关系重新思考的产物,作为一种新价值观来调整人对自然的不当认识和行为。或说,它的出现使人们开始有意识地约束自身欲望,是人对自然乃至对人的自私性的一场思想整顿。这或许是对“How to feed a hungry world”[15]的另一种回答。
4 结论
承认人性的存在,也必须承认人性的复杂性,正是其中自私因素在资本、科技等帮助下扩张而伤害了自然,于是在哲学上给予反思,从机械论的绝对人类中心主义,到环境伦理学,到马克思生态哲学。从人性层面上,不过是努力挖掘其中更和谐的成分,并使之成为社会共识,而上升为伦理、法律等,以指导人们的实践。因此,对人的教育、对人性更良善部分的挖掘和培养可以作为预防和处理生态问题的根本措施之一。
[1] 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M].吕瑞兰,李长生,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2] 丹尼斯·米都斯.增长的极限——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研究报告[M].李宝恒,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3] 包庆德.生态哲学的研究对象与性质[J].内蒙古社会科学,1998(2):6-9.
[4] 周志山.马克思生态哲学的社会视阈与科学发展观[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5):85-92.
[5] 何萍.自然唯物主义的复兴——美国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评析[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2):13-20,115.
[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357-616.
[7] 盖示山.世纪之交的哲学和人类——第19届世界哲学大会侧记[J].哲学研究,1993(11):76-78.
[8] 余谋昌.生态哲学与可持续发展[J].自然辩证法研究,1999,15(2):47-50.
[9] 陈红桂.从生态哲学走向发展哲学: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必然[J].理论探讨,2004(1):26-29.
[10] 朱光潜.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问题[J].文艺研究,1979(3):39-42.
[11] 包庆德,张燕.关于绿色消费的生态哲学思考[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4,20(2):4-7,28.
[12] 卫建林.历史没有句号——东西南北与第三世界发展理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361.
[13] 张喆,刘贵振.政府和政治人行为的自私性表述——浅析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理论盲点[J].全国商情:经济理论研究,2005(9):61-62,76.
[14] 叶平.人与自然:西方生态伦理学研究概述[J].自然辩证法研究,1991,7(11):4-13,46.
[15] 匿名.How to feed a hungry world[J].Nature,2010(466):531-5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