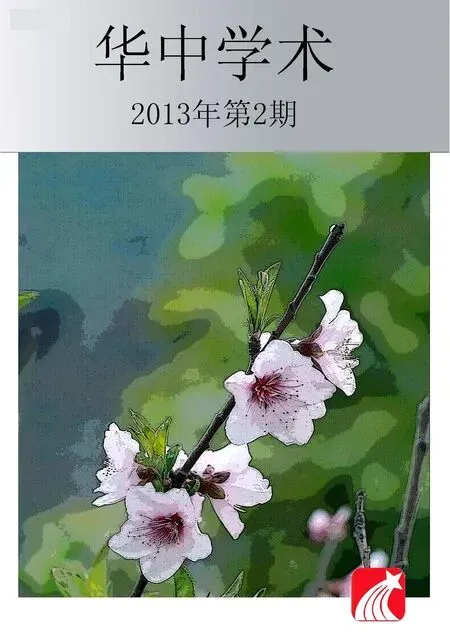“动+介”组配及“V+自+O”结构功能研究
2013-04-12罗耀华
罗耀华 牛 利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动词到介词的演变,引起很多学者的关注。演变之后,大部分介词用在动词前作状语,但也有少数可以置于动词后与所带的宾语一起充当动词的补语,或者先和前面的动词结合再带宾语,如“到、给、向、往、在、于、自、以”等。从构成动介复合词的可能性来看,越是古代汉语的介词越是容易后附于动词成为复合词,如“……于”、“……以”、“……自”、“……在”式复合词数量相对较多[1]。“自”是古代汉语中就存在的介词,一直沿用至今,其后附于动词并与之复合的可能性比较大。
目前“自”及相关结构的研究还相对薄弱,值得进一步研究。首先“自”的词性问题,“自”的介词用法很早就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基本上为“从”所取代,除动词前的“自”的介词性很强外,保留在动词后的介词“自”词性有无变化?其次,介词“自”的语法化问题研究还不够深入。“V+自+O”结构中,“自”前的“V”句法语义特征如何?“自”后的“O”需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本文考察“V+自+O”结构,并试图对上述问题进行回答。
一、动词V的句法语义特征
以《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为参考,通过对北大CCL现代汉语语料库、现代汉语平衡语料库的检索,发现能进入“V+自+O”结构中的V有99个,列举如下:
裁、采、产、抄、承、出、传、创、诞、得、订、定、夺、发、仿、购、归、获、寄、剪、荐、借、来、炼、流、录、买、飘、起、抢、窃、取、娶、摄、始、驶、溯、偷、袭、写、选、学、移、译、引、源、缘、摘、肇、转、长、载、征
编译、采集、产生、抄纂、承继、承袭、出身、传承、传袭、发现、发源、翻译、改编、继承、剪接、来源、剽窃、取材、取名、收编、溯源、脱胎、撷取、选编、选辑、选录、选聘、选译、沿袭、沿用、延续、演化、衍化、衍生、遗传、摘编、摘录、摘选、摘译、摘引、转抄、转录、转引、转载、转摘、追溯
(一)V的音节限制
从音节的角度来看,“V+自+O”结构对V的音节数量具有一定的限制。一般而言,单音节动词更容易进入这种格式,双音节动词大部分进入格式受限,随着语言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双音节动词能进入“V+自+O”结构中。根据台湾“中央研究院”现代汉语平衡语料库和近代汉语标记语料库搜索结果,现代汉语平衡语料库中双音节的V有19个,而近代汉语标记语料库中无双音节的V。
语料表明,能进入“V+自+O”结构中的双音节动词大多数与自身构成成分有关。一类是双音节动词中的两个构成成分分别可以进入该结构,如“来源”、“摘选”,它们都可以分别组成“来自”、“源自”、“摘自”、“选自”,可见这些动词的两个构成成分都可以单独进入“V+自+O”中。一类是双音节动词只有前一成分可以进入该格式,后一成分不能进入该格式,如 “取材”、“出身”,其中只有“取”、“出”可以进入到“V+自+O”结构中,而“材”、“身”都是名词,后面不能跟介词。一类是双音节动词前一成分不能进入,只有后一成分才可以进入该格式,如“剽窃”、“衍生”,其中“剽”、“衍”不能与介词“自”组合,只有“窃”、“生”可以与“自”组合进入“V+自+O”格式中。
当然,也有少数能进入该格式的双音节动词与其构成成分无关,如“脱胎自”、“延续自”等。另外,进入“V+自+O”结构的双音节动词其内部结构也是不平衡的,其中主要是并列式,如改编、摘引、摘录、摘译;有的是动宾式,如“出身”、“取材”、“脱胎”;有的是偏正式,如“沿袭”、“衍生”、“沿用”。
随着进入“V+自+O”结构中的双音节动词数量的增加,结构更加复杂,这说明该结构对双音节动词的接受度越来越高。究其原因,我们认为有以下几方面:一是汉语的双音化趋势。汉字产生时,以单音节字为主,一个音节代表一个汉字,表达一个意义,在使用过程中,由于汉字数量少,表达时所承担的意义逐渐增多,为了更准确地表达意义,汉字便逐渐向双音节方向发展,因此原先的单音节汉字便被双音节字所替代,如“摘”字,根据方式不一衍生出“摘选”、“摘译”、“摘引”;二是类化的作用。由于单音节的V能进入“V+自+O”这一结构中,精确表达其意义的双音节V也便逐渐地类化后进入该格式,如“摘”能进入“V+自+O”结构中,精确表达其意义的“摘选、摘译、摘引”等也逐渐进入到“V+自+O”结构中。
(二)V的语义特征
能进入“V+自+O”结构的V不多,这一格式除了对V有音节上的限制外,它对V在语义方面也有规约。
首先,能进入此格式的V具有[+源起义]语义特征。[+源起义],即指出事物或事件的来源或出处。进入“V+自+O”结构的V一般都自身具有[+源起义],如“产自、创自、诞自、来自、溯自、源自、发源自、追溯自、演化自”等。当然,并非进入这一结构的所有的V都自身具有这一语义特征,有些是这一格式融合后由“自”在语境中引出[+源起义]的。
其次,能进入格式的V具有[+获得义]语义特征。所谓[+获得义],即从无到有,或从零开始产生获得,或从他物中获取,或从他人手中获得,或从他处获得等,如“出自、裁自、购自、抄自、订自、获自、借自、买自、抢自”等。由于获得某一事物必有其来源,故这类V也可进入“V+自+O”结构。
总之,能进入“V+自+O”结构的V必须具备 [+源起义]或[+获得义],具备[+源起义]的动词基本可以进入这一格式,具备[+获得义]的动词如果在语境中加入“自”能产生[+源起义]的也基本可进入该结构,如果单纯只具有[+获得义]而不能产生[+源起义]的动词则难以进入该格式。当然,古汉语动词的残留用法,如“始自”、“肇自”等除外。
二、“自”的语法化及其演变机制
“语法化是指处在某些特定情境中的词汇项或结构式获得语法功能的过程,或是指语法单位的语法功能增强拓展的过程。”[2]通俗来讲,就是语言中意义实在的词转变为意义较虚的词,或意义较虚的词转变为更虚的词。基于此,“自”的语法化包括两个过程,一是实词虚化,二是“自”的并入。
(一)“自”虚化为介词
“自”最早是一个名词,指鼻子。许慎《说文解字》:“自,鼻也,象鼻形。”甲骨文中有本义的用例。如:
(1)“贞:有疾自”(《殷墟文字乙编》6385号卜辞)因“气息自鼻而出”,名词“自”便引申出动词义,其义为“由、从、始”。例如:
(2)故法者,王之者本也;刑者,爱之者自也。(《韩非子·法度》)
(3)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论语》)
两例的“自”都用作动词,例(2)中动词“自”单独作句子谓语,例(3)中动词“自”后带宾语,“奚自”是宾语前置用法。
动词“自”又进一步引申出介词义,表示“由、从”。介词“自”一开始只能引介方所,由于古人的时空观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于是发展出引介时间宾语,后在引介方所、时间的基础上词义的外延逐步扩大,发展成为可以引介来源、对象的介词。
“自”是汉语中最早出现的介词之一,“自”作为介词早在甲骨文、金文中就已经出现了。这一时期,它主要引介处所和时间,与谓语动词构成状中关系或述补关系。例如:
(4)辛巳卜,子贞,我自兹获。(《甲骨文合集》21829,一期)
(5)其自今日孙孙子子毋敢忘白休。(大系67县妃簋)
西周时,介词“自”的功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可以引介处所、时间,还可以引介方位和对象。例如:
(6)我来自东,零雨其濛。(《诗经·豳风》)
(7)象曰:负且乘,亦可丑也;自我致戎,又谁咎也。(《周易》)
春秋战国时期,介词“自”不限于引介表示处所、时间的起点、来源,还出现了表示处所和时间之“所在”的句子,“自”还能引介事物的来源,能与“及、至、之后、而、以来”等配合使用,形成固定结构,表示与述语有关的范围或者表示时间、空间或某一系列的起讫点,这些用法都是介词“自”到春秋战国时期的拓展。例如:
(8)初,公自城上见己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为吕姜髢。(《春秋·左传·哀公十七年》)
(9)先君叔振,出自文王,晋祖唐叔,出自武王,文、武之功,实建诸姬。(《国语》)
(10)我自夏以后稷,魏、骀、芮、岐、毕,吾西土也。(《春秋·左传·昭公九年》)
(11)自陕而东者,周公主之;自陕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处乎内。(《春秋·公羊传》)
(12)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也;无不亡之国者,是无不抇之墓也。(《吕氏春秋》)
两汉时期,由于介词“从”的兴起,介词“自”的部分功能逐渐被“从”取代,“自”逐步走向衰落。
六朝以后,“自”已经不是一个常用介词了。在《世说新语》中,介词“自”引介时间有5次,引介处所有9次,但这一时期的佛经中“自”无介词用法,可见,介词“自”主要保留在书面语中,口语中很少使用。
总之,自六朝以后,由于“从”的兴起逐渐取代了“自”的介词地位,介词“自”的使用越来越少,口语中很少出现,偶尔出现在书面语中,介词“自”的用法一直沿用到现代汉语中。
(二)实词虚化的机制
第一,隐喻。隐喻是指由一个认知域到另一个认知域的投射[3]。事实上,隐喻主要在一个实词义向另一个实词义转变以及由实到较虚转变的过程中起重要作用,隐喻机制只在虚化的早期阶段起作用[4]。“自”在早期虚化过程中,隐喻起到重要的作用。“自”最早是“鼻子”义,是名词,之后由“气息自鼻而出”隐喻出表动作的“由、从、始”义。由于“由、从、始”动词义必须指出事物的出处,于是后面便引进处所和方位词。根据人们认识事物的认知域投射的一般规律,由空间投射到时间,由较抽象的方向投射到具体的对象,“自”便产生“引进时间”义和“引进对象”义。这一系列的演变过程都发生在由实到实、由实到较虚的转变之中。至于“自”的“引进动作行为起自的处所和时间”、“引进动作行为发生或存在的处所、时间”义,我们认为是泛化的结果,即实词的语义部分消失,从而造成自身使用范围的扩大。
第二,句法位置及其内部的不平衡性。在多数情况下,词汇的语法化首先是由某一实词句法位置的改变而诱发的[5]。“自”最早单独做谓语,然后进入“自O”格式中,接着进入“自+O+V(P)”或“V(P)+自+O”连动结构中,“自O”进入连动结构便为其虚化做好了句法位置上的准备。
“自”进入连动结构是其虚化为介词的句法前提。当“自”进入连动结构中,刚开始还保持着动词特征,但是连动句是一个结构上不平衡的句式,它由两个动词连用,而一个句子中一般是只有一个动词为句子的核心动词,另一个则要降级为次要动词。由于“自”具有语义非终结性,当其进入“自+O+V(P)”、“V(P)+自+O”连动结构时,一般很容易降级为次要动词,它一直以次要动词的地位在使用的过程中就很容易进一步失去动词义而被虚化为其他成分。它之所以进一步虚化为介词,首先是连动结构这种句法结构容易产生介词用法,另外也有其自身语义变化的因素在内。这也符合时间一维性影响介词衍生的观点[6]:“在时间一维性的作用下,那些语义范畴与动作行为特征密切相关的动词,经常用作次要动词,长期使用的结果退化掉了与指示时间信息有关的动词句法特征,最后演变成了介词。”
(三)介词“自”的并入
并入(Incorporation)是指一个语义上独立的词进入另一个词的内部,二者合并成为一个整体的过程。并入包括动词并入(Verb Incorporation)、名词并入(Noun Incorporation)、介词并入(Preposition Incorporation)等[7]。就汉语而言,最早进行汉语并入现象研究的是汤廷池,“汉语语法的并入现象,有发生于复合词内部的词法上的并入,也有发生于词语或词组之间的句法上的并入;有以动词为主要语的并入,也有以名词为主要语的并入;被并入的语法范畴则包括名词、介词、动词、形容词、副词等”[8]。从上可知,“自”并入到其前面的谓词V中,实际上是介词“自”的进一步语法化过程。
第一,“自”的并入过程。
“自”是产生比较早的介词之一,早在甲骨文、金文中,“自”就能用于动词之后,不过常常在这种结构中间插入别的成分,组成“V+O1+自+O2”。例如:
(13)贞,其有来羌自西。(《甲骨文合集》6597,一期)
(14)惟王初迁宅于成周,复禀武王丰福自天。(《殷周金文集录》)
上例中,“自”为介词[9],我们认为其中的“自”仍可能为动词用法。
在甲骨文、金文中,也出现了“自”直接用在动词后的用法[9],形成“V+自+O”结构,但这种用例比较少,这时“V·自”的雏形才慢慢形成,但不够成熟,这时的“自”也可以看作是一个介词。
西周时期,“V+自+O”这种结构日趋普遍,能与“自”组合的V增多,这时这一结构开始慢慢成熟。例如:
(15)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穷也。(《周易》)
(16)乱匪降自天,生自妇人。匪教匪诲,时维妇寺。(《诗经·大雅》)
春秋战国时期,虽然由“自”组成的介词短语的位置基本上移向谓语前,但能进入“V+自+O”结构的V也更加广泛,出现了“至自、出自、还自、反自、退自、归自、济自、入自、降自、涉自、生自、升自、卷自、射自、登自、使自、步自、慕自”等用例,这里的“自”全为介词,这说明这种结构渐趋成熟并逐步稳定下来。
两汉、六朝时期,由于“从”的逐步兴起,“自”已经不再是一个常用的介词了,但“V+自+O”这种结构还是由于某些原因仍然偶尔得以使用,这时的“V”也出现了一些新词,如“得自、发自、始自、肇自、来自、起自、选自、诞自、录自”,这种用法在六朝后仍然得到使用。
到了现代汉语中,这种用法得以沿用并保留下来,且结构更加稳定,其中“V”和“自”结合得也更加紧密,“自”还能赋予V一些其特有的语义,这使得人们更容易把这一结构当作一个整体进行使用,并具有组合成一个词的趋势。这一时期,除了继承一些前期的“V·自”组合外,如“出自、来自、生自、起自、归自”等,还衍生发展出了一些新的“V自”,如“抄自、译自、偷自、产自、取自、源自、仿自”等,其中的V也由单音节发展到可以为双音节动词,如“取材自、转载自、摘录自、摘译自、出身自、转引自”等。
第二,“自”的词性归属及其演变。
“自”很早就有介词用法,“自”与“V”组合在一起时,其性质就有了一定的变化。刚开始组合时,“自”的介词性质还很明显,其后的宾语主要为方位词、处所词和时间词,我们往往可以将“V+自+O”分为“V/自O”。例如:
(17)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处于郓。(《春秋左氏传》)
(18)世子生,则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皆立于阼阶西乡,世妇抱子升自西阶,君名之,乃降。(《礼记》)
进一步发展之后,虽然“自”在六朝以后用例减少,但能进入“V·自”结构的动词明显增多了。到了现代,“V·自”结构又有了一定的突破:首先是动词和“自”结合得更加紧密;其次是“V·自”后的宾语范围扩大,可以是方位短语、处所词、时间词、对象名词,甚至是表状态义的动词和形容词;再次,根据共时研究,进入“V+自+O”格式中的V一般要具有[+源起义],而有些动词只具有[+获得义],具有[+获得义]的动词获得时需要个源头,当其与“自”组合使用时,“自”便把其自身的[+源起义]传染给了动词V,于是,表[+获得义]的动词有了[+源起义]特征,“V·自”的整体义便得以凸显,“自”也就具有了类词缀的功能;最后,现代汉语中“V·自”的V由单音节发展到双音节动词了,双音节动词进入“V·自”结构正好说明“自”具有类词缀的趋势,也说明“V·自”更像一个词。因为双音节动词是由单音节动词类推产生而来的,单音节动词加“自”融合为一个词,便产生与之意义相近的双音节动词加“自”。以上都使得我们不能再把“自”看作是一个纯粹的介词了,反而让人觉得更像是一个类词缀。
“自”由于跟前面的动词在语音上相连,且二者共现频率高,有进入词库的倾向,具体表现在“V·自”之后还可以再带上一个介词,如“来自于”、“源自于”、“发自于”等,这些“V·自”可以看作是一个词了,这里的“自”可以看作是构词词缀。这些用法虽然数量少,但可以看作是“自”之后虚化的一个方向。
“自”的性质由介词到构词后缀的发展构成了进一步虚化的连续统,有很多“自”处于介词一端,有些“自”处于构词后缀一端(这一端出现的数量不多),而处于中间状态的“自”的用法最多,即上面所说的“自”的进一步演化阶段。那些“自”不能认为是介词,也不能认为是演化完成的构词后缀。这些“自”有些特殊之处,一方面,动词后的“自”和其后的宾语仍有直接关系;另一方面,动词后的“自”又和其前面的谓词由于韵律相结合,组合成了一个动词。鉴于此,这种处于介词和构词后缀的“自”,可以归为类词缀。
“V·自”具有词汇化的趋势,且有些“V·自”组合能够进入到词库当中。对于“自”而言,“自”处于介词到类词缀到构词词缀这一语法化的连续统上。
(四)“自”的并入机制
介词“自”并入到其前谓词中有多方面的原因,包括双音化的影响、韵律的制约、重新分析、类推作用等。
第一,双音化的影响。在古代,汉语以单音节词为主,一字表一义,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各种新兴事物的兴起,汉字难以满足社会的发展需求。为了便于交际,人们便在原有汉字的基础上进行改革,发展出双音节词。双音词表义的精确性、交际的灵便性,很快使得双音化成为汉语发展的一大趋势。双音化发展趋势势必会引发语音、词汇、语法各层面的变化。语音上,两个单音字由于共现频率过高便很可能结合成双音节词;词汇上,在双音化趋势的作用下,高频出现的相邻两单音字的语义可能相互融合,最终形成一个新词;语法上,双音化促使同一个句法结构中紧邻出现的两个句法单位发生融合,成为一个语言单位,共同充当句子成分。“V·自”的形成一定程度上是受双音化趋势在语音和句法上的影响而产生的。介词“自”由名词到动词到介词逐步虚化而来,其句法独立性逐步丧失,反而产生一定的黏附性。由于“自”与单音节动词V处于邻近的位置上,且长期共现使用,在双音化趋势的影响下,V与“自”便逐步结合。随着“自”语义的逐渐淡化,它与动词V之间的边界也逐渐削弱,“自”便逐步依附于动词V,与其组合成一个复合动词。
第二,韵律作用。“自+O”最早置于动词之后的句法格式是“V+O1+自+O2”,后来“O1”丢失而形成“V+自+O”的句法结构,这时的“自”还是一个介词。根据韵律学理论[10],汉语的普通重音一般是尾重音,而重音指派是由最后一个动词来指派的,介词不能指派重音给其后的宾语,所以,如果“自”后的宾语得到了重音指派,那么它不能是由“自”指派的,也不能是由动词“V”指派的(因为介词阻挡了其重音指派),它只可能是由“V”和“自”一起指派,即“V”和“自”组合成一个动词单位。那么“V”和“自”有没有组合的可能呢?
陆丙甫把心理学的“组块过程”说引入汉语研究中[11]。根据“组块过程”说,“V”和“自”由于紧连使用,人们便把它们组合成一个组块来使用,并且这个组块也符合韵律学的规则。音步是韵律系统中最小的独立单位[10],一个音步至少由两个成分组成。他还指出,韵律可以改变句法,或者使原来的词序位置发生变化,或者使原来的句法成分在性质上发生演变。“V”和“自”的组合过程中,刚好其中的“V”大部分是单音节动词,其和“自”组合恰好组成一个音步,“V·自”成为一个音步后,就组成了一个独立的语法成分,其后可以加动词标记词“了”,显然属于动词范畴,这时它们一起把重音指派给后面的宾语,使得整个句式符合韵律的要求,也使得“自”的性质由原来的介词演变成了类词缀。
第三,重新分析。重新分析在“V·自”的组合中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所谓重新分析(Reanalysis),是指属于一定范畴的语法关系在语法的运作过程中被重新分析成为另一种语法关系。Langacker形象地给重新分析下了一个定义[12]:没有改变表层表达形式的结构变化,一个可分析为(A,B),C的结构,经过重新分析后变成了A,(B,C)。“V+自+O”最开始是分析成“V/自 O”,如“至/自齐”、“反/自鄢陵”,后来由于“自”的语义范围进一步扩大,其词性更加虚化,再加上韵律的作用,所以重新分析成了“V自/O”。如“引自/《论语》”、“源自/无辜”、“始自/二十世纪”等,这样经重新分析后“V·自”就成了一个整体。
第四,类推作用。所谓类推,指在语言的某种其他规律模式的影响下语法和词汇形式发生变化的过程和结果。重新分析是句法的创新,而类推则是新规则的推广。“V·自”刚开始组合时,V还是单音节动词,随着语言的发展,“V·自”结合的越来越紧密,词义慢慢开始渗透,能进入此格式的V也慢慢增多,到了现代汉语中,“V·自”越来越多,产生了如“来自、源自、始自、摘自、译自、引自”等一列组合。在类推作用的推动下,V慢慢地由单音节动词扩展到双音节动词,如“摘引自、摘录自、摘译自、选译自”等一列具有共同语义特征的词,并且有进一步扩展的可能,这使得“自”看起来更像一个类词缀,“V·自”的词汇化趋势也得到凸显。
三、宾语O的考察
(一)宾语O的音节数量
从韵律上看,“V+自+O”结构语音停顿时一般会停在“自”后,当V为单音节时,单音节的动词就刚好和单音节的“自”组合成一个音步。“V自”是一个双音节的音步,因此后面的宾语一般也要是双音节的词或多音步的短语。当V为双音节动词时,由于语音停顿在“自”后,且介词“自”自身后面本来就不可以接单音节宾语,因此后面的宾语一般也要是双音节的词或多音步的短语。
(二)宾语O的四种情况
根据语料考察发现,“V·自”后面的宾语O,大致可以分为四种类型:表处所的处所名词及短语、表时间的时间名词、表涉事对象的指人或事物的名词、表示状态的动词或形容词,其中表状态的宾语出现得晚,能进入此格式的不多。
第一,表处所义的宾语。“V·自”后面的O表处所义时,可以是处所词或处所短语,表示事物的来源或出处。例如:
(19)“事实上写这篇稿子的记者并没有采访过我,迄今为止两人还未曾见面,也未通过电话,不知上述报道引自何处。”戴均良表示。(翟伟、顾瑞珍《“我国将设50个省区市”传言不实》)
(20)最初的龙井茶产于杭州龙井村。村外有一口“龙井”,井中泉水出自山岩中,四时不绝,水味甘冽。(张爱群《历史悠久的龙井茶》)
第二,表时间义的宾语。“V·自”表示事物的来源或出处,除了表示处所方面的来源,时间也是一个重要来源,所以表时间的名词性词语,也经常出现在“V·自”后充当宾语。例如:
(21)封建社会部分展示了公元前475年到公元1840年的历史,其朝代起自战国,历经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辽、宋、西夏、金、元、明、清。(《中国儿童百科全书》编委会《中国儿童百科全书》)
第三,表对象义的宾语。事物或事件的来源除了可以是处所、时间外,也可能源于某个对象,这对象可以是指人的,也可以是指物的,因此“V·自”后面的宾语,也可以是表对象义的指人或指物名词。例如:
(22)本届年会的礼品取名“乾坤”,意为揭示在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下,更侧重资源、环境、秩序,注重循环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呼吁亚洲和世界共同创造和平、秩序、协调、持续的发展观。其创意出自93岁高龄的国学大师季羡林。(王英诚、孟娜《博鳌亚洲论坛2004年年会花絮:迎宾小姐学历高》)
第四,表状态义的宾语。“V·自”后面的宾语有时可以是表状态义的动词或形容词,表示某一情形源于某一状态,这样的用法后起,用例不多。例如:
(23)伟大和平凡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伟大往往出自平凡。(蒋邦桢《再谈如何强化典型宣传》)
四、“V+自+O”结构的句法功能
介词短语可以作定语、状语、补语,不能作宾语、谓语、主语,然而动介宾结构却有些不同,它们的句法功能不受限于介词短语入句的功能。“V+自+O”作为一个动介宾结构,既可以充当句子的谓语,也可以充当句子的定语、状语、主语和宾语,还可以进入连动句式的第一连动项上。
(一)“V+自+O”充当谓语
语料表明,“V+自+O”可以充当句子的谓语部分,“V·自”和“O”分别充当句子的动词和宾语。例如:
(24)谁都知道,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优秀的影视剧首先得益于优秀的剧作,优秀的剧作出自优秀的编剧之手,这应该是人所共知的常识。(卞庆奎《中国北漂艺人实录》)
(25)胡椒产自苏门答腊、马来亚、西爪哇和婆罗洲。(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
上例中,“出自优秀的编剧之手”充当复句中的小句的谓语,“产自苏门答腊、马来亚、西爪哇和婆罗洲”充当单句的谓语。
(二)“V+自+O”充当定语
“V+自+O”可以充当句子的定语,它可以是主语的定语,也可以是宾语的定语。例如:
(26)日本的节日很多,既有源自中国的端午节、重阳节、春节等,又有日本传统的节日,其中以樱花节最具特色。(《中国儿童百科全书》编委会《中国儿童百科全书》)
(27)这些发自肺腑的话语,不仅仅表达了青海代表团老一代和新一代建设者的心声和精神风貌,也反映了所有参加“两会”的代表、委员的心声和精神风貌。(1996年3月9日《人民日报》第二版)
例(26)中的“V+自+O”充当宾语的定语,例(27)中的“V+自+O”充当主语的定语。
(三)“V+自+O”充当状语
“V+自+O”也可以充当句子的状语,经常在后面加上一个“地”字以显示这种关系。例如:
(28)一位40岁的民工说:“我又看到了希望。真希望具体的管理部门能发自内心地帮我们,把总理的话落实到我们身上。”(周效政《政府工作报告充满人文关怀》)
(29)由于不公正的命运而注定在头脑简单的人之中生活,被剥夺了知识,但是他们更天然地、更出自本性地接近像大部分受教育的人那样的杰出的人呢?(马塞尔·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
上例中,“发自内心”作动词“帮”的状语,“出自本性”作动词“接近”的状语。根据语料,能做状语的“V+自+O”中的V不多,这些V具有[+内向性],如“发自内心”、“出自肺腑”。
(四)“V+自+O”充当主语或宾语
“V+自+O”也可以进入句子中,充当主语或宾语,但这种用法非常少。例如:
(30)出自望族是令人尊重的,因为这种人更容易获得先人庇荫和世交。(T·霍布斯《利维坦》)
(31)它的最大特点在于强调“出自最佳生态环境”。(1995年《人民日报》)
上例中,“出自望族”充当句子的主语,“出自最佳生态环境”充当句子的宾语。
(五)“V+自+O”充当连动句的前一项
“V+自+O”还可以进入连动句式,充当其第一连动项。例如:
(32)国内也有人出自良好的愿望开辟内销市场,但大都以遗憾告终。(1994年《报刊精选》电子版)
(33)第二年他出版的巨作《骑牧队》,其情其景,完全是采取自阿富汗骑牧人家生活所得灵感而写下的带着深情厚谊的形象。(约瑟夫·凯塞尔《回顾历史》)
(六)句法功能小结
总上,“V+自+O”结构主要充当句子的谓语、定语和状语,它也可以充当句子的主语和宾语,甚至进入连动句的第一项。当然,后面几种用法还比较少见,一般来说,只有当“V·自”融合为一个动词时才具有此类句法功能。
通过对“V+自+O”结构的研究,我们发现能进入这一格式的V必须受到语义和音节上的限制;宾语O随着发展演变,种类也有所增加;“自”经历了由名词到动词再到介词的一个实词虚化的过程,它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并入到其前面的谓词中,甚至有可能脱落为零形式的趋势;作为一个整体,“V+自+O”结构的各发功能也突破了介词结构的局限,功能出现泛化。
注释:
[1]陈昌来:《介词及介引功能》,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16页。
[2]Hopper,Paul,J.& Traugott,Elizabeth,C.Grammaticalizati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p.15.
[3]Lakoff,G.&Johnson,M.Metaphorweliveby.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p.10.
[4]沈家煊:《实词虚化的机制——〈演化而来的语法〉评介》,《当代语言学》,1998年第3期,第41—46页。
[5]刘坚、曹广顺、吴福祥:《论诱发汉语词汇语法化的若干因素》,《中国语文》,1995年第3期,第161—169页。
[6]石毓智:《时间的一维性对介词衍生的影响》,《中国语文》,1995年第1期,第1—10页。
[7]Baker,Mark,C.Incorporation.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88.p.10.
[8]汤廷池:《汉语语法的“并入现象”》,《清华学报(台湾)》,1991年新21卷第1期,第215—218页。
[9]黄伟嘉:《甲金文中“在、于、自、从”四字介词用法的发展变化及其相互关系》,《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1期,第66—75页。
[10]冯胜利:《汉语韵律句法学》,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46—198页。
[11]陆丙甫:《语句理解的同步组块过程及其数量描述》,《中国语文》,1986年第2期,第106—112页。
[12]Ronald,W.Langacker.FoundationsofCognitiveGrammar.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p.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