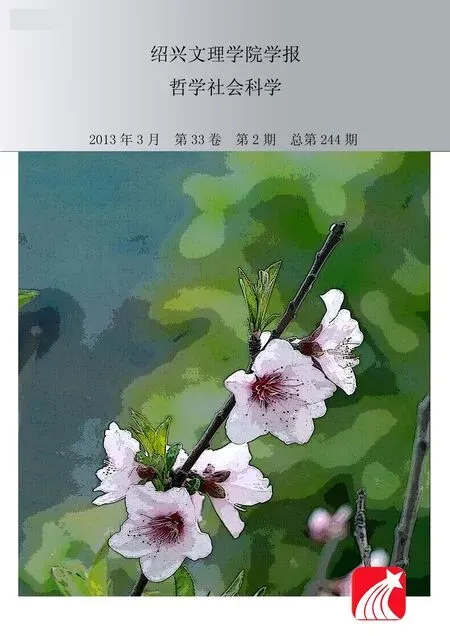论城市文化对鲁迅文艺观及思想的影响
2013-04-11王传习
王传习
(绍兴文理学院 元培学院,浙江 绍兴312000)
在中国近现代化进程中,城市步入转型期,以新的文化特征凸现于社会舞台,成为人口大熔炉,并对现代知识分子产生巨大的吸引力,五湖四海的知识人纷纷涌向城市,以此寻求迈向现代社会的契机。鲁迅正是这千千万万个身影中的一个。终其一生,他先后辗转绍兴、南京、东京、仙台、北京、厦门、广州、上海等地,与城市结下不解之缘,甚至决然地表示:“无论如何,也不能退入乡下”[1],城市构成鲁迅主要的生存空间。那么,半个世纪的生命时光,鲁迅为何一直奔走于城市之途,在新的环境中,呼吸着城市文化空气,从中会吸取怎样的精神养料?这一问题与城市的文化特质密切相关。其中,城市社会的包容性,能够提供丰富的立身立业方式,是城市吸引和影响鲁迅的重要动因之一。
一
按照城市社会学和文化学的理论,城市是社会分工精密的社会形态,形成较为成熟的职业体系,在政治、教育、文化、服务等领域源源不断孕生出就业机会,吸纳成千上万的人口,为之提供广阔的生活空间和用武之地。同时,城市也赋予人们身份和精神自由。欧洲曾流传的著名谚语:“城市的空气能使人自由”,便是指古代农奴逃入城市后,独立存活一年零一天,从而获准成为自由民,得到身心解放。美国城市学家R·E·帕克对此作过精辟论述,认为现代城市是自由人驰骋的疆场:“城市为个人的特殊才干提供了市场。人与人的竞争促使每一项特别任务都会选择最适宜的人去从事它。”[2]该特点正是城市的磁力之一,显示了城市包容、开放性,也是人口大量涌向城市的诱因。20世纪初期,正是中国城市现代转型的时期,如教育、翻译、印刷出版等快速兴起,产生报纸、杂志、出版社、书店等新的文化载体,使一大批固定和非固定的岗位应运而生,促进了工薪、版税、稿费制度的成型,从而使现代职业体系应运而生。这使告别科举、亟待新生的青年知识者看到了命运的曙光,他们往往背井离乡、远走城市,通过谋职、求学等方式而寻求希望之路。鲁迅在漂流“异地”的途中,首要面对的即是安身立命的问题,在此过程中,受到城市文化的直接影响,不仅对鲁迅的现实立足发挥了作用,而且对其文艺观的形成也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整体而言,城市的磁力,往往在鲁迅身陷逆境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如绍兴、仙台、厦门、广州等,当鲁迅每次遇到急流险滩,感到举步维艰之时,现代城市都充当了他的诺亚方舟,发挥了施救作用,使他重燃希望。它适时挽救了“乡间”[3]和“孤岛”[4]上一颗疲命挣扎的灵魂,帮助鲁迅从精神困境中找到一条生路,从而制止他退化为“村人”[5]、“木偶人”[6]。这从鲁迅的“东京→绍兴”“东京→仙台”“北京→厦门、广州”等行程中可见一斑。
鲁迅最初告别绍兴,是迫于改变运命的急迫感而作出新的人生选择,转入南京、东京求学,在这个早期拐点上,城市为他搭建了理想的天梯。有学者注意到:“这是从相对闭塞的传统的乡土中国的绍兴走向相对开放的南京,鲁迅由此开始接触日本与西方现代文化。”[7]从鲁迅在东京涉足翻译开始,继续受到城市的无形影响。有研究者认为:“直接动机可能是经济,用卖稿来补充微弱的留学生官费。当时兴旺的上海出版界很需要翻译小说。”[8]东京、上海,使鲁迅能够初步通过文艺实践,一方面实现理想吁求,一方面也有助于改善个人的生活境况。直到“弃医从文”,鲁迅才真正面临立足问题,并受到城市的直接影响。东京作为发达的国际都市,给予鲁迅的不仅是“新知识”的刺激,而且把他从“乡间”仙台救援出来。通过东京、仙台的对比,鲁迅开始意识到都市的优越性,深信东京具有“从文”的条件,因而自觉回归,并把它作为从业的起点。
回国后,当鲁迅在绍兴岌岌可危之际,城市再次向他伸出橄榄枝,使其脱险的是“人才多于鲫鱼”的“京华”。这是一次命运攸关的转折。在对大城市的翘首企盼中,鲁迅通过同乡许寿裳和蔡元培等关系,在教育部谋取到佥事一职,终于在京城找到一席之地,拥有固定收入和较稳定生活,此间,他兼做作家、编辑,另在北大、女子师范学校、世界语学校等兼任教职,从此正式完成向都市的转移。从鲁迅个人层面讲,这次进京意义非同小可,以此为转捩点,鲁迅真正摆脱了“村人”危境,较为顺利地找到了一条通向城市的通道,跻身城市社会。实际上,这一契机并非唾手可得。同样在京漂泊的绍兴籍作家许钦文,深刻体会到落户京城的艰难。他与鲁迅一样也曾寄居绍兴会馆,但生活一无着落:“于失业中从故乡漂流到北京,虽然住在会馆里,无须出房租,在大学里旁听,也不用交学费,但吃饭总是个大问题。”[9]身在人海茫茫的北京城,他从《语丝》《莽原》等新文学刊物那里难能获得酬报,因为“北京的新文学作家们郑重宣告取消稿酬”[10],而到别处谋职又投靠无门。为求一份工作,许钦文几经波折、遍尝冷眼,过着动荡不定、收入微薄的卖稿生活,经常遭遇“搜索枯肠写不出而恐慌”的情况,还曾从同乡、师友那里吃到闭门羹,甚至感到“精神上饱受创伤,心理上发生变态”[11]。来自异乡的知识者,在立足京城的过程中面临重重困难。在谋生压力下,许钦文作为城市边缘人,遭受了薄情寡义、人心浇漓,折射了异乡知识人在城市生存的血泪史。相比之下,得到同乡友人帮助的鲁迅,在进京之初没有经受太多冷遇。另外,漂泊城市的异乡人固然命运不济,但滞留乡间的知识分子下场更为凄惨。许多不幸的知识者“闭居越中”、郁郁而终,最典型的应为留日回绍的范爱农。鲁迅原本与范爱农的境况不相上下,都是留日回来的新式知识分子,但自鲁迅赴京后,就与畏友相隔于城乡,命运也有了天壤之别。当周围的友人终于跳出火坑、远赴京畿,沦落小城镇的范爱农更加形单影只、焦灼不安,也同样渴望早日摆脱乡间,因此“也时时给我信,景况愈困穷,言辞也愈凄苦。终于又非走出这熟人的家不可,便在各处飘浮”。反复托请鲁迅帮助谋职,热切期待着来自城市的福音书,“也许明天就收到一个电报,拆开来一看,是鲁迅来叫我的。他时常这样说”[12]。但每每音信杳然,他终被城市拒之门外,直至穷愁潦倒、落水身亡。如果将鲁迅与范爱农作一对比,我们会发现,由小城镇到都市的转变具有不可小觑的意义,它们其实已不仅仅是两个地点,而是现代知识人命运的分水岭。
同样,鲁迅在南国陷入“孤岛”“深山”时,上海成为他新的去向,对他脱离厄境起到了重要作用。鲁迅认为上海“较便当”,而且自信能够通过“卖点文章”[13]为生。在上海,他还作出了一个重要选择,即彻底摒弃了政府、学院等从业空间,主要以自由撰稿人、编辑、特约撰述员为业,还时时面临文网的封锁。即使如此,他也斩钉截铁地表示不“回到乡下”。这说明,城市给了鲁迅较为自由的立足空间,使他自食其力,不仅可以摆脱固定职业的限制,而且能够在精神上无所顾忌,因此,身心得到极大的解放。这也是鲁迅生存方式的一次巨大变化。
综而观之,在城与乡、都市与小城之间,鲁迅的谋生方式明显不同。在京、沪等发达程度较高的大城市,鲁迅被赋予多重角色,如职员、教师、撰稿人、编辑等,择业面相对较大,甚至兼多种职务于一身。即使在失去固定职业的情况下,也可以找到庇护所,绝境逢生。1926年,鲁迅因女师大事件卷入是非漩涡,并被章士钊免职,生活失去保障,在各种困厄之中,他在城市仍能获得生活来源,“因为我目下可以用印书所得之版税钱,维持生活”[14]。在30年代的上海,鲁迅走上了靠版税、稿费为生的道路,在社会罅隙中找到呼吸空间,如他所说:“现在北新书局尚能付少许版税,足以维持。”[15]终于,鲁迅在城市中把“非正常职业”变成了“正常职业”,争取了自我独立。这与城市得天独厚的优势是分不开的,丰富的从业空间、相对成熟的版税和稿费制度为鲁迅提供了外部保障。正如西方城市文化学者所说,城市是“自由人”的天地。如果置身于乡村和中小城镇,鲁迅无论如何也做不到这一点。相比之下,在中小城镇期间,鲁迅的从业角色比较单一,基本上都是教师的一重身份,立足的空间十分逼仄,生存难度也大得多。
二
尽管上述职业较为庞杂,既包括稳定体面的工作,也不乏临时性的苦差,但是,鲁迅就是以此在城中找到立锥之地,进而发现了自我存在的意义,获得方向感与归属感。城市社会的从业空间,给鲁迅提供了生存条件,不仅解决生计问题,而且提供了理想支柱。这表明,立足于城市,是鲁迅走向现代的关键一步,从根本上摆脱了“村人”“木偶人”的危险,逃脱了“范爱农”式的厄运。20世纪初期的知识分子,正身处于新旧文化激荡的惊涛骇浪中,他们命悬一线,能否被城市接纳,直接决定着他们将来的命运。顺利跨入城市门槛,则意味着得以存活,如果被城市拒之门外,往往被时代所吞没。关键时刻,城市往往能够向知识者伸出援助之手,把他们从乡间、小城镇提拔出来,为之提供了独立生存的可能,开启一扇生活之门。因此,与其在乡间小镇坐以待毙,还不如在城市闯荡漂泊,这便是知识分子从农村和中小城镇涌向城市的内在动因。
然而,城市文化既具体开放包容的一面,也存在冷酷无情的面孔。现代城市作为以工商业为基础的消费社会,人口集中、资源紧张,处处充满社会竞争和利益争夺,解决现实生存问题成为燃眉之急。人海茫茫的城市大世界,还是一个层级社会,情感疏离、缺乏归属感也是城市人群普遍面临的困境,冷漠、势利、诡诈构成了百味人生。城市谋生的忙碌与艰辛、欺诈与残酷,对鲁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鲁迅切身体验了生活之艰,形成了“饭碗”意识,把生存视为生命线。
从东京文艺活动的失利中,鲁迅第一次体会到城市碰壁的疼痛。在国内城市,他也常受到影响和困扰。对城市职场中尔虞我诈、明争暗斗的现象,鲁迅洞若观火:“普通所谓考试编辑多是一种手段,大抵因为荐条太多,无法应付,便来装作这一种门面,故作禀公选用之状,以免荐送者见怪,其实却是早已暗暗定好,别的应试者不过陪他变一场戏法罢了。”[16]许多时候,他常为别人荐职而无计可施,倍感无奈:“至于地方一层,实在毫无法想了。因为我并无交游,止认得几个学校,而问来问去,现在学校都只有减人,毫不能说到荐人的事,所以已没有什么头路。”[17]鲁迅感到在异乡谋职殊为不易:“我交际极少,所以职业实难设法。”[18]他甚至流露出对城市立足的绝望心绪:“静兄因讲师之不同,而不再往教,我看未免太迂。半年的准备,算得什么,一下子就吃完了,而要找一碗饭,却怕未必有这么快。现在的学校,大抵教员一有事,便把别人补上,今静兄离开了半年,却还给留下四点钟,不可谓非中国少见的好学校,恐怕在那里教书,还比别处容易吧。中国已经快要大家‘无业’了,而不是‘失业’,因为根本就没有什么所谓‘业’了。”[19]
这些饱经沧桑的经历,内化为鲁迅的人生经验,使他强烈地意识到城市立足的重要性。鲁迅多次诉说城市漂浮的苦辛,强调以城市生存为要务,从不主张意气用事,轻易地与城市决裂,无论于人于己,他都持这一态度。尤其流落到绍兴、厦门、仙台时,鲁迅更加明确了城市生存的重要性。“一·二八”事变后,周建人因商务印书馆遇焚而失业,1932年被迫改赴安徽任教,期间,鲁迅频频向友人许寿裳、蔡元培求助,如《320302致许寿裳》《320322致许寿裳》《320514致许寿裳》《320618致许寿裳》《320626致许寿裳》《320801致许寿裳》《320812致许寿裳》《3200817致许寿裳》等书信,帮助周建人谋职,几经争取最后才得以成功。对于许钦文、韩侍桁、宋子佩以及流浪沪上的叶紫、萧军、萧红等青年,鲁迅也总是力所能及地帮助安顿,或设法谋职、解囊资助,或推荐作品、代催稿费,为他们缓解生活压力。他还多次忠告章廷谦、李秉中、宫竹心等青年友人要爱业惜业,不要轻易舍弃现有“饭碗”。他向宫竹心提出建议:“先生进学校去,自然甚好,但先行辞去职业,我以为是失策的。”[20]鲁迅对章廷谦也表达了类似观点:“杭州和北京比起来,以气候与人情而论,是京好。但那边的学界,不知如何。兄如在杭有饭碗,我是不主张变动的,而况又较丰也哉。”[21]鲁迅劝勉他们勿忘现实,要稳健地处理好理想与现实的关系。这与鲁迅后期经济状况有关,但更主要是鲁迅多年城市经历的心得。鲁迅的观点,切中肯綮地指明了城市社会的生存特点,也是对中国社会现实的深刻把握。
三
城市不仅为鲁迅提供了“饭碗”,而且对其文学和思想观念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使鲁迅形成了“噉饭”的创作观。一般看来,鲁迅的思想和文艺观以“立人”为核心,创作目的在于“引起疗救的注意”,许多研究者对此反复论说,突出了鲁迅作为思想启蒙者的崇高形象。实际上,鲁迅除了具有启蒙者的一面,也不乏现实人的一面,尤其是鲁迅在城市游走之间,其思想与早期不尽一致,甚至发生较大变化。城市的生存体验,使鲁迅不仅仅停留于“立人”“改造国民性”一类的抽象命题,总把文艺与生存、个人与社会紧密结合起来,他自觉地把文艺放到城市物质语境中加以审视,形成带有现实色彩的思想取向和文艺观。早在北京时期,鲁迅就坦陈“从文”的苦衷:“其实以文笔作生活,是世上最苦的职业。”[22]他还有意地淡化文艺的救国功能,将文学视为“噉饭”之道,在致友人的书信中明确地表示:“兄职业我以为不可改,非为救国,为吃饭也。人不能不吃饭,因此即不能不做事。但居今之世,事与愿违者往往而有,所以也只能做一件事算是活命之手段,倘有余暇,可研究自己所愿意之东西耳。自然,强所不欲,亦一苦事。然而饭碗一失,其苦更大。我看中国谋生,将日难一日也。所以只得混混。”[23]他在《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等文中,对于充斥时髦名词的革命文学论调保持警惕,对过于美好的革命想象持怀疑态度。显然,鲁迅对文艺功能的理解与前期判然有别,很少把“立人”、国民性批判等崇高使命附加给文艺活动,甚或对一些刻意夸大文艺功能的做法表示反感。城市中的鲁迅,多以日常生活视阈审视文艺,不佯作“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或“渺渺茫茫地说教”[24],而自视为一个立足于现世的普通人,显出稳健成熟的姿态。而且,谈及创作缘由,鲁迅也对赚钱谋生的目的直言不讳。他在提到《坟》时说:“于是除小说杂感之外,逐渐又有了长长短短的杂文十多篇。其间自然也有为卖钱而作的。”又提出:“我的译著的印本,最初,印一次是一千,后来加五百,近时是二千至四千,每一增加,我自然是愿意的,因为能赚钱。”[25]在鲁迅那里,文学不被当作笔墨游戏,它与人的生命需要紧密相关,是血汗人生的结晶。这一文学观带有强烈的现实色彩,没有诗意的流露,亦不宣扬拯救国民的论调,却是朴素真诚的精神体验。对此,只有回到鲁迅所在的城市语境,联想到他曾经历的千辛万苦,才能领会其中的深意。
而鲁迅的城市生存体验,不仅仅是情绪式的,经过心灵冶炼,最终熔为“首先要生存”的深邃思想。有关“生存”,鲁迅在《忽然想到(六)》中明确提出:“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26]对此,李长之、竹内好等研究者倍加推崇。李长之在《鲁迅批判》中视其为鲁迅思想的根本,竹内好则认为:“他的根本思想,就是人得要生存。”[27]但“生存”在鲁迅那里具有多义性,本义是指反传统的文化态度,主张彻底摒弃“《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等国粹,在新文化的空气中获得“生存”。从根本上而言,鲁迅所说的“生存”是广义的。除了文化意义,他还强调“生存”的现实意义,主要指“城市”立足问题,也就是他所说的“吃饭”。鲁迅把它视作关乎现代知识分子生死存亡的重要命题。最典型的表现是,当“五四”时期“个性解放”理想热潮炽热之际,鲁迅却冷静地发出一种独特的声音,对“娜拉”去向进行了敏锐的前瞻,鞭辟入里地指明现实生存的重要性,甚至开口不离“钱”字:“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人类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常常要饥饿。为补救这缺点起见,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28]很显然,这番话不是针对乡下人,而主要是对城市中陷于“个性解放”狂热的青年知识分子提出的忠告。鲁迅所寄望的现代“人”,不仅是“观念”革新的人,更是具有现实存活能力的人,是血肉、灵魂健全的生命体。无独有偶,在鲁迅作品中,一直鸣响着生活的咏叹调,拮据的生活成为一个常见母题,失业、欠薪等现实问题频发,对知识分子命运构成潜在威胁,涓生、吕纬甫、《端午节》中的“他”、《弟兄》的张沛君,均为被生计所累的悲剧者,他们的理想,被生活困厄的阴影所埋没。从根本意义上讲,正是由于在城市中摸爬滚打的生存经验,才使鲁迅总把知识分子放于现实生活中进行谛视,对他们的精神进行批判。
综上所述,鲁迅所强调的“生存”,无论对于其自身还是20世纪初期的现代知识分子,都具有深刻的意义。在选择城市的过程中,鲁迅通过争取“饭碗”而挣脱“乡间”,这一经验促使他自觉地从现实出发,确定“人”和文学的坐标,在文艺和现实生存之间找到了结合点。这样,鲁迅逐步探明了知识分子走向现代、寻求安身立命的必由之路:知识分子必须在生存与理想之间找到平衡点,根据社会现实调整思想准星,只有这样才能更充分地发挥自身的作用。这是鲁迅在城市流徙中一步一步摸索出来的经验。所以,鲁迅所建立的,不是某种虚无缥缈、标新立异的理论学说,而是“生存”为核心的人生经验。这是鲁迅最坦诚、最负责任的思想言说。即使在今天,鲁迅的城市生存经验,仍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能够为青年知识分子起到照明作用,帮助他们避开城市生活的陷阱,在现实惊风险涛中更加稳步有力地前行。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全集:卷12[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82.
[2][美]R·E·帕克,E·N·伯吉斯,R·D·麦肯齐.城市社会学[M].宋俊岭,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3]鲁迅.鲁迅全集:卷1[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38.
[4]鲁迅.鲁迅全集:卷11[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571.
[5]鲁迅.鲁迅全集:卷11[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348.
[6]鲁迅.鲁迅全集:卷11[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330.
[7]钱理群.与鲁迅相遇:北大演讲录之二[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8][美]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M].尹慧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9]许钦文.鲁迅回忆录(下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1234.
[10]杨剑龙.论上海文化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J].文学评论,2006(6):171.
[11]许钦文.鲁迅回忆录(下册)[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1236-1237.
[12]鲁迅.鲁迅全集:卷2[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328.
[13]鲁迅.鲁迅全集:卷12[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72.
[14]鲁迅.鲁迅全集:卷11[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528.
[15]鲁迅.鲁迅全集:卷12[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88.
[16]鲁迅.鲁迅全集:卷11[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83.
[17]鲁迅.鲁迅全集:卷11[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28.
[18]鲁迅.鲁迅全集:卷12[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11.
[19]鲁迅.鲁迅全集:卷13[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389.
[20][22]鲁迅.鲁迅全集:卷11[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11.
[21]鲁迅.鲁迅全集:卷12[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35.
[23]鲁迅.鲁迅全集:卷12[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14.
[24]鲁迅.鲁迅全集:卷4[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50-151.
[25]鲁迅.鲁迅全集:卷1[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300.
[26]鲁迅.鲁迅全集:卷3[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7.
[27][日]竹内好.近代的超克[M].李冬木,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28]鲁迅.鲁迅全集:卷1[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