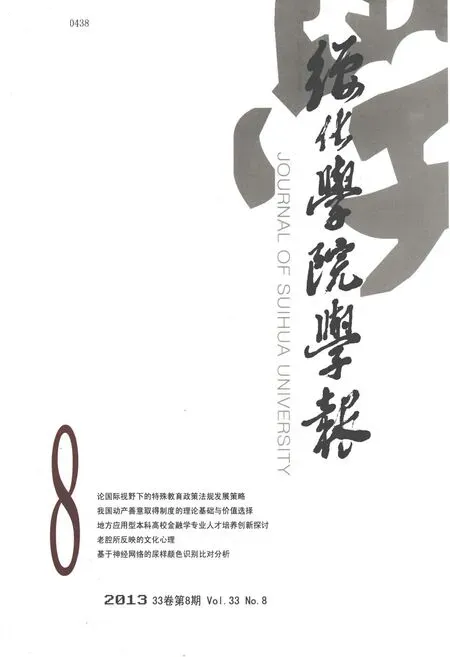表象世界与期待欲疏离的体验——论电影《布达佩斯之恋》的荒谬性哲学价值
2013-04-11陈国元
陈国元
(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河北石家庄 050024)
《布达佩斯之恋》(以下简称《布恋》)是一部以二战为背景的多角恋电影。人的独特生活环境和情感经历展示出的生存状态给予观众噬心镂骨的生命体验,其中的存在主义哲学体悟引发深度的人性沉思。“荒谬”(加缪语)在人“本真”(海德格尔语)的性格流露中体现出的张力,彰显了人作为世界存在物的悲剧性和荒谬性。
一、“此在”的荒谬体认
“此在”即人的存在,有两种状态,“本真的存在和非本真的存在。本真的状态是自我的真实存在,非本真的状态是被平凡的、公众的生活所掩盖的个人存在。”[1]
荒谬“是由于人对世界的合理的期望与世界本身不按这种方式存在之间的对立而产生的”[1],即表象世界与期待欲的疏离。世界的非理性和人对美的渴慕间的张力是荒谬的生存空间。“这三种因素就是造成人生悲剧的三位主角。”[2]《布恋》的荒谬是以死亡为主要依托书写悲剧的。
二、荒谬与死亡殊途同归
(一)安拉斯与拉士路之死
安拉斯和拉士路的死主观上是因《忧郁的星期天》“表达出每个人也有尊严……”(拉士路语),其实死亡是客观要求的。同其他多角恋电影相比,《布恋》的特色是婚姻失语。爱情属摒弃伦理、道德的原生态。若既不打破电影造梦工场的和谐,又做现实收场,死亡是理想的设置,正如路遥对《平凡的世界》中田晓霞与孙少平恋情处理方式一样。另外,蓝色是影片的基调,甚至墓前也放置蓝花。“蓝花……包括了一个心灵所能渴望的一切无限事物……成了浪漫派的图腾。”[3]蓝色对浪漫的表征倍增该片的理想化,为解决现实与浪漫间的荒谬,死亡成为消除矛盾而回归现实的工具。只不过片中这种消失很绝对,两个男人的逝去让爱情三角彻底坍塌。
虽然艺术真实可以脱离实际为人物建构生活之外的理想恋情,但作者的叙述声音明晰地表达了剧作在讲述本真生活。“社会深层神话的集体无意识内核在类型电影中是变化中的显现。”[4]对荒谬地表达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作者通过电影语言回归道德、伦理而重构理性婚姻,进而在理想人性与婚姻理念中形成荒谬。这种荒谬是多角恋与理想人性的悲剧。
(二)汉斯之死
由于倒叙手法,观众在影片初始不知汉斯之死的真实原因。他在祥和氛围中缓缓站起,心脏病突发身亡。临死前他的手伸向妻子颈上的珍珠项链(这是笔战争财),珍珠散落,他抽搐倒地。他倒下后,妻子首先做的不是将他扶起,也不是向医生求助。世界的本来面目却是她急于拾掇珍珠。这并非“阿拉贝斯克”似的迷惑视觉的画面,而是深刻折射了人性,以此突显她心中最重要的东西。期间的荒谬意味不言而喻。金钱与亲情的错置让观众既对汉斯无爱的婚姻有复仇感,又唤起人们对被异化了的夫妻情的悲悯感。
电影话语告知我们汉斯之死的真凶是伊莲娜和她的儿子。然而,伊莲娜是汉斯的女人,她的儿子是汉斯的儿子。两个与汉斯有血肉相连的人最终将他送入曾用以发国难财的棺木。荒谬性和反讽意味因此给予汉斯之死因果报应的结局。这样的文本设置让人类的情感打破“格式塔”式判断,产生具有新鲜感的重新估量。
汉斯死于80大寿时,距他害死安拉斯、拉士路已五十年。五十年内,他被誉为解救犹太人的恩公,开办了全国最大的贸易公司;他凌驾常人之上,未因杀戮而悔恨,否则不会将寿宴安排在他写满罪行的餐厅里。五十年后,他猝死在寿宴上,没有病痛的长久折磨,并非夭折,却有最喜欢的音乐、美食、女人的照片。“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他的死对于观众来说就是悲剧。嗜血狂在幸福中死去与观众觊觎的死有余辜相距甚远,极具荒谬性。
这种荒谬性引发另一个荒谬感,即复仇意义的有待商榷性。五十年前,伊莲娜说:“我恨死他!”(他即汉斯。)五十年后,当彼此都到了纵死不算夭折的年纪,该怎样传达复仇成功的快感?拉士路的绝笔写到:“我不懂得反抗……”伊莲娜读到的正是“反抗绝望”,但带着仇恨的五十年与快乐之间的距离感再次呼唤出荒谬的话语权。
三、人面对荒谬的反应
加缪认为人在荒谬面前的反应是:“自杀”、“在人的生活之外寻求意义”和“在生活之中创造意义”。[1]《布恋》对第一、第三种反应有详细诠释。
(一)自杀
“自杀的根源在于‘看到生活的意义被剥夺,看到生存的理由消失,这是不能忍受的,人不能够无意义地生活’。”[1]
从本质上讲,安拉斯和拉士路的死均属自杀。前者不愿目睹拉士路被汉斯等人戏弄,更不愿在威逼下弹奏自己用心灵谱写的爱情之音;后者看透汉斯嗜血的本质,不想让最后的屈辱降临在他身上。现实中尊严的丧失与自身对唯美、自尊生活的祈愿间的荒谬使其绝望,因此以死传释《忧郁的星期天》。
除了两个男主人公外,自杀同时是富家女、画师等有美好家庭和前途的年轻人的选择。这些人都是《忧郁的星期天》的领悟者。通过影像可知,这是积极向上的群体,战争或生活的荒诞让其在理想与现实的落差间无法容身,思想的超前性使之难以适应现实生活中人作为荒谬存在物的角色。他们是矛盾者,其青春和人生价值在战争下被毁灭,信仰危机致使生命陨落。乐曲在这个意义上有灵异和神秘的气息,似乎预示理想与现实的抵牾,而这又是荒谬在发言。
(二)反抗
同上述迥异的是汉斯和伊莲娜的生存方式。
观众多关注汉斯的恶,但其实他的人生同样是荒谬的。他是个于矛盾中抗衡的人:一方面,顽强的生命力和活泛的商业意识让他成为胜利者,成为具有“强力意志”的“超人”;另一方面,良知偶尔也会使其焕发善意而自责和怀念韶华岁月。但当其他人倾听《忧郁的星期天》走上自杀道路时,他却说曲作“恍似倾诉一些你不愿听的说话”。他的情感不会随曲作流向死亡,而是唯利是图地活着。这种“此在”即是一类面对荒谬却能“在生活中创造意义”人群的代表形态,只不过他的意义属于追求“自我”快乐、创造个人价值。汉斯是荒谬的适存者,“此在”的强者,实践了“本真”的负面存在状态和生活境遇。
与汉斯对比的是伊莲娜如何在荒谬中“创造意义”的。伊莲娜去安拉斯墓前祭扫时说:“今天餐厅重开,希望你保佑我。大家也好运,静待洪水过去。”接着欢快的音乐响起,象征生活掀开崭新的帷幕。这是用正能量抗争荒谬的行为,尽管前文已述其自身也是荒谬的。恰如西西弗,尽管做无用功,却是有坚强意志的英雄,只不过是悲剧英雄。
如上所述,无论在荒谬中自杀还是反抗荒谬,都是“此在”的悖论体现。从荒谬的哲学内涵可判断,该矛盾本身即为荒谬的表征。人自身就是荒谬的悲剧,但这不是叔本华式的绝望,因为萨特的荒谬并非要传达走入死亡,而是让人认知“此在”感后更真实地存活。
[1]赵敦华.现代西方哲学新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19-156.
[2]周国平.诗人哲学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324.
[3]赵勇.诺瓦利斯:寻找梦中的蓝花//周国平.诗人哲学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65.
[4]郝建.类型电影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