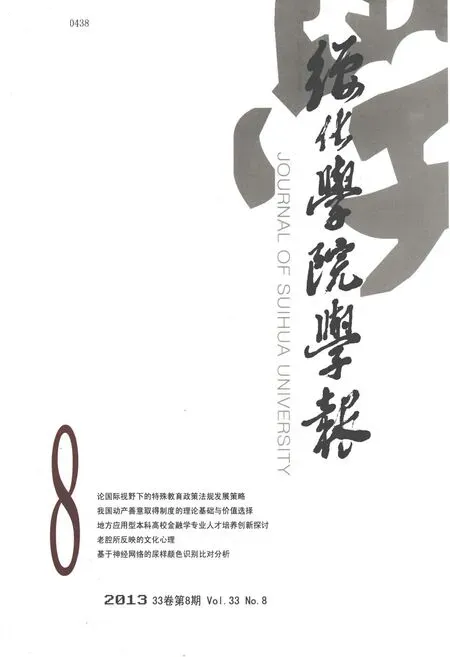海外华文文学影视改编之历史叙事管窥
2013-04-11胡春毅常金秋
胡春毅 常金秋
(1.天津理工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 天津 300384;2.天津科技大学法政学院 天津 300222)
新世纪以来,文学与影视的相互借力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这其中海外华文作品的影视改编功不可没。从影片《金陵十三钗》、《山楂树之恋》到《唐山大地震》,到走纯粹艺术路线的影片《美人草》都影响较大。而电视剧方面,无论是将历史背景与个人命运融为一体的《娘要嫁人》、《一个女人的史诗》和《小姨多鹤》,还是积极介入社会现实、锋芒毕露的《宝贝》、《心术》和《蜗居》,无论是演绎历史题材、海外题材的《正者无敌》、《食人鱼事件》、《基因之战》,还是再现地域文化、惊悚传奇的《上海王》、《狐步谍影》,亦或是穿越历史、融合众多时尚因素的《步步惊心》,这些影视作品大都取得了高收视率与业界的良好口碑,也使得人们普遍关注海外华文影视改编的这一现象。
旅美作家严歌苓的作品与影视互动合作最具代表性,其作品影视改编在历史叙事上存在不同的侧重点。以此研究为原点,探讨当代影视文化产业如何与文学艺术联袂保有其精英意识,同时又积极迎对大众审美文化潮流,将会很有意义。严歌苓将个体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历史融为一体,以特殊的“个人记忆”或者“边缘人物”的际遇激活观众对历史的认知,其中《小姨多鹤》的叙事时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张力。“改编后的《小姨多鹤》颠覆了小说原有的叙事,从语言、情节和人物塑造上十分显见,如同树木生花,绽放异彩。”[1]在历史叙事问题上,同样可以窥见两者各自的长短。
一、标示历史的刻度
2010年前后,根据严歌苓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小姨多鹤》在大陆多家电视台热播。就文学与影视的关系而言,这两种艺术的编创者在讲述故事时也会形成共识,严歌苓对自己的小说的评价也适用同名剧:“小姨多鹤是一个谜,围绕着她,每个人展现了自己的人性,人性在变异,性格在变异,时代也在变异。小姨多鹤实际上是一个大谎言,她不是小姨。对很多人来讲,她是一个看不清面目的人,而且她是中日战争留下来的一个残局,是两国人民的创伤。”[2]与《第九个寡妇》、《一个女人的史诗》相同,严歌苓讲述一个历史时代背景大体相近的中国本土故事,仍然是从个人生活出发,淋漓尽致地关涉中国本土的时代风云,作者似乎无意于宏大叙事,只将竹内多鹤这位战后遗孤的故事大体嵌在王葡萄、田苏菲的历史时代里。正如她所说:“我是有意识,但并非刻意。是想写出历史中颠覆又颠覆的一种状态。我的故事发生在1949年以后,所讲的动乱都是带有中国特色的动乱,是思想的动乱,是概念的动乱”。[3]改编后的电视作品自然也离不开历史叙事,二者的叙事方法却有着微妙的不同。
中国本土的历史标志性事件在小说《小姨多鹤》中起到故事情节的连缀作用,而其本身的叙述发人深省。如以文革为例,严歌苓认为,“文革就是人性到了一个非常激烈、戏剧化的阶段。我在我的所有的小说中对人性有最多的关注,因为人性永远也不能解释,永远都会让你意外,让你意外就是非常丰富。”[4]严歌苓在小说中尽力将历史的风云变幻展现出来,例如:
秃秃的原野眼看着肥厚雪白起来,人和车就这样走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的大雪里。(第一章,9页。以下文中此类引文均出自《人民文学》版的《小姨多鹤》,不另作注,只标注页码。)
电影院门口,小彭指着一张巨大的海报告诉多鹤:这是个新片子,叫做《苦菜花》,听说特别“打”。(第八章,67页)
“四清”工作队在各个厂里清出从解放以后就藏到儿子、媳妇家来的地主、富农、历史反革命,他们遛弯遛到山坡上,就吊死在那里。(第九章,75页)
多鹤在一九七六年的初秋正是为此大吃一惊:心里最后一丝自杀的火星也在凑合中不知不觉地熄灭了。(第十四章,111页)
小说的行文时时或隐或显地标示历史,虽说这种手法多数不见得巧妙,却带有作者的某种写作意图,那就是将历史从褶皱里抓起,用鲜活完整的个体生命演绎被宏大历史叙事湮没的生命时空。电视剧的历史背景呈现也有许多与严歌苓相似之处,鉴于本身的综合艺术影像叙事的优势,在其画面和乐曲方面的充分运用,使得多鹤故事的历史气息更为浑融。可是剧中涉及的时代背景却有选择,有意将历史涂抹打扮起来。弱化了小说中她作为战败国家的遗孤,从自杀殉国、集体逃亡,成为张家的生育机器的一面,剧中着力表现的是危难之际张家对多鹤的保护,接近于编剧林和平所追求的“温暖”效果,成了一场虽惊心动魄却温情脉脉的情感大戏。较为突出的是电视剧的大结局,在剧中中日邦交恢复后不久,多鹤与母亲相认感恩,便戛然而止。省略了小说中多鹤回到日本遭遇的坎坷曲折。对于战争带给人的创伤,少了连续深刻的表现。
二、调试历史的焦点
叙事历史的刻度容易一带而过,但创作者面对那三四十年的历史总要有所聚焦。历史叙事的焦点在电视剧中往往使历史伦理化,剧中人物小彭的历史可谓典型。从采石场的小管理员到革委会干事的升迁过程中,小彭定了钢厂老书记的罪之外就是他的道德败坏。在荧屏中小彭虽有妻子,却一直是单身一人从青年走向壮年,他善变、霸道、阴险,迫害多鹤及其女儿,引起了观众强烈的愤怒,而对于“大跃进”“大饥饿”、“文革”等历史的风云电视剧统统绕过或跳过,残酷的历史本相被遮蔽了。而在小说中,小彭与剧中差异较大,他虽执迷于政治,却也对多鹤充满一定的真诚,文革时期几昼夜工人农民的武斗,成为小彭和多鹤情感融合发展的重要背景,在个人的悲欢中隐含着对那段历史的浓墨重彩,虽不是宏大历史叙事,却实实在在地书写小人物的命运,展现出历史的血肉。因为严歌苓的旅居身份,她的聚焦会显得特别,“从祖国到美国,我也是边缘,我在两边做边缘,游离于主流。这样我就局外一点,观察更冷静,比较容易看出社会中荒诞的东西。”[5]聚焦1949年前后的历史,如“土改”、“反右倾”、“大跃进”、“大饥荒”、“四清五反”和“文革”,成为严歌苓的一种心结,正如她感言“因为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我们对中国这五十年、六十年得有个说法,有个交待。”[2]
《小姨多鹤》关涉到了中日国族间的一些敏感话题,这是中日双方必须面对的问题。毫无疑问,作家严歌苓是持批判立场的。经历过中越自卫反击战的严歌苓,20世纪70年代末就已成为一个“和平主义者”。可是,她不可能忘记日本侵略的伤痛,她一直期望中日两国人民澄清历史,她说“记住那些不忍回顾的历史,我们的民族才是健康的。”[6]2005年,严歌苓创作的《金陵十三钗》就是为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写下的。以其作品《小姨多鹤》感召人们,历史不能忘记,正如小说中有如下的叙述“张俭家这个当代中国民间社会的异类细胞意外、幸运地成为中日两种东亚文化和平共处、相互取长补短、激浊扬清的自然交流场所。这种文化交流从民间日常生活自发、必然地产生、发展,昭示了民族和解、文化互补、协同进步的无限可能。”[7]
在电视剧中这种意识同样得到强化。重建中日邦交的时候,竹内多鹤被日本驻华官员核实其日本战后遗孤身份,这一场戏将全剧推向大结局:
日方官员甲:这个孩子确实是我们要找的人。
日方官员乙:没错,……吃了不少苦吧?
竹内多鹤:如果不是一家中国人救了我,我早已经死了。这场战争伤害了中国人民,也伤害了日本人民,经历了这场战争的人,都痛恨这场战争。(第34集)
同时电视剧以视觉的优势,再现了二战胜利场面的宏大,传达出了被侵略民族的取得胜利后的喜悦,也多次用回顾式的镜头,闪回朱小环被日军追杀导致不能生育的痛苦经历,以此提示战争的伤痛,表达了人们对于和平的向往。
编剧林和平曾说:“希望大家能够认真地看这部戏,不要带着狭隘的民族主义眼光。我所要表达的是人和人的友爱,人性中的温暖。”然而审视过电视剧发现,关于中日的历史文化问题上虽有多处涉及,却趋向于迎合世俗大众的情感逻辑。在电视剧第九集中,朱小环在气头儿上讽刺竹内多鹤,关于日本人身高、走路的姿势和鞠躬的问题,质问多鹤“为什么到我们中国来啊,不在自己国家呆着!还是你们国家不好,羡慕我们国家”;第十六集中,张俭对多鹤说:“我听说你们日本人是我们中国人的后代……”多鹤答道,“有可能。”多鹤的每次在场,使得中日文化认同显得激烈起来,从总体上看,其二战遗孤的身份自然而然使得这场博弈有了分明的倾向。在小说第三章也有一段相似的文字:(张站长指点着纸上的字说)“日本字就是从咱这儿拿去的!”(16页)张站长的腔调透露着普通中国民众的认识,在人物塑造上符合人物的身份,简约而精炼。
从以上对比中可以看到,在大众化的潮流中,电视剧这一艺术形式,极容易走向通俗,消解精英。电视剧多次重复渲染的“优越感”与严歌苓所追求的互补共存,求同存异相差悬殊。对此,有评论者做过深入地阐释,“客居海外各国,能让作家拉开与审美对象客体的距离,更有利于她冷静、超然、独立地写作,这又使得她的小说较之国内的作家作品,更少了一些浮躁、趋时与掣肘,多了一些独立、自由与洒脱。”[8]
三、结语
一个寄居海外的华文作家书写了一个叫竹内多鹤女人的史诗,时时透露出作家的悲悯情怀,既有过往历史的刻骨铭心,也呈现克己恕人的人生姿态。虽然严歌苓的书写并非尽善尽美,比如,历史叙事中有些细节还不够准确,如与张二孩的哥哥(张至礼)的死亡时间相关的抗美援朝的“志愿军”问题;电影《苦菜花》的上映时间等等。然而,瑕不掩瑜,严歌苓的创作依然透着本我写作的姿态,书写着她的想像中国,如她坦言,“‘白色幻想’、‘金色幻想’都和我无关,我只能一心一意用自己的文字码出我的‘中国幻想’……”[9]新世纪以来,众多海外华文作家深处异国他乡,在美洲大陆的张翎、艾米、桐华、石小克、曹桂林,新加坡的六六,旅英的虹影等等作家与严歌苓一样,通过文学书写,表达出对故国家乡的眷恋和反思,表达出独特而形式不一的“中国幻想”,既有对母国现实生活的关切和批评,也有历史文化深层的钩沉与阐释。在其文本的影视改编过程中,历史叙事成为一个考验编创者的重要标尺。严歌苓的文本改编成为华文文学二度创作的典范,既为中国影视创作的原创力提供参照,同时,也在文化研究层面上展现“中国”的镜像。
[1]胡春毅.花开两朵:一个青白,一个浅红[J].电影文学,2011(15).
[2]严歌苓.我渴望书写中国当代史[N].中国图书商报,http://www.cbbr.com.cn/info.asp?id=18410&clear=严歌苓:我渴望书写中国当代史,2008-8-15.
[3]吴虹飞,李鹏.访谈严歌苓:我是很会爱的[N].南方人物周刊,2006-06-01.
[4]严歌苓.严歌苓谈人生与写作[J].华文文学,2010(4).
[5]江少川.走近大洋彼岸的缪斯—严歌苓访谈录[J].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6(3).
[6]严歌苓.失忆与记忆[J].小说月报·原创版,2005(6).
[7]赵修广.历史洪流边缘的异类人生——论严歌苓的长篇新作《小姨多鹤》兼及其它[J].作家杂志,2009(8).
[8]周思明.严歌苓:“和上帝达成—致”的作家[J].艺术广角,2010(1).
[9]周晓红.与严歌苓用灵魂对话[J].WOMEN OF CHINA,20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