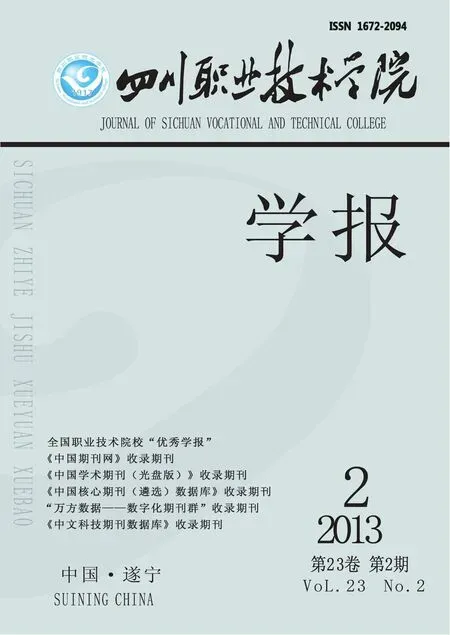论魏金枝四十年代小说代表作《坟亲》
2013-04-11刘家思周桂华周宜楠
刘家思,周桂华,周宜楠
(1、绍兴文理学院,浙江 绍兴 312000;2、宜春职业技术学院,江南 宜春 336000)
论魏金枝四十年代小说代表作《坟亲》
刘家思1,周桂华1,周宜楠2
(1、绍兴文理学院,浙江 绍兴 312000;2、宜春职业技术学院,江南 宜春 336000)
《坟亲》讲述了一个从辛亥革命前期到抗战结束长达四十余年的人生故事,对旧社会中最悲惨的一类人——坟亲的苦难命运进行了深刻的描写,深刻地揭示了黑暗的旧中国底层民众的的血泪史,开拓了中国现代文学的题材领域,对于反映黑暗社会中底层苦难的主题也是一种深化。小说塑造了鲜活的人物形象,丰富了现代文学的人物画廊;同时,有以第一人称叙述的“双视角”和诗性化的叙述与描写显示出鲜明的特色。
魏金枝《坟亲》;思想与艺术成就;四十年代小说
魏金枝是“五四”时期走向文坛著名的左翼作家。他既是诗人,又是小说家,还是散文家、杂文家,又创作戏剧,但小说创作成就最高,受到鲁迅、茅盾、杜衡、施蛰存等人的好评。其小说有《七封书信的自传》、《奶妈》、《白旗手》、《制服》、《魏金枝短篇小说选》等,是乡土文学中具有较大的影响,被称为是“中国最成功的一个农民作家”,对中国新文学的诞生和健康发展做出了较大的贡献。到四十年代,有的人说他的创作不如以前,魏金枝不同意。他说“很有几个朋友,已经认为我的写作,已经不及早期有力”,“可是我反对这些意见”,我“决不迷恋往昔的”,“自己不肯认输”。[1]这显示了魏金枝不断追求和创新的精神。这在他四十年代的小说代表作《坟亲》得到了很好的反映。
《坟亲》是一片著名的中篇小说。写于1946年10月,连载于《文艺春秋》1946年第5期和第6期。1954年收入《魏金枝短篇小说选》时,除了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之外,还删除或修改了一些段落。杨义指出:“魏金枝是一个深沉地解剖民族心理,而又坚执地探寻社会出路的作家,他的创作意识是汲取进步的社会思潮而与时俱进的。”[2]P214这是很到位的评价。这种与时俱进的创作意识,显示了魏金枝创作上不断进取的艺术精神。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的作家很有名,影响力很大,他的创作总是会呈现出自己的创作视域,呈现自己的鲜明特色,但同时也不自觉的长时间地沉湎于停滞性的套路中。比如沈从文的湘西世界及其呈现出翠翠套路,客观上说,虽然感人,但多少呈现出了明显的自足性的停滞状态。有一些作家,如鲁迅虽然多取材于绍兴,但其创作是始终在发展的,呈现了不断追求的轨迹;曹禺也是这样,每一部作品都是一个新的境界,新的状态。应该说魏金枝属于后者之列,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这篇小说显示了这种特点。
一
《坟亲》开拓了中国现代文学的题材领域。小说讲述的是一个长达四十年的故事,描写了旧社会中最悲惨的一类人——坟亲的苦难命运。在江浙一带,有一种人专门给人看守坟墓、管理坟山事物的人,被称作坟亲。这些人整天生活在坟山上,与坟墓打交道,以死人为邻,应该说是社会中最卑贱的一个阶层。魏金枝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深刻描写这一个阶层苦难人生的作家。
小说的主人公阿乜比我大两三岁,从小就跟着他父亲老坟亲给我们看坟墓,管理山场事务。从我能记忆的时光起,他们就只有父子两个,而且不像父子,更像祖孙,因此老坟亲很宠爱他,要是有事到我家来,总是带了孩子一淘的。虽然我们之间没有什么血统关系,却是我家亲戚中走得最热络的。而阿乜童年时活泼天真,总是和我讲一些山里发生的事情和知识,为他对山间宝藏的丰富见识,感到由衷的钦佩。因此我七八岁时就顶喜欢那家住在近山上的坟亲。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要起事,我跟着家里的女人们爬到阿乜家里去避难,我在山上留了两天,发现了各种不同的事物,阿乜总是高兴地做我的领导人,使我充满向往。即便与他分手回家之后,也常在后园对山静坐,连灵魂也飞到山上去了。后来,老坟亲死了,祖母把阿乜收下来看牛,山厂暂时就叫那再醮的婶婶和她丈夫暂时管理。阿乜从此对着家里的所有的人都笑,尤其是父亲,变成了一个老成、知礼、懂世故的小大人,“我”们之间出现一条间隔的堤陇了。因从小营养不良和过度劳累,阿乜身体发育不健全,瘦小乏力,脚踝先天畸形,挑不了大稻捆,踩不动空水车,父亲不满意他,家里吃酒冲鸡蛋时,弟弟吵着要吃,说他“挑不动、车不动、做不动”,他受嘲笑和责难,红着脸,笑着将鸡蛋推给弟弟,但他是个有自尊心的人,后来他却躲在屋里哭起来。他是一个安分老实的人,虽然在祖母的关照和保护下,父亲待他也不薄,但他不愿多麻烦我们,几年后阿乜大量一些,默默地另找雇主了,阴历十二月二十九日就走了。但正月初三的早上,阿乜就来拜年了。一个大热天,阿乜借来看戏第二次来看我们,告诉我在别人家并不好。以后,他也时常来,不但来拜年看戏,凡是我家有什么婚丧喜庆,他也一准赶来帮忙。一年年的过去,我总觉得他心理上的麻木更厉害更深。我十五岁时,也祖母去世1个月前嘱咐父亲给阿乜留心一个女人,成起一份家。祖母去世后阿乜来了,母亲跟他说了这事,他站了一会儿,平平静静的走了。阿乜二十五六岁正值大旱闹灾荒,母亲择配了堂兄家一个茁壮粗大的逃荒女人,可结婚一年以后,阿夫妇反目了,因为我的本家们都到山上种地来了,那些种地的人来了就把这里当作堂子,但为了生活,他只好认命,“并不见怪哪一个”,女人不理睬他们,就要会被逐出坟场。又过了五年,母亲有病,我跑回家去了,又爬上山去找阿乜,见到过他的女人,他们夫妻现在不吵闹了,他说那也没有什么趣味了,这是我很惊异。后来,县里沦陷以后,土匪、游击队都上山了,他们要作窠,把阿的女人打死了。他整天惧怕兵匪,惟一怀恋的是“我”的祖母,睡在她的坟堂上,就能梦见这个“好人”。又过了五六年,父亲去世,我回家了,爬上山去找他,但他以为又是兵匪来了,迅速躲避。这时山上连一棵坟上的松柏也没有了,没有生物,只有稀疏的几蓬茅草,阿乜的茅屋已经倒塌,只剩做灶间的。我好不容易找到他,但他已成山间的鬼影,躲在坟堂间,眼睛看着天空,像一具僵尸。但还盼望世道太平,听到我说会太平的,高兴地说:“我能够过这个冬的。”因为他还藏着一点番薯。阿乜从辛亥革命时期开始到抗战结束四十多年间悲惨的人生历程,从童年的聪明、活泼与欢快,到少年的孤独、勤快与忧伤,到青年的世故、老到与悲苦,到中年的卑怯、无助与凄惨,最后到晚年的怯弱、坚忍与阴冷,深刻地揭示了黑暗的旧中国底层民众的的血泪史,完全“可以作为老中国下层儿女浸透血泪的民国生活史来读”。[2]P214
然而,小说的意义不仅史诗性地再现了底层民众悲惨的人生历程,而且还在与他深刻地揭示了造成底层民众苦难的深层原因。阿乜的苦难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他很小就失去了母亲,与父亲相依为命。可是,老坟亲也是一个苦难的人,一辈子给人看坟,管理山场,自然人生十分悲惨,当他结婚生子,已经是一个有了灰白胡须的老汉,不久就失去了老婆。所以,从外表上看,他们父子更像祖孙。由于家境十分贫寒,老坟亲他依附于坟山的主人们生存,嘴边老是留着微笑,老是低声底气的说话,自然其生活十分凄苦,身子自然弱小,所以他从内到外,很像女人的样子,使我很有点不喜欢他。由于老坟亲体质羸弱的遗传,使阿乜的体质也有了先天的病态。加上贫寒之家始终只能依靠一点山货生活,营养不良,身体自然发育不健全。并且,他从小就在山场中生活,日曝夜露居多,而四季又不是气湿地潮,就是阴风淫雨,或者天蒸地热,或者是天寒地冻,不利于小孩的成长,因此一直瘦小乏力,脚踝先天病变,身体畸形。因此,这就给阿乜都人生先天性地打下了悲惨的底色。应该说,这是阿乜苦难的一种先天性的预设。而之所以会这样,就是因为社会不平等。如果阿乜出身不是这么贫贱,连正常的生存空间都没有,而是一个殷实,或者是富庶之家,也不至于他连身体发育不良,更不会出现了病变也还黯然无知。显然,这里揭露了社会不平等是社会罪恶和民众苦难的根源。同时,阿乜的苦难也是社会动荡、经济衰败带来的道德失范造成的。本来,阿乜在我家放牛、下田,一年年的长大,后来不想更多地给我家添麻烦,到别人家做雇佣,也还勉强,后来我母亲又给他择配了一个健壮的逃荒的女人,成了家,应该说,他的人生进入了正常状态。然而,一年之后,他们夫妻就反目了,什么原因呢?就是社会动乱带来的经济衰败和道德崩溃,导致民众疾苦不堪,正常的生产已经无法生存,只有到山上来开垦种地了。我的本家们也没有办法就跑到山上来种地了。他们叫阿乜夫妇搬走,不是我弟弟,阿乜夫妇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但是有了住了,却老婆与别人有了关系。而这些本家们到这里种地,就把他家当堂子,倘女的不从,早就叫他们走了。为了生活,阿乜低头了,也看到大家都很苦,他们也不吵了。本来,这样也就够苦了,然而阿乜的苦难并没有到头。日寇的入侵中国,县里沦陷以后,土匪、强盗在山上作窠,游击队也在山上作窝,他们要存脚的地方,也要女人。一天,后来几个强盗要奸阿乜的女人,她不肯,就被打死了。还是我母亲帮忙给了一块墓地葬了她。正是这日寇的入侵造成兵匪横行,山上连一棵坟上的松柏也没有了,没有生物,只有稀疏的几蓬茅草。阿乜的茅屋已经倒塌,只剩做灶间的。阿乜整天惧怕兵匪,他已成山间的鬼影,躲在坟堂间,眼睛看着天空,像一具僵尸。惟一怀恋的是“我”的祖母,睡在她的坟堂上,就能梦见这个“好人”。应该说,阿乜最悲惨的一幕,是日寇发动的侵略战争强加给他的。显然,小说既充分显示了层民众的善良朴实忠厚的优良品质,显示了他们无力自保、无援无助、任人宰割的卑怯状态,更揭示了战争是造成民众无以复加的苦难的祸首。由此可见,小说不仅深刻地批判了黑暗社会不平等的罪恶,国民党反动统治对底层民的损害,而且谴责了战争的罪恶。
然而,还有一点尤其值得我们注意,这就是小说主人公阿乜虽然人生如此悲惨,虽然他只能如鬼影和僵尸一样活着,但并没有挤垮他对主体意志以及对生活的希望。他不仅清楚地记得他的女人被枪杀的地方,质问“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呢?”而且盼望世道“能像先前那么的太平”。当他听到我说世道会太平时,他又充满着希望,高兴地说:“我能够过这个冬的。”他说还藏着一点番薯,而且热情又起,他要弄点番薯请客。这一点不仅显示了底层民众坚忍的人生意志,而且反映了民众对社会和平的强烈渴望。对普通民众而言,只要没有战争,只要社会不动荡,在太平社会中,他们凭自己勤劳的双手是可以苟活下去的。
《坟亲》写于日寇投降之后,国民党又掀起内战的特定时代,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无疑是对现实的尖锐批判。应该说,它在题材上是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开掘,是描写黑暗社会中底层苦难主题的深化。杨义指出,“它从社会的贫富悬殊,家庭的伦理情分,和民族的危难环境的交织中,写出了黑暗中国旧式农民苦难的遭遇、苟安的心理和微末的憧憬,写出了人到底能够承受多少磨难,又写出了在这种磨难之下求生的意志是何等顽强,在这里,我们仿佛听着了中国大地在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双重压迫下的沉重的呻吟”,作者“把对乡间父老兄弟的深挚感情,和着人间的血和泪,渗透于字里行间。”[2]P214应该说,这篇小说在“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文学中描写农民的作品中是独特的。
二
这篇小说是魏金枝在四十年代重要的代表作之一,其艺术成就不仅在题材的开掘和主题的深化上,还人物描写上。小说塑造了不仅塑造了阿乜这个诚朴善良、瘦弱勤奋、怯弱感恩而又有自尊心的真实生动的主要人物形象,还塑造了包括“我”在内的多个人物,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人物画廊。
在小说中,每个人物都性格鲜明,血肉丰满,栩栩如生。阿乜是一个从小饱经忧患,饱尝苦难而又诚恳勤劳、本分老实而又自尊心很强的农民形象。这个形象,小时候是聪明活泼而开朗的。虽然是身材瘦小,总是裸露着四肢,很像特意制成的小木棍,分不出粗细,分不出皮肉,但他一动作起来却非常灵活;虽然有些羞涩,有成人似的矜持,但是他又会和我谈着他自己的遭遇与见识,总是滔滔不绝地叙述着他们山上的故事。他告诉我在茅柴棚里去寻松蕈,应该怎样用麻绳甩上石子从树上敲下橡子,怎样去捕捉顿倒了头孵蛋的雉鸡,追赶兔子应该从山上追赶到山下。他待人热情诚恳,我避难到山上,他总是高兴地做我的领导人,像老鼠一般尽量地在山上跳跃,从树林、柴蓬、岩石、坟墓、山涧里钻来钻去。他也有自己的志趣,愿做天空中的飞鸟老鹰,用自己的翅膀去飞。这时的阿乜是淳朴的,独立的,自由的,快乐的。可是,苦难的压迫,他就变了。他父亲去世后来“我”家求祖母收留时,直到跨上大门的阶石,才猛然发现了我,却只是对我淡淡的一笑,就跑到祖母哪里去了;到我家来做帮佣后,他竟不大睬我,不和我玩耍了,而是对着每个人都笑,尤其是对我父亲,简直不像以往的阿乜,而像一个老年人。可以说,是苦难的命运使他从一个快乐少年变成了一个早熟的少年。从此以后,阿乜试着去学习他父亲的习惯,从祖母的暗房边走过,起初唉一声,然后坐在那暗房的门槛上。他已经没有了以前的天真幻想。他有很强的自尊感,不想给人造成什么都做不了,只能吃吃白食的错觉,因此做事时十分卖力,挑不起也多挑一些;而且极想强壮起来,遵照我父亲吃油拌饭,然后做事就格外卖力。当觉得自己强壮无望后,就另找主顾,离开了我家。他很知道感恩,自我家虽然父亲有时不愿要他,也受到过弟弟的直接指责,但是除了自己一个人哭之外,从不怨恨人,而且离开我家后,马上又来拜年,不时来看我们,我家有婚丧喜庆时总是离不开他的帮忙。然而,生活在改造他。离开我家后,他回来时变得很世故,老到,讨人喜欢,所以大家说他有出息。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老实诚恳、踏踏实实的人,却始终沉落在悲惨的深渊中。黑暗的社会使他有一个有人格自尊的人逐渐转变成了一个萎顿卑怯而懦弱的人。他遵照我母亲的择配,讨了一个逃荒的女人做老婆,可后来被游手好闲的弟弟插足,虽然闹起来矛盾,但他认为她不容易,很快也就不计较了。而社会动荡造成了民不聊生,使族人们上山种地,因为弟弟出面,住下来了,他他们就将阿乜都家做堂子,他的女人不从就要赶他们走,他不怨恨他们,觉得大家都不容易。生存的艰难,将人的自尊给消磨了。后来日寇入侵,县城沦陷,兵匪在山上作窠,要强奸他的女人,女人不从而被枪杀了。他始终处于恐怖之中,渐渐地由人变成了一具僵尸,一个鬼影,但他虽然怯弱,但他有着自己坚忍的生存意志,且记着女人被枪杀的地方。他心很仔细,为了生存,他在自己灶房后挖洞以便迅速逃生,并将番薯用土埋起来,兵匪来了就躲藏在坟堂中。尽管如此,还怀着期待世道太平,期望能够度过苦难的冬天。这是一个栩栩如生的农民形象。这个形象,反映了中国农民的思想情感、精神品格以及悲惨的苦难命运。他的精神蜕变的历程,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鞭挞了反动政府的无能,谴责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
“父亲”这个形象非常真实。这个形象最初是在老坟亲去世时实在亮相的。他遵照祖母的吩咐主持料理了老坟亲的丧事,回来后就向祖母汇报,当听到我问有铜锣没有,他说那有铜锣,连砖都没有,显示出他的同情心。一个人的人性,最基本的内涵应该是怜悯与同情心。对弱者是否有同情心,是一个人道德上和人性上健全与否的试金石。只有具有同情心的人才善良、诚恳。他的这个出场,一开始就显示了他的这种基本的素质。于是,我们在下文中才有了认识他丰满性格的充分基础。他的身份有两个方面,首先他是个孝子,其次是一家之主。因此,在家政上,他时时听他母亲的;而在劳务上,则事事靠他说了算。同时作为一家之主,他承担着养家糊口的责任,但他的行为是对外争得口碑、形成社会影响的关键。正是这样,当祖母收留阿乜放牛时,他不想要,和他母亲争执,试图说服她。他说,宁愿在可能的范围之内帮他一点,却不愿意收留他来看牛。因为他除了想把“我”派作用处,不必另找人看牛之外;同时,阿乜“颗粒既小,又是那么瘦弱,只配在散淡的人家里过活,断不配到我家里来做工”。正是在对待阿乜上,小说充分展现了他强健、性急而又慈心的性格特征。开初,当阿乜来后,他为了显示自己意见的正确,就当着我们的面,将他拉到自己面前,用手在他细小的肩上轻轻一揿,他的脚肱,就像藤做到软手杖,弯成一个弓势,并用脚趾叉叉他的脚肱,告诉我们:“你看,你看,这样的脚吓,还挑得起担么?”弄得他脸色发白,伤心地掉眼泪。但他马上又感到自己的举动鲁莽,又拆开大嘴装笑来替自己解嘲。当冒雨抢收稻草时,阿乜因自己挑得过重而跌倒又伤了脚时,他又对他母亲说:“我不要他了,我一定不要他……我又没有叫他挑这么多的,他却偏要挑得这么多。……别人却还会这样说:‘要一个小伙子挑这样重的担,还要在后面推,自然就要跌倒了’。”吃鸡蛋时,弟弟也争着要吃,说阿乜什么都做不动,抢了阿乜的鸡蛋,他竟把弟弟打了两下。虽然父亲觉得难办,因为弟弟说的话不是没有道理,因为家里的规矩是不能下田坂的不能吃鸡蛋。但是,以后吃鸡蛋时还是给他吃,只是叫他在屋里吃。而且,为了使阿乜能养得胖起来,父亲要阿乜每次吃法时在饭里面拌两调羹熟油,说吃了就会胖起来。我们家里没有瘦子,他担心别人说没给他吃饱饭,所以还问他吃没吃饱饭。有一个冷天,父亲以为阿乜生病了,就叫他在家里休息。阿乜到我家来,父亲因他并没有少受祖母的责备,可是他待阿乜还是不薄。可是,阿乜还另找了雇主,离开了我家,这使父亲受冤挨骂,的确是他很生气。于是,当阿乜立即来拜年时,他避而不见。但当他找到他,给他作揖后说明到处找他,是真心来拜年时,又热情款待他,就像款待一位难得的客人一样。可以说,父亲这个形象是一个做事能力强,要求高,又明事理,同情人,待人好的真正的父亲形象。这个形象,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很独特的,显示了中国农民精神性格,有着重要的审美价值和文化价值。此外,小说中还写了老坟亲、阿乜都女人、祖母、母亲、弟弟以及“我”几个形象,每一个形象都性格丰满,生动真实。“我”是一个有着很深的人道主义情怀的知识分子形象,自然不必多说。而祖母和母亲都是慈母的形象,不同的是前者是一个家庭权威和偶像,后者则是一个勤劳、朴实、热情而又具有很强自省力的形象。这两个形象都反映了越地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显示了一种女权意识。就是逃荒的女人,虽然只有侧面描写,但性格很鲜明。她的命运比阿乜更加悲惨。她在故乡无法生存,背井离乡,逃荒出来。为了生存,与阿乜结合了,但阿面是个身材瘦小,毫无男人气的人,而她自己则是十分健壮的人,我弟弟则是一个高大强壮的男人,于是很快与弟弟有了关系,而且为了苟活,后来又被迫接受族人们的蹂躏族,但是她不是那种生活放荡的女人,而是一种无奈。所以,当兵匪要强暴她是,坚决不从,最后惨死在他们的枪口下,用自己的生命捍卫了自己的尊严。显然,这是一个有性格深度的形象。
魏金枝的小说,始终都是写人。在他的作品中,几乎没有意念化的人物,更没有类型化的人物。这篇小说充分反映了这一点。正是因为他描写了个性化的人物,所以,这篇作品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三
这篇小说的审美价值,还体现在在艺术上。文学是一种艺术,必须经过作者的精心构思和有意味的加工创造,才能呈现出艺术的美感,产生一种打动人的审美力量,从而发挥文学应有的作用,推动人类的发展和社会文明的进步。魏金枝的创作质朴深挚,但并不粗糙,而是精心创作的,不断追求的。这篇小说在艺术上显示了新的面貌,呈现了他一贯拥有的特点。
首先表现叙事上。这篇小说叙事结构非常精致。小说以“我”的回忆构成全篇,前后呼应,非常严谨,浑然一体。因此,小说的叙事人是第一人称“我”。有意味的是,小说是以“我”的成长历程来写阿乜的人生历程,不仅用“我”的眼光来观察阿乜的人生状况,而且也构成了一种潜在的对比效应,也使小说增强了艺术的感染力。因此,小说有两条线索,一条是阿乜都人生进程,另一条是我的成长历程。这两条线索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个结构严密的文本。因为是“我”对往事的回忆,所以小说有一个成人的叙述视角,这是小说最主要的艺术视角。但是,因为小说从我的成长经历来写阿乜的苦难人生的。因此小说又一度存在着一个天真诚挚的儿童视角,这主要体现在小说的上半部。在这一部分中,是儿童视角为主,成人视角为辅,主要通过“我”避难进山和阿乜收留在“我”家的生活情状的描写,表现阿乜从童年的聪明、活泼向少年以致青年的世故、老到的转变的苦难人生历程,这时期叙述充满着童真,是一个天真无邪的孩子在讲述自己看到的故事,并用纯真的眼光来看待世俗世界,对不平等的世道于以了批判。在这一部分中,成人视角与儿童视角往往交织在一起,同时存在着一个儿童叙述者和成人叙述者。而小说的成人视角集中在下半部分。这一部分讲述阿乜结婚以后的苦难命运,展示了他从委琐走向悲惨的人生历程。这时我从青年走向成年,主要描写了“我”四次与阿相见的情形。第一次是祖母去世,阿乜来帮忙,母亲遵照祖母临死前的嘱托,和他谈起为他择配的问题。第二次是阿乜二十五六岁大旱荒年,我在外面混得厌倦,回到家里,母亲要将堂叔家的一个逃荒女人择配给他,我觉得这事应该阿乜自己同意,在母亲尚未跟他说之前,先上山跟他说一下,叫他有个准备;第三次是五年之后,母亲有病,我跑回家去了。因为知道他跟他的女人闹了矛盾,而母亲又只是怪那女人,害了阿乜,还带坏了弟弟,就上山去看看他的生活,这是他以由以前的委琐变成了一个卑怯苟活者。第四次又是五六年之后,父亲去世了,我听说他的女人被强盗打死了,就上山去看看他,这时它已变成了惊恐兵匪、躲在坟堂里的一个鬼影,一具僵尸。这样,小说就将万恶的社会,如何一步一步将一个活人变成死鬼的罪恶历程。而小说与众不同的是,他不是描写阿乜与外在世界的激烈冲突,也没有描写韦庄人对阿Q那样的冷漠,而是描写了他始终还有关心他的我和我“家”。然而,即使这样,他的命运还是如此悲惨。这样,就更深刻地揭露了社会的罪恶。
其次,小说在艺术上还有一点是诗意的叙述与描写,这是他的新发展。魏金枝擅长与将叙述与描写紧密结合,形成一个浏亮的文本。这篇小说也拥有这种特征,但更突出的诗意的叙述和描写。纵观全篇,小说笼罩在浓烈的抒情气氛之中,显示了浓郁的诗意。小说中不是会提炼一些诗性的意象予以反复描写。例如祖母和暗房,就是富于诗性张力的艺术意象。祖母住的地方虽然是个黑暗的地方,但祖母信佛,对老坟亲和阿乜关怀备至,是普渡众生、救苦救难的观世音再世。它就是黑暗中照亮人的心魂,燃起人生希望,照明人生路途的明灯。因此,无论是老坟亲还是阿乜,在苦难中总是坐在暗房的门槛上。因为,只有在这里,他们的心魂才有灵光照亮,才有度过艰难的力量。正是这样,她具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性。而阿乜离开我家第二次来看我们时的洁白的新毛巾,也是一个赋予了诗意的意象,既显示了阿乜的生存状态,也显示了他纯洁的心魂。然而,小说的诗性美更体现在叙述和描写上。小说是由一个具有很深的人道主义情怀的抒情主人公形象“我”来叙述的,充满着主观情绪,蕴蓄了深挚的情感张力,显示了诗性品质。请看:
提到祖母,我就真的倒了兴了。因为我也明白,祖母是断不会放我上山的。然而在这样的引逗之下,在我的头脑里,早已充满了对于山的好感。在我那时想来,山那个东西,确乎是个无所不有,取之不尽的宝藏。在那里有奇怪的生物,又有美丽可口的超人工地食物,而云也自哪里飞来,鸟也自哪里飞来。尤其是它的屹立不动的形象,无论暴风,无论骤雨,它也总是巨人般地站着,永不改变他的姿态。因之,有时候就一个人溜进后园,静静的坐在池边的那株橘树下,从竹林的空隙间,去看阿乜告诉我的他所居住的那个山头。远远的望去,在岗上伞样张着的松树下,投出竹丛的尖端,在那里,就是阿乜都家。时常飘起炊烟,袅袅的盘绕着松树,然后升上淡青色的天空。这时候,我就想入非非,连魂灵也飞到山上去了。
这一段既有叙述,又有描写,是叙述与描写交织在一起的典范。首先我们可以对上一段的观点做一些分析。这一段文字是在儿童和成人双重视角审视的结果,即这里存在一个童年的我和成年的我的交织现象。这里的“在我那时想来,山那个东西,确乎是个无所不有,取之不尽的宝藏。在那里有奇怪的生物,又有美丽可口的超人工地食物,而云也自哪里飞来,鸟也自哪里飞来。尤其是它的屹立不动的形象,无论暴风,无论骤雨,它也总是巨人般地站着,永不改变他的姿态。”就是一个成年的我的介入。这两种视角,使小说的叙述富有变化,更加生动,赋予艺术张力。然而,这里还代表了小说另一个非常鲜明的艺术特点,就是叙述与描写充满诗意。叙述人对于山上充满着向往和期待,不仅使其浸润着强烈的主观情绪和深挚的纯真情感,而且语言非常优美,充满诗性的魅力。这里的叙述与描写创造了诗的意境。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山是如此之美,充满着诗情画意,其境界深遂、清幽而开阔。可以说,情景交融,富于韵味。
涂光群说:“魏老最擅长于短篇小说,他的作品数量虽说不是很多,但质量上乘。因为每篇都是精心构思,又讲求文字技巧,决不草率从事。”[3]应该说,这种对叙事的讲究,对诗意的追求,充分反映了这一点,增强了小说的审美价值。对诗意的追求,是他叙事艺术的一种发展,显示了执著的艺术追求。
在四十年代,讽刺和暴露是现代小说创作的重要主题。魏金枝感应着这种时代潮流,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者对民众的损害,表现底层民众苦难的人生,成为他这时期小说的重要指向,但他又有着自己的审美选择,《坟亲》就是这种什么选择的代表。在这里,魏金枝通过对“我”的坟亲阿苦难命运的描写,深刻地揭露国民党统治的黑暗社会将人变成鬼,明目张胆杀人的昭彰罪恶,既表达了对于社会和平安定的主观期望,又寄予来对底层民众悲惨命运的深切同情,同时又对他们坚韧的生存意志予以了礼赞。小说拓展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表现领域,深化了时代主题,丰富现代文学风景,是魏金枝小说创作艺术上的一个新发展。
[1]魏金枝.我与觉悟[J].自由谈,1947,(02).
[2]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二)[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3]涂光群.上海老作家们——十位上海老作家侧记[J].新文学史料,2004,(01).
责任编辑:周哲良
I206.6
A
1672-2094(2013)02-0046-06
2013-02-25
本文系作者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9年度省社科规划重大项目《越中知名现代作家研究》(课题编号09JDY W01Z D)子项目《魏金枝评传》的阶段性成果。
刘家思(1963-),男,江西宜春人,绍兴文理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周桂华(1968-),女,江西宜春人,绍兴文理学院助理研究员,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