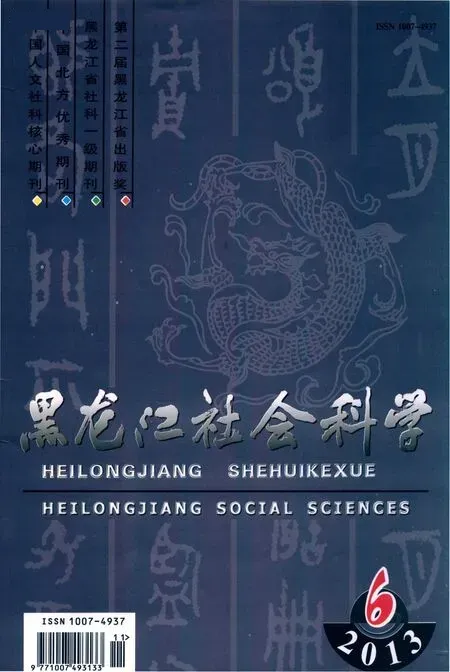康有为对墨子思想的态度和取舍
2013-04-11魏义霞
魏 义 霞
(黑龙江大学 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研究中心,哈尔滨 150080)
无论是考辨中国本土文化“学术源流”的名义,还是论证“百家皆孔子之学”的需要,都决定了康有为对墨子思想予以深入阐发,反倒难免因随感而发导致前后之间有所出入,甚至相互抵牾,致使墨子的思想呈现出巨大张力。而墨子与孔子的关系以及康有为视界中的孔教广、狭之分则无疑增大了这一张力,直接影响着康有为对墨子思想的评价和取舍。在这方面,墨子的命运与老子相似,墨子分属于广义孔教与狭义孔教的两套身份之间的张力却与老子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原因在于,康有为视界中的墨子具有特殊的学术经历——先学孔子之道,后来叛孔子之道。这使墨子与孔子的思想之间呈现出最为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学孔子之道加大了墨子与孔子思想之间的一脉相承和相近相通,叛孔子之道则预示着两人思想异见多多,甚至针锋相对。更有甚者,除了学孔子之道与叛孔子之道,墨子的尴尬和困惑还有作为宗教家与哲学家之间的张力以及由此导致的康有为审视、评价墨子时大相径庭的态度。
一、作为宗教家的墨子
康有为具有泛宗教倾向,在他眼里,无论墨子是否属于孔子后学都是宗教家是确定无疑的。对作为宗教家的墨子,康有为从“救人”的角度给予了肯定。例如:
儒教,孔子特立。传道立教,皆谓之儒。老之教曰道,墨之教曰侠。近耶教藉罗马之力,十二弟子传教,专在教人,创为天堂地狱之说。马虾默德谓之回,其教极悍。释迦牟尼谓之佛,其教专以虚无寂灭,亦藉天王之力[1]108。
孔、孟及佛、墨、宋牼,皆以救人为主,故能不朽,耶氏亦然[2]119。
在这里,一方面,康有为肯定墨子教义以侠为宗旨和特征,侠使墨子所创之教与中国本土文化中的孔子之教、老子之教教旨相异,与西土的耶教、回教以及印度佛教迥然不同。另一方面,他指出,墨子之教在“以救人为主”上与孔教、佛教和耶教是一致的,这等于在墨子之教与孔子之教并立且不同的前提下肯定了墨子之教的独特性和正当性。不仅如此,在墨子是宗教家、是墨教的教主的前提下,康有为不仅让墨子与耶稣相互观照,而且注重墨教与佛教的相似性和相通性。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宣称:
墨、佛近远人之道[1]167。
宋儒于当时则近佛,比古则近墨[1]167。
墨子之道,与佛相类,而墨子行于身前,佛氏行于身后。墨子行之速,故败之速。佛氏行之渐,故延蔓至今日。佛氏无父母妻子,故全讲虚理。墨有父母妻子,故全讲实制[1]110。
上述引文显示,康有为对墨子与佛教的比较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远人以为道。康有为在这里抛开孔、耶而将墨、佛并提,至少表明在他的心目中在远人这一点上墨、佛走得更近乃至别无二致。第二,以宋明理学家的思想来反衬佛、墨相类。第三,在肯定墨子思想与佛教相类的前提下对二者予以区分,并且道出了二者的不同命运。
值得注意的是,正如肯定孔教与佛教相通一样,康有为揭示墨子思想与佛教的内在联系并不妨碍他对墨子的肯定,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肯定、彰显墨学的前提条件。这除了近代的全球视野和多元文化心态之外,还因为康有为本人就是一位宗教家,其兼容并蓄的宗教态度决定了康有为对包括墨教在内的所有宗教都怀有宽容的同情。对此,梁启超介绍说:“先生又宗教家也……无一宗教家。先生幼受孔学;及屏居西樵,潜心佛藏,大彻大悟;出游后,又读耶氏之书,故宗教思想特盛,常毅然以绍述诸圣,普度众生为己任。先生之言宗教也,主信仰自由,不专崇一家,排斥外道,常持三圣一体诸教平等之论。然以为生于中国,当先救中国;欲救中国,不可不因中国人之历史习惯而利导之。又以为中国人公德缺乏,团体涣散,将不可以立于大地;欲从而统一之,非择一举国人所同戴而诚服者,则不足以结合其感情,而光大其本性。于是以孔教复原为第一著手。”[3]486在康有为所讲的宗教中,墨子之教无疑占有一席之地。他不仅对宗教抱有宽容和同情态度,而且在孔教、佛教与耶教的三教圆融中受益匪浅。被康有为奉为宇宙本原的仁是孔子思想的宗旨,也是三教的交汇点和共同点。此外,在宗教宽容的维度上,他对墨子思想抱有肯定和同情,给予墨子以较高的地位,指出“诸子之教,以老、墨为最老辈。”[1]105
进而言之,康有为终身为之奔走呼号的不是宗教自由而是立孔教为国教。他将孔教奉为拯救中国的下手处——“第一著手”。这决定了康有为以传承孔教为己任,他自己也以孔教的当代教主自居。梁启超投其所好,时而誉之为孔教的教主,时而称之为孔教的马丁·路德。传教的需要和特殊身份决定了康有为对孔教之外的“异教”抱有本能的排斥或贬损,这其中就包括墨子之教。按照他的说法,墨子、老子等战国诸子纷纷创教就是为了与孔子争席,以中庸为旨归的《中庸》等经典的出台正是针对墨子、老子等人的极端而反中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康有为再三宣称:
中和是孔子之大义[1]292。
君子时中,孔子皆因其时而发之[1]292。
信道最笃,莫如回之择《中庸》。守道之勇,莫如子路,故举出来。后世有述,指当时老、墨等[1]167。
康有为指出,墨子和老子都反中庸——一个太过,一个不及。因此,墨学和老学都不可行。循着这个思路,他得出了如下结论:“墨学战国时与孔子并,至汉,墨学衰。老学盛于魏、晋、六朝,盖墨学能行而不能传,老学能传而不能行。”[1]110
在此基础上,康有为强调,诸子之中,墨子与孔子争教最盛,超过了老子。墨子之教与孔子的对立之处比比皆是,墨子改孔子之制在本质上就是非时中,集中表现为改孔子的三年之丧为三月之丧,兼爱、非乐也是非时中的结果。由于孔子时中而墨子思想极端,他判定墨子叛孔子之道。对此,康有为不遗余力地申明:
《墨子·公孟篇》谓墨子曰:子以三年之丧为非,子之三月之丧亦非也。墨子谓:子以三年之丧,非三月之丧,是犹果谓蹶者不恭也。三月之丧,墨子改制[1]150。
墨子非儒,故攻三年之丧,以均非时制,皆是创义,故谓同为恭也[1]150。
孔子定三年,最为得中,以德报怨之或人,兼爱之墨子,皆失中,故改制而不能行于世[1]167。
墨子非六代之乐,改三月之丧,非时中矣[1]167。
至此可见,作为宗教家的墨子在康有为价值天平上的分量是不同的,于是出现了对墨子之教以及墨子地位的相反结论。其实,康有为对墨子的评价可以在他所推崇的孔教那里得到最终的解释和印证,因为他对墨子无论赞同还是反对都以孔子思想或孔教为标准。康有为在揭示墨学内容时始终夹杂着与孔子的关系。这样的例子俯拾即是:
墨子非儒,不非“尊天”、“明鬼”,为其相同。墨子之学,其最精处在“兼爱”、“尚同”,其败绩处在“灭等威”、“无差等”、“短裘薄葬”[1]109。
墨子非命。他忘却“居易”二字,知气在上,即鬼神也。《礼运》发挥鬼神甚精[1]173。
尊命为孔子大义,此则杨与之同,而墨“非命”。盖杨主无为,托命自然;墨主有为,故力征经营。力命抑死,则杨、墨相同,而异于儒者,亦与儒氏同也[1]207。
若墨氏之学,“非命”、“明鬼”,皆不可通,“尚俭”亦不可行,若其“非攻”,则孔子有之……至于“兼爱”一义,亦出《大戴》,所谓孔子兼而无私,此二字无可议者。孟子之攻之者,当时自有所在,二千年实无议之者……墨子在战国,与孔子争者也,故自行改制,短丧薄葬,非儒非命,皆力与孔子为难。孟、荀为孔子后学,自当力拒之。孔子最尊父子,特传《孝经》,墨子则无差等,故以为无父,此实不可行者也[4]。
墨子之言“非命”,谬甚。言艺学者亦甚多。孔子立命,实为中人起见(合观墨子“非命”,列子“力命”,可知孔子言“命”)[1]117。
上述引文显示,康有为对墨子思想的概括是多方面的,评价的角度或坐标却只有一个——所有的评价无一不是以孔子为标准的,这再次印证了康有为对墨子既有肯定又有否定的评价受制于他的孔教观。不仅如此,康有为对墨子的赞同或反驳也是这样——在这方面,他对非命、兼爱、尚同以及明鬼的态度即是明证。
二、作为哲学家的墨子
康有为对墨子的态度取决于立孔教为国教的宗教观,也受制于其哲学观。梁启超曾经把康有为的哲学概括为四个方面,即“先生之哲学,博爱派哲学也……主乐派哲学也……进化派哲学也……社会主义派哲学也”[3]488-489。在康有为哲学的这四个方面中,与墨子相关的主要集中在第一方面即“博爱派哲学”和第二方面即“主乐派哲学”。就康有为哲学的这两方面而言,墨子符合“博爱派哲学”,却有悖“主乐派哲学”。可以想象,墨子与康有为哲学既相符又相悖的关系注定了康有为对墨子哲学大相径庭的评价。
梁启超在检视康有为哲学时首先将之称为“博爱派哲学”,并且进行了如下介绍和评价:“先生之哲学,博爱派哲学也。先生之论理,以‘仁’字为唯一之宗旨……故悬仁以为鹄,以衡量天下之宗教、之伦理、之政治、之学术,乃至一人之言论行事,凡合于此者谓之善良,不合于此者谓之恶劣。以故三教可以合一,孔子也,佛也,耶稣也,其立教之条目不同,而其以仁为主则一也。以故当博爱,当平等,人类皆同胞,而一国更不必论,而所亲更不必论。故先生之论政论学,皆发于不忍人之心。人人有不忍人之心,则其救国救天下也,欲已而不能自已。”[3]488依据梁启超的这个说法,康有为的“博爱派哲学”具有两层含义:第一,康有为对仁推崇备至,并且断言在以仁为宗旨上,孔教、佛教与耶教圆融无碍,仁是三教的共同宗旨。第二,对于康有为来说,仁的内涵是博爱、平等;既然平等是博爱的题中应有之义,就应该对所有宗教一视同仁,平等对待。“博爱派哲学”的两层含义是康有为评价墨子的标准,也预示了墨子在康有为视界中的地位:其中,宗教宽容给予了墨子思想自由的存在空间。更为重要的是,康有为赞同墨子的兼爱主张,认为兼爱近仁,与孔子的思想并行不悖。对此,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说道:
墨子甚仁[1]283。
不能以兼爱攻墨子,以无父攻墨子则可[1]283。
《庄子》之论墨子甚么,观《天下篇》,可知其短处不在兼爱也[1]180。
孔子之教,其宗旨在仁,故《论语》有“依于仁”一条。《吕氏春秋》言孔子贵仁。自老子始倡不仁之学,故其《道德经》中,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万姓为刍狗。其教旨与孔子大相反。故向来中国教旨只仁与不仁而已……佛教所谓割肉食鹰,杀身食虎,仁之极,所谓平等者,此也。然而近于墨氏矣[1]227。
依据康有为的分析,墨子甚仁,墨教在仁以救人上与孔教别无二致,可以归为博爱派。与此同时,康有为并没有对二者等量齐观,指出墨子之仁主张兼爱而非等差,与佛教之仁的众生平等相去无几。尽管如此,墨学与佛教一样属于博爱派是可以肯定的,在这一点上,墨子的甚仁与老子的不仁截然相反。有鉴于此,康有为指出:“墨子虽异孔子之道,而日以利天下为事,故《吕氏春秋》曰:孔席不暖,墨突不黔。盖与孔子有同焉。”[5]
对于康有为的哲学而言,墨子是“博爱派哲学”的同调,却是“主乐派哲学”的敌人。对于康有为的“主乐派哲学”,梁启超如是说:“先生之哲学,主乐派哲学也。凡仁必相爱,相爱必使人人得其所欲,而去其所恶。人之所欲者何?曰乐是也。先生以为快乐者众生究竟之目的,凡为乐者固以求乐,凡为苦者亦以为求乐也。耶教之杀身流血,可为极苦,然其目的在天国之乐也。佛教之苦行绝俗,可谓极苦,然其目的在涅槃之乐也。即不歆天国,不爱涅槃,而亦必其以不歆不爱为乐也。是固乐也,若夫孔教之言大同,言太平,为人间世有形之乐,又不待言矣。是故使其魂乐者,良宗教、良学问也;反是则其不良者也。使全国人民皆乐者,良政治也;反是则其不良者也。而其人民得乐之数之多寡,及其乐之大小,则为良否之差率。故各国政体之等级,千差万别,而其最良之鹄,可得而悬指也。墨子之非乐,此墨子所以不成为教主也。若非使人去苦而得乐,则宗教可无设也。”[3]488-489梁启超认定墨子与康有为的“主乐派哲学”背道而驰。应该说,梁启超的这个评价是客观的,也预示了康有为对墨子的否定态度。
具体地说,康有为认为,追求快乐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能,满足人求乐的欲望是仁的具体表现和内在要求。正是基于这种理解,他将乐奉为人生的价值目标和行为追求,大声疾呼“求乐免苦”。与此同时,康有为坚决反对墨子的非乐思想,强调乐与非乐是孔子与墨子的根本分歧,即“孔子极讲乐。墨子不讲乐。”[1]294早在康有为指出墨子是孔教的死对头、处处与孔子作对之时,非乐就是证据之一。对此,他说道:“孔子最讲乐学,故墨子特非之。”[1]151不仅如此,对于墨子的非乐观点,康有为斥之为违背人情、有悖人道,反复从不同角度揭露非乐的错误及其造成的危害。下仅举其一斑:
墨子难行,由于非乐[1]152。
墨子问儒者何故为乐,然则非儒者不为乐矣。儒为孔子所创,故知乐为孔子所制,墨子乃敢肆其轻薄诋诽也。乐所以为乐,欢乐之义,乃真为乐之故也。墨子乃云:犹室以为室。戏侮之甚,可见异教相攻,无所不至[6]133。
按照康有为的说法,与非乐一脉相承,墨子尚俭,这使墨子的思想最苦人道,在现实生活中难以推行,因为其实行起来会给社会、国家和人民生活带来巨大危害——不仅妨碍国家的经济生产、禁锢民智,而且使人生苦不堪言,民气、国气萎靡不振。他再三指出:
墨子其生也勤,其死也俭,最苦人道[2]29。
孔子尚中,而墨子太俭。天下惟中可以立教,偏则不可与治天下。墨子尚俭,其道太苦,其行难为,虽有兼爱之长,究不可以治万世。墨子休矣![1]124
若尚俭,则财泉滞而不流,器用窳而不精,智慧窒而不开,人生苦而不乐,官府坏而不饰,民气偷而不振,国家痿而不强。孔子尚文,非尚俭也;尚俭,则为墨学矣[7]。
康有为进而指出,非乐、尚俭而苦人道最终导致墨子之仁与孔子之仁的渐行渐远,其根本分歧则是孔子尚礼而别,墨子尚俭而同。诚然,康有为宣称,孔子贵仁,墨子也不例外。在这个前提下,他强调,墨子远人讲仁,并且在讲仁时不讲礼,致使墨子之仁由于无文与孔子尚文南辕北辙。具体地说,孔子之仁与文、礼密不可分,尚礼是孔子思想的宗旨,孔子制礼就是为了因人情而治。如此说来,礼是孔教的核心,是用来养人致和的;墨子非礼、非乐,由于丧文、极苦而使天下不和。一言以蔽之,孔子之礼尚别,别所以上下协调;墨子尚同而无别,致使天下不堪,其薄葬主张即是一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康有为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
孔子制礼,以人治人,人情为田,所谓和也。若墨氏其生勤,其死也薄。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则不和也[1]150。
《礼论》“别”字亦孔子一大义,墨子尚同,孔子尚别。尚别,白也。尚同,黑也。尚别,昼也。尚同,夜也。条理极多。擅作典制,指墨子也[1]185。
白圭似墨子,尚质而不尚文者……孔穿为孔子六世孙,亦儒家者。然而白圭、惠子相攻甚力,以其一文一质,宗旨不同,所以交讥。此皆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孔子云: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二子不知孔子改制文质相因之义,故交攻如是[6]64。
夫美者,情所爱乐,号称圆首方足含识之伦,孰有好恶而憎美者。墨子至仁矣,然尚俭太过。庄子以为其道太觳,失天下之心,天下不堪,故去王远。孔子以人为道,故以文为尚,是以其道能行。盖文者,美也,美之为义于文之中,又充实华妙、中于人心焉。盖文之至矣,安得不为天下后世师乎?[8]
在此基础上,康有为进而指出,由于远人以为道,墨子排斥礼乐,不仅有悖人情,最苦人生,而且导致墨子原本出于孔子的兼爱、尚同由于无尊卑、亲疏之别而发生质变,与孔子思想呈现出本质区别,也使墨子从“甚仁”、“至仁”的主观愿望出发演绎出“大觳”的客观后果,并且成为儒、墨相攻的焦点。于是,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礼者,所以治人之魄也;乐者,所以治人之魂也;魂魄治,则内外修,而圣人之能事毕矣。《礼》、《乐》为孔子之制作,故曰:丘已矣夫[6]126。
儒家言命以范人心,设乐以和人志,墨氏皆非之。盖墨氏全是粗迹,毫无精义[1]109。
墨子兼爱、尚同,视至亲如路人,无尊卑、亲疏之别,与儒者异。故荀子攻其二而乱,与孟子攻墨氏“无父”、“无君”、夷子“二本”之意同[6]209。
墨子尚质,贵用,故力攻孔子之礼乐、厚葬、久丧最甚。他篇攻三年丧皆不明,此谓以三年攻三日,(三日当三月之误。)犹果为撅者不恭。以同非先王之制,并是创造。若是三代旧教,大周定礼,墨子岂敢肆口诋诃?且又举与自己所制之三月丧同比哉?盖当时考据通博之人,彼此皆知非三代之制矣。墨子以儒丧三年,愚若婴儿。忘本逐识,此孟子所以谓二本也。乐以为乐,乃欢乐之乐,孔子因人之情而文之,乃制度至精处。墨子听闻未审,乃谓犹室以为室,以此垂之著书,非惟诞肆,亦太粗心[6]118-119。
康有为是中国近代少有的崇尚礼的启蒙思想家。礼有等贵贱、别亲疏之特点和功能,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被用来彰显宗法等级,故而被近代思想家所深恶痛绝。康有为所推崇的礼是孔子时中的表现,与仁、文和乐息息相关,也是出于养人、致和的需要。这使礼成为康有为“主乐派哲学”的一部分,并且与“博爱派哲学”一脉相承。对礼、乐的推崇注定了康有为对墨子非乐以及与此相关的节葬、节用的深恶痛绝,借口墨子非乐有质无文,有悖人情。与此同时,康有为指出,尽管具体主张不同,墨子与老子都漠视礼,这使两人在非乐而苦人生上殊途同归,最终都站在了“主乐派哲学”的对立面。对此,康有为反复强调:
老氏以无为为宗旨,墨子以尚俭为宗旨,故买名誉、饰礼貌者,二氏皆攻之也[6]178。
饰礼淫乐,崇死久丧,其(指《淮南子·齐俗训》的“礼饰以烦,乐优以淫,崇死以害生,久丧以招行”——引者注)攻与墨子同。是老学亦大不以为然者。老学为法净自然,不为饰外也[6]179。
《论语》: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庄子》谓:墨子不与先王同,毁古之礼乐。先王即孔子,托以制礼者也。墨子以绳墨自矫,以自苦为极,无以养人之欲,无以给人之求。乖戾不和,使人忧悲,故其道大觳,其行难为,不可以为圣王之道也。老子谓: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塞人之情,蔽人之欲,是乱天下也。又曰: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开魏、晋清谈放诞之风,乘谬尤甚。老、墨皆攻孔子之礼制者也[6]117。
上述内容显示,对作为哲学家的墨子,康有为同样毁誉参半,因为他是根据自己的哲学对墨子加以权衡和评判的。这就是说,与作为宗教家的待遇相似,作为哲学家的墨子在康有为的视界中也具有两面性。其实,墨子的两面性及其康有为给予的一切矛盾评价均由两条相互交织的线索而来,故而可以从这两条线索中得到解释。其中,一条线索是康有为的宗教宽容与对孔教的独尊,另一条线索是广义的孔教与狭义的孔教。每条线索的张力注定了墨子在康有为视界中的身份错位和思想混乱,这两条线索之间的交叉更加大了墨子身份以及思想的矛盾和混乱。当然,由这两条线索构成的两套标准是相互交叉的,甚至有重合之处:康有为的哲学因循孔教而来,无论“博爱派哲学”还是“主乐派哲学”在他看来与其说是他本人的观点,不如说是孔子思想的题中应有之义。不仅如此,作为康有为哲学的仁、乐等主张按照他的说法就是孔教的宗旨,乃至是一切宗教的终极目标。与此同时,正如宗教与哲学相混一样,康有为托孔言己,他的思想与他所声称的孔子思想是相合的,他推崇的孔教在本质上就是“康教”(梁启超语)。有鉴于此,康有为对作为宗教家与作为哲学家的墨子的褒贬具有一以贯之的共同依据,从这个角度看,对墨子作宗教家与哲学家的区分只具有相对的意义。
[1]康有为全集:第2 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2]康有为学术文化随笔[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
[3]梁启超全集:第1 册[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4]康有为全集:第1 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5]康有为全集:第5 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498.
[6]康有为全集:第3 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7]康有为全集:第6 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434.
[8]康有为全集:第8 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4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