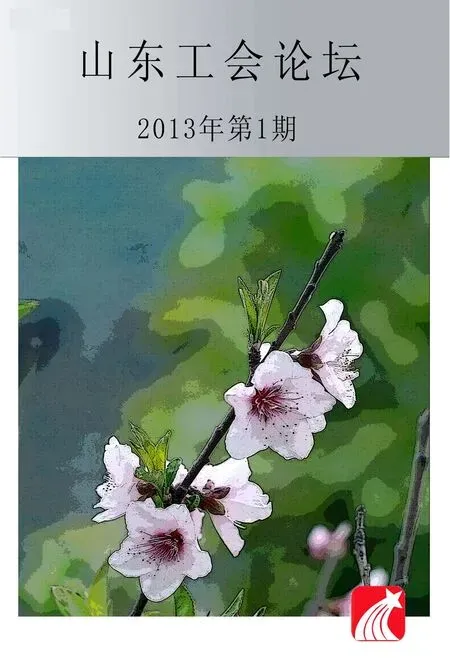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实务探析
2013-04-11刘传稿黄鹤婷朱伟
刘传稿,黄鹤婷,朱伟
(1.中国人民大学,北京100872;2.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北京100872;3.山东省工会管理干部学院,山东济南 250001)
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实务探析
刘传稿1,黄鹤婷2,朱伟3
(1.中国人民大学,北京100872;2.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北京100872;3.山东省工会管理干部学院,山东济南 250001)
我国刑法典对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的规定采用的是空白罪状的模式,而相应的土地管理法规对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的犯罪构成特征又缺乏具体的规定,因此对于该罪的争议一直持续不断。在判断是否构成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时,应当先明确土地使用权的归属,再从法律的角度区分刑事违法和民事、行政违法的界限,进而认定主观的牟利目的和客观的刑事违法。
牟利;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
一、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的法律规定
对于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的构成形式,刑法第228条规定为:“以牟利为目的,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价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二十以下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价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二十以下罚金。”由于该条规定不够详细,在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务中一直纷争不断。本文拟结合相关理论及司法解释,重点分析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在司法实务中面临的问题及解决方式。
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是指以牟利为目的,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情节严重的行为。[1]本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情节严重的行为。目前,我国现行的土地管理法规主要有:《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国务院关于出让国家土地使用权批准权限的通知》、《城镇国家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等。违反土地管理法规,即违反上述一部或数部法律文件的规定。土地使用权转让是指土地使用者依法获得土地使用权后,将土地使用权再次转移的行为,包括出售、交换和赠送。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属于情节犯,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的行为必须达到情节严重,才能构成该罪。2000年6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0〕14号文件《关于审理破坏土地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对“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作出了规定。
以上是从法定的角度对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进行论述,但是在实务中,有很多问题仅从该层面难以妥善解决,本文拟结合实际案例,尝试对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进行多视角的探析,对认定该罪提供一个可行的路径。
二、司法实例
被告人刘某,男,1965年生于山东省青岛市,系青岛市某工业物质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因某国有盐厂对其公司负有债务170万元到期不能偿还,刘某申请法院拍卖该盐厂的一块土地使用权,约240000平方米(该宗土地原以划拨的方式取得),2003年12月,刘某通过竞拍以430万元的价格拍下了该宗土地的使用权,国土部门为其办理了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的过户手续。2004年8月,刘某将该土地使用权以10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某民营公司,并在国土部门办理了土地使用权转让手续。2010年11月16日,刘某被其所在的区人民法院以非法倒卖土地使用权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法院认为,刘某没有实际投入资金进行开发,取得土地使用权系为转卖赚钱,足以反映出被告人刘某主观牟利的目的,被告人刘某与某区国土资源局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在未按照合同约定对土地进行投资开发的情况下转让土地使用权,违反了《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中有关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的规定,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构成非法倒卖土地使用权罪,应予惩处。
三、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的多视角认定
(一)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是否应以取得土地使用权为前提
依照我国当前法律规定,“土地使用权”应当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土地使用权”是指依法通过划拨和受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证后拥有的土地使用权。广义的“土地使用权”是指除了狭义的土地使用权之外,还包括通过租赁、抵押等事实占有的方式所取得的土地使用权。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当然应限制于狭义的“土地使用权”,因为根据我国物权法的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转移要以登记为准,不进行登记不动产物权在法律上是不发生变动的,因而土地使用权不通过土地主管部门登记变更是不可能发生转移的。这就要求行为人在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之前,应依法取得土地使用权,否则不可能将土地使用权再行转让。有人认为,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的理解和适用应当以行为人实际交易的土地权利的内容来判定是否构成该罪,不应当以行为人是否拥有土地使用权作为构成该罪的充分必要条件。[2]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不可取的。它违背了我国物权法规定的不动产物权变动登记的原则,必将无限扩大该罪处罚的范围,导致刑罚权的滥用,使刑法不当延伸至民事和行政领域,不仅使刑法难以发挥保障的作用,反而会侵害众多人的民事权利。德国刑法学家耶林说过:“刑罚如两刃之剑,用之不得其当,则国家与个人两受其害。”[3]
(二)以牟利为目的的认定
牟利的意思是指取得的利益超出了应该获得的,一般形容贪婪的攫取巨大利益,违反道德,甚至法律。该罪的成立不能将行为人取得土地使用权获得的收益和其转让土地使用权支出的费用简单相减。认为只要在转让土地使用权的过程中获取了巨额利润就是以牟利为目的的观点是不可取的。考查是否以牟利为目的,应综合考虑行为人转让土地使用权的起因、受到的损失等各种因素。以牟利为目的,必须要求行为人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的终极目的是为了获取巨额利益,在攫取巨额差价的过程中,其行为和土地管理法规的要求是逆向的,并且其没有具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明其行为的正当性。如果行为人有合法的理由转让土地使用权,而不是为了通过转让行为单纯获利,那么即便在客观上真的获取了利润,也不能以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论处。
在上述案例中,刘某所在的工业物资有限公司因对该国有盐厂享有债权,且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盐厂应当付给刘某的公司货款本金170万元,自债权确定后,盐厂一直没有履行判决,刘某所在的公司因此资金缺乏,经营困难,以致不能按时参加年检被吊销营业执照,刘某因此所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在取得土地使用权的过程中,刘某支付了430万元的各项费用,尽管刘某通过转让土地使用权获取了400万元的利润,但刘某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实现其债权,挽回损失才将土地使用权进行转让的,在这种情况下,认定刘某主观上以牟利为目的是不妥当的。
(三)关于“非法”的认定
该罪规定要求以违反土地管理法规为前提,可见该罪罪状属于空白罪状,空白罪状最显著的特点是某种具体犯罪的构成要件需要参照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加以确定。空白罪状可以使刑法典具有包容性、超前性和严密性,但是空白罪状的高度开放性有扩罪的潜在隐患,可能使刑法典的处罚功能不当扩大。此外,空白罪状将犯罪的具体特征留给其他的法律文件去规定,而被参照的法律文件往往对具体犯罪构成要件规定不够具体、明确,这就使得空白罪状的参照依据缺乏具体性,进而使现存的罪名变得十分模糊。具体到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该罪的的成立要以土地管理法规的前置性判断为前提,其具体犯罪成立条件的界定需参照土地管理法规,而是否符合土地管理法规就成为构成犯罪与否的关键。这里存在一个争议的焦点,即是否只要不符合土地管理法规的规定就是该罪所描述的“非法”呢?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5年第7期《桂馨源公司诉全威公司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案》可以对此问题提供一个司法实务方面的参考。国土资源局同意转让方以出让方式取得诉争土地的使用权,双方签订有《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转让方办理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诉争土地具备了进入市场进行依法转让的条件。关于投资开发的问题,法律关于土地转让时投资应达到开发投资总额25%的规定,是对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标的物设定的关于物权变动时的限制性条件,转让的土地未达到25%以上的投资,属合同标的物的瑕疵,并不直接影响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效力,该项规定不是认定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效力的法律强制性规定,以合同未达到25%投资开发条件认定无效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4]在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份判决中,明确了以下立场:第一,当事人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就可以转让土地使用权,这是土地进入市场依法转让的唯一条件。第二,投资不到25%不是构成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罪的前置条件。最高院的判决提出了土地管理法规中对土地投资开发程度的规定,特别是25%的规定只是物权变动的要件而非转让合同生效要件,投资不到25%只是“物权变动时的限制性条件”,而不是认定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无效的条件,当然也就不是认定构成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罪的条件。本案中,刘某和区国土资源局签订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缴纳了土地出让金,取得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认定,其符合转让土地使用权的条件,依法有权利同他人签订《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受到限制的仅仅是区国土资源局所主导控制的“物权变更登记”。
由此,我们可以转让土地使用权的前置性条件做以下归结:持有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或依法批准的使用土地的文件;按照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支付出让金;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如果不满足上述三个条件,即可认定是刑事违法,违反土地管理法规其他规定的,可认为是民事或行政违法,适用刑法以外的法律进行调节。
(四)申请人基于行政许可做出的行为不具有可罚性
根据最高法院的认定,投资不到25%只是“物权变动时的限制性条件”,它制约的是土地行政管理部门对物权的变动,即制约土地行政管理部门变更土地使用权的行政许可。但本案中,刘某转让土地使用权得到了区人民政府主管部门的批准,政府主管部门的行政许可决定了对刘某的行为不能进行刑事处罚。
根据《行政许可法》的相关规定,行政许可的性质就是“赋予行政管理相对人权利”。《行政许可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行政许可,是指行政机关根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查,准予其从事特定活动的行为。政府部门的行政许可,赋予了行为人转让土地使用权的权利,在政府行政许可的背景下,法律赋予行政管理相对人的权利得以实现。应当视为行政管理相对人在政府主导审批下实现权利的行为,不具有刑事处罚性,这也符合《行政许可法》所确立的信赖保护原则,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取得的行政许可受法律保护。[5]否则,在依法取得政府行政许可的前提下,如果不考虑政府的主导,对行为人进行刑事追究,不但理论上解释不通,实践中也必然影响政府的威信。
本案中,刘某在2004年8月取得《土地使用权证》后,向所在的区国土资源局提出申请要求转让土地使用权,并填报了《出让土地使用权转让申请表》,在申请过程中也没有任何的欺骗、隐瞒、行贿等非法活动,该申请经区国土资源局审批,准予转让,变更了土地使用权登记,向受让方颁发了土地使用权证。政府部门的行政许可,赋予了行为人转让土地使用权的权利,政府的行政许可,也使得投资不到25%只是“物权变动时的限制性条件”不再是物权变动的障碍。因此,刘某基于政府的行政许可而转让土地使用权的行为,应当受法律的保护而阻却刑事违法性。
四、结语
刑法第228条关于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的规定采用的是空白罪状的立法模式,内容比较简单,加上在认定行政违法的程度和形式符合刑法入罪标准时存在一定的难度,以及实践中行为的复杂性,使得法条规定存在一定的空白和模糊,加剧了罪与非罪的认定难度。因此,在认定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的过程中,应该坚持正确的法律运用逻辑:首先,应当明确土地使用权的所属,然后,从法律上区分刑事违法和民事、行政违法的合理界限,最后,准确认定主观的牟利目的和刑事违法的客观表现。司法机关严格把握入罪标准,既不能放纵犯罪,也不能扩大刑事处罚范围,谨慎、准确地适用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
[1]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第五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456.
[2]卢煌.构成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罪是否必须以取得土地使用权为前提[EB/OL].http://www.110.com/ziliao/ article-172335.html.
[3]陈兴良.刑法的价值构造(第二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292.
[4]《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J].2005,(7):13-21.
[5]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第三版)[M].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271.
(责任编辑:滕元良)
D924.3
A
1008—6153(2013)01—0058—03
2012-12-13
刘传稿(1982-),男,山东梁山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研究生。黄鹤婷(1989-),女,陕西西安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硕士研究生。朱伟(1982-),男,山东济南人,山东省工会管理干部学院财务处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