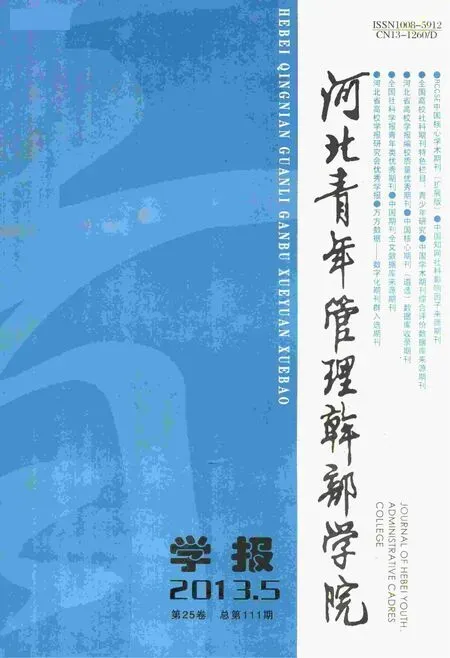嵇康玄学思想成因新探
2013-04-11张立恩
张立恩
(曲阜师范大学,山东 日照276826)
一、竹林时期的政治现实
竹林玄学所在的历史时期大约在魏齐王曹芳嘉平初至魏元帝曹奂景元年间(250-263)。在这段时期,司马氏与曹魏氏两集团间的政治斗争日趋激烈,国家政权日趋分化,政局动荡不安。晋宣帝司马懿为人“内忌而外宽,猜忌多权变”[1]17-18。正始十年(249)正月,司马懿趁曹爽兄弟随魏帝祭扫明帝高平陵之机,发动政变,迫使曹爽交出大权,并以谋反罪诛曹爽兄弟。嘉平三年(251),王凌欲拥楚王曹彪为帝,以伐吴为名请求发兵。司马懿以谋反罪发兵讨凌,凌事败被害。之后司马懿进军寿春,开挖王凌坟墓,剖棺暴尸,并将与王凌事牵连者诛灭三族。“司马懿父子的坚忍阴毒,连子孙也感到羞耻,以至怀疑晋祚能不能长久保持下去。”[2]15“明帝时,王导侍坐。帝问前世所以得天下,导乃陈帝创业之始,及文帝末高贵乡公事。明帝以面覆床曰:‘若如公言,晋祚复安得长远!’”[1]18正元二年(255),魏扬州刺史前将军文钦、镇东将军毋丘俭起兵寿春,称“矫太后诏,罪状大将军司马景王,移诸郡园,举兵反”[3]486,司马师率军10万征讨,杀死毋丘俭,文钦逃入孙吴。甘露二年(257),魏征东将军诸葛诞于寿春反。司马昭督军26万征讨,三年(258)正月,诸葛诞兵败被杀。甘露五年,魏帝曹髦预感司马昭篡权之心,率宿卫百人讨昭,被司马昭亲信杀死,司马昭遂立曹奂为元帝。至此,魏政权已被司马氏所控制,魏名存实亡。
这种政治现实严重破坏了名教的社会功能,在客观上成为嵇康玄学思想生成的外部条件,激发嵇康玄学思想的形成。通过嵇康的诗文材料来看,其玄学思想的发展经历了由名教与自然合一到“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演变过程①余敦康先生认为“稽康原来也是以名教与自然相结合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的”,“在原来的精神支柱崩溃以后承受了巨大的内心痛苦继续从事新的探索。”后即“在《释私论》中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口号”。此说甚是。见余敦康,《魏晋玄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第302—306页,促成这一演变过程的外缘因素②外缘因素即可然因素,无此可然因素则必无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之玄学思想。则是司马氏伪名教统治。司马氏借名教之名而行毁名教之实的做法将名教与自然的冲突推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名教失范的残酷现实,对一般人而言大可不必理会,甚至一些陋儒还可借此诛除异己,成为“一批与时代精神相背离的‘寡廉鲜耻贪冒骄奢之鄙夫’”[4]300。但真正的思想家不可能对此熟视无睹,名教失范使“嵇康在现实的社会中对司马氏的假名教感受痛切”[5]。作为一介书生,他无力扭转现实,只能一面在自我的精神世界中高扬理想,一面以己之高洁与世俗对抗。诚如鲁迅先生所说:“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魏晋时所谓崇奉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是偶然崇奉,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嵇康,都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但实在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渎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6]535当然,政治现实只是嵇康玄学思想产生的外部条件,玄学思潮对嵇康的影响亦不可忽略。
二、玄学思潮
玄学的本质“是一种阐发内圣外王之道的政治哲学,它力求与世界协调一致,为当时的不合理的政治局面找到一种合理的调整方案。但是,当现实变得更不合理,连调整的可能性也完全丧失时,玄学就从世界分离出来而退回到自身,用应该实现的理想来对抗现有的存在”[4]301。“其意义主要是一改汉代建立在经验世界范围内的烦琐经学和谶纬神学,而把目光投向了世界的终极本体,重新揭示出万物存在的依据,其核心即是名教存在的根据和价值。”[7]玄学思潮的发展要求玄学家“用应该实现的理想来对抗现有的存在”,嵇康顺应玄学思潮的发展要求,自觉承担起玄学演化的时代课题,其着眼点即名教与自然之关系。玄学思潮对嵇康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纯任自然的生命形式。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8]501,“土木形骸,不自藻饰”,[1]1116而且他“头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9]272,完全是一幅纯任自然、不修边幅的形象。二是纯任自然的人生境界。他说:“息徒兰圃,抹马华山,流磻平皋,垂纶长川。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9]12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他更明确表达了自己渴望过一种淡泊宁静,充满亲情慰藉的生活,“今但愿守陋巷,教养子孙,时与亲旧叙离阔,陈说平生,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愿毕矣。”罗宗强先生亦认为,嵇康渴望返归自然,但又并非不食人间烟火,不是缥缈虚无而是优游适意、自足怀抱。这正是玄学思潮作用于人生理想的一种典型反映。
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玄学思潮对嵇康人生境界的影响是以儒学为基础的。嵇康了无牵挂、怡然自乐的人生境界是司马氏华丽伪名教下的一种简单的真实,他以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保持着名教与自然的合一,“越名教而任自然”只是对当时名实相背的名教的一种摒弃。正是为此,他才没有像庄子那样要泯灭自我、返归自然,达到身如枯木、心如死灰的坐忘境界,而是在“越名任心”的玄思中保留了一份充满人间意味的境界。不论是政治现实的逼迫还是玄学思潮演化的内在要求,都要求“越名教而任自然”玄学主题的形成,但历史之所以最终选择了嵇康,这又必然与嵇康本人的性格气质息息相关。
三、嵇康的性格和气质
嵇康性格“恬静寡欲”喜欢“弹琴咏诗”[1]1116。在《述志诗》中他说:“浮游太清中,更求新相知。比翼翔云汉,饮露食琼枝。多谢世间人,夙驾咸驱驰。冲净得自然,荣华何足为!”[9]289-290表明自己恬淡寡欲、冲净自然的个性。冲净自然之性的实质是保持自我、崇尚自由,不为世俗所羁绊。这种性格一方面是家庭环境造就的,嵇康早年丧父,由母兄抚养成人,母兄对他多溺爱。他在《幽愤诗》中对此有所说明:“母兄鞠育,有慈无威”[9]295;另一方面又源于道家思想的影响,他自幼“学不师受,博览无不该通,长好《老》《庄》”[1]1116。嵇康恬静寡欲的个性使他对自然有种特殊的感悟力,当他早期玄学思想无法实现时,他便转而与阮籍、向秀等人一起做竹林之游,探赜玄远。在恬淡自由的性格之中,嵇康又有其刚烈与狂傲。嵇康曾从孙登游汲郡山中,“登沈默自守,无所言说。康临去,登曰:‘君性烈而才隽,其能免乎?’”[1]1117孙登对嵇康性格的评断不可谓不确当,及后来嵇康因吕安事被捕下狱,作诗自责云:“昔惭下惠,今愧孙登。”[1]1119但嵇康的刚烈并非生性好怒,而是源于一种嫉恶如仇的正义感,否则其好友王戎就不会说:“与嵇康居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9]12对待朋友他能“含垢匿瑕,宽简有大量”[1]1116,对待是非原则,他则“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9]274比如,他的好友吕安,其妻徐氏被安兄长吕巽奸淫,巽反污蔑安不孝,诬其入狱。吕安引康为证,康义不负心,保明其事。嵇康的这种强烈的正义感还以一种蔑视权贵的狂傲表现出来。嵇康“尝与向秀共锻于大树之下,以自赡给。颍川钟会,贵公子也,精练有才辩,故往造焉。康不为之礼,而锻不辍。良久会去,康谓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会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1]1120嵇康的刚烈和狂傲深为钟会所嫉恨,后来钟会借吕安事以“言论放荡,非毁典谟”[1]1120之罪进谗司马昭杀死嵇康。
就嵇康的个人气质言,儒道兼有,其恬淡寡欲是受道家文化的影响,而其“刚肠疾恶,轻肆直言”[9]274、“直性狭中,多所不堪”[9]270则明显是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虽然他说:“六经以抑引为主,人性以从欲为欢,”[9]143具有明显反儒色彩。但笔者以为,嵇康此论实无奈之言,“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1]1108,嵇康绝不可能将批判的矛头指向司马氏的黑暗统治,因而只能借批儒达到否定司马氏伪名教的目的。就嵇康的人格与处事方式来看实则更符合儒学精神。首先,嵇康对理想世界的执着追求是儒学精神的体现。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10]188。嵇康以身殉道的事实,正是儒学精神在他身上的体现。孔子说:“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10]165又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10]94在司马氏专权的无道之世,嵇康能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9]12,此正是其“言孙”。无论是与阮籍等人做竹林之游,还是与向子期锻铁大树下,皆是其“无道则隐”。其次,就毁弃礼法言,嵇康除“头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闷痒,不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转乃起耳”[9]272之外,一生并无真正毁弃礼法之行为。嵇康头面不洗、忍便不起的这些行为正符合孔子“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10]234的主张。孔子说:“唯酒无量,不及乱”[10]115“不为酒困”[10]106,嵇康则在《家诫》中告诫儿子嵇绍“不当至困醉”[9]311。子贡说:“君子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10]240嵇康则说:“夫言语,君子之机。机动应物,则是非之形著矣,故不可不慎。”[9]307如上所云,则嵇康之精神与孔子儒学精神不可不谓一脉相承也!嵇康儒道兼之的性格气质,使他在人生境界上始终表现出渴望返归自然的一面,“目送归鸿,手挥五弦”[9]12;而在现实中又能恪守儒家道德原则,既不会像钟会之流,虽为谈玄名士却人格下流,也不会像山涛、王戎之辈,一面高标理想一面曲己应势。
综上所述,政治环境是嵇康玄学思想产生的现实条件,玄学思潮构成了嵇康玄学思想产生的文化条件,嵇康本人的性格气质则是他玄学思想产生的必要条件。当政治现实迫使他不得不放弃对名教与自然合一的努力时,玄学思潮便自然成为慰藉心灵的良药。玄学思潮塑造了嵇康追慕自然的气质,这种气质使得他追求一种恬静寡欲、超然自适的生活。但即便是这样,一个简单的理想却依然难容于世,于是他性格中的刚烈狂傲被彻底激发出来,促使他以一种决绝的态度倡导“越名教而任自然”之道,藉此与司马氏伪名教相抗衡。
[1]许嘉璐.二十四史全译·晋书[M].上海:汉语大辞典出版社,2004.
[2]陈寅恪,万绳楠.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M].合肥:黄山书社,2012.
[3]许嘉璐.二十四史全译·三国志[M].上海:汉语大辞典出版社,2004.
[4]余敦康.魏晋玄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5]陈明.嵇阮的人生哲学与人生道路[J].求索,1990,(6).
[6]鲁迅.鲁迅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7]史向前.嵇康与魏晋玄学思潮[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4).
[8]柳士镇,刘开骅.世说新语全译[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
[9]夏明钊.嵇康集译注[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
[10]杨伯峻,杨逢彬.论语译注[M].长沙:岳麓书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