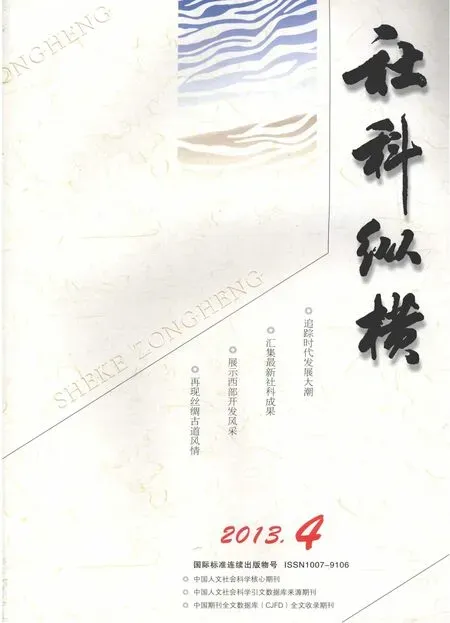《礼记》的生态环保意识和可持续发展意识
2013-04-10王云飞
王云飞
(开封文化艺术职业学院基础部 河南 开封 475004)
在《礼记》一书中,先民的论述反映了环保意识、节俭意识、农业、建筑业生产的时令意识、工商管理的标准意识以及通过行政干预维护可持续发展的意识。
一、环保意识和可持续发展意识
《礼记·王制》[1](以下引同书只写篇名)指出:“田不以礼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围。诸侯不掩群。……獭祭鱼,然后虞人入泽梁。豺祭兽。然后田猎。鸠化为鹰,然后设罻罗。草木零落,然后入山林。昆虫未蛰,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杀胎。不殀夭。不覆巢。”[1]这是说,古人打猎讲究时令、不杀光杀绝,不在春季杀动物,不杀幼兽和母兽,不伤胎、卵,不毁巢穴。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来年有可渔之鱼,可猎之兽。鱼苗幼崽是重要的生产资料来源。保护好这些资源,有利于未来获得更多的动物。这就需要休渔休猎。这是可持续发展的选择。《曲礼下》进一步指出:“国君春田不围泽,大夫不掩群,士不取麛卵。”[1]春季渔猎要留种,不取幼兽与雏鸟、鸟卵。反对竭泽而渔。这种保护幼小动物的思想,是古代士人从可持续发展,对资源加以储备的角度进行的可贵的宣示。古人保护动物的观念和现代保护动物的观念不同。古人是为了储备资源,保护进一步发展的基础。我们今天保护动物,主要是保护生物多样化,保护稀有野生动物,保护生物链和基因库的完整性。当然,也含有保护稀有资源的意味。不少濒临灭绝的珍稀动物都曾被人们用作重要的中药材。古人的“万物有灵论”和佛教的“不杀生”戒律,在一定程度上,为动物和植物的保护起到了屏障作用。《内则》指出,“雏尾不盈握弗食。”[1]在周代贵族的食谱里,虽然有鸟类,然而,鸟尾抓不满手是不可以吃的。显然,清醒的士大夫们,在为贵族定一些规矩。不要肆意杀戮小兽、小鱼、小鸟,要考虑未来生存的需要。总之,保护生物多样化,保护稀缺资源,就是保护我们人类的未来。
二、标准意识和工商管理思想
《王制》指出不准许粥(鬻)於市的若干产品。例如:圭璧金璋、宗庙之器、牺牲、戎器、用器不中度、兵车不中度、布帛精粗不中数、幅广狭不中量、奸色乱正色、锦文珠玉成器、衣服饮食、五谷不时果实未熟、木不中伐、禽兽鱼鳖不中杀,这些东西都不能上市。[1]前三种和第九、十种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等级尊严。其它八、九种情况,很明显,是统治者想要建立一种工商管理制度,使上市的商品“标准化”。如上所述,军需品、官印、祭品、宗庙之器不能卖;大众用品的成色或数量不足不能出售。而且从资源保护着眼,动物幼崽鱼苗不能杀,果实不熟不能卖,伐木要符合一定的直径标准和季节要求。商品还要符合美观和民族习尚。这些要求是笼统的,尚无便于操作的细则。然而,这也足以说明,已经具有对商品质量的诉求,即从数量到质量对商品建立起一定的标准,并使这种标准制度化。我们知道,秦始皇陵兵马俑坑等处出土的上万件秦代兵器尺寸大小、成色都令人震惊的实现了标准化。汉代士人的标准意识更加普遍化。把对物品制作标准的要求从武器领域推广到日常生活用品领域。这就是所谓秦汉人的标准意识。标准化有利于机器制作的方便和使用、维修的方便。当然,在上述“不粥於市”的东西中,有些是为了保护生产资料的资源,如未成材的小树、未长成的禽兽鱼类等动植物不能捕捞、采集,更不能投入市场。所谓“奸色乱正色”则是对商品的正宗性进行鉴别,对不符合统治者要求的则要加以淘汰。很显然,保护树木、幼禽幼兽的观点是出于对保证社会可持续发展而考虑的。有些则是统治阶级企图实行专享制度,如“用器不中度”;有些是特权制度,如戎器等军用物资不准上市。这是从维护统治阶级政权和社会稳定的愿望出发而提出的美好愿望和正确建议。
三、基于农业生产的时令意识
立春以后,“帝籍”,借以为全国人民建立农耕的榜样。皇帝籍田,以身作则,以示农耕的重要性。“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天地和同。草木萌动。王命布农事命田舍东郊。皆修封疆,审端径术。善相丘陵阪险原隰土地所宜。五谷所殖。以教导民必躬亲之。乃修祭典,命祀山林川泽牺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杀孩虫胎夭飞鸟。毋麛毋卵。毋聚大众。毋置城郭。掩骨埋胔。是月也,不可以称兵。称兵必天殃。兵戎不起,不可从我始。毋变天之道,毋绝天之理,毋乱天之纪。”[1]汉代人充分认识到,春季万物复苏。因地制宜,种植五谷。教民勤农事。以隆重的祭祀向公众宣告保护山林川泽—切生灵,并且祭祀所用牛羊豕不得使用牝母。因为,雌性动物可以大量繁殖幼崽幼雏,为人民大众提供生活资料。为了有效实行这些愿望,就要借助神威,害雌兽就是冒犯神灵。民间习惯,伐木要在秋后落叶之际和春季发芽之前。这时期木料坚固。发芽之后,树木就空虚。士人还要求不毁鸟巢,不杀幼小虫类、飞鸟。不要破坏虫卵,如青蛙卵。掩埋腥秽以作肥料。停建城郭以不违农时。春季不言兵,不兴兵戎,从我做起。充分显示了汉代士人热心建设国家,保卫和平生活的美好愿望。以上适合春季的工作和所禁止的一些不良作为,都是从时令着眼,最终服务于社会生产和民族生活可持续发展这一根本要义。汉代还能够根据春季气候反常与否来推测年成丰歉,以便及时防止自然灾害。
汉代士人根据历史积累的经验,孟夏之月“毋起土功,毋发大众,毋伐大树。……命野虞出行田原为天子劳农劝民。毋或失时。命司徒循行县鄙,命农勉作,毋休于都。”[1]在古代,夏季是十分不适宜搞建筑的。夏季风雨暴作气候无常,不利土功。同时,树木内已空虚,木不坚固,不宜砍伐。春夏之际,都是从事农业生产、中耕除草、点种秋作物的重要季节,不可失去时机,致使土地荒芜。征用土地也要考虑在作物收获之后。那么,什么时候从事起房盖屋、建立城郭合适呢?种麦(寒露至霜降)前后,雷始收声,“可以筑城郭,建都邑穿窦窖,修囷仓。”[1]兴土工,建筑民居、建筑防护工程,同时主要建立仓窖,储存粮食、薯类、菜类,以备冬春之用。“草木黄落,伐薪为炭”,正当其时。仲冬之月,“命有司曰,土事毋作,慎毋发盖。毋发室屋,及起大众,以固而闭。”[1]“毋作大事,以妨农事。”[1]这是说,仲冬时节冰坚水冷,不适宜搞土木工程,小心人畜冻伤、薯蔬冻坏。不要轻易动用劳动力,以安众庶。这反映了汉代士人为劳苦大众着想的良苦用心。
《月令》全篇以“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将天象、气候、时令与人事:政治、法律、生产、生活、祭祀、军事等等联系起来,而且,在时令与气候、收成、灾祥的关系上,论述得比较合乎自然规律和辩证法思想。《月令》在《逸周书》中作《月令解》第五十三,是个残篇。[2]说明早在周代就已经有成熟的用来指导农业生产生活的书籍。以吕不韦为代表的秦代政治理论家们对古已有之的关于节气时令的观点给予系统化的表述,更加符合当时人们的社会理想。他们将“理想”融入了对自然、社会、人生的体验、经验、教训和建设美好社会的期望之中。当时的宗教意识已由泛灵论过渡到多神论,并和大一统思想并存。五行思想的运用非常成熟,有关气象的解释表明作者精通天文星经,将社会生活神秘化——一切归于天象与时令。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一切按照循环论和机械唯物论思想家们安排的顺序循序渐进。这些思想及其来源一并反映于当时的农业社会,也在一定程度上适合当时的农业社会。作者竭力使人相信,这是皇天上帝的安排。气候反常造成的后果显然经过长期乃至数代人的总结而形成了预言性的猜想。这些臆测对于今天进行长时段天气、墒情、灾情预报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例如:“仲春行秋令,则其国大水。……行冬令,则阳气不胜,麦多不熟民多相掠。行夏令,则国乃大旱,煖气早来,虫螟为害。”“季春行冬令,则寒气时发,草木皆肃。民多疾疫。时雨不降,山林不收。行秋令,则天多沈阴。淫雨蚤降,兵革并起。”[1]这些记载毫无疑问,是对自然和社会生产过程长期观察的记录和总结。近年来,新闻多有秋冬树开花的报道,是时令反常、厄尔尼诺现象的表现。至于“兵革并起”的说法,与气候反常,蒙古高原牧草不足,引起匈奴南侵有关,这是曾经有过的史实。只是作者做了机械化的理解。民间谚语说道,该热不热,五谷不结。由此可知,《月令》对于工农业生产、对于气象预报具有重要的史料、参考价值。文章主体当是周代早中期史官的记述。秦相吕不韦及其门客加以整理、发挥,汉代士人做过改动并给予充分肯定。
《月令》作为资政文书,也提出了赈灾济贫、省减刑罚的思想:在仲春之月,“安萌芽,养幼少,存诸孤。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肆掠,止狱讼。……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发仓廪,赐贫穷,振乏绝;开府库,出币帛,周天下。”[1]在青黄不接之际,开仓济贫扶困赒济众生,这反映汉代统治者为了政治稳定,认识到关心民众生活的必要性。所谓“命工师令百工审五库之量、金铁、皮革筋、角齿、羽箭干,脂胶丹漆,毋或不良。百工咸理,监工日号。毋悖于时,毋或作为淫巧以荡上心。”[1]政府注重兴修水利,“修理隄防,道(导)达沟渎。”注重交通,“开通道路,毋有障塞。”注重工商管理,讲求百工质量。这些无疑是对的。但是,政府对实业管理过严,过于干预,其结果必然导致抑制科学技术的正常发展。他们容不得创造发明,容不得创新,容不得标新立异,甚至容不得简单的技术改造和革新。一旦有新事物出现,不合乎封建政府的标准,他们就会斥之为“奇技淫巧”。认为这些全要不得,正是这些迂腐的思想,窒息了中国古代志士贤良的聪明才智,扼制了科学技术的发展。这一思想影响至深至远,以至于清代慈禧太后将修铁路视为破坏风水,将新生事物视为异己力量,欲除之而后快。历代新生事物的发明创造者都生存得非常艰难,常常遭到无端打击。这些行为追根溯源,可以归咎于《礼记·月令》篇。这是它的重大理论缺陷。
四、节俭意识的发扬光大
《曲礼下》倡导节食节用的节约思想。这一思想显然是受到了墨家的思想影响。“岁凶。年谷不登,君膳不祭肺,马不食谷。弛道不除,祭事不縣。大夫不食粱,士饮酒不乐。”[1]要求年景不好的时候,君主也不能食动物肉。马不喂谷物。大夫不吃精美主食,贵族饮酒不得用乐。这些思想无疑是可贵的。
《檀弓上》记载了具有高风亮节的子高先生要求将自己死后葬于不食之地的故事。“成子高寝疾,庆遗入请曰,子之病革矣。如至乎大病,则如之何。子高曰:吾闻之也。生有益于人,死不害于人。吾纵生无益于人,吾可以死害于人乎哉?吾死则择不食之地而葬我焉。”[1]成子高在卧床不起时,提出生要有益于人,死要不害于人的重要思想。要求在自己死后葬在不能供养人的硗薄闲地,不占据耕地良田。他的这一思想,显示了一个贤士大夫的高风亮节,闪耀着人本主义的光辉。节葬是对节俭观念的具体要求之一。“刍灵”、“明器”都是古圣贤废除野蛮的人殉制度的伟大发明。“明器”即“冥器”。原本殉葬用生前实物。为了避免人力、物力资源的无谓浪费,后来就造出家具、器用的模型以便代替实物来为死去的亲属殉葬,这种模型就是“冥器”。死者生前喜欢狗马,或喜欢他的侍从、卫士,死后有可能会被殉葬。圣贤们想出个好办法,这就是雕刻些木器或用火烧制些陶猫、陶狗、陶鸡、陶马或陶佣。使那些活灵活现活泼可爱的生灵、那些墓主生前的亲信得免于活埋而死亡的威胁。陶制动物和陶俑是一种造假,但是,这种造假行为却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它使动物和人得免于无谓的送死,保护了生物、生产力和生活资料,保证了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孔子为明器者,知丧道矣。备物而不可用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用殉乎哉。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塗车刍灵,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谓为刍灵者善。谓为俑者不仁。不殆于用人乎哉。”[1]伟大的思想家孔夫子认为以明器治丧很合理。用活着的人的器具去陪葬是不道德的。死者并不会使用。孔子认为造刍灵的人愿望是善良的。他还认为,用人去殉葬根本上是大逆不道的,应当杜绝的。即使用陶俑这样象征性的“俑殉”也是不道德的。如果“俑葬”合理,那么,就不能保证奴隶制时代“人殉”的死灰复燃。这样,我们就破解了孔子所说的:“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这一名言。古文字中,用、甬、俑可通作,俑即用人为殉之意。据今人考证,孔子所在的春秋时代尚未出现陶俑。人殉又叫做作俑。所以,孔子这句话的本意是:“最初用人殉葬的人,是要断子绝孙的吧!”这说明,孔子反对惨无人道的人殉制度。其实,俑人的发明者是伟大的。俑人的出现首先避免了活人的殉葬,保护了大批健壮的宝贵生命。所以,我们应当承认,“刍灵”、“明器”、“俑人”的发明同样是伟大的历史性进步。我们可以想见,古代士人为保护生灵、保护财产、保护生产力、保护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而煞费苦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人们尽到了节葬、节财、全活生命的努力。这种努力不亚于蒸汽机的发明!
春秋战国时代的志士仁人们已经充分认识到:薄葬可以养廉,厚葬必将伤贫。《檀弓下》记述了一则贤士陈子亢反对人殉的戏剧性故事:“陈子车死於卫,其妻与其家大夫谋以殉葬。定而后陈子亢至,以告。子亢曰:以殉葬非礼也。虽然,则彼疾当养者孰若妻与宰。得已则吾欲已。不得已则吾欲以二子者之为之也。於是弗果用。”[1]这里,子亢扮演了一个圣贤的角色。面对殉葬定义,他指出这不合礼法。奉养因病垂危之人,谁也比不上他的妻子和家臣。言外之意,即他的妻子和家臣最适合殉葬。这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使主张殉葬的子车之妻和家臣在死亡威胁面前不得不放弃人殉的主张。这一史实,是春秋战国时代贤良的士人为争取保护人的生命权,保护社会精英,保存劳动生产力,保存可持续发展所做巨大的努力。其结果是进步战胜了陈腐,文明战胜了野蛮,正义战胜了邪恶,避免了生灵涂炭。
综上所述,《礼记》中富有资源和环保意识、工商管理的标准意识、防灾减灾意识、适时播种和采猎的时令意识、勤俭节约和节葬思想。所有这些观念都是为社会生产和生活得以可持续发展服务的,是古代社会活动经验的重要总结。
[1]陈澔·礼记集说[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P70~71,P19,P158,P83~100,P43,P51,P55.
[2]黄怀信等撰.逸周书汇校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615-617.
[3]孟珂·孟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