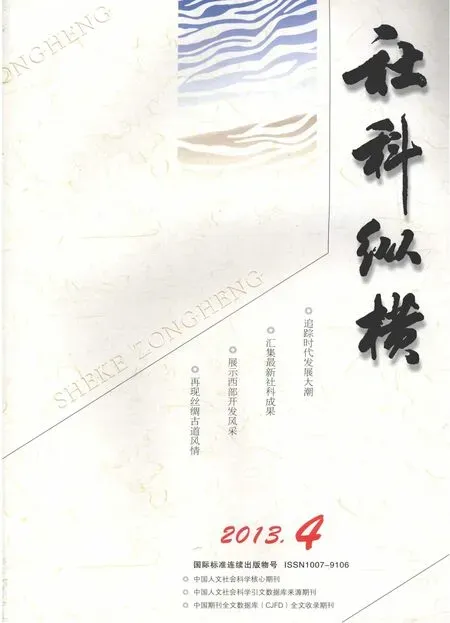“栩栩如生”的中国传统雕塑——试谈艺术考古学与中国传统雕塑研究的关系以及存在的问题
2013-04-10杨宇辉
杨宇辉
(西北民族大学美术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00)
日前,周晓陆先生在和西美研究生的讲座中谈到当前艺术考古学者在美学方面的知识匮乏时曾风趣地说到,学考古的学者们在描述古代艺术品时最爱使用的词是“栩栩如生”,似乎除此之外无以表达对艺术作品的具体感受,而这种似是而非的概念化理解居然一直作为对传统艺术的规范描述文本在社会上大行其道,周先生玩笑道:“我看吉祥村的小姐们就很‘栩栩如生’嘛”!众皆哗然。笑毕细想并联系我所学习的雕塑专业,不禁深有感触。本文的探索,只是进行局部的验证——它并不企望成为系统的论述。尤其因为,本文不打算过多探究有关文化的溯源及雕塑本体论等方面的问题,而仅仅想指出当代中国雕塑应当或可能具有的语言形式。换言之,本文将仅提供一些分析假设的雕塑“语言工具”。
中国传统雕塑的研究与艺术考古学的关系历来极其紧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二者几乎可以相互转化,这主要是由于艺术考古研究中所涉及的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所决定的。从分类来讲,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考古学研究中的人类精神文化创造物及其遗存,主要分为艺术遗迹和艺术遗物两大类。其中艺术遗迹主要分为壁画和雕塑,艺术遗物则主要分为绘画、雕塑、碑刻和工艺美术等。不难看出,除了其中的绘画部分以外,其他各种类型几乎都与雕塑有着紧密联系。从艺术遗迹中的建筑雕塑、宗教雕塑、陵墓雕塑到艺术遗物中的玉器(雕)、陶器(雕)、铜器(雕)、瓷器(雕)以及其他如漆、木、金银等各种材质的遗物,无不反映中国传统雕塑形态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而这岂是区区一个“栩栩如生”便可概括得了的。
但是,翻开中国古代雕塑史,长期以来在中国传统雕塑研究中使用的却多是类似于“栩栩如生”的模式化称述。例如:“青铜器艺术代表了商周雕塑的最高水平,渲染了威严神秘的气氛,形成了端庄、华丽、气质伟岸、形象乖张的艺术特性”;“秦始皇兵马俑其兵俑体态与真人相等,数量众多、形态各异、栩栩如生;其马俑形象写实、身材矫健、活灵活现”;“汉代雕塑在继承秦代恢弘庄重的基础上,更突出了雄浑刚健的艺术个性,霍去病墓石雕群在形式上突出了石雕作品的雄浑之势和整体之美”;“隋唐佛雕作品既显博大凝重之态,又不失典雅鲜活之美”……如此种种,不一而足,看似严谨缜密,实则空洞无物,对中国传统雕塑的形态特征和美学取向,仅停留在表面称述的层面,缺乏对其内在精神和形态机制方面的研究,而其方法论的核心部分更是未能摆脱过去唯意识形态的思想束缚,将社会学考察作为研究的主要方向。如此,既不利于对传统雕塑深化研究和理论总结,更不利于对传统雕塑的核心价值进行当代转化和继承。
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很复杂。首先是由于在中国美术史上雕塑一直未能摆脱实用性功能的束缚而成为独立的艺术形式,因而缺乏系统化的发展脉络。虽然出现了众多雕塑艺术形式,但其核心价值,即基于形而上追索的美学追求却从未真正独立出现。另一方面,中国传统雕塑的创作者主要是工匠,正所谓“形而下者谓之器”,中国传统雕塑不但未能像中国传统绘画那样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甚至主流知识分子对雕塑的记载文字也属凤毛麟角,如此才造成面对中国传统雕塑时考古学界与雕塑学界的普遍失语,因此可以说:精英文化的缺位直接导致了传统雕塑理论的缺失,而价值系统的重建则需要艺术考古学与中国传统雕塑研究重新定位,回归艺术的本源。
艺术是源自人的形而上冲动的关照人的终极境域的物化行为,其价值首先表现为确立人的精神归属。而其中形式的功能则表现为提供恰当的途径,也即语言符号的功能。言说方式对于言说内容而言,则仅表现为一种符号媒介。“符号思维和符号活动是人类生活中最富有代表性的特征,并且人类文化的全部发展都依赖这个条件”(恩斯特.卡西尔)而文化,是人的外化、对象化的结果,或说是符号活动的现实化和具体化。在人—符号—文化的三位一体结构中,符号无疑是人类文化活动的核心问题。正是“符号功能”建立起了人之为人的“主体性”,也正是因“符号现象”构成了“现象界”——文化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形而上的诸因素(哲学、宗教、艺术)通过符号活动实现着其超越现实的形而上品格。其中,艺术则负担着人对终极价值的追问和达至超越之境的绝对中介作用。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围绕着这种绝对中介作用的各个符号系统(艺术形式)不断完善,同时也使人的混沌地存在转化为明朗地形而上的价值存在。或许只有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对中国传统雕塑的美学研究与艺术考古学研究才有真正实现契合的可能性。
在对艺术考古学研究成果给予关注的基础上,也有必要关注这样一幅人文图景:一对对应的形式因素,矛盾对立的两极。它代表了天与地、刚与柔、动与静和所有对立的自然因素,在内部张力和外部压力的作用下由两极的对立状态向对方弯曲、运动,产生了对立事物的相互转化,而这个转化的联系形态则必然是圆形。在圆形空间中,对立的两极挪让呼应、联系扭合,而圆的外界面则曲润光滑,体现着对立两极的浑然一体以及自然造物相互依存和循环往复的人文价值规范——这就是代表古代中国人把握世界和理解人的存在境遇的终极图景:“太极”。
与太极所揭示的人文价值相对应,中国的传统雕塑正是通过对雕塑造型的全部内在矛盾,如动与静、实体与虚空的转化、协调中获得了形势和精神的平衡与自足。雕塑的“实物感”被强烈自足的“实体感”所取代。这种“实体”的物理形象特征被自足的形式所弱化,转而代之以强烈意向化的符号特征,雕塑的语言符号功能因此突破了以形、以象描摹事物的主客分离的审美距离,直接切入古代审美人群的“天人一体”的终极关怀。雕塑的实体存在与泛灵论的“道”的追求之间的矛盾被弱化并调和了。从某种意义而言,作为形而上的语言符号系统,中国的传统雕塑正因其对自然物象客观描摹的有意舍却,从而使其符号功能达至相对纯化的境界。这并非古代中国人缺乏摹写物象的能力,而是源自对物象之后的形而上追求及对雕塑这一符号化的言说方式的形而上要求。
在中国传统雕塑的动力学形态上,所有向外放射的、外拓的形体都被扭转、压制,形体内部的矛盾因素被主动强化,从而更加突出了力的内外对抗。同时在整体形态的内敛、收聚特征下,通过对矛盾因素提供不同的空间范围,也即造成可控的内部力环境,实现了雕塑中运动与静止之间矛盾的动态平衡。雕塑带给感官的物理实在被力的形式化运动所取代,故而使雕塑的整体形态呈现出完整、运动、充满矛盾但又平衡自足的审美特征,这也正是中国雕塑传统中最为本质的造型原理和形态机制。
面对传统艺术,我们不免一次次被其中超然、从容的终极体验所感动,这是人的本然状态,也是艺术的必然归属。传统,并不是我们继承得来的一种先决条件,因为我们理解着传统的进程并参与到传统的进程中。而在这个理解并参与传统进程的过程中,我们只有对艺术这一符号系统所承负的精神内涵予以充分而深入地关注,时刻关怀人的本然处境和终极境域,建构中国化的当代语言符号体系才将成为可能。
[1]孙长初.中国艺术考古学初探[M].文物出版社,2004.
[2]恩斯特.卡西尔[德].人论[M].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3]潘知常.中国美学精神[M].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