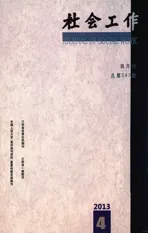从“残废”到“障碍”:称谓的演变对残疾人社会工作的影响
2013-04-10何乃柱李淑云
何乃柱李淑云
从“残废”到“障碍”:称谓的演变对残疾人社会工作的影响
何乃柱李淑云
一定程度上,对“残疾人”的称谓,从“残废”、“残疾”、“残障”再到“障碍”,其实都是“他称”,是污名化和贴标签的过程。有较强话语权的“他者”如政府、社团组织、公众等,对残疾人称谓的演变过程、称谓折射的价值观与认知、称谓的演变对残疾人社会工作的影响比较明显。文章建议将传统的“残疾人社会工作”的称谓改为“身心障碍者社会工作”。,这一称谓改变体现了价值理念更加人性化,进而影响到社会工作实务的开展。
残疾人社会工作价值观身心障碍者
一、价值观:社会工作服务方向的指南针
社会工作的核心是价值观,是社会工作信仰体系的重中之重。与解释“是什么”的“知识”不同,价值观和伦理涉及的是“应该是什么”(莫拉莱斯·谢弗,2009)。价值观在“残疾人”社会工作实务中扮演着指南针的角色。
社会工作者,作为服务的提供者、文化的他者,对服务使用者的称谓间接反映了其秉持的价值观和理念,也将决定其服务态度的持守。价值观协助社会工作者运用社会工作的知识和技巧设定与案主及社会有关的目标。从需求评估到设定服务目标,开展社会工作服务实践到帮助案主,价值观自始自终在影响着社会工作实务。例如服务对象是否应该参与日常菜谱的制定?服务对象的照片和姓名是否应该在活动室墙上公开?媒体来访是否要注意一些回避媒体的服务对象?服务对象晚上是否应该住在日间训练中心?失去行动能力的服务对象是否应该参与外出活动?
价值观也会影响到服务机构的运作方式。它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以下几个针对服务机构的问题:生活不能自理的服务对象接案不接案?服务对象生病了工作者是在机构内立马就医还是打电话给监护人来领回家治病?服务对象称谓工作者为老师还是社工?服务计划的制定是工作者自己讨论出来还是与家长一起商议并听取服务对象本身的意愿?家庭贫困的服务对象是否要缴纳服务费用?少数民族吃清真饭的服务对象要不要接收?社会工作服务机构主导或推崇的价值观对社会工作实务有直接的影响,同时服务机构管理层的价值观对服务的具体实操有重要的影响。
立法者、政策制定者、管理者所秉持的价值观和理念,也影响着社会工作者服务时所秉持的价值观,影响着服务使用者的生活品质,其不正确的价值观有可能会伤害到他们的尊严。社会工作的价值观和伦理并不是对情况好坏的情绪反映,而是协助工作者谨慎决策的基本标准。
因此,残疾人社会工作实务中必须注意社会工作者自身的价值观与专业的价值观伦理间的调适与价值澄清、社会工作机构的价值观和社会大众价值观的调适与价值澄清,社会工作行政层面的人员自身的价值观与专业的价值观和伦理间的调适与价值澄清。价值观扮演着功能性的角色如告诉工作者应该怎么做;同时作为终极价值反映了工作者理想的终极状态,如每个服务对象都应该远离歧视。
工作者要避免把自身不恰当的价值观带入实务中,最终承受选择后果的是案主本身,所以案主在选择时考虑的应该是自己的价值体系而非专业社工的价值体系。当然,价值观也会随时间和情境的变化而改变,这种改变可能是案主自身的改变,也可能是服务提供者价值观的改变。下面将介绍中国政府及公众对“残疾人”群体的称谓从“残废”到“障碍”的演变过程及其折射出的价值观的演变,并讨论其对身心障碍者社会服务工作的影响。
二、从“残废”到“障碍”称谓的演变折射出价值观的改变
(一)“残疾”是“鬼上身”?
起初,人们对于“残疾”大多是从神话或宗教术语的层面来理解,如认为“残疾人”是被魔鬼或幽灵附身;或者认为“残疾”是“上辈子造的孽”,被看做是对过去所犯错误的惩罚(世界卫生组织,2011)。这种观念至今仍存在。
案例1:Z是某西北某自闭症机构的创始人,同时也是自闭症孩子的家长。她深刻认识到家长之间互助和自助的重要性,于是成立了家长联谊会,定期开展活动。据她2012年8月份口述,起初许多家长对自闭症都不了解,觉得是不是鬼附上孩子的身了,还是其他的文化因素影响才会造成自闭症孩子的出现。于是有的家长替孩子改了名字,有的家长请来了道士帮家里看风水甚至是跳大神驱赶恶魔,有的家长听信一些风水先生意见以为给孩子吃了兔头孩子就好了,也有的家长挪祖坟希望能让孩子恢复正常,有的请来了中医也去了西医院但孩子还是没好,也有的家长听了先生的意见用蛇泡酒埋在院子里30天后给孩子喝,但是最后孩子还是没一点好转。
这种神学模型视角下的“残疾”观,目前在中国的民间社会尤其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尤为明显。2011年初,笔者在兰州市对85户心智障碍人士家庭进行了调查,当问及“残疾”的原因时,2.4%的人把“残疾”归因于“社会文化因素”。这种将“残疾”归因于宗教或巫术的价值观,影响着父母的看法和行动,也将会对社会工作者的实际工作造成一些阻挠和影响。这种观念是不可取的,会耽误孩子极为重要的特殊训练或教育。
(二)“残废”——以能否创造经济价值为准的歧视性称谓
“残废”一词在古文献中也有出现过。《魏书·显祖纪》:“永军残废之士,听还江南。”清·黄六鸿著的《福惠全书·刑名·贼盗》:“如伤人未中要害,不致折损残废,约略数日可愈者,不报伤人亦可”(相自成,2002)。可见,人们常说的“残废”一般指四肢或身体某部分丧失了功能,即“失能”。后果是失去劳动能力,无法创造经济价值,无法就业。起初中国政府也将“残废等级”界定为残废轻重和失去劳动能力的程度。
案例2:笔者所在的村子是一个客家人聚集的村落,村子里有几个“残疾人”。一个是“哑巴”(女,有语言障碍),一个“断了手”(男,肢体障碍),一个走路一拐一拐的还得了鱼鳞病(男,肢体障碍)。在笔者小时候的记忆起,这三个人就被村里的其他人骂为“残废”,有时故意取笑其不能劳动不能赚钱,也没人给这两个男的做媒介绍媳妇。至今,女的被卖到别村给人家做二婚,一个男的病逝了,剩下另一个男的至今孤身一人,在村中毫无社会地位。
人一旦“残废”,意味着被社会和家人所抛弃和歧视,会处于一种无助和消极的状态。“残废”的称谓折射的是人们以创造经济价值为本的观念,而非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在这种价值观主导下,这个群体的人生活在社区当中常被歧视、毫无尊严。
(三)“残疾”——医疗模型和优生学模型下的称谓
从19世纪到20世纪,随着科学和医学的进步,人们逐渐认识到“残疾”有生物和医学的原因,是身体的功能和结构的损害造成的。这种观点被称为“医学模型”视角,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康复”理论。医学模型认为“残疾”是一种病,通过用药和手术可以康复。但事实上,医学模型话语下的“康复”用在身心障碍人士身上几乎是一种讥讽,或许“复健”一词用在身心障碍人士身上更为适宜。当然,“病”、“患者”等词用在身心障碍人士身上也极为不妥。
随着医学和科技的进步,对于一些“残疾”的研究取得了突破。如1866年,英国医生约翰·朗顿·唐(John Langdon Down)首次描述了唐氏综合症的病理,1965年,世界卫生组织将此病,命名为唐氏综合症(又称为(21-三体综合征或“先天愚型”)。了解了唐氏综合症的症状后,人们又进一步提出了“唐氏筛查”的医检项目(张敏、王晓飞、佟冬梅,2004)。这被称为是优生学视角,即希望通过受控的选择性生育来改善人种、减少“残疾”。但事实上,并非只有身心障碍者才会有障碍。
医学模型和优生学模型视角下的“残疾”的称谓,虽然弱化了歧视,但称谓本身还具有浓厚的怜悯和施舍味道。而且“残疾”称谓和“残废”的称谓以及神学视角下的“鬼上身”的“残疾人”一样,被称为是“个体型残疾”,即认为“残疾人”所经受的问题是由于他们自身伤残的结果导致的。但事实上呢?思考以下案例:
案例3:杨先生是一名青年画家,生活在西北某市,主要从事山水画创作,年幼时因为掉进建筑工地桩洞而造成肢残。轮椅是他出行的唯一可以借助的辅具。办画展时他需要外出邀请嘉宾,打车时几次有空车的士都不停下来,好不容易停下来央求了好久司机才愿意让他坐车。走到一栋大楼前他又被五级阶梯难倒了,因为这栋楼没有供轮椅行驶的坡道。
从故事中,容易知晓医疗模式关注此人不能走路的事实而试图补偿其丧失的功能如安装假肢或提供轮椅,但缺乏坡道成为了障碍的症结。这样一来,社会工作者要提供的服务就是针对“残疾人”的个体本身如提供身体康复服务以及协助心理调适,目的是使“残疾人”适应“残疾”后的特殊变化。所以,当时医药的、心理疗法式的个体型社会工作在“残疾人”社会工作中占着重要的内容。
在这种个体型“残疾观”的影响下,社会工作者很容易就会先入为主地认为“残疾”是一种悲剧,并且将自己和“残疾人”区分开来,称谓自己为“正常人”,这种称谓是错误的,应该称谓自己为普通人更为合适,因为正常与“不正常”对应,一般指精神异常的人。所以社会工作者在口头上避免称谓自己为“正常人”,贴错“标签”。
(四)“残障”——“社会型残疾观”及养护理念下的称谓
“残障”一词表达的意思是残损在个体,障碍在环境,所以需要创造无障碍的环境来给“残疾人”创造福利,蕴含着“残障”仍然是家庭和社会的负担。“残障”称谓的出现,反映了1960和1970年代,人们对个体的、医学的“残疾观”表示不满,提出了“社会型残疾”的称谓(迈克尔·奥利弗,鲍勃·萨佩,2009)。
1981年国际“残疾人”年提出的第一个正式目标是:“帮助残疾人在身体上心理上进行调整,以适应社会的需要”,但是“真正的问题是:对残疾成员,社会愿意在其工作模式上、制定预期目标上做多大程度的调整?”社会型残疾观要求对全社会进行调整,但“并不是社会本身自愿的事”,所以出现了诸如身体损伤者反对隔离联合会(Union of Physically Imparied Segregation,UPIAS)(迈克尔·奥利弗,鲍勃·萨佩,2009)。
“社会型残疾观”质问社会工作者:是为“残疾人”工作,还是与“残疾人”一道努力?是为“残疾人”制定个人康复计划和寻找补偿,还是把重点转移到改变社会环境使之不能够、不恰当地限制功能受损者?“残疾观”由个体型转为社会型,不意味着个案工作的取消。
在此基础上,人们在质问:是谁“残疾”了?不是个体,而是社会。因为一些社会的障碍不仅仅限制了个体损伤的人,也限制了其他特定的群体。于是,障碍的称谓逐渐被人们所接受,因为有障碍人群体不仅仅是“残疾人”。由此“残疾”不再界定为个人的问题,而是社会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重点是促进社会障碍和社会的改变,而不仅仅是医疗(世界卫生组织,2011)。
(五)“障碍”:强调“人在情境中”的“受限”、“支持”和“参与”
“障碍”这个称谓近乎中性,有积极的意义,强调的是人和环境互动的障碍,这种障碍可能因为功能或其他的限制而产生,不仅仅限于“残疾人”这个群体,强调“参与”与“支持”这两个维度。《残疾人权利公约》认为“残疾”是一种演变中的称谓,“是伤残者和阻碍他们与其他人平等的基础上充分和切实地参与社会的各种态度和环境障碍相互作用所产生的结果”。《国际功能障碍和健康分类》(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Functioning,Disability and Health,简称ICF)认为的“残疾”包括损伤、活动受限和参与受限,是伴有健康问题和环境因素以及个人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这种环境可以理解为家庭、社区、社会常规、文化、政治因素、自然条件、支持系统等(美国智能及发展障碍协会,2010)。
2005年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在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普查时,就采用了ICF的标准和理念,取代了1980年代使用的ICIDH-1(国际残损、残疾和障碍分类),使得人们对“残疾”的理解从疾病或异常转变到损伤,再转变到功能缺陷,最后转变到障碍的着眼点。
不过,中国政府还一直使用“残疾人”的称谓,包括2006年把“Convention of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翻译成《残疾人权利公约》。创办于1988年的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一直在使用“残疾人”这个称谓。《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对“残疾人”的界定为:“残疾人是指在心理、生理、人体结构上,某种组织、功能丧失或者不正常,全部或者部分丧失以正常方式从事某种活动能力的人。”
在台湾,“残疾”的称谓早被摒弃,并被“身心障碍者”的称谓所代替。台湾《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对“身心障碍者”的界定是:“各款身体系统构造或功能,有损伤或不全导致显著偏离或丧失,影响其活动与参与社会生活,经医事、社会工作、特殊教育与职业辅导评量等相关专业人员组成之专业团队鉴定及评估,领有身心障碍证明者。”台湾身心障碍者的称谓类比于中国大陆的“残疾人”的称谓。可以发现,身心障碍者的称谓更能体现《国际功能障碍和健康分类》(ICF)的“限制”、“障碍”以及“参与”、“支持”的理念。笔者呼吁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应该尽早使用“身心障碍者”的称谓来代替“残疾人”。
由此,笔者建议将传统的“残疾人社会工作”的叫法改为“身心障碍者社会工作”。因为称谓的改变反映出价值观理念的改变。
三、称谓的演变对身心障碍者社会工作的影响
称谓的演变其实质反映的是价值观的改变,即社会工作者及公众对身心障碍者接纳度更好,更加人性化。从“残废”到“障碍”,对“残疾人”称谓的演变会从价值观与理念、知识结构、技能与方法三个层面对身心障碍者社会工作产生深刻的影响。
(一)注意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服务理念和工作目标
1.树立“正常化”(Normalization)的理念。正常化的理念始于19世纪40年代的瑞典,通过6年的倡导,瑞典政府将“正常化原则”制定为一个社会政治性的原则,让身心障碍者也可以平等使用非障碍者的服务,可以在同一个社区中过着“正常生活”(李崇信、周月清,2008)。但反观中国的身心障碍者服务体系,政府办的服务机构基本都是整栋或整层楼,所有的身心障碍者都要求进入接受服务,吃喝拉撒睡玩医全部在里面,这无形之中将他们隔离起来,失去了参与社会生活的机会,这严重违背了“正常化”的理念。
2.培育和实践社区化的服务理念而非隔离式、封闭式的服务模式。所谓社区化主要包括两个重要要素:一是强调身心障碍者生活或居住在真实的、与普通人一样的社区里,享受与普通人一样可以享受的社区资源,而非将其隔离;二是对身心障碍者开展训练时,不应该过多使用模拟场景来训练,应在真实的社区环境中教会其融入(inclusion)社会的技能。如案例所述:
案例4:老邱是西北某市一名智障人士,因为家境贫寒和无提供专门服务的机构,他一直呆在家里,直到H智障人士服务中心的成立。在H机构,社工XM为了锻炼了智障人士的社会适应能力经常带着老邱和其他智障人士到超市直接学习购物,到网吧学习如何上网,到社区体育场锻炼身体,到电影院去看电影,甚至到北京去旅游,大大提升了智障人士的生活品质和自主生活能力。
3.培养去机构化的理念,从“机构康复”向“社区康复”转变。机构康复因为存在以下几个弊病而逐渐被社区康复取代:(1)只面向少数人提供服务;(2)服务费用和成本昂贵;(3)只教会服务使用者在机构应该怎么做,没有教他们回家后或者走向社会后如何融入社会、正常生活;(4)令服务使用者对专业人士和社工产生依赖;(5)使身心障碍者脱离了家庭和社区。因此,社区康复在19世纪70年代被世界卫生组织认可并在约90个国家和地区推行。去机构的意义在于不再使“回归主流”的身心障碍者再次进入机构被隔离;协助正在机构的身心障碍者回归社区,使其在社区中融入社会;改善住宿机构的硬件和软件环境,真正践行正常化的理念。
4.从“使能”再到“支持”。传统的医疗模式下的身心障碍者的服务以医疗康复为主,但逐渐地人们明白了身心障碍者的医疗康复可能性为零,进而社会性康复得到了普遍的认同。这需要社会工作者也转变理念,从“使能”转变到“支持”的维度上来。如案例所述:
案例5:S是某智障成人服务机构的社工,2010年她开始接触智障人士服务时感到非常头疼。家长经常要求她多训练自己的孩子数学方面的技能,提供记忆能力和数字使用能力。她也很用心地开展训练,如教智障人士数数、学会找钱、学会看钟点等,但坚持了一年成效很差。某次,一位香港社工的话点醒了她。这个香港社工说:智障人士在某些方面如记忆和数字称谓方面本身就差,我们要做的不是提高或改善他们这方面的能力,因为几十年的经验证明这些缺陷是很难通过训练得以提升了,而应该提供“支持”帮助他们消除“障碍”,如教智障人士使用计算器来代替自己算数,使用刷卡技术代替找钱等。这让社工S大为震惊,原来自己服务的理念和方向错了。
对身心障碍者称谓的演变,其实要求的是工作者服务价值观以及期望和工作目标等都需要做相应的调整。除了以上陈述的四点外,社会工作者还应该避免让自己陷入“专家指导”的角色,多给服务使用者机会度和支持度,让服务对象有机会“参与”和“自我决策”(Self-determination);多从优势视角挖掘服务对象的潜能,进而可以减少其行为问题的发生;培育和时间去差异性(Dedifferentiation)和尊重个别差异的原则等等,最终提高身心障碍者的生活品质(Quality of Life)(Robert L.schalock等,2010)。
(二)通才抑或专才——服务身心障碍者对知识结构的要求
在美国,1970年以前,身心障碍人士和他们的家庭所获得的帮助主要是通过保健服务或其他民间组织取得。而1970年的西鲍姆报告(Seebohm Report)改变了一切。西鲍姆报告促使了社会福利改革和身心障碍者法案的出台,使得身心障碍者专业社会工作形成并逐步开展探索(迈克尔·奥利弗,鲍勃·萨佩著,2009)。当社工遇到身心障碍者时,我们不得不思考社会工作者培养是通才教育好还是专才教育(指专科训练)好的问题。
笔者从多年的身心障碍者社会工作实务看,要做好身心障碍者的服务并不是紧靠医药社会工作者、康复训练师、物理治疗师、精神病专家可以支撑起一切的。身心障碍者社会工作除了需要掌握社会工作的价值观、基本知识和方法外,还需要了解智障、自闭症、脑瘫等的界定和基本常识,需要了解相关的福利政策和法律法规等等。从技能和方法上看,社工还需要学习掌握一些评估的工具如ISP(Individualization Service Plan)、SIS(Supports Intensity Scale)、PCP(Personal Central Plan)、ABA应用行为分析法、大运动疗法、农疗、智障人士职前训练评估工具等等。从角色上看,社会工作者需要扮演专家、资源链接者、社会行动者、专业服务提供者、宣传员等角色。此外,身心障碍者社会工作已经从需要不同专业一起共事发展到多元专业共融的阶段。何况,当前从事身心障碍领域服务的社会工作者大多数是本科毕业生,而中国大陆当前的社会工作教育处于发展初期,尚未达到分门别类甚至较为专一的阶段。由此,笔者认为身心障碍者社会工作需要的通才教育下的社工方可胜任。
四、结语
有一句著名身心障碍者工作的口号是:“没有我们的参与,不能作出与我们有关的决定”(Nothing about us without us)。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对身心障碍者的称谓,从“残废”到“障碍”,其实都是“他称”,都是污名化和贴标签的过程,这一过程中占有较强话语权的“我们”,依据刻板印象将人性低劣强加在身心障碍者的身上。“残废”、“废物”、“傻子”、“哑巴”、“瞎子”、“聋子”、“瘸子”、“残疾”、“弱势群体”等称谓不应该出现在他们的头上,“可怜”、“悲催”、“累赘”、“没用”、“需帮助”、“需照顾”、“需养护”、“不正常”等标签也不应该贴在他们的身上和出现在我们的嘴上。
对身心障碍者的称谓,影响着身心障碍者社会工作的价值理念与实务。本文也赞同将传统的“残疾人社会工作”的称谓改为“身心障碍者社会工作”;建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改为“中国身心障碍者联合会”;建议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改为“中国身心障碍者保障法”,建议将“Convention of the Rights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在中文语境之前翻译的《残疾人权利公约》改成《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
因为这一称谓改变体现出的价值理念更加人性化、正常化,进而影响到社会工作实务的开展。为身心障碍者“正名”的过程,就是社会工作者在价值观、专业伦理上自我反思和成长的过程。当有一天公交车上“老弱孕残座”的字眼消失时,当有一天甘肃省博物馆的门票不再明文写着“智障人士不准入内”的文字时,社会才是真正的和谐与健康。
[1]李崇信,周月清,2008,《社区居住与生活的理念与实践》,财团法人台湾启智技艺训练中心。
[2]世界卫生组织编,香港复康会世界卫生组织复康协作中心等译[Z]。社区康复指南—以社区为基础的康复, 2011。
[3]相自成,2002,《赈谷(中)—中国历代有关残疾人保护的政治法律制度》,《中国残疾人》第10期。
[4]张敏,王晓飞,佟冬梅2004,《唐氏综合征》,《国外医学·护理学分册》第8期。
[5]美国智能及发展障碍协会著,2010,《智障障碍:定义、分类和支持系统(美国智能及发展障碍协会定义指南第十一版)》,台湾心路社会福利基金会译,台湾:财团法人心路社会福利基金会出版。
[6]迈克尔·奥利弗,鲍勃·萨佩著,2009,《残疾人社会工作》,高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7]莫拉莱斯,谢弗主编,2009,《社会工作:一体多面的专业》,顾东辉王承思高建秀等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8]ROBERT L.SCHALOCK等著,2010,《智障障碍与其他发展障碍的生活品质—从个人、组织、社区到制度上的应用》,彭心仪译,台湾:财团法人心路社会福利基金会出版。
编辑/汪鸿波
C916
A
1672-4828(2013)04-0049-06
10.3969/j.issn.1672-4828.2013.04.006
何乃柱,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兰州慧灵智障人士服务协会中心理事长;李淑云,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社会工作硕士研究生(甘肃兰州730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