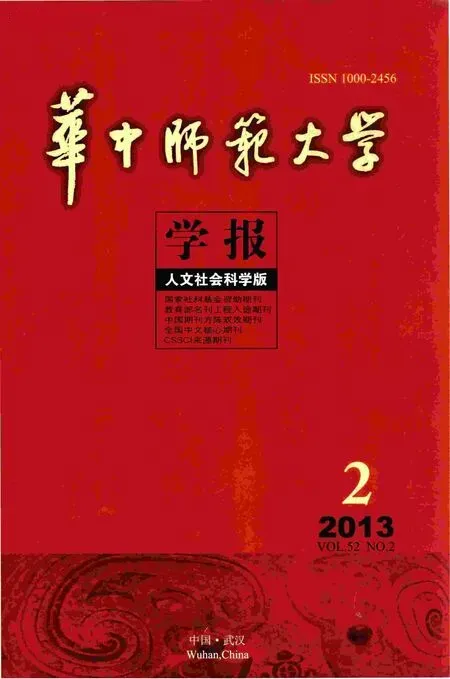中国电影史链条上的主旋律电影及其未来走向
2013-04-09彭涛
彭 涛
(华中师范大学 信息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北 武汉430079)
主旋律电影研究已经涉及了文化研究、意识形态研究、类型研究等诸多方面,但对主旋律电影的史学意义还鲜有论者关注。主旋律电影概念提出及其创作实践迄今20余年,考察其史学意义已当其时。本文认为,包含在本论题下的讨论应该涉及两个向度:其一,它所来何自?即它的发生、地位和电影史学意义;其二,它之向何方?即它未来可能的走向。关于第一个向度,本文将考察主旋律电影的发生及其“家族相似性”,探讨主旋律电影与中国电影史上其他时段发生的一些电影形态之间的关系,如左翼电影、十七年电影和文革电影等,在第二个向度,将立足主旋律电影的创作历史和现状,进行合乎逻辑的推测或预判。
一、主旋律电影的发生及主旋律电影“家族”
从发生学角度看,考辨一个概念为什么发生比考辨它何时发生更为重要,或者说考辨概念位于知识谱系中的坐标位置关系比找到坐标点更重要。1987年初,电影界意识形态主管者首次提出“突出主旋律,坚持多样化”的口号,“主旋律”、“主旋律电影”等概念自此在文艺界流行。倡导者在提出这一口号时,声称针对的是80年代后期娱乐片初潮中出现的“媚俗、庸俗、粗制滥造之作泛滥于市,‘裸、露、脱’频频闪现于银幕”的现象。但笔者认为,其初衷并非如声称的那么单一。真实原因恐怕更在于电影传统的意识形态功能弱化,以及受到了潜在挑战。
电影历来被中国共产党视作具有强大宣传功能的文艺样式。自30年代左翼时期成立党的电影小组开始,中国共产党始终强调对电影的影响和领导。其方式,有时是置于宏观的文艺政策之下,如正面提出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双百方针”等口号,有时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方针和政策。如,1949年底,电影局制定了“争取进步片优势,保证工农兵电影主导”的方针①。有时是通过“运动”的方式进行的。如建国后多次文艺运动都始于电影界,之后扩大、影响到整个文艺领域。对影片《武训传》的批判如是,对《早春二月》、《北国江南》等影片的批判也如是。前者更由党的最高领导者亲自发动并上升到政治高度。通过这些运动,中国共产党确立了电影、文学及整个文艺与政治的从属关系。而那些刚从旧时代走过来的电影艺术家们,也通过这些运动,逐渐对新时代的文艺生态萌生了感性认知,逐步调整创作理念和心态,寻找新的创作方法去适应新的时代。
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学艺术活动的方式中,对提出什么口号一向十分慎重。口号既是政治风云际会的风向标,又对具体文学艺术活动产生极大的方向性影响。1979年10月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中国共产党重申“双百方针”,1980年又用“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取代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1980年代新的文艺政策因此被表述为“双百方针”和“二为方向”。前者是统领的方针,后者是方向的指引。它们对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的发动和进行都产生过重大影响。既有方针统领,兼有方向指引,可是电影界为什么还要提出一个“主旋律”口号呢?这实在是很不寻常的事情。其背后复杂、深层的动因,恐怕不仅与电影创作实践有关,更与当时的思想文化背景相关。
1980年代是一个因选择太多而缺少沉静思考的年代。当时一个重要现象就是各种思潮涌入,思想文化领域进入“多声部”时期,价值、理念日趋多元。显然,这些绝大部分来自西方的思潮和价值是异质性的,它们导入,“即使当时走在思想解放运动最前列的人,仍没有产生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或者说还缺乏自明性”②。但是,这些未经选择而涌入的思潮,不但受到思想界、学术界的追捧,尤其在青年大学生中拥有广大市场。而与此相伴的是,传统价值尤其是主流意识形态不断受到质疑和挑战,主流意识形态的领地日渐收缩。对来自以异质价值为参照的质疑和挑战,主流意识形态保持着足够的警觉。这表现为1980年代思想文化界多次收与放的反复,以至有所谓“单年自由化、双年反自由化”的说法。1986年底的学潮和随后主要领导人的因此去职,标志着新一轮“反自由化”运动的开始。在这一背景下提出“突出主旋律,坚持多样化”,其用意首先在于服务于新一轮“反自由化”运动。基于这样的认识,笔者以为,“主旋律”口号提出的初衷,是基于对异质性价值的疑虑或者排斥,是主流意识形态对其领地日渐收缩的一种“应激反应”③。
与“主旋律”口号提出初衷相联系的另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这一口号在电影界首提?
诚然,相较于其他艺术样式,电影更被主流意识形态所重视,尤其在电视还不太普及的年代,电影承载了主流意识形态更多的宣传功能。在电影领域具有更强的“阵地意识”是可以理解的。但笔者以为,另一个重要因素,恐怕与这一口号当时还没有凝聚成整个意识形态领导层的共识有关。这不仅后来才为我们知晓的、当时最高领导层对思想文化界认识、评价的差异或分歧所证,也被这一口号提出时的“级别”所证。过去,中国共产党重要的文艺政策和方针一般由级别非常高的,甚至最高领导人提出,而“主旋律”口号由当时电影局领导在行业内部的创作会议上提出,显然只能用部门共识或行业共识来解释。至于此后,“主旋律”口号不断“升格”,成为中国共产党重要的文艺指导政策,则是1989年之后,尤其是90年代的事情了。
当然,主旋律概念的提出,与电影创作实践也有关联。尽管在整个1980年代繁复的电影生态中,着重承载了主流意识形态功能的电影创作如革命历史题材、现实改革题材的电影创作连绵不绝,有些甚至影响甚大,如《从奴隶到将军》、《西安事变》、《风雨下钟山》、《孙中山》、《花园街五号》等影片,但那个时代最辉煌的还是第五代电影。尽管从深层讲,第五代电影并未背离主流意识形态的总体要求,他们更多的是对于形式和技巧的极度迷恋,而对秩序、整体性等传统价值仍持认同立场。但即使如此,其“异教”的嫌疑始终未除。而1980年代后期出现的娱乐片潮流中,“媚俗、庸俗、粗制滥造之作泛滥”,“裸、露、脱”等表面问题确实存在,并且许多影片对江湖义气、行侠仗义等民间价值不加区别地认同,也与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认知不一。基于这些因素,“主旋律”概念的提出,“主旋律电影”的发生,就是一种逻辑的必然了。
不过,虽然作为一种有名号的主旋律电影是1987年提出的,但它却不是孤立、凭空冒出来的新玩意儿。其实,只要稍稍考察下中国电影史就不难发现,早在主旋律电影发生之前,类似的电影实践就在长期进行。它们形成的电影形态与样式,与主旋律电影具有维特根斯坦所说的“家族相似性”。笔者称它们为“类主旋律电影”,它们包括左翼电影、十七年电影和文革电影以及新时期电影中的革命历史题材、现实改革题材电影和典型人物为原型的电影。因此,讨论主旋律电影在中国电影史链条上的位置,必须同电影史上这些电影实践相比较。
二、主旋律电影与左翼电影
1930年代的左翼电影,是我们可以追溯到的主旋律电影最远端的历史渊源,二者的逻辑联系,我们起码可以从四方面来指认。
其一,主旋律电影在其意识形态内核上,与左翼电影有很大的承继性。主旋律电影最核心的价值范畴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左翼电影都在当时历史情景许可的限度内,对三者进行过大量书写。30年代,中国面临的最主要危险是日本帝国主义入侵,民族矛盾是最主要的焦点。因此,这时候的左翼电影“也含有对国民党统治社会的不满,但是反对外来侵略的爱国主义精神,几乎成了贯穿它们各种题材、样式影片的共同要求”④。当时许多有影响的影片《大路》、《狼山喋血记》、《塞上风云》、《上海之战》等,都是那一时期爱国主义的力作。而且,它们在市场上的表现,也超过了单纯的表现对黑暗现实不满的影片⑤。左翼电影贯穿的爱国主义精神走向,一直绵延到今天的主旋律电影创作中,并以民族主义的基本形象呈现。而集体主义的价值内核,在左翼电影时期是包含在团结起来抵抗外侮的逻辑叙述中的,到主旋律电影时期,则将其外延几乎扩展到了各个层面。社会主义价值,虽然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很难公开书写,但它内在地包含在对旧制度的批判和对未来中国的想象之中了。
其二,在创作方法上,主旋律电影与左翼电影一脉相承。有论者早指出,“在创作方法问题上,左翼创作群确立并坚持了新的现实主义的艺术原则”⑥,这种新的艺术原则,当时的特征是“以新民主主义的社会思想、文化思想及电影思想为共同基础,以彻底地、毫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为共同旗帜,以暴露的、批判的社会现实主义为基本倾向”⑦。在1949年以后,这种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被革命现实主义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所取代,并用来区别表现新旧两个社会,即用传统的批判现实主义手法表现旧中国,以肯定或赞歌式的手法表现新中国。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在新中国经历了许多曲折和迂回,在新时期,许多人呼唤现实主义回归——事实上——也在很大程度上回归了。但在主旋律电影创作领域,更多地沿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判断,恐怕更接近创作实际。
其三,在电影生产的文化领导权上,主旋律电影与左翼电影一脉相因。在今天,中国共产党及其主导的主流意识形态占据着主旋律电影的绝对文化领导权,这已是无需论证的事实。而左翼电影时期则不同。那时,一方面,国民党政府企图以集权方式控制文化主导权,并且官办了一些电影制片企业,如中央电影制片厂等,但当时中国电影的主要生产基地——上海复杂的政治文化生态,又使这一控制企图往往落空。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影响下成立的左翼作家联盟(1930年3月2日),及之后成立的左翼剧联(1931年1月)和左翼剧联领导下的“电影小组”(1932年初)对电影给予了极大关注。夏衍、阳翰笙、田汉等一批左翼人士的加盟到电影创作队伍中,改变了电影创作队伍的构成,使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意识”渗透到了电影作品中。正因此,才有所谓“党领导了左翼电影运动”⑧之说。此外,在实现文化领导权的方式上,二者也十分相似——即都十分注重影评工作,强调影评的舆论导向功能。
其四,主旋律电影和左翼电影虽处不同的历史时期,但都面临着相同的政治、商业(市场)和审美之间的复杂纠结。在电影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上,左翼电影强调“作品的形式与内容,始终是内容占着优位性的”⑨,因此左翼电影往往存在着忽视作品形式的倾向,有些作品制作粗糙,形式苍白,内容空洞,但许多左翼电影的优秀制作,做到了内容与形式的和谐统一。那时期的一些名作,至今仍是中国电影史上熠熠夺目的经典。而主旋律电影由于强调电影的教化功能和社会效果,也同样遭遇了类似境遇。在1990年代,主旋律电影既要面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电影作为文化工业,必须考虑盈利能力的“市场焦虑”,又要面对在审美趣味多元,娱乐和艺术样式多样条件下观众流失的“接受焦虑”。因此,如何在政治、商业与审美之间,保持一种适度张力,是两种形态电影共同的历史境遇,左翼电影的某些优秀之作,对今天的主旋律电影仍有启发意义。
正因为上述这些原因,李少白先生认为左翼电影(他将其置于整个三四十年代的“进步电影”的“共名”下)“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电影发展,具有很深的影响,直到今天也还没完全失去它的影响,不管人们怎样看待这些作用,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是有利于电影发展,还是不利于电影发展;或者在一定条件下起过积极作用,到后来又走向了自己的反面”⑩。笔者很认同这种看法。但是我们同时也要看到,主旋律电影和左翼电影有着明显的路径差异。首先,左翼电影以底层苦难为铭写基调,强调阶级压迫和差异,呼唤人民的觉醒,鼓励以斗争的方式推翻旧世界,建立新秩序。尽管左翼电影的创作内源性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电影小组的领导,但其表现是以“人民性”的方式呈现的。《渔光曲》、《马路天使》、《十字街头》、《桃李劫》等影片,放在今天,依然闪耀着动容的艺术和人性光辉。它们是中国电影史上的不朽诗篇。其次,左翼电影的不少优秀之作,在反抗民族压迫、阶级压迫的主题下,同时还包含了个性解放的因子,如《新女性》、《桃李劫》等影片,它们是五四文化传统的血脉流转。而主旋律电影在民族独立、阶级解放的主题下,往往遮蔽或消弭了这一主题。今天的主旋律影片,如何在关注中国人民历史苦难的同时,更多地关注“现实问题”,在宏大叙事话语中,如何给“个人”留有一席之地,仍是需要探索的问题。
三、主旋律电影与十七年电影和文革电影
主旋律电影与十七年电影和文革电影的关系,是探析主旋律电影在中国电影史链条上位置的另一个重要节点。
第一,从价值范畴看,十七年电影对社会主义价值观从潜在提倡上升为显性要求,并以一种“霸权”话语的方式,支配和规范着其他叙事话语。集体主义价值观则被逻辑包含于社会主义价值观念之下。而爱国主义价值观,更多体现在“热爱新中国”的表述之下。满足这些价值尺度的途径,一是在生产方式上,除了创立中国共产党自己的电影事业外,还将所有私营电影企业国有化,二是通过大张旗鼓和接连不断的文艺批判运动,不断规范和“净化”电影作品的“意识”,以实现党和国家的意志。而在主旋律电影时期,那种类似批判《武训传》的文艺批判运动没有重演。尽管地下电影、独立电影被认为有挑战主流意识形态的嫌疑,但执政党领导文化的方式已经大为温和,一般只是动用行政处罚的手段,或者掐断其通向大众市场的路径。
第二,十七年电影经过曲折探索后建构起的基本叙事模式,为主旋律电影提供了前导性经验。当左翼影人千呼万唤的时代降临之后,电影人以极大的激情拥抱新的时代。“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电影艺术家,不管他们在组织上是不是共产党员,他们都首先把自己看作是一个革命者,可以这样说,在古今中外的文艺史上,没有任何艺术家群体,能像本时期中国艺术家那样,如此忠贞不渝地贯彻执行党与政府制定的文艺政策”⑪。但历史的悖论之处颇像恋爱和婚姻,恋爱时节,顾盼生情,待到朝夕相处之时,才发现彼此有诸多不适应。《武训传》、《关连长》、《我们夫妇之间》等作品的际遇,都说明他们还没有找到适应新时代的言说方式。于是,在学习、强制改造和自我批判中,电影人经历了一个痛苦的涅槃过程。在1959年前后,他们终于寻找到一种符合新政治语境的言说机制。大批红色经典之作,如《青春之歌》、《红色娘子军》、《洪湖赤卫队》、《女篮五号》……都诞生在这年前后。这些作品,在新的意识形态与叙事方式之间寻找到了合适的契合点,正如有的学者概括的:“十七年的电影表述中,历史话语是最主要的话语。也就是说,任何关于党的现实和政治权威的陈述,都在电影中演化为历史叙事的肌理”⑫。今天的时代与十七年相比,尽管政治文化生态已经发生极大改变,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已成过去,文化上大众文化、流行文化乃至后现代文化盛行,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崛起正在进一步改变现实的政治、文化生态,但是,中国共产党仍牢牢掌握着文化的领导权,尤其在主旋律电影(包括主旋律叙事)场域,“党的现实和政治权威的陈述”,仍是影片叙事的内在逻辑支撑,它们规范了影片的题材选择、主题表达以至叙事的民族形式。
第三,十七年电影确立的基本电影美学形态和主要审美范畴,仍为主旋律电影所继承。有人在论述十七年电影时认为,“长期以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两结合’既是作为能体现中国式社会主义特点的创作方法出现的,同时也自然而然地构成了中国文艺、中国电影的基本美学形态”⑬。因此,中国电影美学形态是国家意志的影像呈现。在今天,尽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口号不提了,但无论从创作方法还是美学形态上,主旋律电影实际上仍然在继承这一传统。同时,在今天大众文化的滚滚浪潮中,在“娱乐至死”的理念支配下,“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传统,也在主旋律电影中变相复活。十七年电影确立的主要审美范畴,如偏重正剧,推崇崇高,弘扬英雄主义和阳刚之美,注重塑造“典型”等传统,也仍为今天的主旋律电影所继承。不过,在新的时代思潮和文化语境中,其书写方式已发生了很大改变,如英雄书写的更新,阳刚美中对阴柔美的兼容,革命话语中嵌入进欲望叙事等等。主旋律电影在坚守传统价值和审美范式的同时,具有了更大的开放性、兼容性。
文革电影政治上恶劣的名声,数量上的极端匮乏,是迄今对其研究少之又少的原因。从逻辑上讲,文革电影是左翼电影、十七年电影中革命逻辑被极端荒谬化的结果。文革电影虽然宣告了极端意识形态化的破产,但我们不能忽视的是,部分文革电影形式上的精致。像许多宫廷艺术一样,最谄媚的歌功颂德,包装着最精致、奢华的外饰。文革样板戏电影的文词、唱腔、演员的表演,招招试试,莫不凝聚着刻意的匠心。这也使它们至今仍可作为一种大众娱乐样式,在事实上抽离了意识形态内容后,不断以“碎片化”的方式复活在各种大众文艺的舞台。主旋律电影在意识形态上对文革电影的背离是极其正当的,但笔者以为,部分文革电影形式的精致,又恰恰是某些主旋律电影应该借鉴的。
四、主旋律电影与新时期电影
新时期电影(本文所指“新时期”从1976年10月算起)是在多元格局中起落消涨的。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的一批揭露文革和极左思潮的影片,沿用的逻辑仍然是文革化的。最终,这条道路被实践证明是一条死路。第五代导演从电影语言的探索开始(部分第四代导演如张暖忻、吴贻弓、杨延晋等也是力行者),到用影像探寻民族文化之根,直至成就了他们辉煌的国际声誉。但这种声誉也不免尴尬。一方面,市场、观众对这种陌生的小众化的电影是拒斥的,另一方面,第五代导演告别革命的姿态,或对革命个人化言说的方式,都有逸出主流意识形态规范的可能。与此同时,类主旋律影片的创作在1980年代仍是一个显著存在。但这类影片创作面临着如何处理主流意识形态的现实与历史事实上“断裂”的问题。于是,创作中就呈现出两种倾向,一部分如《小花》、《今夜星光灿烂》、《从奴隶到将军》、《佩剑将军》、《风雨下钟山》等影片,较多地继承了十七年电影传统。另一部分影片,如谢晋的《天云山传奇》、《牧马人》、《人到中年》、《芙蓉镇》等,在书写伤痕,反思历史时,试图寻找一种新的叙事策略,缝合历史与现实的断裂。这类影片是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成果。但是,如果沿着反思的路径深化的话,最终难免与主流意识形态产生严重抵牾。因此,在1990年代的主旋律电影书写中,这类影片渐次退出就在情理之中。
198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电影生态的构成大致由三方面构成:艺术电影(包括那些无法公映的所谓“地下电影”)、商业电影和主旋律电影。在这三方构成中,艺术电影的式微已无须论证。以市场为导向的商业电影,也因中国电影与市场运作几十年的隔膜而举步维艰,左支右绌。而主旋律电影,则因其独特的工具性而受到体制特别关注,被各种政策扶持,并占据了各主流媒体和杂志的显赫版面。正如有的学者指出,“中国电影的多元性被主流政治意识形态所主导,主旋律不仅作为一种口号,而且作为一种逻辑支配着中国电影的基本形象”⑭。也就是说,在艺术、商业和主旋律构成的当代中国电影生态中,主旋律电影是作为中国电影的一种“基本形象”示人的,艺术电影的个人化、创新性表现方式,商业电影的大众叙事逻辑和市场导向,其幕后都支撑着主旋律电影的逻辑。比如欲望书写,曾长期是中国电影书写的禁区,甚至在1980年代的某些艺术电影和商业电影打破这种禁忌之后,类主旋律电影和主旋律电影前期的书写,仍不敢在“欲望”上稍有流连。到1990年代,随着大众文化的流行,在新的社会价值坐标系里,欲望的合理性得到充分肯定,欲望书写开始以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方式进入主旋律电影中。具体来讲,它是以一种欲望与禁忌纠结的方式呈现的。一方面,主旋律电影中开始悄悄释放隐秘的欲望,“革命”不仅自我指涉,而且也成为欲望投射的对象。“革命”图景中羼杂进“可看”的成分;另一方面,但凡涉及革命的宏大领域,欲望的投射都有极其明显的限度,有着不可逾越的禁忌。这种特点在影片《黄河绝恋》、《红樱桃》、《红河谷》、《红色恋人》中表现最为充分。在近期电视剧如《潜伏》中,也有精彩呈现。
总之,笔者认为,1980年代末提出的主旋律电影,它由1949年之前中国现代电影多元格局中的一脉——左翼电影发端,发展到十七年和文革中的一元,再到80年代的多元共生,及至90年代被大力倡导,再到最近几年开始被当作一种文化产业,当作文化软实力的载体,其间发展的路径也许曲折迂回,但它和电影史链条上其他时期的电影一样,其作为主流意识形态重要载体的功能始终未变。
五、走向一种共同文化
主旋律电影实践二十余年来,自身也在不断变化、调适,“与时俱进”。它在坚守自身的价值范畴同时,也兼容、挪用了一些其他非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范畴,主旋律的内涵在扩展、丰富,疆界在拓宽,其“面目”变得越来越模糊,越来越难以指认。那么,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主旋律电影将向何处去?
“主旋律电影”是在特定政治文化语境下提出的一个概念。文学艺术史、学术史乃至政治史上,任何一个概念、术语或口号,其所以发生或被命名,自有其内在逻辑,也自有其理论阐释的有效性,或对实践路径的指向性。无论来自西方的“现代性”、“后现代”、“公共领域”等概念,还是中国近现代文学文艺思潮中的“诗界革命”,“文学革命”、“革命文学”、“国防文学”,“左翼电影”、“文艺为大众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双百方针”的概念或口号,都具有这样的特性。但同时,没有任何一个概念、术语或口号一劳永逸,凝固不变。随着社会政治形势的变化,文学艺术思潮的变迁,学术范式的更新,它们都只会在各自领域的某一历史时段中占据某一位置。从这种意义上讲,主旋律电影也将是一个历史概念,是历史过程中一个时期的文艺现象,并且也将终结于未来历史的某一个时点。对此,我们不必讳言或忌谈。但同时,作为主导文化或主流文化现象,主旋律电影所代表的也是一个永恒的文化现象。它不仅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存在和发生过,也将在未来同样存在和发生。因为,任何时代或社会,无论是自觉生成还是提倡的结果,都客观存在和需要一种主导文化,作为一种“团结的文化”(伊格尔顿语)或社会整体性的象征。也正是基于这样的信念,笔者认为,主旋律电影仍将是长期存在的一种电影或文化现象,不管将来它是否拥有现名。
从这种意义上看,主旋律电影与主流意识形态或现实政治的密切联系,或者说文化与政治与权力结盟,不仅在政治上有其无可厚非的合法性,而且也有逻辑上的合理性。但我们同时也应更清醒地认识,要完满实现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不是要将文化政治化,而是将政治文化化,即要强调“文化对于政治的优先权”⑮,把政治或意识形态的“合目的性”要求,置于文化的大框架之下。如果沿着这一思路,预探主旋律电影未来发展方向的话,笔者认为主旋律电影具有广阔的前景。
首先,电影作为一种文化工业,本质属性应该是属于大众文化。阿多诺站在批判的立场,尖锐地指责“文化工业的全部实践就在于把赤裸裸的赢利动机投放到各种文化形式上。甚至自从这些文化形式一开始作为商品在市场上为它们的作者谋取生存的时候起,它们就或多或少地拥有这种性质”⑯,认为文化工业的逐利动机剥夺了“艺术作品自治”的权利。但是,反过来说,像电影这样的文化工业,要实现“艺术作品的自治”,如果没有投资再生产的冲动,没有一定数量的受众支撑起来的消费市场,那么它就只能是孤芳自赏的“自治”了,只能在逼仄的一隅顾影自怜。因此,我们有必要重估电影作为大众文化的价值和文化影响力,尤其对主旋律电影而言。因为,一方面,在主旋律电影的前期发展中,正是只重视其“社会效益”而忽视了它的文化工业属性,从而导致大量受众的流失,使其希望的传播效果成为空中楼阁;另一方面,我们还要注意克服把主旋律电影当作“高雅文化”的倾向,认为既然是主流的,就必须有一种雅正严肃的形式。这正如伊格尔顿所提醒的,“高雅文化是意识形态武器中最不重要的一种,完全独立于意识形态的幻想之真理的内核”⑰。而在西方,情况早已发生了改变:“在一种意义上,高雅与后现代文化日益融合,成为西方社会的文化‘主导’”⑱。那种固守“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之分的观念,只会在文化形式和接受之间竖起一道高高的壁垒,阻滞了主旋律文化走向大众。目前,主旋律电影的大众文化定位障碍基本破除。近年来,主旋律电影借助类型影片的经验,已取得很好的社会效果和市场效果。只要在未来,我们不重犯上述两种倾向的错误,主旋律电影的生产投资和消费,将进入一个良性循环的轨道。这几年国内电影市场升温、不少主旋律电影登上票房排行榜就是明证。
其次,自新世纪以来,电影管理层,直至意识形态最高领导层,都已充分意识到主旋律电影不能单单作为意识形态工程去扶持,而且应该将其放在文化产业的高度去认识。以发展产业的思维,对待主旋律电影的生产和再生产。2011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六中全会,从战略层面确立了中国未来文化产业的发展方向。在这一重大外部利好条件下,主旋律电影必将获得一个更好的发展空间。
再次,主旋律电影要更好地发展,走向更多的大众,必须走向一种“共同文化”。笔者这里使用的“共同文化”概念,借自S·艾略特、雷蒙德·威廉斯和伊格尔顿等人,但和他们的内涵有所不同。他们在使用这一概念时,并非指强迫大多数人接受和认同的、建立在“同一性政治”基础上的“共同文化”,而是指一种“共享的文化”,即无论哪种文化,即使它暂时还是弱势的,只要它能被大家认同并共享,就是“一种共同文化”。笔者这里使用的“共同文化”概念有三层含义:其一,是指主旋律电影在其文化价值观念上应该更加开放,争取更大“通约数”。事实上,主旋律电影实践二十余年来,一方面它坚守其最核心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价值范畴,另一方面也兼容了传统、民间乃至西方的某些价值范畴。笔者以为,在主旋律电影今后的发展道路上,应该有更宽阔的胸襟,吸纳一切“有价值”的、“普适”的价值。与社会、与世界的价值“通约数”越大,认同的空间就越大。其二,这种“共同文化”在形式上既是高雅的,同时也是大众的,是能为大多数人所轻松接受和认知的;在价值取向上,它应该是主流的,带有均值性质,既不能太前卫,也不能太保守。目前,它应该和中共十八大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结合和互动。其三,这种“共同文化”要有一种相对恒定的价值观作支撑,即其内容要相对稳定,其影响力应持续时间较长,范围应该能够覆盖到各个阶层。比如,金庸的武侠小说及其改编的电影或电视剧,就是在看似最不讲规则的江湖,最容易犯禁的领域,将儒家的家国观念,忠孝观念,江湖的道义观念糅合到一起,成为人物核心的价值系统。无论什么情节,什么人物,是争抢武林秘籍也好,是挖空心思想做武林盟主也好,是走遍江湖,了结江湖恩怨也罢,其价值评判总是这一套恒定的原则。而这套原则,不仅在香港,在中国大陆、台湾、澳门及东南亚华人圈,都能被广泛认同。这样的文化,是堪当“共同文化”的——当然,笔者不是在这里主张复辟儒家文化。
我想,如果我们的主旋律电影走向了一种这样的文化,一种融合了传统价值和现代价值,本土价值和外来价值的文化,那么它就有可能创造出一种具有广泛文化辐射力的“共同文化”,主旋律电影就会走向一条前景更广阔的道路。
注释
①⑪胡菊彬:《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第23页,第4-5页。
②许纪霖:《中国知识分子十论·知识分子死亡了吗》,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0-11 页。许先生“自明性”之谓,其指向是思想解放运动的目标,笔者这里仅就西方思潮的引进而言。
③“应激反应”(stress response)是个医学名词,是指人或动物机体受到损害时,外部或内部的胁迫所做出的积极的生理生化反应。本文借用这一名称,指称主旋律电影面对“异质性”价值渗透时的主动防御性反应。
④⑩李少白:《电影历史及理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第108页,第107页。
⑤如左翼电影中几部以表现农村阶级压迫著名的影片《狂流》(夏衍编剧,程步高导演)、《铁板红泪录》(阳翰笙编剧,洪深导演)、《春蚕》(夏衍根据茅盾小说改编,程步高导演)、《盐潮》(郑伯奇、阿英据楼适夷同名小说改编,徐欣夫导演)、《丰年》(阿英编剧,李萍倩导演)等,在票房上都不尽人意。关于30年代左翼电影的部分市场表现,参见葛飞:《市场与政治:1930年代的左翼电影运动》,《文艺理论与批评》2005年第5期。
⑥⑦周晓明:《中国现代电影文学史》(上),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5年,第170页,第166页。
⑧程季华:《党领导了中国左翼电影运动》,《电影艺术》2002年第5期。
⑨罗浮(夏衍):《“告诉你吧”——所谓“软性电影的正体”》,《夏衍全集》(第6 卷),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24页。
⑫杨远婴:《中国电影导演的代群结构》,见杨远婴主编:《中国电影专业史研究·电影文化卷》,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6年。
⑬金丹元、徐文明:《“十七年”中国电影中的基本美学形态与国家意志》,《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⑭尹鸿、凌燕:《新中国电影史:1949-2000》,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2年,第154页。
⑮乔瑞金、薛稷:《雷蒙德·威廉斯文化观念思想探析》,《晋阳学刊》2007年第5 期。
⑯(德)阿多诺:《文化工业再思考》,高丙中译,见陶东风、金元浦、高丙中主编《文化研究》(第1辑),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99页。
⑰⑱特瑞·伊格尔顿:《文化的观念》,方杰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63页,第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