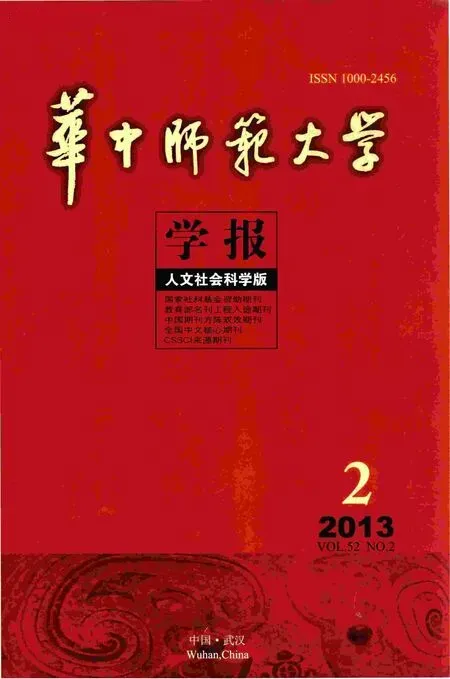格己致知——从德国哲学论哲学之为“知己”的科学
2013-04-09叶秀山
叶秀山
(中国社会科学院 哲学所,北京100732)
一
最近这几年,我的工作重点一直是放在了从康得到黑格尔“德国古典哲学-德国唯心论”这一段。这一段的哲学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来说,不应是生疏的。但是“熟知非真知”,往往越是熟悉的却越是大而化之,“不(再)读(他们的)书,不求甚解”。
我们学习研究哲学的过程,也体现了黑格尔说的由“抽象”到“具体”的发展过程。学习研究哲学也有个“循序渐进”的问题。多年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一直强调的是读经典原著,这个原则是很重要的,是做哲学始终要坚持的;不过坚持这个原则,并不是说不读其他的书,二手的资料甚至入门的书,也是可以或应该参考的。
实际上,“读原著”也是“循序渐进”“逐步深化-逐渐提高”的,也就是说,是一个从“抽象”到“具体”的发展过程。
应该说,“读原著”要想“知道”一个“大概”,也是不容易的。我年轻的时候读书往往抓住书中的“好段落”甚至“好句子”来体会,觉得是精华所在,后来发现即使记住了许多“名言”,对于书的整体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慢慢觉得读书-尤其是读哲学书,要从整体上把握哲学家的思想脉络,而不能只抓“细节”,不了解整体,那些细节贯穿不起来,而哲学是要求“理路”上“贯通”的。于是,就注意全书的“大关节目”,知道一本书的“思想”的“体系”,写书的人是一层层写下来,读书人也就要一层层读下来,但写书人是有个整体构思在逐步展开的,读书人也要对这个整体构思有所把握,“大关节目”才会贯穿的起来。“大关”和“节目”是通着的。
这样,读那些本来就“难懂”的哲学家的书(经典原著)就很累了。我相信,对于一般读者说,读一两遍是不可能懂的,要知道个“大概”,也要多读几遍,更何况,要从这个“大概”进入到“具体-深入”,那就可能会把书读破了。
这就是我近几年仍在做“德国古典哲学”的原因,我总觉得对这些著作的理解是不够深入的。
二
对于康德,他的哲学思想是我从在北大学习时就接触到的,工作以后又多次做过有关的题目,但是这几年我感到,我对他的哲学思想的理解还是相当表面、相当肤浅的,之所以如此,不仅是因为不够用功或者不够聪明,而是不够“迂回”。此话怎讲?
我过去读康德的书,也是注重他的三大《批判》的关系,“大概”的理解是不错的;但是在反复阅读这三大《批判》并且反复阅读他后来的一些著作甚至相当短的文章后,慢慢发现许多思想在他的第一批判里已经留下了“位置-余地”,包括第三批判“目的论”问题,都是想到了的,这样包括他的一些短文章,在“理路”上都是相互“照应”的,所以读这些文章也能“加深”对他的主要思想的理解。
理解康德,不仅要从他的三大《批判》“迂回”出去,到他的其他的著作,而且要“迂回”到费希特、谢林,特别是黑格尔。理解康德要读黑格尔的书,反过来,理解黑格尔,也要读康德的书,否则难以深入。
从哲学的历史发展来看,黑格尔对康德的理解,由于他自己也有一个成熟的体系,就可能有一些偏见,或有不很准确之处;但就思想承续关系来说,在思想的深度上,可能比一般研究康德的著作,要好一些。这样,研究康德,在研读有关康德的研究专著的同时,我觉得研读黑格尔的著作尤为重要。这一点扩展开来说,研究哲学史,注意研究一个独立的哲学家对另一个独立的哲学家的思想评论,应该是第一位的工作,譬如研究柏拉图,研读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就应是必修之课。每个成气候的哲学家都是自身独立的,哲学史上那些林林总总的大家们都是独立的,他们之间或如莱布尼兹所谓的是一个个相“异”的“单子”,它们把自己的哲学体系“包裹”得严严实实,但它们却是“互相反映-相互照应”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每个“单子”都是一个“世界”,也都是一部“历史”。
我自己这些年反复读黑格尔的书,感到不仅对理解黑格尔本人的思想常读常新,对于理解康德以及费希特、谢林也大有好处;又由于他的体系庞大,不仅他的哲学史讲演录,他的其他著作,对于做哲学史,竟然也可以是重要的参考书。
欧洲哲学的传统,苏格拉底强调“认识你自己”,如同对于我们的“思无邪”那样,不很愿意只限于从道德修养方面去理解。“认识你自己”不仅仅是“人贵有自知之明”的意思,欧洲哲学由此开出了一个大传统,到黑格尔总其成,欧洲哲学成为“‘知己’之学”。
“知己”不是不要“知彼”,“知彼”当然非常重要,人的一切生存条件,都要有“知彼”的支持,利用“彼”,改造“彼”,以为“己”所用;然而“知己”同样重要,“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则“盲动”,“不知己”同样“盲动”,“盲”为“不明-无明-无知”,“知己-知彼”,其“知”也“一”。何以为“知”?中国传统说,“格物致知”,西方人按照他们的传统说在“哲学”上是“格己致知”。
从这个角度来看,从康德到黑格尔他们的工夫都做在了“格己-认识你自己”上。
他们这个“知己”的“己”,不是指“人”的“生理”或“心理”的种种结构,限于这样来“对待”“人”,“人”亦是“彼”;这个“己”是指“(包括人在内的)一切事物”的“自己-自身”,康德的“物自身-我自身”。
康德说,要“认识-知”这个“自身”,先要看看“你自己”都有什么“能力-功能”,在这个意义上,“知彼”必先“知己”。这个“你自己-己”乃是人的“理性”。一切“可感”的,都应作“彼”看,只有“可理解的”才是“己”,于是“理性”在何种意义上可以“知己”就是一个需要研究思考的问题。
这样,康德就要在“格物致知”之前,先要做一番“格己”的工夫,探讨这个“己-理性”在何种意义上有“格物”的“能力”。可是,大家知道,康德却得出了“消极”的结论,按照他的“批判哲学”,“知己-认识事物自己”是“不可能”的。“知”似乎只能“限于”“知彼”;然而,这个“彼”,作为“知识对象”来说,又是“自己-主体”“建立”起来的,所以“知彼”又必先“知己”。这是康德面对着“自己”提出的复杂问题。
对于这个复杂问题,康德的结论虽然很消极,但功夫并未白费。康德“格己”的工作,得出了对“界限”的“知”。“认识你自己-的界限”原本也是古代哲人的意思,这层意思,到了康德,哲学的意义大大加深了,“人贵有自知之明”不仅有修养上的意义,而且有哲学上的意义了,应该说,康德的推动之功,不可磨灭。
当然消极总归是消极的,康德为“知识”划定“界限”,指出对于“事物自身-自己”是“不可知”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自知”(对“事物自身-物自身-我自身”的)“无知”竟是最大的“知”,是“大智慧”。
于是在这个意义上,尽管康德在“认识你自己”这个欧洲哲学传统上作出了很大的推进,但由于“批判哲学”在“知识论”上的消极性,其“所知”只是“知彼”,而非真正的“知己”。也就是说,康德知识论所提出的问题仍是“知识-科学”如何对于一个“异己”的世界会-可能“有所知”。尽管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强调了“主体-己”的“能动性”,但“客体-彼”仍是“两个”“不同”的世界,他的“知识论”要解决的问题和他的工作之着力点,在于“演绎-论证”“自己”何以有可能对于一个“异己-彼”能有“真知识”,亦即“主体-自我-己”的“知识”如何会和那个“异己-彼”的“客体世界”“相符合”、“相一致”。
“符合-一致”也还是“二合一”,两个“异质”的东西的“一致”和“符合”带有“偶然性”,为了避免这种理论上的漏洞,就必须使“二”“归一”,使“异质”的转化为“同质”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康德批判哲学的工作不仅在那“哥白尼式的革命”,而在于找到一个“围着转”的“轴心”:“理性-知性”“先天立法”“职能”,“理性-知性”为一个“异己-自然”的世界“立法”,则有可能促使“异己”“归化”为“自己”,使“二”“归”“一”。
就这个问题来看,康德的工作只是一个“开端”,或者说,他在“知识论”上的“知己”的工作只做了一半,还遗留一个“事物自身”在“彼岸”,没有“归化”进来。这就是说,那个“异质”的“彼”只是在“现象”上“归化”了,在“本质”上,尚留在了“知识王国”的“外面”,这个“彼”“自己-自身”“不可知”。
不过,按批判哲学,这个“彼自身”虽“外在”于“知识”,却仍“内在”于“理性”,或者甚至说,就“理性”来说,“彼自己”恰恰是最“内在”的,是完完全全“内在”的,它只是“思想体-本体”,这个“彼自己-彼本体”当然可以“无矛盾”地对它进行“思考”,但因不“开显”为“现象”,缺乏“感性直观”的支持,因而不能形成“知识”,因为“理性”在“知识领域”-“知性”只有权为“现象-自然”“立法”;但是,在“道德王国”,“理性”为“自由”“立法”,情形就大不相同。“道德领域”是“理性”“自己-自由”“产生”出来的一个“世界”,原本是“理性”“自己”的“世界”,不是感性的自然世界为“理性”“提供”出来的,因而“善-德性”“自己”有能力“自由”地“开显”“自己”的“世界”,这个“世界”的“实在性-现实性”无须“求诸外”,无须“求诸彼”,只须“求诸内-求诸己”;只是“道德王国”与“知识王国”之间依然“壁垒森严”。
康德看到了这两个“壁垒森严”的“王国”有“统一”的必要,故有他的第三《批判》来“沟通”二者,我们对于这个《(判断力)批判》的理解和研究,尚需做很大的努力。之所以对这个《批判》研究得不够,也是因为在这种“统一”的工作方面,费希特、谢林,尤其是黑格尔有更好的工作成绩出来了。
在某种意义上说,康德的“自己”似乎也是被“分割”了的,“我”有一个“自己”,“你”也有个“自己”,虽然在“理性”上为“一”,而在“知性”上为“二”,“彼”也有一个“自己”“在”“彼岸”;黑格尔说,实际上这个“彼自己”就是“我自己”,原本是一个“自己”,“自己”为“一”。
按照康德,“彼”分为“现象”与“本体-本质”,“本质-本体”“不可知”,然而,实际上恰恰是那个“本质-本体”才是“可知”的,因为“现象”的“本质”是“概念”,只有“概念”的“体系”才是“必然”的“知识”。
当然,康德的“知识论”也是由“概念”组成的,但他的“概念”是一种“形式”,其“内容”是要从“外面-感觉经验世界”提供出来的;黑格尔的“概念”本已“蕴含”着“内容”。在这个意义上,康德的“概念”是“相对”的,“相对”于一个“异己”的“感觉经验世界”,而黑格尔的“概念”是“绝对”的,是“自己”和“自己”“相对”。
其实,康德的“知识王国”也是“理性-知性”“自己”建立的,也就是说,“可以直观”的“现象界”这个“知识-可知的”“对象”也是“理性-知性”“自己”“建立”的,所以,“经验的条件”和“经验对象的条件”是同一个“条件”,即“先天性”的“知性纯粹范畴”,“感觉”只能提供“材料”,只有“理性-知性”才“给予”这些材料以“规定”,在这个意义上,对康德来说,“经验对象-自然”的“规定”是“理性-知性”“自己”“给予-建立”的,因而作为“知识王国”的“基础”的“理性-知性”,在“现象界-可知对象”范围内,也蕴含了是“自己”与“自己”“相对”的意思在内;但这层意思还有待开发,因为“概念”的“内容”还是需要“直观”来“提供”的,那个不提供“直观”的“本体-彼”则只能被排斥于“知识王国”之外,于是康德不得不保留了一个“在”“现象”之“外”的“本体”,这个“本体”对于“理性”的“知识能力-知性”来说,就不是“自己”有能力加以“规定”的,只能是一个没有“直观”“内容”的“概念”,而“概念”无“直观”,则是“空洞”的。这样,对于康德来说,“本体-本质”只是一个“空洞”的“思想体-概念”;只是到了《实践理性批判》里,这个“思想体-本体”才有能力-有权力通过“意志自由”在“道德王国”“证明”“自己”也有“实在性”,也是可以“直观”的,“理性”才“有权”对其作出“规定”。“意志自由”的“产物”-“道德-德性”的“世界”,同样也是“实实在在”的,但这个世界,不是“感觉经验”“给予-提供”的,而是“理性”“不受感觉经验”制约地、因此是“自由”地“建立”起来、“规定”了的。“实践理性”在“道德领域”为“自己”“建立”了与“自己”“相对”的“(道德)王国”,在这个“王国”里,“理性”才真正是“自己”与“自己”“相对”。
就这层意思来说,黑格尔的工作正是把康德的“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统一”起来。就“领域”来说,双方都“扩大”了自己的“疆土”;就“立法权”来说,“理性”“统一”了自己的“权力”,行使着“自己”的“统一”的“最高”的“权力”。于是“理性”拥有“绝对”的“权力”。
“理性”被康德“列土封疆”之后,“分割”了“权力”,黑格尔为“理性”收回了“自己”的“权力”,“统一”了“疆土”,成为一个“理性”的“绝对”的“大帝国”,黑格尔在“结合”了“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后,“建立”了一个“理性”的“绝对王国”。面对这样一个“王国”,人们有一种“恐惧”和“厌恶”之感,也许是事出有因的。
在经过对刚刚过去的法国革命的反思之后,黑格尔对自己的“绝对哲学”是有进一步阐述的,经过他的阐述,对于上述疑虑,虽不能完全消除,但或可有所疏导。
我们看到,黑格尔在费希特之后,不由“实践理性”入手,而从“理论理性”入手,来完成“理性”的“统一大业”,是很重要的改变。
这个思路的转换对于哲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既然从“理论理性-知识”入手,则康德为这个领域所设定的种种“界限”都不能不有所正视和交代,因为既曰“知识”,就不是抽象的形式,而是有内容的,具体的,也就是有规定的,“理性”既然已经“僭越”到“物自体-事物自身”这个“思想体”领域,要对它作出规定,作出“限制”,则这种“僭越”的“权力”之“合理性”需要“论证”,黑格尔的“绝对知识”之所以可能,要做出“演绎”。
不错,由费希特发扬的“实践理性”精神,已经“僭越”了“理论理性”的“界限”,这个“权力”也是康德“给予”了“理性-意志自由”的,但是康德只赋予“自由”对“自然”的“范导”性意义和作用,没有赋予它“建构”的意义和作用,所以“自由”对于只限于“自然”的“知识”言,仍是一个“禁区”,因而是“不可知”的。
然则,黑格尔的“绝对知识”恰恰是以“自由”为“知识”的“对象”的,“绝对知识”就是“自由知识”,而不仅仅是康德意义上的“必然知识”,“绝对知识”因其“自由”而“必然”。
其实,康德既已认定“现象界”感觉材料的“规定”性是由“知性”“给出”的,则“理性”“有权”给出“本体界-事物自身”的“规定”性这个道理,就该已经蕴含在内,黑格尔把这层道理阐发出来,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更进一步,“知识”的“界限-规定”莫过于它的“对象”,“对象”原本是“知识-知性-理性”“自己”“设定-树立-建立”的,于是“对象”“自身”的种种“规定”,既是“对象”“自身”的,也是“知识-知性-理性”“自身”的,在这里只有“同一”的“自己-自身”,并无“我自身-我自己”和“物自身-彼自身”之分,或者说,这个“二”原是“一”“分(化)”出来的。“相对-限制”原是“绝对-无限”“分(化)”出来的,“规定”“出自”“无规定”,“有序”“出自”“无序”,“秩序”出自“混沌”。
在这个意义上,“绝对知识”“蕴含”了一切的“界限”,它有一个“过程”“开显”这些“界限”,逐渐地“扬弃”种种界限,“吸收”种种“界限”,又“回归”到“绝对”“自身”。“绝对”这个“游子”在“饱经风霜”之后,又“回到”“自己”的“家园”。这个“路程”有一种“精神”的“支持”,不会“半途而废”,“精神”保持-支持着“理性”之“自由”,使“意识”“看到-认识到”,即使在“受限制”的“条件”下,“自己”也是“自由”的,“精神”就意味着,“理性”在“对象”中已经有能力“认识”到“自己”,在“相对”中,“认识到”“绝对”,在“必然”中,“认识到”“自由”。
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的“绝对-自由”就无须“推迟”到“无限”的“时间绵延”中,“推迟到”可望不可及的“彼岸”,而就“在”“此岸”,在“相对”中就“有”“绝对”“在”,在“必然”中就有“自由”“在”,不必“等到”“海枯石烂”,“此情绵绵”而抱憾“终生”。于是,“绝对-自由”“无所不在”,“人生何处不相逢”,只要有这样一个“哲学”的“意识”,则“芳草萋萋”,“四海”可以“为家”。
此番“气象”,岂非海德格尔“此在”的“境界”?
三
黑格尔以后的欧洲哲学,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做过一些,都是很粗浅的。开放伊始,新材料一下蜂拥而来,应接不暇,经过一番“迂回”,再从欧洲哲学历史发展的历程来看,会有一些新的体会,可惜近年他们的书读得少了,以后要补课的。
欧洲哲学“现象学”这个系统,黑格尔以后,胡塞尔特别是海德格尔应是“推陈出新”的环节,影响所及,至今不衰。
表面上看,海德格尔讲“存在”,黑格尔讲“意识-理性-精神”;海德格尔强调“有限性-时限性”,黑格尔讲“绝对-无限”,好像是完全“相反”的思路,实际上,他们之间在“精神”上的“相通”之处,也是有迹可循的,并非我做惯了哲学历史,总想找出些“共同点-联系”来。
当然,海德格尔哲学对于黑格尔哲学是有重大“变革”的,他把哲学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从“意识-理性”移到了“存在”,但并不是“又一次”的“哥白尼式革命”,不是“主体”又“围着”“客体”“转”了,不是这个意义上的“轮回”,而是一个“推进-发展”;如果我们可以把黑格尔哲学叫做“客观(什么)主义”,那么海德格尔似乎是在“客观性”问题上“推进”了一步,“客观”不再是理解为“精神”,而是理解为“存在”。这样我们也许可以说,海德格尔的“存在”相当于-类似于黑格尔哲学体系中“客观精神”的“地位”,但在这个“客观”中,海德格尔吸收了黑格尔“绝对”的意思,也就是说,海德格尔的“存在”兼有了“客观”与“绝对”的意义在内,而我们已经知道,在黑格尔意义上的“绝对”,是“独立-自由”的意思,因而海德格尔这个“客观-存在”也具有“独立-自由”的意思在内,它是“绝对”的“一”,而蕴含着“多”,开显为“多”,这个“多”并不离开“一”,是“一”的“具体化”,是为“Dasein”,“Da-seian”仍是“Sein”。
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的“存在”就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自然”的“存在”,这种“存在”,胡塞尔已经将它们“括出去”“搁置”起来了,海德格尔强调了“括不出去”的“理念”的“实在性”,强调了那个“括不出去”的“存在”之“存在性”,而这种“存在性”既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自然”,则就蕴含着“历史性”,“时间性”。“存在性”是“历史”的,“时间”的,而不仅仅是“自然”的,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人文”的,是“历史”的“存在”,“时间”的“存在”,“人文”的“存在”,对于“个别”的、“自然”的“人”来说,它是占支配地位的“客观”的“力量”,是“历史”的“命运”,这个“命运”是“独立-自由”的,是“不以人的意志转移”的“客观”“力量”。
“存在”的“力量”不仅仅是“自然”的,因而不是“天命”,而是“人(的)命(运)”,“历史”的“命运”,这种“命运”是“人”“自己”“造成”的,“人”是“历史”的“创造者”。从这个意义来说,“存在”又是“人”作为“Dasein”“自由”地“创造-产生”出来的。
于是,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就从“此在(Dasein)”的分析入手讨论“存在(Sein)”,是“由此及彼”,由“知此”而到“知彼”,而无论“彼”“此”皆为“存在”的“状态-存在方式”。“存在”作为一个“历史”的、“时间”的“力量”看起来是个“客观”的“彼在-在彼”的“异己”,但实际上却仍是“自己”,是“人”“意识到-觉悟到”“自己”原是一个“Dasein”,才“开显”出来的这样一个“异己-在彼-彼在”的“Sein”。
“Sein”虽是由“Dasein”“觉悟-体会-意识”到的,但却“大于-强于”那个具体有意识、有理性的“人”,“彼”“大于-强于”“此”,“历史-社会-形势”“大于”“人”。就历史来说,就社会来说,一般都是如此。“英雄好汉、帝王将相”都有“不得已”的地方。
“此在-Dasein”在这个意义上之所以“弱于-小于”那个“Sein”的“彼在”或因为“此在”是“现在”的,而“彼在”则是包括了“已在”和“将在”的,在“时间”上占了“优势”,“彼在-Sein”占有“优先权”。
黑格尔有自己的办法维护着“现在”的“优先权”,他以“概念-逻辑”的方式将“时间”提升为“永恒”,“永恒”亦即“永恒的现在(现时)”,“概念”的体系“超越”“时空”,“时空”中“万事万物”无论“过去-现在-未来”被“概念-逻辑”的体系“一网打尽”,概莫能外,“过去-现在-未来”任何事物的“本质”都是“合理的”,可以“理解”的。“历史”的“本质”是“有规律”的,“历史”与“逻辑”是“同一”的,“历史事实”的“发展”“本质上”也就是“事实”“概念”的“合规律”的“推演”,这个“发展”的“本质”是“可知”的,也就是说,是可以“推论”的,“合逻辑”的。
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以“概念-逻辑”之“无时间性”来“超越”“时间”之“流”;海德格尔既标出“存在”,则无此便利,“存在”“必”“在”“时空”中,“时间”之“无限绵延”,“空间”之“无限广漠”,“沧海桑田”,甚至可以“瞬息万变”,“世间”“何时-何处”寻出“存在”?海德格尔既不用黑格尔的“存在的概念”与“概念的存在”为“同一”这样一条“思辨”的理路,则必从“时空-存在”本身寻求一条切实的理路。
代替黑格尔的“逻辑性”的“概念”,海德格尔提出了“死”这样一个“存在性-生存性”的问题,将“无线绵延”“时间之流”以“死”作一“了结-终结”,以“断”其“流”,使“混迹”“流”中之“(芸芸众生)诸存在者-Seiend”“超拔-超越”出来,成为“Dasein”,由“此”进入“Sein-彼”。“人”作为“有死者-会死者”“意识到-觉悟到”“有”一个“大于-强于-寿于”“此-己”的“彼”“存在”。
“有限”“开显-提示”着“无限”,“时间之断”“开显-提示”着“时间”之“流”,“无限”“在“有限”中,“流”“在”“断”中,黑格尔也曾说到,有限生命的死亡,“精神”就突现出来,“精神”为“不死”。
当然,海德格尔将“时间”之“有限性-有时限性”-“死”的问题提出来作哲学思考,反映了欧洲哲学在当代的新的动向,使这个哲学传统接触到新问题,有一番新的面貌。
“死”是“存在者”的“结束”,也是“存在”的“开始”。“结束”是“完成”,“事物”的“本质”在这个“全-过程”中,所以黑格尔也认为“过去”“有-存在着”“事物”的“本质”,“本质”“在”“过去”;对于“人”的“生命”来说,“死”是“生命”的“完成-终结-全过程”,这个“过程”,是“生”的“过程”,也是“死”的“过程”,但“死”也还是一个“界限”,是“生命”之“流”的“截断”,有一个“临界点”,这个“点”,是“生命”的“终点”,是“人生”的“终点(驿)站”,“乘客们-诸存在者”“下车-离世”“进入”“各自”“自己”的“世界”,这个“世界”对于“车厢”里的“人”来说,是“另一个”“世界”,但这个“另一个”“世界”是“各位乘客”的“真实”的“世界”,这个“世界”是“实在”的,也是“本质”的,“乘客们-诸存在者”“真实”地“存在”于这个“世界”中,这个“世界”是“各位乘客”的“自己”的“家园”。在这个意义上,“人生旅途”中之“芸芸众生”,都“在”“回家”的“路上”,是一条“回归”之路,不是“回归自然”,而是“回归自由”,“回归存在”;就黑格尔来说,是“回归精神”。黑格尔的“精神”或海德格尔的“存在”是“人”的“家园”,“家园”是“人”“自己”的。
“人”不必“等到”“自然生命”的“终结”就“有能力”“认识-觉悟”到自己的“家园”,海德格尔这种“觉悟-意识-认识”的“能力”使“人”不仅仅是“有死者”,而且是“会死者”。他说,一切“动物”都只是“有死者”,只有“人”是“会死者”;又因“有能力-会”“死”,“人”也就有“能力-会”成为“不死者”,犹如黑格尔指出“理性”因“精神”的力量“有能力-会”在“有限”中“认识-发现-把握”到“无限”,在“必然”中“认识”到“自由”,在“异己”中“认识”到“自己”,于是“人”的“理性”“有能力-会”在“过去”中“发现-认识”“(永恒)现时”,扩展开来,在“死”中“见”“生”,“死”“留住”了“生”,“死-无”这个“龛阁”中“存放”着“生-有(存在)”;“置之死地”而“生”,“生-死”之“转化”才不是一种“迷信”,而是有“道理-理路”上的“根据”的。人间一切“祭祀-祭奠”都意味着“阻止”“死者”“回归”“自然”,而力图将它们“留住”“在”“自己的家园”,而一切“传统”“留住”的“习俗-制度-伦常-礼仪”等等,皆是“祖宗的法规”,“人”“在”这些“法规”中“生长”,又施行种种“变革”,形成“新”的“法规”“传流”下去。“法”“大”于“人”,但“法”又是“人”“设立”的,是“人”的“精神-理性-知识”的“产物”。
“理性”为“自己”“立法”必有“二律背反”,这是康德指出的“铁律”,黑格尔积极正视了这条“法则”,因势利导,以此“推动”“事物”之“变化发展”,为“历史”的“发展-进步”“推波助澜”;海德格尔提出“天-地-人-神”,“事物”之“存在”为此“四大合一”,“存在”为“四大”的“自由”“组合-游戏”,“天-地-人-神”也就是“天-地-生-死”,“死”对“会死者”言,将使“人”“提高-升华”为“神”,不是基督教意义上的“神”,而是古代希腊意义上的“不死者-(诸)神”,这种“提升”只在“一念”之间,即将“混迹”与“彼”之“大千世界”,“回归”到“自身”之“此在”之“觉悟”,就可“认识”到“死”的“存在”之意义。这样,海德格尔的“向死而生”推到一个“万物静观”的“境界”,难有黑格尔那种“掌握矛盾”于“股掌之间”的“恢弘气度”了。
然则,无论“动-静”,皆为“知己”;“由此及彼”、“推己及人”,或如后来法国列维纳斯那样“由人及己”,“由彼及此”,皆不失“认识你自己-知己”这个欧洲哲学的传统。
上个世纪以来的欧洲哲学,由于信息科学的发展,著作之多,新学说流传速度之快,皆使人应接不暇,许多书要好好读,在这样的“世界”中,做哲学也难,只能以加倍的努力,迎接信息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