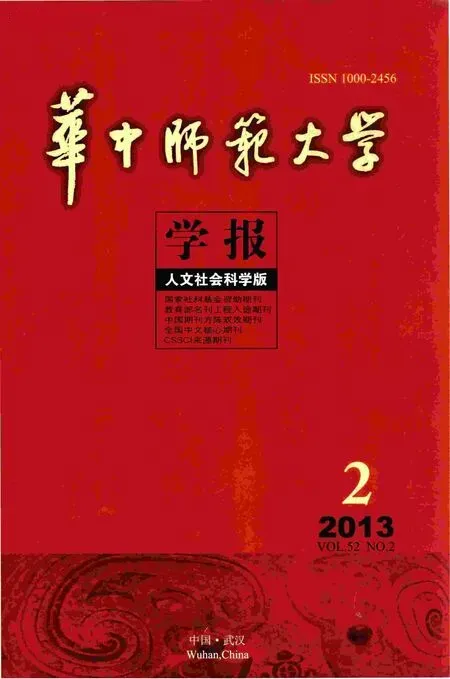中国农户的历史变迁与行为特征
2013-04-09梁东兴
唐 鸣 梁东兴
(华中师范大学 政治学研究院,湖北 武汉430079)
中国农村民主发展内源于现代国家对乡土社会的建构。其内在逻辑在于“农村民主的发展是党的利益代理动员和农民的利益考量回应之间结构性紧张的产物。”①然而,伴随着现代国家对乡土社会的建构,乡村社会本身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变化着的乡村社会既是国家建构的结果又反过来影响国家的进一步建构。因此,这要求我们至少对近几十年来中国乡村社会变迁进行深入考察。考察中国乡村社会的变迁,必须首先对农户的变迁进行考察。这是因为乡村社会作为与城市社会相对的一个社会子系统,其内核是乡村地区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是乡村人口不断结构化而形成的群体存在状态。而千百年来,农户一直是中国农村最基本的生产、生活、交往,以及政治责任单位。从这一点来说,乡村社会的实质不过是农户行为的集合,农户之间不断结构化而形成的群体存在状态便构成了生动多样的乡村社会。进一步地,在笔者看来,所谓农户行为就是农户在社会实践中为实现自身主观意图所表现出来的一切活动,这些活动的主要方面是农户为达至自身认同逻辑而外化于一定场域的行为表现。因此,影响农户行为特征的因素主要有三个方面:农户的自身特点;农户的认同逻辑;农户的活动场域。这三个方面决定了我们在以农户为基本单位研究乡村社会时的三个基本视角。②本文正是依据此种逻辑考察了构成中国乡村社会变迁基础的中国农户的历史变迁与行为特征,并试图将这一变迁过程与结果比较完整地呈现出来。
一、挣扎于土地的原子化小农
长期以来,中国是一个以小农经济结构为主导的传统农业社会,农户在小块土地上辛勤劳作以养家糊口,往往过着生于斯、死于斯的自给自足的封闭式生产生活。这种延续数千年不变的生产生活方式使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深深打上了小农的烙印。对于小农这样一种经济形态,马克思在考察法国农民时曾做了详尽的描述:“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这种隔离状态由于法国的交通不便和农民的贫困而更为加强了。他们进行生产的地盘,即小块土地,不容许在耕作时进行分工,应用科学,因而也没有多种多样的发展,没有各种不同的才能,没有丰富的社会关系。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小块土地,另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一批这样的单位就形成一个村子;一批这样的村子就形成一个省。”③从马克思的这段话,我们可以生动看出小农的如下特征:拥有小块土地,但由于缺乏分工和应用科学而生产效率不高;生产同质,生活条件相同,自给自足;思想狭隘,相互隔离,政治保守。马克思同时指出小农经济存在于极为漫长的历史时期,对社会发展影响深远。他认为“自耕农的这种自由小块土地所有制形式,作为占统治地位的正常形式,一方面,在古典古代的极盛时期,形成社会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在现代各国,我们又发现它是封建土地所有制解体所产生的各种形式之一。”④恩格斯通过自己的考察进一步印证了马克思的结论,他认为法国和德国小农生产方式的“家庭是自给自足的,几乎生产它所需要的一切,而村庄则更是如此。这差不多是十足的自然经济,货币几乎根本不需要。”⑤不仅如此,恩格斯还明确指出:“我们这里所说的小农,是指小块土地的所有者或租佃者——尤其是所有者,这块土地既不大于他以自己全家的力量通常所能耕种的限度,也不小于足以养活他的家口的限度。”⑥这就明确阐释了小农概念的特定内涵。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论述不仅明晰了小农的特定概念,还深刻揭示了小农经济的基本特征,具有较强的普适性,为我们认识中国传统农村和农民提供了理论支撑。
中国是一个农业文明悠久的国家,农户构成社会组织的基本单元,这种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形态典型而久远。早在春秋时期,古人已经认识到井田制下“民不肯尽力于公田”的弊端,各国为刺激生产积极性、扩大剥削量,先后进行税制改革,如管仲采取“相地而衰征”的措施,鲁国实行“初税亩”等,这些改革在客观上承认了土地的私有权,加速了井田制的瓦解。战国时期以“废井田,开阡陌”为主要内容之一的商鞅变法,更是以法令的形式废除了井田制。这样一来,到战国时期,井田制彻底崩溃了,代之而起的是多种形式的土地私有制。土地私有制的形成,使我国逐渐产生了以耕种土地为业的自耕农。这些自耕农在小块土地上辛勤劳作,将土地视为命根,长年累月附着于土地以获得生活的依凭,小农经济由此不断产生、形成和发展。汉唐至明清时期,自耕农人数大大增加,小农经济得到较快发展,同时由于密集的劳动投入和长期的精耕细作,中国传统小农生产土地产出率和劳动效率均有很大提高,为中央专制主义集权统治奠定了重要的经济基础。然而,由于土地分配的不公和人地矛盾的日益加剧,自清代中叶以后,小自耕农的劳动效率不断下降,中国的小农经济日益内卷化,传统的小自耕农经济开始走向破产和没落。而“这个半无产化了的小农经济的形成,正是新中国成立前农村数世纪以来大规模动荡的结构性基础”⑦,也是“促成十九、二十世纪大规模农民运动的乡村危机的根源”。⑧
因此,1949年以前的中国乡村社会是典型的“一袋马铃薯”,在中国共产党通过“政党下乡”把农民动员起来以前,这种原子化的小农形成的是一盘散沙的局面。这一时期的农户总体来说具有以下特点。
1.从自身特点看属于原子化小农。所谓“原子化小农”是指农户之间互不联系、高度分散化。几千年来中国农民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狭小的生产规模使农业和手工业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将农民束缚于“男耕女织”的家庭经济结构之中。一方面,落后的生产方式、不发达的社会分工使小农的社会交往狭隘,与外部世界相互隔绝,村落成为他们的整个“世界”;另一方面趋于封闭的自然经济、同质的生产方式使得即使在村落内部,也甚至出现“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互不联系的生活状态。因此,在长久的自然经济的束缚下、生产方式的控制下、重农逻辑的约束下,这些自我封闭的状态不仅成为乡土生活的常态,甚至潜移默化成为农民的精神束缚,形成了中国传统农民封闭保守、自立独立的独特心理。这种独特的心理进而又强化农民不愿交往、拒绝交往,以至于“传统小农绝大多数农民完全依靠自家的资源生产、生活,除了亲戚邻里之外几乎没有任何交往,甘愿在家庭这一最小的社会空间单位里度过一生80%—90%的时间。”⑨也正因为此,中国传统农民有着强烈的小农意识,即为满足个人温饱,在一小块地上自耕自作,无约束、无协作、无交换而长期形成的一种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这种意识使小农往往自私自利、小富即安、缺乏自律、宗派亲族严重。
2.从认同逻辑看生存性价值居首。传统农户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他们紧紧依附于土地,从土地获得自己几乎全部的生活所需。他们用泥土打造土坯房屋供全家居住,在自家的土地上辛勤劳作以获得必要的粮食和菜蔬,穿着自家女人纺织出的棉布衣服。因此,小农不仅从土地获得必要的生活资料,甚至还自己生产一些基本的手工业品,以至于“在经济上每个农家,除了盐铁之外,必要时很可关门自给。”⑩小农这种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一方面使得其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自己家庭生活所需,缺乏交换的动力,因而“交换是有限的,市场是狭小的,生产方式是稳定的,地方和外界是隔绝的,地方内部是团结的。”⑪另一方面,由于土地面积狭小零碎,生产工具简单落后,加之可供投入的资金十分有限,因此吃饱穿暖的生存需要成为小农的主要生活目标。他们即使经年累月地辛勤劳作,一般也很难有较多的劳动剩余,小农的购买力因之极其有限。因而对于大多数小农来说,“除了少量次要的必需品外,他们极少购买城市产品。即使到20世纪,城市产品的渗入仍然很有限,只是棉纱或棉布,以及火柴和火油。”⑫因此,几千年来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和简单落后的生产工具决定了满足生存需求是传统农户的首要目标和主要行为逻辑。家庭内部的分工、劳动力的配置以及与外界较少的交往都围绕这一逻辑展开。“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等生活和风俗习惯也由此形成。
3.从活动地域看局限于村庄集镇。在费孝通看来,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黏着在土地上动弹不得的,“靠种地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城里人可以用土气来藐视乡下人,但是乡下,‘土’是他们的命根”。“种地的人却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侍候庄稼的老农也因之像是半身插入了土里,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在这个因流动少而“土气”的封闭地域中,农民的“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即一种“差序格局”的亲属圈,这种亲属圈“以‘已’为中心,像石子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且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⑬在传统乡村社会,不仅农户的社会交往局限于狭小的亲属圈,其生产消费交换活动也局限于村庄集镇的狭小范围。这是因为,在传统农业社会劳动生产率较低,为了获得足够的生活必需品以维持家庭的生存,要求农民必须将大部分时间用于从事农业生产。同时由于农民的外部就业机会比较少,只好在单位土地上投入更多劳动,以期通过“过密化”生产最大化生活必需品,生存性的生产活动由此局限于村庄以内。尽管,当农户仅依靠农业无法解决生存问题,而必须借助于劳务市场和家庭手工业时,也往往不过是农忙劳作,农闲务工或者交换手工产品,这种简单的小规模产品交换很难突破村庄集镇的地域范围。
二、组织进公社的集体化小农
中国农业曾长期领先于世界其他文明古国,并让我们炎黄子孙引以为自豪。然而正如毛泽东所言:“在农民群众方面,中国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⑭纵观中国历史,历代统治者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利。他们视农民为“鱼肉”,为所欲为,任意专横地向农民榨取税收,没收财产,使农民始终处于悲惨的境地。尤其到了近代,广大农民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多重压榨,加之农业生产增长与人口增长不同步,导致人均资源占有量大幅度下降,又屡遭战乱,农业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农业生产全面衰落,广大农民处于悲惨生活的境地。1949年后,新中国的成立打碎了旧的国家机器,但是占农村85%~90%以上的小农经济仍然是非常落后的,尤其经过长期的战乱,已到了难以维系的地步。为了促进农业生产,尽快恢复国民经济,建国初期(1949~1952年)着力对小农制进行了改造。一方面通过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使占乡村人口总数60%-70%的3亿多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获得了大约7亿亩土地,免除了他们过去每年向地主缴纳的350亿公斤粮食的超重地租。”⑮另一方面着力建设真正实现“让农民当家作主”的上层建筑,由此农民经济上“耕者有其田”,政治上“当家做主人”,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被空前激发出来,农村生产力获得了极大的恢复和发展,农民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改善和提高。但是土地改革不仅没有废除小农制还使小农制因此获得了新的典型形式。首先,土地改革并没有改变个体农民传统的经营方式,绝大多数农民仍然在零碎的小块土地上以一家一户为单位进行独立自主的农业生产经营。“特别是经过这次土改,我国开始形成了以自然村落为单元‘不分男女老幼、一律平分土地’的农地分配政策惯例和平分机制,使明清时期以后出现‘地权分散化’和‘耕地细碎化’的发展趋势更加凸显。”⑯其次,土地改革也没能改变个体农民传统的生产条件,土地改革后农民仍然运用传统的生产资料进行着和以前没有任何区别的生产劳动,传统农业的生产水平并没有得到提高。因此,土地改革后只是土地的所有权发生了改变,从生产经营的形式上来说,农村仍然是清一色的小农家庭经营,与几千年沿袭下来的经营形式并没有根本差别。旧中国汪洋大海般的小农经济格局和小农社会“一盘散沙”、“相互隔绝”的状态依然没有改变。
土地改革后,中国农村汪洋大海、一盘散沙的小农经济显然与工业化战略是相矛盾的。1952年底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完成了土地改革,并在已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区及时地引导农民开展生产互助合作。这期间强调对生产中的困难,要求开展灵活多样的互助合作来加以克服,尚未对小农经济改造做出全面布置,而是要求在农村工作中注意小农经济的特点。但是,起因于1953年的粮食等农产品供应紧张,使中央领导集体强化了小农经济与工业化矛盾的认识,从而加速了对小农经济的改造。1953年12月16日的《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最终在全国范围内拉开了对小农经济大规模改造的序幕。由此,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就轰轰烈烈地开始了,在短短3年时间里,亿万分散的个体农民被组织起来,走上了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道路。1958年8月,从更好解决“三农”问题的愿望和适应赶超战略出发,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进一步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此后两三个月内,全国农村普遍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建立起一种全新的社会形态。这种体制的突出特点表现为:“政社合一”的组织体制、“一大二公”的组织规模、封闭集中的经营管理制度等。因此,人民公社从功能上说几乎是无所不包的,已经远远超出了单纯的生产管理组织。此后,人民公社虽然进行了多次调适,但其作为中国农村基本经济体制的地位及其主要的功能并没有实质性的转变。这种模式一直持续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长达20余年,成为改革开放前中国农民生产生活的基本组织模式。这一时期,农户总体上来说具有以下特点:
1.从自身特点看成为集体化小农。从1953年农业合作化之后,尤其人民公社时期疾风骤雨式的改造,使传统小农的面貌发生了极大的改变。首先,人民公社确立的“集体土地所有制”彻底颠覆了传统小农赖以存在的物质前提,建构起了农业生产经营的全新基础。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认识,小农之所以存在,在于家庭对小块土地的拥有。人民公社这一体制的设计显然正是为了改变这种小土地所有者“一盘散沙”的局面,因此它不仅事实上使农民完全失去了小块土地,也几乎失去了与土地关联的一切权利,直接解构了传统小农存在的物质前提。其次,人民公社统一的“集中劳动”形式还彻底改变了传统小农“外在于国家”的局面,建构起了农业生产经营的全新方式。在传统中国社会,“王权止于县政”,小农社会由乡绅自治,农户除了纳粮与国家权力之间没有直接的交往关系。但到人民公社时期,实现了“生产的集中化和大型化”,在军事化的政治组织推行的计划经济下,农民的经济活动受到严格控制,小农个体成为公社的社员。不仅如此,人民公社政经合一的管理体制和军事化的管理方式,还事实上严密控制了农民的人身自由,建立起了小农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层级关联,使农民紧紧依附于公社、听命于组织动弹不得。这样,传统小农开始直接进入国家行政调控体系,从形式上也似乎消失了。然而人民公社二十余年的建设实践表明,这种通过个体小农捆绑式集体化所建立起来的生产模式只是在形式上改变了小农的传统经营方式,小农经济的实质并未真正改变。在农业生产技术进步有限和工业化战略的强势逻辑下,人民公社不仅没能摆脱传统农业的耕作技术和方法,其经济生存状态也仍然是自给和半自给的,各公社之间缺乏横向的直接联系。因此所谓的农业集体经济不过是农民个体经济的袋装化。这种经营方式的弊端在人民公社后期大量显现,人民公社后期很多公社“人齐才下地”,“出勤不出力,干活儿一窝蜂”,“集体偷懒”和“免费搭车”现象越来越多,生产效率逐渐下降,这也是人民公社体制最终无法维系的根本原因。
2.从认同逻辑看本体性价值转变。民以食为天,传统农民对小块土地的依赖而形成的小私有心理使中国共产党推动的集体化一开始并不为农民所主动接受。为此,中国共产党在土地改革后通过不断地政治运动强化集体化意识,改造农民的小私有心理。在持续在的政治运动中,“忆苦思甜”是重要活动,通过回忆过去的痛苦生活,感受到今天的生活幸福。农民“向后看”的思维惯性和强烈的感恩意识使得“吃水不忘挖井人,翻身不忘共产党”,由此这种高度集中化的人民公社体制得以迅速建立。不仅如此,在“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习人民解放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持续政治动员和宣传教育下,农民对自己的未来有了不同于以往的新的期待,他们开始将个人的劳动与国家的兴衰、民族的命运、人民的解放和子孙后代的幸福联系起来,认为自己的劳动是有意义的,参加生产劳动是当家做主人的光荣表现,人民公社由此为农民提供了生产生活的新的意义系统。当然,促使农民的本体性价值逐渐移位的原因并非单纯的共产党政治宣传的组织高效,人民公社这一体制本身也一定程度上使农民可以从生产和生活中获得意义感。一方面,人民公社促进了小农的平等化。长期以来,中国传统社会是由家庭本位往上构成的等级社会,强调人伦秩序和道德规则,人与人之间辈分差异尊卑分明。新中国的建立和土地革命的轰轰烈烈开展,彻底铲除了剥削阶级、埋葬了人剥削人的旧社会,解除了加在农民身上的经济政治枷锁,建立起了农民千百年来渴望的基于人人平等的全新社会。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运动的开展从形式上来说则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平等化的趋势,至高级社时期,农民成为公民化的公社社员和国家主人,成为集合意义上的一个分子,大家不仅相互之间经济上平等,在国家面前也扮演着毫无差别的同质角色。因此,这种平等感极大促进了农民对人民公社时期价值宣传的认可。另一方面,人民公社本身为小农获得新的人生意义提供了载体。在人民公社内部,人人都是社员——公社的一员,大家集体劳动,共同消费,相对平等,从而为长久处于弱势地位的小农挺起胸膛做人提供了可能,小农开始自己认可自己,在能够满足生活需求的情况下,他们是钟情于这种生产意义系统的。因此人民公社的产生的确为一定的理想主义和新的目标意义的确立提供了可能。不仅如此,人民公社集体化的生产生活方式、频繁的会议和文娱活动,还有利于农民组织起来,在人与人的交往中相互接纳和认可,从而获得超越经济目标的新的价值意义和认同逻辑。
3.从活动地域看牢固束缚于公社。国家为了解决与分散小农交易的难题,从农民有限剩余中提取资源来建设暂时不能反哺农业的现代工业化体系,而设计的充当提取资源的中间人的人民公社制度,对乡村治理结构产生了根本和深远的影响。这一体制的建立,最终达至了“满头乱发无法抓,编成辫子就好抓”的乡村格局,国家政权史无前例地渗透到农村每一个角落,农民成为牢牢依附于公社这个“常青藤”的“藤上的瓜”。首先,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严格的层级管理制度使农民不可能脱离公社。根据党的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人民公社不仅负责党政各方面工作,而且负责组织农林牧副渔业生产和工商业发展,负责统管全社的生产安排、劳力调配、物资调拨和产品分配,拥有了对社内几乎全部资源的控制力,人民公社实际上成为最基层的治理单位。在这一治理单位下,广大直接从事生产的农民与生产资料相分离,广大直接组织生产的基层管理者经营管理权与自主权相脱节,农民被束缚于土地和狭小的村落地域,缺乏自由发展的空间。不仅生产效率无法提高,还造成千篇一律的农民僵化的体制性人格特征。不仅如此,为实现对农民经济行为的控制,也为了培养农民的公有理念和提高国家防御能力,公社还推行了军事化的组织管理。农民的个人行动就纳入到人民公社的统一管理范围之内,并最终纳入到国家整体行动的目标。当时的男女劳动力,全部按军事编制,组成班、排、连、营、团,由公社统一领导、统一调配、统一指挥。在建立人民公社的初期,甚至实行口粮、柴草均由公共食堂统管,农民社员连自己家庭开伙的自由都没有了。这样,农民的行为就几乎全部被公社控制,整个农村的社会结构非常单一,乡村社会形成了“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局面。其次,僵化的工农分工和职业身份世袭制,导致了城乡分割,限制了农村劳动力的流动,进一步将农民长期禁锢于农村。自1958年1月新中国第一部户籍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颁布开始,直到改革开放初期,城乡实行了严格的二元户籍管理制度和二元就业制度,“加上农村人民公社和农产品统派购销制度,强化了政府对农村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配置管理,城乡之间的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被禁止,人为地割裂了城乡之间统一的要素市场,农村内部、农业内部,甚至农民家庭经营内部的生产要素配置,也受到国家行政手段和政策的严格控制。这些制度的综合作用,导致改革开放前城乡成为两个相对封闭的经济社会系统。”⑰
三、流卷入市场的社会化小农
人民公社作为中国农村一场强制性的制度变革,以规模空前的方式疾风骤雨般地改变了中国农民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毋庸置疑,这一体制为新中国在一穷二白和外资缺乏的情况下迅速推进国家的工业化作出了巨大贡献。正是有了这个体制,才为国家汲取农村资源集中用于支持工业建设提供了基础,粗略估计,1952-1978年,农民的贡献高达6000亿元。同时,在人民公社体制下,由于自上而下层层严密控制,农村社会比较稳定,这客观上也为我国进行工业建设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仅从农村自身发展来说,这一体制也并非一无是处。一方面,正是人民公社体制的强烈冲击,彻底打破了千百年来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极不公平的农村治理结构,从此告别了农村一盘散沙的局面。另一方面,人民公社时期国家权力对乡村资源的整合和动员能力大大增强,因而也为农民提供了不少的公共服务。这一期间,我国农村教育、卫生等公共服务的改善是非常大的,尤其集中人力兴建了众多的农村水利设施建设。但是,人民公社这一体制是在国家力量强势介入乡村社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很大程度上违背了农民的愿望,也难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规律。研究表明,这一时期不仅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和消费水平没有实质性的改善和提高。更为严重的是,1978年全国农村尚有2.5亿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生活在极度的贫困状态,比例高达农业人口总数的30%以上。不仅如此,从全局的角度来说,这一体制还直接造成了工农业发展严重失衡,就业结构转换滞后于产业结构转换,“三农”问题日益突出,不仅危及国民经济的发展,还危及社会的稳定,成为重大的政治问题。正如1978年12月10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发言时所指出的:“建国快三十年了,现在还有讨饭的,怎么行呢?要放松一头,不能让农民喘不过气来。如果老是不解决这个问题,恐怕农民就会造反,支部书记会带队进城要饭。”⑱可见,农村已经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境地。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中国农村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促进农村生产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政策措施。其政策导向突出地表现为市场化取向下以赋权与放活为内核的路径探索。包括实施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促进农民家庭经济和乡镇企业,取消农产品统派购制度和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农村新体制等。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进入工业化中期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要求我们将进一步将长期实行的农业养育工业的政策逐步转变为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促进城乡经济社会统筹发展。由此,中共以进一步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积极推进城乡二元体制向一元体制转变,探索建立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主要表现为:以加大“三农”财政投入为标志开始向建立覆盖城乡的公共财政制度推进,以取消农业税为标志开始向基本实现城乡统一的税赋体制过渡,以实施农村义务教育“两免一补”为标志开始向基本实现城乡同等的义务教育制度转变,以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为标志开始向基本实现城乡平等的医疗服务制度方向迈进,以探索建立农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标志开始向基本实现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制度方向努力,以全面保护农民工权益为标志开始向基本实现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就业制度方向发展。总的看,废除人民公社体制而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是继农村土地改革后农民的第二次大解放。土地改革使农民在经济上对地主的依附关系被废除,农民从此成为平等的、更具独立人格的人,为当代中国民主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在废除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和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后,农民进一步获得经济上的自由,成为流卷入市场的社会化的新农民:在生产经营方面,农民有了生产经营自主权,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在就业方面,农民与土地捆绑在一起的制度被解除,有了自主择业权,可以实现就业的非农化转换;在政治权益上,政社分设和村民自治替代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后,基层民主逐步发展,农民的民主权益得到尊重和保障。
经过这一时期的发展,当前的农户总体上来说具有以下特点:
1.从自身特点看小农逐渐社会化。人民公社体制的废除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使农民与外部社会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使从集体化中解放出来的小农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地进入市场。在市场化强势逻辑的塑造下,传统小农开始脱离以往经济形态,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等日益走向社会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生产方式上,市场无处不在,影响着生产资料的获得和劳动产品的交换,社会化的生产活动因此替代自给自足成为主要方面。在生活方式上,货币无处不在,影响着从吃穿住用行到教育、医疗几乎全部生活资料的获得,货币收入的增加因此成为家庭的主导追求。在交往方式上,“熟人社会”不再一如往常静止不变,来自市场的机会和风险从各个方面对既有的圈子产生着持续不断的冲击,来自自主的学习和判断相比祖辈传递的生活经验似乎更加重要。可以说当前的小农已深深地卷入市场和社会之中。然而,社会之“大”并没有改变小农之“小”。一方面,从存在基础来说,当今的农户仍然是恩格斯所言说的“小块土地的所有者”。由于社会总人口的增加、耕地面积的减少等各种原因,在现阶段农村人口的人均占有耕地面积不断缩小。同时随着计划生育的不断推行和农村生育观念的持续变革,当下农村的大家庭日益减少,农户的家庭人口数量相比以往也普遍更小。另一方面,从行为特质来说,当今农户也仍然具有马克思所言说的“生产效率不高、生产同质、政治保守、思想狭隘”的小农特征。由于耕作的土地数量小,无法进行规模化经营,加之劳动人口少,无法进行分工和协作,因此当今农户难以走出低效农业的陷阱,生产效率不高的局面并未改变。生产效益不高又导致小农在应对优胜劣汰的大市场时往往充满恐惧,保守、狭隘的小农意识甚至由此得以强化。尤其,如果小农长期得不到良好的教育、培养,没有形成市场必需的决策、风险、信息、合作意识等,必然加剧相当一部分小农在残酷的竞争中被淘汰而对市场产生怀疑、恐惧甚至排斥。然而,无论小农愿意不愿意、主动还是被动,市场化的进程已不可阻挡地使他们流卷进来,走向社会化。因而正如徐勇教授所言:“当今的小农户已越来越深地进入或者卷入到一个开放的、流动的、分工的社会化体系中,与传统的封闭的小农经济形态渐行渐远。如果我们仍然将当下的农户称之为小农的话,那么他们已成为迅速社会化进程中的小农。”⑲
2.从认同逻辑看社会性价值凸显。实际上,当小农不可避免地流卷入市场之后,市场对小农而言就不再仅仅是日常的经济活动领域,而是成为一种根本性的生产生活方式或逻辑渗透到小农行为的方方面面。这其中变化最快的和最根本的方面,在于市场化在带来现代性,促使小农走向大社会的同时,急速地解构了传统小农的本体性价值,一种消费膨胀、面子主义、相互攀比的社会性价值追求在矛盾中凸显出来。在传统中国社会,由于生产生活方式封闭和生产力低下,本体性价值主导着农民的认同逻辑。这其中传宗接代、延续香火和光宗耀祖等是其核心内容,构成农民安身立命的基础。因此传统中国社会农民是生活在祖荫之下的,人生的根本目的在于向下繁衍后代、向上光宗耀祖,有限的生命通过无限的子孙繁衍和家族兴旺来获得永恒意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便是这一逻辑的真实写照。新中国建立以后,灵魂不死,来生转世的说辞虽然被现代性的尤其是唯物主义的意识形态所消灭,但是“人多力量大”的人口政策不仅没有触及甚至还助长了农民传宗接代的观念。因此在改革开放前,农民的本体性价值始终稳固地占据着农民认同逻辑的重要方面。市场化则对农民的认同逻辑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在市场化下,农民个人的生活已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化的影响。市场充斥的货币逻辑一时泛滥,货币的多少成为农民衡量生活好坏的重要参照。灵魂不死、来生转世的观念既已被主流意识形态证明是错误和愚蠢的,生儿育女、传宗接代的热情被子女的不孝等“证伪”成为功利主义考虑的一部分。农民有限的生命因此不再能被无限的子子孙孙的延续向下传递而获得永恒的意义。中国农民传统的安身立命的基础因此动摇,本体性价值随之失落。而“一旦缺失本体性价值,农民就更加敏感于他人的评价,就十分在乎面子的得失,就会将社会性价值的追求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⑳因此,随着本体性价值追求的失落和社会性价值追求的凸显,现在的小农早已不再奉行“袋中有粮、心中不慌”的农民哲学,他们在市场原则的刺激下,纷纷从“一亩三分地”中洗脚上岸,入城淘金,“摇身一变”成为奋战于“世界工厂”的“城市工人”,希望借在群体内的竞争获得优势和承认,来填补日渐失落的代表着人生根本意义的本体性价值追求。
3.从活动地域看进入市场难“入城”。在传统中国,农户可以关起门来过日子,直至人民公社时期,农户仍被牢固束缚于乡亲邻里的公社圈子。随着人民公社的解体和二元户籍制度的废除,劳动力有了自由选择地域的权利,而小农全方位、深度社会化带来的巨大货币支付压力,最终迫使他们纷纷流入市场,无论愿意不愿意、恐惧不恐惧,都得在风险倍增的市场中游弋。这是因为,在生产要素的配置全方位市场化,由家庭走向外部社会后,传统乡村社会小农依赖家庭手工业和打零工的收入再也无法满足社会化后迅速膨胀的家庭消费。在土地增收无望、投资缺乏资本的情况下,农民只能依靠最富裕的资源——劳动力,解决货币支付问题。就业社会化由此成为解决货币危机和压力的“新拐杖”:农民开始大量地进入市场,尤其翻山越岭来到机会较多的繁荣城市寻找就业机会和增收途径。农民由一个“家庭人”彻底转变成了“市场人”。这一现象突出地表现为随着沿海工业在1980年代末的快速发展,大量中西部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了离土又离乡的城市打工生活。尤其那些人多地少,经济贫困的农村地区,进城务工经商可以获得远高于农业的收入水平,且同样的务工经商收入在全国劳动力市场形成后具有更高的边际效用,农民因此有着更强烈的外出务工经商的积极性。自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的最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一波又一波农民离土离乡,进城务工,他们甚至拉友结伴,乐此不疲。其宏大的场面就连2006年免除农业税也未能有根本的改变。据统计,目前中国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数量在1.6亿左右。大量农民背井离乡来到城市,对农村和城市的影响都是巨大的。一方面农村因为大量劳动力进城而出现劳动力不足的情况,一些乡村年轻人大量外出,“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问题突出,村庄“空心化”严重,日益凋敝。另一方面大量农民涌入城市成为新生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然而,由于工业化超前发展,城镇化严重滞后,稳定可靠的非农就业机会和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机制尚未跟上,使得长期积压下来的“农业人口负担”虽大量涌入城市,却并不能真正在城市安家和成家立业,一时也无法获得与城市人同等的待遇。各方面研究表明,从当前农民工的总体状况来看,他们虽然来到了城市却并不能真正“进入城市”,他们中的大多数无法在城市获得稳定的就业和较高的收入,因而也无法举家在城市体面而有尊严地生活下来。城市一方面吸引着农民,让他们趋之如鹜、挥汗如雨;城市又常常排斥着农民,让他们遭遇鄙夷和不公、白眼与孤独。而这,也许正是当下中国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迅速发展的共同烦恼。
注释
①参见唐鸣、梁东兴:《利益的代理与考量:农村民主的发展逻辑》,《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0第3期。
②学界在研究乡村社会时由于研究的基本单位与视角不同,往往得出不同的结论,容易形成各说各话的局面。笔者认为农民的原初认同逻辑决定了农民的一般行动单位,农民的一般行动单位决定了乡村研究的基本单位和基本视角。本文中,农民的认同逻辑是指支配农民行动的价值需求,这一价值需求主要取决于农户本性价值、社会性价值、生存性价值三个方面价值需求的现实考量与互动消长。本体性价值是个体对人生意义的深沉思考与追问满足,解决的是人何以为人的安身立命问题。社会性价值是个体从社会中获取的评价与尊严满足,解决的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生存性价值是个体改造自然获得的生产与生活满足,解决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这方面的思考将另文论述。总体上说,笔者赞同徐勇教授等倡导的以农户为基本研究单位,并试图在本文中以农户的自身特点、认同逻辑、活动场域为基本视角来“重识农户”。
③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77页。
④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09页。
⑤⑥恩格斯:《法德农民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86页。
⑦⑧黄宗智:《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17页,第301页。
⑨沉石、米有录:《中国农村家庭变迁》,北京:农村读物出版社,1989年,第16页。
⑩⑬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2页,第7、26页。
⑪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233-234页。
⑫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08页。
⑭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34页。
⑮董辅礽:《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82页。
⑯张新光:《小农理论范畴的动态历史考察》,《贵州社会科学》2008第1期。
⑰郑有贵:《目标与路径:中国共产党“三农”理论与实践60年》,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4-85页。
⑱陈云:《陈云文选(1956-1985)》,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12页。
⑲徐勇:《“再识农户”与社会化小农的建构》,《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⑳贺雪峰:《当代中国乡村的价值之变》,《文化纵横》201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