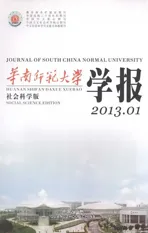城乡教育一体化的制度束缚与破解
2013-04-08邬志辉
邬志辉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要“建立城乡一体化义务教育发展机制”。向城乡教育一体化目标迈进的过程就是突破城乡二元教育制度束缚的过程。那么,当前促进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的制度束缚是什么?怎样破解这些制度难题呢?本文拟就此问题进行探讨。
一、城乡教育一体化的制度分析困境
所谓城乡教育一体化就是适应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需要,把城市教育和农村教育作为一个整体,突破城乡二元分割分治的制度障碍,由各级政府在辖域范围内或跨越行政区限制,统筹规划城乡教育发展、统筹设计城乡教育政策、统筹配置城乡教育资源,改变优质教育要素资源单一“向城性”流动格局,实施向农村倾斜政策,努力提高农村教育质量,逐步缩小城乡教育差距和身份束缚,确保城乡公民享受平等的受教育权益,实现城乡教育协调、合理与可持续发展的过程。
对于我国城乡之间教育呈现的二元结构状态,社会各界基本没有异议。对于城乡教育二元结构突破点的选择,学界也基本取得共识,即“统筹城乡教育发展,关键在于制度设计”、“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重点在于突破城乡二元分割分治的制度束缚”。但是,对于什么才是城乡二元教育结构的制度束缚,学界的认识有较大差异。一些学者只是罗列诸多教育制度的城乡分轨现象,并期望通过制度合轨来实现城乡教育的一体化;还有一些学者把城乡二元教育结构放在一个更大的城乡二元社会背景中进行考量,分析其成因的历史性、综合性和复杂性,期待“综合治理”和“渐进改革”。总之,似乎大家都把导致城乡教育二元结构的制度根源归结为内外两大方面:一是教育内部的制度根源,如管理体制和财政体制;二是教育外部的制度根源,如户籍制度和就业制度。[1]
把城乡教育二元结构归结为教育管理体制和财政体制的人相信,只要各级政府职责清晰,统筹城乡的重心和层级上移到省,城乡教育一体化目标就一定会实现。应该说,近年来国家对教育管理体制和财政体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比如“省级统筹、以县为主”体制、“两为主”政策、“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等等。政府的职责逐渐明晰了,统筹的层级也逐渐上移了,可为什么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依然困难重重呢?把城乡教育二元结构归结为户籍制度的人认为,只要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界限,以合法固定住所为落户的基本条件,放宽大中城市的户口迁移限制,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管理制度,那么就可以让进城务工人员获得市民身份,享受与市民一样的教育待遇。但是,河北、辽宁、江苏、河南等地在省域内实行了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上海、浙江、广州、重庆等地也建立了用投资、技术、土地、学历等换取城市户口的“有条件准入”制度,可为什么户籍作为一种社会屏蔽机制仍然阻碍着进城务工人员子女享受同城的学习和升学待遇与权利呢?城市为什么在实质性的教育利益上不愿做出让步呢?我认为,以上对城乡教育二元结构的制度分析虽然在方向上是正确的,但还没有找到问题的真正症结所在。
二、城乡教育一体化的根本制度束缚
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的根本性制度束缚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中国特色的“经济功能取向”的地方政府职能定位。从职能上看,“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是承担公共管理的重要载体,是国家公共事务的承载体、实际行为体”[2]。政府虽然承担着多种职能,但公共服务应是其最基本的职能。即使政府承担着一定的经济职能,也主要是为经济的良好运行提供法律保护和政策规范,而不是直接从事经济行为。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推进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完善,地方政府较强地承担了经济主体角色,公共服务和社会建设职能相对偏弱。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是GDP,地方政府把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经济建设上,有的地方政府甚至把自己当成了企业或公司,找项目、跑市场。为了获得预算外的财政收入,利用“占补平衡、增减挂钩、指标转换”的土地政策缝隙,大量征用农民土地以换取土地出让金,但土地出让金却几乎不用于教育。这就是为什么我国财政性教育支出占财政预算内总支出的比例连年增长而占GDP比重却始终达不到4%的根本原因。[3]我们不能说各级政府不重视教育,但与重视经济的程度相比仍然处于次要地位,“教育优先发展”思想还没有从根本上树立起来。在各级政府总体上没有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战略地位的前提下,期望政府能把农村教育放在重要地位、积极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建设只能是幻想。
二是“城市决定农村”的权力结构关系。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为了获得工业化发展的“启动资本”,逐步形成了城市控制和支配农村却又严重依赖农村的“殖民化”管理体制和权力结构关系。即使在改革开放之后,城市一元化领导下的城乡关系格局也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从空间形态看,政府都设在城市(或城镇),政府的行政级别与城市的规模、城市所拥有的资源总量呈高度的正相关。在中国,不仅农村是属于城市行政辖区之内的空间区域,而且所有地方的农村都是由城市领导的,这就导致了无论是空间城市化还是人口城市化,城市都支配着农村的局面。“一方面所有城市的发展都要向农村扩张,另一方面农村自己却没有对应的谈判主体……因此,从这两个关系的结构来看,所有关系到利益取向或分配的问题实际上都是从城市角度考虑的,至少是以城市为出发点。”[4]城市与农村之间的不平等主体地位和城市支配农村的权力结构关系,导致空间和人口两种意义上的农村在教育利益分配问题上处于被施舍和被剥夺状态。农村权力的边缘化必然导致其在生存境况和受教育权益上的被排斥,而精英政治的神秘化和庶民政治的妖魔化,更是加剧了城市支配农村的“合法性”。在事关农村教育发展的重大问题上,是城里人在替乡下人做决策。在决策过程中听到的基本是城市的声音而不是农村的声音,理所当然地,决策的结果往往对城市有利而对农村不利。在这种城乡关系体制下,农村只是弱势的受动者,且由于居住分散化,也比较缺乏组织性,难以形成“有机的团结”,难以对政府的决策施加压力与产生影响,他们只能盼望城市的道德觉悟和悲悯施舍。由“城里人”设计的城乡教育一体化在多大程度上能符合“乡下人”的需要和利益诉求,本身就是可质疑的。
三是农村产权缺失导致的城乡单向一体化。农民所具有的最重要资源就是土地和劳动力。劳动力的价值是由健康状况和受教育程度决定的,农村医疗保障和公共教育服务水平低下使农村劳动力无论在城市就业岗位竞争上还是在农村劳动生产率提高上都处于弱势地位。最重要的是农民与市民享有完全不同的产权制度。厉以宁先生发现,城里实行的是土地国有制,无论是祖传的房屋还是新购的商品房,城市都有房产证;而农村实行的是土地集体所有制,祖传的房屋也好,农民在自家宅基地上建的住宅也罢,既没有产权也没有房产证。[5]农民对所承包的土地和宅基地没有产权,导致他们不仅在城市政府征地过程中无法通过市场手段谋求自己的利益,而且也无法实现土地和房屋的抵押、转让和合法出租,因而也就不能引导城市资金向农村的转移和流动、实现城乡双向一体化。这跟教育有什么关系呢?农村产权缺失和城乡单向一体化的结果是农村的荒废与破败,而乡村衰败不仅导致无法吸引优秀教师到农村任教,而且导致优质教育资源的“向城性流动”。而进城的农村人又难以获得市民身份和平等的教育权益,进而导致社会身份的代际传递。如果不突破这一恶性循环,城乡教育一体化便很难实现。
四是城乡区隔化的城市主流社会态度。在城市社会中,还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区隔“城市人”与“乡下人”的观念制度。“城市人”与“乡下人”的二分法本身就是封建等级思维的产物,它是为完成社会身份标签化职能设置的。在社会观念中,城市人是“上等人”,农村人是“下等人”;城市人是聪明的,乡下人是愚笨的。对此,费孝通先生早就有批判:“乡下人在城里人眼睛里是‘愚’的……但是说乡下人‘愚’,却是凭什么呢?乡下人在马路上听见背后汽车连续的按喇叭,慌了手脚。东避也不是,西躲又不是,司机拉住闸车,在玻璃窗里,探出半个头,向着那土老头儿,啐了一口:‘笨蛋!’——如果这是愚,真冤枉了他们。我曾带了学生下乡,田里长着包谷,有一位小姐,冒充着内行,说:‘今年麦子长得这么高。’旁边的乡下朋友,虽则没有啐她一口,但是微微的一笑,也不妨译作‘笨蛋’。乡下人没有见过城里的世面,因之而不明白怎样应付汽车,那是知识问题,不是智力问题。正等于城里人到了乡下,连狗都不会赶一般。如果我们不承认郊游的仕女们一听见狗吠就变色是‘白痴’,自然没有理由说乡下人不知道‘靠左边走’或‘靠右边走’等时常会因政令而改变的方向是因为他们‘愚不可及’了。”[6]在二分的思维中,既然农村人是“下等人”,所以就不应该享受“上等人”的教育服务。这种封建的等级观念不仅在普通民众的观念中存在,甚至在一些政府官员的观念中也存在。
三、城乡教育一体化的制度难题破解
首先,突破“经济型政府”的职能束缚,创建公共服务型政府并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是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所谓“基本公共服务,指建立在一定社会共识基础上,由政府主导提供的,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阶段相适应,旨在保障全体公民生存和发展基本需求的公共服务。”政府不是企业,不能以赚钱和营利为第一目的,政府要以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为根本职能。因此,为了改变政府较多介入市场活动和注入过多财政资金到企业的状况,必须改革政府绩效考核标准,适当淡化以GDP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指标在政府绩效评估体系中的权重,建立以公共服务绩效为核心内容的政府考核体系;同时加强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以便使地方政府既有积极性又有能力加强公共服务建设。教育是第一基本公共服务,应该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为此需要在体制上建立地方政府统筹、多部门共同参与治理的教育管理机制,改变传统的人事权、财政权、土地管理权各据一方(管事的不管人财物、管人财物的又不管事、事权与财权相分离)的状况,理顺条条和块块之间的体制障碍。并通过强化地方政府及其领导的教育努力程度和教育绩效考核,真正实现地方政府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战略地位的目标。
其次,突破“城市决定农村”的权力结构,建立“社会公众参与”的治理新机制。从教育政治学的视角看,我们应该关注这样一些问题,即“是谁在做决策?”“这些决策对谁有利?对谁不利?”“在决策过程中我们听到的是谁的声音?”“什么人发不出自己的声音?”我们发现:在事关农村教育发展的重大问题上,是城里人在替乡下人做决策;在决策过程中听到的基本是城市的声音而不是农村的声音。理所当然地,决策的结果往往对城市有利而对农村不利。因为城市的教育行政级别高于农村,高行政级别所掌握的教育资源也多于低行政级别,上级有权作出决定并命令下级执行。在这种城乡关系体制下,农村只是弱势的受动者,且由于居住分散化,也比较缺乏组织性,难以形成“有机的团结”,难以对政府的决策施加压力与产生影响,他们只能盼望城市的道德觉悟和悲悯施舍。在“城镇统治农村”的城乡教育关系体制下,尽管在事关农村教育发展等重大问题的决策上存在着“体制内的民主”,但却不一定是“有机的民主”。按照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所有的人都是知识分子”的观念,能参与教育决策的人也都是知识分子。但知识分子是具有“有机性的”,即知识分子必然是与某个阶级、某个社会集团相联系的。葛兰西曾专门区分了“城市型”和“乡村型”两类知识分子,[7]认为国家对社会的控制有两条路径:一是通过社会行使“霸权”职能;二是通过司法行使“直接统治”和“管辖”职能。知识分子“就是上层建筑体系中的‘公务员’……是统治集团的‘代理人’,所行使的是社会霸权和政治统治的下级职能”[7]。“作为每个主要社会集团有机范畴的知识分子”在教育决策时必然代表该社会集团的利益,无论教育决策人过去是否出身于乡村,但现在作为城市社会的一员,必然有意无意地会更多地代表所属利益集团的利益,从而导致对农村身份人口教育利益的排斥。为了提升城乡教育一体化的决策质量,反映多元利益主体的教育诉求,应改变传统的统治型教育决策结构,探索建立“社会公众参与”的多中心教育治理新机制。让社会公众特别是农村的教育利益相关者参与城乡教育一体化决策,不仅是迎接信息社会挑战的需要,也是回应社会对透明性和责任性政府的呼唤、多途径满足城乡公民合理需求、协调教育利益冲突、推进善治的内在要求。[8]我们可借鉴国际社会广泛使用的听证会、共识会议、公民陪审团等社会参与治理新模式,推进教育决策的城乡一体化。
最后,突破“城市人”与“乡下人”的观念束缚,建立“统一公民”的观念制度。观念作为一种社会主流态度,会以“集体遵守”的方式影响人的行动、规范人的思维。在迈向城乡教育一体化的伊始,我们需要一种“新的启蒙”,需要全体民众的重新觉悟。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教育规划纲要》也提出要“在财政拨款、学校建设、教师配置等方面向农村倾斜”,但城市社会认同“自己的教育福利”被“乡下人”分享吗?认同“外来的”的务工人员应享受同城教育待遇吗?地方政府认同把教育资源投放到农村吗?如果城市人没有在观念中形成以上认同,在“农村教育的命运掌握在城市手中”的体制下,我们还会对城乡教育的一体化抱有希望吗?在现代社会,“农民”是一种职业而非社会身份,既然是一种职业,不仅所谓的“乡下人”可以从事,就是所谓的“城里人”也可以从事。任何合法的职业都应该是平等的,他们的子女在教育权益的享受上不应该被人为地加以区隔。尽管国家实现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要形成“统一化公民”的社会主流态度,还需要一个全社会的启蒙过程。这个启蒙工作虽然需要在社会教育、政府官员教育中率先启动,但从根本上看,这种“观念的变革”必须发生在学校里,通过学校的变革来实现对社会的改造。如果在儿童身上不能形成“统一公民”的观念,那么未来的城乡一体化社会就不可能实现。
[1]褚宏启.城乡教育一体化:体系重构与制度创新——中国教育二元结构及其破解.教育研究,2009(11).
[2]万俊人.现代公共管理伦理导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204.
[3]周志忍,陈家浩.政府转型与制度构建——中国教育资源配置的政治分析.政治学研究,2010(4).
[4]李慧芳,孙津.城乡统筹中新型城市形态创制的要素关系.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8(2).
[5]厉以宁.走向城乡一体化//程志强,潘晨光.中国城乡统筹发展报告(2011).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5.
[6]费孝通.乡土中国与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12.
[7][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张丽,张跣,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9、7.
[8]OECD.Citizens as Partners——information,Consultation and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Policy.Paris:OECD Publishing,2001:19-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