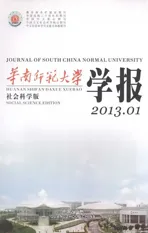免费时代农村教育的“人财困局”
2013-04-08葛新斌
葛新斌
2004年元旦,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宣布了一项重大惠农新政:准备用五年的时间逐步取消农业税,并增加对农业的投入,逐步扩大对农民的补贴范围。2005年12月底,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议,自2006年元旦起,废止实施了48年之久的《农业税条例》,取消除烟叶以外的农业特产税,全部免征牧业税。从此,中国延续了2600多年的“皇粮国税”步入历史博物馆。这一划时代的惠农新政,随即对农村教育政策产生了直接影响。中央政府决定,从2007年秋季开始,免除农村公办义务教育学校学生的书杂费。2008年秋季,全国城镇公办义务教育学校同样免除学生的书杂费。至此,我国义务教育进入了免除学费和书杂费的新时代。在上述重大政策转变的同时,中央政府还出台了一系列的配套政策与措施。于是,我国农村教育的面貌“为之一变”!然而,实地调查显示,与城镇学校相比,农村学校仍可一言蔽之曰:“硬件不硬,软件更软!”本文即从农村学校的“人”(师资队伍)与“财”(教育经费)两个方面略作梳理与分析,以期寻求相关问题的有效解决之道。
一、农村的教师队伍仍然很簿弱
1980年之前,农村教师队伍的主体是民办教师。在计划体制时代,我国农村教育规模较小,师资培养体系尚不健全,每年培养的新教师数量极为有限。尤其在“文革”期间,各级各类师范院校停止正常招生,农村学校更是无法得到正常的师资补充。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各级各类师范院校开始源源不断培养出新的师资,他们逐渐补充到了农村学校之中。1980年代初,国家出台规定,不再吸纳新的民办教师入职。1986年《义务教育法》颁布之后,随着农村教育规模的扩张,师范院校毕业生开始大量进入农村教师队伍行列。1990年至2000年十年间,随着“普九”达标验收工作的大力推进,中央政府曾明确宣布:“决不把民办教师问题带入21世纪!”于是,各级政府通过“关、招、转、辞、退”等措施,到2000年之后,农村学校已经不再任用民办教师。[1]然而,在民办教师退出历史舞台后,农村教师队伍之中又出现了代课教师人数迅速膨胀的现象。从2006年开始,随着各大媒体不断曝光代课教师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中央政府开始坚定决心解决代课教师问题。各地通过实施“代转公”考试等措施,使得代课教师人数从形式上开始大为下降。然而,最近研究者发现,一些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学校仍在以极低的薪资,聘用不叫“代课教师”的代课教师——“临聘教师”。这些人员往往学历很低,并且大都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教师教育。这值得我们认真反思:在不解决合格教师有效供给的前提下,以往那种通过简单行政命令的方式,“一刀切”清理某类人员的做法,究竟其成效如何?
就整体状况来看,当前我国农村教师队伍普遍存在着学历达标率较低、职称结构偏低、学科结构不合理、人员素养不合格等情况。譬如,广东某山区县拥有在编教师4 130余名,其中,高中教师学历达标率为63%,初中86%,小学98%,具有本科学历的初中教师仅占8.2%;全县教师拥有高级职称者为77人;音乐、体育、美术、英语和信息技术学科的教师多为其他学科教师兼任或经短期培训后转任。之所以会出现上述情况,根源就在于农村教师待遇过低。以广东为例,目前珠三角地区的中小学办公教师,月入往往在六七千元以上,高中教师甚至月入过万。而欠发达地区的中小学教师月薪却只有两千元左右,个别地方的公办教师月薪甚至还不足千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巨大的收入落差,必然导致经济发达地区的“人才吸留”效应。于是,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学校就会普遍出现“新人进不来,能人留不住”的窘困局面。研究者多次实地调查皆发现,2000年以后,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学校基本上招聘不到素养较高的教师。甚至出生于这些地方的较高层次的师范院校毕业生,也很少有返乡任教者。与此同时,欠发达地区的骨干教师和优秀校长却又在源源不断地流向经济发达地区。于是,欠发达地区的教育领导者对于较高层次“国培计划”“省培计划”之类的教师继续教育项目,往往怀抱着“爱恨交织”的心态:一方面,他们希望通过高层次的教师培训活动,输送本地的骨干教师出去增广见闻,提高专业发展水平;另一方面,他们往往又担心通过这些培训活动,本地的教师结识到经济发达地区的教师,从而埋下“顺藤摸瓜”而“离家出走”的种子。
如前所述,农村教师队伍建设中的诸多尴尬,其根源即在于农村教师收入偏低。而农村教师收入水平的高低,又直接受制于目前“县财支付”的农村教师工资发放机制。这种机制也是我国现行教育投入体制欠合理的一个具体表现。对于欠发达地区的县级政府而言,更是一笔十分沉重的财政负担。近年来,一些欠发达地区陆续出现了中小学教师为争取更高收入和待遇水平而导致的大规模聚集事件,就已突出地反映出当前农村教师工资发放机制的脆弱性。
面对上述情况,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既非闭目塞听,更非无所作为。相反,自2000年以来,为解决农村教师队伍建设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从中央到地方都在连续不断地出台相应的对策与措施。譬如,2000年全国农村税费改革后,各地政府出台的“教师工资发放县级行政首长负责制”,即从根本上遏制了全国范围内大面积拖欠农村教师工资的现象。到2007年,在要求地方政府清理代课教师的同时,中央政府又出台了教育部所属六所师范院校招收免费师范生的政策,至今已有两届免费师范生毕业后从教。此外,中央政府还出台了“农村教育硕士培养计划”、“中西部农村特岗教师计划”和“中小学教师国培项目”等政策;一些省级政府也出台过“农村教师上岗退费计划”、“城镇教师支援农村教育计划”以及发达地区对口支援欠发达地区的“千校扶千校计划”。就这些政策措施的实际效果而言,可以说,它们都在一定程度上,从某个侧面缓解了农村师资队伍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然而,就整体效果而言,这些政策措施目标并非一致,其影响也常有相互抵牾之处。尤其是这些政策措施往往“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治标不治本,无法有效解决农村教师队伍“新人进不来,能人留不住,整体素养偏低”这一“老大难”问题。
针对这种局面,多年以来,研究者曾在各种场合和向政府提交的咨询报告中,反复提及一个“标本兼治”之策:即进一步加大中央和省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尽快建立欠发达县域农村教师工资保障机制,以实质性地提高欠发达地区农村教师的收入和待遇水平。其具体措施包括:一是提高农村教师工资投放的财政统筹层级,把目前农村教师工资的“县财支付”方式,调整为“省县结合”体制;二是以省级行政区划为单位,根据各地的经济发展状况和消费水平,把全区划分为若干个不同的农村教师工资标准区域;三是在核定全区县级财政支付教师工资能力的前提下,对照该县省定教师工资标准,由省级财政补足县级财力无法支付的差额。只有如此,才能大面积和实质性地提高欠发达地区农村教师的收入水平,避免出现解决“民办教师”问题后又来了“代课教师”,解决“代课教师”后再冒出“临聘教师”之类的现象,进而吸引社会上较高素养的人员到欠发达地区农村学校从教。
二、农村教育经费依然很短缺
1985年5月中共中央颁布《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把“发展基础教育的责任交给地方”。于是,在县域范围内,逐渐形成了县、乡(镇)和(行政)村“三级办学”的局面。在这种体制下,农民通过缴纳农业税费、集资办学款、农村教育费附加、“三提五统”(三项村提留和五项乡镇统筹款)以及书杂费等费用,支撑起了我国实施义务教育之后的农村教育大厦。当年粉刷在农村学校斑驳土墙上的醒目标语——“人民教育人民办,办好教育为人民”,就直观地揭示出“分级办学”体制下农村义务教育不过是“农民自己办学”的事实真相。越来越沉重的教育负担,是构成上个世纪末期农民负担过重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稳定农村基层政权和社会的稳定,从2000年开始,中央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推行农村“税费改革”政策。这一惠民政策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也给农村教育带来了致命危机,随后全国范围内再次出现了大规模拖欠农村教师工资的现象。为破解这一困局,2001年5月,中央政府出台《关于我国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规定免除乡村两级的教育投入责任,从而确立了“以县为主”的农村教育投入体制。在此体制下,县级财政主要用于保障教师工资的按时足额发放,上级财政转移支付款抵补农村教育费附加减收的经费缺口并用于农村学校的基建投入,书杂费收入用作公用经费以维持学校的日常运作。这就是当时农村教育经费投入的所谓“三保政策”。
然而,欠发达地区县级财政大都难以满足本县教育基本的经费需求,“以县为主”体制有效运作的前提条件在欠发达地区并不存在!有鉴于此,2005年12月,中央决定建立中西部地区农村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其实质即加大对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农村教育经费的转移支付力度。2006年6月,修订后的《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了省级政府统筹规划与实施本地区义务教育的法律责任,从此我国农村教育经费进入“省级统筹”时代。这种体制的实质含义在于:一方面,对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农村教育而言,中央财政开始承担起更大的财政责任;另一方面,对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来说,省级财政应承担起更多的均衡发展农村教育的责任。正是在此背景下,以中央和省级财政转移支付资金为后盾,从2006年秋季开始,我国农村教育开始翻开既免学费又免书杂费的历史新页。
不过,我们更应清醒地看到,农村免费义务教育仍然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上运行。近期调查发现,目前,仍有不少农村学校存在着办学用房紧张、功能场室配备不足、教育教学设施设备短缺、公用经费短缺以及缺乏教研和教师继续教育费用等现象。尤为严重的是,还有不少地方存在着极为沉重的农村教育债务。这些债务主要形成于世纪之交的前后两个十年之间:一是1990年代各地“普九”达标验收,农村地区大量举债建校,后因农村“税费改革”后取消农村教育费附加,造成“普九”建校债务陡然无从偿还;二是自2000年以来,历经“以县为主”和“省级统筹”两次体制调整,中央和省级财政虽然加大了对农村教育经费的专项转移支付力度,但每次体制变迁之后的专项转移支付额度皆无法抵补在原来体制之下经费减收的缺口;此外,上级转移支付的财政专项资金又往往要求基层财政予以经费配套,这就造成了地方政府在财力吃紧的情况下,仍要举债“配套”上级财政专项资金的局面。上述几个方面的因素叠加起来,致使农村教育债务越滚越大。可能会令人大感意外的是,即便在经济总量、财政、税收和居民储蓄总额连续多年均居全国第一位的广东,截至2012年初,据不完全统计,全省农村义务教育债务仍达50多亿元。[2]如果上级财政对此“作壁上观”,那么,这些债务就永远难以如数清偿。
针对上述问题,中央和省级政府并非无动于衷,而是通过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等政策措施,对欠发达地区农村教育加以扶持和帮助。就现有情况看,我国的财政转移支付资金主要包括三类情况:一是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主要是根据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前三年内下级财政上缴上级财政的平均额度来确定;二是专项转移支付资金,主要用于抵补2000年农村“税费改革”后基层财政农村教育费附加以及2007年农村义务教育免费后书杂费减收的缺口;三是财政专项资金,主要用于解决上级政府较为关注的教育热点问题,如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农村学校信息技术教育设备装配和农村中小学校舍安全改造等,都曾设有财政专项资金。从上述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运行效果来看,虽在中央政府确立对中西部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之后,中央和省级财政对农村教育的转移支付力度都在不断加大之中,然从总体上看,我国的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还存在着以下突出问题。
首先,财政转移力度与农村教育发展所需资金之间缺口较大。现有转移支付资金数量不足,经常让人产生“杯水车薪”的感慨。譬如,多项实地调查皆发现,在2000年农村“税费改革”之后,上级财政拨付的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往往无法抵补基层财政农村教育费附加减收后的经费缺口。[3]同样,在2007年农村义务教育免除书杂费后,上级财政仅按普通中小学的生均公用经费标准拨付高等级学校减收的书杂费缺口。[4]由此,每次改革之后,农村学校就有“雪上加霜”的感觉。其次,现有转移支付制度有待进一步完善。如现有财政专项资金的设置较为随意、相关部门及其主管人员资金管理权限过大、专项资金运作不够规范、资金使用效益偏低等现象较为普遍,极易造成滋生腐败的温床。再次,转移支付资金的拨付方式欠合理公平。譬如,不少财政专项资金往往要求基层政府给予经费配套;最近一段时间,不少地方又兴起“以奖代拨”政策。由于欠发达地区县级政府财力不足,就很容易导致或虚假出资,或举债配套,或干脆不再申请相关的专项资金等不良现象。这类资金拨付方式对欠发达地区既不公平,更不利于扶助欠发达地区发展农村教育事业。最后,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的后续监管乏力。目前,一些地方也在尝试通过“县、市(区)党政主要领导基础教育实绩考核制”和“收支两条线”等途径监管相关资金的使用情况,但因缺乏更加切实有效的监督措施,在一些地方,针对“专款专用”要求,甚至出现了“专吃专款”的调侃说法。
为切实缓解农村教育经费长期短缺的困境,学界一向主张必须尽快建立起基于公共财政体制之上的公平合理和法治长效的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针对上述现行问题,我们认为,在强化“省级统筹”体制的前提下,可考虑采取如下具体措施:一是科学测算欠发达地区农村教育经费缺口。上级财政部门可在各县现有财力及其发展潜力的基础上,根据当地农村教育发展的经费需求量,测算出未来若干年内该县农村教育经费的短缺额度。二是加大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根据上述经费缺口额度,上级财政部门实质性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的财政资金数量,同时,把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并入一般性转移支付之中,并逐步裁减和压缩财政专项资金项目及其额度。三是强化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的绩效考评。可尝试引入“第三方评价”和采取财政资金竞争性分配等方式,加强对财政转移支付资金使用成效的绩效评估,并把评估结果与后续转移支付额度直接挂起钩来。如能采取上述改革措施,农村教育经费长期短缺的局面或可稍加缓解,农村教育方有可能奠定较为扎实的物质基础。
农村教师队伍建设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归根结底,皆跟农村教育经费投入不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经费投放的多寡,既与农村教育投入体制变迁的“倒逼机制”相关,更与教育事业相对于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发展的“边缘化”位置结缘。[5]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速乃至最终完成,我国农村教育问题必将渐次展开并不断得以破解。待到我国大多数居民都已进入城镇地区居住和生活之际,农村教育的“人财”问题即将得到一种“釜底抽薪”式的解决。当然,到了那时,随迁入城的农民工子女能否真正平等地享有教育权利,则会成为另一个重大的教育和社会问题。
[1]方征,葛新斌.我国编外教师问题及其政策启示.教育理论与实践,2010(8):32-36.
[2]冼伟锋.广东农村为化解农村义务教育债务向债权人劝捐.南方农村报,2012-03-31.
[3]葛新斌.兴宁农村费税改革后教育状况分析——以教育经费变动为中心.开放时代,2003(5):83-97.
[4]张霞珍.免费义务教育:政府亟待处理的三对关系——基于广东省某县义务教育经费的调查.教育发展研究,2008(7):35-38.
[5]葛新斌.农村教育:现代化的弃儿及其前景.教育理论与实践,2003(12):37-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