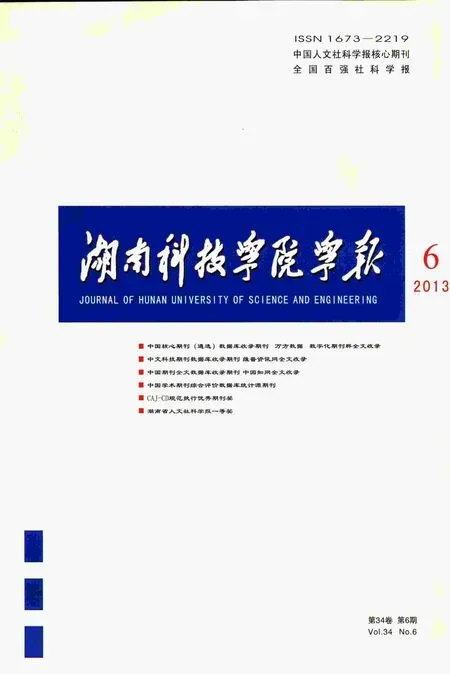神以守形 顺其自然——庄子养生之道刍议
2013-04-07胡梦琳罗浩波
胡梦琳 罗浩波
(喀什师范学院,新疆 喀什 844007)
养神之道可以从养神和养心两方面来论述。养神是从心理上调节,通过怡养心神,调摄情志、调剂生活等方法,从而达到保养身体、减少疾病的目的。养形是在养神的基础上进行身体锻炼以求达到增进健康、延年益寿的目的。养神和养形的兼固使人拥有了健康的体魄从而可以长寿。描述慨括人的生命活动整体的哲人很多但庄子应该是最早从神形方面来论述的。《庄子·徐无鬼》有“劳君之神与形”。庄子把人的生命存在按照物质与精神划分正好对应人的形体和精神。同时认为两者又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区分影响的关系。庄子正是着重于神形两方面来阐述养生之道的。相对于养神和养形两方面,庄子更重视养神。《庄子·刻意》曰:“纯素之道,唯神是守。”
一 明白事理与内敛葆光
庄子谈养生首先就是摆明人的位置,把人从唯我独尊的狂大中转变到自己在宇宙中沧海一粟的渺小之感。而现代人却少了对大自然的敬畏感更多的是满足个人私欲对自然的破坏及对生命的漠视。庄子极其珍视生命,他认为只有明白事理,淡然处之,才能保重身体,保全本性。庖丁解牛是说庖丁为文惠君表演解牛,技艺高超身手不凡。他解牛的过程像是一个漂亮的行为艺术,从把牛牵上到其麻木到使牛的十二经脉瓦解,筋骨分离,整个过程环环相接丝丝入扣,让一旁的文惠君看得眼睛发直,赞不绝口!而庖丁只是解释为熟能生巧,从解牛时看到整个牛到看到牛的结构以及最后的闭上眼就能下手肢解,都是顺着牛的自然结构去解牛,而不会硬来,这样按其规律明白事理掌握技能就可以做到。即循着牛的天然结构,依着空挡,按其天理,顺顺当当,自然而然,游刃有余。在庄子看来,人为了沽名钓誉而做坏事就正如刀刃触及牛体的硬骨一样,会伤及己身。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当我们在生活压力之下,当我们被社会角色所规范并且不切实际的追名逐利时,我们是不是已经被束缚了本性而浑然不知呢?贪欲往往折损了人的本性,使人成为物质的奴隶。人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如果一个人没有意识到生命的本初,不能够明白事理那就必然会做出损性而伤命的事情,这与庄子的养生观是背道相驰的。
庄子认为只有明白事理保持内心的恬淡清静,以淡漠自然的态度去面对,才能淡然处之才有利与养生。在这方面,庄子与古西腊的悲剧文化又有共同之处,那就是面对苦难的世界,而以审美心胸来提升人的精神世界。通过这则寓言,庄子也告诉我们:只要你心中有大境界,你才能够看清超越言行的内心真正的质地。也就是说,内心里面的这种真正的大道、大辩、大仁、大廉、大勇,一切都不是表露与外的,是内敛与心而不张扬的。这种内敛于心却又能涵泳天地万物的地方,庄子说,叫做天府,是天地万物的府库。这天府里无限博大,就好像你往里加水永远不会满,从里面舀水,永远不会枯竭,你不知道它源头是哪里。庄子说:“此之谓葆光。”葆光是什么呢?就是你内心保全的、潜藏不露的一种大的光明。你心中有大境界,才能拥有这种大光明。它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普照万物,光芒永在。从认识你自己,到倾听你自己,到涵养、孕育你自己,这是一个美好的人生历程。每一个人都拥有一个天府,每一个人都拥有一种葆光的能力。到这个时候,人就不以外在的事功来看待自己的能力同时遵循内心的本初意愿,这无疑是领略到养生的根本。
二 相濡以沫与相忘江湖
庄子对相濡以沫这一道德行为的态度是有所保留的所以他说“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崇尚自然主义,强调个体价值的庄子对于孔孟理想中的相互扶持仁义道德的画面微有颇词。对于这些令人有点窒息的关爱使他产生了深深的不信任。由此可见,儒墨所谓的仁爱、兼爱在庄子这里是行不通的,他所强调的是主体自处之道,强调的是不因世俗价值或规范戕害自身生命的完满。那么仁义之说、礼乐制度的繁荣正是由于人们疏远了淳朴的天性,缺失了天赋的道德,没有了自然流露的情感,才导致了其兴起。在庄子看来孔墨身体力行的道德说教只是在给世人强加限制和规矩,就如同春蚕吐丝,作茧自缚;飞蛾扑火,自取灭亡。这也正如困于岸边垂死挣扎的鱼却仍陶醉于那些看似温情脉脉的相呴、相濡之恩,实在有点自欺欺人。当君臣、父子、夫妇、长幼之间几乎都是赤裸裸的利害关系时,那仁义的虚华外衣不正如相濡以沫场境所能提供的那一点点有限的水分!所以庄子认为与其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也许认为儒家墨家也是反对巧言令色和临丧不哀,也很注重人际交往中的真情。相反,庄子道家的老死不相往来,相忘于江湖却是极其的冷漠无情。但如果仅仅这样来理解儒道的分歧就是没有明白问题的核心与关键。问题的本质在于,儒墨爱人利人,这已经先把自我与非我对立了起来,已经违反了自由律;儒墨预先假定了要为别人做好事,这就以经在名利之中。由此可见庄子的“相忘于江湖”可称之为“不仁之仁”、“不义之义”。庄子反对从爱憎出发建立道德信仰,不强调为别人服务的动机,也不强调利他主义的效果,这种动机与效果都是外在的。对与孔子的“立人”、“达人”,庄子提出了“圣人”的概念。因为“利人”“达人”是站在了人伦教化的立场,因此带有制礼作乐的固执;而庄子的“圣人”是重视个体精神的独立,要作圣人就必须取消任何价值判断的。所以,最高的动机和效果无须刻意表现出来,圣人“为而不恃”,无心插柳柳成荫,只要客观上符合了事物的内在尺度,这就是人的最高道德。同时庄子特别向往上天入海的境界,乐于描述出游儵鱼的从容自得,这也折射出庄子选择“相忘于江湖”境界的必然性。从另一方面看,我们现代人生活的物欲横流的社会何尝不是个流动的、让人捉摸不定的甚至有点险恶的江湖,我们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好执着的,相忘反而是一种更好的状态。因此我们更应该具备好的文化心态,明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而不是要求人们如何资源补救,如何患难与共。我们应该构建一个使每个人都能充分地享受到自我发展所需要的资源的空间。大家为创造繁荣富足、公正和谐而宽松自由的社会空间而努力,从此没有为了争夺资源而产生的算计之心和争斗之心,有的只是超然大度之心和悠然自得之心,此时的相忘无疑也是一份洒脱之情。老庄也许并非真正淡漠于人际感情,而是痛感社会人际关系的虚伪,宁可与之背离。他的高度理性的精神境界背后,其实是有深挚热烈的人文情怀的。
三 薪火相传与鼓盆而歌
庄子在《养生主》里说:“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大意就是油脂在柴火上烧完柴火也燃尽了,但火种却可以传续没有穷尽的时候。”在当今社会人类的寿命已经远远超过远古,但在心理上对生命的留恋和对死亡的畏惧却也更胜于从前。当今人的生活中有太多的难言之隐和牵绊纠结,生又何欢死又何惧的心态对我们来说更是难得。庄子在《大宗师》篇推崇的是真人,所谓的真人就是不知道喜欢生命,即出生了他不欣喜;也不知道害怕死亡,即死去了他不抗拒。真人存活于世的标准就是不会有意做什么去辅助天然更不会因为心智的欲求而逆天而行。“若然者,其心忘,其容寂”,“喜怒通四时,与物有宜而莫知其极”。真人就是心里能忘怀一切容貌宁静淡然,有这与四时相通的性情,对生活可以坦然应对的人。借助真人的描述也传达了庄子对死亡的态度是既不找死也不怕死。这对于我们现实生活中因受到挫折或压力就心理失衡而采取对生命最草率的处理就选择轻生的人又何尝不是一种应该学习的做人境界。
《庄子·至乐》:“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就更是体现了庄子对生与死的解悟与超脱,这是了悟大道、达生至乐的庄子至极的作为。在这里,庄子似乎是在最不应该的时刻和场合作出了令人最不可思议的举动,故惠子说:“与人居,长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而当其狂歌之际,不择时地、不择乐器,丝竹可,鼓盆也可,唯取其顺口达情而已。庄子之所以能够笑谈生死是因为他已通达生死之理不再为生死之变而产生悦生恶死之情,他是真正窥透人生之究竟、达到人生极高境界的人。在庄子看来,死亡只是自然归律的一种,人的生命本是上天赐予的,而死亡则是上天收回了自己的赐予。现代人要学会达到通达生死的境界,要明白个体生命的生死现象的本身,就是父母没征求我们的同意把我们带到这个世上,那么流光要把我们的年华带走是我们更加无能为力的。凡是通达生死的人才能更平和的去活,这在现代医学中也有案例去诠释,这无疑是养生的精髓所在。
四 循乎天道与回归本性
庄子认为工具革命带来的进步包含对人类的否定与排斥同时物欲导致了人类的灾难。人类和自然关系的异化以及人类智慧强加于自然都不是正当的做法。庄子说,“大道合乎自然”。那么,什么是真正的天地大道呢?大道无非是一种规则。由于我们年龄境遇学养出身的不同就注定了我们的阅历沧桑各不相同,所以别人的经验我们也许有参考价值但更重要的是真正了解自己的内心。庄子说,在天地之间,真正了解自己内心的人叫做善养生者。那么智慧巧谋显然是对人性本然状态的破坏,人类“好知”行为的本质在庄子看来就是在进行着“邪恶”行为,这些行为包括统治阶级的私欲或别的邪恶势力最终必然会给社会带来灾难。现代人总是把是非善恶的观念强加于社会,甚至强加于大自然,这无疑会自食恶果的。庄子所一再强调的至德之世和真人,从本质上讲的就是人的本真之性。后人所理解的真人是和“神仙”相提并论究其根本是没有理解庄子所并隐喻着人的本真之性。庄周无意泯灭人的智慧,但他不赞成以抽象的知与名将世界二元分割。他认为,人的最大不幸在于人自己,在于人精神上的遮蔽,以及由此产生的人的异化。
如果人人都在与天斗地斗人斗甚至自己斗的涡流中转圈,那么生活的本然面目,天道本性必然会被严重破坏。《应帝王》中的一则寓言更有着深长的意味: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倏与忽时相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通过这则寓言我们是否也领悟到“天道忌满”的真谛,这仿佛也给人类文明发展前景抹上了浓烈的悲剧色彩,似乎预示着越过于完满的改造就越接近于毁灭。这也是庄子在警示后人无论出于怎样的动机,运用多大的力量来改天换地或者人为的去把人改造成什么样子,只要是违被了自然与人的本性,实际上就是自取灭亡。天道是没有原因的是变化无常的,它存在于无际无涯的空间和无始无终的时间里,我们是不可知的,所以就应有对自然的敬畏之心要循乎天道。人类的慧智微不足道,想穷尽其理,必致心志迷乱,终无所得。所以庄子有句名言“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庄子·养生主》)同时庄子肯定主张做个心性顺随自然的人,他授予我们一副混沌的眼镜,一种难得糊涂的生命境界,也就是间接授予了我们自保天年的生存艺术。
五 抱神以静与调和阴阳
庄子提倡的养形的根本是抱神以静,也就是保持寂静的心理状态,不过度劳累精神,这样形体就不会疲劳。《庄子·在宥》说:“无视无听,抱神以静,形将自正。必静必清,无劳女形,无摇女精,乃可长生。”也就是告知我们要想要形体自然而然地正,那就必须先要把精神归于沉静,只要内心保持安宁清静,形体才可以长生。《庄子·外物》说:“静然可以补病,眦城可以休老,宁可以止遽。”庄子也是给我们现代人提供一种神气恢复最快捷有效的方法,即保持双目不左右流盼,闭目养神,就可以心神安定,防止衰老。《庄子·天道》说:“静则无为……无为则俞俞,俞俞者忧患不能处,年寿久矣。”当我们不再那么忧心重重躁动不安疲于奔命之时,生命也会呈现出宁静安好悠然自得寿比南山之状。庄子的怀疑主义为最高的认识和自由的境界扫除了世俗认识和偏执的障碍,知觉的方法则是通向自由的必由之途,“心斋”、“坐忘”则是具体的修养方法。《庄子·人间世》中有“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收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万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也就是说,了解一事物,如果以耳来感应就会执着于耳;如果以心来感应,就会执着于心。最理想的状态是以“气”来感应,因为“气”是无形的,所以不会以任何形式来制约人对“道”的理解。“心斋”就是要自虚其心,回复心灵本来的明净。庄子借用颜回的回答,指出“坐忘”就是要忘记自身,忘记知识,超越于认知之上,达到心对道的体悟,从而达到精神的绝对自由。坐功,静坐以求精进修为,这有点中国特色。此法最终目的是使心灵空虚寂静,即达到“心如死灰”的境界,使人的意识活动停止游思浮想。最终使人的机体生命活动免除干扰,那么人体生命活动就可以按其固有规律正常运行,最终达到养生长生之目的。
再者,庄子的养生论是以阴阳学说为基础的,他明确的强调阴阳调和对养生的重要性。《庄子·则阳》说:“阴阳者,气之大者也。”《庄子·秋水》说:“自比形于天地而受之于阴阳。”不管是在一般事物的存在状态中还是人的心理状态中都存在阴阳。对于事物存在,阳表现为刚强,阴表现为柔弱;对于心理状态,阳表现为喜悦,阴表现为哀怨。“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庄子·天道》)“以巧斗力者,始乎阳,常卒于阴”(《庄子·人间世》)。由此可见,庄子认为天地万物的生成变化过程有一个条件,即阴阳二气在一种合乎秩序的相互作用下完成。故防治衰老,贵在调和阴阳,而阴阳调和了才能流通气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二者相伴,贯通周身,熏濡百节,流通则生机正常,滞塞则淤结病生。《内经》也说“生之本,本于阴阳”,又说“阴平阳秘,精神乃治”。所以,调和阴阳则精神充旺,邪不能侵,得保健康。调和之道,须顺时以养阳,调味以养阴,使阳气固密、阴气静守,达到内实外密、健康有寿。例如:《素问四气调神大论篇》也提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这种“顺时摄养”的原则,就是顺应四时阴阳消长节律进行养生,从而使人体生理活动与自然界变化的周期同步,保持机体内外环境的协调统一。那我们就应该要学学庄子描述的彭祖,做到饮食得当,身体锻炼适宜,养心养气,淡泊名利,平和心境,调和阴阳,最终我们就能长寿。
总而言之,庄子学派思想是中国古代养生学中的宝贵遗产,他告诉我们人类的生命活动是遵循自然界的客观规律而进行的,人体自身具有与自然变化规律基本上相适应的能力,如果人能掌握其规律,主动地采取各种养生措施适应其变化,就能避邪防病,保健延衰。以上大概梳理了庄子养生之道的脉络,希望对于当今人体养生科学的发展有一定的借鉴作用。我们应当认真汲取庄子学派养生思想中的精华,从而让现代人从中参悟一些道理来让自己诗意的栖居于这个纷扰的世界。
[1]张立新.先知的智慧:比较视野下的先秦思想文化精华[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
[2]刘笑敢.庄子哲学及其演变(修订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