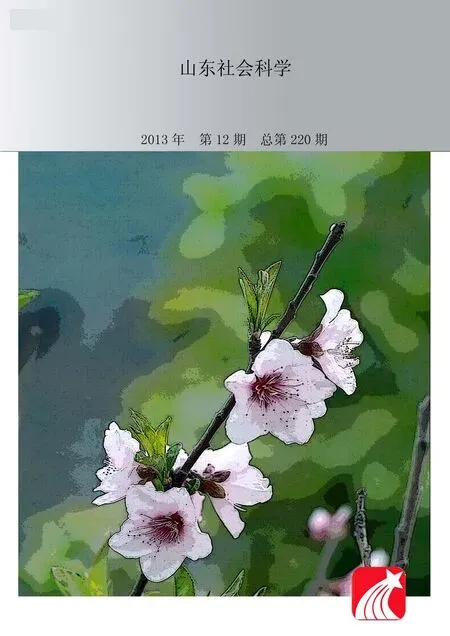托克维尔的局限与法国革命中的“病毒”
2013-04-07童圣侠
童圣侠
(浙江大学 光华法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08)
“我觉得在法国大革命的病变中有某种特别之处,但我无法很好地描述并分析它的起因。这是某种新的、未知的病毒。世界上的暴力革命有很多,但法国的大革命者那种过度的、剧烈的、激进的、绝望的、鲁莽的、几近于疯狂但又强大而有效率的特征,在我看来,在过去许多世纪的社会动荡中是没有先例的。这个新的狂热来自哪里?谁造就的?谁让他们如此有效率?谁让他们经久不衰?……为了清晰了解这个对象,为寻找准确描绘这个对象的方式,我绞尽脑汁。除了大革命中所有已被解释的东西之外,它的思想和行动中还有某种未曾解释的东西。我能感到未知的东西在哪里,但我很徒劳,不能揭开蒙在这上面的幕纱。我仿佛通过一个陌生的东西来摸索它,这个东西妨碍我去触摸它或认识它。”①[法]托克维尔:《政治与友谊:托克维尔书信集》,黄艳红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289页。这段话出自1858年托克维尔写给其好友凯戈莱的信件,它向我们展现了托克维尔晚年在进行《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后续研究中所面临的困境。②在《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前言中,托克维尔给出了他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之后的研究计划:“从思想上说,我已着手的这部著作不应到此告终。倘若有足够的时间与精力,我的意图是透过这场漫长革命的起伏兴衰追踪这些法国人……注视着他们随着种种历史事件而变化、改造,却丝毫不改变的本质。……首先,我要和他们一起经历1789年的最初时期,……在简要追溯这场大革命的进程时……然后,我将考察这个社会本身……最后我试图推测我们的未来”。结合上述引文,这个计划留给我们的问题是,托克维尔在计划的哪里遭遇了困境,以及为何会在那里遭遇困境。这有助于我们看清托克维尔之困境的实质。参见[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32-33页。他觉察到某种大革命的“病毒”,这种“病毒”是大革命的动力,且是使大革命具备其特征——狂热、有效、经久不衰(持续性)——的关键所在。值得注意的是,他在两年前已经完成了他自诩为“要阐明,这场在几乎整个欧洲同时酝酿的伟大革命为什么爆发于法国而不在他处,为什么它好像自发地产生于它即将摧毁的社会,最后,旧君主制怎么会如此彻底、如此突然地垮台”③[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32页。的论著《旧制度与大革命》,也就是完成了对大革命之原因的解释。因此,我们可以说托克维尔在两年之后,在他之前的解释(旧制度之外的)之外,在“与当时的人一起来体验大革命”④在与凯戈莱的通信中,托克维尔在阐述他在进行《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后续研究方法,即研究大革命本身的方法时说:“这是我特别想描述的,随革命的发展而在社会状况、制度、思想以及法国人的风俗中渐次产生的变迁,这就是我的主题。为了看清这些,到现在为止我只找到了一种办法,那就是通过阅读在某种意义上与当时的人一起来体验大革命的每个时刻……”。参见[法]托克维尔:《政治与友谊:托克维尔书信集》,黄艳红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289页。之中,发现了新的大革命的关键动因。这表明,至少之前的方法和解释已无法揭开这种“病毒”的面纱。这是托克维尔的局限所在,也是托克维尔之困境的原因。若无法揭开其面纱,之前的方法和解释就存在致命的缺陷,以至于我们只能片面地理解或甚至无法理解法国民主进程之动荡的一般原因。因此,本文试图通过对托克维尔之局限,即其解释和方法的缺陷的分析,来发现“病毒”之所在,进而认识这种“病毒”,最终理解法国“民主病”之症结。
一、《旧制度与大革命》中革命的“缺场”
既然这种“病毒”处于托克维尔的解释之外,那么我们就必须了解托克维尔的解释本身的界限。首先要明确的是他写《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动机和问题意识,这有助于我们理解这本书的意义。在1850年托克维尔给凯戈莱的信件中,托克维尔已经开始思考他将要写的著作的题材。托克维尔的出发点是对当代问题的思考。“法国1848-1851年间短暂的革命循环与1789-1799年间更长的革命周期之间的相似性启发了他。”[注]张茗:《从美国民主到法国革命——托克维尔及其著作》,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96页。他把“1789年至今的巨大时间范围(我一直称之为法国大革命)”[注][法]托克维尔:《政治与友谊:托克维尔书信集》,黄艳红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192页。视为一个整体进行反思。他把1848年革命视作1789年大革命的延续,并且试图从大革命和拿破仑中寻找1848年革命和路易·波拿巴的原因、结果和未来。[注]这样的观点,同样可见于托克维尔给斯托菲尔的信:“在1789年、1815年、1830年,人们都认为,法国社会受到暴力病症的侵害,但病症过后,健康的社会肌体会变得更有活力、更加持久。今天我们看得很清楚,这是一种慢性病,它的起因更为深刻,它的发作是间歇性的,存在的时间要比人们想象的长久。这不是某个政府不可能的问题,而是任何一种持久的政府都不可能的问题,我们注定要长期摇摆在专制主义和自由之间,无论哪一方我们都不能长久维系之。”参见[法]托克维尔:《政治与友谊:托克维尔书信集》,黄艳红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160页。我们同样能在《托克维尔回忆录》中找到相同的观点。“这是又重新开始的法国大革命,因为人们向来是这样看的。”参见[法]托克维尔:《托克维尔回忆录》,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00页。这样的考量赋予了《旧制度与大革命》不同的意义,它不仅背负着解释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使命,更是背负了解释法国这种经久不衰的革命动力以及革命所造成的绝对主义后果的使命。对这种使命的理解是我们理解《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前提,也是我们对其进行评价的标准。它要探求的是法国“革命——专制”循环的一般原因,以及其中的历史连续性。
其次,《旧制度与大革命》的解释逻辑是我们发现托克维尔的解释之局限的关键所在。《旧制度与大革命》旨在揭示大革命之所以发生的一般原因。在1836年,他撰写的《1789年前后法国社会政治状况》一文中,他已阐述了其对法国大革命的基本思考:“即使没有这场革命,革命所作的一切也会产生,对此,我深信不疑;革命只不过是一个暴烈迅猛的过程,借此人们使政治状况适应社会状况,使事实适应思想,使法律适应风尚。”[注][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317页。可见,在托克维尔看来,革命是一个寓于历史必然性中的特殊现象,并且没有其自身的原因和价值。革命仅仅是社会民主化过程中的一个特殊的环节,所有的动机和结果都在旧制度中,并且革命仅仅是一个“整理、协调和法制化”的过程,即便它确实创造了什么,也只是一些“次要的事物”。这样的判断虽然从不同的角度解释了革命的意义,却使革命的动因变得更加模糊了,以至于托克维尔只能用“奔向自由的更强大的新冲动”[注][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313页。来充当这种必然性突变的动力。
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托克维尔对大革命进行了类似阐述:“它决不是一次偶然事件。的确,它使世界措手不及,然而它仅仅是一件长期工作的完成,是十代人劳作的突然和猛烈的终结。即使它没有发生,古老的社会建筑同样也会坍塌,这里早些,那里晚些;只是它将一块一块地坍塌,不会在一瞬间崩溃。”[注][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61页。因此,革命本身再次遭到抹杀,中央集权的完型似乎就成了革命的终点。我们可以大致这样归纳托克维尔的观点:中央集权化的过程剥夺了贵族的政治自由,这也是旧制度中唯一拥有政治自由的阶层。因此,这意味着中央集权消灭了旧制度中几乎所有政治自由的因素,以至于在贵族没落、社会日趋平等化的过程中古老的自由精神完全失去了传承并消失殆尽,剩下的便只是个人主义的败坏。不同的阶层和团体仅考虑自身的利益,人与人、团体与团体之间的联系日渐疏远,对他们之间不平等的仇恨与嫉妒日渐滋生,这尤其表现在贵族与第三等级之间。最终在三级会议的摩擦中,一种仅剩的、病态的、基于自身利益和平等诉求的自由精神点燃了这场史无前例的革命,并彻底确立了“中央集权——个人主义”的政治社会形态。在该论述中,托克维尔赋予了革命一定程度的实质动力:个人主义的败坏导致了个人、阶层和团体之间的分裂与对立。他几乎把革命描述为了一个利维坦产生的过程。尽管托克维尔进一步完善了他对革命的阐述,但革命本身始终缺乏独立的意义,其动因完全寓于历史必然性中。革命在这样一本旨在论述革命的论著中“缺场”成为了托克维尔理论中的奇观。革命事实上成了托克维尔对革命的解释理论的界限。
最后,尤为重要的是“民情”这一概念(尽管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民情概念出现次数并不多,但却无处不在)。其重要性大致体现在以下两个问题之中:第一,为何中央集权制在革命之后得以存留?乍看之下,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表达了革命前后的中央集权制存在当然的承继关系,但我们认为革命前存在中央集权制的事实并不能理所当然地成为革命后产生中央集权制的原因。同样,个人主义社会的中央集权倾向也不能成为革命后产生中央集权制的充分条件,这仅仅是一种倾向和可能性。其中需要某些条件使这种可能性实现,托克维尔对此的解释大致有两点。一是在上文中提到的自由精神的缺失,二是革命后人们对秩序的渴望。前者是主要原因和一般原因。当然,这里所谓的自由精神属于民情范畴,因此它才能成为解释革命的一种持续、客观的因素,中央集权制好像一遇到革命就隐藏到了民情中,革命后才自动显现出来。第二,托克维尔在对革命的动因进行最终的解释时引起的疑问。无论是在1836年的文章中,还是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托克维尔最后都把革命归咎于“自由精神”的迸发。事实上,尽管制度、社会状态等等赋予革命以客观基础,但这些毕竟不能解释人们的普遍激情和革命理想。革命“意味着一种更强调主动性和偶发性的唯意志论角度”[注][波]彼得·什托姆普卡:《社会变迁的社会学》,林聚任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91页。。因此,托克维尔才必须用“自由精神”来解释革命的发生。但托克维尔巧妙地赋予了这种“自由精神”以客观性,并将它以民情(如民族性格、民族特征)的形式纳入到社会学范畴,不仅解决了革命的唯意志论特点,也解决了革命之经久不衰的一般原因。同时,民情产生于漫长的历史环境,和革命也就自然没有什么瓜葛了。以上两点揭示了“民情”在托克维尔理论中的重要性,它把历史发展中人之行为的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结合为一体,在历史客观性的基础上赋予其可变性(这种变化是渐次而缓慢产生的),使托克维尔可以合理地回避革命的偶然性,从而跃过革命强调革命前后的历史连续性。民情概念最终几乎完美地帮助托克维尔把革命本身排除在对革命的解释之外。
二、托克维尔的局限
革命的“缺场”使托克维尔在一些问题的解释上并不足以让人信服。这主要体现在解释革命动力的持续性以及1848年革命时的牵强附会。正如傅勒所指出的:“既然大革命已通过执政府的行政宪法奠定和完成了旧制度的大业,为何还要有1830年、1848年这些补充的革命呢?”[注][法]弗朗索瓦·傅勒:《思考法国大革命》,孟明译,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232页。若革命本身没有其独立的动力与意义,那么当外部动力终结之时,革命也就不会再发生。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寻求革命的持久动力的一般原因,自然要诉诸一种历史循环论。托克维尔也在不同的场合表达了这种对法国未来的判断。[注]参见[法]托克维尔:《政治与友谊:托克维尔书信集》,黄艳红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160页。但很显然,这种万劫不复是托克维尔不愿意接受的。因此,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末尾作出了或许连他自己都无法说服的解释,他诉诸“对自由的酷爱时隐时现,再隐再现”和平等激情的“始终如一”,诉诸“对立、极端、任由感情摆布的民族性格”。而这种民族性格与他一贯反对的“种族论”[注]关于对“种族论”的批驳,可详见托克维尔在阅读了戈比诺的《论人类种族的不平等》后给他的信件。参见[法]托克维尔:《政治与友谊:托克维尔书信集》,黄艳红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226-229页。却有异曲同工之处。最大的悖论还在于,他最终似乎在其所忽视的地方找到了他要寻求的答案。
傅勒早已指出托克维尔理论中“革命”缺场的问题。他认为“在起源与结果之间,在路易十四和波拿巴之间,有一页空白。托克维尔没有写出这一页,他提出一些问题,但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为什么旧制度和新制度之间的这种连续程序走了一条革命的道路?在这样的条件下,革命者的政治投资又意味着什么?”[注][法]弗朗索瓦·傅勒:《思考法国大革命》,孟明译,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35页。傅勒在一定程度上把该问题归因于托克维尔的治史方法,这种治史方法既赋予了其独到的洞察力,也使他丧失了一部分洞察力。马克·布洛克的那句名言“通过过去来理解现在,通过现在来理解过去”是对托克维尔的最佳注解。当代的问题始终是托克维尔关注的焦点所在。把对当代问题的思考融入对历史的思考中,以获得对过去、现在与未来的进一步理解,这是托克维尔运用的基本方法。从托克维尔对1848-1851年的反思中我们也几乎可以看到他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所有的思考痕迹,[注]详见[法]托克维尔:《托克维尔回忆录》,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96-97页,以及[法]托克维尔:《政治与友谊:托克维尔书信集》,黄艳红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153页。甚至会让人以为托克维尔仅仅是把对当代的思考直接应用到了对大革命的解读中,并以此来支持他对法国历史之整体的把握。另外,托克维尔写给凯戈莱的信件中所说的研究困境也让我们体会到托克维尔的研究方法:最大的困难是“由本来意义上的历史与历史哲学掺杂在一起造成的。……我担心它们会彼此损害,担心我没有那种取舍材料——这些材料应支撑我的思想——所必需的高度才能”[注][法]托克维尔:《政治与友谊:托克维尔书信集》,黄艳红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193-194页。。
治史方法上的得失是显而易见的,对史料的应用和对历史的分析包含了作者的所有假设、前见和意图。而在此之外的因素,将遭到理所当然的忽视。这是一个建构历史的过程,根据问题的不同,历史也将具有不同意义。因此,托克维尔对革命本身的忽视也将变得可以理解。不过治史方法上的得失在这里不宜被理解为局限,因此问题仍没有解决。托克维尔似乎付出了代价,却仍没有弄清楚他自己提出的革命原动力的问题。反而在遭其忽视的革命之中隐约感受到了那种关键的动力。那么合理的解释就是托克维尔的假设、前见或是意图本身就存在问题。
“中央集权制——个人主义社会”是托克维尔的基本逻辑,也是自王朝复辟以来理论家们对法国政治社会现状的基本判断。大革命摧毁了所有的旧社会纽带,但未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纽带,导致了社会原子化。社会原子化使得除了中央政府之外,没有人能够承担公共事务的责任,因此,出现了两极化的趋势,个人退回私人领域而政府扩大权力范围。这是包括托克维尔在内的当时大多数自由派人士的忧虑之处。他们因此希望以对社会的研究为基础构建政治科学。我们发现这一逻辑的背后存在几个问题:旧有社会的纽带被摧毁的同时,社会是否没有建立起新的纽带?若社会没有建立起新的纽带,一种即便是非常短暂但稳定的政治社会秩序是否可能?进一步地,人们何以认可中央政府及其行径?在英国自由主义者看来值得追求的状态,在法国自由主义者眼里却是社会瓦解的态势。这一方面说明了他们所面对的问题的不同,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他们考虑问题时可能具有片面性以及个人主义所具有的多种维度。前者注重哲学维度而忽视社会维度,后者则恰恰相反。法国大革命所产生的一套与旧社会全然相异的话语体系和意识形态被托克维尔视作民情的产物和激情的迸发而遭到忽视。就好像大革命之后,人们回到了霍布斯的自然状态,而拿破仑乘虚而入篡夺了主权。革命没有创造什么,只是摧毁了什么和保留了什么。因为在托克维尔眼里,制度、社会、民情才是真实存在的,而观念、思想、意识仅仅是前者的产物而不具备自身独立的逻辑。他在论述18世纪的哲学家们的观念如何形成时说:“他们这些思想是眼前的那个社会自身的景象向他们自然提供的。”[注][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81页。社会唯实论和保守主义的理论倾向在他那里显露无疑。因此,他无法看到个人主义社会中的纽带和基础,无法看清在完全脱离了真实社会的大革命洪流中的扩张力量。对他而言,一切动因只能在大革命之前的制度、社会、民情中产生。或许正因如此,尽管托克维尔确实发现了意识形态的问题,却仍服从于“社会”的叙述而对前者保持沉默。[注]傅勒在书中提到托克维尔曾在《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笔记片段中洞见了革命意识形态的动力性质。参见[法]弗朗索瓦·傅勒:《思考法国大革命》,孟明译,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231页。可惜,“大革命的起源是一回事,大革命则是另一回事”[注][法]达尼埃尔·莫尔内:《法国革命的思想起源(1715-1787)》,黄艳红译,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437页。。大革命中不仅有起源,还有大革命本身以及大革命的遗产。而法国革命的“病毒”,正如托克维尔自己所说的,还在大革命的“思想与行动”中。
三、法国革命中的“ 病毒 ”
至此,我们必须到托克维尔止步的地方寻找法国革命的“病毒”。傅勒在这里找到了奥古斯丁·古参(Cochin)。他认为:“托克维尔探求的是(历史)连续性的秘密,古参则考察(历史)中断问题。”[注][法]弗朗索瓦·傅勒:《思考法国大革命》,孟明译,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278页。古参致力于探索雅各宾主义的核心。他认为“雅各宾主义是一种社会政治组织类型完成了的形态,这种社会政治组织是18世纪下半叶在法国传播开来的”,古参称之为“思想社会”[注][法]弗朗索瓦·傅勒:《思考法国大革命》,孟明译,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248页。。傅勒认为这种“思想社会”是“一种社会化形态,它的原则是,其成员要想在里面扮演角色,就必须去掉自身的一切具体特征,去掉自己真实的社会存在。……它预示了民主的运转机能。因为民主也是在一种足以建构个体的抽象权利中使个人平等化的,这种抽象权利就是公民身份,它涵盖并确定了每个人的人民主权的份额”[注][法]弗朗索瓦·傅勒:《思考法国大革命》,孟明译,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249页。。可见,“思想社会”是一种全然不同于传统社会的社会形态。我们说它预示了民主的运转机能,不如说它本身就是民主政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种新的合法性基础。当真实社会的一切差异和等级都被否定后,政治必须在抽象层面建立认同和共识或者说意识形态,这就是“思想社会”的作用,它是所有形式的民主政治所必须具备的,也是托克维尔无法觉察到的地方。而法国的特殊之处在于“思想社会树起来的是一种纯粹民主范式”[注][法]弗朗索瓦·傅勒:《思考法国大革命》,孟明译,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252页。。纯粹民主范式消除了政治与社会的一切距离,也就是说,它使原本可与真实社会保持一定距离而发挥统合作用的“思想社会”完全替代了真实社会而发挥作用。这种极化过程使原本仅仅是意识形态的东西成为了真理,而“思想社会”则成为了超然的存在。“思想社会一旦上升到其曲线的最高点,就变成了一个政党,自命代表社会和国家,处于对等地位。”[注][法]弗朗索瓦·傅勒:《思考法国大革命》,孟明译,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256页。“人民”就成为了这个“政党”。这是雅各宾主义的确立过程。然而,纯粹民主仅作为意识形态,尚不足以发生足够的影响,它还必须获得权力。因此,在古参看来,是纯粹民主挑选了雅各宾的领袖们并统治了国家;是“思想社会”以人民的名义开启了一种“清洗机制”,而粉墨登场的各路领袖只不过是纯粹民主逻辑扩张过程中不断被拣选的代表者。他们要做的仅仅是根据共识划分社会阵营并清除反叛者,从律师和神甫到斐扬派和吉伦特派,他们最终背叛了雅各宾主义,最后由罗伯斯庇尔和圣茹斯特促成了雅各宾主义的完型并终结了这一过程。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没有人能够控制革命。这是贯穿于大革命过程的逻辑,也是一个否定的逻辑和在否定中寻找肯定的逻辑。“人民”最终只能在简单粗暴的否定中确认自己并统治自己。至于纯粹民主的来源,古参始终未加以回答,也不在他的理论视野之内。
古参展现的是法国大革命的动力机制。他发现了大革命的创造,即“思想社会”与雅各宾主义。它们不仅弥补了托克维尔理论的空缺与局限,也显示了意识形态在革命中的强大动力。但对于我们的问题而言,由于古参不同于托克维尔,他的理论焦点仅仅集中于大革命本身,因此,他的研究成果是否可以用来解释法国经久不衰的革命动力尚需检验。若能够用于解释我们的问题,我们必须探求在1794年寿终正寝的雅各宾主义是以什么形式潜伏在之后的历史之中的。但是古参把大革命中的斗争和矛盾完全简化为雅各宾意识形态的扩张过程,使他忽视了这个过程中与雅各宾主义相对抗的观念,忽视了托克维尔所关注的传统因素,因此他无法理解为何1789年首先会出现主张代议制的观点。
虽然古参的理论焦点限于大革命,但上文的论述中已提及,在他的理论中其实揭示了民主社会所必需的新的认同机制和意识形态,也就是“思想社会”。包含公民身份和人民主权的一整套意识形态或者说是话语体系成为所有近现代政治社会凝聚力的核心。尽管法国“思想社会”的极化导致了深重的苦难,但并不能否定它在现代民主国家中不可或缺的地位。而 “思想社会”的极化,也就是雅各宾主义中包含的深刻历史原因。古参并没有追问形成纯粹民主的过程,其仅仅说它是在1750年前后形成。傅勒对此进行了简短的分析,认为它在卢梭那里得到了最系统的界说,并为革命话语作了准备;而在托克维尔那里,它可能被视为法国长期以来绝对君主制和启蒙思想的产物。可见雅各宾主义不仅包含了“思想社会”的特征,也包含了法国的传统因素。毋宁说大革命所创造的是一种新的形式,传统的、现代的思想和观念在其中得到了筛选和重组。大革命是经这种筛选和重组的极化模式,而之后的法国史也在很大程度上是这种不断的筛选和重组的过程。也因此,大革命的幽灵才有可能在革命后的法国历史中不断地重现。
由此可见,法国革命的“病毒”不仅在于这种新形式,还在于这种形式下的筛选和重组的过程。古参把纯粹民主视为大革命时期这种筛选和重组的结果,并称之为雅各宾主义。但事实上即便是罗伯斯庇尔也未曾用纯粹民主来表达他的愿望,并且他还曾经抨击“那些希望建立‘纯粹民主……’的人”[注]Pierre Rosanvallon,The History of the Word ‘Democracy’ in France, translated by Philip J. Costopoulos, Journal of Democracy, 1995, 6, pp.148.。至少在1793年以前,民主与纯粹民主在语义上几乎没有区别,当时的人们始终将民主等同于纯粹民主,并视之为无政府主义和混乱的源头。因此,在当时人们的理解中,他们追求的并非民主。西耶斯赋予代议制以正当性基础并使其区别于民主政体,而布里索则通过定义“共和制”来与直接民主相区分,民主在他们看来始终意味着古希腊与古罗马,意味着自由人与奴隶,法国不适合也不能进行这样的实践。可见,无论是西耶斯还是布里索,无论是高额的纳税选举制还是两级选举制,他们在追求人民主权和公民理想时,始终试图把这种理想仍旧束缚于现实的基础之上。因为他们知晓,古典的纯粹民主、公民理想是以粗暴的排斥和牺牲为基础的,他们希望建立一种温和的区分标准以满足现实与理想两方面的诉求。但很显然,在1789年绝对的人民主权形象随着西耶斯发表的著名设问“第三等级是什么?是一切”确立时,现实的束缚已是不可能了。所有的法国人都希望拥有政治表达的权利来成为这个“一切”的一部分,成为公共意志的表达者,使自己成为自己的主人,从而实现自我的解放与统一。所有问题都转化为了政治问题。这是“思想社会”形式的内在动力。因此,用波考克的话来说,大革命就是一个“亚里士多德的公民理想”不断摆脱“盖尤斯的法律公民(臣民)”的过程,也是一个人自我从物质、社会现实和历史传统中解放出来的过程。[注]参见[英]波考克:《古典时期以降的公民理想》,许纪霖编:《知识分子论丛》(第二辑),吴冠军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4-55页。最终这种冲突在一个民选领袖的卡里斯玛中暂时得以共存。而当卡里斯玛遭到瓦解时,冲突则会再次显现出来。
在大革命之后,人们都在致力于终结大革命,并为大革命的原则套上缰绳。贵族思想早已在“思想社会”中被排除,“中间体”[注]这里借鉴法国当代学者皮埃尔·罗桑瓦龙先生的“中间体”说法,泛指介于国家和个人之间的各种社会或政治形态(比如协会、行会、工会、政党、地方政府、民间的各种自律组织等等),类似于“公民社会”概念。参见[法]皮埃尔·罗桑瓦龙:《法兰西政治模式:1789年至今公民社会与雅各宾主义的对立》,高振华译,沈菲、梁爽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引言第13页。也随之遭到遗弃,可资利用的似乎只剩下启蒙思想。而政治理性主义正是启蒙思想在政治领域中的体现,它企图在政治与社会中间划定一条温和的界线,并把一切的理想和激情放逐到社会和物质利益之中,把政治的统一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以遏制雅各宾式的公民理想。但这仅仅是回避了问题,而非解决了问题。社会现实所固有的不平等将会以社会问题的形式重新激发公民理想的激情。可见,政治理性主义的代表们其实是企图用另一种社会虚构来束缚大革命的原则,公民在这一虚构的社会中只意味着所有权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被称为是“现代人的自由”。他们虽然自诩以社会为基础构建政治制度,但正如罗桑瓦龙所评价的,对于他们而言,“社会联系显得像是一种建构,而不仅是一种前提条件”[注][法]皮埃尔·罗桑瓦龙:《公民的加冕礼:法国普选史》,吕一民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139页。。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法国人实则在用一种乌托邦对抗另一种乌托邦[注]罗桑瓦龙把基佐的理性自由主义视为一种自由的雅各宾主义也说明了政治理性主义学说的乌托邦色彩。参见[法]皮埃尔·罗桑瓦龙:《法兰西政治模式:1789年至今公民社会与雅各宾主义的对立》,高振华译,沈菲、梁爽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170页。,他们企图在大革命的“思想社会”中置入其他的原则以缓和大革命的意识形态,但显然乌托邦之间不可能达成任何调和。他们所做的毋宁说是在构建另一种理性主义的意识形态以压制大革命的意识形态。这是两种关于“公民——社会——国家”的想象,它们分处社会现实的两端,无法与社会现实相契合。因此,他们始终是不稳定并且容易互相转化的。托克维尔对此可能会说:“法国人对普遍体系的崇尚使得他们难以在两者之间获得任何妥协。”诚然,对普遍体系的崇尚是前提,但对普遍体系的崇尚并不足为惧,令人畏惧的是普遍体系的社会化和意识形态化,而当一种解放的逻辑与激情在其中迸发时,革命也就势不可挡了。至此,或许我们能粗略地理解法国革命的“病毒”所在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