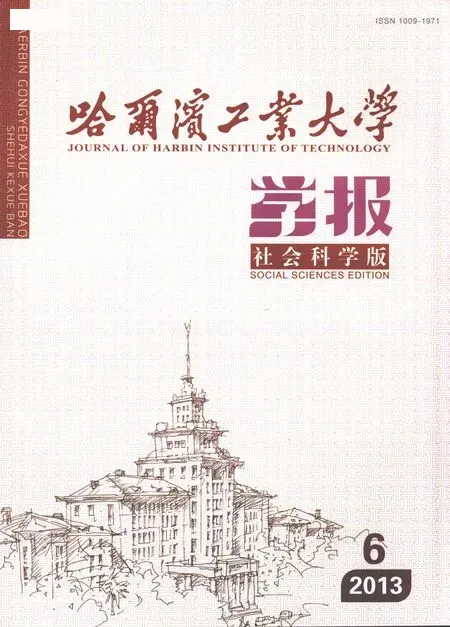西江流域水神崇拜文化的生态根源
——以蛙崇拜与蛇—龙母崇拜为例
2013-04-07申扶民
申扶民
(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南宁530006)
·生态文明建设·
西江流域水神崇拜文化的生态根源
——以蛙崇拜与蛇—龙母崇拜为例
申扶民
(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南宁530006)
西江流域的水神崇拜文化源远流长,影响深远。其中,最为典型的是以蛙崇拜和蛇—龙母崇拜为代表的水神崇拜文化。水神崇拜文化根源于西江流域以水为主导的生态环境。蛙崇拜根源于稻作生产的自然生态以及族群繁衍的社会生态;蛇—龙母崇拜根源于“水事”生态以及族群认同的社会生态。西江流域的水神崇拜文化孕育于西江流域以水为主导的生态环境,以形象的方式见微知著地反映了人类文明与生态环境的紧密关联,是西江流域生态文明的文化表现形式。
西江流域;水神崇拜;生态文明
人类文明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一定的生态环境,因此,从发生学的意义上来说,任何人类文明模式都是某种类型的生态文明。①今天人们所谓的生态文明,通常是指狭义的生态文明,即工业文明所导致的生态环境问题引发人们对生存和发展模式的反思,进而提出超越工业文明的可持续发展的新型文明理念。作为一种理想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意味着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的和谐共生、永续发展。而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任何人类文明形态都产生于一定的生态环境,就此而言,人类所有不同模式的文明都属于广义的生态文明。纵观世界各地的人类文明起源,大都发轫于江河之畔。尼罗河之于古埃及文明,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之于古巴比伦文明,恒河之于古印度文明,黄河之于古华夏文明,莫不如此。水是生命的源泉,人类择水而居,文明因水而兴。以水为主导的生态环境孕育了人类最早的生态文明模型。由于人类文明肇始于江河流域,水神崇拜成为文明初始阶段具有普遍性的一种文化现象,与水密切相关的一些动物通常被人们崇奉为神灵。骆越民族所栖居的西江流域,江河纵横,水神崇拜成为骆越文化的一个标志性元素。其中,最为典型的当属蛙崇拜和蛇—龙母崇拜,它植根于以水为主导的生态环境,是西江流域生态文明的突出文化表现形式。
一、蛙崇拜的生态根源
作为水神而被广西西江流域的先民顶礼膜拜的蛙,与人们的稻作生业模式须臾不可分离。稻作活动因水而存在,在长期的稻作过程中,人们发现水稻的生产和蛙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神秘的因果关系,后者主宰着稻谷的丰歉与否,因而逐渐树立起蛙的神灵地位。与稻作生产相伴随的是人类自身的繁殖,对后代瓜迭连绵的渴望与蛙强盛的生殖力之间的人蛙同构,在社会生态层面树立起蛙以始祖图腾的崇高地位。随着稻作文化的发展,蛙崇拜的艺术表现既成为骆越民族的独特文化标识,也是这一族群对所处环境生态适应的形象体现。
(一)蛙崇拜与稻作生产的自然生态
水稻耕作自古以来就是广西西江流域的一项重要生产活动。温暖的气候、丰沛的水源、肥沃的河谷平地等生态环境的天时、地利因素,为水稻的生产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是稻作文化得以产生和发展的生境。一方面,根据考古发掘,广西西江流域是世界上最早培育水稻的地区之一;另一方面,与稻作农业密切相关的以“那”(“水田”之义)冠名的地名在这一地域极为普遍。据考证,带有“那”字的地名,“就广西而言,70%以上集中在左、右江流域。这些地方的土壤、雨量、气温、日照等都宜于稻作”[1]。由此可见,适宜的生态环境是稻作文化源远流长的根基所在。
在稻作农业的生态链当中,水是一个关键性的生态因素。顾名思义,水稻因水才有稻。水的存在,既是天时的产物,又是地利的结果。天上行云布雨,地上江河纳水,滋润土壤,孕育万物。稻因水而生长,人因稻而生存,三者处于生态系统的不同生态位,在“水→稻→人”这条生态因果链上,水是根源。而水的根源又在哪里?在漫长的稻作活动中,骆越先民给出了自己的解释,那就是蛙。在他们看来,蛙声、雷鸣以及雨水之间存在着某种神秘的内在关联,于是,在万物有灵的原始思维里,蛙被幻化为主宰雨水的神灵。根据壮族的神话传说,蛙是雷神的儿女或使者,代表天上的雷神在地上掌握着滋养万物的甘霖。为了祈求天降甘霖,五谷丰登,人们一方面将雷神人格化,天空是硕大的肚子,云朵是憋在肚子里的尿,电闪雷鸣是撒尿的动作,下雨便是尿流到了地面。因此,在稻作生产中,因需要雨水而祈祷雷神的祈雨仪式就应运而生了。另一方面,更为具象化和更为人们所熟悉的蛙,在各种节庆活动中备受尊崇。作为雷神派驻人间的“雨水使者”,蛙成为以歌求雨的蚂里歌的唱诵对象,“大年初一敲铜鼓,请蚂进村同过年。让它(蚂)坐上大花轿,全村男女庆新年。……从此年年降喜雨,从此月月雨绵绵。人畜安宁五谷丰,欢乐歌舞落人间。”[2]壮族人们以最重要的礼器铜鼓,来恭请蚂过最重要的节日新年,从经久不衰、流传广远的歌谣来看,这绝非一时一地的偶然现象,而是具有深厚民族心理积淀的文化表现。蛙之所以在壮族人们当中享有至上的礼遇,究其缘由,乃是因为蛙使得“年年降喜雨”、“月月雨绵绵”,才有“人畜安宁五谷丰”的好年成。
(二)蛙崇拜与族群繁衍的社会生态
生物圈中的众多生物种群,唯有人类种群既具有自然性,又具有社会性。在社会生态位上,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而形成群体生活模式的不同族群。因此,人类自身的生产和物质生产具有同等重要性。在稻作文化中,蛙不仅作为主宰水稻生长的自然生态因素的神灵而存在,而且也作为稻作民族自身繁衍的社会生态因素的图腾而存在。长期以来,稻作农业一直是一种需要投入大量人力资源的生业模式,因而稻作文化中人自身的繁衍与水稻生产就显得同样重要。对于骆越先民来说,稻作活动中最直观的丰殖形象莫过于水田中的累累稻穗和成群蝌蚪,在他们的神性思维里,水是养育稻谷和蝌蚪的乳汁,而生命的乳汁最终是由蛙所掌管的,因而蛙又被视为具有无可比拟繁衍能力的女神。
人们只有生育众多、人丁兴旺,才有可能既延续自身族群的世代相传,又维系稻作文化的生生不息。在这种情况下,蛙的形象由掌握水稻生产的水神向操控人类繁殖的神灵转化。壮族民间称蛙为“娅圭”(意为“蛙祖母”),很明确地将其作为始祖来尊崇。这种“人蛙互渗”的始祖图腾文化源于先民的原始思维。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列维—布留尔运用“互渗律”来解释原始先民的思维模式,“在原始人的思维的集体表象中,客体、存在物、现象能够以我们不可思议的方式同时是它们自身,又是其他什么东西。”[3]69-70壮族先民将原本异己的蛙视为同类或者说将自身引为蛙的同类,并且在辈分上将蛙尊奉为祖先,而自己甘做蛙的子孙后辈,人与蛙可以相互转化,融为一个共同体。这一看似荒诞不经的现象恰好就是图腾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一切图腾形式的社会都容许这样一些包含着图腾集团的成员个体与其图腾之间的同一的集体表象。”[3]70通过蛙图腾的“人—蛙”同一表象,作为始祖的蛙将旺盛的生殖力传承给作为子孙的人,从而达到瓜迭连绵、多子多孙的生育目的。在壮族传统的蛙婆节上,第一个找到青蛙的年轻男性被认为是雷神的女婿,即蛙婆的郎君,通过与雷神、蛙婆的姻亲关系,以求获取如同蛙一般的强大生育能力。西江上游的红水河流域,不少地方供奉着蛙婆的塑像,状貌多为孕妇的形象,其生殖崇拜的意图显而易见。
蛙作为自然界的一种生物和生态链上的一个环节,在骆越先民及其后裔的崇拜中,被神化为主宰稻作生产和族群繁衍的神灵,其无边法力来自水(乳汁),在它的哺育下,五谷才能丰登,族群才能兴盛。因此,蛙崇拜在西江流域的深远影响,就在于它作为稻作文化生态根源的象征。
(三)蛙崇拜的艺术表现及其生态意涵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宣称:“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的武库,而且是它的土壤。”[4]这说明,神话是其他艺术滥觞的母体和原型。对于西江流域的骆越先民来说,神化的蛙也正是该族群艺术创造的一个重要源泉,艺术也成为蛙作为稻作文化生态根源的一种形象揭示。其中,最具地域和民族特征的蛙崇拜艺术表现形式莫过于崖壁画和铜鼓。
位于西江上游的左江流域,是崖壁画分布最为密集的地方。据《续博物志》记载:“二广深谿石壁上有鬼影,如澹墨画。船人行,以为其祖考,祭之不敢慢”[5]。从两广现存的崖壁画来看,该书所载应当归属于左江流域,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花山崖壁画。花山崖壁画画面宏伟,作为画面载体的巨幅悬崖峭壁矗立于明江之畔。画面上布满了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图像。其中,为数众多的一种造型几乎雷同,只是在形体大小、身体朝向方面有所不同。观其姿态,表现的是一种群体舞蹈的图腾祭祀活动。形体高大、正面挺身的舞蹈者,上肢张开曲肘上举,下肢叉开屈膝半蹲;形体较小的舞蹈者侧身面向前者,亦步亦趋地模仿前者翩翩起舞。从舞蹈动作来看,这些形象正是人蛙互渗的蛙图腾表现形式。花山崖壁画所处的左江流域,恰好是最早种植水稻和以“那”命名最集中的地区之一。因而,以蛙图腾为主要表现内容的崖壁画在这一区域最密集,就具有逻辑合理性与历史必然性。花山崖壁上的“人蛙”形象,作为骆越先民的图腾艺术,通过对蛙神的顶礼膜拜和动作模仿,以求稻作生产的风调雨顺以及后代繁衍的人丁兴旺。因此,以花山崖壁画为代表的蛙图腾艺术,以一种形象的方式诠释了稻作文化依存于自然的生态根源。
铜鼓是骆越先民最卓越的艺术创造之一,不仅历史悠久,而且使用极为广泛。就地域分布而言,骆越铜鼓“以左江—邕江—郁江—浔江两岸及其以南地区最为密集”[6]30。由此可见,铜鼓在广西西江流域被人们普遍使用。那么,何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有学者指出:“我国的铜鼓艺术是与稻作农业联系在一起的,它是源于稻作农业的一种艺术。”[7]这一论断是有充分理由的,最具说服力的就是铜鼓上的蛙形象。事实上,这一地区的铜鼓也通常被称为蛙鼓。蛙的形象而非其他物种形象被装饰于铜鼓之上,既非纯属偶然,也非蛙较其他动物形象更为美观,而是因为蛙被奉为稻作文化的神灵。因此,饰有蛙形象的铜鼓被人们当作法器,用于祈祷神灵的护佑,以求五谷丰登、人丁兴旺。即便是研究铜鼓的外国学者,也深谙蛙鼓的神灵象征意义,“铜鼓饰以蛙的图像,通常都与水,特别是与咆哮着的急流中的水神联系,当铜鼓被打击时,发出隆隆的雷声,激动人心。铜鼓也象征着主宰丰收的自然神,能保证农业丰收,居民繁衍。蛮人把铜鼓埋在土中,是希望天上的雷与地下的水接触,使水流得更快,土地得到灌溉”[6]85。从铜鼓的蛙形象构造特征来看,许多鼓上铸有叠蛙塑像,几只蹲踞的蛙层叠而上,其姿态多为交媾状,看似色情的构型实则寓意生命的繁衍。因此,以铜鼓艺术为载体的蛙崇拜,也是反映稻作文化生态根源的一种符码。
二、蛇—龙母崇拜的生态根源
揆诸史乘,骆越之地大部归属于西江流域。史书多称其为化外瘴疠之地。然而,江河纵横、林深草密、地广人稀的所谓“南蛮”之地,却是千里沃野,孕育了与中原文化风格迥异的骆越文化。从文化发生学的角度来说,最初的差异源于地域生态环境的不同。尽管都发轫于江河之畔,中原文化和骆越文化均有“蛇—龙”水神崇拜,但在由自然物种“蛇”向幻化神灵“龙”的转化过程中,二者却产生了重大差异。前者形成了君权神授的皇权龙图腾,后者衍化为利泽天下的龙母。二者的歧异根源于各自自然与社会生态的不同。对此,本文不做探究,主要考察西江流域骆越文化当中蛇—龙母图腾的生态根源。
(一)蛇—龙母崇拜与“水事”生态
南一环站、芜湖路站均为主体宽约13 m的岛式站台车站,两层三跨结构;覆土厚约3.2~4.1 m,底板分别位于粉细砂层和强风化泥质砂岩中。高架主桥桥墩承台高2.5 m,置于车站顶板上。水阳江路站为主体宽度为11 m的岛式站台车站,车站为双层双跨矩形框架结构;覆土厚度约3 m,底板位于黏土层,高架匝道桥桥墩置于车站顶板上。三站均位于车水马龙的城市主干道上,车站周边高楼林立,最近的高层建筑距车站基坑仅约5 m。合肥轨道交通1号线芜湖路站与高架桥同位合建单平面如图1所示。
1.蛇崇拜与“水事”生态
历史上的广西西江流域,属于南蛮腹地。此地的骆越先民也因此而被视为未开化的蛮人。他们的族源自然不同于中原的华夏先民,根据许慎《说文解字·虫部》的解释,“南蛮,蛇种。”[8]由此可见,蛇是南蛮族群的的共同祖先,蛇成为他们共同的始祖图腾。为何蛇与蛙一样会成为骆越先民崇拜的对象?究其根源,还是在于人们所生存的生态环境。从这一地域的自然地理条件来看,由于“陆事寡而水事重”,“于是民人披发文身以像鳞虫”[9]。这说明,骆越先民的栖居空间是以“水事”为重的水居环境。在这样的生态环境中,人们的劳作活动大都与水有关,江河之畔的耕作或江河之中的捕捞活动,都使人置身于水环境当中。除人之外,蛇(鳞虫)也是生存于江河水域的一种重要生物,并且它的存在对人身安全构成了潜在甚或实际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之下,人们为了化险为夷,通过图腾崇拜,将蛇由不祥的危险之物转化为护佑的始祖神灵。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将自身“拟蛇”化,或“披发文身以像鳞虫”,或“断发文身以像龙子”,通过身体上的局部特征肖似蛇,不以“像鳞虫”、“像龙子”为耻,反而奉蛇为祖先。看似屈尊纡贵的行为,实则出于自我保全的策略,消解来自自然界的威胁,化生态链上的凶险环节为安全壁垒。从人类生态学的角度来说,这是人类在生物圈中的文化生态适应的一种典型体现。这种一厢情愿的企图不一定会产生实际的效果,但至少在人们的心理层面筑起了一道安全屏障,这对于先民而言比什么都要重要。
根据考证,广西西江流域的蛇图腾发端于以大明山为核心的区域。大明山是西江上游的重要水源地,水系发达。考古发掘资料表明,环大明山地区是骆越先民活动的一个重要据点,出土的蛇图腾石雕证明了骆越民族是崇拜蛇的。沿袭至今的民俗生态也从不同侧面反映了蛇图腾文化的深远影响。如这一地区的壮族人忌讳捕杀和以蛇为食,是视之为崇奉对象的;壮族民间的“三月三”歌圩也源于蛇图腾崇拜,大明山脚下武鸣县马头镇廖江流域,是广西西江流域历史最为悠久、规模最为宏大的歌圩之一,每逢节日,祭祀活动的盛况蔚为壮观。因此,无论是从历史文献、考古发掘,还是从经久不衰的民俗活动来考察,骆越先民及其后裔的蛇图腾文化,都源自这种“水事重”的生态环境。
2.龙母崇拜与“水事”生态
西江流域的蛇崇拜有一个显著的特征,那就是由最初的蛇转化为龙,最后上升为对人格神龙母的崇拜。流传于西江上游骆越古国核心地带的大明山地区,以及西江中游古苍梧郡的龙母传说都是由蛇的故事开始的。根据民间传说,大明山下的一位“娅迈”(壮语,“寡妇”之义)在野外发现一条快被冻僵的小蛇,遂生爱怜之心,将它带回家喂养。小蛇逐渐长大,屋里容不下它了,“娅迈”只好砍断它的尾巴,并给它取名“特掘”(壮语,“秃尾巴”之义)。“特掘”的身躯越长越大,食欲也越来越旺盛,“娅迈”已难以养活它,就被送到河里放养,变为“掘尾”龙。“娅迈”去世时,掘尾龙突然出现,将她安葬于大明山。此后每年的三月初三,掘尾龙都会回到大明山为“娅迈”扫墓。当此之时,天降甘霖,正好滋养了春天耕种的作物。人们认为这是“娅迈”无私的母爱得到了掘尾龙的感恩回报,洒下甘霖,滋润着这片它生长的故土。人们因此而对“娅迈”感恩戴德,尊奉为龙母,并建龙母庙祭祀,“娅迈”也由此而被拟神化,成为骆越民族的崇拜对象。至今,环大明山地区仍留存有不少龙母庙或龙母庙遗迹,它们大都位于发源于大明山的河流之畔或两河交汇之处。这当然不是偶然的地理巧合,而是一种必然的文化现象。因为河畔的土地正是人们最密集的耕作区域,风调雨顺是作物能否丰收的关键所在,这取决于龙母的恩泽,所以人们就会在此建庙供奉衣食之母的龙母。
根据多数史料的记载,西江中游的龙母事迹,最初流传于今广东境内西江流域的悦城境内,龙母祖庙至今还屹立于西江与悦城河交汇之处。刘恂在《岭表录异》中记载了龙母故事的原型,“温媪者,即康州悦城县孀妇也,绩布为业,尝于野岸拾菜,见沙草中有五卵,遂收归,置绩框中。不数日,忽见五小蛇壳,一斑四青,遂送于江次,固无意望报也。媪常濯浣于江边。忽一日,见鱼出水跳跃,戏于媪前。自尔为常。渐有知者。乡里咸谓之龙母,敬而事之。”[10]这则龙母故事与大明山龙母故事的相同点就是龙母都是年老的寡妇。这一地区另一有代表性的龙母传说来自《太平寰宇记》:“昔有温氏媪者,端溪人也。居常涧中捕鱼以资日给。忽于水侧遇一卵大如斗,乃将归,置器中,经十许日,有一物如守宫,长尺余,穿卵而出,因任其去留。稍长五尺,便能入水捕鱼,日得十余头。稍长二尺许,得鱼渐多。常游波中,滢洄媪侧。媪后治鱼,误断其尾,遂逡巡而去。数年乃还。媪见其辉光炳耀,谓曰:‘龙子复来耶?’……媪殒,瘗于江阴,龙子常为大波至墓侧,萦浪转沙以成坟,人谓之掘尾龙。”[11]979这个故事的掘尾龙则与大明山的掘尾龙相似。从西江流域的三个龙母传说来看,大明山龙母故事的龙母和掘尾龙分别与后两者当中的一个具有相似的对应关系,从中似乎可以推测,大明山龙母传说可能是后者的原型,即西江龙母文化可能是顺着江河的流向从上往下传播的。根据考古发掘的资料,环大明山地区曾是骆越古国的活动中心,以蛇—龙母崇拜为代表的骆越文化曾盛极一时,而包括今天广西梧州地区和粤西南西江流域处于骆越古国的势力范围,骆越文化也必然波及和影响到这些地区。当然,文化传播的结果会因为各种原因而发生变异,龙母传说的不同版本就是一个例证。相比较而言,古苍梧地区龙母图腾文化受水生态影响更为显著。由于流经这一地区的西江水系更发达、水域更宽广、水量更大,龙母文化中所蕴含的“水事”生态因素更为明显。西江中游沿江而下,凡有江河汇流之处,大都建有龙母庙。居民无论是以耕作为业,还是以捕鱼为生,无不对龙母虔敬有加。民间盛行摸龙床、饮圣水等习俗,甚至造船都模仿“掘尾龙”,谓之“龙掘尾”。在人们心中,龙母就是一位“利泽天下”的女神。
(二)蛇—龙母崇拜与族群认同的社会生态
1.蛇—龙母崇拜与骆越族群认同
人类社会的构成,实质上就是一个多元统一的生态系统,从宏观至微观层面,分别由不同民族、种族、族群与个体所融合共生而成。社会生态不仅如同自然生态,与地域环境息息相关,而且为精神层面的文化信仰所左右。相似的自然环境和文化信仰,在根本上铸就了某一地域的社会生态。人类社会初期,相似的自然生态往往会催生相似的神灵崇拜,而共同的神灵崇拜则具有强大的整合社会生态的功能,从而在世界各地产生了各自拥有自身神灵崇拜的民族、族群和部落。
历史上,作为“南蛮”的骆越族群被称为“蛇种”,蛇是他们共同崇奉的始祖图腾。骆越先民的属地,上至西江上游的环大明山地区,下至西江中游的古苍梧地区,蛇—龙母崇拜成为一种普遍的习俗。不少地方都树有蛇图腾石雕塑像,或建造龙母庙,平时香火供奉不断,而在特定的节日里,祭祀活动的宏大规模尤为壮观。长期而共同的神灵崇拜,代代相传,相沿成习,于无形中成为形塑社会生态面貌的文化土壤,整合统一族群的精神纽带,逐渐促成和日益强化人们相互之间的族群认同感。蛇—龙母崇拜在水神崇拜的基础上,转化为以“水事”生态为共同地域特征的人们的共同祖神崇拜。骆越民族就是在蛇—龙母祖神崇拜的基石上日益壮大的。根据考古发掘和史料记载,骆越古国的版图就是骆越民族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的一个日益扩展的空间化认同过程。骆越古国的文化中心坐落于环大明山地区,由此轴心经由西江轴线向西江流域辐射,逐渐形成一个以蛇—龙母崇拜为认祖归宗对象的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骆越王国。而另一方面,从文化心理积淀的角度来说,一旦骆越民族及其后裔作为一个共同体存在,为了强化族群认同,就会有意识地建构一个全体成员认同的文化符号,并通过各种形式进行巩固和延续,于是就有了历久不衰的建造庙宇、祭祀神灵、举办节庆等各种活动,而这正是蛇—龙母崇拜绵延不绝的社会生态根源。
2.龙母崇拜与华夏族群认同
龙母崇拜不仅在骆越民族的族群认同上发挥着强大的凝聚作用,而且在更大范围内起到沟通岭南骆越文化与中原华夏文化的桥梁作用。在文化交流的基础上,骆越民族与中原华夏民族日益认同,最终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多民族融合的格局。
在骆越民族与华夏民族日趋认同的过程中,中原王朝的历代统治者依靠的不仅是武力征服,而且巧妙地利用了文化的怀柔感化手段。这种恩威并重的“胡萝卜加大棒”政策,在客观上促进了民族的认同与融合。历史上,最早用武力征服岭南的秦始皇,同时也是最早在这一地区实施文化怀柔策略的最高统治者。鉴于龙母崇拜在岭南地区的深远影响,秦始皇采取了顺应民意的做法,给予龙母最高的尊崇和礼遇,以促进民族的认同感,这一举措成为扩大和巩固龙母崇拜的社会生态根源。根据《太平寰宇记》的记载,“秦始皇闻之,曰:‘此龙子也,朕德之所致。’诏使者以元之礼聘媪。”[11]979秦始皇将母慈子孝的龙母事迹,归功于自己的德政,并对龙母礼遇有加,从而在自己的统治合法性与龙母崇拜之间建立起因果联系,其结果是一方面巩固了秦朝对岭南的统治,另一方面促进了骆越民族与华夏民族的认同和融合。正如通过开凿灵渠以联结纵贯岭南岭北的水路,秦始皇统一了中国,通过将龙母“利泽天下”的水神形象塑造为“天下归心”的慈母形象,秦始皇促进了民族的统合。此后的历代统治者沿袭了秦始皇的这一举措,使原本源远流长的龙母崇拜由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褒扬而更为根深蒂固,族群认同和融合的社会生态进一步提升了龙母的地位和影响。
在蛇—龙母崇拜与族群认同、融合的相互关系中,一方面,根源于自然生态的水神崇拜促进了具有共同信仰的族群的认同与融合;另一方面,日趋定型和巩固的族群共同体在文化惯性的驱动下,又世代承袭和强化了对文化传统的体认,而这正是蛇—龙母崇拜文化经久不衰的最为重要的社会生态根源。
结 语
西江流域的水神崇拜文化,以形象的方式见微知著地反映了人类文明与生态环境的紧密关联。西江流域以水为主导的生态环境,从根本上决定了人们依存于水的生存方式以及社会形态,并孕育了人们最初的精神产品——水神崇拜文化及其表现形式。由此可以推知,不同神灵崇拜文化的形成,并非随机出现的偶然现象,而是扎根于特定生态环境之中历久弥坚的精神信仰。
[1]游汝杰.从语言地理学和历史语言学试论亚洲栽培稻的起源和传布[J].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0,(3):13.
[2]潘世雄.铜鼓入土原因论[J].广西民族研究,1985,(2):57.
[3][法]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M].丁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13.
[5][宋]李石.续博物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5:108.
[6]蒋廷瑜.铜鼓艺术研究[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
[7]覃乃昌.壮族稻作农业史[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7:97.
[8][汉]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1:789.
[9][汉]刘安.淮南子[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7.
[10][唐]刘恂.岭表录异[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11.
[11][宋]乐史.太平寰宇记[C]//清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配古逸丛书景宋本(影印本).
The Ecological Roots of Water God Worshiping Culture in Xijiang River Basin—Examp les of Frog W orshiping and Snake-Dragon M other W orshiping
SHEN Fu-min
(College of Liberal Arts,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Nanning 530006,China)
The water god worshiping culture in Xijiang River basin,which runs a long course from a remote source and has profound influences.Among them,themost typical are frogworshiping and snake-dragon mother worshiping.The water god worshiping culture is rooted in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dominated by water of Xijiang River basin.Frogworshiping is rooted in the natural ecology of rice planting and the social ecology of ethnicity multiplying;snake-dragon mother worshiping is rooted in the ecology of'water business'and the social ecology of ethnicity identity.Thewater god worshiping culture breeds from the peculiar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Xijiang River basin,and it is the cultural form of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of Xijiang River basin.
Xijiang River basin;water god worshiping;ecological civilization
B933
A
1009-1971(2013)06-0128-06
[责任编辑:王 春]
2013-08-03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广西西江流域生态文化研究”(10BZX081)
申扶民(1973—),男,湖南邵东人,教授,博士,从事美学与文艺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