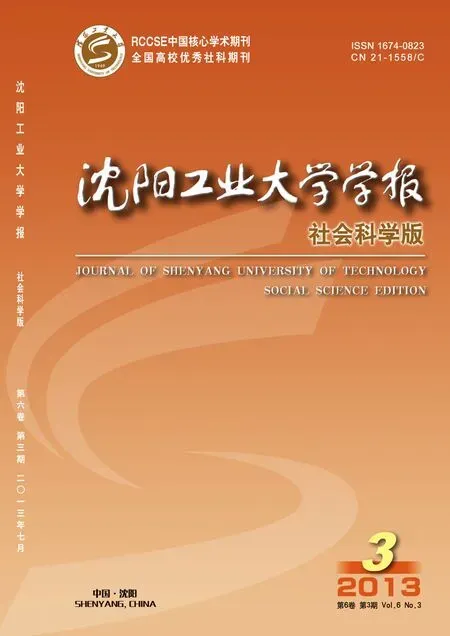从澳大利亚土著文化保护看天津民间文化遗产的传承创新*
2013-04-07王静
王 静
(天津外国语大学 英语学院, 天津 300204)
2008年2月13日,时任澳大利亚总理的陆克文对向曾经遭受不公正对待的澳大利亚土著人及其后代进行了正式道歉,这一道歉被誉为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的“历史性讲话”。陆克文在讲话中不仅就澳过去政策给土著人带来的侮辱和贬低表示深刻反省,也表达了政府想要建立一个平等的澳大利亚的意愿。工党政府这种尊重文化多元性的态度产生了一定的社会经济效益:承认民族文化的现实差异,督促土著人在自身发展中取得更大成就,如积极参与社会和联邦政府事务,发展城市经济,扭转人们对土著生活落后的传统看法;提倡平等、自由和相互尊重的态度,使土著人可以在宽松的社会环境中拥有享有自己的文化传统的权利,比如双语和双文化的教育让更多的土著儿童加强对本民族文化传统的认知,增强他们的民族自豪感;多元文化政策的实施有利于调动土著人和非土著澳大利亚人建设国家的积极性,从而有效缓解因为文化差异造成的民族冲突。
澳大利亚把以土著文明为代表的民间文化遗产作为表现文化多样性的载体,这种推崇和重视文化多样性的做法受到越来越多国家及其政府的关注和支持。作为积淀了600余年历史底蕴的文化名城,中国天津如今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如何通过对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进行保护、传承和创新达到发展城市文化多样性的目的?这已经成为自2010年以来天津市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课题。澳大利亚政府在多元文化政策方面的成功实践,或许可以给在文化的多元共存方面摸索中的天津市一些启示。
一、澳大利亚保护土著文化遗产的成功实践
1. 政府管理和土著参与相结合,有力保护丰富的土著文化资源
到目前为止,土著文化被看作民族、国家文化的代表,它是一种独特的、易于辨别的民族身份的图象志,被视为澳大利亚的文化标签。久远的发展历史、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广阔地域造就的土著文明成为澳大利亚多样化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这种多样性在1788年英国人占领新南威尔士后的200年中一直受到种族主义政策的抑制,土著文明面临几乎被完全同化的危险,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澳联邦政府推行的一体化政策,使土著人“有权决定他们的未来,有权保留他们的民族特点,有权保留他们的独特社会”[1]。一方面,民族意识的觉醒固然能够促使众多土著人重新认识自我在澳大利亚社会中的价值,提高其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从而引起本国社会和国际社会的重视;另一方面,澳大利亚政府以尊重土著文化传统和生活习俗为前提,在推进土著人人口城市化进程、提高土著人教育水平、将土著人经济发展纳入到全澳经济发展事业中所作出的努力也不容忽视。
在政府职能部门的设置方面,联邦政府设有土著事务部,下分设传统处、宣传发展处、通讯和特别服务处以及管理处[2],上至国家针对土著人政策的颁布与实施,下至土著人的衣食住行、教育调控、新闻传媒等,都由土著人自己管理。这种自主管理的方式可以鼓励土著人民积极参与地方及联邦政府政治生活,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提高他们对公民权利的认知,也便于地方政府和联邦政府倾听土著人的声音,在关键时候执行民意。在教育方面,联邦政府通过拨款鼓励土著人开设并管理自己的学校,将双语和双文化列为土著人教育的基本内容,从学龄时期就开始加强学生对本民族文化特点的认识。这种教学手段可以在最大范围的人口中保留和传承土著文化,加强下一代对本民族文化的坚定信念,从而避免“被偷走的一代”悲剧的重演。在经济生活中,联邦政府通过帮助销售旅游产品和土著艺术品等系列措施促进土著聚居地(如北领地行政区)的旅游业,不仅发展了当地经济,也使当地土著居民在生计和生活方面得到保障,更让全世界的旅游者折服于原生态土著文明的独特魅力,从而达到有效保护土著文化的最终目的。在艺术领域中,联邦政府鼓励各类艺术团体的展示和演出,最具代表性的是澳大利亚的国宝级舞蹈团“澳之火”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开、闭幕式上的精彩表演以及2002年在北京上演造成不小轰动的“梦回圣地”舞蹈晚会[3]。
2. 融和不同文明的艺术形式,有效延长土著文化遗产的寿命
作为印澳板块的一部分,澳大利亚大陆长期隔离于其他各板块之外,而土著民族更是在白人到达澳大利亚之前与外界完全隔绝。隔离的地理环境使土著民族没有机会与外民族交融,其民族文明发展的开放度几乎没有,几近完全封闭。正是这些因素决定了土著民族在抵抗外来文化攻击和文化自我修复方面呈现出敏感性和脆弱性。如1788年澳洲沦为英国殖民地以后,原本居住在东南沿海的土著人被强势的欧洲白人文明所驱赶,最终他们“被逼进社会的边缘地带而隐匿于偏远内陆地域”[4];受到进入澳洲大陆的白人所带来的传染病的影响,大量的土著人死于疾病,而且“在欧洲殖民越是集中的地区,人口的衰落就越是迅速……到1888年年底,塔斯马尼亚的土著人已全部死亡,维多利亚州的土著人也几乎死亡殆尽,新南威尔士州幸存的纯土著血统也寥寥无几了。”[5]地域隔离造就的土著文化的脆弱性和敏感性让联邦政府、各类社会团体以及具备民族责任感的土著个人意识到延长土著文化寿命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保护和传承土著文化遗产的同时也应有所创新,这样才能永久保留民族的历史记忆。
目前,众多艺术家考虑的创新在于如何利用非土著的文化载体表达土著艺术精髓。例如,在文学领域中,虽然土著人用“梦创时代”的独特视角阐释自然与人之间的托管关系,澳大利亚的很多日常用语、地名、动植物名称也都带有土著语言的痕迹,但由于土著人只有口头语言而没有书面语言,他们只能采用口头传说、音乐、舞蹈、绘画等其他形式记录自身文明。在这种情况下,在写作语言上土著作家只能采取妥协的态度,即用白人的语言也就是英语来描写本民族的故事。然而,土著作家借用的只是英语这一语言表现方式,在写作过程中尤其是土著女性作家“巧妙地对英语进行改良,使其夹杂大量土著词汇,从而可以更确切地表达土著人的喜怒哀乐”,“她们用改良过的英语讲述土著人的历史,成功地从文本内部对殖民者的叙事方式和语言进行解构,从而赢得了话语权”[6]。又如,土著传统绘画中的“点画”已经成为澳大利亚旅游纪念品的标志性图案,经常出现在杯垫、T恤、笔、日记本上,虽然有人批判这种行为亵渎了原来点画所代表的神圣意义,改变了土著艺术的文化内涵意义,但有一点不可否认,就是这种普及更有助于非土著人接触并了解土著文化,增加土著文明的开放度,也有利于土著人建立全新的民族认知观,长时间地保存本民族的文化记忆。再有,为了弥补土著传统绘画如岩壁画、树皮画、透视画不易长期保存的缺陷,很多土著画家(如阿尔伯特纳玛吉拉)尝试用西方的水彩颜料和技法进行创作,将土著文化的主体与西方艺术媒介创造性地融合在一起;为了使土著音乐能够得到澳洲非土著人甚至世界的认可,1986年成立的“约索印第”乐队就是由土著人和西方音乐人组成,他们使用土著的传统乐器将摇滚和传统的演唱方式相结合,受到了人们的喜爱[7]。所有这些创作者的努力都预示着土著文明和白人文明冲击对立的态势已经成为历史,澳大利亚人乐于以包容和鼓励文化多样性存在的态度来看待社会中两种文明的存在。
3. 司法实践保护土著人传统文化习俗的表达
澳洲土著与大地建立了一种独一无二的托管关系,并将这种关系与自然、精神、道德联系在一起。他们通过各种象征手法表现这种关系,并称之为“梦创时代”。梦创时代在澳洲土著文明中被认为是世界的伊始,梦创时代的信仰基于一条最重要的原则,即生活在澳大利亚大陆上的人们对土地负有特殊的责任——他们属于土地,他们只是受托保管先人创造者的家园。虽然这种信仰在澳大利亚的发展史中曾经不被白人殖民者认可和尊重,一度几乎被剿灭和强制同化,但历史的悲剧在今天的澳大利亚不再上演,自20世纪70年代的一体化政策开始,澳大利亚政府通过自然遗产产权制度强调土著居民享有相对自然文化遗产而言的托管者地位——Matthew Rimmer指出,1993年澳大利亚《联邦原住民土地权法》与1999年的《联邦环境保护和生物多样性保存法》都规定了使用制度:“首先,当土著民拥有合法的土地产权时,其可以控制附着于土地和水源上的生物资源的使用。其次,土著民可以利用土著土地使用协议制度所获得的利益。最后,土著土地产权制度的重点在于许可使用制度”[8]。在开发土著文化保护区的过程中,澳大利亚政府非常“重视保护区当地社区的参与权,创立了遗产开发保护中政府与当地土著社区共同参与的独特模式”[9]。这种模式不仅可以使土著人合理合法地利用当地自然文化资源,更体现了澳政府对土著人信仰的尊重,从而有利于“梦创时代”传说的延续,让土著人在政府政策的保护下继续履行先人赋予他们的责任和义务。
1994年澳大利亚最高法院对昆士兰州Murran-doo Yanner猎捕鳄鱼一案的审理就可以很好地说明当土著文化传统与国家法律相违背时产生的冲突应如何解决。在澳大利亚,野生鳄鱼受到严格的保护,必须持有申请射杀的执照才能够猎取有限数量;而在土著传统习俗中,鳄鱼肉是土著居民获取蛋白质的主要来源之一,鳄鱼皮也是他们制作手工产品的主要原材料。1994年,Murrandoo Yanner在昆士兰海滨一处沼泽猎得两只体长在一公尺内的小鳄鱼,被路过的白人发现报警而被逮捕,被告人Murrandoo Yanner在法庭上宣称,猎取鳄鱼是上天基于精神信仰而赋予土著人的权利,而且他这么做是替他所属的部落(Gunnamulla)获取食物。初审时,地方法官将Yanner无罪开释。但是昆士兰州高等法院的检察官认为Yanner的行为触犯了昆士兰州的法律,因此向巡回法院提出上诉。最终在澳大利亚联邦的最高法院上,陪审的大法官以绝对多数的投票推翻了昆士兰州高等法院的二审裁决,判定Yanner无罪。在土著人口仅占约1%的澳大利亚,这项判例清楚地表明了立法者维护土著文化和精神信仰的态度,也说明了土著文化得到越来越多的澳大利亚人(尤其是以联邦政府为代表的白人文化)的尊重,成为澳大利亚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二、澳大利亚保护土著文化的实践对天津市的借鉴意义
1. 利用政府扶持形成文化自觉
相比其他种族的人口而言,澳大利亚的土著人口仅占人口总数的1%,其人口乃至文化上的弱势地位非常明显。如果没有联邦政府的支持和保护,仅凭存在历史的长久和土著人的自我保护意识,土著文化遗产不可能成为澳大利亚多元文化的一部分,更不可能被誉为民族、国家文化的代表和澳大利亚的文化标签。所以,在保护处于弱势地位的民族文化或当地文化中,政府的扶持尤其关键。从天津的现实层面上看,不论是有形的具有文化价值的城市资产,如五大道地区的小洋楼建筑;还是无形的与传统文化、习俗密切联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杨柳青木版年画、相声、高跷,都随着城市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城市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以及全球化程度的深入而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因此,保存并使民间文化遗产得到传承成为政府部门不可推卸的任务。增加财政投入支持民间文化遗产固然是实际工作的一方面,但政府的提倡、宣传最终使保护民间文化遗产成为社会共识也不容忽视。因为民间文化遗产终究依托文化氛围而存在,有自己的发展空间,即便有再多的资金投入,没有当地民众对于保护事业的认可和支持,文化遗产的保护也无从谈起。目前,天津市已经意识到在市民中普及保护文化遗产意识的重要性,在这方面做出很多积极有益的尝试,如2012年6—12月持续开展的“非遗年”系列活动秉着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的原则,进一步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广大市民尤其是青少年中的认知度;2012年5月17—22日在天津中医药大学举办的“非遗进校园”活动,吸引了众多在校大学生关注文化传统和传统医德之间的关系、中医药文化的历史,青年人对中医药体系中的文化遗产有了更加直观生动的认识;还有自2008年开始在试点小学的音乐课程中加入京剧内容,2012年9月底开幕的天津市青少年美术创意成果展被看作从少年儿童的视角阐释中国传统的年文化等。可见,天津市正在寻找适合年轻一代特点的教育方式来帮助他们认知实践民间文化传统。
所以,要想实现对民间文化遗产的有效保护,政府的角色至关重要,它不仅是文化遗产保护的前台后援,更是使民间文化遗产赖以生存的文化空间得以存续的幕后支持,它可以在更大范围内唤醒公众对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使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得到整体稳定的空间,从而在全社会形成费孝通先生提倡的“文化自觉”。
2. 强调传承人在文化遗产继承中的专属权利
作为文化遗产的支持者,政府必须明确“只鼓励宣传,不强行介入”的原则,因为和全球化进程和城市化速度相比,民间文化遗产囿于其地域限制的出生地和狭窄的发展空间,具有很强的敏感性和脆弱的自我修复能力,一旦政府越过支持和鼓励的底线,强行介入或不科学地推动其发展,民间文化遗产所具备的传统文化特点就可能轻易消失。就像1994年澳大利亚土著人猎捕鳄鱼一案的终审结果向全澳表明了联邦政府对土著文化传统的宽容、忍让和尊重一样,如果一味强调野生鳄鱼稀有而判Yanner违反相关法规,土著文化传统很有可能在之后与国家法律的频繁冲突中无法保持赖以生存的文化空间而走向消亡。正如国际民俗协会中国分会会长苑利所说:“并不是所有的保护都能起到保护作用,……好心的保护也会变成令人痛心的破坏。而且,保护力度越大,破坏的力度也就越大。”[10]因此,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中,除了需要政府尽到支持的责任,公众保护意识的觉醒,还需要传承人的规律传承和以此带动的文化遗产的产业化。
对于传承人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重要性,学者曾经有过以下评论:“只有依靠与这些文化遗产相依为命的真正主人,保护才能有可靠的保障。因此,应该由传承者自己来确立他们的文化当中什么是最值得保护的,并且积极参与保护措施的决策以及这些措施的实施。”[11]35如同土著人Yanne在法庭上强调捕鳄在他们只是为部落猎食而不是追求野生鳄鱼的经济价值一样,作为遗产真正主人的传承者们深谙传承对象的真谛,他们不会为了经济利益对文化遗产,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商业化的操作,因为不当行为会加速文化遗产的灭失。现实层面的天津就存在很多坚守传承素养的民间艺人,而他们的坚守付出也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和经济的回报,如天津市妇女创业中心协助建成的“大郑剪纸”,天津市第一家民营剧团“刘荣升京剧团”,以及传承传统相声艺术的“名流茶馆”等。
因此,文化遗产的科学保护需要各个方面的共同努力,“立法、政府行为、商业行为、个人参与这些因素有效配合”[11],才能真正实现对文化遗产的切实保护和传承。
3. 运用新形式增强文化遗产的影响
当前在我国,民族民间文化的产业化也成为一种趋势,这既是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不断深化的结果,也是我国扩大对外开放、成为世贸组织一员的必然趋势。如今的民间文化遗产已经不可能孤立地存在于狭小的出生地域里了:一方面,劳动价值的追求和产品商品化使得民间文化遗产必须具备一定的商品性价值,否则就会被大众文化轻易吞噬;另一方面,随着旅游业的日益繁荣,民间文化遗产作为反映一个民族或某个地区文化基因的载体,势必走向旅游市场满足其需求,只有按照市场的需求对民间文化遗产进行科学的包装和推广,民间文化遗产才能显露出勃勃生机[12]。所以,如何利用新形式对民间文化遗产进行合理利用成为文化界必须解决的问题。澳大利亚的土著艺术家们运用西方艺术的表现形式延长土著艺术品的寿命,或许可以给天津致力于文化遗产保护的人们一些启示。比如,杨柳青年画中的胖娃娃抱鱼形象早已深入人心,是否可以考虑将这一图案推广到日常用品上以扩大天津特色年画的影响?老美华的津派旗袍制作技艺是否可以独立出来,用在其他类型的服装制作中,以使服装的销售者和穿着者都能感受到津派服装技艺的高超?总之,在民间文化遗产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中,一定要有所创新,与时俱进,才能不被时代发展的洪流所湮没。
土著作家利用殖民者的英语记录土著的文化传统及历史,这说明文化载体可以利用新形式达到保留文化因子的目的,民间文化遗产也不例外。目前,天津市就正在尝试利用网络的形式来扩大民间文化遗产的影响。不满足于在地方新闻网站设立专门频道宣传报道当地民间文化遗产,天津市成立了专门的“天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网”,从政策法规、名录项目、传承人、古今天津、实地保护等方面向受众全方位介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历史及发展现状;“非遗讲座”、“专访视频”和“传习展示DIY”以直观动态的形式演示非遗的文化魅力;“项目名录”则以图文的形式详尽介绍了“汉沽飞镲”、“杨柳青年画风筝”等非遗项目,并接受商业演出和订单的预订业务。
三、结 语
民族或地方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是社会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标志,文化遗产的保护记录着社会文明以往的发展历史,它的传承又体现出对于将来社会文化发展前景的规划。不论是澳大利亚的土著文化传统,还是天津市的民间文化遗产,它们的存在使一个国家或一个城市呈现出文化差异性,如何将“文化遗产的示差作用”[13]纳入到国家或城市发展文化多样性的轨道上来,成为决策者和建设者们面临的课题。澳大利亚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历经40余年的努力,终于在全球化和白人文化的语境中做到了穿越文化界限,对土著文化采取包容和尊重的态度;而天津市民间文化遗产的保护则刚刚起步,如何以600年的文化底蕴为基础,充分利用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为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创造有利的氛围,并将民间文化遗产科学产业化成为文化工作者们的首要任务。在保护传承文化遗产方面,只有尊重个体特点,借鉴成功发展形式,追求文化遗产的劳动价值但不把经济利益作为首要目标,才能促进社会的繁荣进步,建成和谐社会,达到费孝通先生期望的境界——“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14]。
参考文献:
[1] 阮西湖.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对土著居民的政策 [J].民族研究,1987(4):32-38.
[2] 阮西湖.澳大利亚土著居民考察记 [J].社会科学战线,1987(4):338-342.
[3] 张丽娟.澳大利亚土著民俗文化精粹简析 [J].语文学刊,2009(9):133-134.
[4] 刘丽君.澳大利亚土著文化及其滞后原因 [J].汕头大学学报,1997,13(6):51-58.
[5] 陈为.澳大利亚土著 [J].民族译丛,1981(6):51-52.
[6] 方红.述说自己的故事:论澳大利亚土著女性传记 [J].当代外国文学,2005(2):101-108.
[7] 黄燕敏.浅谈澳大利亚的文化与艺术 [J].苏州大学学报,2008,28(5):59-60.
[8] 韩小兵.非物质文化遗产权权利性质的探讨 [EB/OL].[2012-12-02]. http://www.bj148.org/fxyj/lltj/msyms/201107/t20110722_153780.html.
[9] 汤自军.基于产权制度安排的我国自然文化遗产开发保护研究:以湘西为例 [D].长沙:湖南农业大学,2010:1-158.
[10] 苑利.非物质文化遗产科学保护的几个问题 [J].江西社会科学,2010(9):20-25.
[11] 张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空间保护 [J].青海社会科学,2007(1):33-41.
[12] 李昕.全球化视域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J].东岳论丛,2010,31(8):126-128.
[13] 李昕.文化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产业发展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7):171-175.
[14] 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 [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3):15-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