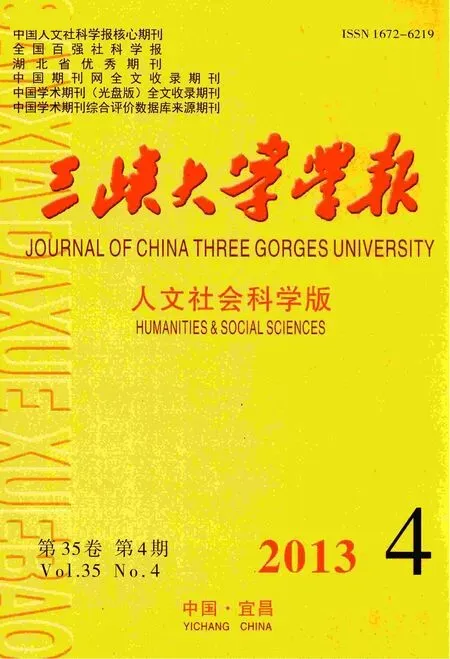论当下戏剧创作中的“半部杰作”现象
2013-04-06闫小杰
闫小杰
(南京大学文学院,江苏南京 210046)
本文所谓的“半部杰作”现象,并非指戏剧作品的未竞之态或前优后劣之状,而是指就戏剧精神而言,某些剧作一方面能够以审美的眼光观照人类世界,从而揭示生活的本质,表现人性的复杂,指出道德的边界,引发人们的思考;另一方面却缺乏对生活进行质疑、批判的勇气,以道德判断和价值判断代替审美判断的现象。与戏剧精神的分裂状态相对应的是情节的大幅跳跃或人物情绪的斗转突变,在美学风格上则多带有悲壮的色彩。这类作品虽然在主题的挖掘方面要高于一般的主旋律戏剧,但它为了宣传某种道德而指出人类道德困境的真实目的,却使其沦为颂歌一族,与主旋律戏剧不谋而合。“半部杰作”悲剧的产生是由作为知识分子的剧作家的自由意志同主流意识相互博弈并最终妥协的结果。
一、戏剧的精神分裂
戏剧是剧作家对于生活的诗意发现,其精神价值在于批判现实、反思人生、发掘人性、叩问灵魂,在于以审美的、超功利的态度去看待人类全部的实践性世界。但当下的戏剧却大多在自己的独立思考中杂合着宏大教条的宣扬,在深层的人文关怀中透露着对某种道德的首肯,价值立场极为模糊,精神状态高度分裂。
吕剧《补天》主要讲述建国之初新疆建设兵团的故事。建国初期,解放军20万大军挺进边疆、屯垦戍边。为了解决兵团战士的婚姻问题,国家以建设边疆的名义征调两万女兵入疆,于是八千女兵怀着对未来的无限憧憬踏上了西去的列车。但迎接她们的不是工厂、学校、文工团和营房,而是恶劣的自然条件和繁重的体力劳动,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她们的婚姻也要服从组织分配的原则,所嫁对象或者身体残疾、或者老丑不堪。这遭到了她们的强烈反对,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就此凸显。这是该剧最为敏锐、最为大胆、也最为耀眼的地方,因为它把人逼到了不得不做出选择的角落,真实地写出了人类的精神搏斗和道德困境。对女兵们来说,顺从就意味着放弃自身的利益,反抗就意味着无视20万兵团战士的利益,如果说前者是不人道的,后者就是人道的吗?事实上,这种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冲突“不是一个政府、一个政党、一种政策或一个个人的偶然行为造成的,而是一个民族在追求自己的生存与发展的过程中无法避免的。全部人类发展史上都充满了这种悲剧性的冲突”[1],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背后就折射出了同样的问题。但该剧在揭示了这种人类发展史上永恒的对峙之后马上转入对女性奉献精神的歌颂,最终肯定了以国家的名义侵犯个人利益的合理性,这是集体利益至上主义的另一种宏大宣传,它使该剧所蕴含的人文关怀性质大打折扣。
话剧《马蹄声碎》是近年来革命军事题材中最好的作品之一。它抛开了革命领袖的传奇经历,也放弃了战争场面的诗意渲染,而是以长征途中五个追赶队伍的女兵的故事为切入点,揭开了长征的神秘面纱,使得信仰与牺牲的话题成为人们反思的对象。长征是人类历史上一次艰苦卓绝的军事行动,我们往往惊叹于它的伟大,却忘记了它的队伍其实是由一个个血肉之躯组成的,它所面临的是无数的生死考验:饥饿、困顿、敌军轰炸、恶劣环境、不断被抛弃的命运。该剧对参加革命的个体牺牲的价值进行了深入的思考:田寡妇原本是抱着争取婚姻自由的信念参加革命的,但却因为革命牺牲了性命,这种牺牲价值何在?为了追赶队伍,女兵们克服了种种困难甚至献出了生命,大部队却为了保障队伍的安全屡次抛弃她们。这些来自历史深处的问询中透露出的是对个体生命的热切关怀。但女兵们不怕困难、艰难跋涉和勇于牺牲的行为本身却又昭示了长征的正义性,肯定了个体牺牲的正当性,从而使该剧成为长征颂歌的另一种表达。
晋剧《傅山进京》也是近年来不可多得的好戏。该剧主要写明末名士傅山拒绝康熙皇帝征召、最终全身而退的故事。在改朝换代之际,身为明朝遗老、读书人领袖的傅山的处境是十分微妙的,他的去留关乎天下名士气节和中原文脉的存亡。康熙的强行征召使傅山踏上了进京之旅,在一次次的较量中,他逐渐明白了康熙纳士兴文的真实动机和求贤若渴的真心,他甚至承认康熙已得统治的“正脉”。康熙的英明最终在傅山心头掀起了狂风巨浪,他在午门的痛苦不是哭明朝,而是哭自己。该剧写尽了封建知识分子的进退维谷的处境,可以说是看到了历史深处的悲哀。但该剧同时又极力美化康熙的圣君形象,最终以轻描淡写的“和而不同”抵消了专制与自由这对永恒的矛盾,从而冲淡了傅山悲剧的力度。
豫剧《苏武牧羊》是一个旧题材,但剧作者却在旧题材中翻出了新意。汉武帝年间,中郎将苏武奉命出使匈奴被扣,因为拒不投降,被单于流放到北海牧羊。剧作者深入挖掘了苏武滞留匈奴19年间所经历的肉体和精神的折磨,尤其是他内心深处的孤独、寂寞与信仰、操守之间的纠结与搏斗。但行文至此,剧作者却将这种人生的悲悯弃而不论,转而歌颂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歌颂苏武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高尚的爱国情操,从而将一个活生生的生命个体推向神坛,进入主旋律戏剧的轨道。京剧《飘扬的红纱巾》虽然写到了个人在没有证人的情况下被组织无辜怀疑的人生困境,但却对此不作深究,反而对青春和牺牲精神大加吹捧。
戏剧的精神分裂昭示的是戏剧批判意识的衰落和作为知识分子的剧作家对主流意识的妥协。在以上所举的剧作中,剧作家对题材的挖掘不可谓不深,对人性的揭露不可谓不透,视角敏锐又透着人文关怀,但最终却走入颂歌的俗套,令人遗憾。真正优秀的作品,是那些能够洞察历史真相、人生悲剧并能够将这种发现直陈于人前的作品。
二、情节或人物情绪的突转
“半部杰作”式的戏剧中往往存在两种声音,一种是剧作家自己发出的声音,一种是主流意识的声音,这两种声音往往是截然相反的,但剧作家却以牺牲情节结构和人物形象的统一性为代价生硬地将其混杂在一起,极大地损害了艺术的完整性。
“半部杰作”式戏剧的情节突转通常靠偶然性事件完成。还以吕剧《补天》为例,该剧围绕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设置了两个关键性的情节。第一个是女兵出逃;第二个是潍坊和小沂蒙的抗婚。当初来乍到的女兵们发现眼前黄沙漫卷、一片荒凉的边疆就是她们今后的栖身之地时,以烟台为首的几个女兵们出逃了。她们为维护个人利益所作的努力显然损害到了国家的利益,于是,剧作者在她们出逃的路上专门设置了一场英雄主义的教育来化解矛盾:四个士兵为了保护盲流母子,以血肉之躯铸成了一道天然的屏障,最终被冻死在雪地里。出逃的女兵们在目睹了这个英雄场景后幡然悔悟,放弃了出逃的打算。潍坊原本喜欢的人是杨连长,但杨连长却忍痛把她让给了为救自己而失去一条腿的战友老羊倌。这当然遭到了潍坊的反对,但在得到对方“终身不娶”的许诺后,潍坊放弃了反抗。得知此事的盲流挺身而出,自愿嫁给老羊倌,终于使这对有情人走在了一起。一向顺从的小沂蒙在看到又老又丑的石骆驼的一刹那,精神趋于崩溃,她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这样的丈夫。盲流只有一个,小沂蒙的难题又该如何解决呢?剧作者再次借用了外力的作用,不仅让边境冲突爆发,而且还让小沂蒙在行军途中负伤掉队遇到石骆驼。石骆驼坚实的臂膀和为救自己即将葬身沙漠的高尚情操,终于缝合了二者由于年龄、长相带来的裂痕,在互诉情衷后被黄沙所吞噬。上述两个情节所引起的矛盾都是依靠纯粹的偶然性事件得到解决的,而“纯粹的偶然事件没有戏剧性,它们只有故事性。它们可以看了动人心魄,可以产生深刻印象,可以起激发作用,可以起摧毁性作用,可以引人入胜,可以获得其他种种效果,可是它们没有特殊戏剧兴趣”[3],因为偶然的事件不能代替生活的逻辑,仅有精巧的结构只能使戏剧的内容流于空虚。
“半部杰作”式戏剧的人物情绪变化通常瞬间完成、缺乏积蓄,致使人物性格发展缺少连贯性,或者苍白无力。《苏武牧羊》中旷野的呼喊和李陵造访的情节写得最有力度,它把苏武身处绝境的惶惑与无助和盘托出,这在以往的同类题材中是从没有过的,这才是一个真正的苏武。整整十年,无边的寂寞和深不见底的黑暗几乎要将他吞噬,是归国的愿望支撑着他顽强地活了下来。他与羊为伴、与狼为邻、与雁为友,风餐露宿、天涯飘零。如果说此时的苏武尚是一个常人,他念国思家的情感也出于自然的话,那么得知家乡变故后的苏武却“性情大变”,走上了神化之路。当他从李陵那里得知自己的兄弟无辜被戮、妻儿不知去向、双亲更是气病交加而死的时候,他气愤了、迷惘了、崩溃了。有那么一刹那,他甚至觉出了自己的可笑:当他苦苦为国守节的时候,国家甚至还根本不知道他的存在,这是何等深刻的悲剧!但接下来呢,他却迅速从这种巨大的悲痛中走了出来,以誓死维护国家尊严、重铸民族精神的决心表示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苏武此时的情绪变化显然有失急躁,家国之悲还在心头激荡,怎么能这么快就做出决定,人物情绪变化的动机是什么?这个疏漏在后来的情节中得到了弥补,苏武在归汉前告诉单于:“汉天子虽然一时委屈了我,可汉朝的父老兄弟和汉朝的山山水水和汉朝的一草一木,都牵挂着我,那里的江河是我的血,那里的山峦是我的骨,那里的泥土是我的肉,还有老祖宗留下的典籍,那是我的魂,汉朝是我的娘,我能舍得了她吗?穷也罢,富也罢,苦也罢,甜也罢,她都是我的家,是我们汉人所有人的家,我要回家,我归汉!”这是全剧的点睛之笔,虽然不长,却内涵丰富。首先,它把国家对个体生命的戕害轻描淡写地说成是“娘委屈了孩子”,很明显宣扬的是国家利益至上的永恒信条;其次,它将汉天子、汉朝、汉人、家等概念杂糅到一起,最终以“汉朝是我的娘”激发起人们的爱国情操,从而模糊了爱国主义的边界。而且这段话明显脱离了人物角色,是赤裸裸的道德宣传。恩格斯说:“我们驳斥一切想把任何道德教条当作永恒的、终极的、从此不变的道德规律强加给我们的企图。”[2]因为永恒的、绝对的道德是不存在的,一切道德归根结底是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化,它必将发生变化。
与《苏武牧羊》的情绪瞬间变化不同,京剧《飘逸的红纱巾》人物的情绪是缺少变化。该剧描写一位留洋归国的女青年献身革命的故事。主人公对革命无限憧憬,在一次战斗中不幸被捕,为了营救自己的战友,她先是违心地答应了表哥的条件,后来伺机逃回队伍。但表哥却在报纸上以她的名义发表了一篇与共产党决裂报道,这让她成了组织上怀疑的对象,因为她无法证明自己的清白。在这种情况下,主人公对自己的处境虽无限伤感,却对自己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毫无怨言,反而主动请缨、舍身报国。该剧中方菲对革命的信念无比坚定,即使在“信而被谤、忠而见疑”的情况下也不改初衷,这显然违背常情。本该大幅度挖掘人物性格的地方反而轻轻放过,其结果是人物形象的极度苍白。
三、美学风格上的悲壮色彩
“半部杰作”式的戏剧中往往会触发生活中一些本质性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但这种冲突通常不是在相互对峙中走向决裂,仅仅是作为和解的前奏加以渲染。这种既揭示尖锐冲突又在最后达成和解的做法通常会使作品带有一种怨而不怒的悲壮风格,这种风格的形成是中国传统戏剧理论中的“大团圆”和西方戏剧理论中“正剧”概念相互杂糅的结果。
在西方戏剧理论中,正剧是处在悲剧和喜剧之间的第三个主要剧种,但这种剧却并不被黑格尔所看重,因为它的“主体性不是按喜剧里那种乖戾方式行事,而是充满着重大关系和坚实性格的严肃性,而同时悲剧中的坚定意志和深刻冲突也削弱和刨平到一个程度”[4]。“半部杰作”式戏剧与黑格尔所说的正剧概念极为相似,其事件“充满着重大关系”;其主人公又有着“坚实的性格”,对自己所信奉的教条基本上能够做到深信不疑(即使先前有所怀疑,也一定会在结尾处走向皈依);其创作态度异常严肃,但它却削平了悲剧的力度,使对立双方走向和解。如《傅山进京》一剧,傅山和康熙的对峙凸显的是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和封建专制之间的尖锐矛盾。作为有自己独立思考能力的知识分子,傅山能洞穿康熙笼络人才的真实动机——渐摧中原士大夫之气节,以添天下读书人之奴性;并能总结明王朝灭亡的深切教训——明亡于奴,非亡于满。这也就意味着,一旦他认可康熙的统治,便是承认了“奴性”统治的合理性,便是走向了自己人格操守的反面。但事实正是这样,他每和康熙接近一步,便被康熙的“圣明”感动一次,他们之间的较量成了展示康熙求贤若渴心情和海纳百川气量的最好平台,这也是该剧的真正用意。傅山全身而退、虽胜犹败的结局虽然包含了许多人生况味,但离喜剧的超脱和悲剧的深刻还很遥远。而《补天》中小沂蒙和石骆驼双双葬身沙海的不幸命运虽然能够引发人们的同情,却不能产生崇高感。因为他们的不幸来自于偶然,不是两种精神实体的对抗。他们的遭遇与其说是悲剧,不如说是苦难、是惨剧。同样的,《飘逸的红纱巾》中虽然以主人公的壮烈牺牲作结,却只能引起人们对美好生命过早逝去的叹息,不能产生悲剧感。因为主人公既缺乏对个体生命的自觉意识,也缺乏向命运抗争的意识。话剧《我在天堂等你》中尽管将军的经历充满了传奇色彩,他的一生也的确值得敬仰,但父子两代人的冲突却表现得单薄而生硬,而且子女们对父亲专制的不满还有可能因为父亲的故事而趋于消散。
“半部杰作”式的戏剧多是大团圆的结局。主人公在历经千难万苦之后终于取得胜利,傅山终于全身而退、小沂蒙最终接受了石骆驼的爱情、方菲以生命为代价证明了自己的清白,无论是生是死,主人公都得到了最好的结局。考察主人公命运出现转机的原因,则大多出自外在的力量,而非主人公自己的自由意志。这种外力或以终极道德的面目出现,或以宏大教条的方式出现,主人公要么是宏大教条控制下的工具,诸如苏武之类;要么是某种终极道德的忠实信徒,如《飘逸的红纱巾》中的方菲,缺乏和人类实践世界对抗的意志。于是大团圆的结局是必然的。一方面这样的结局符合传统的审美习惯,容易走向市场;另一方面怨而不怒、能够起到教化的目的,符合主旋律戏剧的要求,但戏剧真正的悲剧精神被消解了!真正的好戏是像《曹操与杨修》那样能够洞察权力的阴暗面的作品,当曹操和杨修各自指天画地表明自己不改初衷却最终势不两立的时候,我们体会到了真正的伟大与渺小!真正的好戏是像《成败萧何》那样能够对人生表示无限悲悯的戏剧,当萧何对着韩信的背影进行良心的跪拜时,我们真正体会到了古人生命中的不可承受之轻!
综上所述,当下戏剧创作中“半部杰作”式作品的审美特征主要表现为戏剧的精神分裂、情节或人物情绪的突变和美学风格上的悲壮色彩。这些作品能够深刻地揭示人类的生存困境,指出道德的边界,却不能将这种质疑生活的勇气贯穿到底,其背后折射的是戏剧人文精神的失落和知识分子价值立场的迷失。面对各类层出不穷的评奖机制、审查制度和汹涌而来的商业大潮,知识分子要想发出自己的真实声音,有时不得不牺牲自己的独立思考和创作个性,表现出对主流意识形态某种程度的迎合。正是这种迎合造成了当下戏剧创作中“半部杰作”的现象,使得它们与经典擦肩而过,成为艺术成就较高的“传声筒”,这是最为令人痛心的事情。当下戏剧创作要实现这种突围,就必须建立开放、宽松的文化氛围,使得知识分子能够尽情地彰显个性、抒发怀抱、追求生活的诗意!
[1]吕效平.人类发展史上的悲剧性冲突——论吕剧《补天》[J].上海戏剧,2005(2).
[2]恩格斯.反杜林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0:91.
[3]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欧美古典作家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一)[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317.
[4]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册)[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2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