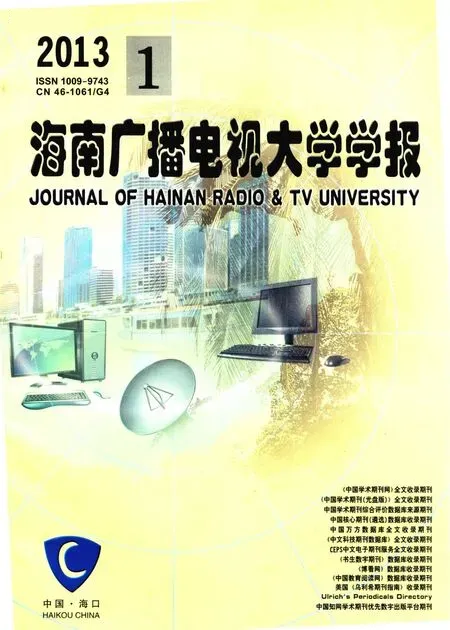浅析红色高棉失败的原因——基于革命党与执政党区分的关系维度
2013-04-06郑鹏
郑 鹏
(海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海南海口570228)
红色高棉亦称“柬共”,一个曾经执政的共产党,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获得了柬埔寨广大农民拥护与支持,最后占领金边取得了政权。然而,取得政权后,没有很好地实现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在一些层面上甚至比原先充当革命党角色时更“极端”,最终导致拥有强大武装的组织在夺取金边并执政仅仅3年8个月20天便失去政权,犹如昙花一现,短短时间内迅速土崩瓦解。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件特别事件,“柬共”失败原因,尤其是从革命党与执政党区分关系维度出发审视,更值得探究。革命党与执政党到底有什么区别?这是我们从革命党与执政党区分关系维度出发审视红色高棉失败原因的逻辑起点。《人民日报社》理论部主任张书林曾在《理论探讨》2006年第5期撰文《区别革命党与执政党的四个维度》,指出区别革命党与执政党的四个维度是:“党政关系的维度、党法关系的维度、党群关系的维度和党内关系的维度”[1]。这种区分角度,为我们分析红色高棉失败原因提供了很好视角。
一 党政关系上没有实现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
马克思主义政党观认为:“政党是以夺取和巩固政权为目的的政治组织,革命党一旦获得革命成功,取得国家政权,就由革命党变为执政党”。执政党所要做的就是通过各种途径来维护和巩固新政权。从逻辑上讲,“执政党要想长期执政,必须善于和有能力维护自己的政权,保持执政的长久合法性。”[1]红色高棉执政后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现象十分普遍,依据以往斗争经验和领导者个人主观意愿施行“恐怖主义”的“恐怖执政”政策更是极为荒唐,其党政不分的“恐怖执政”表现在:
(一)政治上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实行激进的共产主义政策
红色高棉追求建设“纯洁的社会主义”,彻底消灭阶级和城市。红色高棉士兵入城第二天,金边居民接到了紧急疏散命令。红色高棉声称美国飞机会来轰炸金边,金边居民必须全部撤往农村。转眼间,素有“东方巴黎”之称,拥有近200万人口的金边城,变成了一座死寂的“鬼城”。全国所有城市居民几乎全部被迁出。对此,红色高棉还对外宣布“在柬埔寨,城市被消灭了。”在他们的观念中,城市是阶级罪恶的根源,只要消灭了城市,就消灭了阶级不平等,消灭了阶级罪恶。这种观念恰恰同马克思主义有关社会生产力发展观点相违背。
(二)经济上彻底消灭私有制,建设“农业乌托邦社会”
红色高棉无视柬埔寨国内经济基础,要超越土地革命、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等过渡阶段,直接进入共产主义。提出要在10-15年内实现现代化;另一方面,柬埔寨在城市居民被迁往农村之后变成了一个“彻底的单纯农业社会”。红色高棉推广丛林斗争时期实行的合作社制度,取消货币和市场,禁止市场交易,连简单的物物交易也被视为违法。通过施行带有“军事共产主义”色彩的全民供给制,想要建设“没有穷人和商人,没有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社会。但是这种过激政策,最终造成了生产力倒退和劳动者生产积极性下降,即使施行了几次“反对吃闲饭运动”,也改变不了粮食产量下降和粮荒出现的现实。
(三)文化上实行愚民政策,取缔一切传统文化
红色高棉认为“知识越多,头脑就越复杂,坏主意也越多,要进行改造;改造不好的,就要消灭,简单到消灭肉体。”当红色高棉执政失败时,原有的几百名从西方留学回国的知识分子,只剩下15人。红色高棉取缔了包括歌舞戏剧在内的一切传统文化,并严禁西方文化传播。红色高棉宣布禁止印发书籍和各种印刷品,导致国内没有一份出版物。
(四)民族宗教上主张纯洁柬埔寨结构,敌视和迫害其他族裔
红色高棉认为柬埔寨是单一民族国家,因此敌视和迫害生活在柬埔寨的其他族裔。据统计,在其执政期间,“43万华裔有21万人非正常死亡;2万越南裔几乎全部非正常死亡;1万老挝裔有3400人非正常死亡;2万泰裔有3800人非正常死亡”[3]。
(五)外交上推行封闭隔绝外交政策,仇视外国人
红色高棉占领金边后,第一时间便将滞留在金边的所有外国人遣送出境,从此断绝除红色高棉高层之外所有组织和个人与外国的一切联系。
二 党法关系上没有实现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
党法关系是指党与国家宪法、法律关系,党与国家法统的关系。党法关系实质是党能否得到现行法统的支持和拥护,能否融入国家宪法、法律体系之中。红色高棉执政后,没有新的法律体系和以宪法为基础的一整套法律制度。虽然在1976年1月颁布新宪法,国名更改为“民主柬埔寨共和国”,但是宪法形同虚设。刚取得胜利,红色高棉就对原朗诺政府军政人员展开了残酷政治清算。甚至还包括参与过朗诺政府的一些王室成员,而这些王室成员大多只是名义上属于民族联合政府。对这些人员也没有按照法律程序,直接棍棒殴打致死,或直接枪决。在建设“纯洁的社会主义”时,对原来的“剥削阶级”进行残酷屠杀,例如有的人因为在房前私自种了一些蔬菜而被处死,甚至有的人被处死是因为他身体瘦弱、劳作能力弱。在金边南部建立S—21集中营,专门用来杀害红色高棉内部人员。在4年不到时间里,就有2万人被杀害。在处决犯人时,为节约子弹,一般不采取枪杀手段,而是镰刀、锄头、木棒,甚至活埋。在执政过程中“轻法治、重人治”,甚至根本没有法治。恐怖专政成为了惯性,红色高棉的“组织绝对正确”论和波尔布特在党内的绝对权威,使波尔布特被吹捧为“党心”。旧法统被推翻,新法统不成立,施行的是洛克在《政府论》中大声疾呼的“暴政”。
三 党群关系上没有实现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
党群关系是指党与群众关系。党群关系是关系党发展壮大的根本问题,更是决定执政合法、合理、长治久安的根本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革命党胜利夺取政权以后,群众主体将在原来基础上进一步扩大。“理论上讲,革命党和执政党都应当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但事实上,革命党脱离群众的危险程度比较低,而执政党脱离群众的危险程度却是比较高的。”[1]群众都有自己的利益要求,这更要求“执政党必须以利益分析方法为理论指导,把所有守法的人都视为合法公民,把所有违法的人都视为打击对象,保护人民的合法利益;并通过利益协调和缓和利益冲突来保证社会稳定。”[1]
红色高棉成为执政党后,仍用革命党分析群众的典型阶级分析法,根据人们对生产资料不同占有关系,来确定人的不同政治态度和立场。没有认识到成为执政党以后巩固政权和发展经济,领导群众进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性。取得政权后,红色高棉并没有扩大自己的群众基础,反而将原来的城市居民、知识分子、僧侣、技术工人、商人归作“新人”统统视为阶级敌人,下放农村在“旧人(攻占金边前的红色高棉占领区的居民,主要是农民)”监督和管制下,从事超强度的农业劳动,进行改造。很多“新人”因劳累、饥饿、营养不良和疾病非正常死亡,同时“新人”还会遭到任意残杀与迫害。认为知识分子“知识越多,头脑就越复杂,坏主意也越多,就要进行改造;改造不好的,就要消灭,简单到消灭肉体。”让宗教信徒改变自己的信仰和生活习惯,逼迫穆斯林去吃猪肉,对有所反抗的人一律屠杀。在“消灭城市”、“疏散”迁移居民过程中,红色高棉士兵对不服从命令的人和各类异己分子进行有计划的屠杀。甚至连西哈努克亲王也被迫退休和遭软禁,十几个子女也被作为“新人”下放到农村进行改造,不知所终。
四 党内关系上没有实现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
党内关系是指党的各个构成要素之间相互作用关系,包括党的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党员个人与组织的关系,也包括由这些关系衍生出来的党内领导方式、建设方式、活动方式等所涉及到的次一级层面关系。红色高棉执政时期党内关系主要表现在:
(一)中央与地方关系上 坚持“中央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监控地方”。1976年波尔布特提出一个“四年计划”,指示要在全国各地迅速实现粮食产量翻三番,以筹集足够资金支持工业化。各地方明知这一计划与当时实际严重脱节,但各地官员慑于党中央“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监控力”,纷纷谎报数据,仅有的粮食产量被中央超量抽走。在红色高棉内部清洗中,1978年中央认定东部大区的干部和军人亲越南,东部大区的干部和军人便因此遭到最为血腥的清洗。在6个月时间里,一次性处决近10万名红色高棉内部干部和军人,约占当时柬埔寨人口的1/70。
(二)上级与下级关系上 盛行以波尔布特为中心的个人崇拜。波尔布特被尊奉为“党心”,在红色高棉内部确立起不可动摇的最高地位,掌控一切最高决策权。这种高度集中的上下级权力决策体系,最终造成波尔布特专制与独裁。1976年底,波尔布特借“党的躯体已经生病了”,在组织内部进行大规模清洗,内部清洗逐渐成为红色高棉内部生活一部分。
(三)个人与组织关系上 主张“组织绝对正确”论。1977年9月27日,波尔布特在讲话中声称全国总人口中2%是“反革命分子”。红色高棉在金边南部一所高中建立代号为S—21的审讯中心,专门用来审讯、拷打和处决红色高棉内部人员。在这所魔窟关押的2万多人,最终只有6人幸存下来。因此法国学者拉古特把红色高棉组织内部人员清洗称为“自我灭绝的屠杀”。
总之,红色高棉占领金边前,能够践行革命党为人民谋利益的原则,获得了广大农村地区人民的拥护与支持,走出了丛林,取得了政权。但在占领金边取得政权后,红色高棉却没有很好地实现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继续以革命思维和角度审视政权问题,当革命思维在获取最高权力之后不被约束时,结果只能是更加极端,而当暴力由夺取政权的途径变成消灭异己的工具时,便导致了自身迅速灭亡。
[1]张书林.区别革命党与执政党的四个维度[J].理论探索,2006(5).
[2]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瞿菊农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3]徐然.波尔布特及红色高棉的历史悲剧[J].记者观察,2000(3).
[4]岳红雨.红色高棉失败的原因[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2).